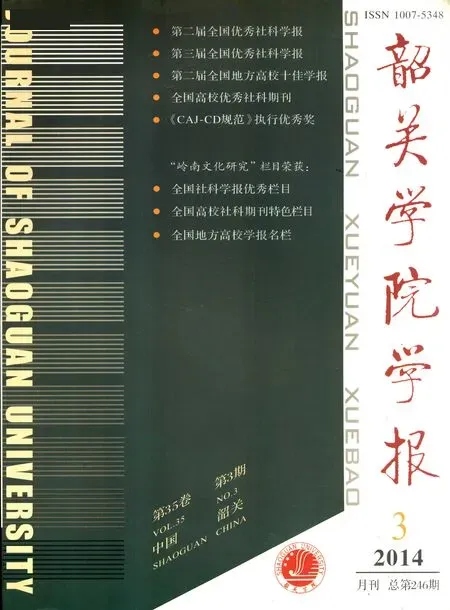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隙论
李晓琼
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隙论
李晓琼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法律道德主义者把“法律强制执行道德”视为“法律对不义行为的镇压”,认为法律强制本身具有正当性。而自由主义者认为法律与道德有明显的界限,法律不得对任何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进行干涉,力图捍卫私人的道德自由。然而,法律道德主义的论断从理论预设到论证过程都不够周全并且可能掉入“道德民粹主义”的漩涡;而后者未将不道德行为进行区分而一味否定强制,则有鼓吹“道德冷漠”之嫌。事实上,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者之间存有间隙。
间隙;法律强制;道德冷漠;第三路径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也曾发生过有关道德的法律强制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法理学论题”[1]。战后西方学界对此论题的青睐缘起于英国的《同性恋和卖淫调查委员会报告》,即“沃尔芬登委员会报告”。报告阐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原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是刑法的功用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秩序与合宜,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外来的侵害或者伤害,并为避免其他人的盘剥或腐蚀提供充分的保护;二是“我们必须保留一部分私人生活的领域给道德或者非道德,对这些领域之调整并非法律的职责之所在”[2]2-3。以此为批驳的靶标,德夫林提出社会为了维系其存在可以也应当对道德原则进行强制,否则便会崩溃。他还将不道德行为与叛国行为相比附,“压制不义和镇压颠覆活动一样,都是法律职责之所在”[2]13-15。而回溯至维多利亚时代,法官斯蒂芬所持的“法律道德主义”观点就更为极端了,他主张法律对道德进行强制执行本身的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法律应当是“对大量形式的不义的行为的镇压”[3]162。然而,法律强制执行道德是否具有正当性?而否定法律强制的理论是否必然导向道德冷漠?在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是否有间隙的存在?对于不道德行为的规制是否还有除此两者之外的第三路径?我们将以哈特的《法律、自由与道德》为分析模板,以此为出发点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一解答。
一、对“法律道德主义”的回应
从法律道德主义论者对其理论进行论证的实证根据角度看,可将“法律道德主义”论断区分为以德夫林理论为代表的“温和论”和以斯蒂芬的理论为代表的“极端论”。
(一)对德夫林“温和论”的回应
“根据温和论的观点,一种共享的道德是社会得以立基的坚实依据;如果没有它,我们就只有一个个个体的集合而不会有社会。”[4]48德夫林的理论立基于一个由性道德与其他道德组成的“无接缝之网”的预设之上,那些脱离其中的人就是对社会的敌视,可能或者注定会导致社会的崩溃,因而应当通过法律进行规制。
对于这一“崩溃命题”,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其立论的基础不能得到经验的证实,也不具有逻辑上的可能性。德夫林认为社会道德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为我们维系社会所必须。这在哈特看来是一种误导。而在哈特看来,正是因为人类保有这些道德才使得社会之维存具有价值。而就德夫林所称之“共享的道德”,哈特认为只是不容忍、憎恨和义愤的结合,其至都可称之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倾向”或者“惯习”而非道德。诚然,“道德”、“伦理”之类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含糊性和开放性。对于一些我们认为是道德的东西,可能别人并不这么认为。那么,“共享的不容偏离的道德”如何确定?对此,哈特的支持者科恩教授通过举例“假如在美国特别是南部各州询问‘黑人和白人是否应该平等?’很可能大部分人会厌恶而坚定不移地说‘不!’于是就断言的这些人的反应即是美国社会的社会道德”[5],进一步批驳了德夫林确认社会共享道德方式的局限性与随意性。
退一步讲,即使一种共享的道德真的存在,也没有理由能够让我们相信任何道德的偏离都会导致社会的崩溃。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表明对为公众接受的性道德的背离,即使在成年人的私人生活之中,也是某种像叛国罪一样会为危及社会之存在的危险”[4]50。哈特将不道德行为区分为“公共场合行为不检”和“私隐的不道德”。毫无疑问,在背离隐私性道德的人并不会给他人带来损害,更不可能导致社会崩溃。哈特进一步指出这一“崩溃命题”可以转换为更为荒谬的命题——将社会道德的改变等同于对社会的摧毁,将道德的变化视为社会的更替。
再退一步讲,是否一个社会想要自保其身便可以不理会其所采用的手段(或称方式)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宜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哈特论道,一个社会若致力于迫害少数者或者其维存的手段中包含酷刑,此社会才是如德夫林所称之“崩溃”[4]21。哪怕道德的偏离会导致社会的崩溃,我们依旧无法回避“法律强制执行道德本身能否获得道德上的正当性”的问题。而事实上并没有经验证据支撑这样的理论——为了维存社会,通过法律惩罚强制执行道德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合宜性。德夫林企图以道德上的罪恶程度通常为大多数法官在量刑时所考虑作为其法律强制理论的经验事实。而在哈特看来,这是法官将其自身当作“道德看管人”观念的复兴,本身就不具有合理性。此外,德夫林以禁止自杀、反对安乐死等为例论证法律强制的基础既不是“对他人造成伤害”,也不能以“受害者同意”来辩护,进而宣称刑法的功能仅仅是对道德原则的强制执行[2]9。而哈特尖锐地指出,这是例子的滥用,这些行为与违反性道德的行为不具有可比性,而对其的强制并不是强制执行道德,而只是“法律家长主义”的体现。
(二)对斯蒂芬“极端论”的回应
与德夫林不同,另一位“法律道德主义”者——斯蒂芬则走向了极端,他把“法律强制执行道德”本身看做是一种道德,因此哪怕不道德行为没有直接对任何人造成伤害,法律也应当对道德强制执行。斯蒂芬认为这种论断就是其反驳密尔的武器,并且是法律强制理论的正当理由。
然而,在哈特看来,斯蒂芬“极端论”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坚持认为对罪犯仇恨和怨恨是正当的且“健康”的[3]162。若要为其“法律强制理论”寻找一个正当性理由,那便只能是“报复论”了。然而,报复“毫无疑问有赖于存在犯罪者的同时也存在着受害者”[2]9,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惩罚的强制执行才能对犯罪者施以与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所对等的报复。然而,违反私隐性道德的行为并没有受害者,将对其惩罚仅仅建基于由不道德行为所招致的报应观念无疑是站不住脚的。这种理论可能被理解为“法律对道德强制执行之所有价值,在于其可以保护一种现存之道德”[4]65。但是正如哈特所质疑的,这种理论是否真的不证自明而无需诉诸批判性道德而被毫无争论地接受,抑或只是苍白无力的宣告?
与德夫林一样,斯蒂芬也预设了社会能够以其所具有的公共道德而被标识出来并且对道德法典的侵犯可能会给其带来极大的麻烦。而其所谓的“公共道德”定义为“在道德上的压倒性大多数”。如同德夫林的“共享的道德”一样,斯蒂芬的这种“公共道德”首先受到“存在与否”及“如何确定”的拷问。哈特以退为进,假设在性道德方面确实存在“压倒性大多数”的道德法典,甚至侵犯道德法典的行为真的给社会带来麻烦。但即便如此,依旧没有经验事实可以证实对道德现状的维存具有理所当然的自足价值,更无法表明法律可以对任何道德进行强制,哪怕其强制执行会给当事人带来痛苦,因为并非所有的不道德行为都为民众所反感。
此外,对于将“公共道德”简单定义为“压倒性大多数”的论断,哈特则流露出对将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与违反道德相等同以及在此情况下道德大多数者迫害少数者的道德民粹主义的担忧。这种民粹主义认为多数者有权决定所有人如何生活并且不受任何限制[4]76。哈特指出,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大多数者利用权力对少数者进行压迫,而在于这种压迫会随着民主理念的传播而被毫无疑义地接受。
二、对“自由主义”的修正
哈特沿着自由主义的进路,以密尔的信条——“在文明世界中,强力能够正当地适用于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的任何成员的唯一目的,就是防止对他人造成伤害”[6]16为基础对“法律道德主义”进行反驳。然而哈特亦明确指出其并不为密尔的观点辩护,因为他认为除了阻止伤害之外还有其他理由足以使道德的法律强制正当化。他认为“一种对它们适当的修正是必要的”。
(一)修正:为“法律家长主义”正名
密尔以“伤害原则”为自由的唯一界限,并且其所称之自由并不包括放弃自由之自由以及伤害自身之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看似已经解释了法律禁止“安乐死”、“自杀”等行为的正当性,但是其反对法律家长主义的主张却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他甚至批评法律对贩毒行为的限制对于潜在的购买者自由的侵犯甚于对于贩毒者的自由的侵犯。对此,哈特认为,密尔的考量“过多的关注了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的心理状态,这些人的愿望比较稳定而不受外界干扰;他知道什么是他所需要的,什么能给他满足和幸福;并且一旦允许就坚决地追求”[4]35。而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理性人”并不常见;反之,更多的人在自由选择中不知所措或者在某种压力之下做出妥协的选择。将保护人们免于其自身伤害的立法解释为“法律家长主义”的体现比“个人的自由选择”更易于被接受。因此,在讨论当前的刑法规制时,应当对传统的“自由主义”进行修正,为法律家长主义正名。
(二)恪守:以反对“法律道德主义”为立基
“这些修正后的原则必须不能放弃对利用法律仅仅去执行实在的道德之行为的反对。”[4]35作为新分析主义法学的旗手,哈特始终站在实证主义的立场反对“法律道德主义”。他提醒人们注意“家长主义”与“法律道德主义”的应然分野,作为对“自由主义”修正的“法律家长主义”关注的是行为所带来的“痛苦”而不是该行为是不道德的。我们认可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法律可以像家长一样为了防止某一行为所带来的伤害而进行强制禁止,比如对自杀、对虐待动物等行为的干预。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赞成可以利用法律对任何形式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规制或惩罚。对于诸如性道德上的“脱轨”行为等并未带来伤害或者痛苦的行为,我们认为应当保留一定的自由选择的可能,这种道德的判断不应成为法律强制的理由。
三、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隙
如上所述,哈特的道德规范对法律强制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驳,那么是否意味着,哈特如传统的实证主义者一样,宣称法律与道德的绝对分野,走向道德冷漠的一端呢?答案是否定的。哈特并没有全盘否定法律对道德的适当介入,他只是以修正后的“伤害原则”为标准将法律可介入之道德范围进行界定,并强调法律所不可触及的领域绝非道德冷漠的地盘,在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存在有间隙。
(一)“间隙”的范围:“私隐性道德”
如前述,道德区分为“公共性道德”和“私隐性道德”。对于违反“隐私性道德”,如成年人私下自愿的同性恋行为或者私密的卖淫行为、姘居行为等不应当为法律所调整;只有那些给他人带来痛苦或者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与合宜的行为才能通过法律进行强制。换言之,“私隐性的道德”的自由空间便是法律所无权介入的。但是,哈特绝非倡导对此类道德怀着漠然的态度。通过法律惩罚来禁止民众实施伤害他人或者自伤与要求他们不做那些违反道德却无害于他人的行为,这是两回事。换言之,即便法律不制裁后者,也不代表社会对其置之不理,放任不道德行为的蔓延。哈特将这种对强制与漠视视为非此即彼的论断,称为“对道德的误解”[4]73。显然,这不为法律强制所管辖的“私隐性道德”便是“间隙”之所在,其可以通过为强制与漠视之外的第三种路径来实现。
(二)路径之选择:自愿而非屈服
道德规范的法律强制是一种蓄意的强制,以威慑为后盾;而道德冷漠是一种道德保守主义。毋庸置疑,漠视是不可取的。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有着非常显著的相似性,对它们的遵守被认为是值得褒扬的事[7]。不管对于性道德还是其他私隐性道德,其偏离行为毫无疑问是对社会善良风俗的损害。同样的,法律强制路径也是不可取。对于社会良善生活的维持,“此处可贵的是自愿的自我约束,而非对强制的屈服,这种屈服看来是相当缺乏道德价值”[4]58。企图通过法律强制推行道德教化的主张如同企图对一种不道德施以另一种不道德的惩罚来达到道德之善一样荒谬。
在禁欲与纵情中间,绝非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如同密尔所宣称的“在关涉善与恶之审慎明辨上,人类彼此之间应当有着相互扶助之觉悟,应当相互鼓励和支持去趋利避害”[6]5-18,在道德的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我们应当选择第三种路径。诸如讨论、建议、主张,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的“告诫”等,这一路径较之前两者,是维护“私隐性道德”的更为理性也是理想的选择。
四、结语
哈特的上述经典论断在跨越了半个世纪后依旧作用于当今社会,为法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风向标。近年来,备受争议的“黄碟案”、“换偶案”、“倡导纳见义勇为入法”等事件,接二连三地激发了我们对于“法律与道德”这一经典关系的思考。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在于他律,道德要求自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推行法律对道德的强制执行,除非这种不道德行为同时违反了现行的法律。当然,我们并不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但是假如我们将“不支持”推向“取缔”,这如果不是心胸狭窄的“道德民粹主义”便是“苛以酷刑的残暴行径”。因此,我们何不向哈特取经,对不道德行为进行区分,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也捍卫私人间的自由。当然,我们并不为私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辩护,我们所主张的是,对这种不道德行为的规制在于自我约束,在于道德教化,在于规劝而非法律强制。“我们的历史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将一事务纳入刑法定位成犯罪并加以处罚相当容易,而欲撤销之却难乎其难”[4]2。因此,法律强制与道德冷漠之间的间隙既是存在的也是合理的。
[1]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53.
[2]Devlin.Patrick:“The Enforcement of Moral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詹姆斯·斯蒂芬.自由、平等、博爱[M].冯克利,杨日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M].支振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科恩.当代英美法理学和法哲学[J].法学资料,1982(3):49-50.
[6]约翰·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译.北京:商务印书局,1996.
[7]哈特.法律的概念[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63.
The Space between the Law Coercion and Moral Indifference
LI Xiao-qiong
(School of Law,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Guangzhou 510320,Guangdong,China)
Legal moralist argues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moral is of legitimacy,as the persecution against vice.But the liberalist considers that the law shall not interfere.Individual behavior which is not harmful to any others.However,these two points of view are necessarily imprecise.The view of legal moralist is linked to moral populism and the view of liberalist seems to preach the moral indifference.Actually,there is a space between the law coercion and moral indifference.
space;law coercion;moral indifference;the third path
D90
A
1007-5348(2014)03-0104-04
(责任编辑:曾耳)
2014-01-12
李晓琼(1989-),女,广东潮州人,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法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