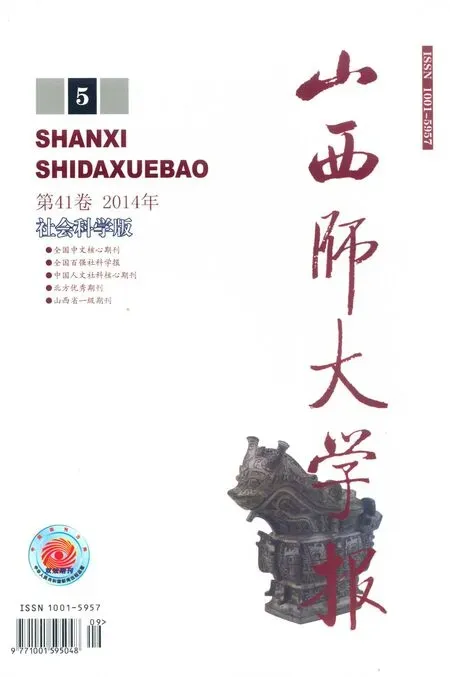唯物史观的诞生历程微探
——基于马克思文本的一种解读
刘文艺
(暨南大学社科部,广州510632)
唯物史观,马克思称之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32。关于这一“结果”,马克思知道,它将遭受反对势力的仇视和诋毁,不过,他更知道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任何的“犹豫”和“怯懦”都无济于事。正是基于对这一“总的结果”——唯物史观——的执着,马克思找到了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科学入口”。不过,唯物史观的发现并非像雅典娜从宙斯沉思的头脑中蹦出来那样轻而易举,它是马克思走近历史、揭秘历史、重释历史的历程的结晶。从文本出发来呈现这一历程,对于我们更切近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遭遇物质利益的难事——走近历史
现实总是向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难题,而对难题解决途径的寻求,又会把人们导向新的领域。《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遇到了“物质利益的难事”,对“难事”的思考,让马克思获得“走近历史”的契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简称《辩论》)是马克思首次公开为经济上窘迫、政治以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穷群众进行辩护的一篇文章。与纯粹的哲学思辨不同,这篇文章“演的是现实生活的戏”[2]135,是基于“理性的法”与“私人利益”的紧张对立,来披露下层贫困群众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的“戏”。
从《辩论》全文看,贯穿其中的原则是“理性的法”。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应“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2]139。如此一来,具有立法权的省议会唯有按照“法的本质”制定法律,才能保证法律的合理与合法。事实上如何呢?省议会不惜“把某种物质对象和屈从于它的某种意识加以不道德、不合理和冷酷无情地抽象”[2]180,根本无视“法的本质”。马克思为此深感困惑。
经过对《辩论》中的事实的分析,马克思很快发现了在“法的背后大耍花招”[2]163的幽灵——物质利益,并揭示了这个“幽灵”的“特征”:它最讲究实际,“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自己”[2]163,把自己看作世界的最终目的;它最为狡诈,知道如何去污蔑法,说“如果法不实现这个最终目的,那末它就是和目的相矛盾的法,对私人利益有害的法,因而也就是具有有害后果的法”[2]165,从而,把法的注意力引向外在的物质领域;它最为卑鄙,紧紧抓住具有狭隘且易于被利益驱使的“立法者”的自私心理,诱使他们撇开法的本质,为私利服务。面对物质利益所具有的强力及其僭越法的本质的现实,马克思有点不知所措。基于物质利益对理性的“亵渎”,马克思只好愤恨地称之为“下流的唯物主义”[2]180、“违反人民和人类神圣精神的罪恶”[2]180。
在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再次遇到这个让它“头痛”的难事。本应该和倡导理性自由的新闻界一起去寻找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根源的政府,却反过来斥责如实报道农民贫困状况的新闻记者;本应该对农民悲惨生活的事实负责任的政府,却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任由他们陷入破产和贫困。面对这些,马克思在为备受委屈的新闻记者申辩的同时,也认识到“不能想象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政府无关,正如不能认为摩塞尔河沿岸地区位于国境之外一样”[2]217。
可政府为什么对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人民贫困状况如此冷漠呢?在理性的法与物质利益的对峙中,马克思痛苦地发现,其实客观的物质关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发现“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2]216。显然,这里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无疑,这个发现对马克思的理性立场以极大冲击,为马克思动摇进而与之决裂埋下了伏笔,如格姆科夫所言,正是“为人民群众利益进行辩护的活动使他逐步打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3]。
事实上,之后不久,马克思就开始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简称《批判》)一文了,这标志着他与把一般国家或法绝对化并视为理性有机体观点的决裂。
在写《批判》之前,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如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哈密尔顿的《北美洲》、马基雅维利的《论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4],形成《克罗茨纳赫笔记》。这为他集中批判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材料。
依据对历史文献的研究,马克思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坚信不疑的在任何地方都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当作谓语,断言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竟然是个伪命题。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2]251,“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2]252,政治国家“是私有财产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2]369。质言之,物质性的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基础和隐秘发源地。
这个发现极为重要,它为马克思亲近历史进而揭秘历史奠定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对此,恩格斯后来这样回忆:“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述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到被黑格尔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5]如何寻找呢?除了解剖市民社会,别无它途。于是,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32
二、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揭秘历史
以往的历史学家都希望在纷乱的“历史事实”或“事实群”中去归纳历史演变的抽象轨迹,马克思则是通过对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色诺芬、李嘉图、穆勒、舒尔茨、李斯特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来深入历史之幽,进而揭示“历史之谜”的。
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机缘是多重的。首先,使马克思深深陷入苦恼的“物质利益的难事”是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层动因。其次,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是马克思走向此路的间接机缘。《法哲学原理》被人誉为斯密《国富论》的哲学式表达,马克思对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应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受到某种间接的驱动。最后,恩格斯对英国状况的卓越描述及其赫斯、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著述,直接为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开辟了道路。总之,1844年,住在巴黎近郊的马克思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书籍的海洋”,废寝忘食地专研政治经济学著作,并写下若干册手稿,因这些手稿写于“巴黎时期”,被后人统称为《巴黎手稿》。通过对《巴黎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和《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的考察可发现,此时期的马克思已由之前所坚持但有所保留的理性立场,转向解剖政治经济学的人本学异化史观,并利用后者历史性地阐释了私有财产的起源、私有财产的非人关系以及私有财产的扬弃路径。《手稿》和《穆勒评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揭秘历史”的关键性文献。
在论述马克思如何“揭秘历史”之前,我们不得不先交代一下他用以“揭秘历史”的利器——人本学异化史观。人本学异化观并非马克思首创,严格地说,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异化和复归的批判逻辑的继承。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实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6]4不过,马克思绝不是非批判地接受费氏这一理论的,他一改“异化”的抽象逻辑结构,把其置放到经济现实的场景即劳动与交往之中,并赋予其“生产性否定”和“交往性否定”的崭新内涵。马克思就是利用这种被他锻造过的人本学异化史观,去祛蔽资产阶级国民经济的。
马克思认为,要想揭露国民经济学暗藏的漠视下层无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就得澄明被国民经济学家当作必然前提的私有财产的“出身”。这如同阿尔都塞所言:“当他(马克思,笔者注)认识这一事实时,他表示这一事实毫无根据,至少在他所谈论的经济学家中,这一事实是没有根据和缺少其自己的原则的。”[7]所以,马克思在《手稿》中强调:“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6]50实际上这个被国民经济学家当作不言而喻前提的“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6]61。就是说,从根本的意义上,私有财产是人的外化劳动即异化劳动的必然后果。当然,这个结论是以马克思对工人异化劳动的三重解析为依据的。
既然劳动产品、劳动本身、“类”作为异己的统治力量与劳动者相对立,那么,它们必然“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6]59,这个存在物是谁呢?马克思说,他“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6]60。众所周知,在马克思的视域中,这个“统治人的异己力量”的化身即为资产阶级。所以,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分析,有力地揭示了为资产者所占有,并认为是理所当然占有的私有财产的隐秘“出生地”。
澄清私有财产的起源之后,马克思解剖市民社会的视界开始由主体性的“劳动异化”转向主体间性的“交往异化”,以进一步探视私有财产的本质。
关于“交往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作为工人、作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对作为工人的人,他的人的特征只有在这些特性对异己的资本来说是存在的时候才存在。”[6]65通过这个概述可以发现,与经济学家只是从商品交换的经济学视角,把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单纯看作一个冰冷的经济事实不同,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作为经济学事实的资本与劳动,而且发现了两者之间所固有的对抗——强制与被强制、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马克思非常看重这个对立,说“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6]78
毋庸讳言,《手稿》所揭示的“交往异化”主要局限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还没有深入到市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当然,马克思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随后所写的《穆勒评注》无疑是对这一缺憾的弥补。在这里,他深刻而详细地论述了本来意义上的交往、交往异化及其交往异化的实质等问题。他说:“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6]170自不待言,“类活动”、“类精神”、“社会的活动”、“社会的享受”等,本来该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及其这种联系下人与人之间的双向肯定和承认。可在现代私有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即交往却以普遍异化的形式出现,“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相反,他同别人的分离表现为他的真正的存在”[6]171。那么,这种与“人”的关系相异化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具体考察了私有财产的几个重要的外化存在形式,诸如货币、银行、信贷、交换、分工等。结果发现,以私有财产的外化形式为中介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是社会的、人的运动,不是人的关系,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6]166,即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进而依据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透露出交往异化的实质——人与人之间基于物的对抗关系。马克思认为,我占有了“物”或“私有财产”,我就获得一种对他人而言的社会权力即支配权力,相反亦是如此。因而,“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社会的权力越大,越多样化,人就变得越利己,越没有社会性,越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6]175。所以,就《手稿》只从私有财产中的劳资对抗来考察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交往异化而言,《穆勒评注》则深入地探讨了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全面的交往异化。这些与异化劳动一起构成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整体。
遗憾的是,此时期的马克思没有去深入挖掘“异化劳动”和“异化交往”之间的矛盾关系,当然也不可能做到对市民社会内在历史驱动力的本真揭示。而是按照人本学历史观的批判逻辑祛魅异化,寻求本真人性的复归。大体上说,马克思从异化的“否定辩证法”中得出解放人的“历史”路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异化交往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觉悟,马克思曾在《手稿》中有这样的表达:“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6]60—61这种表述虽离唯物史观的原理式表达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为马克思打破正在主导其头脑的人本学异化史观的逻辑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马克思洞开了走向成熟的入口。
三、社会现实基底的彻底绽开——重释历史
伽达默尔曾说:“黑格尔哲学通过对主观意识观点进行清晰地批判,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8]伽达默尔的用词可谓严谨之至,在点出黑格尔的功绩——开辟了“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的同时,也暗示了他的不足——没有真正的“走向”社会现实,更不用说使社会现实从本质上向人们敞开了。不过,被黑格尔所无视的恰恰是马克思所重视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经历及其深化,让马克思彻底摆脱了抽象的辩证逻辑——人本学异化逻辑——的羁绊,并在此基础上坚定地走进社会现实“本质性的一度”——物质生产的方式及其辩证运动,使之获得彻底地绽开。毋容置疑,《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是唯物史观的真正诞生地。当然,社会现实不会自动向马克思开启。从写于《形态》之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条提纲》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在彻底清算费尔巴哈人的本质观中的抽象的、寂静无声的“类人”的过程中,实现由人本学异化观向社会现实转变的。
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是以其纯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如此一来,费氏只能把人理解为自然意义上的人,“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9]60。马克思从人的本质能动的实现机制出发,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60。很明显,把与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即“类”作为人的本质的费尔巴哈,只能看到宁静无声的“自然现实”;而马克思却从“真正的人的交往”即社会性中,看到了复杂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依据马克思在《形态》中的论述,社会现实不再是与世俗生活相分离的抽象存在,它有着丰富的现实内容:现实的个人、生产的自然必然性以及物质的生产关系。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考察社会现实的出发点。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现实的个人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有机统一。
生产的自然必然性是社会现实的基础性载体。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0]56很明显,这里的“自然必然性”,不是亘古不变的动物式的自然生存法则,而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即按主体的尺度使自然物合乎主体需要的过程。基于此,马克思把现实的生产劳动理解为“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10]204注(5a)。物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现实的本质性确认。用马克思的话说,“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进行”[9]81注1。无疑,“一定的方式”也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物质性的社会生产关系。之所以说这种方式是“必须”的,是因为“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9]344。并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9]142。
可见,以人、生产的自然必然性和物质的社会关系为三重内蕴的社会现实的透露,不仅让历史唯心主义丧失了庇护的依据,而且洞开了科学表述历史本质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尔纽说马克思“用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统一这个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黑格尔的主体与客体在理念中的统一这个唯心主义观点”[11]。随着马克思对社会现实的进一步切入,其“本质性的一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终被发现。
如果社会现实是唯物史观发生的地平的话,那么,生产方式是这个地平持存、稳固和延伸的源泉。因为生产方式不仅是人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根源,也是生产的自然必然性深入到什么程度和物质的社会关系体现什么样态的根源。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它“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9]80。也就是说,作为人们生活或生命的生产一开始就体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种过程又必然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为条件,概言之,生产方式总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统一体。
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形态》中这样讲道:“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9]124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二者之间产生的这个矛盾即为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用马克思的话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9]115毋庸置疑,这些表述标志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制定工作的基本完成。这种历史观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从物质生产中的基本矛盾出发来解释社会现实。从此以后,“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12]。
唯物史观自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受到马克思的特别珍视,并在他随后的思想建制中获得精炼的表述,如马克思在后来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1]32—33与《形态》中的表述方式相比,这次的表达已比较“成熟”,生产关系的概念从交往、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方式、社会关系等概念中完全“脱胎”出来,与生产力概念一起获得稳固而确定的使用。这构成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最完整、准确的表述。
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发现,对于马克思之后思想建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他成熟时期的作品都是以此为依据,并奠定在这个基础实实在在之上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马克思传[M].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
[4](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M].刘磊,王比铸,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复旦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8](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3卷[M].刘磊,王比铸,杨静远译.北京:三联书店,1963.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