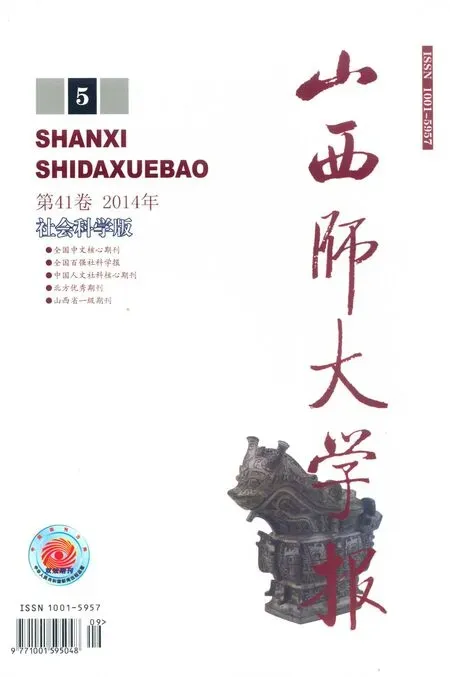女报人与现代中国的性别话语
——以20世纪30年代“新贤良主义”之争为例
冯剑侠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610041)
1935年5月到1936年6月,围绕“新贤良主义”,南京、上海两地三份妇女杂志(《妇女共鸣》、《女声》、《妇女生活》)的女报人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使得“新贤良主义”作为“叫嚷得最响亮的口号”,成为20世纪30年代关于“妇女回家”、“贤妻良母”大讨论中的重要部分[1]341。“妇女回家”因为涉及妇女解放的实质问题,即女性的归属是“固守家庭还是回归社会”这样一个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重大命题,在20世纪曾多次引发讨论,并对妇女解放的政策和路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2]而作为颇具表征性的性别符码,“贤妻良母”体现着传统文化人伦关系中的宗法等级观念、价值取向和性别分工,持续地规范着女性的言语行为,塑造着女性的主体认同。但是,正如女性主义媒介学者凡·祖伦所言:“虽然话语具有规训的力量,它能规定并局限认同和经验,但也常常被抗拒和颠覆。因此,占支配地位的男性话语绝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压制能力,因为总有抵制和抗争与之并存。”[3]46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贤妻良母”的性别话语发生了怎样的意义变迁,女性自身又是如何认知、理解和重构其内涵,成为许多研究者考察的重心。
作为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意识形态建构工具,报刊等大众传媒在性别话语的生成和流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涌现的一批由女性主办(by women)、为女性而办(for women)、关于女性议题(about women)的妇女报刊,为研究彼时的性别话语和女性的主体言说提供了便利。笔者认为,发生在女报人之间的“新贤良主义”之争,正是一个理解现代中国妇女报刊、女性报人与社会性别话语之间关系的代表性文本,但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4]。本文将这场论争视为一个话语事件,试图通过对历史语境的考察和对争论文本的话语分析来解答以下问题:在女报人的性别论述中,“新贤良主义”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反对者又据何加以驳斥?她们试图建构怎样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召唤怎样的性别主体?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权力关系?
一、“贤妻良母”与1930年代的复古思潮
20世纪初,盛行于日本的“贤母良妻主义”进入中国,与传统的女性规范一拍即合,“贤妻良母”成为女子教育的指导思想。[5]然而,在倡导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女权话语中,“贤妻良母”屡受质疑。1909年,男性女权主义者陈以益曾质疑,既然男子教育“不以贤夫良父为目的”,那么以贤母良妻为女子教育原则,“犹教婢女以识字耳,虽有若干之学问,尽为男子所用”,和男尊女卑的谬论毫无差别,仍是将女子视为“男子之高等奴隶”,丝毫没有平等和平权可言。[6]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五四时期,胡适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讲《美国的妇人》中,提出了著名的“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我是堂堂的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才算做我的事业呢?”[7]“贤妻良母”这一延续数千年的女性角色规范,逐渐变成了“做一个人”的女性角色期待的对立面,每逢有论者为“贤妻良母”辩护时,即刻便引来反对者的驳斥,认为“贤妻良母”将女性的职分设定为妻子和母亲,限制了女性从事职业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可能性。尤其在由女性主编的刊物上,论者多一边倒地反对“贤妻良母主义”。如刘清扬在其主编的《妇女日报》上强调:“一个女子所能作的事,并不止于妻与母;一个女子所应作的事,也不止于妻或母;一个女子所愿意作的事,更不止于妻与母。”[8]在石评梅、陆晶清主编的《京报·妇女周刊》上,“贤妻良母”被视为旧礼教强加给女子的片面责任和道德,如同一道枷锁,妨碍女子去追求自己的独立人格,必须加以铲除。
然而,进入1930年代以后,受到从外到内、由上到下力倡传统、高扬母性的复古思潮及政策的影响,“贤妻良母”再度引发国人的关注与讨论,其含义也从女权主义话语中的“女性枷锁”,逐渐转变成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女性美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严重损失人力与男丁的欧洲各国陆续制定奖励婚姻和鼓励生育的措施,营造出一股要求妇女放弃职业、回归家庭,承担“贤妻良母”之责的舆论氛围,其中尤以推行独裁统治的法西斯国家为甚。墨索里尼公开宣称:“妇女应该守在家里,做一个好主妇,好妻子,好母亲,如果她在这方面尽了责,那就是等于对国家尽了责了,如果她有余暇,那她也不妨在互助协会中出点力,不过必须在不疏忽她本责的条件之下去做。”[9]德国纳粹党的性别意识形态坚守“男女有别”的原则,希特勒在妇女大会上明确表示,社会与国家是属于男人的世界,女人的世界则是她的丈夫、孩子与家庭,这两个世界的区隔是“合乎自然”的。为求增殖人口、解决经济恐慌与失业问题,希特勒政权大力鼓吹“结婚是女子唯一的真正职业”,“家庭为妇女的乐园”[10],严格执行“三K主义”的妇女政策(德语孩子、厨房和教堂中的第一个字母),限制妇女就业,使得不少德国妇女只能将职位让给男子。[11]
在中国,“贤妻良母”论与国民政府保守的妇女政策和性别意识形态相契合。在国民党制定的妇女政策中,始终将“培养母性”作为重点,强调女子作为“民族之母”,在“挽救种族衰亡之危险、奠国家社会坚实之基础”中的作用。从国家利益出发,妇女的重要性体现在既是国家未来栋梁(儿童)的孕育和教养者,又是国家现在栋梁(男子)的支持者,因而在与妇女有关的决议案中,不断地强调妇女对于家庭的责任。[12]1641935年开始自上而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则将这股崇尚母性之风推向高潮。但凡与母性抵触的妇女表现——从外表的奇装异服、裸腿裸足、剪发烫发,到男女自由交往,摩登浪漫等行为——都会被各地执政者以新生活运动和“维持风化”的名义加以取缔和严格管制。
在国内外一片崇尚母性之风的鼓励下,保守人士以“家齐而后国治”为理由,鼓吹妇女放弃职业、回归家庭,以尽家庭责任的方式服务于民族复兴,如周瘦鹃在《申报·妇女专刊》的发刊词中直白地劝告女性:“社会和国家有事时,便当挺身而出,为社会为国家直接服务;社会和国家没事时,那么不妨退守在家庭中,做伊们的贤妻良母。”[13]许多男性论者直言不讳其男性中心的性别立场,认为妇女让出职位回归家庭,既能解除男子失业危机,也能给外出工作的丈夫带来温暖与安慰。如李赋京就称赞德国的“贤妻良母”:“说起德国女子在家做事的能力,可说就像一头牛,但事罢之后,换起新装,坐在钢琴上的时候,却是另一种态度。所以她们的丈夫从外面做事回来,一到家中,就感到愉快,心里的烦闷早已忘去一半。”因此,他劝告中国的妇女,“无论如何女子总是女子”,养育孩子就是为社会服务尽责任,“其他的都是次一等的”,除非生活逼迫着不得已,没有必要出去与男子争夺饭碗。[14]
简言之,在1930年代的复古思潮中,“贤妻良母”的性别话语召唤的是兼具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和传统妇女美德的女性主体。在倡导者们看来,女性的人生价值和存在感是通过服务于家庭和民族国家来体现的。当经济萧条、国家有难之际,女性理当让出在社会中的位置,回归家庭以尽“贤妻良母”的本份,至于女性个体的自由意志和职业规划,则成为可被忽略与牺牲的部分。那么,女性论者又是如何看待“贤妻良母”的呢?《妇女共鸣》所极力倡导的“新贤良主义”,与“贤妻良母”论相比,又“新”在何处呢?
二、“新贤良主义”:基于男女平等的“贤良”
《妇女共鸣》是由李峙山、王孝英、陈逸云、傅岩、谈社英等国民党妇女运动家于1929年3月创办、“以督促当局实行男女平等之政纲”[15]为办刊宗旨的妇女杂志,因其“精神一贯、持论正确”,曾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立案时批准为妇女界唯一之刊物。[16]236创刊以来,《妇女共鸣》致力于从舆论上督促国民党履行党纲所承诺的男女平等原则,并对有违这一原则的封建性纲领提出批评。在盛极一时的“妇女回家”声中,《妇女共鸣》曾屡次刊文加以反驳,强调“婚嫁不算女子职业”、“从事职业为妇女唯一之出路”。然而,在对待“贤妻良母”问题上,《妇女共鸣》的女编辑们却认为需要区别对待,既批判对妇女“贤良”的片面要求,同时提倡“贤夫良父”,以分担职业妇女的压力,共同建设优良的家庭。
首先,基于男女平等的原则,《妇女共鸣》的编者从权利与义务对等的逻辑出发,认为中国传统伦理基础的五伦中,每一伦都有对等的人和对等的责任,如君圣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朋友以义,唯独夫妻关系只强调妻子的贤惠,而对丈夫没有任何要求,使其只享受权利而无义务,这种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应该被坚决地否认。因此,从男女平等的立场出发,“新贤良主义”更多地体现为对丈夫和父亲的要求。[17]如蜀龙重新定义了“贤良”的具体内涵,“贤”是夫妻双方相互的温柔体贴、互助精神和高尚人格修养,“良”则是父母双方对孩子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共同分担教养孩子的责任。[18]
其次,通过建构新贤良主义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妇女共鸣》的编者希望打破由于传统性别分工给职业女性带来的困境,她们呼吁那些传统上被视为女性责任的家务劳动和育儿职责应由贤良夫妻共同承担。职业女性的双重负担问题,随着二三十年代女性从事社会职业的增多而日益凸显,当时有人不无悲观地认为“按目前的事实看,要做一个职业的女性,就得放弃组织家庭的权利,否则只有终生做个贤明的主妇。可是前进的女性是绝对不愿让家务决定她们的一生的。于是,要得到经济的独立,要有个职业,便不得不孤独地过苦楚的生活”[19]。而作为职业女性中的一员,《妇女共鸣》主编李峙山曾痛陈“生活上的男女不平等”的困扰:
在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里,男人呢,工作八小时、睡眠八小时、求知与交际娱乐又八小时。女人呢?工作八小时、柴米油盐、缝纫补洗、牵儿抱女、奉亲慰夫等等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睡眠就只有六小时或四小时了。女人在这种不平等的生活下生活着,五年或十年之后,男人的智能,地位可与日俱增,女人的智能和地位确实日渐低落;这种不平等的生活,简直是由平等迈进不平等的一条黑暗的途径,无数的知识妇女整年整月的在这条黑暗的途径行进着,这是如何的可怕呀![20]
正因如此,职业妇女如何能够兼顾家庭,一直是《妇女共鸣》所关心的话题,例如倡导家庭生活协作、男女共同承担家务[21],以及传授职业妇女避孕方法、教育小孩和女仆的方法等。“新贤良主义”也可被视为《妇女共鸣》就如何实现“生活上的平等”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改变“贤良”的内涵和要求,来改造家庭中的性别角色配置、劳动分工和道德规范,以实现家庭领域中的男女平等,使妇女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能够并行不悖。
例如,为了给读者的生活实践以更明确的指引,李峙山以一对自由恋爱、各有职业的新婚夫妻为例,告诫妻子“从职业的办公厅回来,入了家庭的办公厅”,千万不要遵守“历史上得来的贤妻良母的训练”,包揽一切家务,养成丈夫颐指气使的“主人气派”。相反,应该时刻牢记平等、互助的原则,处理一切家庭琐事时,都要“拉着你的丈夫共同操作”,久而久之方可使之步入“合理的贤良正轨”[22]。同样,夫妻之间的经济角色也不用再受限于男子外出挣钱、女子照顾家庭的传统模式,如果一个职业妇女的经济所得在三十元以上,还让她放弃工作做贤妻良母,则是不经济的。相应地,如果男子的职业所得不到二十五元,那么“他应该去抱抱孩子,烧烧菜洗洗衣服”[23]。
三、做“社会人”:反对一切形式的“贤妻良母”
与李峙山等人在认可并维护作为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贤良”话语不同,《女声》杂志主编王伊蔚,《妇女生活》杂志主编沈兹九、罗琼等却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出发,认为“贤妻良母”不仅是对性别角色的片面要求,而且与不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严重妨碍了女性成为“社会人”的解放目标,因而采取了更为坚决的否定态度。
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列宁的妇女解放论》、日本妇女理论家山川菊荣的《妇人和社会主义》等,以及对苏俄妇女在参政、婚姻、教育、就业等方面的状况介绍,被大量翻译并刊载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有影响力的报刊上,从唯物史观出发的妇女解放观广为流传。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运动家们不再仅仅通过反对封建礼教,以及争取妇女民主权利的方式来实现妇女解放,而是坚信妇女的历史地位、道德观念、家庭制度的变化都是社会经济制度变化的结果,导致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度。因此,女性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以寻求民族国家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改造不平等社会经济基础的社会革命为前提,正如《女声》半月刊所倡言的:
我们相信,妇女问题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环,整个社会问题未解决前,妇女问题绝不能有彻底的办法。……目前中国妇女运动的倾向一方是提倡新贤妻良母主义,一方是进行狭义的女权主义。……这两者都不是为大众妇女谋出路,我们不但不应以合作,而且要坚决的反对。我们所需要的是深入群众的妇女运动,从民族解放运动中达到全人类的解放。[24]
做一个“社会人”,是左翼女编辑们共同的自我期许。因此,对李峙山等人建构的“新贤良主义”,《女声》和《妇女生活》的编者们都立场鲜明地加以驳斥。如1935年10月,《女声》编委会召开主题为“过渡时期的家庭妇女问题”妇女问题座谈会。在讨论中,她们把家庭定义为“私有财产制男性权威底下的一种以血统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生活形态”,认为家庭妇女是“不参加一切社会生产事业,专以家事育儿为唯一职务,在意识上是贤妻良母主义者,在生活上是处于依靠男子豢养的一种从属地位”。在《女声》的编者们看来,家庭妇女是被压迫并需要解放的一群人,但由于她们缺乏觉悟、团结和奋斗精神,妇女杂志要肩负起引导她们走出家庭参加解放运动的责任,了解家庭与私有财产制度的关系,明白“家庭既是妇女的牢笼,家庭不废除,妇女就得不到解放”和“废除家庭制度,就必需从废除私有制度着手”的道理,从而投身社会革命。相应地,她们认为《妇女共鸣》所倡导的“新贤良主义”,是对“贤妻良母”内涵的封建性缺乏深刻的认识,“离开经济基础而凭空地去提倡‘贤夫良父’”,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反而替男性欺骗和压迫妇女。[25]
作为《妇女生活》的主编之一,罗琼批评“新贤良主义”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容易混淆视听”。因为“贤妻良母”不是一个生理或伦理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下的产物,只有在私有财产制度的男性中心社会中,男子利用妇女“为妻为母”的特性把妇女束缚在家庭中,做家庭的奴隶。对于《妇女共鸣》试图从道德和行为层面来重新诠释“贤良”的定义,罗琼认为“贤妻良母主义的真意义,绝不能从字面上去追求,因为这是有权力的男子笼络妇女欺骗妇女的借口,谁从字面上去解释贤妻良母问题,那么谁就在无形之中钻入男子们的圈套里面,只能永远去做男子们的奴隶”。而所谓“贤夫良父”,在私有财产制继续存在的前提下,不过是“乌托邦的梦想”、现存不合理社会的“续命汤”罢了。因此,罗琼力主女性要走出家庭、以“社会人”的姿态,投身于合理社会的创造中去,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26]
四、余论
在既往研究中,“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通常被视为同一问题加以讨论和批判,但如若仔细检视和分析《妇女共鸣》“新贤良主义”讨论的文本内涵,不难发现在她们的论述中,“妇女回家”和“贤妻良母”并不是一回事。在1930年代盛行于国内外的复古风潮中,“母性”的生理功能和社会文化意义被凸显和强调,同时面对如职业妇女的双重负担等五四以来女权实践所产生的新问题,寻求解放的中国妇女应当以何种面目出现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领域,是这一时期妇女报刊的女报人们共同思量和反复讨论的主题。她们借助妇女报刊而展开的公共讨论,是为了重新界定和塑造女性的恰当角色,以回应和抵抗复古思潮对妇女解放的质疑和批评,从而创造出丰富而多样的性别话语。
作为国民党的妇女运动家,李峙山、谈社英等女编辑们坚信男女平等的原则,希望实现性别平等,而她们所构建的“新贤良主义”,既是女权主义者与国家政策相协商的结果,同时也可以视为五四时期家庭改良议题的一次回归。[27]从女性生活经验出发,她们试图通过为“贤良”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将话题转向男女平等、相互尊重和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以此来减轻职业妇女的家庭负担。但是,这一改良主义的思路并未得到当时所有女报人的认同。与《妇女共鸣》的女编辑们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构想性别平等不同,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观的女编辑们坚信私有制经济才是对妇女造成压迫的根源,任何形式的“贤妻良母主义”都是对这一制度的维护,必须坚决地予以反对。她们强调妇女只有走出家庭、以“社会人”的姿态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中,建立起废除私有制和家庭制度的合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
但是,不论是力图将传统的贤良道德与现代的独立人格相结合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将母职神话置于私有财产制度框架下加以批判的激进主义者,她们都将民族解放、国家强盛、社会革命等“大我”的利益置于女性个体“小我”的需求、欲望和选择之前。因此,掌握话语权的女报人们,同样对那些不符合“大我”利益的同性(如家庭妇女)施以规训与动员,试图将其纳入到她们所建构的新的性别认同中。
[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2]范红霞.20世纪以来关于“妇女回家”的论争[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3](荷)凡·祖伦.女性主义媒介研究[M].曹晋,曹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Ma Yuxin,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1898—1937).Cambria Press,2010
[5]吕美颐.评中国近代关于贤妻良母主义的论争[J].天津社会科学,1995,(5).
[6]陈以益.男尊女卑与贤母良妻[J].女报,1909,(2).
[7]胡适.美国的妇人[J].新青年,1918,5(3).
[8]清扬.贤妻良母之是非[N].妇女日报,1924-1-3(2).
[9]碧云.论墨索里尼之奖励生育[J].女声,1935,3(11).
[10]碧云.德国贤妻良母制的复活[N].申报·妇女园地,1934-5-20(19).
[11]佩曾.希特勒统治下的妇女[J].妇女共鸣,1935,4(6).
[12]洪宜嫃.中国国民党妇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M].台北:国史馆,2010.
[13]周瘦鹃.发刊辞[N].申报·妇女专刊,1936-1-11(17).
[14]李赋京.无论如何女子总是女子[J].国闻周报,1935,12(9).
[15]发刊词[J].妇女共鸣,1929,(1).
[16]谈社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M].南京:妇女共鸣社,1936.
[17]编者.我们为什么出这个专号[J].妇女共鸣,1935,4(11).
[18]蜀龙.新贤良主义的基本概念[J].妇女共鸣,1935,4(11).
[19]元.女性往何处去[N].申报,1934-2-25(17).
[20]本刊征文[J].妇女共鸣,1935,4(3).
[21]峙山.家庭生活协作计划[J].妇女共鸣,1934,3(9).
[22]毅.怎样使丈夫贤良[J].妇女共鸣,1935,4(11).
[23]凤兮.贤良与女性生产[J].妇女共鸣,1935,4(11).
[24]今后的女声[J].女声,1934,3(1).
[25]妇女问题座谈会·过渡时期的家庭妇女问题[J].女声,1935,3(21 ~22).
[26]罗琼.从“贤妻良母”至“贤夫良父”——读《妇女共鸣》贤良问题专号以后[J].妇女生活,1936,2(1).
[27]Lien Lingling.“Searching for the‘New Womanhood:Career Women in Shanghai,1912—1945”.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