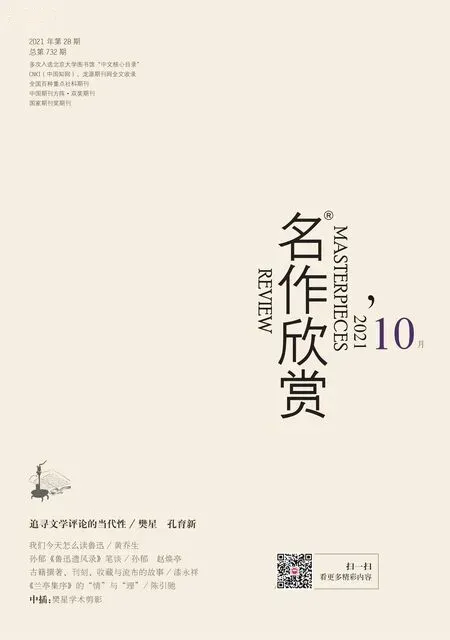生命本身就是自由——瓦西里·格罗斯曼与其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
江苏 董晓
俄罗斯是与苦难相伴的民族,20世纪的俄罗斯更是苦难深重。或许,上帝的这种“恩赐”反倒激发了作家特有的体验苦难的勇气。于是,在这片土地上,曾一度响起深沉的自由之声。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正是这样一位执着于沉重的精神使命的作家。
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是格罗斯曼的绝笔,亦可算作他的长篇《生活与命运》的姊妹篇。后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了中文译本。在《生活与命运》这部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巨著里,作家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民族劣根性进行了反省。由此,该书也被人们称作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苦难意识使他看到了生活的痛苦,超越了社会现象的表层而获得了对事物超前的思考。小说发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对自由的渴望。愈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对历史的思考愈深沉,自由之声愈响亮。作家仿佛要在生命的尽头进一步思考俄罗斯的“生活与命运”。于是,留给了世人这部力作——《一切都在流动》。
历史的沉重赋予了作品沉重的基调。格罗斯曼这位冷峻的作家塑造了他不幸的男主人公——在劳改营里度过了近三十年的伊凡。伊凡带着心灵的创伤从劳改营回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斯大林的去世、伊凡的归来,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给伊凡的亲友们以极大的精神震荡。孤身一人的伊凡四处游荡,但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列宁格勒,都不能让他找回熟悉的感觉。熟悉的城市令他陌生,这种失落感使他陷入了回忆之中。他想起了逝去的岁月,忆起了自己在劳改营里的经历。他带着茫然的心情离开了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租下一间房子,找了一份钳工的活,安定地生活下来。房东寡妇安娜的善良与温存使伊凡忽然间有了一种归宿感,他爱上了这个女人。在宁静的生活空间里,伊凡又回忆起劳改营里的人们,感受着作为一名囚犯和自由人之间的差异,并进而思考着国家机器对人的自由的践踏,思考着自由二字的内涵。然而,女房东安娜却不幸患上绝症。伊凡心中涌起了无可奈何的孤独感。他想起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想起了黑暗的20世纪30年代。在这充满痛楚的思绪中,伊凡力图理解生活的命运,心中期盼着安娜能与他共同分担生活的痛楚。饱经风霜的孤独的伊凡只身来到海边的故乡,站在山坡上,面对空旷的大地,再次感受到生活无情而庄重的流逝,发出了“一切都在流动”的感慨。作家展示了他不幸的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在主人公片断式的思考中,我们感受到他(实则作者自己)对俄罗斯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反思,对近似荒诞的历史进程的认识,对斯大林时代的批判。
整部作品是主人公对历史的感悟。随着主人公的思绪,我们仿佛回到了令人恐怖的20世纪30年代,置身于那一件件令人难忘的事件中,体味着那个时代特殊的空气。反犹太情绪的高涨,所谓“医生事件”给人们心头抹上的阴影,劳改营里地狱般的景象,人性的扭曲、压抑,集体化后农村的人间悲剧,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极端虚伪性和科学研究领域里的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等,都让我们重新体验了那个时代的氛围。
不过,主人公的思绪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过去的追忆中。他的思绪伸向了历史现象的背后,竭力去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俄罗斯大地遭受如此之磨难?
首先,伊凡思考了俄罗斯民族的劣根性。国家机器反文明的行为之所以能实现,根源在于人民中存在着滋养它的温床。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恐怖之所以存在,离不开人民当中普遍存在的“精神上的病症”。小说主人公是站在现代自由观念的高度上考察俄罗斯民族性的。俄罗斯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在强力面前的奴性”,这样,他就会丧失掉自己的良心,会去充当可耻的告密者。因为他坚信,“这样会积聚比黄金和庄稼更宝贵得多的财富——党的信任。他懂得,在苏维埃时代,党的信任便是一切,便是力量、荣耀与权力的保障”。然而,作家指出,“对于这样一位俄罗斯公民,我们是无权指责他的,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无法弄清楚,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因为“即便是纯洁的心灵也无力理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在这里,格罗斯曼沉重地指出了俄罗斯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善”与“恶”的极端的麻木不仁以及奴性气质。是整个国家统治下的社会氛围迫使人们变成了那样,而国家机器之所以能这样做,恰恰是建立在人民低下的人格力量基础上的。这一方面体现为人民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时所表现出来的奴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跟随着国家机器而高涨起来的狂热民族主义情绪。审视俄罗斯的历史,作家发现,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专制统治力量的强化是同步的。这既是对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批判,也是从更广泛意义上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理性批判。
依附于民族劣根性,国家机器得以发挥其威力。作家批判了苏联对人的自由的扼杀:“俄罗斯表面的生活愈接近西欧,俄罗斯工厂的大机器愈是轰鸣运转,火车车轮愈是隆隆作响,轮船汽笛声愈是高亢鸣叫,宫殿窗户内愈是透出西欧化的水晶灯光,那么隐藏在生活深处的俄罗斯与西欧的鸿沟就愈是深广。”这一思想是很有启发性的。人们很容易陶醉于苏联作为一个强大中央集权制国家在重工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格罗斯曼则清醒地认识到,在成就背后是自由的丧失,因而也是文明的退化。格罗斯曼由此进而反思了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所走过的历程。他深深地感到,“几百年来,俄罗斯只有一样东西没有见到过,那就是自由”。彼得大帝建起了巨大的国家机器,而“这一巨大的国家力量迫使人们将自己的自由,将对自由的渴望纷纷呈献给它”。于是,飞速发展的俄罗斯也就离自由愈来愈远,直至斯大林时代,强大的国家机器终于可以凭着最现代的物质基础去肆意践踏人的自由了。
国家机器一旦建立在扼杀人的自由的基础上,那么,它愈是强大,人的尊严、良心,乃至个体的生命,就愈会受到肆意的践踏。男主人公伊凡的归来给他当年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这些人其实是很可怜,很值得同情的。他们无非是一只只小甲壳虫,匍匐在强大的专制政权的脚下,慑于它的威严,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得到组织的信任,一位犹太科学家竟甘愿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人性竟然扭曲到这般地步,在那个恐怖年代并不难理解。同样也不难理解,国家一方面可以让几百万农民纷纷饿死,另一方面却要强行修建并不需要的运河、大坝、水电站,彻底实施农业集体化的乌托邦理想。强大的国家机器可以任意摆布没有自由的臣民,可以任意上演一幕幕虚伪的滑稽戏。在格罗斯曼笔下,所谓民主集中制的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所谓人民愤怒的声讨,所谓红场阅兵式的现场报道,所谓斯达汉诺夫式的劳动模范,所谓义务劳动的创举等国家政治生活中虚伪的把戏,都被剥下了外衣。
格罗斯曼对历史的感悟浸透着强烈的对自由的渴望。主人公伊凡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以前我认为,自由无非是指言论、出版和良心的自由。可是现在我认为,自由包含在所有人的整个生活里。自由意味着:想种地就有权耕地;想做鞋就有权做鞋;想裁衣就有权裁衣;想用自己种出的麦子烤面包就有权这么做;烤出的面包究竟是卖掉还是不卖,全由自己做主;钳工也好,炼钢工人也罢,包括艺术家,都可以按自己的心意生活和工作,而不是根据别人的命令。可事实上无论是著书立说者,还是种地做鞋者,现在都没有自由。”显然,作家在这里道出了自由的两层含义:生存的自由与精神的自由。恐怕任何一个西欧人都会惊诧于这样的分法。然而,“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这一最基本的要求在格罗斯曼那个年代那个国度里却成为一种奢望。这本身就是对国家机器的绝妙批判。在《一切都在流动》中,作家发现,其实劳改营里的犯人倒还有一丁点儿思考的自由,而外边的“自由人”却根本没有。这就是说,劳改营里的犯人反倒更自由些。这个独特而荒诞的现象倒更好地诠释了这个国家反自由的本质。
面对历史的悲剧,作家并没有发出绝望的感慨。他深深地体悟到,虽然在悲壮的俄罗斯历史上,人民因其固有的劣根性而未获得丝毫的自由;虽然现在“斯大林死了之后,斯大林的事业并未死亡,斯大林创立的没有自由的国家依然完好无恙”,但自由的生命力依然是顽强的,自由“不顾斯大林那无与伦比的巨大的强权而成长着。自由依然存在,因为人依旧还是人”。这就是说,生命与自由同在。“无论高楼大厦如何宏伟,无论大炮如何有威力,无论国家政权大得如何无边,也无论帝国强大得多么可怕,所有这些仅仅是过眼烟云,总会消逝的。只有一个真正的力量会留下来,不断发展,永远生存下去。这种力量只存在于自由之中。活着,就意味着成为一个自由之人。”这里,我们看到了格罗斯曼在那个残酷岁月中保持着的历史乐观主义:“人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就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一切生命的历史——从变形虫到人类,都是自由的历史,都是自由从少到多的历史,生命本身就是自由。”这段话似乎说明了格罗斯曼为什么要给这部作品起名为“一切都在流动”的道理。再强大的专制力量终究要随着时间的长河流逝,而在这条历史的长河中,不灭的是人对自由的渴望。这是作品最核心的精神所在。
格罗斯曼以过人的胆识和勇气,直面残酷的历史与现实,对国家乌托邦神话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品读这部小说,可以让我们领悟格罗斯曼对苏联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理性批判。人是会忘却的。不过,我们倒更该记住列宁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格罗斯曼仿佛重新阐释了这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良心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