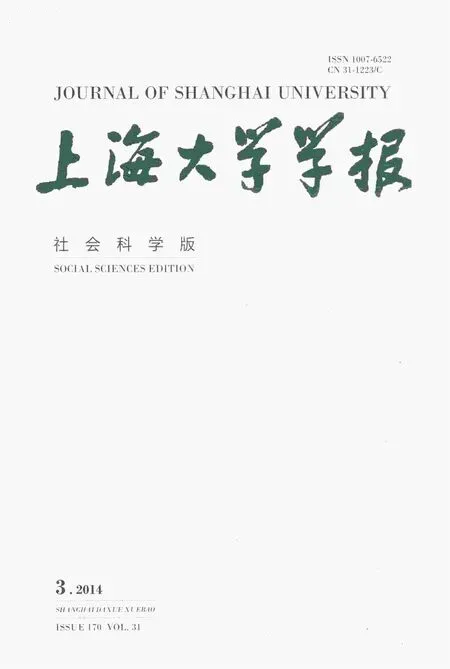恐怖之脸的退隐:西方恐怖片在1960年代的嬗变
聂欣如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200241)
当我们阅读《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1部恐怖电影》这样一本通俗读物的时候,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以1960年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又译《惊魂记》)为界,之前的恐怖电影大多都将一张恐怖的脸作为影片故事的核心,之后的恐怖电影则不再将恐怖之脸作为主要的恐怖元素。一些著名的恐怖片如波兰斯基导演的《冷血惊魂》(Repulsion,1965)、库布里克导演的《闪灵》(The Shining,1980)、福斯特和霍普金斯主演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1991)等,都没有出现狰狞恐怖的脸(或没有把这样的脸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有些影片甚至将恐怖面容作为了喜剧性的表现元素,如英国制作的《美国狼人在伦敦》(An American Werewolf in London,1981)。这显然不是恐怖电影的制作者在审美倾向的传承上发生了变异,而是观众对于恐怖刺激的要求有了改变。这样的改变是怎样发生的?与一般社会思潮的改变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些是本文试图讨论的问题。
西方早期恐怖片的恐怖之源
尽管《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1部恐怖电影》并不是一本权威的有关恐怖电影的著作,但是恐怖片在其中表现出来的自身的倾向却是任何一本有关恐怖电影的著作都不可能忽视的,因此我们可以将这本书作为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这本书中所罗列的1960年之前的恐怖片共26部,恐怖元素大致上是由人、鬼、怪物(怪兽)三种要素构成的,其中鬼片5部,怪物(怪兽)片8部,表现人的13部,其中有人格分裂者、精神病患者、冷血杀手等不同的类型。鬼片和怪物片在容貌上给观众造成的恐惧自不待言,科学怪人、狼人、吸血鬼等都是著名的例子。在有关人的恐怖片中,以正常人面目出现的仅4部,约占总数的15%。在有关人的恐怖片中,一些原本是以正常人面目出现的角色,在制造恐怖气氛的关键时刻,往往一改自身正常的相貌,或显露隐藏已久的恐怖真面貌,如《浴室情杀案》中的小学校长,为了达到吓死自己有心脏病的妻子以谋取其财产的目的,他假扮成一具死尸,在浴缸中复活,两只眼睛套上了只有眼白的眼罩,当这具有眼无珠的男尸湿淋淋地从浴缸中慢慢站起时,果然达到了目的,他的妻子被活活吓死。在《古屋魅影》中,则启用女演员扮演男性,以呈现出家族精神分裂的怪异。《无颜之眼》中剥人脸皮的医生,则是为了拯救自己因车祸毁容的女儿等等。我们之所以把恐怖的容颜作为早期恐怖片最为显著的特点,并不仅仅是因为绝大部分的影片中都出现了令人感到恐怖的脸,更是因为影片的整个故事都是围绕着这样一张恐怖的脸建构的,如《歌剧魅影》(被硫酸毁容的脸)、《科学怪人》(用不同尸体缝合的脸)、《化身博士》(一个人有两张不同的脸)这样脍炙人口的故事,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编拍摄,如果没有了容颜的改变,这样的故事便不能成立了,从而形成了一种“容颜故事一体”的特征。

《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1部恐怖电影》中1960年代之前恐怖片
那么,为什么容颜的扭曲会成为1960年代之前恐怖电影主要的恐怖元素呢?容颜故事一体化特征的形成是偶然的吗?其实,人们对于容颜的恐惧和容颜故事一体化的表现方法,是自古以来形成的人类对于恐惧的两个不可判分的方面。所谓恐惧,大多源于人类对于不能理解之事物的想象,克尔凯郭尔指出:“作为‘恐惧’的形态(如果我们让我们的想象力去构建出这样一种形态的话),它本身看上去是很可怕的,而如果它觉得自己有必要伪装而不是以自身的真实面目出现(尽管它仍然还是它真实的自身),那么它的这种形态就会更骇人……如果我们进一步问,‘恐惧’的对象是什么,那么,不管是在这里还是任何别的地方,答案就必定是:它是‘乌有’。”[1]克尔凯郭尔所举的例子便是西方文化中那个拿着大镰刀的骷髅死神的形象,这个令人恐惧的形象本身是不存在的,是人们的想象所建构的。恐惧是一种人们对于其外部世界无从理解的感受,而人生来便是需要对其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和理解的生物,因此,当人们需要对这些冥冥之中的事物表现其畏惧或战而胜之的情感的时候,往往需要借助于一个外在的、实体化的形象。恐怖电影将人们心中的恐惧表现为一张狰狞恐怖的脸并非毫无由来,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的面具文化,都从侧面说明了这样一种依托于人类容颜的恐惧的外化具有普世的性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自己的研究中便曾描述了乱伦禁忌是怎样演化成神话及其面具的,并指出北美夸扣特尔土著的“斯瓦赫威面具”是一道“防止乱伦行为的屏障”。[2]我国古代文学家苏轼曾在《东坡志林》一书中说过“祭必有尸”,是说祭祀的时候一定要有人扮演神灵鬼魂。李锦山、李光雨在他们的著作中指出:“古人认为厉鬼面貌丑陋,为了惊怖震慑厉鬼,面具的形象要比厉鬼更狰狞,这便是既以其鬼之道,还制其鬼之身。”[3]古人将一切有害事物归咎于一张恐怖面孔的观念,来自于其自身与外部世界充满精灵且不分彼此的观念与习俗,列维-布留尔称之为(人与物之间的)“互渗”,并认为即便是在今天高度文明化的人心中依然保存着这样的感觉,他说:“即使在我们这样一些民族中,对互渗的需要仍然无疑比对认识的渴望和对符合理性要求的希望更迫切更强烈。”[4]尽管人类社会在不断变化,但这样一种感觉积淀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直到20世纪的中叶,我们依然能够在恐怖电影中清晰地看到这些情况。
一张恐怖狰狞的脸与一个故事浑然一体的过程,似乎与西方强调理性的启蒙运动相关。在我国古代的恐怖故事中,并没有这样一种恐怖形式与故事一体化的特征。比如敦煌壁画中《九色鹿》的故事,那个出卖神鹿的人最后应了自己的诺言,浑身长疮落水而死,因果报应并没有必然地与丑陋的脸结合在一起。再如《聊斋志异》中著名的恐怖故事《画皮》,恐怖的厉鬼也早早便被道士降伏,故事的高潮部分是死者的夫人如何忍受疯僧的羞辱最终救活自己的丈夫。故事的目的都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规训,恐怖只是规训的工具,故事的点缀。对于恐怖故事的讲述,强调理性的近代西方则有所不同。美国人在1931年制作的影片《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尽管不是第一部有关科学怪人的影片(1910年便有人在美国制作过同名默片电影,只有16分钟),但却是最早成功演绎玛丽·雪莱小说原作的影片,尽管它也不是完全按照小说的故事进行拍摄,但基本保持了原小说的精髓。故事是说一名青年科学家维克多·弗朗肯斯坦到处收集尸体做实验,引起了他未婚妻伊丽莎白的不安。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弗朗肯斯坦将他用不同尸体合成的“人”放在放电的空间,让其接受能量,结果这个科学怪人活了,但是他没有理智,如同动物,看见火的时候会有攻击性行为,弗朗肯斯坦只能把他用铁链锁起来。一名教授试图通过手术的方法来矫正科学怪人的行为,却被他掐死,科学怪人逃出了实验室。这天正是弗朗肯斯坦订婚的日子,整个小镇都在狂欢。科学怪人在湖边碰到了一个女孩,他看见女孩将花抛向湖中,花浮在水面上,他也将这个如花的女孩抛向湖中,但是女孩却没有浮上水面。科学怪人跑进了小镇,甚至跑到了弗朗肯斯坦的家里,使伊丽莎白受到了惊吓,被淹死的小孩也引起了镇上人们的愤怒,大家拿着武器,点着火把,带着狗去找科学怪人。科学怪人一路逃窜,最后被暴怒的村民烧死在一个废弃的磨坊中。
之所以说这部电影保留了原小说的精髓,是因为这部创作于约200年前(小说初版于1817年)的小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推演到极致,从而使人们反观自身创造力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胡布勒夫妇在他们的书中指出,小说作者玛丽·雪莱深受她丈夫雪莱以及拜伦的影响,而这两人都是当时的“科学狂热者”,“拜伦、雪莱以及波利多里都听说过卢基·伽伐尼,一个意大利科学家,1786年他展示他能够在雷电暴雨的时候,通过用剪刀触碰死青蛙让其肌肉产生收缩。在这个过程中,他猜测缔造生命的‘生物电’存在”。1803年,这位科学家的侄子甚至声称“能让尸体坐起来”。[5]19世纪尽管是科学精神尚未普及到大众的时代,但是在中产阶级的精英阶层中,科学已经使他们能够想象如何通过物理的手段来创造生命,并对这一想象的后果感到不寒而慄。小说的这一特点不仅在当时让人们耳目一新,在电影拍摄的年代使人感到恐惧,而且直到200年后的今天,只要一想到制造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依然使人充满了遐想和畏惧。这也是奥斯本从正面评价启蒙运动时所指出的:“启蒙的本质特征之一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否定性原则。也就是说,启蒙质疑了它自身,它基本上是‘自我觉知的’,它倾向于转向自身,去质疑自身的内容。”[6]正是这样一种质疑的精神,试图穷尽人类创造的源头,并因此而触动了人类认知尚不能企及的那个端点,从而引发了恐惧。诸如此类的对于人类自身能力的反思,引发了一大批与之具有相似主题的恐怖电影,如前面提到的《化身博士》、《失魂岛》等。《科学怪人》之所以成为早期恐怖电影的经典,正是因为它秉持(或者是首创——有待考证)了“容颜故事一体”的模式,将反思深入到我们的知识系统尚不能掌控的那一区域。之所以认为这一类恐怖电影的构成受到了启蒙主义精神的影响,还因为原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因为触及了恐惧而对令人恐怖的事物持绝对否定的态度,尽管没有理性的科学怪人令人惧怕,但他身上还是表现出了人性,比如他在将小女孩扔进水里的时候,并不是出于谋杀的动机,而是出于他的“审美”。在1935年制作的《科学怪人的新娘》中,更是让科学怪人学会了人类的语言,能够与目盲的老人进行沟通,感受人类的友好之情,从而对人类的“容颜恐惧”进行了含蓄的批判。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科学造福人类和带来灾难矛盾心理的曲折呈现。也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人们不再认同“容颜故事一体”模式时,《科学怪人》这部影片看上去并不十分恐怖,倒是那么几个科学家、教授显得神经过敏,追杀科学怪人的小镇居民也表现出了集体非理性的过度狂热。在1931年的《科学怪人》之后,世界各地拍摄了无数有关弗朗肯斯坦制造科学怪物的电影,并演绎出了科学怪人的“客人”、“女儿”、“新娘”、“团伙”、“军队”等不同的故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延续了恐怖电影的风格,这里不再展开。
从“理念的恐惧”到感官刺激
1960年,有两部重要的恐怖电影出现:一部是鲍威尔导演的英国电影《偷窥狂》(Peeping Tom),另一部是希区柯克制作的低成本美国电影《精神病患者》。这两部影片表现的主题都与男主人公的人格分裂有关。《偷窥狂》还追究了这一人格分裂的由来:摄影师迈克的父亲是一名生物学家,从小记录迈克对于恐惧的反应,甚至故意制造让他感到恐惧的事物刺激他,从而养成了他窥视、记录他人恐惧的嗜好,并变态地在工作中伺机杀人并拍摄记录这一过程。影片并没有把迈克描写成杀人狂魔,演员的容貌不但英俊,他所饰演的角色也文静腼腆,对自己的女友亦十分柔情,事情败露后迈克选择了自杀。影片《精神病患者》现在已成为电影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恐怖片的类型范畴。这部影片延续人格分裂的恐怖电影模式,塑造了一个兼有儿子和母亲人格的青年诺曼,他经营着一家汽车旅馆,当他对到旅馆过夜的女主人公玛丽安·克莱恩有好感时,嫉妒的“母亲”便出面杀死了她,而诺曼作为儿子却又维护“母亲”,清除所有留下的痕迹。玛丽安的失踪引起了家人和她所在公司的关注,诺曼杀人的事实最后被发现,他也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那里,他继续扮演着他的双重身份。
影片《偷窥狂》在恐怖元素的处理与利用上属于过渡类型,其杀人的画面大部分放在画外,仅在影片最后,迈克的自杀才被放在画面中表现。不过这是一部彩色影片,刀尖上沾染的红色血迹十分刺目,相对来说,被刺身死的主人公身上却没有血迹。这部影片对于恐怖元素的处理,如同英国电影《鬼杀手》(The Hanuted Strangler,1958。影片男主人公具有双重人格,他的另一杀手人格具有扭曲的恐怖面容),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从1920年代以来,将人类面容的变形作为主要恐惧成分的做法,这种做法表现的是一种恐惧的理念,因为令人感到恐惧的不仅仅是一张脸,而是一个完整的有关恐惧的叙事,而这样的叙事从1960年开始,正在被逐渐淡化。比如影片《偷窥狂》,男主人公迈克的杀人武器是一把装在摄影机三脚架中的尖刀,他还在三脚架上安装了一面镜子,这样被害者便可以在被刺死时看见自己死亡时恐惧的面容,影片中出现的镜子显然不是平面的,因此被害者的面容在镜中扭曲变形。影片并没有把恐怖之脸设置在杀人的男主人公的身上,而是放在了被害者的身上,恐怖之脸尽管存在,但已经不是必不可少的恐怖(叙事)元素了。
《精神病患者》这部影片对于恐怖元素的使用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它不再将人脸的变形作为主要的恐惧元素,而是把对于观众的生理刺激作为主要的恐怖元素来使用。当然,人脸变形也可以是一种生理刺激,不过人们对于这一刺激的感受主要在于造型和审美,因为造型和审美上的陌生感对观众产生了刺激。而在希区柯克的影片中,恐怖的刺激抛开了造型和审美,从更为原始、更为直接的色彩、声音、肉欲等因素上寻找恐怖的刺激点。在这一点上,它比《偷窥狂》那种过渡型的表现更为彻底和坚决。Baumann曾经这样来描写希区柯克这部影片中的谋杀场面:“在必要的时候,还要使用鲜血、谋杀、色情来帮忙,最好是‘三管齐下’。希区柯克便在他的著名影片《精神病患者》的淋浴镜头中心满意足地使用了呼呼作响的刀和汩汩流淌的鲜血(在完成的影片中剪去了刀子完美地刺进人体模型的镜头)。”[7]当然,希区柯克也要考虑当时观众所能够接受的上限,刀刺人体的镜头不得不进行删剪,因为当时的观众还不能够承受这样的视觉刺激,使用黑白胶片来拍摄这部电影,也是为了避免鲜血给观众的刺激过于强烈。尽管如此,当年成千上万的美国妇女,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不敢单独在家沐浴。不过,也有对视觉刺激的做法不表示赞赏的,伊伯特在四十多年之后的评论中便针对今天电影中视觉暴力过于泛滥的现象夸赞这部影片中那些象征式表现死亡的镜头。他说:“浴室一幕在今天看来有几个特点十分突出。与现在的恐怖片不同,《惊魂记》从未表现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血腥场面,也看不到遍体鳞伤的惨状,虽然出现了鲜血,但并不至于血流成河。希区柯克选择黑白片的理由就是他觉得观众无法承受如此大面积的血红(1998年格斯·范·桑特的重拍版则明显和这一理论唱反调)。片中也没有阴森恐怖的音效,取而代之的是伯纳德·赫尔曼尖锐刺耳的配乐。最后一组镜头则用象征性手法表现了死亡:先是血水打着漩涡卷入下水口的特写,紧接着镜头切到马丽昂凝滞不动的眼球,又是一个特写。这一幕直到今天仍然是影史上最震撼的凶杀镜头,它证明了场面调度与艺术手法比画面细节更重要。”[8]在我看来,对今天电影中暴力泛滥的批判无可厚非,但这样的夸赞并没有说出历史的真相。尽管在今天看来,这部影片中的鲜血、色情和暴力已是稀松平常,但这是因为1960年代之后的性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大大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所致,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当年人们在电影院中所遭受的震惊。正如施奈德所指出的:“珍妮特·利(玛丽安的饰演者——笔者注)穿着内衣在电影开始时登场。此处的性暗示在当时看来令人震惊。”[9]这也是前面提到鲜血、暴力、色情“三管齐下”的原因,在今天的观众看来,影片中沐浴谋杀的一场戏是无论如何谈不上色情的。
之所以说1960年之前恐怖电影中恐惧元素的建构还属于审美的范畴,是因为这样的建构尚有一定的规矩和模式可循,也就是说,一个令人恐惧的形象不仅是来自某个任意的造型,同时在伦理上也一定会有可被追述的缘由;换句话说,是人的感知与认知被不可分离地熔铸于一体而形成了这样一个令人恐惧的(同时也是具有审美意味的)面孔,这可以说是一个被观众(包括创作者)所认定的基本范式。1960年之后的恐怖电影则与这样一种具有审美意味的恐怖之脸渐行渐远,旧日观念所依托的范式已经在社会的变迁中被颠覆,人们只能在感官的刺激中重新寻找恐惧的效果。这就是杨国荣先生所说的:“以审美经验而言,其特点在于不同于单纯的感性快感,而美感不同于感性快感的根源之一,则在于前者(审美经验)的形成与一定的审美标准相联系。”[10]
恐怖电影中人物容颜改变与故事构成一体化的特征从1960年开始瓦解,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不再将容颜的扭曲作为恐怖的核心因素,在影片中最为恐怖的浴室谋杀情节中,恐怖的杀人者只是一个背光的轮廓,恐怖的元素被分解为暴力、鲜血以及色情施虐等不同要素。恐怖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物和故事分离,故事并不必然指向这些恐怖元素,如果我们把《精神病患者》中的恐怖元素去掉,它也能够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不过不是恐怖电影,而是推理电影,恐怖元素与故事不再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在今天人们的眼中,《精神病患者》已经很难被称为恐怖电影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人们开始从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从绝对主体的角度来理解人的时候,人们便把自身与外部的事物置于了一个价值相对平等的地位,存在的本身有赖于他者才能呈现,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于是恐惧便不再能够委身于一个实体的面容(如诺曼双重人格彼此混淆)。或者说,人们心目中旧有信仰世界(上帝和魔鬼,天堂和地狱)的崩塌,使他们不再能够相信一张面目丑陋狰狞的脸便是他们心中恐惧的替代者(如果没有魔鬼和地狱,那些恐怖的面容从何而来?),因此也就不再需要建构一个系统(人物、故事)来对此进行说明。当然,对于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如克尔凯郭尔、尼采这样的人物来说,对于主体的信仰早已不在,笛卡尔、黑格尔等先哲反思自我的存在甚至更早,但他们的思想为一般人所接受,成为被普遍接受的思潮和观念,还是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似乎只有在战争的废墟上,人们才能够理解“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一种他所不是和不是他的存在”(萨特)。[11]而这样的思想要渗透到电影这样一种大众文化媒介之中,则需要更多的时间,要到1960年。这是因为,走向现代化工业的社会,在这段时间中实实在在地改变了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人们从家族手工业、农业这样的家庭化生活,被形只影单地抛到了无所旁依的都市人流之中,过去那个令人敬畏的外部世界似乎已经被人类彻底征服,它已不再是一般人所焦虑关注的对象,人们的生活形态和信念被彻底改造和重塑。正如罗洛·梅所指出的:“一些心理治疗师已经指出,越来越多的患者表现出了精神分裂症的特征,而且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精神问题类型不是像在弗洛伊德那个时代一样是歇斯底里,而是精神分裂症——那些分离的、毫不相关的、缺乏情感的、倾向于人格解体并通过理智化和技术阐述来掩盖他们的问题的人的问题……分离的、孤独的、异化的人格类型不仅是神经症患者的特征,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中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的特征,而且在过去的20年中朝向那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得到增强。”[12]也就是说,今天的人们已经从心灵的深处被现代社会所改变。他们即便不是面对一个破碎的有待疗治的自我,即便没有存在主义的理论说教,他们对离散的、并非具有清晰来龙去脉的一体化的恐惧也已经能够有深切的体会,战后西方经济的飞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加速了传统社会心理的解体。一张狰狞的脸的恐惧在生活中随时都有可能遭遇,再也不需要一个完整的故事将其打造成坚固的、恒久的形态。“容颜故事一体”的模式就此解体,成为历史的过去。这就如同《精神病患者》中的女主人公,只不过是因为一时的心血来潮,便卷走了老板的四万美元,然后很快又后悔,想要把钱送回去。她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生活的目的是钱,也可以不是钱,人在压力下可以很快改变,并不需要太多的信念。生活于现代社会的现代人已经不再习惯于把自己的思想延伸到非现实的精神世界之中刨根问底,社会伦理观念的改变致使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大部分成为了多余,“恐怖”作为一种类型电影的元素,已经不再是克尔凯郭尔所描述的那种对于总体人生的反思,而是简单的感官刺激,一种消费行为,一种牟利手段,与对人生的畏惧和思考失去了关联。
从《精神病患者》之后,恐怖片开始走上了“重口味”的道路。在瑞士和德国制作的影片《开膛手杰克》(Jack the Ripper,1976)中,人们可以看到手术刀切割人体的画面,杀人者既是一个善良的医生(他宁愿自己的生活窘迫,也不愿意抛弃穷苦的病人),也是一个残忍的杀手。而美国导演帕尔玛制作的《剃刀边缘》(Dressed to Kill,1980)则是用鲜血向希区柯克的致敬,因为影片中出现了剃刀、浴室杀人、人格分裂等希区柯克式的经典场景和人物设计。更不用说还有许多“血肉横飞”的系列杀人电影,如《德州电锯杀人狂》(The Texas Chain Saw Massacre,1974)、《月光光心慌慌》(Halloween,1978)等。一个新的、纯粹消费恐惧的恐怖电影时代就此开启。
当然,“容颜故事一体”的解体并不等于这样的形式在电影中不复存在,而是说这样的形式不再是一种无可选择的必然。人们还是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创作恐怖电影,只不过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这样的方式已经不是唯一通向恐怖感受的途径,而是被分解成了诸多方式中的一种。也许我们还是会怀念1931年《科学怪人》对于未来的思考,怀念善良的科学怪人遭遇了不公正的对待,正如1994年版的《科学怪人》(又译《玛丽·雪莱的弗朗肯斯坦》),完全按照原小说的故事来建构电影,比任何一个电影版本的《科学怪人》都更为靠近200年前人们的思想,成为了一种经典的怀旧样式,这显然既不是形式手段上的匮乏(影片中也使用了部分感官刺激的手段),也不是观念上的倒退,而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感官刺激的方式,或者感官刺激的方式可能已经使人们感到了疲倦,在我们抗拒扑入眼帘而来的画面时,用眼睛来寻找我们所需要的恐惧也会是一种乐趣。
[1]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文集: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88,289.
[2] [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52.
[3] 李锦山,李光雨.中国古代面具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130.
[4][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51.
[5] [美]多萝西·胡布勒,托马斯·胡布勒.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6.
[6] [美]托马斯·奥斯本.启蒙面面观——社会理论与真理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
[7] HansD Baumann. Horror-DieLustam Grauen[M].Im Wilhelm Verlag GmbH & Co KG:Muenchen,1989:82.
[8] [美]罗杰·伊伯特.伟大的电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32.
[9] [美]史蒂文·杰伊·施奈德.有生之年非看不可的101部恐怖电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117.
[10] 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42.
[11] [美]罗兰·斯特隆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520.
[12] [美]罗洛·梅.存在之发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