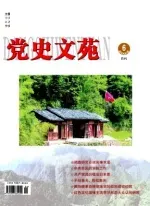毛泽东的新村主义理想在新中国城市空间的实践
朱 斌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广州 510642)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共产党领导权威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新政权开始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以工人新村为代表的城市住宅在20 世纪50 年代逐步发展形成。大量建造的工人新村伴随着新中国各项社会制度的逐步建立、调整和完善,深深地扎根于城市生活空间,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也蕴含着意识形态的意蕴。
一、新村主义溯源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新村”一词属舶来品,始于法国和日本。法国无政府党人亨利·孚岱于1903 年曾在法国与比利时接壤处试办“鹰山共产村”。1910 年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杂志上开始宣传新村主义,他将“新村”描述为:“我们想造一个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喜,便是我的喜;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各人应该互相帮助,实行人的生活”;“只有各人各尽了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能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这一法才能像幸福的人的生活。”[1]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与武者小路实笃通信,较早接触了新村主义思想,并对新村主义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创始者的热心毅力是相当可以佩服的,而且那种期待革命而又怀忧虑的心情于此得到多少的安慰,所以对于新村的理论在过去时期我也曾加以宣扬。”[2]P370周作人于1919 年7 月参观日本九州的新村后,在其《访日本新村记》中写道:“我自从进了日本新村已经很兴奋,此时更觉感动欣喜,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现在虽然仍在旧世界居住,但即此部分的奇迹,已能够使我信念更加坚固,相信将来必有全体成功的一日。同类之爱的理论,在我虽也常常想到,至于经验,却是初次,所以令人荣醉,几欲忘返。”[3]周作人将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思潮带进了中国知识界。
新村主义引起了毛泽东、蔡和森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1919 年春,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后,提出了新村构想并草拟了新村计划书。他指出:“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4]P413在《学生之工作》中,毛泽东对新村社会做了较为具体的描绘:“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 ”[4]P413
新村主义理想对毛泽东等早期共产党人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当时中国社会并没有实现新村主义的土壤,新村主义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理想。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对于绝对的自由,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5]P147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了对这一理论的追求,重新寻求新的救国方案。
二、新村主义在新中国城市空间的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新政权逐步开展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工作,并将工业化作为恢复与发展中国经济的重要任务,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成生产型城市。由于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然而,在工人政治地位提升的同时,城市居民特别是城市工人家庭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短缺。因此,缓解住房压力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一大紧迫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居住情况严重分化,少数显贵及资产阶级住的是花园洋房,与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相比形成了强烈反差。“如果用状况较好的住宅总面积除以居民的总人数,得出的平均值已经很低了。但对于最穷苦的人,可供居住的面积还不到2 平方米,仅够放一张单人床。还有些人上无片瓦,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学徒或小贩夜里就睡在他们白天工作的商店的柜台底下。”[6]P150众所周知,住房是家庭和生活的基本场所,也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基本要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1 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党和新政权将住房重建计划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提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需要。”[7]P131“一五”计划开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性城市的原则下,工人新村成为这个时期城市住宅发展的主要途径。以上海市为例,“1957 年居住房屋总面积比1950 年增加了480 多万平方米,其中工人住房占57.3%”[8]P33。由于建设规模宏大、风格鲜明并主要服务于工人阶级,工人新村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其主要目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迅速组织起一支生产大军,组织起革命的身体更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服务于一个民族国家的工业现代化的梦想”[9]。1952 年5 月,新中国第一个工人住宅群——上海曹杨新村首期工程完工。随着工业化建设的发展,以居住产业工人为居住对象的“工人新村”住宅,成为中国城市居民最先进的居住方式。如上海曹杨新村、济南的工人新村、沈阳铁西区工人住宅区、北京西郊百万庄住宅区、鞍山的工人住宅区和天津中山门工人新村等。
从上可知,毛泽东早年的新村主义理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浮出历史水面。正如李锐所指出:“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荒芜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思想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30 年后毛泽东得以在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展开这一理想图,莫里斯·迈斯纳认为这正是毛泽东主义向“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一种回归。[10]P70
三、工人新村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嵌入
建筑是居住空间的重要物质载体,但建筑空间决不是中性的,权力的诸种关系嵌入到社会生活的空间,往往使其具有意识形态的意蕴。事实上,新中国工人新村中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容。
首先,工人新村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党和新政权看来,“建造住房”首先是体现“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因此,缓解住房压力只是1950 年代建造工人住宅的目的之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新政权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为工人建新村来履行“工人阶级当家作主、依靠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城市”的政治承诺[11]。“阶级”观念的引入使得城市住房问题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作为市政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工人住宅,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新政权对工人阶级的特殊政治关怀,另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新政权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城市空间的实践和建构。
“工人阶级”代表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领导阶层,这一名词在新中国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他们的处境和生活状况具有相当程度的象征性。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2]P2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真正登上了社会主义城市的历史舞台,党和新政权将它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投射到新中国城市空间的面向上。工人新村的建立,满足了社会主义对城市改造的政治诉求:一方面,工人新村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符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另一方面,工人新村充分体现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使他们积极投入到“生产型”城市建设之中,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贡献力量。[13]工人新村的建立让工人体会到当家作主的感觉,把宣传意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落实为具体的生活感受。当时,能够住在工人新村可以说是一种身份的象征、社会地位的象征,新村居民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从上可知,工人新村的象征符号意义不亚于其实际的居住功用,其映射了工人阶级在城市社会空间的地位,作为工人阶级翻身做主人的标志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被迅速认同和复制,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开来。
其次,工人新村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工人新村的建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既属于消费领域的住房建设,同时也是服务于新中国工业建设,受到生产(工业化)与消费(住房)关系的影响。1949 年3 月17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我们已经解放并将继续解放许多大城市,为适应这种情况的变化,必须把过去先乡村后城市的做法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把城市工作做好的中心环节是迅速发展和恢复城市生产,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14]在生产城市的影响之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设计是以“先生产、后生活”为基本原则,“生活”成为“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也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大工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穿越,“组织化”的“生产”形式和“生活世界”的重建之间具有了特别密切的关系。[11]即工人新村为城市工人提供了一种服从于且服务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需要的新住宅形式,这种新的住宅形式具有意识形态的意蕴。
在建造工人住宅的同时,一系列配套公共设施也同时兴建。从新村的空间布局来看,其规划理念如下:“把为全村服务的商业文化、行政机构集中设置,其中设立各项公共建筑,包括合作社(商店)、邮局、银行和文化馆等,组成新村中心。”[15]睡觉之外的其他生活需求几乎都要借助于公共空间,这一模式的兴起有力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中国城市的空间和肌理。20 世纪50 年代新村工人的生活中,一方面通过降低住房标准(缩小私人空间)和公共化私人空间,缓解了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与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服务设施网点系统性的组织,把新村工人日常生活安排在一个以居住区或小区为单元的集体化生活网络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生活空间越是被压缩,国家的意志也越能通达至底层。“工人新村”这样的新居正是一个自愿、互助的集体化生活空间,所有生活便利将由生产财富的工人阶级全体公平分享。工人新村的兴起正是解放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的体现,展现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城市想象的深层面相。○
[1]周作人.日本的新村[J].新青年,1919 年6 卷3 号.
[2]周作人.周作人回忆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3]周作人.访日本新村记[J].新潮,第2 卷第1 期.
[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5]新民学会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华揽洪.重建中国——城市规划三十年(1949—1979)[M].李颖译,华崇民校.北京:新知三联出版社,2006.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8]丁桂节.工人新村:“永远的幸福生活”——解读上海20世纪50、60 年代的工人新村 [D].同济大学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
[9]李芸.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想象:从《上海的早晨》中的城市景观谈起[J].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6(01).
[10][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宁,陈铭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罗岗.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工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6).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3]罗岗.十七年文艺中的上海“工人新村”[J].艺术评论,2010(06).
[14]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N].人民日报,1949-3-17.
[15]何丹,朱小平.石库门里弄和工人新村的日常生活空间比较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