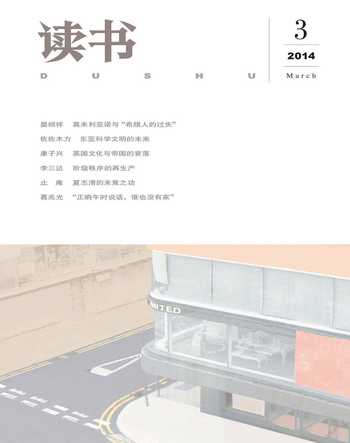拾穗风俗的延续与消亡
张旭
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纪晓岚记载了这么一个场景:乡村麦熟时节,妇女儿童数十人为一群,跟在开镰收割人后面,收所残剩,谓之拾麦。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作者说其事远见于周雅,确切的记载是在《诗经·小雅·大田》篇中,作者还说“遗秉”、“滞穗”,是寡妇之利。
对这一社会现象,唐代的白居易也曾写了《观刈麦》一诗予以记叙。
这种行为传统由来已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我上小学时也曾干过这种事。在当时,与农耕文明初始一样,仍然是体力密集型的农耕劳作。
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但仍然是生产队时期,有一点变化是,把生产队的规模再划小,分成几个生产小组。作为农业机械化标配的大型拖拉机在大队里有,几乎没用过几次,露天摆放久了,成为一堆废铁,在八十年代中期人民公社与生产队解体与实行承包制后,这堆废铁也不知所终。小型手扶拖拉机条件较好的生产队有,但也是经常坏。耕牛犁铧翻斗水车和各类传统手工农具仍然是主流,在日常生产劳作时频繁使用。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看到西汉时期普及的犁铧、东汉时期出现的人力翻车又叫龙骨水车之类的插图,我一点都不陌生。
顺便一说,任何一种新技术的普及,只要有一条始料未及的条件不具备,都有可能成效为零甚至因造成损失浪费成效为负。在集体化时期的农民,对各种长官意志是既敬畏,又因对各项政治运动形式主义长官意志无法充分理解而在私底下予以藐视,他们中相当多是文盲或刚过扫盲线,但根据其目的(关键探究也在于其目的),行为却是充分理性,反智论在农村基层有深厚的土壤,这也是重要根源之一。其实,将一项适用新技术完全普及的工作,也应该是属于创新范畴,其推动者与推动者群体的历史价值与历史贡献,应不亚于全新技术的发明者,这一观点,至今仍然鲜有提及。
但粮食总有一点不够吃,这是肯定的。在饥饱两个绝对程度,也就是在0和1这一区间内,是间杂着严重程度不等的很多种类型的。白居易在他诗中所揭示的情形是一种,纪昀所说的“故四五月间,妇女露宿者遍野”,甚至“盗窃攘夺,又浸淫而失其初意矣”是另一种更为严重的饥馑类型。他在这一条记叙中接着说了一个假托鬼神的故事,这些妇女露宿者竟然“侑酒荐寝,每人赠百金;其余亦各有犒赏。媪为通词(淫媒),犒赏加倍”,导致“贪利失身,乃只博一饱”。与其说反映了人心不古,注意下纪昀是生活在清代康雍乾时期,史称“康乾盛世”,毋宁说反映了在生产力没多大变化的前提下,摊丁入亩制度推行导致高水平均衡陷阱(Mark elvin)更为凸显的社会现实。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一时期,情形与历史时期相比,饥馑程度无疑要减轻很多,没有“大饥荒”年景那么夸张。虽说没挨过饿,虽然粮价便宜,但票证流行并缺少现金,农户的主粮还是主要靠初级分配(处于城市郊区以专事供应“菜篮子工程”的菜农有所例外),消费的主粮仍然要粗细兼杂。秋冬时节以红薯煮粥为早饭,南瓜饼地瓜干红薯或绿豆粉条是间杂主餐。春荒时节的野菜,如荠菜、马兰头、马齿苋、蕨菜与蒲公英的嫩芽之类,也经常由家中的妇孺自行采集,烹熟后摆上饭桌(现在这些可是农家乐餐馆的招牌菜)。只要粮食没有达到充裕程度,对粮食的禁忌行为也很明显,当时一般的农户都会养少量家禽家畜,它们的主食是麦麸谷糠与野菜,还有从城镇饭馆里挑来的泔水,如米汤之类。在那时的观念中,自己如有剩菜剩饭让家禽家畜和家里的猫狗“开荤”,那也是属于浪费粮食之举。以饲料喂养家禽家畜作为商品牟利,是后来专业养殖户出现的事儿。
因此,妇孺历来因无法替代只能是体力密集型农业生产劳作的辅助。一切劳作都是以温饱为目标,妇孺虽然是辅助,但这个辅助是相对无法替代沉重的重体力劳动而言的,在每天劳作时间上并不短甚至还要更长更为辛苦。我还记得在这一时期有几个中老年贫苦的农妇在卖粮时节,从黎明到黑夜都在国营粮食收购站帮忙。粮站收粮对谷麦的品质有硬性要求,在称重入库前,卖粮农户必须用人力风谷车将干谷麦再扇一遍,这就必须要有人帮忙。她们帮忙的收益是混杂在秕谷废弃物中的谷物归她,其实这也是另一种“拾穗”行为。
家庭土地承包制和杂交水稻的完全普及,是距今三十来年才出现的事情,制度与技术的配合无缝对接,使粮食单产与总产量的提高,使中国人普遍告别了饥饿。只要制度不再出现问题,因为饥馑荒年为口吃的导致“人情渐薄,趋利若鹜,所残剩者不足给,遂颇有盗窃攘夺”和因粮食供应不足导致饥饿发生的民变绝迹。
这是农耕文明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这一事件,使“八亿农民搞饭吃”,也就是体力密集型传统劳动生产方式下的饥饿型贫困成为历史的终结。饥饿型贫困,是农耕文明下传统中国最大的国情,现在则取而代之以如何解决可支配现金缺乏性贫困和城镇化时代大潮的兴起。原来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道统”认为,家庭经营这一生产方式是落后的,不是被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取代,就是被社会主义大生产替代。回过头来看,杜润生团队小心翼翼使“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得以推行,制度建设的贡献价值并不比划时代的完全科技创新少。这一点即使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也曾在《德意志国家形态》中说道:“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回过头来看,技术视野条件下的中国农耕文明延续时期之长,鲜有变化,几如静止,对“天不变,道也不变”这一根深蒂固的强大观念也似乎可以有基于历史同情的理解,但从近代以来制度革命制度变迁的时代要求上着眼,由于近三十年来技术革命带来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从七十年代末主粮短缺二三成的普遍情况向现今主粮消费由量到质进行转变,包括拾穗行为在内的一系列“传统古风”也告消亡,如果一味对此视而不见,那就意味着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了。
(《中国农民变迁论—试探我国历史发展周期》,孙达人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10.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