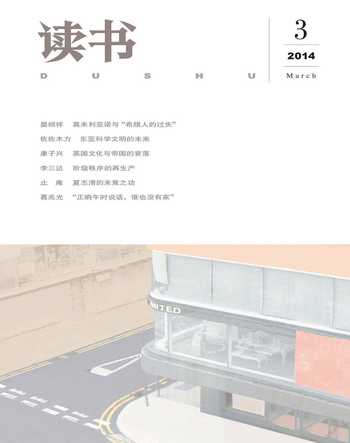看那匹苍白的马
张承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人读书,对外国文学开卷有益。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我也时而读些翻译小说,意在呼吸些舶来的新鲜空气。读过什么忘得光光,唯独记得在上海一个翻译杂志上读过的一个故事,准确说是一个印象,被我下意识地记忆了二十年。
细节早已漫漶不清。但其中描写了一个国际势力组织各种人才,分工合作,拼凑出一部世纪文学名著的故事—使我不能忘怀。长久以来,它给我以持续的刺激,使我牢牢记住它的那个离奇的思路和不祥的形象。尤其题目,那书题如一个镂刻的浮雕,如一帧黑白悖反的胶片,令我长久地忆起。题目大约译为“瞧那匹灰色的马”,作者是日本作家五木宽之。
—就这么,在保留了对它的二十年印象之后,我趁一次去日本的机会,把它重新买到了手。
先是小说的题目需要吟味。
日文的书题是《蒼ざめた馬を見よ》,确实可以译为“瞧那匹灰色的马、看那匹斑白的马哟”。只是,有一个颜色的问题不易说明。
也许日语暗暗继承了阿尔泰语游牧民族对牲畜色彩表达的基因?这个“蒼ざめた”带来的古怪感觉,用汉语说它不清。倒是蒙语中有贴切的对应。“撒了”(saral)在蒙语中是最常用的描述白马的颜色,但那只是一种不纯的白,编字典的蒙古人居然用“污白色”来表达。 “薄了”(būrul)则更文学化,它用在马以外的描写时大都是褒美的。它的含义并不是白,却常用于白,比如翻译“白毛女”一词用的就是它(būrul huhen)。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类马往往不是民间文学赞美的对象;因为一匹不太干净、斑驳杂白的马一掠而过,给人的视野和心里留下的—是不悦的感觉。
所以拿蒙语的色彩感觉来理解这个书题,就多少有了一点必要。因为拥有类近(甚至更强烈)的语言心理,特别对这一篇乃是读解的条件。在这篇小说中,为着要强调一种禁忌和不祥,语言的色彩含义被加强和深化:一匹掠过视野的马,它带着惨白、浅灰、斑驳、污浊的白颜色—于是紧张的感觉被大大夸张、而且宗教化了。
一个意象就这样建立起来。那是一匹古怪的、颜色非青非白的马,倏忽掠过了视野。
它是谁?它是什么?
谁都这么问。就连我,只是因为给人讲这个读来的故事,不知被朋友们问了多少遍。
但我想,若想找到答案,恐怕要耗尽探索者的人生。小说并没有提供清晰的解答。它只是把一个灰白怪马的意象塞入读者的视野,并让他们从此心绪不宁。就像小说中写的,这些读者也似乎—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叙述这个梗概会嫌太长。但梗概一交代完,该写的也就差不多都写了。
梗概大体如下(引号内仿体部分为原文):
某大报的年轻记者鹰野,一天被上司(报纸的社论负责人)叫去谈话。上司并不开门见山,只是饶有兴趣地问及鹰野参与工会活动的事,尤其对鹰野主张的“绝对的言论自由”再三确认。之后,上司拿出一个大信封,让鹰野自己读里面的内容。
这是一封长信,是一个身患绝症即将辞世的日本老学者的临终遗言。
信中讲到,他曾在苏联索契黑海边的度假地,偶尔遇到了他一直倾心研究的苏联文学大师米哈伊诺维奇。他冒昧上前问候,但却遭到拒绝,大师不承认自己是米氏。
日本老学者无奈默默离开,但苏联老作家却又找上门来。他把一个篮子托付给日本人,里面是他的生命之作。他说此书已无望在苏联出版,因此请求日本知音能伸手相助,把作品拿到西方世界出版。
老学者彻夜读完了篮子中的手稿。沉吟良久,最终这位日本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不敢涉险政治,婉言回拒了老作家。
时光飞逝,老学者一直因自己对终生热爱的俄罗斯文学的背叛而痛苦不堪,此刻行将就木,他把此事托付给自己的终生密友即报社负责人,希望他能完成自己的遗愿,救出那部世纪之作。
主张绝对言论自由的鹰野,乃是被选中的赴苏联取手稿的人选。他在大学时期就是俄罗斯文学专业的学生,而且对大师米氏尤为喜爱。一诺既下,他从报社退职,只身飞往苏联。
到达后他两次登门造访,均吃闭门羹。米氏不仅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大部头手稿,更宣布不认识什么日本老学者。
鹰野在闷闷不乐中,一个犹太女孩奥列伽靠近了他。一夜情后,得知女孩恰是大师米氏的家庭秘书!鹰野虽觉蹊跷,仍不管那么多,径自要求女孩帮助他见到大师。于是,一个深夜,女孩领他到了曾吃闭门羹的公寓门前。
女孩开锁入门,两人摸入漆黑走廊。似乎听见隔壁响动。但一进客厅,童颜银髯的大师米氏正端坐等待。俄国老作家谈起了索契海边与日本老学者的往事,又为对鹰野的拒绝道歉,接着取出一个篮子,里面正是那部手稿。
鹰野回到宾馆,连夜把书稿拍成了胶片。接着又托使用外交护照的日本人,把书稿带出了苏联。
那以后,一部奇书在全球轰动。
此书先在日本匿名出版,题为《看那匹苍白的马》。附言说,手稿是一个有良心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带出苏联的。仅迟于日本一周,英译本问世。瑞典著名大社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在欧美读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事情的发展如雪球飞滚。《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一个自己把俄罗斯选为祖国的、三代犹太系俄罗斯公民的故事……如果这部作品应该获奖的话,那么究竟该把奖授予谁呢?我们期待着苏联文化界能进步到—使如此名著之作者能公开自己的姓名和地点。”
德国杂志则推理般地猜测作者是谁,分析他与普鲁斯特、卡夫卡等犹太作家的精神和血缘谱系。巴西杂志则更带拉丁式的浪漫,根据独家的消息大谈“勇敢的日本记者放弃一切金钱要求、拒绝美国出版社高价购买书稿的经过—这一武士式行动”。
紧随英译本,德、法、意等共九国语言译本逐一问世。好莱坞大腕制片人M.詹姆斯宣言要把它搬上银幕。“《看那匹苍白的马》的问世,令人惊叹地、巧妙地波及着电视与广播。它宛如把全世界的媒体都作为对象,在进行它的宣传活动。如此有组织地、强力和急速地,作品的话题扩展到了全世界。”
三个月后,又一个消息震动世界:著名的苏联老作家A.米哈伊诺维奇突然遭到逮捕。罪名是在海外匿名出版反苏小说《看那匹苍白的马》,非法获取巨额美元。
媒体再次亢奋,米氏照片登载于全球各大报。不仅媒体,连亲苏的文化团体也大声抗议,呼吁言论的自由。国际的签名声援已经开始,甚至各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纷纷声明,谴责对米氏的逮捕。左派团体因对米氏评价的不同,发生了混乱与分裂。紧接着,苏联公布了在米氏公寓里发现的书稿打印件、打字机、大批美元、瑞典出版社的支付证明、约稿信等等物证。而米氏本人则表示对一切毫无所知,尤其不承认此书是他的作品。
苏联开始了审判程序,公审日正在临近。西方则口诛笔伐大行抗议,伦敦《泰晤士报》发表的关于立即释放作家的请愿书上,四十九名欧美各国一线作家的大名赫然联署。在公审开始之前,苏联已经陷入彻底的孤立。
话分两头。
鹰野在去年那场现代版的武士行动之后,莫名地陷入了一种孤独。他被安排到一家广播公司担任闲职,每天干些可有可无的杂务。他变得沉默寡言,早从工会活动抽身,并开始考虑结婚过日子。
在他弄到手的这部书稿被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他体味到一种微微的不快。他自学生时代就由衷喜爱的米氏,应该是一位“与煽情主义处于对立之另一极”的作家。而《看那匹苍白的马》“搭乘着庸俗的商业宣传,一路成为快卖榜首,给他带来一种生理的厌恶感觉”。
他回忆年轻时的初读。那时令他感动的原因是 “作品有坚实的结构,又被绵密的细节所支撑,怎么看都有那种俄罗斯文学的庄重安定感。而且一些情节,早已是超越描写的、在深处闪烁般的真实”。
但是此刻读着,却觉察出一种微妙的相违。在这部长篇里,没有他熟悉的那种贯穿于米氏文学中的东西。米氏作品中,随处永远都藏着一种使作品不再安定的、黑暗裂缝般的虚无感。因此小说失去安稳,给人动荡的感觉。这正是鹰野被米氏文学吸引的原因。也许可以说,那是“过早看够了不应该看到的世界的人的干渴的虚无主义”?
“但在《看那匹苍白的马》里,却没有它。有的只是剥露的愤怒,只是对犹太系国民的悲惨命运的、活活的抗议。虽然也能使人感到超越种族响彻人心的痛切,但那与昔日给他以撕咬般刺激的米氏,总之并不一样。或许,他甚至想,这个作家本质上只是一名短篇作家?也未可知。”
在米氏被捕的媒体喧嚣中,鹰野最不能理解的,是米氏居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作者。这怎么也不像米氏。但是苏联方面接续公开的物证,尤其是西方出版社的支付证明和美元现金等物证,使鹰野如陷云雾,困惑不已。
而小说的戏剧性,才刚刚开头。
一天,有一个叫丹尼尔的外国人来访。他开门见山,说因俄国作家米氏的问题,想请鹰野去见一个人。鹰野摆出生硬的拒绝姿态。丹尼尔说:那么你将一生都不明白自己干的事。于是鹰野坐入了他的车,径直开到了横滨。登楼进入一间密室,里面坐着一个人—
居然是米哈伊诺维奇!
鹰野目瞪口呆,丹尼尔娓娓道来。原来,在列宁格勒拒绝了鹰野的米哈伊诺维奇,乃是真的米氏本人。他拒绝,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写过什么世纪奇书,也不认识什么日本老学者。而后来鹰野和奥列伽穿过黑暗走廊在客厅里会见的米哈伊诺维奇,却是一个深夜出演的波兰难民。他在一个“巨大的组织”的指挥下,先在美国某医学院的研究所里接受了整形手术,把相貌变得酷似米氏;然后又在一个著名排演场,在世界闻名的好莱坞名导R的辅导下,学会了所谓作家的行为套路,并谙熟了米氏大师的举手投足—最后他坐在米氏的客厅里,等着日本武士的到来。
而真正的大师米氏及其夫人,那一刻却已被奥列伽一伙的蒙汗药放翻,正在隔壁房间里昏睡。所以穿过黑暗走廊时,鹰野曾觉察隔壁有动静。奥列伽则是一个“坚信自己的犹太双亲均死于苏维埃之手”的年轻女性。不用说,她从鹰野进入苏联时就盯上了他。
“说到底,这不过是从美第奇家族以来就一直反复进行的、所谓知的战争的一例而已。”丹尼尔继续解谜。哪怕苏联正出现柔软的迹象,西方国家想把“共产主义无自由”的标语,按月地钉进世界大脑的总方针不会变。于是,早与“巨大的组织”关系密切的报纸社论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出色的发想:伪造一封日本老学者的临终遗书、虚构苏联文学大师米氏藏有一部世纪奇书而不得出版的故事、并使用日本人启动预案。由日本人操刀,可以不负责任地达到效果。舆论大哗后,他们又利用预先放置在米氏家中的种种物证,把老作家推向风口浪尖。苏联老作家就这样因为一部自己全然不知的“自己的大作”,被推上了专制的审判台。米氏骚动方兴未艾。即便就在今天早晨,丹尼尔说,一家杂志还在谴责专制,说“东方的内部就是如此” 。
核心的情节是:
“那个组织秘密地召集了反苏作家小组。他们用美元买发言,收集了苏联的犹太人问题资料。然后以讨论的方式,让这一作家小组进行长篇小说的制作。他们对米哈伊诺维奇彻底地进行了文体、用语、比喻、会话的研究,当然也绝不能小觑大型电子计算机达到的效果。成为这一部伪作的基础的,乃是一个犹太系难民的无名作家所写的某一家族的历史。组织买下了它,委托专门的作家小组对之进行细部的打磨。之所以那部小说有一些情节很感人,乃是因为还残留着原作的真实。而使作品的结构与文体都扎实像样,也许就得说,那是专业小组集体加工的成绩了!……”
这个组织是CIA吗?谁都要这么问了。
小说答曰:
“这不是一国的情报机关,它是联合了世界自由主义阵营的、统一阵线式的国际组织。”
丹尼尔接着自称:他本人,就是采取与如此谋略相对抗的立场上的一个专家。后文中他又披露了自己也不是独行侠,也背靠着某个组织。他追踪一根根线索,几巡天涯海角,终于抓住了乔装大师的波兰人,并根据他的自供,弄清了这本世纪经典的全貌。
“无法相信!”鹰野大喊道。
“信与不信,随你的便。”
如此的作品,不能不使人重新把目光对准作者。
作者五木宽之接着写道:“在鹰野的眼里,看见了一匹苍白的马。”
如果说五木宽之的《看那匹苍白的马》是一本隐语或谶语之书,那么,这匹不祥的马就是最主要的一个隐语。包括小说的书题,包括戏中戏里那部集体制作的“世纪经典”的书题—随叙事发展和语境变移,这个隐语曾几次使用,含义不断扩展。
五木宽之不露声色地表明了他对短篇小说的观点。
本质上因思想的含义以至于无须拉长篇幅的作品,就是短篇小说。当然,这一借对米氏的感悟写出的概念里,藏着五木对自己这部作品的自负。确实,如此的纸短角多、说清它要说得口干舌燥,其实文库本不过百页。按中国的小说划法,就在小中篇与长短篇之间。
苏联的黑幕专制、与揭露这一专制的国际黑幕;死亡与悲剧的记忆、与一种利用记忆的谋略。在圣经故事中,也有“死亡骑着一匹灰马”的意象。但是难道它就是那种“巧妙得堪称艺术的恶意”、并且“以自由这一观念为钓饵,给世界设置了巨大的陷阱”么?
“过早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是小说反复点击的另一句隐语。
到底看见了什么?作者依然并不打算做出充分的说明,而是引出了另一句隐语:“今天烧哟,今天是烧的日子。”
小说在这里言及一个背景,它同时是小说主人公与作者五木宽之的背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十二岁的主人公被收容于北朝鲜的收容所。每天都有人死,尸体被集中一处等着火葬。每逢到了规定的日子,看守就敲着梆子,边走边喊“今天烧哟”,于是就把尸体拉出去烧。他目击过这一切,“过早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
北朝鲜收容所烧尸体的经历,与纳粹集中营的“烧”、更与西方宗教的“燔祭”遥相呼应。这一笔,夹在一个国际组织伪造营制的一本涉及犹太人历史的大部头构思里,使五木宽之这部短篇达到了相当的难度。
尤其那匹苍白的马。它时时掠过眼前,成了一个冥冥中居高威胁、但又被视为禁忌的意象。随着情节的发展,作者多次使用过这个意象。所谓不该看见的东西,随语境的变幻各有晦涩的所指。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西方文学艺术的先锋,先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迷信之,接着在八十年代摹仿之,后来却逐渐不以为然而最终选择了与之分庭抗礼,并进而在一切文化与政治的领域以批判其为己任—当他们突然回头,发觉早在一九六六年五木宽之就发表了如此一部《看那匹苍白的马》,他们瞠目结舌,只觉不可思议。无法不承认:不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哪怕在今天,这样的思想也是罕见的。
怎么可能呢?
五木宽之怎能拥有如此拔群、甚至堪称预言的眼光?他真的能被称为短篇作家了,凭着这俯瞰着人的认知规律的作品。
幸亏集子中的其他作品,都是“正常的”也即平常的篇什。否则我们就真碰上预言家了。我还没有读过这位作家的背景或个人历史。从文库本扉页上的作者简介得知,《看那匹苍白的马》虽不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早期的最初(动笔第二年)作品。再之前,他有日本战败后在北朝鲜囚禁九死一生的少年经历。他显然对俄罗斯有着独特的把握,而且并非只因出身于俄语专业。他对西班牙内战的观点几可称为“思想卷入”,对共和派倾注了很深的感情。但是,单凭这些,还不能解释“那匹苍白的马”。
凭这一篇可以猜测,他可能是最重要的作家。当然由于这一篇的木秀于林,对它的个案研究应该是一件长期作业。我预感,揭破和究明他的精神履历与思想构成不会是一件简单的事,显然知识界对此远没有足够的基础准备。顺便再抄一个信息:五木宽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说:“美苏冷战结束后,将出现未曾有过的反动的季节。”(新装版第317页,解说)
又是一个惊人准确的预言。
也说不定,他在起步之初得到过一种深刻的启蒙、或者一语点破的指点。总之现象就是这样,他用一匹苍白色的马,提醒世界正临近的危险。当然世界没有留意、甚至根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这对于作者,或许未必一定是一桩坏事。倒是我对自己二十年一直记着他这件事饶有兴趣。找来原作读后发觉,当年怎么吃惊,今天就还是怎么吃惊。
究竟什么才是五木宽之投身文学时的思想焦点呢?换句话说,在他那时的视野里闪过的、那匹不吉利的白马,究竟象征着什么呢?
不知道。如书题的呼唤,我们唯有注视而已。
我们只能追随着—作者潜意识中因阿尔泰语言基因的暗示、写出的那匹“蒼ざめた”saral或者būrul色的联想,注视那匹追逐着我们的不祥的马,看看它最终要带来什么。
二零一三年岁末,日本归后
(引文均见《蒼ざめた馬を見よ》,文芸春秋社二零零六年十二月新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