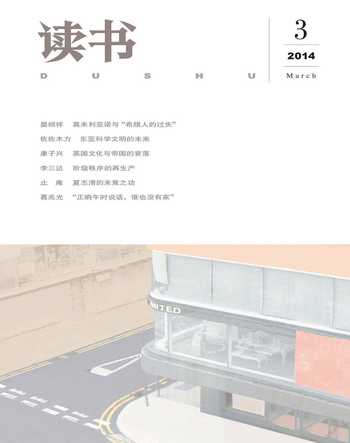老兰培需要一个上帝
曹卫东
曾经,在法兰克福,有一幢并不起眼的五层楼建筑,竟是这座大都会的三大标志性建筑之一。它就是苏卡普出版社,在当代德国知识地图上,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坐标,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苏卡普文化”(Suhrkamp-Kultur)。然而,二零一二年底以来,苏卡普深陷于股东之间权力纠纷的危机之中。二零零六年底,汉堡媒体商人巴拉赫(Hans Barlach)入股苏卡普,这场“精神与金钱的聚合”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从那时起,苏卡普内部的权力斗争,或者说,保卫苏卡普文化的斗争,便拉开了序幕。这位新股东与老股东贝尔凯维奇在经营理念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关键在于,在以亚马逊和企鹅—兰登书屋为代表的大型出版商时代,独立的中小型出版社如何能够实现自身的繁荣。在巴拉赫看来,出版社即便不是螺丝工厂,同样也要遵循经济法则。贝尔凯维奇则有一批作家盟友,他们谴责巴拉赫鼠目寸光,只认眼前利益。两位股东都想把对方排挤出董事会,直到闹上法院。二零一二年底,巴拉赫向法院递交申请,要求解散董事会,一时间满城风雨,曾经的“日不落图书帝国”到了风雨飘摇之际。
权力斗争漩涡当中的苏卡普危机,显然更吸引眼球。相形之下,另一场文化危机显得波澜不惊。媒体平静地报道,二零一三年六月,于二零零六年收购下布罗克豪斯出版社的大康采恩贝塔斯曼做出决定,终止其辞典项目,拥有两百年历史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ädie)不再发行印刷版本。似乎,《布罗克豪斯》早该寿终正寝了,没什么好惋惜的。“再见,《布罗克豪斯》”,这种轻松的口吻构成了媒体为布罗克豪斯送终时的基本姿态:没有《布罗克豪斯》,我们有维基百科;而正是维基百科,埋葬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布罗克豪斯》。
十八世纪中后期,出版业已开始冲破王政时期书业管理制度的藩篱,并且脱离了造纸业、印刷业和零售业,成为一个自成体系的独立产业。这个时代不仅涌现出狄德罗和达朗贝尔这样的思想英雄,也成就了庞库克(Charles-Joseph Panckouke)这样的出版商。作为《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庞库克深谙,出版业的要义不在于满足社会需求,而在于提供社会需求。他通过各种营销手段,让《百科全书》大化天下,最终谱写了一段思想史传奇。出版业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洗礼,虽然没有像法兰西民族那般轰轰烈烈,但最终却积淀了一份厚重的精神遗产。在十八世纪,莱比锡便成为德国出版业中心,一年一度的图书展览会吸引了全欧的出版商。
一八零八年,布罗克豪斯(Friedrich Arnold Brockhaus)以低廉的价格获得学者吕贝尔(Renatus Gotthelf LÖbel)和法学家弗兰克(Christian Wilhelm Franke)合著的六卷本百科全书的版权。辞典甫一问世,便大受青睐,布罗克豪斯余生不得不疲于应付盗版商的侵扰。一八一二年,不过短短四年,布罗克豪斯便更新出版了十卷本的第二版。可以说,这是一部为德国有教养的市民阶层量身订制的辞典。这是一个身份认同的标志,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许多人来说,它就是一张进入知识精英俱乐部的入场券。到了一八一九年,这部百科全书已经出版了第五版。凭借在商业上的大获成功,以“布罗克豪斯”为名的专业百科全书出版社就此诞生。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九年的第十版更名为《大布罗克豪斯》(Der Groβe Brockhaus),此时它已有二十一卷的体量。二零零五至二零零六年的第二十一版最终定名为《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这是由三十万个条目构成的篇幅达三十卷的庞然大物,而价格更是不菲,接近三千欧元。这是布氏的知识帝国最为辉煌的时刻。
“百科全书”(Enzyklopädie)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έγκύκλιος παιδεία,意为全面的或普遍的教化。在历史上,其所指时常游移于教本(Lehrbuch)和辞书(WÖrterbuch)之间。据说,最古老的百科全书可追溯到老普林尼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百科全书,即作为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体系的总汇,无疑是自培根以降的现代科学和以法国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启蒙运动的产物。当培根意图肃清误导人类认识的四种幻象(种族幻象、洞穴幻象、市场幻象和剧场幻象)时,这位现代科学之父已经开辟了祛魅的或合理化的思想道路。他将世界万象还原成一系列原子的机械组合,由于它们不为任何先在的价值所渗透,便成为感性观察和理智归纳的单纯对象,从而成为可以为人类所把握的知识体系的对象。培根晚年致力于写作巨著《伟大的复兴》,但终究未竟,只完成了第一卷《学术的进展》和第二卷《新工具》。按照原计划,这将是一部篇幅六倍于老普林尼《博物志》的百科全书式著作。
在某种意义上,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法国百科全书派所从事的,不过是培根的未竟事业。当他们向法国公众展开了《百科全书》所绘制的世界图景时,现代科学和主体哲学便爆发出革命性的力量。在狄德罗的自我理解中,“百科全书的宗旨是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时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代的业绩对未来的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商务印书馆,62页)一部百科全书必须是一个知识的统一体,这是启蒙主义时期从事百科全书编撰和研究的基本观念。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布氏百科全书仍以此为宗旨:“诸理念与诸事实之间构成圆环。这部辞典将此圆环作为微观宇宙,在有限的篇幅内赋予它以直观,这不是为了解答某个科学问题,也不是为了操练某种技艺,而是为了在人本身与超越于其日常生活视野的世界之间,建立起熟悉的关系,使人得以理解概念,得以洞悉事物的有机关联,得以综观总体。”这种关于知识的总体性理念,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最高程度的哲学表达,《精神现象学》开篇就指明,真理作为科学的体系,乃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所以哲学本质上就是“百科全书”。
当然,这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本身便根植于一种普遍主义的主体认识论。而这样一个认识主体,同时是一个伦理主体和政治主体。启蒙主义者常常自命为世界公民,即便像康德这样毕生没离开过柯尼斯堡的人,也在构想着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基于普遍主义的逻辑和世界主义的立场,若古在《百科全书》中认为,所谓的“祖国”,无关乎出生,而关乎自由国家,因为,“专制制度之下没有祖国”。所以,《百科全书》是世界公民的百科全书,是启蒙先驱写给市民阶层的通行教本,其进路是一种理性的教化,根本目的在于塑造现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
然而,十八世纪同时也是民族主义高奏凯歌的世纪。在美国和法国发生的姊妹革命,用民族—国家概念终结了这个世纪。启蒙方案究竟没有兑现,相反,从启蒙方案中孕育出的现代民族国家,最终完成了弑父的举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资本主义、印刷术和人类语言的宿命多样性这三重因素的结合,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语言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勘定了民族共同体的边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摧毁了中世纪的封建壁垒,塑造出一个同质化的社会。而印刷术的发展,使同质化的社会得以获得共同的教化。由此,民族国家作为衡量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单位,才登上历史舞台。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特殊主义。它本身只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的现实化,如果不是世界现象,至少也是一种西欧现象。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期间喊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也是其民族精神的浓缩。但这些蕴藏着普遍主义意味的价值,还不是后来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文化民族主义多是落后民族的意识形态,比如德意志民族,用普莱斯纳的话说,德意志民族是“迟到的民族”。虽然到了十八世纪,它初步形成了文化民族(Volk),但并没有塑造出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民族(Nation)。正是在大革命的血与火当中诞生的法兰西民族,为德意志民族提供了一个民族团结的典范。在启蒙时代,德国知识分子多以世界公民为荣,而现在,他们愤然归皈民族,信仰民族文化的价值。在思想史上,费希特的思想转型也许最能反映德国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节点上的抉择。就在法国人占领的柏林,费希特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他认为,德意志民族作为“源初民族”(Urvolk),完美地代表了整个人类。他进而意图把这个“源初民族”教化成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居于人类理性王国的中心。费希特创造了一个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也就是将启蒙价值和德意志文化合而为一的典范,对德国思想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于《布罗克豪斯》,只有在这一思想史语境中,才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这部百科全书首先无疑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的出版者布罗克豪斯虽然不是启蒙思想家,但也是时代的产儿,多次与当局的书报检查制度发生冲突。但另一方面,它所诞生的一八零九年,已经是德意志人民族觉醒的时代。而布罗克豪斯同时也是政治评论家,晚年甚至还以记者的身份介入到一八一三年的莱比锡战役中。这位灵魂人物的政治倾向表明,这部辞典不可能完全继承法国《百科全书》式的普遍主义立场。根据出版史资料,德国市民对法国《百科全书》同样有着阅读的需求,但德国出版商和知识分子没有选择翻译的方式,而是选择另辟蹊径,这种举动本身便表明,一部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百科全书,应当别有怀抱。
《布罗克豪斯》应运而生,它的原始命名是“特别为当代编撰的社交辞典”,并聚焦于历史、政治和文化。公共交往功能和文化认同功能,显然是这部辞典的初衷。当法国《百科全书》最终成为摧毁旧制度的攻坚武器时,德国的社交辞典却在旧制度的庇护下,把它的思想结果当成谈资。这就是德国知识阶层所理解的“坚定”(Festigkeit)和“审慎”(Besonnenheit)。《布罗克豪斯》的预期读者是“有教养的市民阶层”。这个以商人、公务员、教师、律师、医生、工程师和艺术家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一方面呼吸着人文主义的时代气息,另一方面也沐浴着虔诚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源流。启蒙运动发端于宗教宽容思想,它的无神论倾向主要针对僵化的宗教教义。而德意志民族特殊的虔诚主义传统,本身便反感教条主义。在神权教义遭到清算的时候,虔诚主义的宗教情感反而保存下来,并在康德等启蒙主义者乃至浪漫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从法兰西到德意志,百科全书的理念悄然发生变奏。从普遍主义到特殊主义,便是这场变奏的内在旋律。对于落后民族而言,《布罗克豪斯》无疑更有吸引力。后来,许多非英语国家都把它作为百科全书编撰的典范。相信这些举动,不仅关乎形式和体例,更关乎理念和价值。而此后,几乎每个国家编撰的百科全书,都无一例外地加上国别的定语。然而,百科全书的内在旋律并未因此而终结。“百科全书”的原初意义,即“普遍的、全面的教化”,仍不时要求它重返普遍主义的曲调。二十世纪初,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还在畅想着一部完美的“世界百科全书”,它是新型的、自由的、综合的、权威的、永恒的“世界大脑”,能够帮助世界公民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为世界和平做出最大的贡献。然而,不无反讽的是,这个构想却是他为《法国百科全书》(一九三五至一九六六)撰写的一个词条。在当时,威尔斯借以做出如此构想的还是缩微技术,而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威尔斯式的构想是否成为可能呢?
二零零一年,维基百科(Wikipedia)诞生。二零一一年,高歌猛进的维基百科以一种令人瞠目的自信,在全球范围内征集签名,以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这才不过短短十年。当维基百科以这种早熟的狡黠进行营销时,《布罗克豪斯》似乎已不堪其辱,选择了体面的退场。二零零六年,贝塔斯曼收购布罗克豪斯出版社时,还胸有成竹地规划着发行一个新的版本,然而到今天,这种信心难以为继。出版社也认识到,在出版业的黄昏时期,百科全书的传奇早已成为往事。就像猛犸只属于冰川时代一样,布氏的知识帝国只属于印刷时代。布氏的终结也不是孤立事件。同样在二零一二年,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环球百科全书》已经相继宣布停止发行印刷版。维基百科在这场生存竞赛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取胜之道,不在技术,而在理念。
维基百科有两个核心理念,一个是“内容开放”。这是由copyleft协议衍生的理念。在构词法上,copyleft是对“版权”(copyright)的反动。在copyleft协议下,基于超文本技术的信息资源,不受传统版权的约束,允许任何第三方不受限制地复制和修改,以及再发布材料的任何部分或全部。由此,维基百科便自我理解为一项由大众广泛参与的协作计划。词条的编者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其中当然不乏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更多的是外行人。在反复编写的过程中,产生越来越多的编写者,越来越完善的词条必将吸引更多的读者;而在这些读者当中,也势必涌现出越来越成熟的编写者。凭借着这种自我组织程度和自我增殖模式,维基百科将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速度,同化为自身的成长速度。所以,才不过几年光景,维基百科的词条数便超出了老家百科全书的世代积累。而它的读者群更远非后者所能比拟。据统计,单是德语版的维基百科,现在每天就有三千一百万的点击量。
一开始,传统百科全书还能够借权威性进行攻势防御。然而,网络时代实在日新月异,这个攻势防御阶段终究难以为继。二零零七年,德国《明星》杂志聘请专家对维基百科和布氏百科进行对比。他们随机抽样了五十个词条(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宗教等领域),按照正确性、完整性、时效性和可理解性的标准,得出二者的平均分。结果令人哗然,前者比后者高出一筹。在其中四十三个词条中,如“哈茨四”(Hartz IV)、“U2潜水艇”(U2)、“青霉素”(Penicillin)、“摩西”(Moses)等,前者的解释均优于后者。而后者只在六个词条的检测中优于前者。在时效性的评价范畴中,前者敏锐于后者,这在情理之中。而在正确性的评价范畴中,由志愿者编撰的词条,竟优于专家手笔,这则在意料之外了。这项测试显示,布氏百科只在可理解性的指标中胜出,维基百科的解释过于冗长。当然,简明本来就是布氏百科的传统优势。
以传统百科全书为代表的专家知识,无疑是主体性哲学的产物,知识就是主体对客体加以把握的结果。百科全书的知识之所以是可靠的,是因为它们出于专家和权威之手。《百科全书》是由当时最杰出的思想精英书写的,狄德罗一人写了一千两百多条,孟德斯鸠独自完成了四百条。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参与过《美国新百科全书》的编写。而在维基百科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主体间性的认识论模式,认识的机制不是主体之于客体的纯然把握,而是主体之间的一致赞同。这种转型的直接结果,便是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知识的生产者化身为匿名的芸芸大众,一个词条的最终呈现,经过了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编写者不断讨论和改写。维基百科的创始人说:“我想在未来,人们看到《大英百科全书》,会说不错,但一篇文章只是由一个人写,几个人审查,我更愿意看到一篇文章由上百人审查,而且是在不断讨论的基础上受到检阅。”这是知识生产的大众化与专家系统之间的较量。《明星》杂志的测试结果表明,专家的权威地位面临大众的颠覆。然而,这分明又是由专家系统做出的权威答案。这个戏剧性的场景,将专家系统置于了尴尬的地步。
与此同时,知识的消费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发生着相应的改变。百科全书的庞大体积和精美装帧,是其所有者之购买力的表现。自启蒙主义时代以来,百科全书就是市民阶层的身份标志和交往媒介。这个阶层用百科全书的知识通货,保持着有序的社交活动,在确证自身社会地位的同时,也塑造着集体的世界想象。而当互联网覆盖并重组这个世界时,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宣告崩溃。大众正在以数不胜数的社会方言,交流着抛散在网络当中的知识碎片。传统百科全书将自己理解为知识的统一体,着力建构知识间内在的、有机的关联,并呈现为“知识树”的形态。而在维基百科这种超文本语境下,这种统一的形态已被非线性的网络形态所取代。不同的信息空间被叠合在一起,而又漫无边际地离散开去。置身于去中心的信息空间中,人们获得的,也许只是星际迷航般的失重体验。就在《布罗克豪斯》终结之际,德国《时代周刊》以乐观主义的笔调写道,维基百科已将比例尺为1∶1的地图展开在我们面前,启蒙的方案仍不断推进。似乎,维基百科这部“自由的百科全书”已全面实现了威尔斯的构想。
维基百科的另一个理念是“中立观点”,也就是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这是启蒙时代以来,事实与价值发生分裂之后所导致的思想困境:启蒙理性所能把握的,不是价值,而只是事实。所以,当启蒙理性僭妄时,便意欲对它加以殖民,而当启蒙理性清醒时,便应当对此保持沉默。价值中立所表达的,无疑是启蒙理性面对价值问题时无能为力的宿命感。在这个意义上,倒真可以学着《时代周刊》那样做出论断:维基百科继续推进着启蒙的困境。网络世界中匿名的主体有无穷的策略来取消自己的身份,也有无穷的方式来变化自己的身份。互联网是大众化的社会空间,却变本加厉地分化出越来越“小众化”的身份认同。花样翻新的亚文化,正在割据这个社会空间。很难想象,这个世界当中,能有什么真正严肃的价值问题。在“内容开放”的理念下,知识正以一种狂欢化方式进行着生产,而在“中立观点”的理念下,知识却呈现出碎片化形态。
借助于超文本技术,这场知识生产的狂欢正在以解构主义的逻辑改变知识的命运。文本没有固定的意义,一切只是能指的漂浮,一切只是书写的游戏。真理与意见之间,丧失了应有的界限。而就在维基百科已然自居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当下,我们有必要追问:这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还是一种沉重的精神状况?福柯曾说,为了遏止文本意义的无限膨胀,需要一个“作者”保证意义的稳定。“作者”就是最后的权威。当维基百科最终解构了“作者”的时候,知识共同体乃至政治共同体的拱顶石也随之坍塌。海涅曾讲过一段思想史轶事: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里杀死了上帝之后,由于善良的老兰培需要一个上帝,便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让上帝复活了。今天,当《布罗克豪斯》寿终正寝之时,我们依然眷恋着它的庞然身影。莫非,这就是德意志式的“坚定”和“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