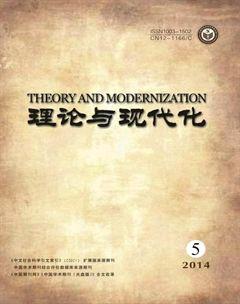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康宇
摘 要:“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政治伦理;先秦;和;分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5-0056-07
先秦时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自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确立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理念后。孟子、荀子先后又做了发挥,创造出“为政以德”、“德法并重”等一系列统治道德规范原则。进而,建构出以“仁义”为核心,强调以德为尚、民为邦本的“王道”伦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和”与“分”两个范畴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先秦儒家“和”与“分”范畴内涵及其在政治伦理思想中的运用
在先秦儒家看来,“和”是一种形上本体。《中庸》上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与“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自然世界与社会人事都应遵循“和”的规律与指向。但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和”又可落实为一种道德品质。“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际关系和谐是礼法有效应用的根基,是社会秩序稳定、安宁的保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是,君子能“以和待人”,宽容处事但不随波逐流,小人则恰恰相反。《中庸》也讲:“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 “中节”是说由对道德准则的恰当把握而完全符合,即“和”是个体行为、语言的标准,是个体内在道德修养与社会外在伦理控制共同要达到的效果。
如何实现“和”呢?先秦儒家设计的路线是:其一,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自觉固守自己所处的等级地位,并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如孔子总结的那样,“道之将行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只有知命、安命,人们才能不违背已有的等级区分,在“无争”中“尽伦尽责”,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诸多和谐。其二,在“和”的过程中,要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不是“同一”,而是对立中的统一,它应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故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的关系原则。同时,也不要因为“和”,为取悦他人和世俗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不讲原则。若“入流”,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下》)。
当“和”这一范畴具体化于政治伦理思想时,先秦儒家将之转化为“人和”的社会管理理念、“政和”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共和”的奋斗理想。
“人和”指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 “人和”之所以会被看作比天时、地利更有价值、更为宝贵的要素,是因为它对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发生过多的动荡,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1]荀子的说法更为直接,“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 “和”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尺度,也是社会管理的目的。只有“贵人和”,人际交往、社会秩序方可和谐。
为了实现“人和”,统治者要做出表率,“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只有君主礼、义、信,臣民才能敬、服、情,从而一个人们共同遵守特定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统一一致,情感相互依赖,少有矛盾冲突的“人和”社会才能实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人和”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忠与信:为人“忠而有信”(《论语·学而》),处事“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言行相符。这样才能达成彼此间相互信任、理解宽容、共同促进的和谐社会局面。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显然,“人和”虽然是“王道”的目的,但它需要受到“礼”的节制。这里的“礼”,广义地讲是指典章制度,或曰一切社会规范及相应的节文仪式,狭义地说就是道德规范。荀子也强调:“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社会管理需要“人和”,但必须在“礼”的范围内行事。究其原因,礼是先秦儒家哲学形上本体“仁”的具体体现与外在表达,“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和”最终也是要实现“仁”的意义,故“人和”与“礼”之间也形成了内在联结。
“政和”是说,社会秩序稳定,阶层和睦,国治天下平的政治和谐状况。孔子强调德治,孟子倡导仁政,其目的均是为了达成“政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对于先秦儒家来说,将道德作为政治的根本纲领,并且要以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去感化百姓,是政治伦理的客观要求。若想巩固统治,维护良好社会秩序,执政者必须以德服人,通过爱民、利民,征服民众之心,“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谓道德之威”(《荀子·强国》);以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的手段,以仁爱之心获得百姓认同和自觉拥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在实践中,首先要明确“民贵君轻”。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离开了民,君只能成为孤家寡人。君主只有利民、惠民,使民众安居乐业,才可能真正让社会和谐稳定。所以当子张请教孔子如何从政时,孔子要他“尊五美,屏四恶”,即尊崇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以惠民为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摒弃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出纳不吝,不进行教化而一味诛杀的暴政、虐政行为。孟子主张制民以产,省刑罚、薄税敛,君主与民同乐。荀子要求“天立君以民”——君主是天为民兴利除害所立,君主要时刻为民众着想,爱护万民,养育众生。其次要构建“天下为公”的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在这样的社会里,君主讲仁政,臣子秉公执法,百姓讲诚信,天下一家、安宁和平。此外,社会还要形成选贤任能的贤能政治制度。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强调:“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显然,贤能的任用已然是社会政治和谐的保障。至于如何去做,先秦儒家将之总结为:以德才兼备为贤能标准,官吏要积极荐贤举能,国家要善于用才,大胆提拔人才,信任贤能。
“共和”准确地说是一种政治理想:社会乃是一个大同世界,“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礼记·礼运》)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在“共和”中,人自身、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社会间和谐共生,儒家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理想,得以充分实现。
与“和”相对,“分”范畴在先秦儒家视阈中也存在多重含义。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代表了等级“区分”;孟子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孟子·告子上》)代表了认识论上的“差分”;荀子说:“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代表了社会角色意义上的“分工”;等等。而在政治伦理思想中,“分”这一范畴有着特定的指向——“名分”。
第一,“名分”指代着“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君子也者,小人之成名也”(《礼记·哀公问》),君子是尚德而成就美名的人,他志于道、重于行,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小人”是道德贫乏的人,其追求的是外在感官的满足。“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对于“小人”来说,“君子”是他们道德的榜样,所以在社会阶层划分上,君子为尊、小人为卑也就顺理成章了。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论语·卫灵公》)在政治权力分配上,君子应为“劳心者”,小人应为“劳力者”。“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荀子·富国》),“德”与“力”间理应是“役”与“被役”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对于“义”与“利”追求的不同,决定了君子与小人之间存在“上”、“下”的区分。因此,二者间有着本质的阶层差异。
第二,“名分”突显着“大人”与“小人”的差异。“大人”是先秦儒家所构建的理想人格模式。“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孟子·告子上》),“大人”重精神气节,有独立的道德意志,“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成为“大人”需要个体发挥仁义礼智之“心”充实自己,达到“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告子上》)。与之相比,“小人”缺少“心”的思维能力,常用感官去认识外物,故只能受外物的蒙蔽。所以在社会职分排位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由于所具德性的不同,“大人”居于社会上层,“小人”只可居于社会下层。“大人”与“小人”的资质不同直接决定了其社会等级之分。
第三,即使是在“庶人”中,同样存在“名分”。先秦儒家将“庶人”界定为地位低下的“民”阶层,“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孟子·万章下》)。“民”阶层的特点是个体德才能力并非出众,但却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因此孔、孟、荀等十分重视对之进行德性培养,诸如“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孟子·尽心上》)等,并且进一步对“民”进行了类别划分,提出“四民”说—— “士”、“农”、“工”、“商”。“四民”虽共属“庶人”阶层,但却有着等级序列差异。“士”居“四民之首”,“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士虽然社会身份低于“大夫”,但潜在着向上流动至社会管理阶层的可能性。“农”、“工”、“商”分属三种性质不同的行业,这不仅是一种职业分工,更内含着等级上的区分。“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荀子·富国》),也就是说,“农”为本,“工商”为末。
因为“四民”的等级位置不同,所以他们各自需尽的伦理义务亦有差异。“士”的角色要求是“学习道艺”,以成就德性、立身入仕为目标;“农”以生产劳动为业,其定位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荀子·王霸》),“工”、“商”关乎 “力”,为“君子所役”,其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遵守社会秩序。对此,荀子做了总结:“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荀子·荣辱》)无论是“尽田”、“尽财”、“尽械器”还是“尽官职”,都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尽分守职”。
二、作为政治伦理范畴的“和”、“分”关系及内涵剖析
在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和” 与“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和”与“分”有着共同的理论依据——天人同构。“天”是最高的伦理“本体”,其内含着“天道”,规定着万物的运行规律;“人”是伦理的载体与道德行为的实际执行者,他所遵循的“人道”是人行为的客观规律和人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天”规定着“人”,“天道”制约着“人道”。天人之间彼此和谐是人自身得以顺利发展,伦理世界秩序得以维护的根本保障。“天道”、“人道”在根本上是相通的,可外显为“诚”,“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而 “诚”又体现在“良心”上,“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良心”是“天德”,在政治生活中可转化为人伦规范与制度规则,它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然而,当“良心”落实于具体行为个体时又会出现“化性起伪”的可能,“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这种“性伪”实际上让人与天在“合”的同时,又走向了“分”。此外,另一种情况同样导致了“天人相分”,即“道”是普遍的,而作为天与人沟通枢纽的“礼”既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道”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原则,它无法被改变或者被否认。“礼”是具体的,其内在精神内核是“分”,它允许在各种关系和不同情境中出现不同的表现“道”的形式,它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紧密联系,或者受其制约。“道”需要诸多不同形式的“礼”做为体现,只有这样才能符合道德情境与道德文化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要求。既然个体所习得的“礼”存在不同,那么形式上的“天人相分”也就具有了内在的合理性。
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天人相分”,其基础皆是人与天的对应。因此,“和”与“分”在本质上具有同根性。所以孔子、孟子在强调天道与人性同一时,又坚信个体对天道的感知、体悟差异是社会中政治地位尊卑上下之“分”的源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荀子在大讲天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不同时,也强调“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论》),“分”的最终走向仍是“和”。
其次,“和”与“分”有着相似的人性假设指向。对于人性论问题,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论断,认为人具有共同的本性,但在后天发展中人性彼此不同。孟子进一步深化了孔子的看法,指出“人性善”是人的先验本性,良知、良能是人心先天就具备的。由此,他提出“人性善”的理论假设。因为“人性善”,所以君主推行“善政”便会容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而“为政以善”的直接结果,必然是臣民之和、天下之和,“为善必王”,天下必治。
与之不同,荀子将人性预设为“恶”。他说:“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荀子·性恶》)。既然人性本恶,那么若任其发展不加约束,则人人均会趋利避害,造成社会动荡不安。所以必须制定礼法,结合道德教育,使人“去恶从善”。践行于政治生活中就是“以礼定分”:“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荀子·富国》)。故“礼”可以作为“道德之极”、“人伦尽矣”的规范体系,维护社会良性运行、和谐政治伦常秩序。以善德为基础的“礼”,通过“分”确定了阶层等级差别,从而使社会能够实现“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荀子·王制》)的理想治世与万物和谐的局面。由此可见,由“性恶”推出的“分”,绝非侧重于突显个人权利、义务的意义,而是从“和”的维系着眼,旨在追求社会有序与政治稳定。“和”与“分”对于人性假设的出发点虽不相同,但最终的指向均以道德维护政治,以确保“道统”的正常延续。
最后,“和”与“分”有着一致的客观效果——“群”观念的确立。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具有社会性,它使人与人之间可以沟通、理解,形成“群”的合力。而在“群”的力量帮助下,人们可以战胜自然,生存发展。从“和”的视角看,个人要有对整体利益负责的精神,对群体做出积极贡献的意识。直接的做法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通过推己及人的方式,达成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共同向上。要让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突显与保障,个体与个体间必须协同努力,以“群”之“和”促进社会发展。
从“分”的角度上讲,则是人能“群”,因为有“分”,“分”定而“群”立。正是因为有“分”,人群秩序方得以确立,个体间方可和谐相处,“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荀子·王制》);因为有“分”,人的心理欲望得以控制,安于社会现实,“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荀子·富国》);因为有“分”,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与他人和平共处,“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国》)。
可见,通过“分”人际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保持了协调、和谐,社会群体得到了统一,从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去战胜外界,满足人类整体的需要,“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从而使理想中的“政通人和”真正实现。
为了让“和”与“分”的伦理观念彻底地贯彻,先秦儒家在设计君主制度时颇下了一番功夫。从“分”出发,他们先确立了“礼”与“法”两种社会控制方式。“礼”侧重于礼义、道德规范等;“法”侧重于刑罚等强制性手段。礼法各有自己独立的调控范围对象,“夫礼将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大戴礼·记礼察》)之后,他们明确了社会分层的意义。通过不同个体身份地位的差异,将世人以“礼”划分为“贵贱有等,长幼有差”;通过德能衡量,划定个体在社会大体系中应有的职分,“德以叙位,能以授官”(《荀子·致士》)。并且还制定出“礼贤下士”、“选贤举才”、“使贤任能”的人才选拔制度。此外,他们还设定了社会利益分配制度。孔子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这里的“均”即是按“差等”原则进行分配的一种形式。荀子讲:“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患之民完衣食。”(《荀子·正论》)物质财富的分配一定要符合名分等级,等等。
从“和“出发,他们一再强调“尊卑有等”、“群而相宜”、“分而有序”等政治原则。所谓“尊卑有等”,即个体必须有“亲亲”、“尊尊”的意识:坚守家族内明确的亲疏远近、长幼顺序,明确各自的道德义务,做到父慈子孝、夫义妇顺;严格划分国家政治领域中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不可逾越。同时让“亲亲”与“尊尊”互通,使得“忠”、“孝”达成有机联系,促成社会亲如一家,但又等级分明。“群而相宜”是说,个体与社会相互和谐,群己关系融洽。个体要知道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群体的力量,故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群体的力量大小取决于社会是否有“分”,“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荀子·富国》)。“分而有序”要求“农农、士士、工工、商商”,每个人各尽其职,让社会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整体。做为社会统治者、管理者的“德者”、“智者”、“能者”,与做为社会被统治、被管理的“小人”和谐相处、其乐融融。
为什么“和”与“分”两个貌似不相关的范畴,在先秦儒家政治伦理中会形成如此紧密的联系?剖析其本质,可以看出:“和”实际代表着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分”实为伦理中心主义的体现。“和”是儒家一直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其政治伦理的内在精神;“分”是道德的现实实践,是其政治伦理的外在表现。正如孔子、孟子、荀子等设计的那样,人们在践行“分”时,必需明确内在“和”的走向;奉行“名分”、“职分”时,必须以维护“人和”、“政和”、“共和”为目标。当然,“和”与“分”之间也存在张力。所以孔子等也强调,遵循“和”的原则并非一味求同,要在“分”中不断培养人们“和”的意识。显然,他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强制性不只是被动地给定条件,而是主动地具有创造性的工具。如果没有了“和”,“分”就成为空泛的形式主义,缺少了“和”的“分”也极易失去灵魂,从而破坏人类的美德情感。“和”与“分”的关系,可以用“理一分殊”的说法做出极好的解释。“和”是普遍的、基本的原则,它无法被改变或否认,而“分”是具体的,是在复杂社会实存中不同的表达“和”的模式。“分”是为了更好的“和”,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和”的有机组成。
众所周知,儒家政治哲学传统讲究“内圣外王”。从这个意义上考量“和”“分”关系,那么“和”就是一种“内圣”,“分”即是一种“外王”。“和”将天道、人性等内在要求展现得淋漓尽致,“分”则将抽象的政治伦理具体化,变得有操作性。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后者是前者的指向。至此可以断定,“和”与“分”的不同,不是目的的差异,而是手段的区别;不是价值取向的分歧,而是方式途径的多样。
三、先秦儒家“和”、“分”思想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
先秦儒家政治伦理中的“和”、“分”思想直接影响了后世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维与治国理念的形成,它与讲究宗法等级、孝亲尊君、安分守己的自然经济社会的内在要求极为适应,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政治发展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时代的变迁已经让其伦理内涵与外延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其高扬的治世方略、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受到批判,其设计的政治理想与道德追求日益暴露出“空想性”的缺憾,但其内具的逻辑理性、辩证精神,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却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要以“民本”为基础。从本质上讲,“和”与“分”之间的对立统一,根源在于先秦儒家想要达成的政治目标是形成在“民本主义”基石上的“尊君”。“贵和”是政治秩序稳定、民众集体归属感生成、社会成员凝聚力形成的前提,君主的统治能够世代延续的根本。“和”的客观效果必然要“尊君”,因为“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君是天为民兴利除害而设立的,“尊君”也就是“尊天”,也是对维持“和”做出的一种贡献。“有分”的目的在于“安分”,进而让人“无争”,社会政治得以和谐。若让人“有分”、“安分”,除了制度上的“名分”、理念上的“类分”外,统治者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关爱也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看到,孔子一面讲“为政以德”,另一面也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一面认为“保民而王”(《孟子·梁惠王上》),另一面又强调“劳心者”与“劳力者”的不同分工。由此,尊君主张与民本理念的并存并行亦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质。
现代社会虽然社会实存已与几千年前的先秦境况大不相同,但是同样需要“和”、“分”有序的社会政治局面。“以民为本”必须作为一种“执政理念”被强调,作为一种历史经验总结被“扬弃”、升华。
启示之二:社会政治伦理建构必须坚持美德与规则的统一。以美德伦理学的视角考量,“和”代表着美德,“分”代表着规则。“和”与“分”在道德评价中得到了统一。在先秦儒家看来,“和”是一种道德行为,是人人追求的修养目标。不过,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这种道德行为要融入到具体的“分”的道德规则中。由于存在“分”,所以人们要遵循“礼”。 “礼”不仅定义“道德”或适当的人的行为,它也限定了作为一个人的意义。简单来说,“和”的道德行为不是由独立于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个体所实施的活动,而是由在各种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来实践的。也就是说,社会中那些符合“和”的道德行为是在社会关系中实施的符合“分”的道德规则实现中完成的。
这样一种兼顾“美德”与“规则”的“和”、“分”伦理关系构造,其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它恰到好处地将个体的“终极关怀”与“底线伦理”统一起来,将道德行为与道德规则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化解于“无形”中。现代社会政治伦理的建构同样需要这样的“兼顾”。当道德与法制、民主与专政发生矛盾时,“美德”与“规则”的辩证统一可以恰如其分地解决问题。
启示之三:社会政治道德设计不可忽视“伦理生态”问题。作为一种文化,道德合法性的生成依赖于能够被社会确证自身的存在现实性与价值合理性。“存在现实性”来源于道德的“实践理性”,既受理性指导并得到理性确证,又具有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价值合理性”则源自道德与社会中其他要素的整合。上述二者的均衡问题又可统称为“伦理生态”问题。
先秦儒家关于“和”、“分”伦理范畴的设计严格遵守着伦理与文化生态、伦理与经济生态、伦理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均衡。它既赋予“和”以“天道”精神、“分”以“人道”理念,基于此规范天伦与人伦,又使让人安身立命的智慧与文化自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将“和”、“分”的政治伦理内化于社会职业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之中,又让“道德生活”与“道德生活方式”整合统一;既以“和”彰显政治上“德”-“得”相通原理,以“分”明确社会行为中的“必须”与“应当”,又让秩序理性与民主品质相互和谐、共生共荣。
毫无疑问,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充满“文化理解”、能够迎合并促进体制改革、跃迁的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先秦儒家提供的“伦理生态”智慧高效、易行,实为可资借鉴的重要参照。
参考文献:
[1] 张锡勤.中国传统道德举要[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250.
On the “Ag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of
Confucians Political Ethics in Qin Dynasty
Kang Yu
Abstract: “Ag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are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Confucian Political Ethics in Qin Dynasty. In political life, “aggregation” may be embodied as “people”, “governance” and “republic”, while “separation” as “birthright”, “duty", etc. “Aggregation” and “Separation” seem a pair of opposed categories, but inextricably are linked to each other. They have common theoretical basis, similar assumptions of human nature and consistent objective results. They are Confucians “moral idealism” and embody the thinking philosophy of “ethical centrism”.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an gain enlightenment from them.
Keywords: Political ethics; Qin Dynasty; Aggregation; Separation
责任编辑:王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