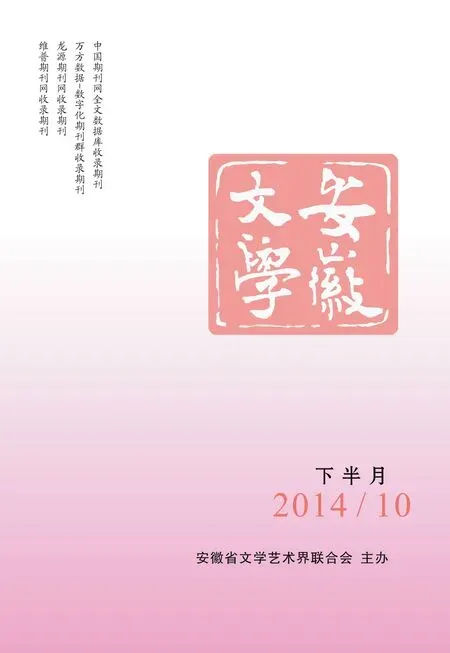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思考
朱燕颐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和源头,目前学界普遍采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一“两分法”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方式,更多是基于政治和历史的考虑,以1949年这一对于中国十分重大的政治转折点作为现当代文学史前后两端的分界线。但是,随着文学史的思考模式不断完善,我们发现这种简单以政治事件划分的方式过于粗糙。尤其是1976年前后,中国文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在原先的两分法划分方式中并没有得到体现。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也引发出许多新的思考和探讨。
一、被质疑的“现当代”
“现代”这个词在汉语中本没有,《俱舍论》中提及的“若已生而未灭名现在”中的“现在”,与如今的“现代”意思相距甚远。它是个舶来词,首次被使用于公元10世纪末期,用于将古代与现代进行区分。在世界史上,普遍公认的“现代”是指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兴起以后的历史时期。[1]
中国的文学史上,“近代文学”的概念由陈子展在1929年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中第一次提出。之后,钱基博在193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提及了“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但是他的“现代文学”指的是1911至1930年的中国文坛。这一个名词的提出带有随机性,本来他想沿用“近代文学”,但是这与西方概念的“近代文学”有很大的差异,得不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同。于是钱基博只好使用“现代”一词来区分。
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文学”概念,并不是来自于这个词的诞生之地——西方知识体系,而是来自前苏联。前苏联在当时对于意识形态高度重视,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简明章程》和《世界通史》中,建构了“现代史”的概念,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理解历史的框架,将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五四”运动则成为现代史的开端。那么自然而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就成为了“现代文学”的开端。与之相应,另一个在共产党历史上的大事件就是新中国的成立,于是这一个事件也就成为“当代文学”的开端。如此划分产生的主要矛盾有:(1)“五四”时期大量的知识分子其实受到了之前一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影响,比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章太炎等等。虽然在以破为主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都曾批判过这些传统文人,但是依然不能否认他们的维新思想对鲁迅等人影响的深远。甚至这一影响一直绵延至今。(2)当代文学史的划分以建国为起始,但事实上,从建国到 “文革”,中间这一段时期文学基本处于停步状态,并且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强行介入,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与发展中的文学史线路脱节。一直到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之后,文学的发展才与之前的线路接上,并且开始发生转变,由此诞生“新时期文学”。
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三分法”
基于这些矛盾,有些学者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文学历程的发展与政治剥离,一直向前推至世纪之交的清朝末年。他们主张从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寻找现代性的萌芽,从而顺理成章地延续到新文化运动大量启蒙知识分子的出现。这样的分期方法能够将历史与文学史相结合,更易寻找到文学思潮产生的规律性。
秉持这一分期方法的学者们也十分关注 “现代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晚清的最后时期。由于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遭受巨大的打击,开始反思一直以来“唯我独尊”的闭关思想,走出国门,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术。这一时期的留学热潮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学习日本是一条学习西方的捷径,所以大量来到日本留学,所学大多为文学等社科学科;第二个时期,知识分子来到欧美,以理工为主,直接学习西方的经验和技术。第二个时期,知识分子们不再如第一时期只是简单照搬西方经验,而是开始懂得思想启蒙的重要性。留学的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工作成为启蒙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进化论》的传入,对国人思想起到极大的影响。从现代性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形态变迁,曾经是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摆脱极左政治模式的一个重大策略。[2]
但这一理论观点是以五四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为基础,寻求的是启发五四知识分子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原因,因此找到的也是这套知识体系的起点。而五四知识体系并非文学史唯一的线索,后期出现的自由主义作家等,与五四精神和内涵并不一致。单凭此来划定文学史是不够科学的。而且这一概念也并不能清晰地标示出历史的性质,只是划定了一个模糊的范围。倘若继续追问,五四知识分子启蒙者,这些晚清到五四之前的文人们,他们的思想又来源于何处,是否要继续前推,那么就永无尽头了。思想的体系并不是突然就萌发的,而是一代一代不断的积累不断的萌发和成长才渐渐完整的。于是有一些学者对此也提出质疑,比如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他认为对现代性有所启蒙的并非是精英知识分子,而是如西方文艺复兴一样,更多来自民间,来自世俗。可是我们要看到,现代性的推动的确主要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推动的。如果他们没有传入西方的思想,没有振臂高呼,没有起义游行,这些西化的思想和观念怎会深深植入人们的心中并传播下去呢?
另一种划分方式是“三分法”,将当代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文学分为一个时期,之后的文学为另一个时期。前一时期的文学称为“新中国文学”,后一个时期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持这一观点的理论者认为1976年前后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50-70年代,是一个文学断档期,将它“属上”、“属下”都有些勉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分期法的论述者不同,持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将文学与政治完全割离开是不正确的,文学史应当从政治和文学综合的角度进行划分,单纯从政治或者文学方面都不够准确,而应当依据文学规范的更替,在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中,应当看出不同的文学史规范。而所谓的文学史规范主要是指制约一个时期文学史的总体原则,包括基本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体制、运行规则和权力话语。从这个角度,新文学的文学史规范与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有非常大的不同。[3]
新中国的文学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学。许多文学史都是以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来解释中国的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在这个时期,文学被高度政治化,甚至成为政治的传声筒。文学的思想、主题被限制在社会主义的范畴之内,文学的功能被理解为宣传、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文学本身也被作为政治动员的一部分。许多曾经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的启蒙姿态被转换成服务和学习,并且服务和学习的对象是他们曾经启蒙和引导的对象。此时的文艺政策也十分紧张,文学任务被规定为政治任务。巴金、丁玲等一批作家的创造开始发生很大的转变,而像赵树理等一批来自工农的乡土文学作家开始走到前台,他的《地板》是为了配合减租减息,《李家庄的变迁》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登记》是为了新婚姻法的实施。同时一批歌功颂德的典型化作品也大量涌现,文学被限制在政治的框架内。
“文革”结束后,文学又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新时期文学首先在与政治的关系上有了一个实质性的变化,经过“文革”等严苛的思想统治,人们开始反思这二者的关系。文学虽然依旧要为政治服务,但是距离被拉开,有了一定自由度,也有一定自由发展的空间。1979年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指出应当让艺术家发挥个人创造精神,在艺术实践中摸索写作主题和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作家的个人主体性得到了很大的发挥。进入90年代后,商品经济也逐渐蔓延到文学领域,文学的价值形态也由一元走向多元。[4]作家开始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喜好,并且这种兴趣和喜好已经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写作。可以说,五四时期的启蒙者已经开始慢慢走下神坛,迎合读者和受众。也因为这种转变,引发了许多关于现在文学现象的反思和探讨,比如网络文学、拜金主义文学等等。
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分期方法是对现代文学上限的探讨,那么“三分法”的划分方式就是对当代文学是否应当分开的讨论。这种分期方法虽然看到了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但它忽略了这断裂之中内部的联系。在这一时期,依然有许多从事地下创作的作家,比如“朦胧诗”的诗人们,坚持着对于新的文学方式的摸索,并与新时期文学形成承接。同时,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以1985年为界,80年代文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前期,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都与对“文革”的批判、反思有关。整体的取材和主题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具有社会—政治干预性。80年代中后期,“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成为热门话题,这一命题既延续了对文学在人的精神领域的独特地位的关注,也表现了对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精神的某种背离。当代作家们注重社会政治问题的传统出现分裂,日常生活和世俗开始进入作家的视野。同时,“文学自觉”既是一直期待,也可以说是对80年代后期已存在的部分状况的描述。在这一时期,文学史的“重写”也开始被人们关注,并且开始具有理论表述层面的凝聚和加强。
90年代的文学,是否可以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一个文学阶段看待,一直存在争议。分歧主要在于与80年代文学关系的不同理解,即八九十年代文学的“延续”与“断裂”关系的不同认识。一方面,“当代”确立的文学规范在80年代的瓦解趋势,在90年代仍在继续推进。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难以忽略的社会背景和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规约力量,已明显内化为文学的“实体性”内容,这是难以忽略的事实。并且伴随着“文化经济”的出现,文化与政治的疏离逐渐加大,原先的政治权力和精英文化所构建的文化格局也在逐步改变。意识形态权力经典的监管方式仍然继续发挥,但更具弹性的更多运用经济集团活动的方式,开始逐渐有取而代之的趋势。主旋律文化虽然一直被国家反复强调,并制定为一项文化战略措施,以消闲为主的流行文化依然以不可抵挡之势在逐渐蔓延。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二元对立开始有了互相融合的趋势。“文学大众化”的通俗、流行文化,在大众传媒这一媒体的巨大革新帮助下迅速崛起,并占领了文化市场的主要领域。[5]
这两种文学的分期方法分别对目前 “现当代文学”的上下两个部分提出质疑并给予解决,但各有不完整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将二者整合,我更认同另一种观点,将整个封建主义终结之后的文学整合,按照不同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划分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三、第三种划分:民国文学与共和国文学
长久以来,1912到1919年七年间的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在以政治权力为划分标准的文学史架构中,它被迫被安上“近代文学”概念,以满足“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定位。但事实上,在1912年之前的晚清,无论是从社会性质还是文学脉络来看,都应当被归为古代文学的范畴。它的下限不应当止于五四,而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之后、民国建立之初的1912年。
南京大学的丁帆教授认为,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史还是社会史,抑或是文学史,只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之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终结(1911年 10月 10日的武昌起义),一个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共和国体与政体的诞生(1912年 1月 1日),成为中国历史上将“古代”与“现代”断然切开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断代———与长达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国体和政体告别。因而,从此断开,既合乎中国历史(包括文学史)切分法的惯例,同时又照应了中国文学史“现代性”演变的史实内涵。[6]而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说是20世纪文学史,应当在现有的戊戌变法为起源的理论上再往前推进十年。[7]严家炎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滥觞应当是从19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之所以将1912年作为文学的切点,是因为它和以上延续了几千年的各个朝代的封建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本质上的告别,从此开始了一种新文学,即内容上的人本主义主潮和形式上的白话文创新实践。这一阶段,一直到1949年,文学一直是以自主和启蒙的态度来进行的,它们被称为“民国文学”。
那么这一文学的终点在哪里呢?它是否在1949年就中断了呢?其回答是否定的。它一分为二,在大陆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而突变为“共和国文学”,但在台湾依然延续着。
(一)共和国文学
其实这样的划分,在某些政治意识浓厚的人眼中并不是完全妥当,甚至可能被拔高到“分裂”层面。但事实上,在台湾学者的心目中,共和国文学有自己的发展线索,与他们本土的文学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词已经被大陆专有,所以台湾开始称自己的文学为“台湾文学”,甚至台语文学。大陆的共和国文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介入之下,沿着极为严苛的模式发展。文学成为政治的传声筒,但是依然有许多文人在进行着文体和语体的创作与改革。这条线索已经为我们所熟知,在“当代文学史”中也已被论述得十分详细。它大致被划分为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至今的文学。80年代文学一方面继续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经西方一系列文艺思想的传入,开始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一系列“新”与“后”的摸索与探讨。90年代至今的文学逐渐开始扭转了精英主体的地位,商品经济的介入让读者从被动的接受者和被启蒙者转变为主导者。许多文学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引发了对传统回归的热潮,一方面也让作家更关注社会和民生,更多地让文学与各种社会因素相融合。它不再是清冷孤傲的九天玄女,而成为需要适度迎合和不断创新的人间女子。
(二)台湾文学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反共思想在文学上表现为“战斗文学”的倡导。“战斗文学”从题材上来看,大部分属于“回忆文学”,这方面的作者主要有陈纪滢、王蓝、姜贵等,主要要求作家要放弃个人主张,为政治服务。20世纪50年代后期,台湾作家开始厌倦“战斗文学”,部分青年产生逃避现实和颓废的情绪,现代主义因此开始萌芽。从1956年起,现代主义文学以新诗为标志,开始进入文坛。而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开始于现代小说的出现。《文学杂志》和《现代文学》这两个刊物倡导小说家们的创作要回归到作家的本心和情绪表达。同时,存在主义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作家注意强化小说主题的比喻性、形象的抽象化和手法的荒诞性,并广泛运用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为依据的意识流手法,代表作家有白先勇、聂华苓等。[8]此后,西化思想也开始在台湾蔓延,女性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等也逐渐开始产生。
20世纪70年代后,台湾的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发生急剧变化,文学界也开始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做出反思。这也激发了作家反抗殖民经济和买办经济的民族意识以及反抗文化侵略的强烈愿望,“乡土文学”也随之产生。乡土作家主要表现台湾乡村和都市的具体社会生活,用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言和形式揭发社会内部矛盾、体现民族精神,批判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殖民化危机。[8]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与民国文学有很大关联,作家基本是延续了五四时期的批判精神来进行反思和创作。但由于军事对峙,两岸文学也处于隔绝状态。
1987年之后,文学界解除了戒严状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大众消费的流行,台湾的报纸副刊逐渐变成大众的文化论坛,都市文学开始成为文学主潮。都市文学的主要特点在于作家有强烈的都市意识,比如王幼华的《面先生的公寓生活》、张大春的《公寓导游》等等。文学开始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台湾的文学发展不像大陆有比较明显的断裂,它一直呈竹节式发展:50年代的“战斗文学”,6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70年代的乡土文学,80年代的后现代文学,90年代女性文学、后殖民主义和同志文化等等多元发展。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由于“泛蓝”、“泛绿”板块的形成,出现南北分野的现象。以台北为基地,北部文学延续民国文学的传统,创作具有鲜明的中国意识和色彩;南部则延续乡土文学传统,用异议和在野文学特质和本土化色彩浓重的“台语”写作,逐渐想要脱离中华文学,建立自己独立的台湾文学系统。
虽然台湾现在依旧用“中华民国”称号,但是目前的台湾文学与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文学也相去甚远。如此分期可以说在大范围内已算全面,但毕竟每一种分期方法,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科学合理。
文学史的命名和划分,还在不断的讨论和完善之中。政治形态不应成为主导,但也不能完全与之剥离。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话语有相似之处,也有其独特特征。如果硬是要文学史按照革命史路线来走,将一切都与共产党党史挂钩,那么文学史的划分就会显得生硬,许多本来一脉相承的文学思潮和现象就会出现断裂。在特殊的年代,当权者必须利用一切方式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以求团结和鼓舞更多力量。但是到了如今,科学合理地划分文学史,为文学史命名,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观念的转变,在一代代文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一定能够最终达成。
[1]百度百科.“现代”词语起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5310.htm.
[2]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
[3]张卫中.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再思考[J].暨南学报,2010,32(3):128-133.
[4]吴义勤.多元化、边缘化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价值迷失[J].南方文坛,2001(4):40-41.
[5]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12.
[6]丁帆.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了的七年(1912-1919)[J].江苏社会科学,2011(1):161-168.
[7]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2.
[8]古远清.从“战斗文学”到后现代文学——台湾文学六十年[J].名作欣赏,2009(8):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