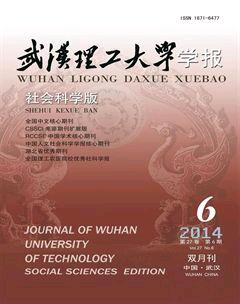从文本校阅到文化细读
柯尊斌+程芸
摘要:荷兰汉学家伊维德元杂剧研究的最主要特点是以中国传统的“文本校阅”结合西方的“文本细读”,并进而上升为“文化细读”。他认为,元代形成的杂剧文本在明代经由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而被改写,而这些文本改编背后,则存在着语境、意识形态、商业目的和戏曲表演等主导因素的制约。伊维德元杂剧研究的思路和视角,可为国内的戏曲研究提供多方面的借鉴或启发。
关键词:伊维德;元杂剧;元曲选;文化细读
中图分类号:J809文献标识码:A
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为标志,元杂剧进入现代学术领域,至今已走过了一百年的历史。这期间,杂剧文本的几次重要发现曾一度掀起元杂剧研究的热潮,甚至使得元杂剧研究成为现代戏曲学聚焦的中心。但由于年代相对久远、文献乃至文物留存相对有限,许多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议。以杂剧文本为例,元代杂剧的本初面貌到底如何?明代抄本、刊本在多大程度上可视为“真正的”元杂剧?后世对元杂剧文本的改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今天对元杂剧的认识?这些问题既是元杂剧研究不可回避的,也可为文学(艺术)传播/接受史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个案。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荷兰籍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的“文本校阅”与西方的“文本细读”方法,并进而上升为“文化细读”,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伊维德教授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是欧美汉学界的领军人物,国内曾作过一些介绍或访谈①,本文则着重从学理上来探讨其元杂剧研究的独特思路和学术方法,以期既能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内深化我们对海外汉学的认识,同时也能对国内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一、文本校阅:元杂剧被如何改写
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发现之前,学界对元杂剧的认识主要是围绕着明人臧懋循的《元曲选》而展开的,后来随着元刊本以及若干种其它的明刊本、钞本的发现,元明时期杂剧文本的种种不同就成为了无法绕开的问题。而臧懋循《元曲选》对元杂剧的“改写”,则更成为了一个聚焦点。事实上,对《元曲选》的非议甚至可追溯到臧懋循那个时代,并延续为现代学者的一个传统看法。正如邓绍基先生所指出的,“最早批评臧懋循删改元剧的,是他的同时代人王骥德”,而当时又有“徐复祚和凌濛初毅然为臧氏辩护”,其后有清人对臧氏“猛攻”,至近代又有郑振铎、孙楷第等先生对《元曲选》提出严厉批评。[1]173182,190203尤其是《元刊杂剧三十种》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不同版本的杂剧文本被陆续发现以后,“引起人们对元剧版本问题的重视,人们对元刊本与《元曲选》本的相异,对《元曲选》本与其他明刊杂剧本的相异,也更重视了。”[1]174
考察不同版本元剧之间的差异,最基本的方法便是中国传统的文本校阅法。把今存元刊本杂剧与《元曲选》以及其他的明代版本相互对校,就可以从不同版本的差异中寻求到文本演变的某些痕迹。伊维德教授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元杂剧被如何改写”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并总结出明人改写元杂剧的两条路径:
其一,从明初宫廷演出本到《元曲选》。
在若干明刊元杂剧中,臧懋循《元曲选》因与《元刊杂剧三十种》表现出更多且更明显的不同,而被认为对元杂剧的“原本”有更多的删改,并遭到许多学人的严厉批评。对此,邓绍基先生借用日本学人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况》中的观点指出,“像这样厉害的改窜的痕迹,并不能只责备《元曲选》的编者,因为改窜是与岁月俱增的。”他还认为,许多剧本到臧懋循手中时“已是这个面目”,其“所据改本或出于元末明初,而臧氏又做过若干修改,并非是臧氏直接大改元刊本。”并且“戏曲剧本在流播过程中出现改动,主要原因同演出有关”,对臧氏不必批评太过[1]173203。也就是说,邓先生这里已经指出了一种可能:臧懋循编辑《元曲选》时,其所用底本已非元刊原本,而是经前人改动后的文本。
伊维德教授将元刊本与明代宫廷演出本、《元曲选》进行对校,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元刊本在明初被宫廷演出所吸收并改编,成为现存宫廷本,而臧懋循据宫廷本为底本,并再次改写而成现存《元曲选》。这是明人改写元杂剧文本的第一条路径。
他以同时存有元刊本和《元曲选》本的《赵氏孤儿》为例,将这两种版本进行细致对比,发现前一版本只有曲辞而几乎没有完整的宾白和舞台指导,后一版本的对白和舞台指导却很完整,而且这两种版本的曲辞也有差异。他认为,这就表明“后来的版本并不是之前文本的简单扩充版。后出的版本增加了完整的第五折的内容,而且,虽然曲调旋律的顺序明显保持不变,但几乎每一曲调的内容都被大量改写了。因此,这两个不同版本的《赵氏孤儿》在情节、人物塑造和主题上都有着显著差别。”显然,臧懋循在编《元曲选》时对所选定的文本进行了大幅改写,有时甚至大量重写[2]。
张国宾的《薛仁贵》杂剧现存有元刊本和《元曲选》本,将这两种版本进行对校,伊维德发现二者差异很大,并且后者的改写有时显得很拙劣,很难将这些拙劣的改动都归咎于臧懋循,所以他提出假设:“《薛仁贵》后来被重新接纳为明朝宫廷演出剧目,并因此被大量改写。所以,《元曲选》版《薛仁贵》可能融合了三种类型的修订文本:宫廷审查官员出于意识形态动机的改编,历代演员出于戏曲演出需要的改动,以及文学编者出于文本需要的修订。”[3]
基于以上对文本演变过程的分析,伊维德认为,从元刊杂剧文本到《元曲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改写过程,首先,明朝统治者将杂剧引入宫廷演出,“意识形态的压力迫使许多剧本要重写,”而《元曲选》的编者所据的底本便是这些被修改过的宫廷手抄本,他们又将这些宫廷演出本改编为供文人阅读的案头文本。“因此,可以说这些剧本从商业性的城市舞台,经过宫廷官宦机构,最终流入学者书斋。”“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元杂剧文本实际上与元代的演出脚本已经相去甚远。”[4]
伊维德进而发现,元刊本杂剧并非完整的演出脚本,这些文本的形成是为了一些特定目的:给那些听不懂唱词的观众准备的;或者专为主要演员“旦”或“末”准备的演出脚本,至于次要演员的道白和舞台指示,则由演员们临场发挥;或者像明初的皇室剧作家朱有燉那样,将剧本刊刻出来作为纪念品赠与现场的宾客;而一些明初的文本则是为了提供给宫廷演出审查官员的检查而写成的;最后,到了《元曲选》的编者们,则是为供文人案头阅读而作[2]。
成书于明代中晚期的《元曲选》文本经过了历代文人、演员和宫廷的重重改写,已不能反应元代文本的原貌。为此,伊维德教授主张在撰写文学史时,不应将其放在元代部分讨论,而应纳入明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围[5]。
其二,李开先对元杂剧的改写。
伊维德教授据明嘉靖时期人李开先的《改定元贤传奇》,又“发现”了元杂剧文本传播的另外一条路径,而这一路径与《元曲选》的形成过程存在较大差异。他认为,《元曲选》的底本大多直接来源于明代宫廷演出本,臧懋循等人据此底本进行再加工,而李开先等人的改定工作却是“以李开先所拥有的元代刊本为底本的”[6]。这些元代底本经过李开先等人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精细改写,从而使其由粗糙的演出文本变成了供文人案头阅读的文学文本。伊维德认为,“李开先本与宫廷本在编辑方针上大相径庭,但却从两个不同的途径为我们提供了元杂剧在16世纪经历大幅改写的案例。”[5]这是元杂剧文本演变的另一条路径。
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中有马致远的《陈抟高卧》,而《陈抟高卧》另有元刊本留存至今,郑骞先生曾将不同版本的《陈抟高卧》的曲辞作了对比,认为现存《陈抟高卧》文本来源于明代宫廷演出本。在此基础上,伊维德将这一元刊文本与李开先本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对比,发现“这一文本的元刊本与后世版本间最明显的不同是,后来的版本中出现了更为成熟的舞台指示和更完整的对白。”“对元刊本与《改定元贤传奇》本《陈抟高卧》第一折中的舞台指导及对白之间差别的详细讨论,可以看出李开先及其合作者们的改定工作是以李开先所拥有的元代刊本为底本的,他们通过增加一些更加详细的舞台指导和简短对话将这些舞台演出本改编成了供阅读的案头剧本。”[6]从而否定了郑骞先生认为《陈抟高卧》现存文本来源于宫廷版本的观点。
伊维德进而指出,通过对现存宫廷演出杂剧文本的研究可以发现,一方面,由于明代初期一再明令禁止舞台上出现皇帝形象,因而那些拥有皇帝这一角色的元刊本杂剧在被改编为明代宫廷剧目时一般都会去掉皇帝角色,而李开先本所存杂剧中有四部仍保留有皇帝这一角色。另外,明代的宫廷演出本“不仅大量减少主演所唱曲子的数量,同时又为剧中其他角色增加大量对白,甚至为他们增加新的演出场景”,[7]因而明代宫廷演出本很少保留较长的完整曲辞。但李开先本中有四部杂剧“都包含四组较长的完整曲辞,最后一组曲辞都较长且复杂,每部剧作的对白都相对较长且具有较强的功能性。”[6]且这些宾白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指导表演,而是便于文人阅读时能更好地理解曲辞。宫廷演出本则是在考虑演出的情况下“被任意自由地编辑出来的”,从这一方面说,李开先所改写的文本与宫廷演出本也有着很大差异。
在此基础上,伊维德教授推测,“这些剧作中的曲辞非常忠实于其元代原始版本的原貌,任何数量和内容上的改动都是非常小的”,“李开先的《改定元贤传奇》本质上是一种混合文本,它结合了许多个体元代剧作家的创造力和一个编辑团队的细致研究。由于这些编辑们非常热衷提升杂剧的地位并坚持其道德教化的性质,这些编辑们也处于将演出脚本改编为文学文本,将娱乐变为艺术这一过程的开创地位”。[6]而更晚出现的《元曲选》以意识形态主导下形成的宫廷演出本为底本,并受传奇大团圆观念的影响,以及“他本人所代表的17世纪早期江南文化精英阶层的审美追求与哲学思考”的驱使,对杂剧文本进行大刀阔斧地改写,不仅在对白和舞台指导方面进行改进,且大量改写曲辞,甚至改动情节,这与李开先主导下的文本改写路径是截然不同的。
二、文化细读:文本改写的背后
通过以上对伊维德教授相关研究的梳理,我们注意到,这位重要的海外汉学家显然并不满足于对中国传统的以文本校阅为基础的版本比勘,事实上,他在仔细校阅元杂剧不同版本的时候,已经从“文本细读”走向了“文化细读”。关于海外古典戏曲研究者的“文化细读”,笔者曾在总结近年来相关研究动向的基础上撰文指出:“海外研究者在娴熟地运用比较文学、文化诗学、女权主义、分析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来解读古典戏曲文学时,不但继承和发扬了英美新批评学派的‘文本细读功夫,事实上,他们已经将以往那种强调文学语言的独特性、文本的独立自主性,崇尚文学研究的客观性,并带有形式主义特点的‘文本细读,发展为一种具有模式化特点的‘文化细读。”[8]“所谓文化细读,就是立足于作品本身的细读但并不停留于机械、枯燥的文字比勘,或者纯文学审美层面的修辞分析,而是细致考察文本各部分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并且将文本阅读与‘互文阅读、文本分析与语境研究综合起来,从作为整体的文化和历史的高度来开展剧本文学的研究。”[8]笔者以为,伊维德教授的元杂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对近年来海外汉学界所盛行的这种“文化细读”,发挥了某些先导的作用。
虽然李开先、臧懋循等明代文人对元杂剧的改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且这些元刊文本从早期商业演出本到明代宫廷手抄本,再到文人案头本,已经有了一个明晰的演变过程。但其中的每一具体环节如何对文本进行改写,又有哪些因素对这种改写造成影响等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仍需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采用新的视角和理论,才能有所突破。伊维德在文本校阅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这些文本改写背后的思想内涵,从而将这种文本校阅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细读”的高度,对以上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以文本细读和版本校阅的方法为基础,找出不同版本杂剧文本之间的细微差别,通过重点关注这些细微差别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意义,从而发现除了刊刻造成文本的差别外,这些杂剧文本被改写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文化层面的因素,包括:文本书写语境的变迁、意识形态的影响、商业性目的以及戏曲表演本身发展演变的要求等。正是这些隐藏其后的文化因素,共同主导着杂剧文本的被改写。
“语境”是一个包含广泛的复杂概念,文本书写的语境是一个历史时空范畴,包括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简单说即是指文本书写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的变迁必然影响文本的书写,戏曲文本的形成与演变也受此影响。
按照伊维德教授的观点,现存元刊杂剧文本是在演出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元杂剧的演出最初是不需要脚本的,然而,主要角色“旦”或“末”一人主唱到底的体制要求为主演者提供一个详细的脚本。有时为了现场观众能更好地理解演员的唱词,也需要为其刊印一种“助听本”,这种文本只提供剧中较难唱段的曲词,而不需要完整的演出脚本。于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所形成的元代杂剧文本便是所谓“元刊本”,这些文本往往只有曲辞而缺少完整的宾白和舞台指导,或者只有主要角色的完整脚本,而缺乏其他次要角色的部分。
到了明初,杂剧被引入宫廷演出,一方面,内廷演出环境的变化要求对演出进行一些改动,主要是减少曲词并大量增加对白。同时,明初一再明令禁止搬演帝王,因而,那些拥有皇帝这一角色的“驾头杂剧”纷纷被改编,皇帝这一角色被替换为朝廷高官或宦官。而李开先所改定的一些杂剧则因不适合在宫廷演出而保留了皇帝这一角色。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杂剧文本因语境的变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被不同程度改写,而与元代形成的文本有了较大差异。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方面,意识形态决定着哪些剧作可以在宫廷上演,而哪些不合适,这就直接影响杂剧文本将如何被改写。比如上面提到的《陈抟高卧》,我们所见到的李开先本仍保留了皇帝角色,就可证明其在当时不适合在宫廷演出,因而其文本改写也与宫廷本不同。再如,关于汉朝建立的故事在元代演出很盛行,而这些剧作对帝王这一角色都持否定态度。考虑到朱元璋的低微出身,以及他对功臣的残酷迫害,还有马皇后的强势性格,这些都与刘邦和吕后的故事很相似。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代朝廷会禁止在舞台上扮演帝王后妃了[9]。这些意识形态对明代宫廷有关汉代建立故事题材杂剧的演出起到了抑制作用,也对后来关于汉代灭亡的三国故事的盛行产生影响。这也就启发了我们另一方面的思考,通过对意识形态如何影响戏曲的考察,我们发现,戏曲演出有时也会反过来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如上所述,元代关于汉朝建立题材杂剧演出的盛行就影响了明初朝廷对戏曲的态度。
除语境变迁和意识形态之外,杂剧表演自身的演变以及文人、书商的商业目的都会对杂剧文本的演变造成影响。以元刊本《拜月亭》为例,伊维德教授细致分析了这一文本的舞台指示和宾白部分,以此来考量元杂剧舞台表演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而从表演的角度反观文本形态。通过对《拜月亭》文本中的演员穿戴、上下场、宾白以及动作科范内容的分析,伊维德指出,在元代,杂剧主要处于民间商业演出阶段,演员对表演早已烂熟于心,除了主演有时需要脚本之外,其他演员则需要靠演出时临场发挥,也许剧作家“仅仅写出粗略的剧本大纲,同时为那些主演分别写出不同的角色文本”[7]。
明初,杂剧主要在宫廷演出,除了去掉皇帝这一角色外,“宫廷演剧能容纳更大的演出团队,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一些次要角色的不断扩张,这种扩张是以牺牲主要角色的唱腔,尤其是最后一折的唱词为代价的。”另外,那些批判社会以及无关风化的剧作也在减少,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元杂剧的文本内容[6]。
此外,还有一个影响杂剧文本的重要因素,就是读者市场的需求。伊维德认为,元代最需要杂剧文本的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而书商们最便利的方式便是从主演那里得到脚本,这直接影响了元代的杂剧文本形态[2]。到了明中后期,杂剧的演出衰歇,一些文人和书商为了迎合阅读趣味,选择那些受欢迎的杂剧文本,并将其改编为方便案头阅读的文本,这便是李开先和臧懋循等人对文本改写的导向[5]。
正如何博在《文化细读:北美学界明清传奇研究的新模式》一文中所总结的,北美英语学界的中国戏曲研究一直秉承着“文本细读”的传统,但20世纪末以来,他们的“文本细读”在“文化诗学”理论的影响下,呈现出对传统细读模式的全面超越,开始转向“文化细读”的模式。何博在文中借用申丹所提出的“整体细读”理论,认为只有从“文本细读”上升到“文化细读”,通过这种“整体细读”的模式,“才有可能挖掘出作品中至今仍未见天日的隐含文本,对作品进行更深度或者全新视角的阐释。”[10]伊维德教授对元杂剧的研究,正体现了这种从文本到文化的超越模式,从而能够将元杂剧的文学性与社会性结合起来,挖掘出隐藏在文本之外的文化内涵。
三、反思与启发
伊维德教授继承了荷兰汉学重视原始资料和文本文献的传统,他在元杂剧研究中采用“文本细读”与“文本校阅”相结合的方法,对现存元杂剧文本的版本进行“考镜源流”的辨析,找出那些不为人注意的细微差别,发现掩藏在文本改写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特别是语境、意识形态、戏曲表演等因素,从而将其研究提升到“文化细读”的高度。“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以为,这种研究方法与思路可以引起我们多方面思考:
首先是“文本细读”法的运用。
这一方法在欧洲和日本的汉学界都广受重视,尤其是运用于研究中国经学、古典诗词和现代诗,然而,在小说、戏曲等叙事性文本的研究中尚不多见。国内的戏曲研究虽早已有“文本校阅”的方法,但大多停留在通过对校不同版本的差异来考察文本的版本分疏,而缺乏更进一步的理论性思考。伊维德教授将“文本细读”移植到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中时,积极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文本校阅”法,常常能在细读剧本的过程中发现通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道白和舞台指示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对这部分内容的“校阅”,才使其发现了文本改写所蕴藏的文化内涵。
反观国内的戏曲研究,我们在阅读文本时,很多细微信息往往被不经意地忽略掉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文本阅读不够仔细或囿于成见,但更重要的可能却是缘于我们因“熟悉”而产生的某种障碍。这时,一种“陌生化”的视角就显得尤为重要,而“文本细读”正是出于“陌生化”的需要。海外汉学家之所以常常能从平常的文本中读出新意,恐怕正是由于其“陌生”的缘故。对此,郭英德先生曾评价说:“北美地区学者身居异域,擅长运用‘他者的眼光观察中国古典戏曲,捕捉和审视中国学者习焉不察或置之不顾的学术话题……他们能够对中国古典戏曲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与剖析,得出一些富于启发性的结论,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11]汉学家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也说过:“正是因为有了‘距离的组织,自然提供了不同的、相对冷静的视角看待问题”[12]国内的研究者虽然没有这种天生的“他者”眼光和“距离”,但是,“文本细读”这一方法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途径,正如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所说:“从文本出发的细读,正是摆脱成见的一个好方法。”[13]
其次,将文本作为研究的本体,而非语境。
宋耕先生在伊维德和奚如谷(Stephen H. West)对元杂剧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的思考:文学研究是应该从文本出发还是从语境出发?宋先生指出,我们长期以来都是“主观地从语境本身出发,生搬硬套地将结论套在文本上”。[14]这样一来,我们在读文本之前已经对一些问题有了一种先验的假设,这时再去读文本只是来确认这种假设,而难以发现新的问题。以伊维德教授为代表的海外学人的这种以文本为本体的方式,也许对我们一直强调的“知人论世”方法的偏差能有所纠正。但从文本出发并非不考虑语境,伊维德在研究中也很重视发掘那些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信息,从“文化细读”的高度来阐释文本改写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他曾说:“我们研究文学,一方面要详细地阅读文本,若不读肯定不行……另一方面,需要考虑文本之外的情况,比如背景等等。”[15]事实上,伊维德将语境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看作元杂剧文本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可见其对文本之外的文化内涵的重视。
第三,重视对元杂剧宾白和舞台指示等因素的研究。
总体而言,我们的古典戏曲研究更关注曲辞,而忽略宾白和舞台指示。即便如孙楷第、郑骞这样的名家,在文本校阅和细读的过程中也是重点考察曲辞的变化,而对宾白和舞台指示有所忽略。伊维德在戏曲研究中非常重视文本的整体性,对宾白和舞台指示等内容进行了反复细读和校阅,才能有新的发现。另外,将文本与表演结合起来研究,关注文本之外的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也是伊维德在研究中比较重视的思路。20世纪末以来,北美地区的戏曲研究开始注重对经典剧作的“重读”,如何从“旧作”中读出新意,从前人反复耕耘的土地培育出新苗,这就需要新的视角和方法。我们的古典戏曲研究是否有必要“重读”经典,这或许是伊维德等海外汉学家为国内研究者所留置的一个更有价值的问题。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的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选择,本着“批评性研究”的态度对海外汉学进行反思,取长补短,或许是我们传统文化研究走向新变的必经之路。
注释:
①参见王筱芸的《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群体综述:以20世纪80至90年代为中心》,《国际汉学》2011年第1期; 季进、王吉的《说唱文学与文学生产:哈佛大学伊维德教授访谈录》,《书城》2012年第2期;霍建瑜的《徜徉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广场:伊维德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2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邓绍基.古典戏曲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Wilt L.Idema. The Many Shapes of Medieval Chinese Plays: How Texts Are Transformed to Meet the Needs of Actors, Spectators, Censors, and Readers[J].Oral Tradition,2005,20(2): 320334.
[3]Wilt L. Idema. The Remaking of an Unfilial Hero: Some Notes on the Earliest Dramatic Adaptations of the“Story of Hsüeh Jenkuei”[M]∥As the Twig is Bent.Essays in Honour of Frits Vos, ed. by Erika de Poorter (Amsterdam: J.C. Gieben) 1990:83111.
[4]伊维德.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J].宋耕,译.文艺研究,2001(3):97106.
[5]伊维德.元杂剧:版本与翻译[J].凌筱峤,译.文化遗产,2014(4):4656,157158.
[6]Wilt L.Idema. Li Kaixians Revised Plays by Yuan Masters (GaidingYuanxianchuanqi) and the Textual Transmission of Yuan Zaju as Seen in Two Plays by Ma Zhiyuan[J]. Chinoperl Papers ,20052006(26):4766.
[7]Wilt L.Idema. Some Aspects of Paiyüeht'ing: Script and Performance,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uan Hanch'ing[C].ed. by Tseng Yongyih .Taipei: Faculty of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94:5577.
[8]程芸,何博.英语学界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的新动向(20072011)[J].戏曲研究,2012(3):171189.
[9]Wilt L. Idema. The Founding of the Han Dynasty in Early Drama: the Autocratic Suppression of Popular Debunking[M]∥W.L. Idema and E. Zürcher, eds., 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SinicaLeidensia XXIII . Leiden: E.J. Brill, 1990:183207.
[10]何博.文化细读:北美学界明清传奇研究的新模式[J].戏曲研究,2013(2):158171.
[11]郭英德.中国趣味与北美地区中国古典戏曲研究[J].戏剧艺术,2010(1):418.
[12]木叶.王德威汉学研究趋向融通[N].文汇报, 20101018.
[13]张宏生.对传统加以再创造,同时又不让它失真:访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斯蒂芬·欧文教授[J].文学遗产,1998(1):111119.
[14]宋耕.文本、语境与意识形态:海外元杂剧研究及其启示[J].国际汉学,2003(1):273285.
[15]伊维德,刘涛.为学与为师[J].西湖,2009(11):99105.
(责任编辑文格)
Abstract:The main feature of the Dutch sinologist Wilt L. Idema's research on Yuan Zaju is that he combines Chinese traditional method of “comparative texts review” with western method of “close reading” elevating them to “cultural close reading”.In his point of view,the texts of the dramas formed in Yuan Dynasty have been rewritten in the Ming Dynasty via two distinctive ways.However,these adapted texts are restricted by certain leading factors,such as the context,ideology,commercial purposes and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etc.The ideas and perspectives which Wilt Idema employs in his research on Yuan Zaju can provide various references or inspirations for the domestic studies of dramas.
Key words:Wilt L. Idema;Yuan Zaju;Yuan Qu adapted;cultural clos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