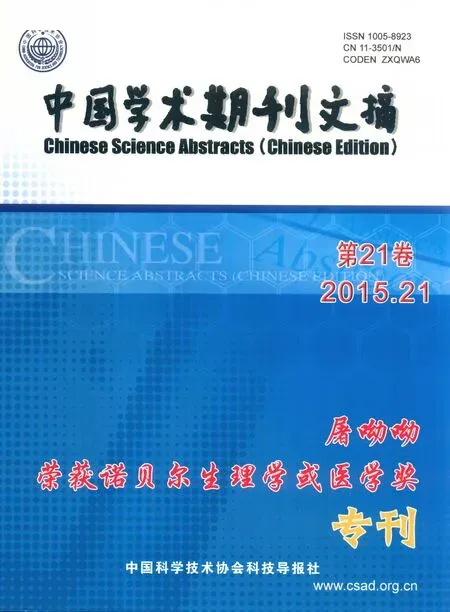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抗肿瘤特性研究进展
杨华,谭先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北京100730)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抗肿瘤特性研究进展
杨华,谭先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北京100730)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癌症已然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最大危险因素之一,而目前的抗癌药经常会产生对正常组织细胞的细胞毒作用以及出现肿瘤细胞的耐药现象。因此,找到一种高效且特异性强的抗肿瘤药物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青蒿素是从菊科植物黄花蒿的叶和花蕾中提取的有效抗疟疾成分,含内过氧化基团的倍半萜内酯化合物,主要衍生物有双氢青蒿素、蒿甲醚、蒿乙醚等。与传统肿瘤药物相比,青蒿素类药物可选择性杀伤肿瘤细胞,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其不良反应,同时很少存在交叉耐药现象,最大程度发挥其抗肿瘤作用。近年来人们开始对青蒿素类药物的抗肿瘤作用机制进行大量研究,以期进一步明确其作用靶点,为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奠定基础。
青蒿素类药物的抗肿瘤机制
青蒿素衍生物在体外和动物模型中都显示出其特有的抗肿瘤作用。一项对体外55种细胞系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青蒿琥酯对白血病、大肠癌、黑色素瘤、乳腺癌、卵巢癌、前列腺癌和肾癌细胞均有抑制作用[1]。双氢青蒿素对胰腺癌、白血病、骨肉瘤和肺癌细胞的抗肿瘤作用甚佳[2]。蒿淀粉单用或与其他配伍药合用的协同抗肿瘤作用均比青蒿素要强[3]。双氢青蒿素、青蒿琥酯和青蒿醚可通过协调肿瘤细胞生长、凋亡、增殖、血管形成、组织浸润和转移的基因和蛋白表达来发挥其抗肿瘤作用。这类含有过氧化桥结构的药物对肿瘤细胞的杀伤和控制是通过相当复杂的不同通路间相互作用完成的。
活性结构青蒿素类药物的抗癌活性位点与其抗疟疾作用的位点相同,起主要作用的部分仍为其过氧化桥结构。研究显示,过氧化桥部分的缺失虽然不能使其抗癌能力完全消失,但却大大削减了其抑制肿瘤细胞的效果。因此,青蒿素类药物的一部分抗癌机制是非过氧化桥依赖性的[4-7]。研究证实,铁、血红蛋白或血红蛋白结合蛋白都参与了青蒿素类药物的活性作用[8-10]。在体内大多数系统中,癌细胞中富含的铁激发了青蒿素类药物的细胞毒作用[11-14]。而且,青蒿素类药物与携带铁的复合物结合时发挥作用远比不含铁时作用强很多[15-17]。有研究表明,应用琥珀酰丙酮,一种血红蛋白合成抑制剂,可减轻双氢青蒿素对 HL-60(人前髓细胞性白血病细胞)的细胞毒作用[14]。同样,给予铁离子螯合剂也可降低其药效[18]。与正常细胞相比,癌细胞核酸代谢旺盛,需要大量铁质,多数肿瘤细胞表面有高密度的转铁蛋白受体,而正常细胞转铁蛋白受体较少,从而使青蒿素类药物对肿瘤细胞的作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活性氧簇作用青蒿素类药物的过氧化桥结构与亚铁原子起反应后断裂可产生以碳为核心的自由基或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这些自由基可通过促进凋亡、抑制细胞增殖及血管形成,或直接损伤DNA 等途径发挥其抗肿瘤作用。研究显示,青蒿素类药物的细胞毒作用与细胞质裂解、强氧化应激以及抑制肿瘤浸润和转移相关[19]。ROS在青蒿素类药物对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杀伤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肿瘤细胞由于缺乏抗氧化酶而使其更加容易受到ROS的损伤,因此,强氧化应激是抗肿瘤药物抗肿瘤作用的普遍机制。对于青蒿素类药物处理过的肿瘤细胞,通过显微镜可以观察到由于ROS的作用使其亚细胞器发生早期胀亡的形态学改变。
与此同时,微点阵分析发现青蒿素类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通过氧化应激酶调控的。对青蒿素类药物敏感的细胞下调氧化应激酶,而氧化应激酶的过表达使肿瘤细胞降低了对青蒿素的敏感性[1]。对HL-60细胞系的研究显示,ROS较早(1 h)且快速的产生与诱导凋亡相关,而且IC50与ROS的水平直接相关[20]。一项新研究发现,青蒿琥酯作用过的Hela细胞其ROS产生的时间(16 h)比其细胞毒作用(48 h)的显效时间早,从而说明ROS的作用可能是青蒿素类药物损伤作用的启始因子[14]。线粒体中的电子传递链在ROS的产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Hela细胞中发现了与电子传递链不相关的ROS的产生,表明Hela细胞中可能存在其他产生ROS 的途径。
青蒿素的抗瘤性也许还受Ca+代谢、内质网应激和翻译控制肿瘤蛋白表达(translationally controlled tumor protein,TCTP)的调节,TCTP通过与钙离子结合产生作用[1,12,21]。虽然最初认为TCTP基因的表达与青蒿素的抗肿瘤活性相关,但目前还没有找到证据来证明此种相关性。肌浆钙离子三磷酸腺苷酶(sarcoendoplasmic Ca2+ATPase,SERCA)在青蒿素抗肿瘤机制中的作用与其抗疟疾的机制相似。以往研究表明,10 μmol青蒿素就可以使细胞内钙浓度升高从而抑制SERCA的作用[22]。然而,关于青蒿素二聚体作用机制的研究显示,ROS介导的内质网应激与SERCA抑制不相关。青蒿素二聚体与毒胡萝卜肉酯(SERCA抑制剂)的活性相似,但由于毒胡萝卜肉酯缺乏内过氧化桥部分并且生成很少的ROS使它们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
各项实验研究均显示出青蒿素类药物的多效性,然而其抗肿瘤细胞的细胞毒作用机制是根据与肿瘤细胞作用的特殊位点及其特性而改变的,因此,青蒿素类药物的抗肿瘤机制有待进一步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细胞调控作用肿瘤细胞不可控性的增殖多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细胞增殖信号扩大以及对生长抑制信号敏感度下降,细胞程序化死亡和凋亡的异常也可引起异常的细胞增殖。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可以通过干扰细胞周期动力学或阻断增殖通路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大量研究证实,双氢青蒿素和青蒿琥酯是青蒿素类衍生物中抗肿瘤潜能最佳的两种衍生物,而双氢青蒿素的作用比青蒿琥酯更强[1,23]。有研究表明,淀粉对包括黑色素瘤和乳腺癌在内的7种细胞系有明显的抗肿瘤作用[3]。青蒿素类药物对肿瘤细胞可产生细胞抑制和细胞毒作用[3,24]。青蒿素类药物可通过影响肿瘤细胞周期中的任何阶段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其中最普遍的影响是对G0/G1~S期的抑制。对肿瘤细胞整个周期中各阶段同时产生影响的作用被称为细胞抑制作用。双氢青蒿素可影响骨肉瘤、胰腺癌、白血病和卵巢癌细胞的G2/M期,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同样,青蒿琥酯也可以干扰骨肉瘤、卵巢癌和其他不同类癌细胞的 G2期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25,26]。目前认为,青蒿素类药物抑制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变细胞周期中调节酶的表达和活性来完成的。青蒿素类药物可通过降调周期蛋白依赖激酶(cyclindependent kinases,CDK)的转录活性、抑制CDK启动子或增强CDK抑制剂的活性来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活性。双氢青蒿素可抑制核转录因子kappa B(nuclear factor-kappa B,NF-κB)的活性从而阻止胰腺癌细胞的增殖而促进其凋亡[27]。对于肺癌细胞(SPC-A1),双氢青蒿素可通过下调survivin 蛋白(一种调控凋亡和细胞周期中G2/M期的蛋白)来抑制其细胞增殖[27-28]。总之,青蒿素类药物对不同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是通过干扰多种途径实现的。
凋亡调节作用凋亡在抗肿瘤治疗中的研究颇为深入,因为对肿瘤细胞凋亡的调控是控制肿瘤生长的一项有效的治疗途径。细胞的凋亡过程受到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2(B-cell lymphoma /leukemia-2,Bcl-2)基因家族的调控,包括促凋亡基因Bax和抗凋亡基因Bcl-2,以及这两种基因对线粒体的作用[29-30]。Bax/Bcl-2比值的增高引起了细胞色素C的释放从而激活了细胞凋亡蛋白酶导致细胞死亡[30]。在多种肿瘤细胞系中,青蒿素类药物均能快速使细胞发生凋亡现象。200 μmol /L的双氢青蒿素作用白血病细胞1 h即可诱导凋亡现象的发生[8]。对肿瘤细胞凋亡诱导作用的敏感性与此肿瘤细胞中抗凋亡基因Bcl-2及促凋亡基因Bax的表达相关。大量研究表明,青蒿素类药物通过调控Bax /Bcl-2的比值来诱导细胞凋亡[9,16,22,31-33]。研究发现,双氢青蒿素和青蒿琥酯可促进骨肉瘤细胞的细胞色素C释放、Bax过表达、Bax/Bcl-2比值增高以及细胞凋亡蛋白酶3和9激活,而发挥其促凋亡作用[16,34]。一项微点阵分析研究显示,c-myc的表达水平与双氢青蒿素诱导的凋亡能力相关,高表达c-myc的白血病细胞(HL-60)和结肠癌细胞(HCT116)对双氢青蒿素引起的促凋亡作用更明显,而且,双氢青蒿素对将c-myc基因敲除后的HCT116细胞的促凋亡作用明显减弱,c-myc 基因的降调与此细胞G1期的增殖抑制相关[9]。对于转移性黑色素瘤细胞(A375,G361)和Jurkat T淋巴细胞的研究表明,双氢青蒿素的促凋亡活性与NOXA (一种促凋亡蛋白)的上调、细胞凋亡蛋白酶3的激活以及氧化应激相关[35-36]。在肺组织细胞中,双氢青蒿素通过提高钙浓度和p38的活性而促进凋亡[37-38]。诱导凋亡是青蒿素类药物抗肿瘤作用的最佳之处,因为凋亡可以避免炎症的不良反应以及坏死引起的细胞损伤。
抑制血管形成对恶性肿瘤的患者来说,恶性肿瘤细胞的侵袭能力与其病死率和发病率相关。肿瘤细胞播散到原发灶以外其他器官的过程是恶性肿瘤细胞穿过细胞外基质到达血管并在其中存活,而最终种植在远处器官。E-钙黏蛋白(一种结合Ca2+的跨膜蛋白,在细胞黏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表达和无功能是肿瘤细胞侵袭的重要条件。一系列基因编码的细胞外基质蛋白酶、活性因子和黏连蛋白均在肿瘤转移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发挥作用。近来研究发现,纤溶酶原激活抑制剂1(plasminogen activator inhibitor 1,PAI-1)和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TIMP-1)与肿瘤的转移相关[39]。青蒿素类药物的最大益处在于它对高度恶性和强侵袭能力的肿瘤仍有抗转移能力,而其抗转移能力与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基因家族的表达相关。12.5 μmol /L青蒿素可使肝癌细胞系(HepG2和SMMC 7721)的MMP2减少、TIMP-2增多,从而降低其转移能力。同时青蒿素可通过增加E-钙黏蛋白的活性或激活Cdc42来增强细胞间的黏附作用而抑制肿瘤转移[40]。研究表明,不同的肿瘤细胞其抗转移能力是通过不同的介质表达的,例如:在非小细胞肺癌和纤维肉瘤中,双氢青蒿素通过AP-1 和NF-κB 的反式激活或失活使MMP2、MMP7和MMP9的表达水平下降[37,41]。还有研究表明,在老鼠的肺Lewis瘤中,青蒿素可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的作用来延迟淋巴结的转移及淋巴血管的形成[42]。
恶性肿瘤组织的生长、转移和成瘤需要大量的血供才能维持,因此,肿瘤细胞通过调节与新血管系统形成和重建相关的蛋白和通路来诱导新血管的形成。在血管形成的过程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bFGF)及其受体和细胞因子的作用是使内皮细胞大量增殖,其作用机制包括缺氧所导致的缺氧诱导因子-1α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 alpha,HIF-1α)和芳香烃受体核转运蛋白的激活等多种机制。血管的形成受到血管生成抑制因子、内皮抑制因子、凝血酶敏感蛋白、TIMPs、PAI-1和其他因子的共同调控。鉴于它们在肿瘤形成中的作用,前血管形成因子以及调控血管形成的任何分子均可成为抗肿瘤治疗的靶点。微点阵分析研究显示,青蒿素、青蒿琥酯和其他青蒿素类衍生物通过调节血管形成因子基因的表达来抑制新血管的形成[43]。青蒿素类药物可通过降调生长因子(VEGF和FGF)、HIF-α、血管生成素(angiopoietin,ANG)、富含半胱氨酸血管形成诱导素 61、金属蛋白酶(MMP9、MMP11、BMP1)和胶原来抑制血管形成。同样,青蒿琥酯也通过上调血管形成抑制剂而抑制血管形成[43-46]。50 μmol /L双氢青蒿素通过降低VEGF flt-1和KDR/flk-1的受体来抑制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血管形成能力,同时在淋巴内皮细胞和 Lewis肺肿瘤细胞中存在同样效果[47-48]。在胰腺细胞(BxPc-3)和Babl /c裸鼠中,双氢青蒿素通过抑制NF-κB的DNA结合以及下调其血管形成相关靶点(如VEGF、IL-8、Cox2和MMP9)而抑制血管形成[49]。以往研究显示,NF-κB水平的降低与抑制肿瘤增殖和转移相关,表明NF-κB的调控是双氢青蒿素抑制肿瘤作用的关键。总之,NF-κB 在抗肿瘤药物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青蒿素类衍生物还显示出其他的抗肿瘤特性,青蒿琥酯可以通过负调控Wnt信号通路使组织细胞重新分化。
青蒿素类药物的临床应用
青蒿素类药物的抗肿瘤作用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并已经开始应用到个别临床案例中[6,50-51]。蒿甲醚和青蒿琥酯在抗肿瘤治疗中显示出非常好的耐受性和非常少的不良反应。青蒿琥酯可有效治疗喉部鳞状细胞癌,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可显著减小肿块体积[51],而且青蒿琥酯和标准化疗药物联合应用可增加皮肤癌患者的生存期,减少肿瘤转移率[6]。此外,蒿甲醚半衰期长,且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因此用蒿甲醚治疗巨型垂体腺瘤可显著提高疗效。一项对120例晚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研究显示,青蒿琥酯联合长春瑞滨以及顺铂可使晚期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一年生存率提高13%,并可显著提高疾病控制,抑制疾病进展[50]。值得一提的是,青蒿琥酯的不良反应很少。
青蒿素类药物的抗肿瘤前景
青蒿素类药物的抗疟疾治疗已经应用于临床多年。近来研究显示,青蒿素类药物拥有很多新的生物活性,最受关注的当属其抗肿瘤活性。有证据表明,青蒿素类药物对恶性度高、转移能力强的肿瘤是很好的治疗选择,而且,其抗疟疾机制中的过氧化物桥可协同其他抗肿瘤药物一起杀伤肿瘤细胞而没有增加不良反应。
研究表明,青蒿素类药物通过多种不同的分子途径实现其抗肿瘤作用,然而,青蒿素类药物导致的细胞死亡机制尚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对青蒿素类药物发挥其药效的决定簇研究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青蒿素类药物活性中抗肿瘤作用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了,精确的分子机制(如在肿瘤细胞中ROS怎样、何时、在什么部位被激活)仍未得出确切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与ROS不相关的作用机制应该引起关注,因为这些在抗疟疾作用中没有明显作用的机制有可能是青蒿素类药物对一些肿瘤细胞发挥细胞毒作用的关键。此外,青蒿素类药物所产生的DNA直接损伤和P53 基因毒性作用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青蒿素类药物真正的潜质及优势仍有待研究、探索与发现,但目前研究所发现的强大的抗肿瘤作用足以使其成为抗肿瘤药物研究中的焦点,为肿瘤治疗开拓一片新天地。
摘编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466~471页,图、表、参考文献已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