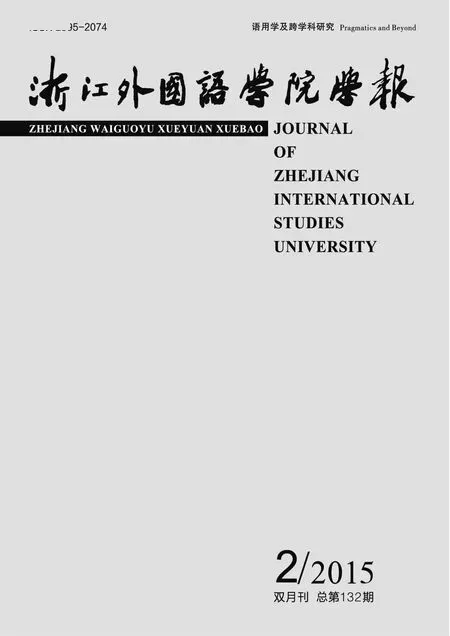从《象的失踪》到《再袭面包店》
——谈两篇小说中的“我”
关冰冰,杨炳菁
(1.浙江外国语学院 欧亚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2.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北京 100089)
从《象的失踪》到《再袭面包店》
——谈两篇小说中的“我”
关冰冰1,杨炳菁2
(1.浙江外国语学院 欧亚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2;2.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语系,北京 100089)
无论从小说内容还是研究脉络来看,《象的失踪》和《再袭面包店》除均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外,完全是两篇不同的小说。但加藤典洋从“我”与女性关系入手,将两篇小说联系在了一起。对文本详加考察就会发现,从“我”与其所处社会之间的关系入手将会进一步探明这两篇小说所具有的延续性。
村上春树;《象的失踪》;《再袭面包店》;“我”
一、前言
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象的失踪》(「象の消滅」)和《再袭面包店》(「パン屋再襲撃」)同是发表于1985年8月的作品。虽然刊登两篇作品的杂志风格不同,读者群也不尽一致,但它们均受到好评并被日本文学研究界所关注。
《象的失踪》是由“我”讲述的大象消失的故事;而《再袭面包店》则描绘了“我”和妻子在深夜对麦当劳进行的一次抢劫。除均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外,两篇小说看似毫无相似之处。但日本评论家加藤典洋却在其专著《用英语阅读村上春树的短篇1979~2011》中将二者联系到了一起。加藤认为,与其他短篇小说集相比,这部收录了《再袭面包店》《象的失踪》《家庭事件》(「ファミリー·アフェア」)等六个短篇的小说集的特色,在于所收录的短篇集中发表于1985年8月至1986年1月这短短的5个月中。而其中《再袭面包店》《象的失踪》和《家庭事件》是可以被称为“前期三部曲”的一组作品。具体而言,在《象的失踪》中,“我”由于未能从某种闭塞的状态下恢复过来而错失与女编辑的进一步交往;《再袭面包店》中,“我”在妻子的帮助下从某种闭塞的状态下得以恢复;《家庭事件》中,“我”和自己妹妹的相处则显示其恢复的中间状态[1]。
考察加藤将《再袭面包店》《象的失踪》以及《家庭事件》称为“前期三部曲”的理由会发现,加藤是通过小说中“我”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将这三个短篇联系起来的。这一论述存在合理性,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从三篇小说的内容来看,《家庭事件》完全是以“我”和女性的关系为主旋律的,而在《象的失踪》和《再袭面包店》中,“我”与女性之间的关系仅是小说中的部分内容。因此,如果抛开“我”与女性这一观察视角,便可以发现,在《象的失踪》和《再袭面包店》之间,较之“我”与女性这一内容,“我”自身所发生的变化更能体现这两篇小说之间的联系。即在《再袭面包店》与《象的失踪》中,“我”具有一种“延续性”。《象的失踪》中“我”所遗留的问题可以通过解读《再袭面包店》中有关“我”的情况加以解释和说明。
为了阐明两篇小说中“我”所具有的“延续性”,解决《象的失踪》中“我”所遗留的问题,本文将首先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对《象的失踪》中的“我”和《再袭面包店》中的“我”分别予以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揭示两个短篇中“我”所具有的“延续性”。
二、《象的失踪》中的“我”
《象的失踪》以“我”的口吻叙述了一头老象突然失踪的故事。村上虽然借助“我”讲述了象的离奇失踪,却没有提供失踪的真相。而更为有趣的是,“我”的叙述并非全都与“象的失踪”有关。小说用大量笔墨刻画了“我”的生活、工作及与人交往,这些不但与“象的失踪”没有直接关联,而且对破解失踪真相也毫无帮助。对于此种看似奇怪的处理,笔者曾作过分析并得出如下结论:“‘我’其实并不仅仅充当‘象的失踪’这一事件的叙述者。在‘我’的内部同时存在着高效合理与‘不合时宜’的两个‘我’,而那个‘不合时宜’的‘我’与象具有共通性,也是以象为外部载体的。”[2]77这就是说,大象其实代表的是不合时宜的“我”,大象的失踪象征着不合时宜的“我”的消亡。然而,小说并没有在大象失踪之后立即结束,小说临近结尾处有这样两段描写:
自从经历大象失踪事件以来,我时常出现这种心情,每当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我往往感到周围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大象事件之后自己内部的某种平衡分崩离析了,从而导致外部事物在我眼中显得奇妙反常。责任怕是在我这一方。
我仍然在这急功近利式的世界上依据急功近利的记忆残片,到处推销电冰箱、电烤炉和咖啡机。我越是变得急功近利,产品越是卖得飞快。我们的产品宣传会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我们不无乐观的预想。我于是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许人们是在世界这个大厨室里寻求某种谐调性吧。式样的谐调,颜色的谐调,功能的谐调。[3]44
两段话分别描写了大象失踪对“我”产生的影响以及大象失踪后“我”的状态。第一段话的内容让人明白,“自从经历大象失踪事件以来”,“我”就无法在某种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这就是说,“我”已丧失了对事物进行判断的能力并由此进入到一个无法进行选择的状态。“我”之所以如此,是缘于“自己内部的某种平衡分崩离析了”,而这种平衡的“分崩离析”则是由“象的失踪”所引发的。如果“象的失踪”代表着不合时宜的“我”的消亡的话,那么,不合时宜的“我”的消亡便导致了判断和选择能力的丧失。
不合时宜的“我”虽然消亡,但高效合理的“我”却依然存在。第二段话便是对处于此种状态下的“我”的描写。高效合理的“我”在社会上是成功的。因为“我”不仅销售业绩飞涨,而且与周围人的关系也日益融洽。而这些皆来自于高效合理的“我”所拥有的功利性和协调性。
由上述两段话可以推导出以下两点:其一,高效合理的“我”具有功利性和协调性却承担不了判断机能,但也正由于此,“我”才会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其二,虽然不合时宜的“我”承担了判断机能,但最终却无法摆脱被社会消灭的命运。那么,综合这两点便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个体是不能拥有判断力的。决定其生存好坏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个体的判断力而在于是否具有良好的功利性和协调性。
在《象的失踪》中,“我”以象的失踪为界发生了质变。此种质变的具体内容就是“我”从一个能对事物进行判断的人变成了一个毫无判断能力的人。而对比质变前后的不同便可以明白,村上是通过大象失踪这一离奇事件,来批判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泯灭个体判断力、只注重功利性和协调性的弊端。但这里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为何只有不合时宜的“我”才能承担判断机能,而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又注定被消灭?对于这个问题,小说并没有给出解答,而仅是在小说临近结尾处的两段话中描写了人们对大象的遗忘以及即将到来的冬日的肃杀情景,并以“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3]44结束了全文。
三、《再袭面包店》中的“我”
《再袭面包店》主要描写了“我”和妻子对麦当劳的抢劫。从叙述时间来看,该小说比《象的失踪》复杂,其中存在着回忆整个事件的现在;“我”与妻子婚后两周极度饥饿下的谈话及抢劫的深夜;“我”与同伴对面包店进行袭击的十年前这三个时间点。其中,“我”既是叙述者又是主人公。
(一)初袭面包店时的“我”
“我”与同伴的抢劫虽然只出现在对妻子的讲述中,但从时间顺序看却是最早发生的。彼时的“我”和同伴都“一贫如洗”[3]6,于是对一家面包店实施了抢劫。抢劫“可以说成功,也可以说不成功”[3]7,因为填饱肚子这一结果,并非通过真实的抢劫,而是以听瓦格纳的音乐为条件实现的。在那之后,“我”回到学校完成学业,毕业后进入律师事务所并与现在的妻子结了婚。
通过“我”的讲述可以知道,抢劫源于饥饿感,而之所以产生饥饿感则是因为当时的“我”和同伴“懒得做什么工”[3]7。也就是说,当时的“我们”拒绝以工作的方式赚取可以买面包的钱。如果说打工挣钱买面包是一种通常的社会行为的话,那么“我”和同伴拒绝工作,并企图以抢劫的方式获取面包就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拒绝工作的“我们”“虽然贫穷但却保持了自我主体性”[4]24,而这样的“‘我们’如果顽固地持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性’的话,便只能与‘现实’对立并格斗”[4]24。
虽然“我”和同伴坚持主体性,以“反社会”的姿态进行了抢劫,但面包店老板提出以听瓦格纳音乐来换取面包,这使“我们失去了战斗对象”[4]24,坚持自我主体性的企图也就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我们从那次事件中受到的打击要比表面上的强烈得多……我们还是觉得里边存在着某种严重的错误。这种谬误给我们的生活投下了阴影”,“瓦格纳音乐”从此成为“不容有任何怀疑余地的紧箍咒”[3]10,“我”最终放弃与现实对立回到学校,并与大多数人一样在毕业后进入社会,成为其中一员,从而“被纳入到‘现实’当中”[4]24。“‘我们’被‘现实’吞没整合,那是与所谓世界是何物的现实相对峙的世界观的丧失。而丧失与‘现实’对峙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主体’的根基、自我的基础的丧失。”[4]24
综上所述,初袭面包店是“我”和同伴固执于自我主体性的行为。经历了那次抢劫,“我”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并被社会所吸纳,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
(二)再袭面包店时的“我”
“我”和妻子的抢劫无疑构成了小说的主干。当时的“我”已经“返回大学顺利毕业出来,一边在法律事务所工作,一边准备参加司法考试”[3]9。与此同时,“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结了婚。相比十年前,“我”可以说是发生了质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并建立了家庭,这是非常符合现代社会常态的生活模式。“我”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可见的物质层面,而且体现在相对隐秘的精神层面:
我至今也弄不清楚将袭击面包店的事告诉妻子是否属于正确的选择,恐怕这也是无法用正确与否这类基准来加以推断的问题。就是说,世上既有带来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也有造成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为了避免出现这种非条理性——我想可以这样说——我们有必要采取实际上什么也未选择的立场,我便是大体抱着如此态度来生活的。发生的事情业已发生,未发生的事情尚未发生。[3]1
这段话虽然是现在的“我”对再袭面包店的回忆,然而“至今”一词表明,不论是现在还是当初对妻子讲起第一次袭击的那个夜晚,“我”都无法对自己行为的正确与否进行判断。这就是说,在对麦当劳实施抢劫时,“我”已然是一个对事物缺少判断力,甚至连判断行为都要放弃的个体。这种精神层面的变化是由第一次抢劫直接造成的。在第一次抢劫后,“我”失去了自我主体性,失去了选择和判断的能力,因此第二次抢劫中的所有一切都是在妻子的主导下得以完成的。“再袭”“是恢复夫妻的‘主体’,以真实的自我面对现实并生存下去,为获得此种自我而进行的殊死搏斗”[4]25。虽然“我”的表现决不能说是一种积极的、恢复自我主体性的行为,但引发“我”此次“再袭”行为的同样是“饥饿感”。
小说以海底火山形象地描写了“我”的“饥饿感”。如前所述,“饥饿感”是“我”与同伴进行第一次抢劫的原因。彼时的“饥饿感”是“我们”固执于自我主体性而与现实进行反抗的结果。第一次抢劫后,“我”虽被社会吸纳,但以“饥饿感”为表征的“我”的自我主体性却并未彻底消失而是如火山般沉入大海。而火山能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就随时可能再次爆发,这便如同“我”的自我主体性总会有恢复的冲动一般。而新婚两周后的深夜,“饥饿感凶猛得那般异乎寻常”,“就像心窝深处活活生出一个空洞,一个既无出口又无入口的纯粹的空洞。这种无可名状的体内失落感——实实在在的不实在感——有点恍若登临尖形高塔顶端时所感到的近乎麻痹的恐怖”[3]5,“而且愈演愈烈,以致脑芯都痛不可耐。胃的底部一发生痉挛,其震颤就通过离合器金属丝传到头颅中央”[3]11。这促使“我”谈及第一次的面包店抢劫及妻子提议“再抢一次面包店”以解除“紧箍咒”。
但由于再袭的目标最终是麦当劳,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从‘欢迎光临麦当劳’开始、依照‘麦当劳待客规则’所运转的机器人般的世界”[4]25。店长主动要求给钱因为保了险,但反对“把正面的卷帘门放下,关掉招牌灯”“制作三十个汉堡包”因为违反规则或账簿上非常麻烦,而妻子主导的“我们”的“抢劫”仅仅是要求关门、关招牌灯,做三十个汉堡包,甚至要可口可乐时还“付了这部分款”。因此,“‘我们’这次所做的也并非是与‘现实’的格斗,仅仅是违反了麦当劳的方式”[4]25。也就是说,在试图恢复自我主体性的过程中,“我”和妻子遭遇到较第一次抢劫更系统、更程式化的社会组织,从而导致此次恢复主体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我”的“饥饿感”虽然暂时得到满足,再次望向海底时“海底火山的姿影已不复见”[3]20,但主体性恢复的失败使得此时的“我”只能“闭目合眼,等待汹涌的潮水把我送往相应的地方”[3]20。再袭面包店并没有带来希望的结果,“我”最终只能放弃幻想随波逐流。
(三)讲述现在的“我”
《再袭面包店》虽然以回忆开篇,但结尾却是对再袭后的“我”的描写,即小说的结尾并未与开头相呼应。这一处理使人很难推断现在的“我”究竟处于何种状态,不过从小说的行文中还是可以窥见现在的“我”的一些蛛丝马迹:其一,不论是在再袭之时还是在叙述这一故事的现在,“我”都是一个缺乏判断机能的人。其二,从小说结尾处亦可以知道,“我”最终放弃了恢复主体性的幻想。概而言之,第一次抢劫时,“我”和同伴固执于自我主体性而与现实对抗,意外的结果虽然使得“我”被社会吸纳从而丧失了自我主体性,但体内还存在着反抗现实、恢复自我主体性的冲动;第二次抢劫是由妻子主导的试图恢复主体性的过程,“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但依旧失败,“我”更加被社会所牢牢吸附,最终只能任其随意摆布而随波逐流了。
四、《象的失踪》中的“我”与《再袭面包店》中的“我”
通过对《象的失踪》与《再袭面包店》中的“我”所进行的总结和分析可以看出,《象的失踪》描写的是“我”从具有判断力到失去判断力的质变过程;而《再袭面包店》则讲述了“我”从拥有自我主体性到失去自我主体性,然后试图恢复自我主体性却以失败告终的历程。虽然《象的失踪》中的“我”与《再袭面包店》中的“我”并非同一人物,但两个“我”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延续性”。即《象的失踪》中从具有判断力到失去判断力的质变过程对应着《再袭面包店》中“我”从拥有主体性到失去主体性的这一过程。虽然《象的失踪》也在某种程度上描写了象的失踪对“我”所造成的影响,但没有对失去判断力后的“我”作进一步的刻画。而《再袭面包店》不仅描写了“我”自我主体性的丧失,而且描写了在此之后的状况。失去判断力的“我”其实就是失去自我主体性的“我”,这是两个“我”存在“延续性”的基本前提。仔细阅读这两篇小说,不难发现这两个“我”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从内心世界来看,在《象的失踪》的结尾,“我”在大象失踪后时常出现的心情是“每当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3]44。这意味着“我”在判断力上的缺失。而到了《再袭面包店》的开头,“我”则“至今也弄不清楚将袭击面包店的事告诉妻子是否属于正确的选择”[3]1。这种搞不清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表明其也处于判断力缺失的状态。两个“我”虽然在描写上有所不同,但其性质却是完全一致的。即无论是《象的失踪》中的“我”还是《再袭面包店》中的“我”都已经丧失对事物的判断力。
其次,从生活状态上来看,《象的失踪》中的“我”是公司广告部的一名职员且单身一人;而《再袭面包店》中的“我”则是一个就职于律师事务所的已婚男人。虽然两者的生活状态有所不同,但无论是作为广告部职员的“我”(高效合理的“我”)还是就职于法律事务所并已结婚的“我”,至少从表面上看,都已是社会的普通一员。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比比皆是,完全符合社会的常态。但深入分析即可发现,上述两个“我”之所以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是因为具有共同的前提,即不具备对事物的判断力。
最后,从判断机能的承担者来看,《再袭面包店》中的“我”在第一次抢劫后丧失了自我主体性并由此进入到无法进行选择和判断的状态。这说明判断机能是由具有自我主体性的“我”来承担的。而在《象的失踪》中,判断机能是由不合时宜的“我”来承担的。由于不合时宜的“我”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注定被消灭,因此可以明白不合时宜的“我”应该具有与社会常态相悖的性质。换言之,《再袭面包店》中具有自我主体性的“我”和《象的失踪》中不合时宜的“我”同样承担判断机能,也同样具有“反社会”的性质。
通过上述三点论述可以明白,虽然两篇小说在文字描述上有所不同,但《象的失踪》中不合时宜的“我”与《再袭面包店》中拥有自我主体性的“我”是同质的。如果一定要说二者有何不同,那便是在《象的失踪》中,不合时宜的“我”与高效合理的“我”首先共存于“我”体内,其后不合时宜的“我”随着“象的失踪”而消亡。而在《再袭面包店》中,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一个在初次袭击面包店后丧失自我主体性且符合社会常态的“我”。论述至此,《象的失踪》中的谜团便迎刃而解。人类的判断机能是由拥有自我主体性的“我”,即不合时宜的“我”来承担的,但不合时宜的“我”在这个社会中注定被消灭,那么高效合理的“我”将会怎样呢?《再袭面包店》给出了答案:自我主体性虽然丧失,但试图恢复的冲动却依然存在,这种冲动就如隐藏在大海深处的火山那样随时可能爆发。然而,个体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均质化,自我主体性不但没有生长空间,而且那种固执于自我主体性的行为在与社会发生冲突时也会因为无法明确其战斗的对象而最终失败。只有不具备自我主体性的个体,才能很好地在社会中生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从“我”的角度来看,《象的失踪》仅仅描写了“我”从拥有判断力到丧失判断力的质变过程。这一结果是由于“象的失踪”,即不合时宜的“我”被消灭所造成的。但小说却未解决为何只有不合时宜的“我”才具有判断力,而不合时宜的“我”又注定会被消灭这一问题。由于不合时宜的“我”就是拥有自我主体性的“我”,因此,通过阅读《再袭面包店》便可以解开《象的失踪》所留下的谜团。两篇小说通过“我”发生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再袭面包店》是《象的失踪》的延续,是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批判。
[1]加藤典洋.村上春樹の短編を英語で読む1979~2011[M].東京:講談社,2011.
[2]关冰冰,杨炳菁.“我”与“象的失踪”——论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象的失踪》中的“我”[J].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5):72-77.
[3]村上春树.再袭面包店[M].林少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4]田中実.消えていく<現実>——『納屋を焼く』その後『パン屋再襲撃』[J].国文学論考,1990(3):24-25.
FromTheElephantVanishestoTheSecondBakeryAttack:AnAnalysisof“I”inTheseTwoShortStories
GUANBingbing1,YANGBingjing2
(1.SchoolofEuropeanandAsianLanguagesandCulture,Zhejiang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Hangzhou310012,China;2.JapaneseDepartment,BeijingForeignStudiesUniversity,Beijing100089,China)
TheElephantVanishesandTheSecondBakeryAttack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both contents and research measures,except that these two short stories are narrated from the view of the first person. However,Norihiro Kato connects these two with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 and the female characters. Moreover,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texts further discloses the continuity of these two short storie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 and the society.
Haruki Murakami;TheElephantVanishes;TheSecondBakeryAttack;“I”
I313.45
A
2095-2074(2015)02-0107-06
2014-01-26
关冰冰(1970-),男,吉林长春人,浙江外国语学院欧亚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杨炳菁(1972-),女,天津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