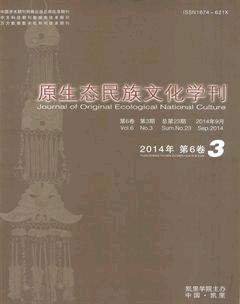蒙古草原的傩文化
邢莉
摘要:跳查玛是蒙古草原的一种傩文化,具有较为鲜明的草原文化色彩。草原的傩文化是在藏传佛教内的昭庙内进行的,昭庙是蒙古族查玛文化的特定的文化空间。人们经历了世俗世界和鬼神世界的并行不悖的双重人生,正是通过这个仪式,民间愿望的两种趋向——避祸和求福得以呈现。跳查玛这一特殊的流程向我们表明,人们满足的不是认知的理性经验世界,而是感知的感情世界。正是这种感情形式和宗教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才使得我们可以透过跳查玛那些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仪式窥视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草原;傩文化;跳查玛;文化空间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4)03-0113-06
一、跳查玛:蒙古草原的一种傩文化
傩和傩戏是我国各民族存在的极为古老的传统文化现象,是远古人类一种原始祭祀仪式和宗教型戏剧。目前对我国南方傩文化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成果,而对我国北方傩文化的研究传统却比较薄弱,以至于国外学者认为我国北方民族没有面具。实际上我国北方民族的傩文化也源远流长。外国的民俗旅行家,曾经深入到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多次提到蒙古萨满巫师的面具。波兰学者尼斡拉兹叙述布里亚特蒙古萨满巫师面具的情形:“靼靼之萨满彼等一白桦树之皮制造假面具,以栗鼠之尾托于假面之上作须眉。”僧正尼鲁.浑.亚罗斯罗夫在布里亚特人中发现了假面。此种假面旧时系一鞣皮、木材及金属所支撑者,斑面修髯。此种假面在萨满之用品中已绝迹。蒙古萨满的面具的质地有三种:木制、皮制和金属制。
遥远的原始时代过去了,但是这种宗教意识和宗教舞蹈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喇嘛寺庙举行的跳查玛表现出来。蒙古地区的傩舞,最早始于1811年,据内蒙古的毛都噶查的喇嘛金巴札木苏说,历史上内蒙古99旗,外蒙古57旗都跳《米拉札玛》。跳查玛要戴各种各样的面具。内蒙古各地召庙很多,演出内容不同,所戴面具也各异。
黑煞神:头带青色鬼头面具,呈人的头盖骨状,眼睛为两个深洞,下颔突出,给人以恐怖之感。
白煞神:头带白色的鬼头面具,3只眼睛,两眼为深洞,下颔突出,阴森可怕。
蝴蝶神:圆眼巨嘴,为丑恶嬉笑的面孔。
海螺神:脸谱亦为嬉笑丑恶的嘴脸。
鹿神:鹿神的面具一般为蓝色,亦有的呈黄色,头顶上伸出2只公鹿的角,头部还显现出梅花鹿的斑纹。
狮神:头戴卷毛面具,3只眼睛。
鳄鱼神:头戴鳄鱼头面具,为青蓝色,鼻大嘴丑。
凤凰神:头戴青色凤凰形面具,娇小玲珑。
星神:有文曲星和武曲星两种。面具为骷髅金冠,三角眼,巨嘴,横眉怒目,满脸杀气,威风凛凛。
天王神:面具根据天王殿内四大天王的原型制作。东方为持国天王,南方为增长天王,西方为广目天王。面具为巨眼阔耳,方鼻大嘴,威风凛凛。力大无比。
护法神:护法神为大威德金刚。面具呈各式各样的兽类形状。狮子巨头环眼,大象锯齿阔嘴,老虎龇须怒目,豹头獠牙巨齿。
弥勒:即民间传说中的弥勒佛。传说他平日手挽布袋,见物即乞,所得全部献给寺庙。面具为和尚模样,圆鼻圆脸,笑容可掬。
金刚神:金刚神为护法神,号称四大金刚。他们头戴的面具各不相同。一为象头,一为夜叉头,一为狮头,一为猴头,脸谱都为3只眼,怒目圆睁,锯齿獠牙,耳垂一只特大的耳环,个个都是凶神恶煞的模样。
自救度:女人像,慈眉善目,安详宁静,在佛教为观音菩萨的化身。
绿救度:女人像。在佛教里为文殊菩萨的化身,面相亦慈眉善目,和蔼可亲。
白老翁:为白胡子长者模样。白发皓髯,秃头阔嘴,善眉善目,温顺而滑稽。
鬼众:均为骷髅面具,森然可怖。其中包括与人作祟的鬼,有乾闼婆、食血肉鬼、厌寐鬼、饿鬼、热病鬼等。
阎王、阎王坐骑、阎王妻:阎王及阎王妻均属阴曹地府。阎王头戴青色牛头面具,3只凶眼,面目狰狞。阎王坐骑头戴似麒麟的面具。阎王妻戴似牛非牛的面具。
喇嘛跳查玛的面具怪异奇特,形象逼真。有喇嘛化装成人、神、兽、魔、鬼等角色出场。无论表演的内容如何,出场的人物多少,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为驱鬼者,包括佛教的护法神、动物神、菩萨、罗汉、长者、娃娃等。一为鬼众,包括阎王及各种鬼魅,梅花鹿为魔王的象征。
跳查玛时,喇嘛在庙内进行驱除鬼魅、禳除灾祸的表演,其服饰往往与其扮演的角色相配合。蝶神上身穿花缎紧身小袄、红兜肚,下身穿花衣裤、花裙、花鞋,手戴花手套,为花蝴蝶样。扮度母的头戴大沿遮帽,帽顶插五根雉鸡翎,身着各色筒裙。四大金刚着五彩锦缎大袍,肩上披五彩绣花披肩,脚穿花缎鞋。大威德金刚身穿五彩战袍,袍上绣有海水江涯图案,腰部绣有八宝缠腰图案,脚穿薄底靴。鬼众均穿白衣白裤,阎王着没有扣子的套头筒裙。
跳查玛时,各角色的头饰引人注目。归纳可分为几类:
骷髅型:有的头戴骷髅型的五佛冠。冠上立着塔型的宝珠顶,顶上的绒珠摇晃。
模拟型:海螺神则戴螺壳帽,鹿神头戴逼真的鹿角,救度母戴大沿的太阳帽,帽顶插五根雉鸡翎。其头饰皆模拟所扮演的角色。
装饰型:有的戴特大的耳环,有的戴大串佛珠。天王戴五佛冠。
跳查玛时每个角色手中都持有物或法器,可分为三类。
模拟型:跳天王时四大天王手持物与佛像所塑的四大天王相同。东方持国天王手持琵琶,南方增长天王手持宝剑,西方广目天王手持水蛇,北方多闻天王手持宝伞。
骷髅型:有的人手持骷髅,例如护法的黑煞神就手持骷髅。女神手中也有骷髅。
关于法器,多数跳查玛的人手持法器。有的手持金刚杵,系一种铜制的神器,上面雕有各样的佛教图案。有的手拿嘎达斯,为钉状铜质神器。有的手拿五彩穗的法棒,有的左手持小皮鼓,右手拿弯型鼓锤,有的拿铁箍、钩子。
跳查玛完全以舞蹈的形式出现。清咸丰年间成书的《古丰识略·人部》卷37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此间于正月十四日夜半,各寺俱登楼吹角,角以铜骽骨为之。传集喇嘛僧众妆束,黎明齐集五塔寺前,如天魔舞,有青狮、白象,以纸粘木为之,足有轮四,牵走如生。日出后各归寺闭门,扮演其扎萨克喇嘛或达利麻在殿上,南面据高坐褥以黄缎为之。著极厚,褥数层,高数尺,对面寺门前张黄伞一。喇嘛假寿星面具北向坐,关列小儿高二尺余,戴小沙弥面具者五合掌,侍东西廊突出戴假面具,衣灰白色,紧衣憔悴作枯骨形者数十皆以三尺许小儿为之。殿阶西南侧坐喇嘛十人,作两行列,列各五,戴毡帽高二尺,前钧后坡脊起如摺扇形,衣紫布衫,袒柄鼓园径二尺,柄注于地,以右手击之。寺门内,寿星稍北数喇嘛围案吹角声鸣鸣,与鼓声上下应其如,枯骨者数十人聚阶下做大周转。每角一声,辄翘一足作商羊舞,进退以鼓为度,约炊许,轰然。仍东西散殿上出一老人,亦假面具,白髯眉,衣锦袄,裤靴具,黄色有织绣纹下阶,徐徐作龙钟态,笑容可掬,数小童扶掖以行,亦作大周转。依寿星立殿上,又出一人装束如女子,头插雉羽六徐,舞作东西,盼顾下阶,向大周转,以手中拂下指,拂柄作骷髅形,衣锦衣云肩,下垂飘带数十百条,如戏班中宫衣冠前后围,亦小骷髅形,高寸余,约七、八枚。数刻殿上又出八人。两次下妆束如前,女子头插雉羽,四皆执拂,左右午殿上又出数队或两人、或四人对舞而下。约二十余,有牛首者、龙首者、鹿首者,皆假面具。以漆髹之状貌,狰狞如蛇神牛鬼,袍五色,与前十六女子穿花舞,以一牛首与插雉羽六者居中,所舞似无多式样,惟前后旋转及以衣袖与拂左右翔顾耳。舞毕,东西列老人者仍作前态上,至正坐前以首至地,袖出一物如帛,献之,名日递哈达。摩顶受其寿星者,亦扶五沙弥上,如大壶卢旁生数小壶卢(葫芦),黄伞盖随至阶,寿星诣正坐前献哈达,如老人而退,正坐者起立,音乐导送入别院,舞者复对对作商羊而退入殿内,寿星老人皆入,外鼓角大作,数人舁一纸塔,上面作千百骷髅形,至庙外焚之。
据所载,跳查玛时,必须配以佛教音乐。大多在喇嘛庙前两侧排列长喇叭4支,各长4.5米,在跳查玛之前和跳查玛的整个过程中吹响,声如牛吼,传数里外。另有大鼓8面,分列门两侧,直径约1米、高约1米,下有木座立于地,鼓锤很长。除喇嘛号和大鼓外,伴奏的乐器还有羊角号、锣号、唢呐、羊皮鼓、钹、铜铃等。跳查玛时,喇叭、大鼓、铙钹按规定同时演奏。演奏这些乐器的目的并不在于恐吓有恶意的神灵,而在于促进喇嘛内心的静修。因为它有利于召请佛教的神灵下界,并使之依附于喇嘛禅师之身,以利于禅师进入迷狂状态,具有与恶魔搏斗的强大力量。
近代各喇嘛寺庙的宗教活动延续了跳查玛的习俗。其表达的内容与清代相同。但出场的人数、顺序、所跳的舞步不尽相同。
西部土默特地区大型跳查玛有28套,内有骷髅、舞神、天神、鹿神、土地神、老寿星、水牛、白蝴蝶神、欢乐神,等等。先后出场40多人次,而小型的只有七八场,出场者10到20人次。东部喀拉沁地区有喇嘛化装成人、神、兽、魔、鬼表演。其出场顺序为男鬼、四大天王、蝴蝶、狮子、八大金刚、护教伽蓝、大威德金刚、弥勒佛和娃娃、老寿星和娃娃、鹿神。最后由表演者列队绕庙三周,然后由喇嘛焚烧“白扔”,佛事完毕。
根据调查,一般而言,跳查玛的场次如下。
第一幕:跳白鬼,扮白鬼的喇嘛把白土撒向观众,观众后退,又叫“净坛”。第二幕:跳黑鬼。第三幕:跳螺神。第四幕:跳蝶神。此前四幕为序幕。第五幕:跳金刚。第六幕:跳星神。4人跳名叫四星神,10人跳名叫十天干,12人跳名叫十二地支,最多的为28人跳,名叫二十八宿。第七幕:跳天王。第八幕:跳护法神。这时梅花鹿出现,即魔王的化身出现,众佛一起攻之。第九幕:跳自救度。第十幕:跳绿救度。第十一幕:跳弥勒。这时上场的达几十人次。弥勒用绳子将魔王捆绑住。第十二幕:斩鬼。两名喇嘛抬一三角形大匣,装有一面人,面人的头部、咽喉、两手腕、胸部、两腿、两足等9个部位全部用铜钉钉于匣内,表示化装梅花鹿的魔王被捉住,弥勒把一斧型刀交予金刚。金刚用这把刀把人的脑袋砍下,是谓“打鬼”。第十三幕:送祟。斩鬼之后,众人合庆胜利。有两名喇嘛抬一三角架,架上插一金箭,金箭是用纸糊成的,红杆、黑羽翅,金镞。表示佛祖释迦牟尼用金箭将魔王的灵魂钉在三角架上,喇嘛将三角架焚化,表示魔王彻底被歼。跳查玛的尾声为绕寺,即在第二天日出前众喇嘛列队围寺绕一周,亦即除恶务尽。
每年正月,北京雍和宫跳查玛的规模较大。笔者在1994年观看了北京雍和宫的跳神,基本上延续了这个模式。
跳查玛是喇嘛寺庙内举行的一种大型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舞蹈,而后演变成蒙古族的民间节日。从本质上说,跳查玛属傩文化的一种。《绥蒙辑要》载:“喇嘛庙内跳布占数次,汉人称为‘跳鬼,为祓除全牧之灾,并占一年之吉凶。此项为跳布札,即远近蒙汉人民以及王公士官,不召自至,磕头礼拜,欢跃数日,汉商借以做买卖,犹汉人于乡镇赶集也。”近代胡朴安在《中华风俗志》卷九说:“蒙俗打鬼,除不祥也,每年六月为止,在庙内用喇嘛戴面具跳舞。挥长鞭打人,着鞭者亦不怒也,诗云:头角狰狞面具装,怪衣飘拂舞如狂,长鞭挥处无人避,打鬼除灾好致祥。”
早在《周礼·夏官》里就有方相氏率领百隶从人行傩时的记载:“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方相氏在率领百隶从人行傩时,必须头蒙熊皮,戴铜制的四目面具,身穿黑色上衣和红色夏装,手持戈矛盾牌,逐宝甓踊跳跃,意驱鬼逐疫。跳查玛与之非常相似。
旧民俗志往往记载跳查玛源于藏族地区的跳布札,又名跳布踏。清徐兰芬的《徐松西域水道记》引《打鬼歌序》写道:“打鬼者,梵语布札……今京师番色僧寺,上元除夕亦为之。”《清会典》载:“布达拉众喇嘛装诸天神佛及二十四宿像。旋经颂经,又为人皮形,铺天井中央,神鹿五鬼及护法大神往捉之,未则排甲兵幡幢,用火枪送之布达山,以除一岁之邪。”蒙古族的跳查玛就是藏族的跳布札。藏族叫“羌姆”。关于其产生有几个传说。
传说一:过去某藏王欺压百姓,百姓不堪其苦,故以跳神诱藏王往观,众百姓遂刺杀之,为了纪念,每年巡礼举行跳布扎。
传说二:乌斯藏有地方有一石房,久为邪祟所占据,白天黑夜夺人之食。当地喇嘛便假装诸佛之像,入石房捉住魔鬼痛打,石房之祟被驱逐,称之为打鬼。
传说三:古藏王朗达尔玛生性残暴,无恶不作,并企图毁掉佛法,吐蕃佛教衰落,民不聊生。有一名叫拉隆布勒多尔吉的僧人将自己所骑的白马染成黑色,将弓箭藏舞服之中,趁国王看歌舞之时,从袖中抽出弓箭向国王刺去,朗达尔玛中箭身亡。拉隆布勒多尔吉乘马渡河,马立刻变成白色,因此逃离了追捕,人们为了纪念拉隆布勒多尔吉而跳布札。
传说四:打猎为生的白老人和黑老人打猎时遇到苦行僧米拉日巴,米拉日巴劝他们不要杀生,并向他们宣讲佛理。白老人听了规劝,皈依了佛教。而黑老人依旧嗜杀成性,甚至起了射杀米拉日巴的念头,他瞄准米拉日巴的头部和腹部各放了三箭,米拉日巴闭目祈祷,稳如泰山。黑老人才相信佛法无边。与白衣老人一道皈依了佛门,全局在欢乐的“奉献舞”中结束。
关于跳查玛起源的传说非常多,此不一一列举。传说虽各异,但都说明跳布札的主旋律都是驱魔。魔的形象有的是具体的人物,有的是看不见的神秘的邪恶,而且说明藏族跳布札的来源是西域佛教。意即跳布札是藏传佛教的驱魔仪式。
实际上跳布札的来源并非起源于佛教,虽然吸收了很多佛教成分。藏族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为苯教。根据不少藏族学者研究,在2500年之前,青藏高原就普遍存在着各种原始巫教即苯:天苯、魔苯、赞苯。天是代表整个自然力量的意象概念,魔苯是某种神秘力量的象征;赞是苯教古籍中掌管主宰人家的神。据苯教史籍记载。在聂赤赞普之前500年左右,就已有第一代象雄王赤维色希日坚了。而藏民族文化传统的苯教正源于象雄。据藏族文献记载,藏族直到八世纪中叶之前还信仰苯教。八世纪中叶赤松德赞当政时从印度迎请擅长佛教的旧密金刚乘巫术的莲花生大师,在修建桑耶寺奠基仪式上:“制定所喜的祭祀物品,又说出了镇伏凶神的歌词,在虚空中作金刚舞……”莲花生以带入的“所谓教外别传的密宗(续部)金刚舞为基础,又吸收了藏族具有原始巫教色彩的民间图腾舞、人物面具舞、藏族古歌舞“阿卓”等艺术因素,将舞蹈形式用来表演降魔伏怪的故事。莲花遗教后在桑耶寺落成开光大典上,驱鬼镇邪仪式咒术的“羌姆”的演出成为藏传佛教寺院傩的滥觞。在公元11世纪,佛教的后宏期,阿里古格王意希沃、降曲沃二修建托林寺庙,翻译了大量佛教密宗的经文,又给“羌姆”以影响。藏传佛教的各个派别宁玛、噶举、萨迦,还有佛教化的苯教寺庙都按照各自的教义发展了羌姆。藏族的“羌姆”是印度的密教和藏族的苯教融入了佛教的结果。
藏民族远古信仰的原始巫教,在巫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苯教以及由印度传来的本土化的佛教,其教义、经典、仪轨各不相同,虽然各有特色,但彼此存在着互相吸收和互相交融。自明代以来接受了藏传佛教的蒙古族也存在着跳神的习俗,旧的民俗志学者认为这只是对藏族傩文化的因袭,当然蒙古族的“跳查玛”是从藏族地区传入的,但是每个民族在接受一种文化的时候,必然有其本土文化的因素。
二、蒙古族傩文化的草原文化特色
蒙古族的傩文化具有草原文化的特色,主要呈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草原傩文化的面具具有民间色彩。蒙古族跳查玛的面具之一为白老翁。白老翁白须白发,浑身素白,手持一拐杖。“这根拐杖完全相当于萨满们一般使用的马头杖,萨满们把这种拐杖当坐骑使用”。他是主管畜群和丰收的神。众所周知,蒙古民族从事的是畜牧业,畜群牵系着牧人的命运。白老翁的形象融入了跳查玛的面具中,表示牧人对牧业丰收的希冀。跳查玛中有骷髅神。骷髅神可以追溯到阴山岩画出现的史前时代。盖山林先生认为:“在大坝沟中,有一些类似人的骷髅的头像,显然这是古代骷髅崇拜的遗迹。在大坝沟的骷髅岩画,使我们想起在内蒙古和西藏地区流行的喇嘛教的‘查玛节在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跳神仪式,跳神时喇嘛所戴的面具,与骷髅岩画十分相似。”“从死人崇拜到头骨崇拜,发展出面具崇拜及其舞蹈和表演。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精灵或魔鬼”。在黑龙江省原依克明安旗(现划归富裕县)境内流行“浩黑麦”,意即骷髅之意。多选在春季进行,活动者反穿羊皮袄,头戴骷髅面具,另有戴仙鹤面具随行,到各家拜年,寓意故乡祖先来看望后裔族人。生活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先民同澳洲非洲的土著部落一样,也都存在着加工、保存英雄的头颅,制成面具,在祭祀时戴上,目的是避免灾祸。另外面具中有蝶神,蒙语称“额尔伯黑”为“蝴蝶”。“这是萨满巫师为不育者求嗣的舞蹈。有6个或8个儿童戴着憨态可掬形象夸张的面具,在白老人的带领下,跳起儿童的舞蹈,而那个戴面具的老人,则象征着保护儿童的萨满神灵”。
其二,如果把傩规定为具有特定含义的鬼神信仰、祭祀媒介、杀牲奉献、面具装饰的泛指符号的话,鬼神信仰是其产生的核心。蒙古族的跳查玛的主旨是驱鬼。鬼神观念产生在遥远的原始社会,在人无法把握自然和把握自身的时候,人们在以神鬼的观念解释一筹莫展的世俗世界。否则生命就有不解的困惑,世界就不可思议,一切就没有秩序。一切福祉都是神带来的,一切灾难和疾病都是鬼带来的。蒙古族的萨满巫歌就有驱鬼词:“不吉利的八个鬼呀/今后不许再来这家/再来除非炒米长出庄稼的时候/再来除非鸡蛋变成小鸡的时候/再来除非棉花变成丝的时候/再来除非死狗头能够大叫的时候。”对于鬼——给人们带来疾病、灾荒、瘟疫、破财、死亡等一切灾难的无形的超自然的力量和有形的超人物,人们都要驱除。人们往往把自然界中存在的某些奇异的猛兽视为“鬼”。根据有的学者考证,“鬼”字的另一种解释是指古代的确存在的一种似猿似猴的野兽,如章太炎先生在《文始》称鬼头的上半部即狒狒的古文:“披发,故独言其头;似人,故谓之鬼;鬼亦疑之怪兽”。在科尔沁蒙古族的萨满中“鸢”就是鬼的一种。萨满降服鸢鬼时唱道:“在那坨子上走的人/是从地狱中走过来的啊/啊嗬嘿呀/两个白鸢的鬼魂啊。”而降服鬼魂的是萨满:“附体的我在叫你呐/两个白鸢的鬼魂啊。”
“好和麦”是科尔沁地区萨满巫师的驱鬼舞蹈,“德德日麦”是蒙古萨满巫师为人治病驱鬼镇妖的法术。“德德日麦”即表现“替死鬼”神穿病患者的衣服,头戴着患者形象的面具,跳着滑稽可笑的舞蹈,在萨满巫师的诅咒下,蹒跚离去的情形。这与跳查玛最后的仪式非常相似。在跳查玛的仪式中,笔者在1994年正月看见在北京雍和宫烧掉了一个代表邪恶的替身。用火烧掉,也包含着原始信仰的崇火习俗。蒙古语族语言中保留着突厥词“奥特”(火),火经中也有“奥特汗、嘎拉汗”的记载。这两个词表示的是一个概念,这使我们推测到,当蒙古语的部落和突厥人毗邻而居并有许多共同的习惯时,他们已经知道崇拜火了。最古老的火的颂歌里唱道:(火)“你有穿透额图根(大地)的温暖,你有深入云端的浓烟。”“我用烈酒来祭奠你,我用金银来装扮你。在你的头上倒油,用油来款待你。献给你9支蜡烛、9支香、9种绸缎和羊背”。对火及火神的崇拜是萨满教的多神崇拜之一。
其三,草原的傩文化是在藏传佛教内的昭庙内进行的,昭庙是蒙古族查玛文化的特定的文化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致力于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提出了文化空间的概念。根据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中发表的最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展现、表达、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制品和文化空间。”如何理解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文化空间?
文化空间从其自然属性而言,必须是一个文化场所,“即具有一定的物理空间和场所,必须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性;从其文化属性看,则应该具有岁时性、周期性、季节性、神圣性、娱乐性,等等”。在特定的时间,在草原上建立的昭庙内进行的跳查玛活动就形成特殊的文化空间,被草原民众所享用和认同的重要的文化空间——即民间信仰的文化空间,就是“与自然威力有关的任何一整套制度、信念和习俗,这种自然威力是力量、神、鬼、精灵还有妖魔”。或者说这种民间宗教就是“一种由文化上形成的与文化上假定的超人交往所构成的习俗”。可以这样说:生活在宗教的逻辑中进行,而宗教在生活的脉络里展开。
跳查玛的日期各地不一。有的在正月十四日、十五日,有的在正月二十九至二月初一,也有的在农历正月初七、初八,六月十四、十五日跳。跳查玛时,内蒙古民众聚集,观者如云,成为民间盛大的节日。据《古丰识略·人部》卷37记载:
是日,观者如堵山,男女番众亦结伴来,城巷衢为之塞满,男女由寺内出,入有一喇嘛手青卷巾拂其额,辄喜。有抱儿跪求者,有自以额就之者,掷钱数文或数十文不等。喧笑而散,云看跳神毕矣。
它虽具有人类童年时期驱傩活动的原始模仿性、艺术象征性、宗教神秘性,但是更具备娱乐色彩。人们经历了世俗世界和鬼神世界的并行不悖的双重人生,正是通过这个仪式,民间愿望的两种趋向——避祸和求福得以展示。跳查玛这一特殊的流程向我们表明,人们满足的不是认知的理性的经验世界,而是感知的感情世界。正是这种感情形式和宗教思想的内在统一性,才使得我们可以透过跳查玛那些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仪式窥视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以家庭为单元的传统的牧业经济活动和社会,其结构相当脆弱,黑灾(旱灾)白灾(雪灾),生老病死等都可能严重影响一个家庭的经济生活并导致破产,正是这种个人命运的不可预测性为跳查玛提供了广泛的心理基础,正是畜牧业封闭的经济地理环境,为跳查玛的存在提供了长存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