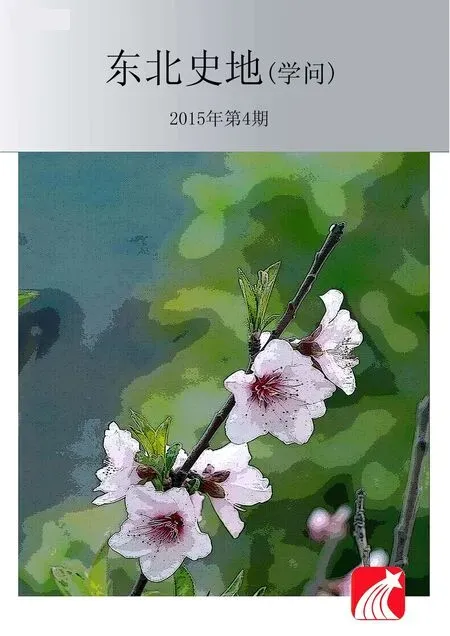瑷珲十里长江俗记(节选三)
富希陆 撰 富育光 整理
瑷珲十里长江俗记(节选三)
富希陆 撰 富育光 整理
瑷珲地方世居的达斡尔人,主要以坤河为最,其他还零散世居在富拉尔基、达音炉、新发屯等地方,同余所居康熙朝拓建的满人聚居的官屯大五家子村仅数里之遥,轸翼相辉,往来密切,多为亲戚关系。清末,有位著名的德巴克什,姓苏勒哈喇,人称德五爷,达斡尔人,来自尔莫津,俗称爱米人;还有一位索先生,也是达斡尔人,他们都是大秀才,满汉齐通,能够专门用满语讲聊斋故事和三国、水浒等。从正月到春耕前,能连续数十日为族人讲唱,听众不单为本族人,相邻六七十里外的满族、索伦、鄂伦春人,都骑马套车来听讲唱。他们还用流畅的满文为本族和满族诸姓书写萨玛神谕、谱牒和满文说部。逢年遇节,车马迎送,倍受尊敬。听说德五爷死时,入葬的书,便是满文聊斋。
东海窝稽部人与黑水女真人,古代萨玛死,要风葬。风化后再捧拾神骨为室中神灵,存放于专缝的小桦篓内,挂在北墙,外迁必携带。人死也有将神骨先放椁中,可使子嗣不绝。
北民有“魂萦故里”之说。人死必将其所用之衣物、狗、马等以及一切用器,全要随其入葬,进行火葬,俗称“烧饭”。最早亦有水葬、土葬、风葬之习。盖此观念,意在安魂,使其不再返回人世寻觅心爱器物,使子孙不得安宁。传人死起“殃”时,送葬人要从火上过,要漱口、洗手,使魂气不能带回家。“殃”气亦指魂气而言。萨玛认为,人初死之游离气为“殃”,时间长而游离不移曰“魂”。“魂”发生作用于人于物,而生异兆曰“灵魂”或“魂灵”。魂浮游、延续时间越长越古久,其魂气与神气越不可匹敌。萨玛言:“初魂易伏,久魂为神。”人死其气不灭,其魂永存,常留人间。魂非妖孽、鬼怪,只不过为宇宙间气化、气运、气行、气凝、气聚形态而已。故萨玛以祭祀收摄魂气。鬼惧萨玛,萨玛不惧鬼也……
古萨玛“神判”,或称“神验”、“神断”,是萨玛教中一项庄严的祭程。“神判”就是本氏族中所发生或所遇到的任何重要事宜,要经过极其隆重而庄严的祭祷仪式,祈神进行公正的裁决评判,而确定氏族部落中一时无法解决和认定的事物。神判的祭祀手段,主要是通过神卜,尽管方法与形式各族各部落有许多不同,通过卜筮,如经火、水、猛兽验卜,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企盼神灵助佑,判断是非吉凶,故曰“神判”。
“神判”多源于以下诸因:
一、氏族内发生重要的争执与械斗,氏族诸首领众说不一,难以统一,关系重大,唯以“神判”,方可明断曲直;
二、数个分支部落,分配不匀,争执不下,请神以“神判”方法予以财物分配,各支谨照神谕,遵守办理;
三、氏族确定各分支之住地、猎获地址、水源分配,以“神判”方式固定下来;
四、氏族新推举之首领,人数与任人不统一,或突然来客和入伙的外来人,不知其心迹真伪,举行“神判”裁定后,族人信服,号令统一,等等。
凡发生上述情况后,便要由穆昆主持,萨玛祭神,举行“神判”,也有的小氏族由氏族担任专门卜筮的人进行“神判”。如前文介绍,火祭中各分支族人的住址选择,用野鸡飞落办法“神判”营址。如全氏族迁徙一地后,以鸟飞翔办法,确定在哪里安家落户好。又如,双方长期不睦、争战,用过火池的办法,各族人都要从烈火中穿过。用火的“神判”,洗净身上的邪秽,烧除互不信任、互相攻讦的魔鬼心理,变成团结勇武之大部落。再如,东海窝稽部的满族人钮姑录氏(郎姓),往昔每年春雪融化后,便到石岩中捕捉巨蟒数条,拿回部落,与本姓中之年轻人进行斗蟒祭礼。据传春天的巨蟒(北地无蟒,即选最粗大的蛇),刚苏醒不久,急着想吞吃食物,性情暴烈,性喜撕斗,林中小兽类都十分惧怕。全族人经过祭祀、焚香、击鼓,年轻壮士突然抓住巨蛇,将其皮与肉分开,巨蟒死去,由此卜定,全年是否风调雨顺。蛇弱易死视为年景不好、多为瘟情。若年轻壮士与蟒搏斗,蛇猛缠人身,束紧如铁环,越缩越紧,而人力不能支,便有另外壮士冲上去,将米酒与烟火烧烤掐着的蛇头,蛇便舒展长躯,放其生还荒野。凡这种形态便视为大吉,说明今年年景好、人畜无灾。这种蟒蛇卜便是“神判”,判定一年是否顺利。而与蟒蛇搏斗的年轻壮士,经“神判”后便被视为非常人,可选为首领,族人诚服。由此可以看出,占卜不一定都是为了求神降福、祈问未来,占卜在初民时期还起着重要的裁决和平衡势力的作用,是安抚部落的一种手段。在初民期,氏族之间的维系主要依靠首领的组织力和生产力低下情况下的相互依赖。但在原始初民时期,也存在对某种生活资料的争夺问题。原始初民对氏族内部出现的矛盾,还没有更有效的解决和说服办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氏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思想意识,还都非常简单低下,原始的宗教观念、灵魂观念、鬼神观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占据着当时社会的主要思想阵地。神可以抉择一切。于是,便用“神判”的方法决定各方面的争执,以求得氏族间的稳定与和睦。“神判”便成了重要的、任何方法不能替代的占卜法。用这样占卜,使全氏族各方人士都相信,这是神祇给定下来的,是最合乎公理的,以此平息内部纷争,达到统一和安定。因此,可以说占卜术在古代所以非常盛行,还有一个社会组织形式方面的需求心理,也是不容忽视的。
近世,萨玛祭祀中占卜,很多是神判卜法的痕迹。在萨玛祭祀中,至今仍保留许多占卜或类似占卜的举动。如,在祭祀中,将野猪牙、鱼牙放在鼓面上,然后通过祈祷再扬在地上。族人大声呼喊,辨其休咎利害等等,实际上已经很少带有真正的神意,真正灵验的神灵助佑作用,变成了简单的模式化的祭程过场,不一定具有真正的测卜意义,只是一种祭祀中的礼序罢了。这也就更进一步说明了,神判占卜从其开始,便是一种借神示的手段,反映人意的行动。“神判”,实际是“人判”,因人之权威性与影响力、感召力,不如神祇强大,故而借神意以占卜。这在原始最初产生时,还能有一定的宗教作用和心理影响,后来逐渐变成一种利用占卜方法而达到一定目的的形式了。
萨玛教信仰,乃满洲等北方诸民,专有之氏族信仰,千百年来,唯有史书所言,乃夷蛮愚氓之习。清定鼎中原初,满洲将此带入长城之内,所祀所为,常为汉人背议,惊讶嬉笑,视为蛮荒所为,竟而不解。然因其执柄民族,互不敢妄议也。有清一代文诰,鲜有妄议萨玛者。萨玛素为氏族之祭,盖其规程向不外传也。故对萨玛礼仪与神祇,不敢妄议也。偶为者,亦将跳神记述,遵官文而概述之,或则浮言美誉,或则避而少论,盖畏言不及也。尤各姓之神谕不为外姓所晓,恪奉先训,诸姓则互守勿言也。
吴宝财,满洲正白旗,大桦树林子人,其爷及叔父,民国间皆本姓名萨玛,伪满后传于宝财,多年主祭,颇有声誉。其神以鹰、蟒、水獭、虎、熊为主,有两次钻冰眼经历,围众千余。宝财常言:“祭神崇德,情发于理,歌发于心。”萨玛非虚言而勤勉,各有敏求之妙,如,一沟一凸,一竖一行之花纹线理,便可讲出全族的部落起源发脉来。再如,萨玛者通史者也,广征博引,勤谙族事,多于神祀时,唱有关天地开辟、万物形成及人类起源之神话古歌,以娱人乐神,崇德极远。四季屯张刚玉家大神神服,绣有很多鸟兽;下马厂祁世和家大神神服,主要以百鸟神彩绣织而成。
满洲俗有成丁礼,满语称“井玄多罗”。多罗礼一岁两举,以虚柳二星为祝期。虚见于秋,柳见于春,龟寿临天,秋狩春围之日也。重礼设于祖像前,焚香叩礼,男女以图喇验身高,增岁则以野猪牙为垂饰。女为公野猪门牙,男为公野猪獠牙,行成丁礼,然后可婚配、交游焉。萨玛教弘道骨肉深情,视为立人之本,凡欲敬神、爱人、劳作,情而痴、情而迷、情而恒,无所不成。
婚娶南方称娶媳妇,北方谓娶姑娘。南方在母家开面后始上轿,北方至男家始用线开脸。
满洲妇女跪拜礼,跪地以右手三摸鬓礼,即“三叩首”、“三抚鬓”。
北人故习,天寒麕居一室,设火炕以煴暖。阖家妇子同宿一室,老者之席,距火炕灶坑最近,次为稚幼,以火炕热度增减之差,为子孙长幼,爱敬之别。
宴客无嘉膳,视家资所有,猪鸡为上。寿诞婚礼宴客,殷富之家,碗碟各数十六,次等之家,八碗八碟,故有“十六席”、“八八席”之别。
瑷珲蒙雍乾嘉道几朝修葺,堪有固北锁匙之誉。十里流波,龙旗舡舰,林岸嵬木石阵,商旅乐聚,物阜昌裕,两翼官学与塾馆齐盛。瑷珲西百余里,有山曰“一架山”,满语称“额木阿林”。该山为孙吴、瑷珲两县界山。头枕黑龙江,绵延北上,是横亘在黑龙江平原上的兴安岭山脉,由三座大山相连,故又称“三架山”。早年,山上临道边,建有关公和岳飞二圣庙,内塑神像数尊,形态伟岸感人。外围朱漆板樯,高大牌楼正门,蔚为壮观。余逢秋之际,常率学生至此野游。其中,“二架山”处有一丘状高耸团山,矗立群峰之巅。山侧,有山体坍垮而成形之半拉卡山,山姿别有风韵。相传,此山为康熙年间,清军“神威将军炮”炮轰罗刹匪徒所致。又据四季屯当地耆老言:古有达斡尔人特尔法部长老们,住“一架山”山坳间渔猎,山洞中画有参差星斗图象,时有进山砍柴、捕猎者,常偶有发现。可惜,清光绪年间地震后,踪迹难觅矣。
白蒙古家珍藏一块儿白熊皮,白绒绒的毛色发着光亮,用手抚摸宣厚柔暖,谁见谁喜爱。这是其祖在世时喜欢用之坐垫儿。白蒙元很健谈,知道不少北猎趣闻。白熊又叫北极熊,是北极一带最大的凶猛动物。全身厚厚的白毛,耳朵和脚掌亦都是白毛,只是鼻头为黑。白熊牙齿锋利,能跑。白熊在雪中育崽,小白熊十二月出世,没毛,靠母熊乳汁,长得很快,几个星期后,便跟着母熊出去猎食海豹。北极熊冬眠,不涉食,转入夏天,捕捉海豹、海象,躯体非常肥胖而强劲。早先,满洲等北方猎人常远涉北海以北,捕获鹰、貂和各种动物,同北地野人交往亲密。相互以物易物。北人尤喜用白熊皮、海象牙、鲸须等,换绸缎、布帛、酒、茶及日用品。白家这块儿先人们留下来之白熊皮,乃是六十年前稀罕遗物。
瑷珲城萨布素大人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率宁古塔、乌拉兵,来黑龙江建旧瑷珲城于精奇里江西岸,又称黑龙江城,俄称“维笑勒伊村”。该地原属后魏黑水部,勿吉地,唐曰“黑水府”,金为“合懒路”,明为黑龙江忽里平寨。康熙十三年(1674)始筑城,二十二年(1683)设将军一员。二十四年(1685)在此处建瑷珲新城。雅克萨之战胜利后,考虑将军衙门僻处江东,与内地交通及公文往来有诸多不便。于是,迁至下游十二里之江西,选择了俄国人顺治八年(1651)烧毁之达斡尔屯寨“托尔加城”旧址,重新建起了新瑷珲城,亦叫黑龙江城,或叫瑷珲新城,即今之瑷珲。当时初建的瑷珲新城规模,按《盛京通志》载:“内城植松木为墙,中实以土,高一丈八尺。周围一千三百步,门四。西南北三面,植木为廓,南一门,西北各二门,东门临江,周围十里。”“内城中的副都统公署在城内,原系将军公署,康熙二十九年(1690)将军移驻墨尔根,改为副都统公署,大堂五间,堂司房二间,户兵刑工四司房十六间,仪门五间,大门三间。”内城中的大人府南有演武亭,“演武厅三间在城(即内城)西北”。有永积仓、贮谷仓二百十三间,在城南二里,康熙三十二年(1693)设,管仓者为七品仓官一员。除此,还有北营、南营、船库,设八旗水师营,官兵水手防边操练,春秋两季四十天,有大船、花船、桨船,到吉林码头去修补船舰。在瑷珲下游一架山的江套子中,还设有泊船地。
漠河冬无阳春,夏无酷暑,春秋两季相连。九月中旬即进入冬季,长达八个月以上时间,多西北风和暴雪,常有冰淞出现,一片白茫茫,行人不见影,极端气温在零下50多度,为全国低温之最。漠河,每年六月下旬夏至前后九天中,白天显得特别长,晚上八点以后太阳才落山。但黑夜并不降临,黄昏仍很明亮,像有云的白天,到午夜百米内景物依稀可辨。这便是人们传讲之漠河白夜。此时,人们总好在江边下棋、打球、垂钓,常可看到神奇的北极光。北方天空中突然现出一个明亮的光点,光点逐渐扩展,愈来愈亮,色彩斑烂变幻无穷。在漠河到每年夏至,天空只要没有云层阻挡,便容易看到极光。北极光形状很多,有条状的、伞状的、扇状的、片状的、葫芦状的、梭状的、圆柱状的、球状的等等,颜色为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相间,色彩分明,由初升到消逝,变幻神奇莫测,五颜六色,缤纷绮丽。其时,据北方耆老讲,漠河地理纬度同北海南岸纬度大体一致。虽然北极光一年四季都有,但因为天气云层的关系,事实上很难年年都见到,常常是十几年才能见到一次。早年深入到遥远北海一带捕鹰貂的人们,能经常看到壮观的北极光,视其为神迹,卜远猎丰盈吉顺。
额苏里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先祖由宁古塔随戍瑷珲,时清军为选定征战罗刹之便捷要地,最初并未屯兵瑷珲,而是首先选定在黑龙江畔一处有几户达斡尔人家的小屯落作为屯兵之所。此地,恰在黑龙江畔瑷珲与呼玛之间,有一条由西南流入黑龙江的小河,从屯边经过。该屯达斡尔人叫“额苏里”。这条无名小河,因清军在这进驻后,军事联络方便,遂叫成了“额苏里毕尔汉”,即“额苏里小河”之意。该河流入黑龙江河口的段落,水深流急,而且河床两岸古树参天,翠柳成荫,不仅交通便利,更可隐蔽征俄战船,是天然的战略要地。雅克萨战役胜利后,清兵选择精奇里江口西岸,平川地带屯兵筑城,即旧瑷珲城,永戍黑龙江,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后,将军衙门感到与内地因有江水相隔,公文传达不便,迁于江西筑建新瑷珲城。自此数百年间,荒僻的江东沃野出现了数不尽的旗屯,一直伸延入精奇里江的上游,有不少村庄部落,良陌千顷,牛奔马嘶,沃野谷香。精奇里江口,咸丰初出现海兰泡集镇,人口密集,商贾林立,日渐成为北疆名镇。
雅克萨城又名红衣炮城,康熙二十二年(1683)征剿罗刹,运用神威大炮十三尊,令罗刹败北。从此清军兵驻雅克萨城地方,嗣经奉命撤防之际,奉请神炮凯旋,独有一炮摇之坚不可动,始遗于彼。道光之前,有查边者旋称,尚见此炮半陷土中,以至咸同年间有人去看,仅见炮口,而后光绪之初,已无信息。昔有人云,神炮已被敕封“镇北侯”。
富连群撰《玛虎朱陈志略》:瑷珲旧有玛虎戏,不只活跃于集镇闹市,且多倡行于沿江村屯。不独满洲诸姓喜爱,汉人与爱米人、索伦人、棲林人、白俄亦好之,称龙江特有之风。逢年节婚寿喜宴,常有玛虎戏与黑水秧歌。玛虎戏之源,据依公(依郎阿)笔录观之,清初有之。统领玛喇,圣祖朝来瑷珲,携来《诗经》、《孟子》、《左传》、《本草纲目》,为瑷珲有古经文之始。玛喇统领常驻索伦兵中,与土民亲若手足。回京师留萨公歌律三十九篇,玛虎曲牌百二十一首。由此思之,玛虎之戏在当年瑷珲戍营旗军中,必有盛传,不言而喻也。
沙玛(即“萨满”,音译)跳神皮玛虎,民间儿女亦戏戴皮玛虎,求趣乡里。“玛虎”(mahu),系满语,意即鬼脸、面具。“皮玛虎”为满汉组合词,指以皮革缝制成的面具。玛虎既是萨满跳神的必备神具,又是民俗歌舞不可缺少的道具;既被尊为村寨的守护者,又被奉为氏族至尊的神祇。据载:明季“女真部族城寨中,常有高柱称望柱。柱头雕以怪兽、鬼面,常奉为瞒尼神。亦有以皮木雕绘各种面谱,竞跳马虎,俗称跳马克辛以自娱。”《吴氏我车库祭谱》亦记述:“原祖居下江,传奉皮脸神三具,妈妈神壹,熊头神壹,巴柱神脸壹。二祖阿塔里率族西迁,船逆水遇风,神器仅余神书数册,岂非天意……”由此可见,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曾有着丰富的萨满面具文化,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跳神面具。
玛虎者,满语也。汉语“假面”之意,也称鬼脸。久之,满语渐废,时人不解玛虎之意,传言“玛虎子”为鬼怪之意,附会也。
头罩玛虎演绎故事,即谓玛虎戏,瑷珲普用满语,俗称“玛虎朱陈”、“玛呼主春”、“玛虎朱春”,实即满洲罩面小戏。在瑷珲,玛虎并非装饰或陈设之物,自古素为满洲各望族大户萨玛、穆昆达、噶珊达、扈伦达、哈拉达部族珍藏之宝,皆有谱牒档色入案。各种玛虎造型,非闲庸者为,皆有尊贵身价、辈分、地位、名份。若绘神形,亦属世奉神祇和百灵魂体,各有履历故事、各有代代诵歌之功业。头罩玛虎,绝非余兴,初发轫于说古、颂古,发于缅怀、祭拜和演绎各代祖先故事。瑷珲早年有《阿骨打发兵》、《萨大人龙宫借粮》等,也有玛虎小戏,围众拥挤,喜爱其形,喜听其歌。考其源,皆清末至民国以降,传流之故事。下马场祁世和之父亦会玛虎小段,并言宁古塔亦玛虎小戏之源,盖传于清康熙朝戍边诸姓。据本家先妣美容额嬷所言,宁古塔玛虎戏很盛行。火茸城南柳毛沟子和江西老狐狸崴子,皆有部落。玛虎戏很有名,亦有汉尼堪流人倡演勒勒戏。宁古塔为文化荟萃之所,多姓喜玛虎戏,戏中有萨玛故事,有猎物幻女救人,戏中人各罩玛虎,唱做技绝惊座。远戍瑷珲后,偶有稔此技者,在军中献艺,人聚如潮,缅萦乡情,台上下声泪俱合,世代传继,阖众不泯。瑷珲满民祁大姑、徐大铁嘴,小五家子关锁柱玛发之子关大咧咧,皆为早年崇耀人物,闲游沿江各村屯,争相厚待之。
先父德连公,民国至伪满初年,为本姓总穆昆,常向族人传讲家传。瑷珲玛虎喜耍者,传自祖地宁古塔。若逢年节或婚寿喜宴,玛虎戏与黑水秧歌齐驱竞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奉旨北上,由火茸西沟营子、家口百六十员车马并行,先舟后车,又换大江船进至老瑷珲,行走四十余日,达玛哈咬钩八月天,抵萨哈连,离家情,别乡情,思亲情,骨肉分离情,戍地未卜情,罗刹凶险难卜情,何期返里情,千情万情,皇恩浩荡,皇命如铁,号兮,哀兮,思兮,悲兮,寄宁古塔乡情于歌焉、舞焉、戏焉,故乡小戏慰思者,玛虎戏化哀酒,成为宁古塔戍边诸姓满洲家传古风。查瑷珲至呼玛,沿江八百余里,满洲卡伦、官屯、哨口、水师营三十六处,玛虎戏分为呼玛路玛虎戏、黑河口玛虎戏、瑷珲玛虎戏三大支,各有千秋。
康熙间兵进呼玛河,宿帐有玛虎莽式,并携入雅克萨城,《唱雅克萨》、《罗刹思乡》、《萨哈连龙旗亮》,便是当年满语玛虎戏小段子。后人如大五家子老何家三姑、四季屯富家老房子顺和叔,伪满时还能头戴玛虎,扮唱小戏,有情有调,听者啼笑道彩,声泪俱下。
玛虎戏,形态自如,见情生情,无拘无束,易于直达胸臆,且玛虎遮面,依己情之奔荡,尽情宣泄,唱不尽则身动,用头、手、肩、腰、四肢、腕节、足掌作舞。喜耍玛虎朱陈者,皆异口同声畅言,玛虎造诣达精深上乘之位,非苦习不可得。往昔,玛虎朱陈多用满语,后满汉杂居已多改用汉语,近世颇与东北小戏相杂糅。尽管如此,仿学玛虎朱陈者在瑷珲不减,遍及卜奎、三肇一带。不仅满人喜看,如大五家子达斡尔亦有多年影响。因其声情并茂,招徕不少汉儿也争喜之。九十余年来,瑷珲满洲众姓唱诵祖德至诚,有竞歌于野者,有设棚聚友者。此风据传康熙间来自宁古塔,戍居瑷珲沿成一景焉。
(待续)
责任编辑:王卓
K892.2
A
1009-5241(2015)04-0084-05
富希陆黑龙江省瑗珲大五家子村满族老人富育光先生父亲已逝富育光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长春1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