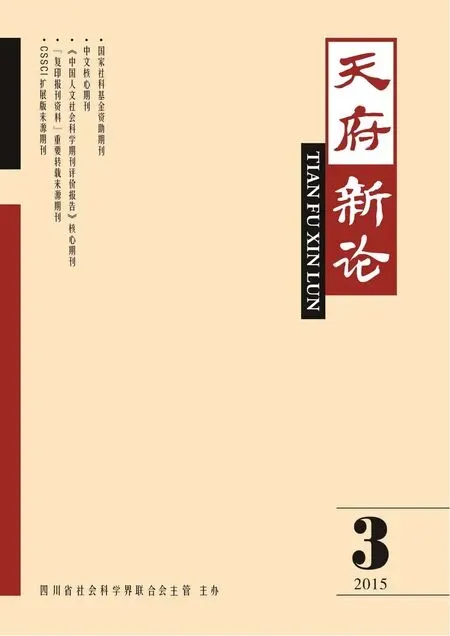超越暴力革命:梁启超有关卢梭论述对自由和权利的探讨( 1899-1901)
范广欣
超越暴力革命:梁启超有关卢梭论述对自由和权利的探讨( 1899-1901)
范广欣
[摘要]本文集中讨论梁启超从1899年到1901年介绍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文字,看他如何逐步深入探讨自由和权利的内涵,也希望以此作为个案探索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波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梁启超是将卢梭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将卢梭理论定位为一套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学说,而不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他对自由的诠释覆盖了从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到政治自由的丰富内容,并且最终超越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倾向的限制,肯定个人自由的独立价值。晚清新文化运动代表中西两个思想传统第一次认真的对话,其对现代基本价值的介绍融入了多方面的资源,包含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梁启超对卢梭的看法之所以异于他人,是因为他把卢梭当成西方自由传统的一员,他对卢梭的解释结合了多位其他思想家的见解。他所介绍的思想自由、“天赋人权”等观念,也融入了儒家思想的因素。
[关键词]梁启超;卢梭;自由;权利;晚清新文化运动
近代中国第一波新文化运动开始于晚清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梁启超、严复、刘师培、马君武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将许多重要的西方现代观念,包括革命、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等等,引入中文世界。他们对这些观念的介绍既广且深,不仅推动了变法改良和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斗争,也促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转型,为1915年开始的第二波新文化运动创造了条件。
本文集中讨论梁启超从1899年到1901年介绍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有关文字,看他如何从不同角度逐步深入探讨自由和权利的内涵,也希望以此作为个案探索晚清第一波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梁启超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由于他和刘师培、马君武等人的宣传,卢梭成为最受欢迎的西方理论家。与其他人不同,梁氏将卢梭理论首先定位为一套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学说,而不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到1901年为止,他认为这套学说有助于扭转中国的命运,因此做了不遗余力的宣传。然而,自1902年起,他发现卢梭理论吸引年轻一辈颠覆基本社会秩序,而且不利于他们组织起来从事政治运动,因此转而支持以伯伦知理为代表的德国国家学说,与卢梭理论相抗衡。也就是说,从1899到1901年是梁启超从卢梭理论入手,积极探索近代自由和权利学说的重要时期。下文将指出,梁启超对自由的诠释并不像其他学者认为的那样,只强调以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为目的的公民参与,重集体轻个人,而没有触及近代自由观念的基本内涵;而是覆盖了从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到政治自由的丰富内容,并且最终超越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倾向的限制,肯定个人自由的独立价值。①其他学者的观点,可参见: Peter Zarrow,“Anti-Despotism and‘Rights Talk’: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Human Rights Thinking in the Late Qing”,Modern China 34 ( 2008) : 184-195; Peter Zarrow,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1885-1924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104-117; Edmund S.K Fung,“The Idea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Revisited: Plural Conceptions and Dual Responsibilities”,Modern China 32 ( 2006) : 454-458.
一、思想自由与天赋人权
梁启超介绍卢梭学说始于1899年8月起在《清议报》上连载的《自由书》。但是在1901年末发表《卢梭学案》之前,梁氏并无专文讨论卢梭学说,他往往将卢梭与约翰·密尔和孟德斯鸠等人相提并论,把他们都看作西方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1〕从《自由书》开始,梁氏对西方自由思想的介绍有两个基本思路贯穿其中,其一是思想自由,其二是“天赋人权”。这两个思路也体现于他的卢梭论述。
《自由书》一开始便彰显思想自由的意义。梁启超在叙言中引用密尔阐述此书的缘起:“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2〕有趣的是,这句话并不见于密尔《论自由》( On Liberty)原文。尽管密尔强调思想自由是人类最重要的一项自由,而且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密不可分,但他并没有将自由与(特定)人群的进化( evolution)联系起来。〔3〕从字面上看,人群进化不是密尔,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家关注的焦点。梁启超将自由与进化相连可能是受严复的影响。②严复1899年开始翻译密尔《论自由》,1903年以《群己权界论》为名出版此书。进一步分析,中文“进化”一词,与对应的英文“evolution”含义并不完全吻合,前者包含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意思,后者只是适应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演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将思想自由与“进化”联系起来,并不十分违背密尔的原意,因为进步( progress)正是《论自由》反复强调的价值观念。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渗透,梁启超关心的是自由与否如何影响不同人群(族群、国家等)的竞争,而密尔关心的则是自由如何推动全人类的进步。
很明显,在人类的各项自由中一开始便引起梁启超关注的是思想自由,而非与政治自由相关的内容。除了思想自由,密尔原书讨论的重要自由还包括“品味和追求的自由”( liberty of tastes and pursuits)和“个人合群的自由”( the liberty of…combination among individuals),也就是个人不受阻碍实现自我价值的自由和集会结社的自由,却被梁启超忽略。〔4〕这两项自由对于人们争取合理政治制度的斗争都不可或缺。思想自由,尽管可以有效用来批判“腐败或暴政”( corrupt and tyrannical government),却不足以推动根本的政治变革。〔5〕这样看来,梁启超热切期望传入中国的首先是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所倡导的批评公共事务的自由,而非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倡导的政治自由。
然而,继续阅读《自由书》可以发现,梁启超介绍卢梭等人的自由学说不仅是要批判旧世界,更是希望开创新世界。他甚至指出可以通过“革命”完全恢复人民的“自由权”。〔6〕要掌握梁启超对“革命”和“自由权”的理解,除了思想自由,我们还必须讨论《自由书》的另一个基本思路,即天赋人权。天赋人权的观念是19世纪70年代明治维新早期日本知识界理解西方自由学说的产物,具体而言,是加藤弘之创造了“天赋人权”这个术语,用来翻译西方的“natural right”(今译“自然权利”)。
梁启超早在写作《自由书》以前已经开始向中国人介绍这一观念,甚至直接使用这一术语,却没有详细加以讨论。他在1899年2月的《爱国论》一文引用“西儒”的观点指出,“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和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同样“损害天赋之人道”;正是明白了这个道理,欧洲各国人民才“赴汤蹈火”,不惜流血奋斗争取民权。〔7〕他在《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更直指“天赋人权”说在欧洲的盛行导致数千年等级社会的根本转变。〔8〕
1899年9月,梁启超在《自由书》中转录深山虎太郎《草茅危言》一文,向中国读者更详细地解释“天赋人权/民权”观念。该文开篇便指出:“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养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根据引文,民权源自上天给予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天赋人权是绝对的价值,无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剥夺一个人的自由。这便隐含着对传统社会奉为圭臬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挑战,因为所有这些政治或者家庭的权威据说都不能否定民权。文章还指出人民及其权利先于政府的设立,很明显是受卢梭等人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指出三代和孔孟均注重民权,则是尝试沟通西方自由权利学说与儒家理想。最后结论是,改革秦汉以来的积弊必须从恢复民权开始。〔9〕
仔细解读“天赋人权”,可以发现这个观念不完全是“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的对应,在中文语境中还融合了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某些核心价值。这个观念使浸润在儒家传统中的人特别容易联想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诗经·大雅》)、“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中庸》)等经典名句及其诠释。因此,透过这个观念来了解自由和权利,梁启超(及其读者)所获得的认识与欧洲启蒙思想家必然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因为天在儒家传统中是最高的道德权威,由上天所赋予并根植于人性的自由和权利不能不是高尚的,而不可局限于满足个人私利和物欲。自由和权利必须包含一种转化性的力量,一种道德的力量,可以超越个体,服务人群,小到贡献国家,大到造福全人类。从这个逻辑出发,财产权,这一洛克等自然权利思想家最看重的权利,恐怕便不能轻易地被早期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为“天赋人权”。然而,“天赋人权”所包含的道德理想色彩和群体意识却与卢梭的权利观颇为契合。另外,也必须指出,梁启超对“天赋人权”的支持一开始就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置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之下。对他来说,自由不是终极价值,而是从属于人群进步和民族竞争。〔10〕
至迟1901年开始,梁启超多次用“天赋人权”的观念概括卢梭学说。〔11〕这个观念涉及自由、人性和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人了解卢梭关于自由和权利的独特论点的确有帮助。①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四章《论奴隶制》中阐述自由与人性和道德的关系如下:“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而且取消了自己意志的一切自由,也就是取消了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性。”见Rousseau,“of the Social Contract”,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45。中译根据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必须指出,“天赋人权”更适合描述卢梭的“社会的自由”( civil freedom)和“政治权利”( political right),而非“天然的自由”( natural freedom)和“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梁启超便曾直接把“天赋人权”与“政治上之自由”联系在一起。〔12〕实际上,卢梭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然权利论者,他认为政治权利不是自然权利的延续,人们通过缔结社会契约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便放弃或至少中止了他们在自然状态(前政府/无政府状态)中所享有的权利。②《社会契约论》的副标题是“政治权利的原理。”用“天赋人权”概括卢梭自由和权利论所包含的意思是,人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虽然直接受到社会契约和法律的保障与约束,归根结蒂却还是源于其在自然状态中所享有的、上天赋予的绝对自由,因为没有这一自由,他们便不可能选择参与契约、进入社会。引申开来,当人们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得不到基本保障时,他们便可以选择与腐败社会决裂,恢复行使自然权利,回归无政府状态或重建合理政治社会。到这一步,暴力革命的含义便呼之欲出了。
综上所述,梁启超早期介绍卢梭学说同时受思想自由和“天赋人权”两个思路的影响。他一方面觉得应该优先引入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观念,着重对旧世界的意识形态批判;另一方面又用“天赋人权”概括卢梭学说,不仅直接肯定政治自由,也间接支持人民反抗的权利。梁启超如何在两个思路之间取得平衡?他对“天赋人权”的赞赏是否意味着他变得更着重政治自由而非思想自由呢?下文将指出,梁启超介绍卢梭学说并不是倡导激烈变革乃至暴力革命,他宣传“天赋人权”其目的还是为中国人争取思想自由。具体而言,梁启超不主张立刻给与人民政治自由,更无意鼓动推翻旧世界的武装斗争,而是期望用这一学说教育、感动中国人,将他们从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学会热爱自由,向往自由,拥护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
二、从思想自由到文化革命
仔细研读梁启超在《自由书》中最倾向“革命”的文字,可以发现他在通过“革命”恢复“自由权”之前,预设了一个容易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步骤,即人民的觉悟。根据他的观察,政治变革依赖人民的“进化”,卢梭的自由和权利观便是教育人民、促使其迅速“进化”的利器。〔13〕具体而言,当人民通过启蒙而“自悔”、“自悟”,决心“不放弃其自由权”时,他们就能够起而“革命”,完全恢复“自由权”。〔14〕卢梭的学说也可充当“破坏”的力量,以克服中国人的“恋旧”情绪,驱使他们争取“进步”,并与其他国家竞争。梁启超指出,卢梭社会契约论是最适合中国的“医国之国手”,它已经在欧洲和日本奏效,必能将中国引入一个“国国自主,人人独立”的新世界。〔15〕
所谓卢梭理论在欧、日奏效,说明梁启超心中的“革命”并非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君主制度,因为欧洲许多国家和日本虽然经历了某些改良,君主制却依然保留且基础巩固。而且,梁启超并不认为“恋旧”情绪或者保守势力须被新兴力量完全克服。相反,他认为两种势力应达至平衡,以避免“暴乱”。〔16〕这一点说明,他不希望变革与暴力相连,而希望自由和秩序可以并存。
要进一步考察梁启超如何理解自由和革命的关系,梁启超1900年4月给康有为的信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这封信中,梁启超发现自己不得不反驳康有为对自由学说的攻击,他试图说服恩师卢梭理论并不会在中国导致暴力革命。这封信表明梁启超决心用卢梭等人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学说,将中国人从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一言以蔽之,他要用卢梭理论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在此基础上,他希望中国人心灵的改变可以引起政治现实的和平演变,最终实现一场没有暴力和苦痛的政治“革命”。
这一时期( 1899-1901)的一系列其他文章表明,约翰·密尔对思想自由的看重和来自宋明理学的深厚影响结合在一起,使梁启超坚信思想必须引导实践,自由独立精神的养成必须先于新世界的建设。他甚至断言:“精神一到,何事不成?”〔17〕因此,毫不奇怪他强调实现政治自由必须从心灵自由开始。他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澄清,他宣传自由不是针对压迫者,而是针对人民的“奴隶性”。他指出,“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各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18〕也就是说,不知道珍惜自由、热爱自由的“奴隶性”是中国长期政治腐败的根源和国家独立的障碍。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便是宣传、灌输自由思想,使人们觉悟,追求自立,不受他人的限制。他将自由与人的本性相连,显然是受“天赋人权”观的影响。引文再次说明,梁启超之所以赞颂卢梭理论,不是要立刻落实政治自由乃至反叛的权利,而是要用“天赋人权”的观念教育国人,使他们从心里爱自由,不愿受别人摆布。
对梁启超来说,卢梭等人的理论首先是帮助中国人从本国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用“数千年之腐败”概括中国历史,用“奴隶性”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伤痛,都开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先河,而带有鲜明的文化革命的色彩。其实,他最想介绍给中国人的仍是思想自由,却表现得非常激烈。梁启超宣称:“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19〕第一句非常接近卢梭原文,强调自由是“天赋人权”。〔20〕第二句,便直接用自由否定三纲。这一言论对浸润在儒家传统中人来说不啻振聋发聩。因为传统等级制度的卫道士认为,三纲意味着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的绝对权威,不接受三纲才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梁启超在信中批评康有为“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的说法,指出民权自由,尤其自由思考和自由讨论,是开发人民智力的前提。康有为的观点其实很有代表性,许多反对激进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运动的人,都主张人民必须先接受教育,才能承担自由所带来的责任和风险。①约翰·密尔也认为自由原则只适用于文明社会。见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7,10.梁启超的回应是,人们必须接受包括卢梭理论在内的自由学说的熏陶,才能充分运用自由掌握并发展新学问。他们也需要自由以挑战传统的君主制,寻求不一样的政府形式。当梁启超指出只有自由才能培养智慧而富裕的国民时,很明显他把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当作建设繁荣的政治社会的前提。〔21〕那么,他到底期待什么样的政治变革呢?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梁启超期待的是没有暴力和动乱的政治转型。他尝试说服康有为在中国提倡自由不会导致法国大革命这样的“惨祸”,因为中法两国“民情”根本不同。卢梭的理论足以在法国导致祸乱,却是适合治疗中国之病情的良药,因为法国人容易冲动,而中国人因循守旧,数千年来无论是学术或政治都缺乏变革的动力。具体来说,“中国于教学之界则守一先生之言,不敢稍有异想;于政治之界则服一王之制不敢稍有异言。”为治疗这一病症,梁启超期望引入自由学说,使中国人至少热血沸腾、头脑发狂一次。他觉得新势力在中国不可能彻底击败旧势力,而最多和旧势力达致平衡,最终自由和秩序可以并存。〔22〕可见,对梁启超来说,卢梭的学说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其唯一的效用是平衡中国人守旧的国民性——“国民性”是五四的词汇,梁启超用的是“民情”,但在这个语境下意义是一样的。他认为,没有新势力的冲击,人民过度守旧会导致惰性乃至“奴隶性”;然而,没有旧势力的阻碍,新势力就会变得过于激进,破坏基本的社会秩序。①这个说法和托克维尔(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表达的观点颇为接近。后者认为,民主(平等)力量无制约的发展,没有贵族(等级社会)势力的平衡,便会破坏自由。See 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Harvey C.Mansfield&Delba Winthrop ( Chicago&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梁启超进一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惨祸”是由革命者以自由的名义造成,而不真是自由本身的过错,卢梭不应该为大革命负责。他认为,自由就意味着“自治”,“自治”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不受别人的统治;第二,真正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私欲而行为得体。两层意义互相关联,一个人必须具备一些内在的条件和能力才能够不被他人所控制,也无意控制别人。对梁启超来说,这样的人珍惜自己的自由,也不会侵犯别人的自由,法国大革命的问题正是以自由为名,侵犯别人的自由。显然,他不可能接受自由与自治/自制、权利与责任的分离。〔23〕
回到政治自由与思想自由的话题,梁启超的观点也许可以概括如下:思想自由应该是无条件的,它本身就构成一切学术和政治进步的前提;而政治自由是有条件的,任何人行使其政治自由都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不能破坏社会的基本秩序。人民必须先获得一定的觉悟和自我控制、自我提高的能力,才能够获得政治自由。梁启超受到西方自由学说和宪政法治的影响,强调行使自由必须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同时,他的儒学修养使他坚信,归根结蒂法治的维系不是靠制度的保障,而是靠人民的觉悟。〔24〕要提高人民的觉悟就不能离开思想自由,一切启蒙和文化革命都必须以思想自由为前提。
三、从群体竞争到个人自主
上文指出,梁启超介绍卢梭等人的自由学说有两个基本思路,即思想自由和天赋人权,但是这两个思路都受到进化论的制约,都以人群的进步和民族的竞争而非个人的基本价值为最后的依归。梁启超在1901年末连载《卢梭学案》(以下简称《学案》)才终于肯定个人自由的独立价值。②《学案》先连载于《清议报》,1902年又连载于《新民丛报》,可见梁启超对内容的重视。《学案》是梁启超对卢梭理论最系统的介绍,包含了对卢梭自由学说最浪漫主义的诠释,而以个人自主( individual autonomy)和人民主权为核心。下文集中讨论个人自主,因为人民主权强调的还是群体的政治自由,讨论天赋人权时已有所涉及,而个人自主的观念在这篇文章中才第一次展现,反映了梁启超讨论卢梭自由学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学案》由一个简单的卢梭传记和正文组成,个人独立是正文前半部分的焦点。前人的研究揭示《学案》的正文源自一部法文欧洲哲学史,中江兆民将全书译为日文,梁启超又将日文本与卢梭章节翻成中文。③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收录于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5-63页。中江兆民是明治时期在日本介绍卢梭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将Alfred Fouillée所著的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 1875)译成日文,题为《理学沿革史》( 1886)。以往的学者或者完全忽略这一传承关系,或者只注意梁文与中江译文的差异,而忽略《学案》所传递的完整信息。以下分析希望既注意梁启超的独特贡献,也注意把握中国读者的整体观感。当时大部分中国人读梁启超的文章,像学生听老师上课,为授课内容所感动,却并不像今人读学术文章那样介意观点是否原创。
有趣的是,《学案》对个人自由的诠释似乎更接近洛克而非卢梭,甚至带有无政府个人主义( anarcho-individualism)的某些色彩。正文先通过四个例子(其中第四个例子不见中江原文而为梁启超所加)力图证明自由是国家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基石,再仔细解释为什么国家的创立必须以契约精神为原则:因为人人自由平等,两人以上互相合作便必须订立契约,引申开来,一国中人互相交际,无论为什么目的都必须依赖“契约之手段”,既然所有人与人之间的交际都要通过契约,国家的创立也非依赖契约不可。〔25〕这个说法对传统权威和所有新旧政治权威都具有颠覆性。传统权威受挑战,因为契约关系预设各方的平等自由,而不承认任何的等级差别;政治权威受挑战,因为当契约被当作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时,统治者便很难诉诸武力或其他压迫性的手段,令人民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这样,社会契约论便被用来否定所有不尊重个人自由和其他个人利益的政权。
《学案》强调,社会契约不会“剥削”个人自由而以“增长坚立”个人自由为目的。〔26〕具体来说,首先,社会契约不会把人民的自由和权利赋予个别统治者。《学案》认为,这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霍布斯和格劳修斯( Hugo Grotius)相关理论根本不同之处。根据梁启超的原文,“民约既成之后,苟有一人敢统御众人而役使之,则其民约非复真契约,不过独夫之暴行耳。”这句话相当忠实于中江兆民的日译,只有“独夫”一词是梁启超所加,特别提醒中国读者儒家反暴君的传统和卢梭理论之间的联系。〔27〕《学案》接下来解释个人自由不能放弃,因为自由不仅是权利和责任,而且是道德的来源,霍布斯的理论违反了道德的基本原则。〔28〕梁启超还特别在正文之间插入按语表明自己的意见,指出如果契约要求完全放弃权利,这样的契约根本就不值得遵守。〔29〕《学案》还指出,根据卢梭的学说,即使人们愿意放弃自身的自由,他们也无权放弃后人的自由,中江的日译批评父母把孩子卖给他人,是违背了天地的公理,超越了父亲的权限,梁启超还要加上“文明之世所不容也”。他又通过按语指出,根据传统的中国习俗,父母可以出卖子女为奴仆,杀害子女也罪减一等,都是因为“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权”。〔30〕这样,《学案》便批驳了霍布斯等人的理论,证明人们不可以把自由和权利托付给少数统治者。接下来,便要处理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否要求个人把自由交给人民全体或者说人民的国家?
《学案》并不否认,卢梭的确指出加入社会契约时,各人应把所有的权利交给国家。《学案》认为,根据这个说法社会契约便非常接近“共有政体”,企图把个人完全融入国家。我猜想,所谓“共有政体”指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构想,因为“共有”意味着公有制,而“政体”则意味着政府形式,合起来就是实行公有制的政府形式。然而《学案》试图说服读者,尽管不无相似之处,但卢梭的理想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真民主主义”。《学案》将卢梭的集体主义倾向追溯到柏拉图哲学和希腊罗马共和政治的影响,两者都重视国家多于个人,还引用卢梭在其《政治经济学》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加以证明。〔31〕《学案》对这一倾向提出质疑,认为个人固然需要在财政上支持政府,却不可牺牲“自由权”。无论以什么理由牺牲个人自由,都与社会契约论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因此,《学案》认为,社会契约中注重国家而牺牲个人的内容并不代表卢梭的真实想法。卢梭关于每个人将权利交给所有人便是交给自己的辩护,《学案》认为是“英雄欺人”,反问当每个人都已经被国家“吞吐”、“消融”之后,又怎么能恢复其固有的权利呢?〔32〕
为重新确立卢梭个人自由捍卫者的形象,《学案》指出,卢梭其实只要求个人放弃一部分权利和自由,以供群体维持基本需要。社会契约不单不会使个人放弃些许权利,还会增加他们的利益。这也许是从捍卫个人自由的角度解释卢梭所能提出来的最有利的证据。卢梭的确说过类似的话,然而,他紧接着便指出,只有主权者才有权决定哪一部分个人自由和权利必须放弃。〔33〕也就是说,人民的国家必要时可以要求个人牺牲一切。
梁启超翻译的《学案》总的来说把卢梭当成现代民主的开创者,强调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无论是统治精英、其他传统权威,还是人民的国家,都必须尊重个人自由。通过将卢梭的学说与霍布斯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区分开来,《学案》将卢梭刻划为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最坚定的支持者。
四、结论
从1899到1901年底,梁启超有关卢梭论述比较系统地向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介绍了现代自由的观念,其重心则一直放在思想自由上。梁启超希望运用他在日本所享有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做启蒙的工作,把中国人从传统文化和政治权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思想上做好准备,迎接以保障人民各项自由为目的的政治改革。透过“天赋人权”,梁启超向中国人介绍了政治自由,“天赋人权”这个观念也涵盖各项基本的公民权利,乃至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然而,梁启超并不急于落实这些激进理念,他宣传“天赋人权”还是服务于思想启蒙的目的,希望人们受启发而热爱自由、反对压制。1901年末的《卢梭学案》受中江兆民相关译文的影响,第一次把个人自主放在群体竞争之前,承认个人自由作为终极价值,标志着晚清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高峰。
梁启超是中国第一波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正如李大钊、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一样。必须指出,梁启超的文章从晚清到民国初年反复刊印、长期流传,渗透到中国知识界的每一个角落,滋养教育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梁启超对思想自由的鼓动深入人心,他个人对思想启蒙的贡献不可忽视。
晚清新文化运动代表中西两个思想传统第一次认真的对话,其对现代基本价值的介绍融入多方面的资源,包含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从政治上说,当时最重要的思潮包括暴力革命、自由人权和国家主义。梁启超的卢梭论述坚持从自由人权出发,而不像其他人集中于暴力革命,这一倾向从未改变。他在1902年以后,逐步放弃对卢梭的支持,转向国家主义。虽然如此,他对卢梭理论的基本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觉得这种对自由和权利的浪漫主义追求不能解决反而加深中国的问题。他对卢梭的看法之所以异于他人,是因为他把卢梭当成西方自由传统的一员,他对卢梭的解释融合了孟德斯鸠、康德、密尔和洛克等人的思路。从文化上说,梁启超的论述固然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烈的反传统、反思国民性的因素,但中国传统文化也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他对思想自由、思想先于行动的强调,反映了《大学》由内而外,先格致诚正,再修齐治平的模式。他对“天赋人权”的阐发,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自然权利论,而是受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影响。他强调个人自由不可侵犯,也不忘联系儒家反暴君的传统。梁启超介绍的这些观念,反映了两个文化的融合如何塑造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传统,无论我们视这个传统为遗产还是为包袱,直到今天它都还影响着我们对现代社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C〕.北京出版社,1999.339、340;梁启超全集:第十册〔C〕.北京出版社,
1999.5932.
〔2〕〔6〕〔7〕〔8〕〔9〕〔10〕〔12〕〔13〕〔14〕〔15〕〔16〕〔17〕〔25〕〔26〕〔28〕〔2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C〕.北京出版社,1999.336,349,275,314-315,342,458,383-384,340,349,349-350,349,338-339、375-376、455,504,506,505,505.
〔3〕〔4〕〔5〕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Inc.1947,12、14,12,15.
〔11〕〔2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C〕.北京出版社,1999.384、455、458;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册〔C〕.北京出版社,1999.558.
〔18〕〔19〕〔21〕〔22〕〔23〕〔2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册〔C〕.北京出版社,1999.5931,5932,5932,5931-5932,5931-5932,5932.
〔27〕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C〕.北京出版社,1999.504;中江兆民.中江兆民全集:第六卷〔C〕.126.
〔30〕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C〕.北京出版社,1999.505;中江兆民.中江兆民全集:第六卷〔C〕.128.
〔31〕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C〕.北京出版社,1999.505-506; Rousseau,“Political Economy”,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6.
〔32〕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C〕.北京出版社,1999.505-507; Rousseau,“Of the Social Contract”,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50.
〔33〕Rousseau,“Of the Social Contract”,in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61.
(责任编辑:赵荣华)
[作者简介]范广欣,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研究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15-03-13
[文章编号]1004-0633 ( 2015)03-002-7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