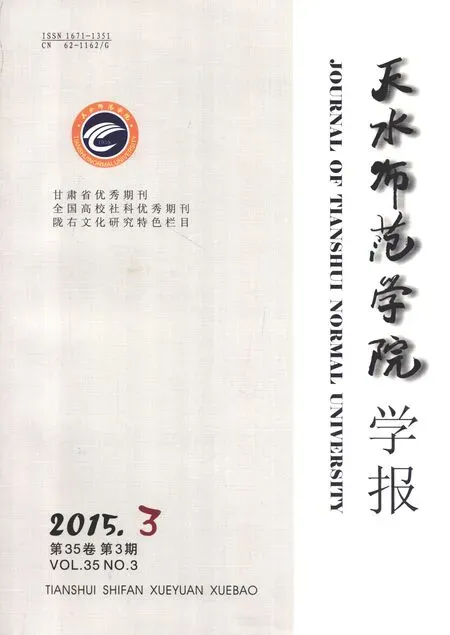敢以莲心犯尘世——薛方晴长篇小说《染坊》简论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1-1351(2015)03-0124-04
收稿日期:2015-03-19
作者简介:薛世昌(1965-),男,甘肃秦安人,天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
薛方晴,1942年生于甘肃秦安县,1967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薛方晴女士有胆有识、能诗能文,古体诗词、新诗、散文、短篇小说、学术论文,她样样皆能,她也懂音乐,通声律,能写歌剧,能写电视剧,笔触所向,均有斩获。出版有古体诗词集《莲香阁吟》、现代诗集《莲香阁咏怀》、小说散文集《人生旅程的倾诉》、电视连续剧剧本《飞将军李广》、《不会干涸的爱河》、《料峭春风更寒》、八幕历史歌剧《麦积烟雨》、六幕历史歌剧《飞将军李广》等,2014年,她的长篇小说《染坊》又出版面世。这部四十万字的巨著,通过对书中各色人等的细腻描述,发出了一位白发老人对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真切响应,彰显出当下时世知识分子高尚的人文精神,在读者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本文欲通过下面的粗陋述评,阐发其思想内涵、判断其艺术价值,并表达自己对作者虽身居乡野却心忧天下之宝贵精神的真诚敬意。
一
《染坊》的基本主题或云情感底色,无疑是作者对国家的深深热爱。李秋明说《染坊》“掏心掏肺呈忠略”,可谓深谙了此书的创作动机。一个“忠”字,拈出了作者的款款心曲并广获读者共鸣。而呈现于爱国这一情感底色之上另一个分明的主题,就是反腐。作者对中国社会这些年让人发指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透视与揭露。小说运用了几乎所有的叙事手段,层层描述了从教育、学术、医疗,财务到行政,从演艺圈、新闻界、基层乡镇到公安部门等各个方面的社会腐败。阅读本书,几如阅读当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甚至像是阅读人耶鬼耶的《聊斋志异》。在现象描述的同时,作者也形象地探讨着造成腐败的根源。为此小说屡屡深入到人性深处——随着描写的深入,我们的情绪渐渐地从震惊、愤怒而变为扼腕悲叹:腐败,居然是那样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社会的“腐败化进程”居然是那么的不知不觉又似乎合情合理甚至还无可奈何!小说中那个一直劝说丈夫让他不要太贪的妻子对于腐败似是而非的认识和摇摆不定的态度,正表现出我们几乎所有人对腐败的默许与纵容。这一人物形象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我们默许其腐败的,我们纵容其腐败的,我们有时候还与其共谋的,甚至我们现在还要清剿的那些腐败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情性相关的家人与亲属——甚至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说本书触及到了人生与社会的某种悲剧性,则这种“反腐就是反自己”的悲剧性即是其一。
但作者最终把自己对腐败中国的思考凝聚为“染坊”这一书名。“染”字喻言出中国式腐败瘟疫一样的空间普遍性,而“坊”字则以其字眼的古旧道出了腐败在时间上的历久性。这一命名与台湾柏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酱缸”之喻不谋而合神理暗通。“染坊”也好,“酱缸”也罢,都隐喻着由腐败的体制和腐朽的文化所共谋而形成的腐败的社会——人性异化最为可怕也最无可逃避的外部规定力。人性如水,它的模样取决于装它容器的模样。中国人不是天生贪婪无度,亦非天性贪赃枉法,中国人只是因为体制的不健全,才膨胀了自己贪婪无度的物欲,也是因为文化的不够健康,而释放了自己贪赃枉法的魔性。在这方面,作者的思考确乎是深沉的。小说最后,她借人物之口警醒世人:“但是,没有人民自己的觉醒和奋斗,只依靠上层领导的决心,利益固化的藩篱是很不容易突破的。反腐倡廉尽管消灭了一些老臣和苍蝇,但腐蚀污染社会的染坊依然存在,祸国殃民的贪腐分子还会从染坊中滋生出来。” [1]392作者立身偏乡僻壤但是发声于脏腑天庭的这种国民性警醒,和鲁迅当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用心何其相似!
二
描述腐败的现象,探析腐败的成因,终归是为了寻找疗救腐败标本兼治的办法。在治本方面,作者和鲁迅一样,试图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中国民众施以唤醒。作者没有片刻忘记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比如她对保姆收贿、司机纳赂的描写,公正且深刻。公正之处在于,在目前这样一个腐败不堪的社会大染坊里,不论大小,只要手握权力,只要是“当权者”,则他们几乎无一不贪;深刻之处在于,狐假虎威的贪污比真狐狸真老虎的贪污更为可怕——苍蝇比老虎更可怕。如果连所谓质朴的保姆都开始了腐败,如果连所谓工人阶级的司机师傅也开始了腐败,则中国的腐败就会演变为无处不在的“云结构”——不是雾霾胜似雾霾。不过,作者虽然在人性的挖掘方面志在不小,也不同程度地让人物步入过灵魂反省的圣殿、感受过自我搏斗的艰难,但本书在人性的探讨方面显然没有全面清算的计划,而只想对症下药,只想咬住诸多人性当中最具当下色彩也最致腐败加剧的一种——“贪婪”——并把它放大了给人看。相比于如何慢慢治本的思考,作者想得更多也让她更显焦虑者,是如何迅速地治标。面对中国当下塌方式的腐败,作者觉得:如果说目前中国第一位的要务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么《染坊》的当务之急就是大声地说出反腐的紧迫、表明社会的呼吁、喊出自己的响应!
自古疗救之法,扶正而去邪,国家的治理也是如此,反腐去疾的同时,需要倡廉扶正!于是,作者在本书中不惜笔墨地塑造了以康健夫妇与李圣达夫妇为典型的一批出污泥而不染的知识分子形象,从而形成了本书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旨:知识分子的责任认领与形象修复。这也是许多读者觉得《染坊》虽然描写了大量的腐败却也充满了正能量的原因。作者一定觉得:面对滔滔洪水,堵固然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疏导!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屡遭摧残的骞顿命运已是一个令人皆知的事实。不只是当年的“反右”,也不只是十年“文革”,历次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本质上都泄露着一种共同的气息:对于知识分子的蔑视。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又适逢钱本位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人们只尊重官僚知识分子与资本知识分子。于是中国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就成了对知识分子以及知识本身的认识问题与态度问题。身为中国当代“知识史”和“知识分子史”的亲历者,作者在小说中对那些优秀大学生的倾情描写,对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典型的形象塑造,于是就肩负了这样一个重大的使命:对那些在现实生活中被扭曲的被抹黑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扶正,对知识分子社会价值进行深度的形象思考与形象确认,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进行重塑——为他们招魂。相比于本书作为底色的爱国主题,本书的反腐败主题是相对切实的;相比于本书解构性的反腐主题,本书的倡廉主题相对也就是建构性的——《染坊》通过康健他们的形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可能没有官吏们世俗地位的显赫,却有着人格的尊严与心灵的宁静;他们可能没有虚浮的富贵,但是却活得真实、踏实!他们同样是幸福的也同样是成功的!而那些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格高尚的、为事业而努力的、为真理而奋斗的知识分子,他们才是真正中国的脊梁!
三
《染坊》的主人公康健出身于贫穷西部的一个偏僻山村,后以勤奋的学习考入首都名牌大学,且以优秀的成绩学成于水利专业,复以报国寻梦的壮志到了三峡电站。他真才实学而又勤奋睿智,身居要职而能竭诚于事业,两袖清风但是一身正气,忧国忧民却能脚踏实地地从自己做起、从对身边人的影响开始……这是一个浑身充满了人生正能量的优秀知识分子形象,他和同样优秀的妻子和朋友,以一组人物群像的方式共同谱写出值彼污浊时世里一种洁身自好的人生合唱。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人物关系,往往有一个不言而喻的镜像式设计,即在一个黑脸的旁边,往往会安插一个红脸,让他们互为映照。《染坊》也是这么做的。作者在通过一种人去描写人性之贪婪的同时,没有忘记通过另一种人去描写人性对贪婪的超越,即人们在作品中既看到了对腐败现象的猛烈抨击,也看到了对廉洁人生的由衷赞美;既看到了对腐败滋生而民众戻气纵横的深重忧患,也看到了对洁身自好之浩然正气的乐观自信……和那些一味抹黑的让我们身陷绝望的写作不同,《染坊》在不讳言腐败、腐化、腐朽的同时,却能同时看到健康、看到神圣、看到光明。
然而这种对照式相辅相成的人物设计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即在可信度与真实性上,这一红一黑两组人物可能会极不对等,并主要表现为红色一组的不够真实与不够可信——他们往往失之于太过完美!也就是说,在《染坊》中,康健这一类正能量的人物形象,在其正能量形成与正能量释放的过程中,存在着两个危险的走向。其一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曾经的“高大全”人物形象,其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普遍的才子佳人模式。然而,本书的作者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她一意孤行地倾情打造着本书的正能量之核心人物——康健和李圣达、邓月、刘音笛等。她的笔端饱含着自己对这几个人物的热爱,她让这些人物的成长绕开了所有可能让他们不伦不类的撞击与变异,她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些人物的天真,同时也保护着自己对人生历七十多年而不变的某个美好想象。这想象几乎纯洁到了不允许自己的人物有丝毫的藏污纳垢之程度——如果我没有误读的话,她甚至不惜让他们走向形象的扁平化。有人认为《染坊》是“批判现实主义”的, [2]5我认为这话只对了一半。在“反腐”的即“去疾”的这一半上,《染坊》确乎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在“倡廉”的即“扶正”的这一半上,《染坊》则是浪漫主义的:《染坊》的一组红脸人物太完美了!他们长相英俊,习惯优雅,甚至不抽烟,也不贪酒……而这分明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疏离。
难道作者这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么?不是!作者这样写,不是要重蹈高大全形象之覆辙,也不是要重回才子佳人之旧路。作者这一明知故犯的艺术设计,首先是要在小说的情节安排上实施这样一个反转:就在这样的童话人生中,贪欲在悄然滋生;就在这样美好的对面,腐败却在悄然隆起!甚至,正是我们的真善美,却促成了别人的假丑恶!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就先要写出人生的有价值;“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也就先要写出人生的无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呈现出毁灭与撕破的那个可怕过程。其次,这一明知故犯的艺术设计,是作者有意地要用坚贞不渝的美好爱情与情同手足的同窗情谊,去对抗丑陋,至少去对比丑陋。曾几何时,“恶劣的道德环境破坏了人们对于善的感受力,破坏了人们对怜悯、同情的感受力。我们的作家乐于叙写丑的和恶的东西,乐于展示人的阴暗的心理、卑下的欲望、粗俗的举止、低级的趣味和残忍的想像。我们的作家不是培养人们对生活的眷恋的热情,而是鼓励人们以一种游戏的、放纵的态度敌视生活。” [3]也许,作者是痛感于当下文学的这种颓废,意欲有所振作。她一定这样想:自己的红脸人物如不这般完美,如何去与那些黑脸人物抗衡?没有浩然的正气,何以消解汹涌的戻气?
和小说中正面人物正义形象的鲜明性相比,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即那些腐败者的形象刻画,相对就显得苍白。作者虽然写到了好多腐败人物,但大部分都是面目模糊一坏了之。作者在倾情打造自己喜爱的正面人物之同时,对自己不喜欢的反面人物没有给予艺术上公平的待遇。作者为什么不也热爱一下自己的黑色人物呢?小说毕竟不是道德。小说是艺术,小说的态度是美的态度而不是道德的态度。所以莫言下面的一段话值得作者认真体会:“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一个人,哪怕是技艺高超的盗贼、胆大包天的土匪,容貌绝伦的娼妓,都可以进入他们的故事,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故事时,总是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表情。” [4]106
四
为了顺利地推出自己的这一组无比珍爱的红脸人物,作者甚至牺牲了小说的情节复杂性与矛盾尖锐性。
作为长篇小说,《染坊》的矛盾冲突多重多样但并不尖锐,故事情节够不上曲折,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情节淡化现象。如果说一本长篇如一个棋局,则《染坊》就是一盘缺少对杀的棋局。按说,《染坊》中那几十个有血有肉有性格有愿望的人物之间,免不了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龌龊争执,而其愿望受挫所形成的是是非非甚至戏剧化的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又按小说的反腐败内容,本也潜藏着比较激烈的生死抉择,为什么小说在总体上却呈现出一种和风细雨般的“和谐叙事”呢?
前面已经说过,本书一个更为深刻的主题是:知识分子人格的重塑与使命的认领。为了实现这一主题意愿,为了坚定地诠释“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这一知识分子永恒的人格理念,为了体现这一理念的康健与李圣达形象的鲜明性,本书在人物关系的设计上,显然回避了矛盾的激化而选择了矛盾的消弥。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其人物关系的设计,由于要在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收获对立而又统一的艺术张力,故常常在设计为亲密的同时也设计了背叛、设计为朋友的同时也就设计了仇敌、设计为付出的同时也就设计了索取……体现在任何一个人物的自身,他是强大的他同时却也是弱小的、他是慷慨的他同时也一定是吝啬的、他是爱一个人的同时却也是恨一个人的……而康健和李圣达这两个男主人公,在作者双峰并峙的描写中,不是让他们两极分化,而是让他们志同道合;邓月和刘音笛这两个女主人公,也是两水并流式设计,作者同样没有让她们分道扬镳,而同样让她们情同手足。小说中这两对主要人物之间超常也超稳定的和谐关系,即从根本上消弥了矛盾冲突激烈化的可能。于是本书的矛盾冲突更多地就体现为“参差的对照”而不是“强烈的对照”。问题于是产生:“参差的对照”与“强烈的对照”,哪一个是更好的对照?
张爱玲说:“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是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 [5]36《染坊》的作者显然和张爱玲英雄所见略同,她们看来都不喜欢大砍大杀式的绝对的冲突,而更喜欢小打小闹式的相对的冲突。于是这一矛盾冲突的相对性,就表现为本书中大量的矛盾偏移、矛盾搁置与矛盾弱化。矛盾的偏移,表现为腐败者不是本书的主要人物而是次要人物;矛盾的搁置,表现为一些屡劝不改的腐败者,至小说结束也并没有东窗事发。矛盾的弱化,表现为对那些已经发生的矛盾,作者并没有让它继续激化。正由于小说中情节的基本淡化与人物总体上的顺风顺水,有人认为《染坊》是一部散文化的小说:“全书犹如一篇凝重而优美的散文,形散而神不散。” [6]3
五
小说不是政治,也不是新闻,而终归是一种叙事的艺术。作为艺术的小说,其主题思想与人物形象乃至于情节设计,最终要落实到小说的细节描写与小说的叙事语言。
《染坊》有很多让人过目不忘的细节描写,如邓月的孩子出生后,作者写道:“(孩子)从娘肚子里一出来就睁着眼睛看房梁”。只一个动作,就栩栩如生。小说描写,往往也会遇到类似的情节,如《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与李逹打虎,就是描写对象的“撞车”。重复当然不好,于是就有两种选择:要么避免重复,不去面对同样的对象,要么直面重复,同中求异地描写出不同的情景。《染坊》也曾多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比如,当康健和李圣达夫妇渐渐地有了一官半职之后,当他们渐渐地操控到一定的权力之后,腐败也就找上了门来。于是,邓月劝夫、刘音笛劝夫、刘京华劝夫的情节次第出现。同是劝夫,却如何能写得不同,这就是作者面临的一个艺术挑战。作者才情富赡地处理了这一点:邓月劝夫,是邓月从母亲那儿看到了贪的可恶;刘音笛劝夫,是因为刘音笛本来就出身平民,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刘京华劝夫,是由于她的胆子小怕出事。如果我们顺着一个“劝”字看过去,则邓月劝母、康健劝岳父岳母、其实也都雷同于一个“劝”字。甚至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一“劝”而立骨,堪为当今一部“劝世良言”。再如就私下收受贿赂一事,康健的讯问保姆,李圣达的讯问司机,也是无独有偶,和而不同。最精彩的是本书对广东李氏家族开会场面的描写。这无疑是一种解构性的开会,因为它和中国人习惯而已知的那种开会不同。但这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开会——如何把会开得经济又有效,实用却不走形式,他们的会议还真是一种启发。总之,在进行这些描写的时候,作者不惧重复,敢于犯言,写出了自己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收取了碰撞生辉的艺术效果,堪称领会了小说描写之要义。
《染坊》无疑是作者一生“沉浸于创造和劳动” [7]7而在自己的“烈士暮年”,以一颗不已的壮心对大众关注的一个热门的政治性话题一次勇敢的文学介入。她的学生马星慧写诗称赞自己的老师:“佳编迭出真堪敬,最敬莲心不染尘”。作者确乎是一颗莲心,但这颗莲心却并没有“自高洁”。这位良知未泯、痛恨腐败、想有所作为却又菩萨心肠的柔弱女子,虽然缺乏痛下杀手残酷地面对残酷生活的果敢与严厉,虽然她的天生丽质似乎更适合于写作散文与诗歌,但是她却毅然而然地拿起了长篇小说这一并非顺手的重型武器而与时世的丑陋对抗,像鲁迅《纪念刘和珍君》所讲述的那个奇女子,她一定觉得最重要的是表现出自己挺身而出拍案一怒的姿态,而不是这样的姿态最终会有什么效果。因此,她终归是神勇的,而不是力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