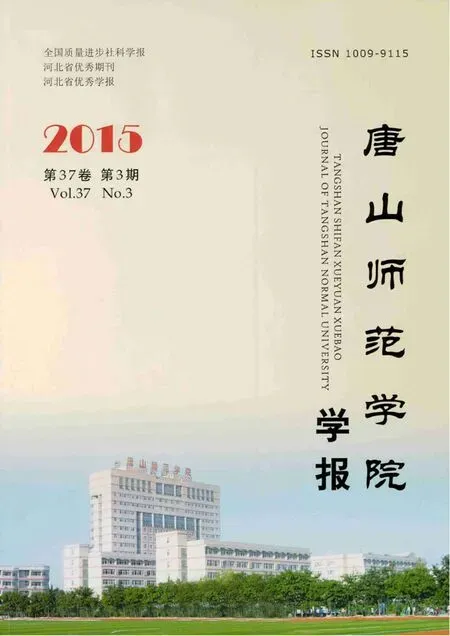古汉语三种“以为”结构及相关问题研究
程文文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 400715)
古汉语三种“以为”结构及相关问题研究
程文文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重庆400715)
古汉语中有三种“以为”结构:“A以为B”、“以为B”和“以A为B”。其中“A以为B”可以变换为“A以C为B”和“以A为B”;“以为B”可变换为“以之为B”;“以A为B”可表行为活动和意念活动,“以为AB”是由表意念活动的“以A为B”结构变换而来,表行为活动的“以A为B”结构已经语法化且沿用至今。
A以为B;以为B;以A为B;等值图式
一、引言
《马氏文通》首次阐述“以为”的语法作用:“‘以为’二字有两解,一作谓词者,则‘以为’二字必连用;一作以此为彼者,则‘以为’二字可拆用。”[1,p105]古汉语中“以为”有三种形式:“A以为B”“以为B”“以A 为B”。以上三种形式的“以为”有多种变换结构。“A以为B”有两种变换结构:“A以C为B”和“以A为B”;“以为B”可以变换成“以之为B”;“以A为B”结构可以表示行为活动和意念活动,语义相通使得表示意念活动的“以A为B”结构可以变换成“以为AB”,最终“以为AB”结构替代了“以A为B”,“以为”作为复合词表示“认为”之意沿用至今。表示行为活动的“以A为B”结构语义具有自足性,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书面语中。
二、“以为”结构
(一)A以为B
古汉语中“A以为B”结构的“以为”为两个词,“以”为介词,所以,这种结构在理解的时候有以下两种情况:
1. A以C为B
“A以为B”结构中没有宾语前置现象,在理解的时候通常要将省略的论元补充进来,语义才完整,所以“A以为B”可变换为“A以C为B”。“A以为B”一般处于后面分句中,前面分句论述的是“以”和“为”之间省略的成分“C”。如:
(1)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诗经·鹑之奔奔》)
(2)夫颛顼,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论语·季氏》)
(3)[武]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汉书·苏武传》)
(4)蔺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例(1)“我以为君”即“我以‘人’为君”。例(2)“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即“昔者先王以颛顼为东盟主”。例(3)“匈奴以为神”即“匈奴以[武]为神”。例(4)“赵王以为贤大夫”即“赵王以蔺相如为贤大夫”。上面几例均为典型的“A以为 B”,我们在理解时将其变换成“A以C为B”,因为“以”和“为”均为及物动词,后面添上论元,才能保持语义的完整性。所以,这种“A以为B”结构一般处在一句话的后半部分,前面的部分是对“C”的介绍,为了避免上下文重复,所以在说“A以为B”时将上文论述的“C”成分便省略不谈,但是在理解的时候要将“C”补充进来才能给人传递准确完整的信息。
2. 以A为B
“A以为B”结构中,“以”的宾语“A”前置,所以还原之后的格式为“以A为B”。“A以为B”常常是以单句的形式出现,因为这个结构本身传递的就是完整的语义,基本不需要其它信息,即使“A以为B”在文中以分句的形式出现,由于其自身语义具有自足性,所以,“A以为B”格式可以将结构还原为“以A为B”。如:
(5)维是褊心,是以为刺。(《诗经·魏风·葛屡》)
(6)秋以为期。(《诗经·卫风·氓》)
(7)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
(8)仁以为己任,不亦乐乎?(《论语·泰伯》)
崔棠华先生认为这种“以A为B”结构“以”为介词,“为”是动词,由于“A”宾语前置导致介词“以”和动词“为”衔接在一起[2,p70]。例(5)“是以为刺”可以变换成“以是为刺”,“是”指代上文中的成分,在这里还原为“以”的宾语。例(6)“秋以为期”可以转化成“以秋为期”。例(7)“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即“楚国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例(8)“仁以为己任”可以还原为“以仁为己任”。这四个例子的转换情况是一致的。这种情况和上面论述的“A以为B”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中“A以为B”常是单独的一个句子,前面没有分句,即使有分句,分句中主语或宾语与“A”的关系一般为指称关系。为了避免重复,“A”一般以代词的身份出现,指代前一分句中的成分,“A以为 B”具有语义自足性,所以“以”的宾语可以还原,因此可以转化为“以A为B”的格式。
在“A以为B”结构中,还原后的语序是“A以C 为B”还是“以A为B”,可以从“A以为B”结构的句法位置来判断:若“A以为B”处于后一分句中,且“A”为名词,前面分句介绍的成分为“C”那么,“A以为B”便是“A以C为B”的省略形式;如果“A以为B”是一个单独的句子,或者“A以为B”处在后一分句中,“A”为代词,前面分句必定是对“A”的介绍,这种“以A为B”句式的正常语序便是“以A为B”。所以在还原“A以为B”结构时,句法位置是关键。
(二)以为B
在“以为 B”结构中,“以”和“为”均为动词,所以,“以为AB”结构本身传递的信息不完整,这个结构不具有语义自足性,所以在理解的时候需要根据上下文将动词“以”和“为”的论元补充出来语义才完整。我们将这个论元用代词“之”替换。因此,“以为 B”还原之后的格式为“以之为B”。如:
(9)二国治戎,臣不才,不胜其任,以为俘馘。
(《左传·成公二年》)
(10)公子荆之母嬖,将以为夫人。(《左传·哀公二十四年》)
(11)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例(9)“以为俘馘”可以还原为“以之为俘馘”,“之”指代上文的“臣”。例(10)“将以为夫人”是“将以之为夫人”的省略,“之”指代上文的“荆之母嬖”。例(11)“卒以为将”是指“卒以之为将”,“之”指代“孙子”。在结构“以为B”中,“以为”通常位于后面的分句中且前面通常没有主语,“以”和“为”之间通常省略宾语“之”,“之”代指上文出现的成分,因为上文已经出现,为了避免语义重复,“以”和“为”之间的成分“之”可以省略,但是在理解的时候,只有将省略的“之”补充进来才能完整的知道“以为B”传递的信息。
(三)以A为B
古汉语中,“以A为B”结构有表行为活动和意念活动两种用法:
1. 行为活动
表示行为活动的“以A为B”结构,“A”和“B”一般都是名词或名词短语,“以A为B”是兼语结构,“A”是“以”的宾语,“为”的主语。“A为B”是主谓短语做动词“以”的宾语。如:
(12)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战国策·赵策》)
(13)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14)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墨子·公输》)
例(12)“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中“君”是动词“以”宾语,动词“为”的主语,即起初的时候,我把您看做天下的贤公子。例(13)“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贾生”是“以”的宾语同时也充当“为”的主语。例(14)“以牒为械”,“牒”是“以”的宾语“为”的主语。表示行为活动的“以 A为B”结构语义上具有自足性,这个结构本身就可以传达完整的语义信息,与前面的“以为 B”和“A以为 B”结构相比更为完善。“以A为B”没有宾语前置现象,且动词“以”和“为”后面都有论元,无需根据上下文补充。这也是“以A为B”结构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书面语中的原因之一。
表示行为活动的“以A为B”结构不能转换成“以为AB”。“以A为B”结构具有语义自足性,没有必要转换成结构更为复杂的“以为AB”结构,这违反格赖茨先生提出的“方式准则”[3,p127],即说话时要简练。且“AB”是两个名词成分的简单罗列没有太大意义,不符合语义逻辑。行为活动的“以A为B”结构可以用等值图式来解释。等值图式是指人们把两个性质本来不同的物体(包括抽象的物体)加以联系并在心理上做出等值判断的过程[4,p30]。“君”和“天下之贤公子”,“贾生”和“长沙王太傅”,“牒”和“械”是人们在心目将这两种不同的人、事做出的等值判断。
2. 意念活动
表示意念活动的“以A为B”结构,“以”通常译为“认为”,表示主体的主观看法。“以A为B”中的“A”常常后移即形成“以为 AB”结构,由于“A”的移位使得动词“以”和“为”的关系更为紧密,最终形成复合词“以为”,亦可译成“认为”,表达主观看法。这是复合词“以为”形成的主要途径。如:
(15)天子三公既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厉害之辨,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划分万国,立诸侯国君。(《墨子·尚同上》)
(16)上以式为奇,拜为缑氏令试之,缑氏便之。迁为成皋令,将漕最。(《史记·平淮书》)
这两例中“A”可以后移,形成“以为AB”结构。“以天下为博大”即“以为天下博大”。“上以式为奇”即“上式以为奇”。而且古汉语中也存在这种“以为AB”式与之对应。如:
(17)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墨子·尚同中》)
(18)上以为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史记·平淮书》)
如何将“A以为B”“以为B”“以为AB”中“以为”区分开?
前面论述了“A以为B”有两种变换结构:“A以C 为B”和“以A为B”。“以为B”可以变换成“以之为B”;“以A为B”结构可以表示行为活动和意念活动,表示意念活动的“以 A为 B”结构可以变换成“以为AB”。以上三种“以为”的区别如下:
首先,语料的断代上,“以”的“以为”之意为春秋时产生。春秋以前,不存在意念活动用法的“以A为B”结构,“以为”仅仅是表面连用,实际上是两个词。
其次,语义上,根据格式的自足性判断,即判断格式表达的是否为一个完整的意思。行为活动用法的“以A为B”结构主要表达“(谁)使谁怎么样”,意念活动用法的完整的语义应为“(谁)认为谁怎么样或是什么”。所以当看到“A以为B”、“以为B”和“以为AB”结构时,根据上下文判断,“以”和“为”前后是否缺少论元,能否将论元补充完整。所以,根据论元的缺失可以判定“以”和“为”的意思以及在句子中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如:[武]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汉书·苏武传》)“匈奴以为神”在理解的时候我们将这个句子还原为“匈奴认为谁是神或匈奴以谁为神”。这样我们可以判定这句话中“以为”应该为两个词,即“匈奴以武为神”。所以通过判断“论元”的缺失和根据上下文补充“论元”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最后,结构上,“A以为 B”结构一般处于后面分句的位置,前面分句一般是对“C”的介绍,为了避免语义重复,“A以为B”实际上是“A以C为B”的省略。如果“A以为B”以一个单独句子的形式出现,前面没有分句,即使有分句,和“A”的关系一般为指代关系,为了避免重复,“A”一般以代词的身份出现,指代上面分句中的成分,这样“以A为B”结构可以转换成“以A为B”的格式。
三、复合词“以为”的成因
关于复合词“以为”的形成过程,前辈们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谭世勋先生认为:“‘以’和‘为’均是动词,‘以A为B’是兼语结构。‘以A为B’结构有表行为活动(把A怎么样)和表意念活动(觉得或认为 A怎么样)之分,只有表行为活动的‘以A为B’才可以变换成‘以为AB’格式,表行为活动的不能这样变换。‘以为’作为一个动词是由两个动词‘以’和‘为’凝固而成的。”[5,p90]何一寰先生认为,有的是把‘以为’作一个词用的,意思和现代的‘以为’相同,作‘认为’讲,但这种用法在古籍中较少,是比较后起的用法[6,p27]。本文认为语义因素是复合词“以为”的关键。
表示意念活动的“以A为B”结构,有学者认为“以”是介词,“为”是动词。本文不赞同“以”为介词的观点,“以”当为动词。举例而言,始吾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战国策·赵策》)假设“以”为动词,“君”是“以”的宾语同时也充当“为”的主语,“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是兼语短语。例句可翻译成:我把君看做天下的贤公子,“贤公子”指的是“君”。如果“以”为介词,则“以君”为介宾短语在句中作状语,句子的主干便成了“始吾为天下之贤公子也”,“贤公子”指“吾”,与原文的意思大相径庭。所以“以A为B”结构中“以”和“为”均为动词,“以A为B”是兼语结构。这一点是复合词“以为”形成的前提。
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意念活动用法的“以A为B”可以形成复合词“以为”?
《说文解字》《辞源》第一个义项都将“以”释为“动词,用”,说明“以”的本义为动词“用”。《汉语大字典·人部·以》(第105页):“②使;令。书证为《尚书·君奭》:‘我不以后人迷。’④认为;以为。清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以,犹谓也。’书证《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所以可以得出,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以”由本义“用”先引申出“使”义,再进一步引申出“以为”、“认为”之意,最终虚化为介词。表行为活动的“以A为B”结构,“以”的意思为“使”。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语料的时代断定“以A为B”是否为意念结构。具体而言,凡是春秋时期之前的语料,若出现“以A为B”的句式,这种结构应表行为活动,“A”不可以后移,即使可以后移,“以”和“为”是单独的两个词,不是复合词“以为”。《汉语大词典·人部》(卷一第1 092页):“以为”:“①认为”书证为《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及齐,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于桑下。”《汉语大词典》书证一般为初始用例,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复合词“以为”形成的时间应在春秋时期。这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以为”在春秋以前是两个词。这个推论早于姚振武先生“复合词‘以为’直到《墨子》时才产生”的观点。
春秋时期,“以”具有了表示人主观看法的“认为”之意。如:吾以.女为.死矣。(《论语·先进》)在这个例子中“以”可译为“以为,认为”的意思,表示一种行为活动,主语是对“以”后面成分的一种认定,这种认定或许事实果真如此,或与事实不相符合,但“以”的“认为,以为”之义没有变,这种意念活动的“以 A 为B”结构主要表达主语的观点,至于事实是否如此,与这个结构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以”的主要意思为“认为”,“A”移位后没有改变“以”的“认为”之义,且动词“以”和“为”连用表示的还是“以为、认为”之义,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人们便接受来了这中连用的现象,最终形成了复合词“以为”。因此,由于“以”和复合词“以为”均有“认为”的意思,所以,意念活动用法的“以A为B”和“以为AB”具备了语义上可相互转化的条件。语义因素是复合词“以为”形成的关键。如:
(19)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不足忧,乃渡河北击之。(《史记·高祖本纪》)
(20)臣以为其人勇士。(《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上面论述到“以”做“以为”讲时,“以A为B”中“A”可以后移变成“以为AB”结构。“则以为楚地不足忧”中“以”表达人主观看法可译为“认为”之义,可以转换为“则以楚地为不足忧”。“臣以为其人勇士”即“臣以其人为勇士”。“以为”在表意念活动用法的“以A为B”和“以为AB”中,分别作两个词和一个词理解。
所以,意念活动的“以A为B”结构中“A”可以后移形成“以为AB”结构,这两种结构“以”和“以为”表示人的主观看法。“以A为B”为兼语结构,“以”和“以为”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
四、框式结构“以A为B”的传承和发展
据谭世勋先生考察,“以A为B”这种结构甲骨文、金文中均没有出现[2,p92]。《左传》《论语》《孟子》等作品中很常见,所以他推测出春秋初期是“以A为B”结构的萌芽期。先秦时期“以A为B”占优势,到了汉代“以为AB”逐渐取代“以A为B”式而成为主要形式。孙德金先认为:“‘以A为B’式句法结构在现代书面汉语中是一种高系统融合度的文言语法构造,很多情况下没有可以替代的表达式,但语法学界对这一时期的‘以A为B’句关注不多。”[7,p3]刘景农先生提出:“这‘以……为……’式在文言里也习见,可是现代汉语里同样没有和它相当的。”[8,p22]吕叔湘先生认为:“有一类‘以……为……’等于‘把……作为……’或‘认为……是……’”[9,p613]通过前人的研究和统计可以看出“以A 为 B”格式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这一格式为什么能够传承至今?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多。笔者认为,“以A为B”结构具有自足性。
本文界定“以A为B”为框式结构。框式结构(frame construction)是由邵敬敏先生正式提出的,“典型的框式结构,指前后有两个不连贯的词语相互照应,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特定的语用功能,如果去除其中一个(主要是后面一个),该结构便会散架;使用起来,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适的词语就可以了,这比起临时组合的短语结构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就好比现代化的楼房建造,常常采用的框式结构一样,简便、经济、实用、安全”[10,p219]。同时提出了鉴定框式结构的三个标准:一是框式结构由不变成分和可变成分组成,二是具有整体性的特殊语法意义,三是与语境结合紧密,具有特定的语法功能。本文将“以A为B”结构定义为框架结构,此结构符合框架结构的三个必要条件。在“以A为B”结构中动词“以”和“为”是结构中的不变成分,“A”和“B”是可变成分;“以A为B”结构具有整体性的语法意义,这种结构和“把”字句、“被”字句等一样均为“有标识性词的句式”,是一个“完形结构”即整体意义大于部分之和。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中的一个句式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心理上的“完形”,即一个整体结构。语言符号是音义的结合体,语言形式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一种语言形式或语言结构只有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才会具有生命力,才会传承下来。孙德金认为:‘以A为B’结构主要表达主体对于事件的‘认定’意义[5]。罗主宾先生认为,“以 A 为B”结构的整体意义在于“在A形成的集体中,由于某种需要选择可使 A作为 B”[11,p75]。本文认为“以 A 为B”具有客观选择性,使人们将两种客观存在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并且做出等值性的判断。此外,“以A为B”具有强烈的书面语色彩,据罗主宾先生统计,“以A 为 B”格式主要用在公文语体和科技语体中,《毛泽东选集》中“以A为B”句式出现高达400例,近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A为B”句式出现125例。这种结构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口语中用例较少。总之,“以A为B”结构完全具有邵敬敏先生的“框架结构”三要素,因此,“以A为B”是典型的框架结构。因此,“以A为B”结构沿用到现代汉语书面语中,这种结构已经语法化了。如:
(21)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只有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驱散"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才能狠狠打击一小撮进行破坏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夺取更大的胜利。《加强革命团结打击阶级敌人》
(22)关键在于一切以党的事业为出发点。《以己之退促党的事业之进》
(23)如此,则遭遇着以法国资本为背景的帝俄南下政策,由摩擦而冲突。《门户开放宣言之检讨与评价》
本文粗疏考察了古汉语中三种“以为”结构的变换方式和发展轨迹。古汉语中存在三种形式的“以为”:“A以为B”“以为B”“以A为B”。复合词“以为”是由意动用法的“以A为B”结构变换而来,表行为的“以A为B”结构由于其结构和语义的稳定性出现了语法化倾向,所以框式结构“以A为B”结构一直沿用到现代汉语书面语中。
[1] 马建中.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05.
[2] 崔棠华.古汉语中的“以……为……”结构[J].辽宁师范学院学报,1981(3):67-70.
[3]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A]. Cole P, J L Morgan.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127.
[4] 秦玮远,资建民.论奎因对塔尔斯基等值图式 T的误解[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9(6):30-33.
[5] 谭世勋.试论“以A为B”结构的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4):90-96.
[6] 何一寰.“以为”在古籍中的用法[J].中国语文,1966(1):25-29.
[7] 孙德金.现代书面汉语中的“以 a为 b”式意念活动结构[J].汉语学习,2010(3):3-10.
[8] 刘景农.汉语文言语法[M].北京:中华书局,1994:22.
[9]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213.
[10] 邵敬敏.汉语框式结构说略[J].中国语文,2011(3):218-227.
[11] 罗主宾.现代汉语“以A为B”凝固结构语义的认知分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74-80.
(责任编辑、校对:郭万青)
Three Structures of “Yi(以)Wei(为)” in Ancient Chinese and the Related Studies
CHENG Wen-wen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ocument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There are three styles “Yi(以) Wei (为)”in Ancient Chinese:“A Yi(以) Wei(为) B”, “Yi Wei(以为) AB”and “Yi(以) A Wei(为) B”. “A Yi(以) Wei(为) B” could be translated into “A Yi(以) C Wei(为) B”and “Yi (以) A Wei (为) B”. “Yi(以) Wei(为) B”could be translated into “Yi(以) Zhi(之) Wei(为) B”. “Yi(以) A Wei(为) B” includes two meanings: behaviors and mental activities. “Yi Wei(以为) AB” came from “Yi(以) A Wei(为) B” which are mental activities. The behavior of “Yi(以) A Wei(为) B” has grammaticalized and are still used today.
A Yi(以) Wei(为) B; Yi Wei(以为) B; Yi (以) A Wei(为) B; equivalence schema
H141
A
1009-9115(2015)03-0021-05
10.3969/j.issn.1009-9115.2015.03.006
2014-09-19
程文文(1986-),女,山东泰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