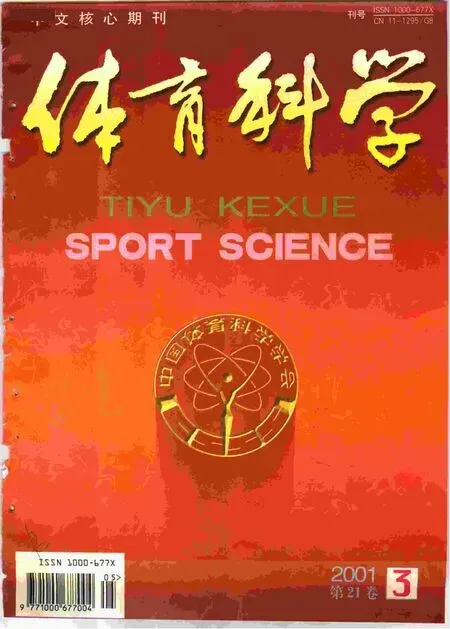归属、规模、规制: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认识
——一种学科方向探究
董德龙,刘文明,SEAMUS Kelly
归属、规模、规制: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认识
——一种学科方向探究
董德龙1,刘文明2,SEAMUS Kelly3
当前,中国体育学科的话语地位及学科符号正在不断规范和前行,其中,围绕“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学科规制”等问题的争论较为集中,理由在于,它们导致了中国体育学科体系分类不明、学位管理的混乱、学问与学说的缺失等问题的出现。然而,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及学科规制更应该是一种学科的外在标准,中国的体育学科在规模和规制上已基本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问题关键在于学科的“内生”发展。研究认为,中国体育学科的基本方向应在学科内容上从学科分类走向问题关注,研究范式由描述研究走向解释研究,知识建构由联姻嫁接走向内生创新,以更快的实现由“历时态”发展走向“共时态”压缩的历史进程。
体育;学科分类;学科归属;学科规模
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体育学科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以来,体育学科的地位得到不断提升,尤其是1996年,体育学科被列为一级学科,更是成为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期间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在经历了学科体系构建、问题论争与学科解释力等发展的历时态演变进程后,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体育学科已经发挥了自身应有的学科价值,在诸学科群中已基本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体系。 当然,与世界许多国家的体育学科相比,中国体育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学科发展上也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如学科归属或学科体系问题。许多研究指出,由于学科归属或体系的分类不明,导致了中国体育学科自身范围的模糊以及学科根基的薄弱,并由此衍生出了学位、学术管理混乱、国家立项或获奖的局限以及学问、学术的缺失[5,21,22]。中国体育学科发展至今,确实暴露出一些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被约束的状态,受外来体育思想的影响也较大,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如何更好地实现从约束走向引领,是每一位体育学人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学科归属的不明、学科规模的有限及学科规制的松散3个代表性论争尤为激烈。研究者对此存有一些疑惑或感悟,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及学科规制更加倾向于学科的外在标准,而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可能对内在标准的需求更加强烈,即学科解释力的强大。当然,不应让诸多蕴含思想的蓓蕾夭折,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更应从这些思想蓓蕾中理性地做出选择。为此,研究者对体育学科归属不明、规模有限及规制松散等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论证,并探究了体育学科的基本发展方向或态度,即学科内容由体系构建走向问题关注,研究范式由描述研究走向解释研究,知识建构由联姻嫁接走向内生创新。
1 学科归属:是否不明?
2011年3月,在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颁布的最新《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版)》中,艺术学成为一门新设的学科门类而独立出来(体育学科没有变化),使得实行30年之久的传统学科门类发生了变化[12],这也使得体育学人对这一问题的论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最为典型的主张是认为学科归属的不明造成了我国体育学科体系分类、学位管理及学术管理一些混乱现象的发生。例如,国家各类课题立项中“体育学”指向的不一,学术管理或者说体育科研管理的混乱,学位管理的规范不足等,对于这些理解似乎存在逻辑上的偏差。研究者认为,学科归属并不是导致以上问题的关键,或者说,学科归属至少在当下不应成为体育学科发展种种问题的源头。
对于学科归属不明的理由之一是对体育学4个2级学科的质疑。不少研究指出,体育学下设的4个2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运动人体科学、民族传统体育)并没有按照学科属性来划分,它们之间存在极大的内容重叠与交叉现象,学科范围模糊、学科性质难以定位等问题,以至于“体育界出现了能在4个2级学科发表学术论文的人”[11,13,23]。然而,研究者认为它们之间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即使体育学科不划分2级学科,体育学人中同样存在这种一人多能的现象,可以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表学术成果,但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泛家”,至少难以达到“大家”风范。这只能表明,一是这类学人的学术质量往往会受到限制,因为研究不够专一;二是表明目前体育学人的研究质量整体还不够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三是学科内部的知识交叉现象明显,具有共通性。如此看来,似乎也只有第3点与学科分类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因果关系,更加倾向于学科发展的一种历时态表现。因此,将这种现象归于学科归属不明或分类的混乱是欠妥的,只有追求学术造诣,提升学术水平,形成专业领域,才能扼制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才能提高学术刊物的示范作用,学科之间的边界也才会越来越清晰和明确。
事实上,要做到严格的体育学科分类很难,尤其是每一个学科的学理性研究很可能会涉及多学科的知识,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不同学科知识的滋养,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彼此的知识联系。因此,学科之间的纠缠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只是有的学科这种纠缠少一些,有的学科会多一些罢了!完全消除学科之间的交叉是不现实的,也没有这种必要,更何况是在学科内部(二级学科)之间实现无交叉了。自20世纪80年代,有不少学人就学科分类进行了梳理(表1),但无论怎样,学科之间的交叉现象依然是存在的,如杨文轩(2009)提出的新的学科分类似乎较为适宜,身体教育、健身休闲、运动竞技学作为新的体育学科分类标准[21],虽然这种分法的正确与否还难以确定,但也表现出对现有的体育学科进行全面归类和囊括的难度。

表1 中国体育学科分类研究示例一览表Table1 Classification List of Sports Discipline in China
体育学科分类标准急需调整的问题,研究者持赞同态度。在国家标准GB/T13745-92《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体育科学被明示的下辖学科有13个[890.10 体育史,890.15体育理论,890.20运动生物力学(包括运动解剖学等)、890.25运动生理学、890.30运动心理学、890.35运动生物化学、890.40体育保健学、890.45运动训练学、890.50体育教育学、890.55武术理论与方法、890.60体育管理学、890.65体育经济学、890.99体育科学其他学科[24]],其后也出现了新版的国家标准(GB/T13745-09[25]),但基本没有改变以上类型的划分。体育学科发展至今,学科群已逐渐多元化和成熟化,一些体育2级学科甚至已相对成熟(如体育社会学),一些体育2级学科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交叉性或种属关系错乱现象,或者在提法上已很少见(如体育理论)。为此,体育学科的二级学科分类需要做出新时期的调整。
国家各级各类课题(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申报中“体育学”术语的模糊,是关乎体育学科归属不明的又一理由。在这些课题申报中存在“体育学”这一项目类别,但主要获批项目为“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学科领域获批项目很少,由此得出是将“体育学”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划了等号。对申报课题类型加以限制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这只是侧重点不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偏重人文社会学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偏重于自然科学类研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体育科学具有多学科属性的特点,无论是研究何种方向,只要申报课题的性质属于其中的一种,选择合适的部门申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课题申报或批准的类别差异,重要的是如何开拓更多的申报渠道推动体育学科的整体发展,就如同2013年教育部的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立项和评奖中首次出现“体育学科”类别那样才更有意义。
目前,体育学术期刊的示范性弱化,也是体育学科归属不明的问题之一,原因是,中国体育学术类期刊时而追寻人文社会学期刊的评比体系,时而又转至自然科学期刊评价体系。然而,笔者认为这也有失公允,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世界优秀期刊同样也是刊发多种学科的论文(如Nature和Science),甚至这些刊物也有体育类论文的发表,或者说,虽然一本期刊只集中一方面或几方面的论文,但仍然是站在一个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下发表论文,体育学科同样也表现出了多重性。因此,将体育类期刊发表论文性质的偏好同体育学科归属的不明冠以因果关系有些牵强。体育学术期刊示范性增强更加依赖于体育学人研究质量的提升和学术态度的规范,而这种提升和规范靠学科归属或分类来实现似乎不太现实。
对于学科或是学术刊物的发展,重要的并不在于这种学科关系或归属,或是学科分类的命名如何,而是在于学科的自身解释力,只要某一学科的解释力得到公认,有社会需求,其学科地位自然就得到认可,学术期刊自身的质量也将得到提升,其刊物的学术指向性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从这种逻辑主线来看,更加关注的应该是学人的学术态度以及体育类学术刊物的真切引领,体育学人根据自身的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爱好选择合适的学术命题,通过提升学术命题的研究质量来促成学术水平的专项化发展,这才是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
体育学研究生学位管理的混乱是学科归属不明的又一表现。在当下中国体育学研究生学位管理中,研究生撰写论文的非方向性,学位论文评审的随意性(相当一部分院校未能按照4个2级学科进行评审)普遍存在。然而,将这些现象归于学科归属的不明则并不成立,一是当前大多数院校仅是从1级学科(体育学)作出了规定,并没有从所属2级学科进行考虑(当然,越来越多的学校也开始从2级学科的角度作出规定),加之招生量的扩大导致了管理和要求上的松懈;二是许多专业的研究生受实验条件的限制,难以完成本专业的学位论文撰写,如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的研究生,许多研究需要具备实验条件或是以高水平运动员为研究对象,而这对于很大一部分学校的研究生培养是有难度的,更何况对于绝大多数的运动人体科学领域的研究生,就更是如此了。当然,有难度也并不是不研究的理由,但相对于人文社会学科可能就简单多了(事实上,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难度也非常大)。笔者认为,学术质量的控制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学术质量本应成为研究生或是体育学人的生命线,应成为学科发展之本。然而,对学术质量的忽视,造成了种种现象的发生。事实上,无论学科专业如何划分,只有学术质量的提升,才能最终促成专业化的形成,无需一味争论学科的分类和归属,分类和归属更应体现的是一种学科的使然状态,至少缺乏学理性的研究内容而确立学科的归属与分类意义不大。
同时,从国际上许多发达国家的体育学科发展来看[26,30],也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学科门类特点,如以美国为代表,其学科管理基本呈现松散性特点,全国学科和专业目录以The 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①(CIP,教学计划分类)来指导,在16个学科大类中(农学、建筑学、文理学科基础、工商管理、传播、教育、工程学、健康科学、法学、图书馆、军事与预防学、交叉学科、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神学与宗教、职业与技术培训[23,29]),体育学并未单列一个大类,而是分散到不同的学科门类中发展的(如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再如,英国将体育相关学科放到休闲、酒店管理和旅游学科当中[6]。当然,不少学者曾以德国为例,强调德国的运动训练、体育管理、体育教育、体育市场等学科均居于世界前沿水平[2,4](龚建林,2007),这与德国将体育学列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有直接的关系。 诚然, 这种学科的门类划分有助于体育学科的发展,而更为重要的是------------
① CIP(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由美国教育部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发布,自1980年 首次发布后,先后在1985、1990、2000年连续发布,目前最新版本为2010年发布的,基本可以反映美国高校学科体系的基本情况。
德国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同。事实上,德国的许多综合性高校体育专业大部分仍然设置在人文学院(系)、艺术与人文学院(系)、行为与文化研究学院(系)、教育研究学院(系)等院校当中,也很少设置单独的体育院系。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说学科归属不重要,或者准确的说,学科归属问题主要是学科门类的独立性问题。因为,体育学的综合性学科性质还是明确的,体育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自然会极大地提升发展速度,这可能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的追求。然而,更应该考虑的是体育学科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就如同艺术学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那样,学科自身的内在建设与时代发展的现实需求才是突破上位的关键因素。虽然,也有不少学者主张,体育学科已具备稳定的学科体系、专业设置和独立设置学科门类的条件和要求。然而,我们缺乏的可能就在于自身的内在建设。因此,学科归属是否明了并不是关键,一是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也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二是中国体育学科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特点,如果说在20世纪80~90年代是以引入为主,那么,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更应注重自身的学科建构,体现出自身的发展特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体育学科的引领发展。学科门类能否独立是体育学人共同的目标,然而,在理想与目标之间,更应注重对学科根基的发展,否则,可能会导致徒有虚表,而缺乏实在。
2 学科规模:是否有限?
有研究认为,体育学科专业数量和专业院校的增加并没有改变规模有限的格局,这一主张的理由主要有两点:1)在中国高校类型序列中,体育类院校属于整体规模偏小的一类,仅占全国高校的1.2%,与艺术类院校所占比例相比中(3.8%),也处于弱势地位;2)体育院校中,传统体育学科与新兴体育学科并存的局面没有改变。从这两点原因来看,并不能完全说明体育学科规模的不足,虽然从与各类高校开设专业数量的对比中发现(如艺术学),体育学科专业开设数量处于弱势,但近些年体育相关本科专业是逐步增加的。2011年,全国已有289所高等院校开设体育教育本科专业。2013年,全国运动训练专业、武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分别增至84所和45所[15],且数量的多少不是衡量学科发展规模的唯一指标。另外,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并存的问题也并不矛盾,传统体育学科只要社会仍然需要,就应该继续存在,新兴学科也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而诞生的,两者的并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更可能是一种历时态的表现,是社会对学科的一种需要,不一定是学科规模导致的。
体育学科难以实现学科之间的交融和互动也往往被认为是体育学科规模有限的又一理由。然而,这种学科交融与互动的不足更倾向于学科规模发展之初的一种表征,至少在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领域,这种交融与互动还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学科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并不是某一门学科发展的“专利”,这一点从20世纪80年代的学科大发展中就可窥见一斑,体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体育学科知识也正是在与其他学科的“交融”中发展的,如典型的运动人体科学、基础理论。随后,逐渐形成的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同样与母学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许多体育学科正是在与其他学科的联姻与嫁接中逐渐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只是这种交流与互动的深度还不够紧密,而这种深度的达成更需要学科内部的知识建构。因此,体育学科规模有限导致难以实现当下学科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存在逻辑矛盾,体育学科规模正是在学科的交融与互动中获得发展和壮大的,也由此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兴2级学科。
学科规模的有限自然会影响学科的发展,然而,一味地追求学科规模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至少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更应该追求内在的学术质量。一门学科的规模如何衡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体育学科规模是否有限还很难做出确切的结论。以专业体育院校为例,中国的体育专业院校多达14所,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占有多数,世界许多国家要么没有专业体育院校,要么仅有几所。因此,从数量上来看,中国已占多数。研究者认为,这种数量的对比意义不大,至少就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发展而言意义不大。世界上许多国家不但没有专业体育院校,甚至在各种类型的高校中也没有设置独立的体育学院,而是把体育学科放在了一些其他部门[如公共健康学院(爱尔兰)、公园娱乐休闲健身学(美国)等],然而,它们的发展依然表现出了世界前沿水平。因此,这种以学科建构为历史特点的学科规模发展时期已经过去,至少目前的重心不应该在此。
3 学科规制:是否松散?
规制松散是体育学科发展进程中的另一个论争主题,其理由在于规制的松散导致了体育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混乱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4点:1)体育学名称。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学科与国家学位管理体系中,“体育学”含义不同(广义与狭义之说[7,22]);以及在各类评奖中,体育类科研成果表现为参杂性;2)体育类学术期刊。主要表现是学术刊物的命名多样化,发表的学术论文呈现出4个2级学科的特点;同时,它们在参与评奖中经常同时获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奖励,即两边靠的做法;3)研究生管理。体育教育训练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生论文撰写中,经常是体育人文社会学范畴的;4)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管理。体育院校对于数量众多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子学科只能顺应时势和特点,追求热点,炒作时髦概念等成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一种常态。
研究者认为,当前体育学科的发展恰恰与规制无关,或者说关系不大,表现在体育学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占有一定席位或明确地位、有独立的学术组织;在院校中开设体育课程;在人才培养体系中有自己的专业方向;有独立的体育学术期刊,这些外在的标准都已具备。问题出在学科的内在标准上,缺乏扎实、严谨的理论体系和科学依据,表现在没有自己特有的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原理、规律等组成的知识体系,至少缺乏学理性命题。因此,虽然体育学科规模是否有限还难以界定,但至少在体育学科规制上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面对体育学科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以上4种混乱现象,笔者认为,国家各类课题的立项或评奖中,“体育学”释义的不清与学科规制的局限关系不大,因为无论“体育学”作为1级学科还是2级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来对待,国家各类课题的立项均会有所侧重。如果一定要在这样的国家课题立项中明确“体育学”的具体释义,或是从体育2级学科来进行申报立项或评奖,那么,与其他诸多1级申报学科相比,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体育学科发展的局限和狭小,这种结果是体育学人最终都不想看到的。至于学术期刊的命名和获奖类型,与学科规制的关系也不大,学术期刊自身的命名本应秉承自身的特点,世界上各种优秀期刊也表现出自身的多元化命名特点,因其多元化命名而得出规制松散并不成立,相反,学科规制建设更应该促成学术刊物的多元化发展。最终究竟哪些期刊才能得到更高程度的认可,取决于这些刊物自身的学术质量了。体育院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管理,与体育学科规制的关系也并不紧密,一是体育院校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体育学科发展,二是体育院校的学科门类相对有限,也导致了体育院校在发展过程中规模的受限,其发展难度也非常大,相比之下,中国各类高校体育专业的发展情况正在突飞猛进,也更加具备学科发展的实力。因此,体育学科规制松散的理由并不充分,更不应成为问题的源头。
4 中国体育学科的基本方向:几种转变
4.1 学科内容:由学科分类走向问题关注
学科体系分类建设一直是体育学科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体育学学者就为此不断努力[16,17,19],并产生了激烈的论争,这种体系论争时至今日仍在延续。如鲁长芬(2009)指出,体育人文社会学和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学科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基础支撑学科,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内容需要重组,身体教育学、运动竞技学、健身休闲学将作为体育学科体系的主体部分得以发展[11]。易剑东(2014)指出,体育学科分类的混乱是导致体育学科诸多问题(科研立项、评奖、学位管理等)的外部掣肘因素[22]。由此可见,关于体育学科体系的论争仍未停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坏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一门学科的规范化、制度化离不开学科知识的交流与冲撞,甚至是激化。但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有所侧重,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体育学学科体系还在论争与借鉴的基础上发展的话,当代的中国体育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国体育学理论体系,如果此时的中国体育学仍以学科体系的归属、基本构成、结构要素等为论争的主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约束中国体育学的发展。因此,中国体育学理论体系在这个新的“十字路口”如何做出选择尤为重要。
问题关注被认为是当下中国体育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呼声,中国体育学是在理论引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体育实践而发展的,对体育实践的问题关注也未曾停止,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中是有所侧重的。中国体育学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系统化发展阶段后,也便进入了以理论体系构建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发展时期,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呈离散型状态,或者说缺乏系统化。进入21世纪,伴随着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加之中国体育事业的突飞猛进,双重的推动力使得体育学对实践问题的关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就使得问题关注为重心的时代的到来。
当然,这里强调的问题关注更应该考虑问题间的关系研究,也就是更加突出关系性或解释性研究的价值取向,这是对世界体育学历时态转型的一种共时态压缩。因为,中国体育学在学科内容上不能局限于单一问题的单一性解决,也不能一味追从国外体育学的发展思路和脉搏,在注重交流的同时,更应体现自我的超越。今天的中国体育学,从学科内容来看,以学科归属和体系构建为突出特点的时期已经弱化,问题关注和问题间关系的关注是必须面对的两种共时态表征,尤其是问题间关系的关注(强调学理性和解释性)对学科内容发展的重要性。当然,这里并不是对学科归属的忽视,只是想表达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需要在关系性研究或解释性研究上做出更多努力,避免停留在以学科体系归属(外在标准)为价值取向的漩涡当中论争不休。
4.2 研究范式:由描述研究走向解释研究
范式理论最早由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自该理论提出以来,学科范式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它主要指的是某一学科社会共同体,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所遵循的一定研究方式,具体可包括学科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知识体系及研究方法等[14],这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该理论强调某一学科的发展是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的过程。根据这一理论,体育学科也同样表现出范式的更替与嬗变特征,或者说,在描述研究、实证研究及解释研究方面应作出怎样的选择,这也是学科发展的一种历史宿命。
中国体育学学科由于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自创建之初就是以引入和借鉴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以学科体系构建为基本价值取向。虽然在这一进程中,也不乏中国体育实践问题的研究,但可以归结为是与实践形成两条路线来走的,一方面是着重于宏观体育理论的组建与探讨;另一方面是体育实践的独身前行,两条路线呈明显的割裂状态,在理论上体现出以描述性研究范式为主体,在实践上呈现的是经验总结为特点。时至今日,许多学者虽正在不断努力,但在体育理论上的跟进仍显不足,即问题的解释力不够,这也是长期以描述性研究为背景下造成的解释力的弱化。当然,导致学科解释力弱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发展历程上来看,中国体育学秉承了原民主德国、苏联的体育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突显了宏观体育理论体系的关注,而缺乏以欧、美实用为特点的体育学研究。从国际体育学科研究的发展态势来看[27,28],目前中国体育学理论研究中,体育学专题的实验性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解释性或学理性的实验研究更是不足,即使是运动人体科学领域,具有原创性的基础性研究也比较少见,绝大多数基础理论仍然是来自于母学科,而大量的都是回顾性的研究或是文献性的研究,在学科解释力上经常变得无奈和柔弱。由此可见,中国体育学必须面对从描述性研究向解释性研究的转变。因为,实践性研究并不是目的,而最终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践性研究是为了提升最终的解释力,而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达成,这也是避免治标不治本现象发生的基本尺度。
4.3 知识建构:由联姻嫁接走向内生创新
知识建构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进程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因为这势必影响到学科的独特符号及话语权的提升,由此也导致不同学科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10,17,20],体育学也不例外,甚至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笔者认为,无论这种争论的结果是什么,中国体育学基本呈现出两种知识建构态度,即“联姻嫁接”与内生创新,并且在这两种态度下已越来越呈现出自身的特色,越来越多的2级学科由此诞生,不论这些学科成立的合理与否,都足以看出中国体育学的发展规模及其学科的深化。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处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成为一种论争取向。不少学者正是在这种争论中论及体育学科的发展,并将其归结为一种学科约束。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种学科关系并不是关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体育学需要其他学科知识的不断滋养,毕竟体育学是一门综合应用性学科[5,19],具有鲜明的自然科学属性和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具有辐射多门学科的特点,关键是在这些关系中如何确立自身的内生机制,并由此确立更多的学术命题。如前所述,中国体育学学科在规制上已占领学科框架中的一席之地,即无论是在国家的学科分类体系中,还是学术组织及专业设置等方面,表现出了很好的外在标准和规制化发展态势,而缺乏的正是学科的内在标准,即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学术命题的不足。
这种争论之初,体育学的基本态度是采用“拿来主义”,这也是学科初建的表现,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完善,采用联姻嫁接的方式来获取知识是历史使然。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学科的内生创新成为一种新的主题,从而也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体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基本关系,有了自身的学科话语权及学科的独立符号。然而,这种学科话语权仍然显得有些脆弱,典型的表现是褪变为一种学科关系上的附庸性[1]。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华勒斯坦的一句话:“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规制化”[9]。事实上,规制化并不是体育学科的专利,任何学科的发展与完善都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规制化危机的发展历程。中国体育学在经历了联姻嫁接的基本态度后,学科的规制化发展也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这是对学科地位的确立,或者说是学科独立性的一种认可,更确切地说,这更是一种外在形态的认可。
然而,重要的是,学科规制的成熟,却并没有带来学科解释力的极大提升,也由此导致体育学科的学术话语权和独立符号还让人感到有些脆弱。这种学科内在学理性知识建构的不足,与当下中国体育实践需求与日俱增的客观实际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形成了一种学术诉求,正是当前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过程的一种最大问责。由此可见,中国体育学学科必须在经历了学科嫁接与联姻的基本态度后,走向新的内生创新知识建构时代。中国体育学在经历了30余年的系统化发展阶段后,已具备规制化确立的条件,或者说又走到了一个新的规制化轨道阶段(内生知识标准)。虽然,这一说法可能还存在一些争论,人们对体育学科的知识结构还存在一些疑虑,但中国体育学的作用已非常明显,这更加需要对学科的内生机制加以建构。
5 结语
当下的中国体育学科正面临着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及学科规制的一些问题或疑惑,学科归属的不明(或种属关系混乱)带来了学科分类、学位管理及学术管理的混乱;学科规模的有限带来的是学科之间的互动与交融的欠缺;学科规制的松散带来的是学问或学说的不足;然而,这些因果关系似乎有些牵强。因为,它们更加体现的是学科发展的外在标准,而当下的体育学科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内生创新发展,即学科发展的动因不应该是外发的,而应该是内生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影响当下中国体育学科发展的关键并不是学科归属、学科规模及学科规制,而在于对学理性命题的诉求,对学科解释力的问责。中国体育学科可能需要从学科内容、研究范式及知识建构3个方面做出思考和选择,即在学科内容上由学科分类走向问题关注;在研究范式上由描述研究走向解释研究;在知识建构上由联姻嫁接走向内生创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只能期望这种“历时态转型”的速度快一些,更好地实现“共时态压缩”的进程,单纯的遵循国外体育发展的历时态轨迹是难以完成自我超越的,这更是对每一位体育学人的历史拷问。
[1]范安辉,王磊,董德龙.关于体育学科危机的几点思考[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8):4-8.
[2]富学新,杨文轩,邓星华,等.美、英、俄、德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对我国体育学科体系建设的启示[J].体育学刊,2007,14(6):7-10.
[3]龚建林,富学新.俄罗斯体育学科的发展状况及其启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9,33(5):45-49.
[4]龚建林,杨文轩,陈琦,等.德国体育学科体系的发展现状及启示[J].体育学刊,2007,14(7):121-125.
[5]胡春雷.关于我国体育学科定位问题的思考[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36(3):6-9.
[6]李鸿江,尹军,郝晓岑,等.中、美、日、英、俄、德六国体育学科研究生培养体制与教育模式的比较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5):69-72.
[7]李建英,石晓峰,王飞,等.对体育学科均衡、协调发展的探讨[J].体育科学,2007,27(5):83-87.
[8]刘湘溶,李宏斌,龚正伟.质疑传统体育概念和体育分类[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35(6):110-113.
[9]李政涛.教育学科发展中的“制度”与“制度化”问题[J].教育研究,2001,19(3):76-87.
[10]鲁长芬.我国体育学科体系研究的必要性及策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8,32(2):6-10.
[11]鲁长芬,杨文轩,罗小兵.对体育学科分类的分析与调整建议[J].体育学刊,2009,16(4):6-10.
[12]罗孝军.体育学科自立门户任重道远[J].体育学刊,2013,20(4):10-11.
[13]邵伟德,马楚红.体育学科分类体系的科学性探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4,40(1)62-64.
[1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5]王和平,王科飞.高校体育专业设置与当前社会人才需求的矛盾与对策[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2(5):114-116.
[16]汪康乐,邰崇喜.论体育科学学科属性及其分类[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11):1453-1457.
[17]王续琨,刘永振.体育科学的学科结构初探[J].体育学刊,2002,9(1):4-8.
[18]吴健.体育学科中“科学”与“人文”两大哲学思潮的考察[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6,21(3):190-193.
[19]熊斗寅.初论体育学的科学体系[J].中国体育科技,1982,(2):18-27.
[20]徐忠,屈世琼.再论体育的科学体系[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0,26(5):19-23.
[21]杨文轩.体育学科体系重新建构刍议[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4):277-280.
[22]易剑东.当前我国体育学科发展的问题[J].体育学刊,2014,21(1):1-10.
[23]易剑东.对中国体育学科发展中两个问题的审视[J].体育学刊,2013,20(4):5-7.
[24]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EB/OL].百度文库,http://baike.baidu.com/ view/3327000.htm,2012-10-20.
[25]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EB/OL].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网,http:// www.cssn.net.cn/ pagesnew/search/ search_base_ result.jsp,2009-05-06.
[26]MICK G,SHANE C.Policy,politics and path dependency:Sport development in Australia and Finland [J].Sport Manage Rev,2008,(11):225-251.
[27]SEBAHATTIN D,HASAN S,MURAT T,etal.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strategies for sports education[J].Social Behav Sci,2012,(46):445-449.
[28]STEPHEN J W,LAWRENCE R K.A profile of sports science research (1983-2003)[J].J Sci Med Sport,2007,(10):193-200.
[29]UNITE STATE DEPARTMENT OF LABOR.Occupation classification [EB/OL].美国劳工部网,http://www.dol.gov/,2012-08-20.
[30]VEERLE D B,PAUL D K,MAARTEN V B,etal.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elite sport systems and policies in six countries[J].Sport Manage Rev,2009,(12):113-136.
Ownership,Scales,Regulations:Consideration of China's Sports Discipline in Current——A Discussion on Discipline Direction
DONG De-long1,LIU Wen-ming2,SEAMUS Kelly3
At present,speak status and subject symbol of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is constantly norms and forward,in which,the debate of “ownership of discipline”,“subject scale”,“subject regulation” is more concentrated,the reason is that they lead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system is unclear,confusion of management degree and the absence of knowledge and theory.However,author thinks that the ownership,scale and regulation more should be the external standard of discipline,the Chinese sports discipline in scale and regulation should be still “up hill”,the key is to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subject;at the same time,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basic direction of Chinese sports science development should be from the “discipline classification” to the “problem concern” in the content,research paradigm is from “descriptive study” to “explanation research”,knowledge construction is from the “grafting marriage” to “endogenous innovation”,by which,it can improve faster sports discipline from “diachronic process” to “synchronic compression”.
sport;disciplineclassification;disciplineownership;disciplinescales
1000-677X(2015)03-0083-07
2014-11-17;
2015-02-1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13YJC890010)。
董德龙(1980-),男,山东潍坊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E-mail:dongdelong@126.com;刘文明(1982-),男,黑龙江望奎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训练学,E-mail:liuwenming@zju.edu.cn;Seamus Kelly,男,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学,E-mail:seamus.kelly@ucd.ie。
1.鲁东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烟台 264025;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3.都柏林大学 公共健康学院,都柏林 爱尔兰 1.Ludong University,Yantai 264025,China;2.Zhejiang University,Hongzhou 310028,China;3.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Dublin,Ireland.
G80-0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