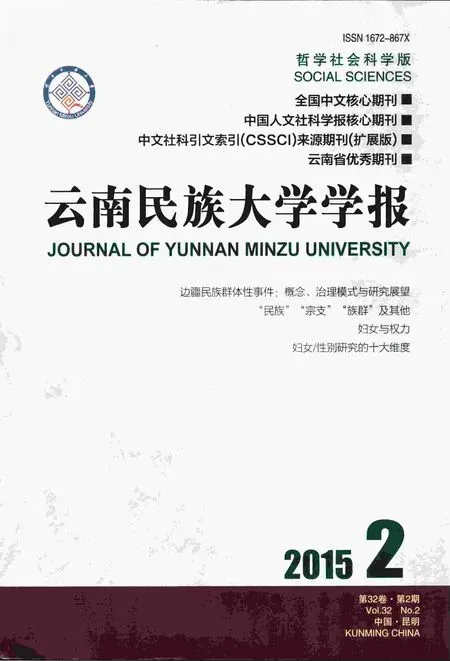资源结构与制度叠加:从老农保到新农保
郑文换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中国社会政策往往采取试验或者说试点的方式进行探索,所以同一政策领域往往出现不同探索阶段的“新” “老”两个制度版本即制度叠加(Institutional laying)的现象,如医疗领域的“老农合”与“新农合”、养老领域的“老农保”与“新农保”等等。其中,改革开放后推行的农保政策的变迁过程尤其引人注意,从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开始酝酿到1991 年由民政部开始推行试点再到1999 年被勒令清理整顿的老农保阶段,再到2003 年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开始试点、2009年出台国务院指导意见再到2012 年全国推广的新农保阶段,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政策变迁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研究不仅能更好地理解农保政策的发展脉络,而且对于制度变迁的研究亦非常难得,但目前关于政策“新”“老”名称变更的研究多从主管部门的不同、“老”政策失败或高层理念的变化来解释,鲜有对这一过程的深度研究。因此,在实地调研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笔者试图通过资源结构和历史制度主义的制度叠加的概念来把握这一变迁过程。本文认为:中国社会政策变迁的动力是行动者所面对的资源结构的转换,是资源结构的转换导致了社会政策的制度叠加结果。
一、既有文献研究
现有研究中对老农保和新农保之间关系的看法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政策失败论,认为老农保失败了,所以设立新农保成为需要;二是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两个制度分别是由不同的部门制定的;三是认为高层理念发生了变化。
老农保遭人诟病的主要缺陷在于: (1)在制度参数上没有财政支持这一块;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传中心:《支持新农保试点,国家财政出重拳——财政部负责人解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财政补助政策》,2009 年9 月9 日。(2)地方筹集的老农保基金遭到挪用流失; (3)因为利率在短时间内急速降低致使原来制度设计时所期望能领取的养老金不能兑现。但是,仔细分析这三个缺陷,并非老农保自身所独有的问题。首先,单纯从技术层面来看,积累式养老保险这种方式本身的一个致命缺点即是因利率或通货膨胀导致的基金贬值问题,这一问题同样也困扰着新农保;其次是老农保基金遭到挪用流失,也不仅仅是老农保自身专有的问题,新农保也未必会杜绝此类问题;第三,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老农保和新农保政策最大的不同在于政策的参数结构不同,老农保主要是“个人(储蓄)账户”方式,国家给予“政策扶持”,而新农保是由国家提供补助金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储蓄)账户”方式两部分组成。新农保设计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这两块的资金管理和资金流通渠道是单独分离的两块,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将老农保的“政策扶持”转变为“财政支持”,即“基础养老金”完全可以贴在老农保既有的“个人账户”方式上面,也就是说,完全可以通过对老农保制度进行边际调试,在政策参数结构上就可以变成新农保,再加上自上而下当年做老农保的那批人现在还在做新农保,因此完全不需要另外弄一套新农保制度出来。
利益集团之争的观点是根据经验判断最容易得出的结论,在1999 年废弃老农保前一年国家进行了部委重组,那么,部委重组导致的部门利益(政绩)之争可以解释老农保和新农保之间的关系吗?沿着巴克曼对中国“大跃进”政策进行研究的思路,①David M. Bachman,Bureaucracy,Economy,and Leadership in China: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可以想象取消老农保和重启新农保是职能部门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但是,通过对叫停老农保和启动新农保期间过程的考察,可以得知,尽管存在主管权之争,②夏波光:《从支柱到配套(1986 -1997)》,《中国社会保障》2009 年第10 期。但叫停老农保并不是部门斗争的结果,当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前身)并不主张完全取缔老农保,③汪泽英,何平,等:《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北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年版,第61 页。加之1998 年机构改革时原隶属民政部的农村社会保险司整体划归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之后在各级地方政府层面上都出现了这种部门、人员、编制的移交,可以说新农保继承了老农保自上而下的整套组织办理系统。④夏育文:《宝鸡:农民热捧新农保》,《中国社会保障》2010 年第1 期。也就是说,现在推行新农保的人员机构大部分还是当时推行老农保的人员机构,民政部、人社部在农保政策领域具有事实上的功能等价性(functional equivalence),因此,利益集团理论的部门利益之争也不能解释新老农保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更迭的原因归结为高层决策者理念的变化。许多研究认为叫停老农保的原因在于决策层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回归到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⑤汪泽英,何平,等:《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北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年版,第60 页。事实上,无论老农保还是新农保均是在中国经济体制发生大转变的改革开放之后出台的,叫停老农保、重启新农保的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是相对稳定的,这种观点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行动决定论色彩。这种高层理念变化的解释有一个潜在假设,即中国农保政策遵循官僚科层制流程,认为政策过程分为政策决定阶段和政策执行阶段,换句话说,就是认为政策由中央高层决定而由行政系统严格执行,高层决定的变化会随即带来行政系统执行上的变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有时候理念变化并不会随即带来社会事实上的变更,更有甚者,有时候理念变化的动因在于地方层面已经造成了既成事实或者说给其提供了政策选项。在国家叫停老农保政策之后,到2002 年仍有1800 多个县的5400 多万人参加老农保,也就是说,在国家叫停老农保后,基层政府并没有随即取消老农保制度,该制度至今也仍在运行。同时,新农保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有一些地方在推行有财政补贴的农保了。因此,高层理念的变化并不能解释老农保为什么能延续下来的问题,也不能完全解释新老农保之间的更迭关系,高层理念的作用还必须经过科层组织体系的协调,政策过程会深深地打上组织因素或者说制度的烙印。如果仅用政治理念的变化来解释从老农保到新农保的发展,换句话说,仅用政治理念的剧烈变化来说明农保政策的产生和停滞的话,很容易忽略了科层体系内不同层级的组织结构及其在政策过程的卷入对政策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两个农保制度基本上是由相同的行动者推动的。这就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相同的行动者针对同一个政策目标要做两套基本类似的政策/制度出来?相同的行动者(政策制定者)如何面对新老农保制度之间制度叠加问题?本研究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均忽视了农保政策过程的核心驱动力量——资源结构的作用。资源结构不仅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同的行动者推动了不同的制度,同时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相同的行动者不对既有制度进行边际修订,而是另起炉灶重新做一套原本可以相容的制度,从而导致制度叠加现象出现的原因。
二、制度叠加与资源结构
制度叠加⑥其他路径还包括置换(displacement)、转换(conversion)、漂移(drift)等。是历史制度主义学派为克服对其擅于解释制度粘性而弱于解释制度变迁的批评而提出的解释制度内生性变迁的路径之一,意指不触动既有制度,但是引入新的制度,使得两套制度同时存在的情况。⑦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eds.,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Ambiguity,Agency,and Powe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5 -16.中国政策模式具有很强的政治-行政性(political - administrative)及其方法(method)独特性①Sebastian Heilmann and Elizabeth J. Perry,Mao`s Invisible Hand: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11:19.,即政策的行动机动性强的特点,其原因首先在于政策决策权的弥散性和政策方法的灵活性。中国社会政策决策权是弥散并局限于“条块分割”的行政系统内,很多层级和系统具有政策决策权,这些决策的产生及推行往往又有独特的行动性方法,比如“大众动员”、 “政策试点”等方法,这些方法同科层体制上传下达的行政执行方式有很大区别。同时,政策又表现出很强的固化性,即使一个省份内部也可能同时存在一种政策的三种不同版本,各种版本最终成为悬浮在基层的一个个“飞地”,形成“制度叠加”。在地方政府层面,制度叠加现象非常显著,比如西南某市新农保与老农保以及地方自己设计的地方新农保等制度形成三种制度叠加状况。
本文强调政策的资源联结特点,将政策视为“重要资源的结构化承诺”②Schaffer,转引自H. K. 科尔巴奇:《政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0 页。。一般来说,政策的出台或者变更往往是支配关系的表达,吉登斯认为“支配依赖的是两种不同类型资源的调集。一是配置性资源,指对物体、商品或物质现象产生控制的能力,或者更准确的说,指各种形式的转换能力;二是权威性资源,指对人或者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种转换能力”,强调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是社会变迁的“杠杆”。③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版,第98 ~99页。政策的形成或变更是行动者在既有的资源结构状态中寻求有利于自己的转换能力的结果,政策过程中的行动者避不开既有政策形成的资源结构的限制(政策会制度化表现政策的粘性特征),同时又可援引其他资源来改变支配关系(改变既有政策的资源结构形成新的行动者之间的资源结构)从而更改政策。因此,本文使用“资源结构”(resource configuration)作为解释政策变迁的核心概念,资源结构是既有政策资源关系的结构性表达,又是一种整体性概念(holism),强调关系的连接而不是矢量的合并计算。资源结构对行动者同时发挥着制约和使能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行动者展开的理性行动,即通过持续维持既有政策资源投入支持既有制度,或通过寻找资源形成新的资源结构/支配关系谋求政策变更。在这一过程中,行动者是理性的并能反思性监控自己行为,资源结构成为行动者维持或变更政策的能力来源。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政策过程,我们可以将资源分成三类,即权威性资源、组织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其中职能部委往往是制订政策的策源地,具有事实上的政策动议权,同时在业务方面具有自上而下的业务指导权限,是一种权威性资源;地方政府拥有覆盖行政区域的组织实体及管辖网络,具有直接动员、组织社会的能力,即组织资源。此外,还有配置性资源,主要以行动者可以纳入到政策过程中来或依据政策而从社会中抽取的资金为主。上述三种资源的组合状态即资源结构可以为行动者设定活动边界,同时也会为行动者提供行动能力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或目标,资源结构的差异就会产生非常不同的制度措施组合即制度型构。下面将用资源结构的概念具体解释新农保的出台以及新老农保并存形成的制度叠加。
三、资源结构与制度叠加:从老农保到新农保
如上所述,我国的社会政策往往采取试点模式进行,政策出台往往是职能部委和基层地方政府之间互动的产物,④郑文换:《地方试点与国家政策:以新农保为例》,《中国行政管理》2013 年第2 期。新老农保均以试点方式出台,就是职能部委和基层政府之间互动的产物。因此,两者在权威性资源和组织资源方面具有功能等价性,而决定两者资源结构差异的关键在于配置性资源即资金资源位置的不同。具体来说,老农保阶段的资源结构是资金资源的位置在“块”上,跟地方政府的组织资源结合在一起,从而牵制民政系统,并且导致其基金管理权限沉淀在基层政府;新农保阶段的资源结构是资金资源的位置在“条”上,与职能部委的权威性资源结合在一起,从而能保证地方政府基本按照“条”的意思采取行动,并且使新农保的基金管理权限尽可能保持在“条”上。这种不同体现在新老农保不同的政策措施组合成的制度型构(configuration)的不同,其不同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首先,老农保的试点层次比较低而具体启动层次比较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是从乡村级开始的,在部委和作为启动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行政距离较远;相反,新农保的试点层次比较高而具体启动层次比较低,试点层次一般是比较大的市(比如地级市),由市通过下面的区县挑选村子来进行新农保试点,在职能部委和试点层次地方政府之间行政距离相对较近。这意味着主管部委的政策组织着力点不同。
其次,新、老农保政策目标指向的农村社区属性不同。老农保选择较富裕的农村社区,并且反对将农村人群分类使之加入不同的社会保险,原因是“改革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但这种转移主要在社区内部进行,而且大多数劳动者是亦工亦农,职业转换极为频繁,因此,不能分设不同的养老保险体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农村全体劳动者多年劳动的结晶。乡村企业的原始资本中有一部分或全部是来源于农业的积累,其资产不仅仅是企业职工集体所有,而且是乡村全体农民的共同财产。”①郑晔,彭维江:《宝鸡模式何以成为全国新农保蓝本》,《宝鸡日报》2009 年8 月4 日。而新农保则选择财政压力大的西部贫困县,并积极推动将农村人群分类使之加入不同的社会保险。新农保政策的试点②有许多地方实施了新农保,比如江苏、成都等地,但是这些地方的新农保并未能经过部委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所以,本文将新农保开始的事件认定为2007 年7 月31 日某村的发放。于2007 年7 月31 日在西部省份财政资源紧张的某市(该市全覆盖共需财政补贴达21000万元③郑晔,彭维江:《宝鸡模式何以成为全国新农保蓝本》,《宝鸡日报》2009 年8 月4 日。)两个最穷的县下面的村开始的。同时,因为新农保主要由国家财政提供基础养老金,所以,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新农保鼓励较富裕、有条件的农民(比如农民工)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第三,新、老农保在资金管理网络方面不同。老农保“建立的管理形式是:乡设‘保险基金理事会’,各村设‘保险基金理事分会’,其成员由村民民主选举产生,具体办理各村的保险业务”④郑晔,彭维江:《宝鸡模式何以成为全国新农保蓝本》,《宝鸡日报》2009 年8 月4 日。。同时,民政部借力的行政层次也相对比较低,一般是县级单位。在保险基金的管理与保险增值方面,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虽然也规定在银行设立基金专户,实行专账专管,专款专用,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老农保资金管理这一块儿比较乱,同时也为保险基金用于地方建设开了口子。新农保在业务管理方面,一般由劳动保障序列的农保处、农保中心负责;新农保试点地区在保险费收缴方面的经验一般是由村干部以及村会计将农民参保费用一齐收缴上来后,交到乡上的财政专户里面,再由乡上直接转入县级财政专户。财政部认为,“《指导意见》规定:新农保基金要纳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单独记账、核算。应当说,这是新农保与老农保在基金管理方面的一个主要区别。”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传中心:《支持新农保试点,国家财政出重拳——财政部负责人解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财政补助政策》,2009 年9 月9 日。
第四,新、老农保的资源注入能力不同。老农保的资源注入能力弱,因为当时“城镇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这块,政府已经投入了上万亿,背上了巨大的包袱。”⑥2001 年4 月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工作人员的访谈,转引自杨刚:《农村养老资源的制度性建构——沿海两地三村养老保障制度实证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2 年。因国家财力有限,为避免重蹈城市制度转型的覆辙,在资源结构上,老农保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资金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坚持自助为主、互济为辅”⑦《关于印发<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 >的通知》(民办发[1992]2 号)。;而新农保则代替“国家予以政策扶持”而直接予以财政补贴。具体来说,在资源注入上,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按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标准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 元”⑧《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 号)。。
第五,政策的一般化能力不同。老农保政策没有进入国家政策领域,维持了民政部部门通知的形式,而新农保于2009 年9 月1 日由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 号),从国家政策层面正式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各地既有的“地方新农保政策”都开始向国家新农保政策靠拢,因此,新农保政策的外推能力/一般化能力远远胜过老农保政策。
通过对上述不同点的论述,可以看出老农保和新农保的措施组合即政策型构不同,表现在财政资源的有无、启动层次、试点层次、组织网络范围(既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政策结构、承诺兑现、资金管理、实施范围、再生产机制(连续还是一次性缴纳、是否代际反馈)等等方面,总结如下表所示。

老农保与新农保的政策型构之比较
政策是重要资源的结构化承诺,新老农保不同的政策型构意味着不同的资源结构。从老农保的措施来看,老农保政策框架下形成的政策型构是以一个个比较富裕的郊区农村社区为依托,在这样单独的农村社区里,成员之间的不同身份在老农保参保上被收敛在一起,并没有对收入较高的乡镇企业职工和纯务农人员做出区分。在资金资源上,也主要是由本社区内聚集的缴费为主,不仅缺少国家中央级财政资源的注入,同时也缺少地方政府财政资源的注入,在资源聚集方面是郊区、社区指向的。尽管一开始老农保并没有形成完全社区自治的模式,一直处在行政序列指导下发展 (开始由乡后由县),并且在事实上资金管理网络也扩展到省一级,但是老农保的试点边界相对清晰,并且向上延伸的渠道比较单一。同时,老农保的养老保险基金存入银行专户,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银行并不扮演财务监督的约束角色,实际上只不过是扮演一个储钱罐儿角色。
新农保的政策型构具有明显不同于老农保的资源结构。国家在中央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地方财政的条件下,在城乡统筹、农村扶贫的大思路下,跟老农保相反,选择经济条件不发达、无法依靠农业社区的自有力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西部地区,通过中央财政资金注入、地方各级地方财政资金注入的方式,将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较高层级的地方政府(如地区级市)纳入到新农保的政策架构中来。在基金管理方面,规定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财政专户,同时,财政资金的注入行为“表明国家将对农民老有所养承担重要责任”①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宣传中心:《支持新农保试点,国家财政出重拳——财政部负责人解读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财政补助政策》,2009 年9 月9 日。。
总体来说,老农保阶段国家城镇社保包袱沉重,资源不足,同时农保基金对地方政府的吸引力使得老农保制度沉淀在地方而同上层的联系较少,老农保跟国家之间网络距离很远并且网络渠道单一,并且各个试点之间并没有连接的渠道,水平、垂直边界均比较清晰,形成了一个个悬浮在社会层面和基层政府层面交界处的“飞地”。新农保阶段因1994 年的财税改革及银政分家,资源逐级向上流动,国家财税充盈,相反地方政府财力枯竭,国家对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补贴吸引着地方政府接受职能部委业务系统的规制,配置性资源即资金资源与系统结合更为紧密,基金管理权限、流动渠道受到系统更多的控制。如果将新、老农保政策型构用图示表示,则如下图一、图二所示:


图一、图二中竖线或斜线表示我国农保政策中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度,圆形或者卵形表示为各个边界相对清晰的试点地区。从上面两个图中可以看出,与老农保相比,新农保制度型构中中央和社会的政策连接渠道增加,老农保跟新农保的不同在于: (1)老农保基金管理权限沉淀在基层政府,而新农保则由财政系统控制,新农保由此不仅受到主管职能部委系统的规管,同时还受到财政系统的规管; (2)老农保要求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也加入农保,而新农保则鼓励农民工加入城镇职工保险,同时,因为“家庭捆绑缴费”原则,使得新农保相比老农保在代际之间的连带渠道以及跟其它养老保险之间的连接渠道也增加了。与老农保的“飞地”特点相比,新农保政策型构更复杂、延伸更广。需要注意的是,新、老农保政策型构的不同不仅体现为资源结构的不同,更是不同的资源结构所导致的产物。
正如图一老农保政策型构示意图所示,国家与老农保制度型构之间的连接渠道单一,只有行政命令通道,而没有资金资源往来的渠道,资金资源与地方政府结合在一起,并且老农保的基金管理处于地方各级政府之手,因此,国家对老农保制度采取叫停行动的手段只有“条”上的业务指导权限,而缺少其他可资利用的政策工具,比如通过控制财政专户中流动的财政资源的流量来消解老农保制度。仅通过上传下达的叫停政令来消解老农保制度,就会遇到地方政府的暗中抵制。因此,尽管在国家下达清理整顿老农保的行政命令后,制度化了的老农保制度仍然留存了下来。在面对老农保制度化的状态时,对于老农保制度化、地方化的情况,政策“试点”模式中具有政策动议权的行动者就会试图去重新掌控政策,但由于“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重新动员沉淀在“块”上老农保制度中的资源的成本很高,于是, “试点”结构中具有政策动议权的职能部委就会重新重起炉灶,在不触动老农保制度的情况下推动新农保出台,形成制度叠加。
综上所述,配置性资源即资金资源与地方结合导致了老农保制度沉淀在地方层面并制度化了,而在资金资源跟职能部委结合的时候就赋予了职能部委吸引地方重新参与到新农保里来的能力。相同的行动者之所以分别设置原本可以相容的两套制度,是因为即使对已经制度化的老农保进行边际修订成本很高,①主要涉及对老农保资金的清点问题,而这会带来问责,从而导致地方的抗拒。还不如重新推动新农保。可见三种不同的资源构成的资源结构不仅影响了政策措施组合,还作为政策遗产(policy legacy)影响了后继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措施。
总之,本研究具体用资源结构和制度叠加这两个概念来把握从老农保到新农保的变迁过程,在近30年的时间内,相同的行动者设计了类似的制度(新老农保的主体制度仍是个人账户方式),并形成制度叠加现象。同时,本研究认为,新老农保政策变迁过程也是理解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启发性案例,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可能是中国社会政策的制度变迁往往发生在行政系统内部,由于与社会的切面较窄,将导致怎样的结果以及政策变迁对于制度内生性变迁具有何种理论意义的问题,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