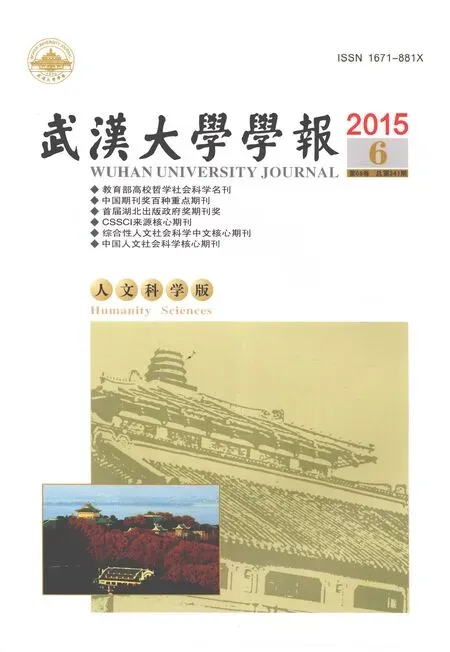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以《应帝王》为中心
张华勇
论庄子哲学的政治意蕴
——以《应帝王》为中心
张华勇
摘要:庄子将治天下视为圣人之“余事”。《庄子·应帝王》通过对有虞氏的批判,道出了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以天下人自治的方式藏天下于天下的政治观念。圣人将天下归还给了天下,从而使得政治走出治乱循环的道路。同时为政者治理天下摆脱了以牺牲自己身体为代价的困境,消解了政治的异化,从而自身从容有余。天下之物本所具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得以有机会脱离人的机制而面向天的机制,这也是其从为政者的“有心”统治宰制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从而能够自正其性命。由此,政治以统治的形态所展开的治理天下的方式得以退隐,无为而治的政治之道在此开显。
关键词:庄子; 政治哲学; 无为而治; 《应帝王》
庄子身处战国后期,他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文化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内圣和外王,并在《内篇》中对这两部分内容作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应帝王》一篇探讨了治天下的政治智慧。在庄子看来,儒家所认可的最高的政治生活形式是尧舜之道以及三代之治,分别代表的是帝道和王道,而这一政治形态是潜伏着危机的。只有当我们追溯政治更为本源的涵义时,政治生活的更高可能性才会得以呈现。庄子道出的圣人之治在批判以“帝道”、“王道”为典范的政教形态的同时,也指向了对最高政治形态的思考。正是庄子对儒家树立为最高的政治典范的反思,使得政治开显了一种新的形态而将政治生活向上提,同时人们的生活样式也有了一种新的可能。略观学界对《庄子》政治思想的探讨,似并未意识到庄子《应帝王》一篇所蕴涵着的丰富的政治意味。本文试图以《应帝王》为中心,阐发庄子对政治之道的思考。
一、 对儒家“相濡以沫”政治观念的批判
庄子对政治的思考是以当时的儒家思想为背景的,儒家思想在庄子那个年代是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一。早期儒家以周公的治礼作乐为其行道的理想,进而形成了以帝道和王道为代表的最高政治形态。虽然这两种政治典范在当时并未明言,但作为一种观念已经为战国时期的人们所接受。这一点在《礼记·礼运》有关大同和小康的描述中明显地道出了。其中关于大同的叙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载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58~659页。
大同叙述了“天下为公”的政治及相应的生活形态,这一形态超越了作为伦理秩序核心的小家,试图将家这一形态扩展到整个社会,把社会变成一个大的家庭。由此伦理亲情就不只是及于私人的家庭范围,而是视天下人为一家之成员,这也是儒家理想的政治生活形式。小康的具体表述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660~661页。
小康则将“天下为公”的理想落实在了每一个家庭之中,以家作为“礼”具体展开的场所,家庭中的亲人是“礼”最直接的相关者。人们的生活形式建基于家之上,周公制礼作乐也正是以家之伦理作为构建国家统治的基础。以小康作为生活形式的周朝在经历了近800年的历史之后最后仍然分崩离析,诸侯纷争以致国不成国,家庭也不再成为维持国家治理最基本的单位。庄子身处战国年代,不得不反思一个已存在了极为长久的朝代依然面临瓦解的原因所在。在《庄子·应帝王》一篇中通过对国家政治之道的思考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应帝王”的题意也就是回应以帝道和王道为中心的政治典范,进而思考政治生活的其他路径。这两种政治典范在当时被视为包含了政治生活的所有可能性,以此作为构建国家秩序、实现人们理想生活形式的政治形态。庄子并未否定这种帝王史观,而是追寻其更为初始的源头,为政治生活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庄子有关政治生活起点的思考首先表现在了对以“相濡以沫”为核心的儒家政治观念的批判。
“相濡以沫”出自《庄子·大宗师》篇,原文是“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中华书局2012年,第247页。本文对《庄子》及注疏的引用以该本为准。本文的引文涉及庄子的内、外、杂篇,对于何者是庄子本人所作不加评论,仅以各篇文字所表达义旨之相通为要。。两条处于干涸之泉的鱼相互吐沫呴气维持彼此的生命,庄子认为如此艰难地保护着对方,还不如身处浩瀚的江湖各自畅游。成玄英疏曰:“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无复往还”,“泊乎泉源旱涸,鱏鮪帕困苦,共处陆地,赬尾曝腮。于是吐沫相濡,呴气相湿,恩爱往来,更相亲附,比之江湖,去之速矣。亦犹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47页。吐沫相濡虽能表现彼此间的恩爱,但相比各自在江湖之中自在地游泳,显然陆上的鱼受着更多的制约。可见,庄子以此为譬喻正是要指明以互亲互爱的人伦关系作为维持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这一机制包含着更多的人为的设置,而忽视了个体自身独立存在的优先性,或者说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的建制,并未虑及存在于人之外的、高于人的天的机制。将国家和社会的架构建立于一人一姓的私人意志,这导致的是社会的运行始终无法摆脱人的干预和设置,个人的目的往往牵引着社会的发展,并暗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后果是个人权威的树立以及个人有能力将自身的目的架于公众利益之上。无论这一目的是出于善良的动机,亦或是将平治天下作为其出发点,并没有为个人的“各正性命”*语出《周易·彖传·乾》。其意是天下万物在乾道流行之中皆能正定自己的性命,而不假借外力来寻得自身的性命之质。乾之德就是要引导事物走上与自身的性命之情相合的成己之路。原文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云:“此二句更申明乾元资始之义。道体无形,自然使物开通,谓之为‘道’。言乾卦之德,自然通物,故云‘乾道’也。‘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言乾之为道,使物渐变者,使物卒化者,各能正定物之性命。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秉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物之性命之所以能得以正定,是万物自化的结果。道体无形,贯通于天地之间,道生物而不成物,天下之物在其中滋养生息,以成其自身的方式回应乾道的生生不息之德性。参见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第9页。提供合适的境域,而这不只是使得公共领域无法成熟建立,处于失落的状态,同时也会时时存在着以个人的意志扭曲正当的社会机制的情况。
庄子在《齐物论》一篇中也表达出了相同的担忧:“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郭庆藩:《庄子集释》卷1,第98~99页。从人的机制来观察、衡量这个世界,看到的是各种错位的景象,因此就有了是非善恶的分别,也就产生了除恶去非的欲望。王夫之云:“居之所安,食之所甘,色之所悦,皆切于身而为自然之觉,非与仁义是非后起之分辨等。然且物各有适而无定论,皆滑疑也。而况后起之知,随成心而以无有为有也?”*王夫之:《庄子解》卷2,载《船山全书》第13卷,岳麓书社2011年,第114页。“物各有适”正指明了每一物处于自身合适的境遇中能够“各适其适”,不以维持与他人投桃报李式、共呼吸共存在的社会关系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而是个体以成就自身的方式来呈现自己原有的自然之性。“成心”的存在往往挤压了“各适其适”的空间,而以其成见来统治天下的事物。此时的政治就退变成了一种以管理国家为目的的治理术,其“政者,正也”(《论语·颜渊》)的政治所应具有的正当性并未呈现,政治也就成为了统治。政治原本具备的促进存在者得以“各正性命”的那一积极作用无法得以施展,统治者的所为往往会通过各种规范和机制将人们培养成社会中的一员,并非是一个具有不同个性的独特的个体。个体自己治理自己,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塑造自身的前提是为政者不以其所主导的统治来规范个体的发展,这样个人才有正其自己的可能,从而个人自身成为一个责任主体,为自己的所为担责。为政者一味试图主导政治的运行,只能使得本应由个人自身承担的责任归之于政府。而这些弊端正是以“相濡以沫”为起点的政治形态所暗藏着的后果。王博在《庄子哲学》一书中也指出了这一点,“它们以无相与的方式相与着,以无相为的方式相为着。比起浓浓的爱,淡淡的水显然更让鱼们感到自在”*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3页。,在陆地上的鱼以相互关怀来体现对彼此的爱意,还不如各自在水中自在地游泳,相对于人而言,自身主体的挺立和主体性的自觉应优先于以“相濡以沫”为主的人伦关系。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第三十八章)当人们将礼义视为生活的最高意涵时,大道自然也就隐遁了。只有在人们的视线不再局限于这一人伦关系之时,那种更高的可能性才会显露出来。
庄子在《应帝王》的开篇即对“相濡以沫”作出了回应,该篇以啮缺和蒲衣子的对话开始,进而引出了“有虞氏”和“泰氏”两种不同的圣人形象:
啮缺问于王倪,四问而四不知。啮缺因跃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93页。
观察两组患者膀胱痉挛[6]的发生情况(发生率、持续时间、疼痛情况及日发作次数)、膀胱冲洗前后生理应激指标的变化及护理满意度。
啮缺问道于蒲衣子,蒲衣子是舜的老师。成玄英疏曰:“蒲衣子,尧之贤人,年八岁,舜师之,让位不受,即被衣子。”*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94页。又曰:“蒲衣是方外之大贤,达忘言之至道,理无知而固久。”*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94页。啮缺是体道不全者,以其自损而求道。王倪是指王者的端倪,象征着王道。有虞氏指的是舜,其所代表的是帝道,“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伏羲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94页。。泰氏所体现的是比帝道更高的境界,吕惠卿解释道:“啮缺非道之全也,以其知之而问也。王倪则王之端所自起也,故其所体也如此也。蒲衣则被衣也,衣被万物而不为主者,唯道为然,而蒲又所以安之也。”*吕惠卿:《庄子义集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151页。蒲衣是“衣被万物”而不主宰万物,庄子在此通过啮缺和蒲衣子的对话质疑了以帝王之道为典范的政治传统,同时又超出了这两者,提出以泰氏为代表的政治路径,从而超越了帝王之道。蒲衣子之所以认为“有虞氏不及泰氏”,原因就在于“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有虞氏包藏仁义以得人,从而获得执政之基。“臧,善也。善于仁义,要求人心者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94页。,其将得仁义视为一种目的,既然提出了仁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对应地就有非仁,从而有了仁与非仁、是与非的分别,进而导致人们纷纷追求仁,由此使得仁义成为了一种可追求的对象而外在化。陈少明指出:“以‘非人’和不‘非人’来划分不同的层次,是反对以任何个人的爱好作为衡量他人是非的标准,要远离是非之地。”*陈少明:《〈齐物论〉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4页。有虞氏把“人”与“非人”对立看待,正是将“个人的爱好”当作社会的评价标准。他虽然为平治天下而对百姓施以仁义,善待民众,同时又尽心尽力治理好天下,教化人们懂得仁义,然正是舜出于善心的作为,将仁确立为了正面价值,由此埋下了后世大乱的根源。庄子云:“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郭庆藩:《庄子集释》卷8,第771页。,尧、舜之时“仁”的出现导致后人竞相追逐,仁之名远过于仁之实。名与利相纠缠成为大乱的根源。“相濡以沫”作为仁的具体表现也包含于这一根源中。庄子通过对“相濡以沫”的批判所要指明的是“藏仁以要人”所代表的帝道的政治形态中包含着对仁义的筹划、经营之迹,崇尚仁、怀藏仁从而达到聚合、笼络人心之效果。虽然这样的作为并非是为了自己,是为天下计,但存在着“用心为治”的客观现象。
有虞氏的“藏仁以要人”的作为使得仁与不仁有了分辨,至此仁作为一种独特的道德品性而为人所尊崇,于是人们出自主观的意愿区别了善和恶、美和丑,各种道德词汇的出现意味着名与实的关系就此分裂,老子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此处老子指出最高的为政方式是百姓不知道统治者的存在,百姓以自发的活动形成社会秩序。圣人治天下而百姓“不知”圣人有之,如此万物自发性的活动才有可能展开。老子认为获得百姓称誉的治理活动本身就已经是圣人之治的退化了,当百姓开始赞颂为政者时,其实就已表明百姓自正其性命的活动受到了干扰。因此,王弼云:“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并作焉而不为始”,万物在圣人之治下蓬勃发展,而不曾觉察到外部作用的存在。万物由此呈现自身本真的面貌。参见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40页。(《老子》第十七章)在老子看来最高的境界是事物的两面并不以对立双方的面貌出现,人们只是“默而行之”,没有对立双方的概念意识,此时其行其言恰恰是最“真”的。当起了分辨之心,人们自然会去追求一般人所称誉的东西并以此为荣耀,同时将此视为生活的目的,试图由此获益,经营、筹划之心也因之而起。释德清也说道:“有虞之不济处,盖以仁为善,故有心以仁要结人心。”*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将仁视为善的,此时真就被掩盖起来,人们一心追求社会所认可的那个善,极力让自己成为这一类型的人,为自己树立良好形象之类的想法占据了人们生活的全部。人们为保全名誉而奔波,竭尽全力成为社会所公认的善人,此时的名已经掩盖了实,也使得人们将自己的生命异化于“名”之中,丧失了个体的自然之性命。庄子云:“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4,第330页。人们殉身于各种名号、“事业”,而遗忘了自身的自然本性。郭象注云:“自三代以上,实有无为之迹,亦有为者所尚也,尚之则失其自然之素。故虽圣人有不得已,或以槃夷之事垂拱之性,而况悠悠者哉!”*郭庆藩:《庄子集释》卷4,第331页。三代以上,人们的生活是“无为之迹”,人们不刻意去分辨、崇尚某物、某种价值。一旦人们有所崇尚,那么崇尚之事物就丧失了其本然之面目。另一方面,各种名号也有可能是统治者为达统治之目的而树立的,以此改造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这些名义也可能成为统治者组织、动员民众的理由。庄子说道:“待钩绳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绳约胶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礼乐,呴俞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4,第328页。统治者以规矩来规范引导人们的言行和思想,刘凤苞云:“削其形则削其性”*刘凤苞:《南华雪心编》,中华书局2013年,第213页。,“曲为仁义之貌以徇人”*刘凤苞:《南华雪心编》,第213页。,在善德的名义下填充其所认可的内容,入侵异化了民众的自然之德,以仁义之名为标准来要求社会中的每个人并以此来选拔各类人士,以此种措施作为治理术来统治天下。这种出于一己之心的治理技术非但无法引导人们探寻、了解自己的本然之性,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鼓励人们向外追名得利的制度,以此方式稳固自身的统治,并以仁义之名赢得统治的正当性,而这正是完全是从人的视域出发、以人的机制来达到统治天下之物的目的。胡文英云:“有人,则不能合于天”*胡文英:《庄子独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3页。,以人的机制主导天下秩序,恰恰是忽视了天的存在的表现,政治的另一种向度消失了,从而自发的天的机制也就隐遁了。人们由“自适其适”从而“各适其适”的“正其自己”的道路无法畅通,由此失去了通达“道”的可能性,人们极可能就成为了统治者所管理下的一个群体。可见庄子对以“相濡以沫”为名而进行统治的批判切中了政治退化为一种治理术的要点之所在,而统治者恰是以仁义来维持其治理现状的。
而泰氏是另一种圣人,这一路的圣人并非总是心系天下,为治理天下而心怀忧患。天下的安治并不是依赖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治理的,个人的成己活动无法由他人来代替,因此只有当每个个体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特的创造者,而不是他人统治下的一员,个人才有可能去探寻自己的本然之性。此时的圣人所做的并不是去积极地行使管理的权利,为治理天下而操劳奔波,尽心尽责去保护每个人,而是无心于天地万物,甚至无心于自己。因此仁义与非仁非义就不再加以区分,仁义自身也就被消解了,“亡己之仁,不求诸人,人自化之”*朱文熊:《庄子新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页。,没有了仁义之名,众人仍皆得以自化。事实上百姓的成就是他们自己的作为所结之果,是他们自发自觉的所为,对于圣人而言并无任何功绩,也就是“无功、无名”,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这一句表达了百姓各成其事,各得其乐的原因不在外部,而是皆发端于自身。个人依照自身独特的道路而得其所是,这是极自然的事。所谓“自然”就是其源头不可捉摸,万物是依其自性去为,因而也就无须一个外在者对此加以指导和规范。王弼曰:“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亲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这也是泰氏安顿天下的方式。参见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第41页。(《老子》第十七章)百姓所成之事,并不归功于某一圣人,相反,认为这些皆是自己之所为。圣人不对百姓所做之事加以干预,不以仁义要求自己,那么仁义之意就不会宣扬于天下,百姓自然也就不去追逐仁义之名。这一境况下的仁之名就暗含于仁之实之中,两者由此而不会分离。这样一来人为的机心就不会出现,百姓以自己的力量成就了自身。圣人之所为就是构筑这样一种境域,使得百姓“自正性命”在这一境域中得以发生。此时的天下不再是一人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每个人都自得其所,这一政治形态不但不会使得为政者伤性害身,也能够让百姓保生。当百姓忘记为政者的存在,为政者也兼忘天下时,最高的政治形态的可能性才会出现,这一形态与“相濡以沫”相对,表述为“相忘于江湖”。
二、 圣人的为政方式及其表达的政治意蕴
圣人所认可的为政方式是“相忘于江湖”,这一方式的展开是以“无为”作为原则的。这里的圣人是指无心于天下而天下大治的为政者,相对于庄子所批判的“藏仁以要人”的有虞氏而言,“其卧徐徐,其觉于于”的泰氏就是这类圣人典范。“相忘于江湖”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为政者不以积极有为的方式参与到个体“自正性命”的过程之中。个体通过不断地寻找适合于自身的道路,从而成就自身。这一探寻自己自然之性的道路唯有依靠个人自身的活动才能得以展开。郭象云:“与其不足而相爱,岂若有余而相忘。”*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47页。若只能以相互依赖的方式才能彼此生存下去,那么个体自我认识、自我成长的活动必然会受到对方的限制,自在自乐的空间也由此受到挤压。事实上万物不依赖于他者,依靠自身就能独立存在,褚伯秀曰:“性命之源涸,处于人伪之陆,而呴濡以仁义之湿沫,不若相忘于道术之江湖。”*褚伯秀:《庄子义海纂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8页。如此自然之性命才可以以事物自己的方式得以展开,避免外在的力量对事物自正性命的活动的干扰和入侵是圣人政治活动的中心内容。郭象则以“有余”一词道出圣人治理天下的方式。“有余”表明每一物顺其自性而为,为政者不费功夫天下依然安治。在这一治理天下的方式中,为政者能够从通常繁重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而得以安顿自己的生命,不因天下之治理迫使自己忽视了作为存在之根本的身体。
庄子在《让王》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为政治国的原则。他说:“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9,第963页。圣人将治理天下视为余事,反观帝王竭尽心力所成就之功业只是试图以一己之意代替众意,虽心系天下,始终为之操劳,然其治理天下的方式恰恰剥夺了事物自正性命的可能性,天下之物无法以顺其自性的方式安顿自身。因而,老子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四十八章)“有事”则意味着统治者对天下之物的积极干预。帝王以天下的安宁作为统治的目的,但其治理的方式入侵了百姓的自然性命,以人为的形式将百姓的生活及成己的过程按照为政者自己所认可的方式进行,这一出自主观意愿的动机并不能让天下之物各得逍遥,只是成为被统治的一员。事实上这一治理天下的模式对为政者而言也是不利的,为治理天下而忙碌操劳,损害了身心。林希逸云:“危身弃生以殉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林希逸:《庄子鬳斋口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第443页。,将自身陷于因心忧天下而无视自身的自然本性,生命由此而处于异化之中,不能“完身养生”。“完身养生”意味着个人的身心达到协调一致的状态,两者都处于本然的位置,精神不再是一味地向外驰骋,而是将注意力收回到了自身之中,重点是凸显了个体自身的重要性。身体不再只是为精神所驱使,而是回到其本然的状态,精神上的从容首先表现在身心的相互协调。庄子的这一倾向表达出了每个人的精神首先是自足的观念,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个人就不应轻易将自己所认可的各种价值观念以各种方式试图让人们接受,因为人们对自身本性的认识只有依照自己独有的方式才能得以认识,不去“破坏天地万物自然本真的天性”,人们才可能“依其自然真性去生活”*陈鼓应在《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一文中指出,《庄子·让王》一篇“多藉辞让名位、利禄表达生命的可贵”,其要是要保持万物的“自然天真的本性”,由此才能处于“本真的生活型态”之中。参见陈鼓应:《庄子论人性的真与美》,载《哲学研究》2010年第12期,第31~43页。。
在庄子看来,将治天下当作“余事”,以余心、余情治国才是圣人的作为,这也正是庄子所要表述的为政者治天下的中心思想。其实质内涵指向的是治理天下的无为原则,圣人的无为才可能使得百姓自正、自治。《应帝王》中庄子借无名人之言道出治天下的原则:“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301页。天下大治而百姓并不知为政者的存在,圣人治天下而不居天下,其所为只是顺物自然,物之成就自身只是其内在本性的自然显露,因此百姓丝毫未曾觉察到圣人的存在。王夫之云:“澹心、漠气以忘其生,无益损于生而生不伤;澹心、漠气以顺乎物,无益损于物而物不害;一也。唯才全而德不形,不悦生而恶死,可以养生,即可以养民。谓生死之在我,则贼其生;谓民之生死在我,则贼其民。以心使气,盛气加人,鄙人之焉也。大公者,无我而已。唯无生而后可以无我,故乘莽妙之鸟而天下治。”*王夫之:《庄子解》卷7,载《船山全书》第13卷,岳麓书社2011年,第178页。顺乎物则物不害,这正是圣人之所为,顺乎物的自性,天下之物依其自身而各不相害,为政者也不防害物之自正性命的活动,物依本性自然而成为一物。唯有当圣人将治天下视为余事,其私心私意才不会融于其间,以无我的大公者形象寄身于天下之中。“藏仁以要人”是私意的表现,“以己出经式义度人”也是私意*成玄英疏曰:“式,用也。教我为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须己出智以经纶,用仁义以导俗,则四方氓庶谁不听从,遐远黎远,敢不归化耶。”成玄英指出这一为君之方虽教化百姓,然其实质是出自一己之智,并将此作为经纶来导俗化民。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90页。,虽然这样的私意不是为了一己之利,但其试图出自一己之意愿谋划天下之治理的主观机心依然存在着,结果就可能害生害物,“贼其民”,“盛气加人”。这也正是庄子提出“圣人无名”的原因。圣人治天下是为营建一种万物能够自生自成的境域,如此一来天下之物成其自身的同时也并未觉察圣人之存在,谓其“自然”而成,圣人也没有获得任何名声。这一治理天下的方式也称为“明王之治”,庄子云:“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有莫举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303页。,物自乐自喜而不见圣人之踪迹。每个人生活在其中都各得其性分,如此居于天地之间而得逍遥,这些是天下之物“自化”的结果。陈鼓应在《庄子浅说》一书中论述庄子“不道之道”一语的含义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陈鼓应在《庄子浅说》一书的“不道之道”一章中说:“所谓‘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这个‘固’字,便说明了‘本来如此’,而不是外来的因素。在《知北游》中也说到‘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所谓‘不得不’,乃属必然之事,庄子十分强调万物的‘自化’”。参见陈鼓应:《庄子浅说》,三联书店2012年,第79页。。当为政者要为天下奔走呼号时,所表现出的形象自然会获得巨大的名声,庄子云:“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郭庆藩:《庄子集释》卷4,第323页。而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4,第323页。,以殉身而得各种不同的事业,所伤的不只是一己之性,也是他人之性。以余心、余情治理天下,将治天下视为“余事”,自然就不会以身殉天下。不将治天下视为以身殉之的事业,身心由此而解放出来,回到其本位,身心作为本己的一部分而得到关注,如此一来天下也回归到了其自然的境况,天下之物皆可自正自化。
三、 “藏天下于天下”的理想政治形态
那么,由圣人之治所构建的政治形态是怎么样的呢?天下在圣人那里又是如何安顿的?圣人治天下并不是将天下视为一己之物,其治天下的方式只不过是还天下于天下,也就是让天下按自身的方式运行和展开,由此天下之物才可能自正自化。天下若属于一个人的,成为一人之所有物,这样治天下的方式就只会以统治的形态展开,以一人的意志支配天下之物,天下就会成为可为人所占有之物而引起各种纷争。
圣人之治则以无为的方式将天下归还给天下自身。事实上当天下之物得以以自身的方式居于天地之间时,天下也就不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而成为天下人之天下。这一政治形态基于的正是庄子所表述的无为原则,庄子云:“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故贵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无擢其聪明,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神动而天随,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郭庆藩:《庄子集释》卷4,第379页。无为之治,不只是安为政者自身的性命之情,同时也安放了百姓的性命之情。王叔岷云:“有为,则不足以尽其有为,……唯无为也,而后各安其性命之情”*王叔岷:《庄学管窥》,中华书局2007年,第200页。,天下之物能够各安其性命之情,虽无为,天下依然大治。老子曰:“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第三章)为政者无为,万物才可能有为。让天下于天下人的为政者,必然就不再怀有占据天下为一己之物的想法,因此其内心也自然豁达而有余,贵一己之身的同时也会贵天下人之身。当为政者“解其五藏”、“擢其聪明”,竭力治理天下,精神奔驰,如此弃身而就物,其身无法自安,天下人之身又如何安?因此,郭象曰:“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怀朴,任乎必然之极,而天下自宾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4,第380页。无为的结果是天下之物自为自宾,其性命皆得其所安。可见圣人治理天下只是让天下自行治理,不以天下自居,亦无取于天下。圣人以贵爱其身的方式使得自身不参与到天下自身的运行之中,陆树芝云:“能贵爱其身者,为天下而不至以身殉天下,天下亦可寄托于其身,以安性命之情矣。”*陆树芝:《庄子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贵爱其身者,能够不以身殉天下,自然也使得天下以其自身的方式运行,而“万物同此天机,自作自息,吾任之而已”*陆树芝:《庄子雪》,第116页。,任天下之物自作自息,从而每一物才能得以自安。
《周易·系辞传》“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马王堆帛书《易传》中作“黄帝、尧、舜垂衣常而天下治”表述。参见丁四新:《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18页。所表述的正是圣人任万物自生自化的治理天下的方式,在庄子那里则以“无为”表达而出。庄子所思考的政治生活的最高形态蕴含于“藏天下于天下”一语之中,这也是圣人之治的天下所呈现的具体面貌。庄子云:“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3,第248页。天下如何避免成为人们争夺的对象,变为一人之财产,如庄子所说以“藏天下于天下”的方式使得天下归于天下,实“乃不藏之藏。不藏之藏,自无所失”*王叔岷:《庄子校诠》,中华书局2007年,第226页。,当天下为天下人所有,如此天下就不会为人所窃。此时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各适其适,各得其所,圣人居于其中同样也游刃有余,其得逍遥,百姓皆得逍遥。圣人恰以无为之治,不自居天下,天下不治而治,其视治天下为余事。释德清云:“与道为一,浑然大化而不分,是藏无形于无形”*释德清:《庄子内篇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由此治天下而无所成名。天下之物以其自身的方式安于天下之中*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云:“藏天下于天下,言藏天下之物于天下之大情,斯物无所得遁矣”,所谓“天下之大情”就是由天下之物自发形成的秩序,这一秩序的形成恰是因圣人任万物自我生长,圣人对天下不加治理,而居于天下之中的每一物皆自生自成,那么作为整体的天下秩序自然就可见。圣人通过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而营建了万物自正性命的境域,如此一来天下之构成就在于生长于这一境域之中的每一物皆可依其自然之本性成为自身。参见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中华书局2012年,第550页。,其实也就是万物自己安顿自己,以自然的方式生活于其间,而人为的方式进行的统治让位于百姓的自正自化。
四、 结语
在庄子看来,要想天下不为人所窃的方法是“天下为公”,当为政者为统治天下采取各种治理措施之时,必然会试图将个体纳入自己所设定的规范之中,如此一来个体自正其性命的活动也就无法顺畅展开。个体自身作为创造者所具有的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自然之本性也不能得以呈现,这样的天下是不能既长且久的。唯有为政者以天下归于天下的方式化裁治理,“藏天下于天下”,此时天下之人得以自己治理自己,各得其所,寄身于天地之间。那些以对天下的支配和占有为目的的统治实质上只是一种治理术,治理的技巧而已,真正的政治是要思考个人生活方式的更高可能性这一问题。还天下于天下,其所采取的治理天下的方式是给予每一物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展开自身的可能性,为这一“自正性命”的过程顺畅进行提供空间及场域。将天下视为一获利品,可以由一人之手转让给另一人的治理方式,更多的只是停留在了统治这一层面。庄子云:“唯无以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也。”*郭庆藩:《庄子集释》卷9,第956页。不将天下视为己有的人,也就会将治天下当作自己整个生命活动的“余事”,同时自身处于余心、余情之中。在此境域中,天下之物自治自化,与为政者相忘于江湖,从而使得为政者不以治理天下牺牲自己本有的情性。以治理术为主导的统治此时才会退隐下去,真正的政治之道才得以彰显。
●作者地址:张华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zhp2297@126.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1JJD720002)
●责任编辑:涂文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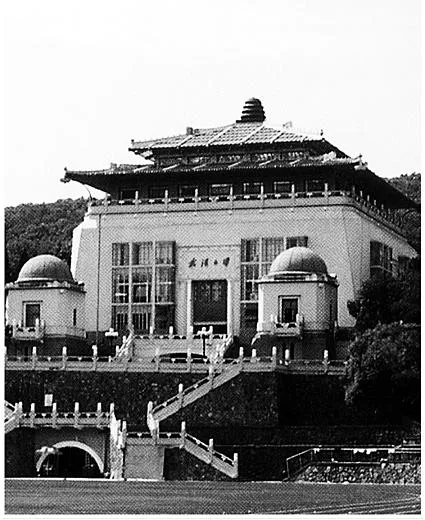
On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 of Chuang Tzu’ Philosophy
——Concerning onYingDiWang(《应帝王》)
ZhangHuayong(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Chuang Tzu sees ruling the world as the sage’s “side line of business”. By criticizing You Yu Shi in Ying Di Wang(《庄子·应帝王》) from Chuang Tzu, he proposed the political idea that the world belongs to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should be hidden in itself in an autonomous way . The sage leaves the world to itself to prevent the political chaos cycle. Politicians can rule easily without the expense of their own body, and avoid the political alie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ings in the world have their own spontaneity and consciousness, which give them opportunity to take the heavenly approach instead of the worldly one. This is also the proces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domination of ruling purposely, and liberating the politician’ own life. Thus the political way of governance retreats, and the method of governing without intervention reveals.
Key words:chuang tzu; political philosophy; govern without intervention, Ying Di Wang(《应帝王》)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