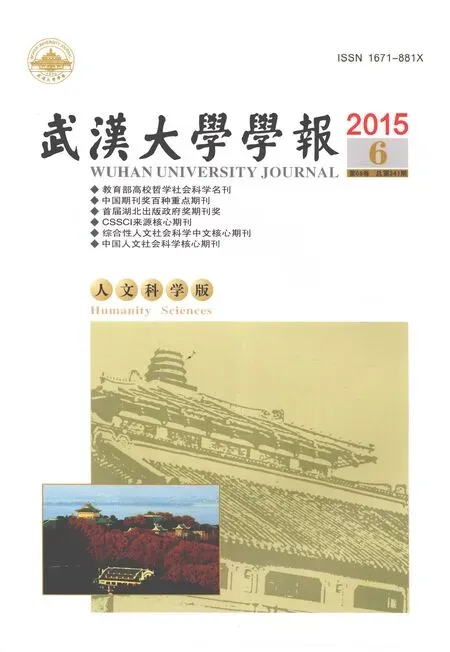明散曲的“缺席”与“在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文体分布研究之一
程 芸 李艳华
明散曲的“缺席”与“在场”
——“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文体分布研究之一
程芸李艳华
摘要:“中国文学史”著作如何处理各类文体的比重,是一个难题。明代散曲的作家数量、作品规模,与其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比重,形成明显反差。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中明散曲的“缺席”或“在场”各各有别,从整体看,彰显出我国文学史书写的一些时代性特征。细密考察“中国文学史”文体分布情形,以为将来的文学史写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明散曲; 中国文学史; 文学观念; 文体
明代散曲的作家数量、作品规模,均远胜于元代和清代,然而综览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类著作,如何把握明散曲在整个叙述框架中的比重,却成为一个疑问。事实上,我国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现象,本是西学东渐和现代学术体制的衍生物,因此,也大都以纯文学的观念为依托来考察古代文学*陈文新、郭皓政:《明代状元别集文体分布情形考论》,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第54~61页。。此为一基本事实,就更为具体的某些文体而言,是否应该写入以及如何书写,则值得我们作更进一步的细密考察。
以明代繁兴的散曲写作为例,这既是折射“纯文学”观念的一种重要文学史现象,也与当时的舞台风尚、表演艺术密切相关,它在“中国文学史”类著述中,是“缺席”还是“在场”,却呈现出细微的反差,由此而彰显的文学史书写的一些时代特征,亦足为后来者镜鉴。
一、 初度登场:1919年以前
“五四”之前的文学史编纂大体而言,更多地继承了传统“经史子集”的文类观念以及视诗文为正统的文体价值观念,对曲体、说部的轻视也大略相同。不过细究若干代表性著述,史家们对明散曲的态度,却已有值得重视的分别。
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载《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陈平原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所据底本为1910年武林谋新室的校正本。,所述以群经、诸子、史传、诗文为主,侧重文字、音韵、训诂、文章作法的论述,明确反对将曲体、说部列入文学史的范畴。第十四篇第十六章“元人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中,他甚至直斥日本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说:
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210页。
林传甲的文学史理念,更符合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法的规定,故其文学史料的视野非常传统,主要来源于传统目录、“文苑传”和“诗文评”。然而,尽管这些材料中曲学的内容很少见,却不能成为林传甲漠视曲体(尤其是散曲)的依据。事实上,明清不少文人曾努力“推尊曲体”,散曲还曾被视为接续雅乐传统的“正音”*程芸:《明代曲学复古与元曲的经典化》,载《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3~168页。,就连《四库全书总目》也在“集部词曲类二”中专门为“南北曲”留下了一个位置。
其实,若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与窦士镛《历朝文学史》*窦士镛:《历朝文学史》,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铅印本,国家图书馆藏。作一比较,更可看出这只是缘于林氏个人观念的滞后,整个晚清民初的学术界,早已存在新型文学观念的脉动。窦著包括五个部分,“文字原始第一”、“志经第二”、“叙史第三”、“叙子第四”、“叙集第五”,其所谓“文学”更类乎中国传统学术的概称。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叙集第五”已经提及“曲”,虽只有寥寥数语,且所述之戏曲多为久传不衰的经典作品,并未提及明代散曲,但仍可看出作者冲破传统观念藩篱的可贵努力。
与林著同名的黄人《中国文学史》*黄人:《中国文学史》,清末国学扶轮社铅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其文学视野要开阔许多,在文体选择上,也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点,既接续了古代“杂文学”这一传统观念,也有现代“纯文学”观念的萌芽。如第十一编“文学暧昧期(近世文学史)”之第二章“明代文学(第一暧昧期)”之第八节“明之新文学——曲、制艺、小说”部分,不但将曲体、小说这两种为当代学者首肯的“纯文学”,与从明清以来就备受争议,而大多数现代学者也认为不适合作为文学史内容的八股文这一“应用文体”并列,还选录了明代7位作者的18首散曲,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开拓精神。然而,该书印数很少,坊间不见流行,因此,黄人《中国文学史》将明散曲列为叙述对象,虽开风气之先,但是否对后来的文学史编写产生过实际影响,却可存疑。
这三种“中国文学史”是草创时期的代表作,撰写时间、问世年代虽有先后,但都曾被卷入所谓“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之争”*王水照:《国人自撰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学术史启示》,载《中国文化》2008年第1期,第54~63页。,因此,它们对于明散曲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看,也代表了“中国文学史”草创时期彷徨于新、旧之间的第一代文学史史家的立场,而明散曲在“中国文学史”类著述中“犹抱琵琶”式的初度登场,更反映了第一代文学史家“文学”观念的艰难转型。考虑到这一时期明代散曲的文献整理基本上还处于空白,在文献材料和理论基础均很薄弱的背景下,第一代“中国文学史”著作对于明散曲的忽视乃至无视,其实又有情可原。
相形之下,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古乐曲教授”的吴梅的《中国文学史》*吴梅:《中国文学史》,载《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陈平原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所据底本是吴梅为北大文科国文门三年级准备的石印讲义。则籍籍无名。就在这部“掐头去尾”——包括唐代文学总论、宋元文学总论和明代文学总论三部分——的讲义中,吴梅用了四五百字来描述明代散曲的概貌,这大概是“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对明散曲论述得最为系统、完整的文字了。吴氏之作本为课堂讲义,未见正式出版、发行,不但几乎被后人遗忘,他本人似乎也要“刻意抹去”*陈平原:《不该被遗忘的“文学史”——关于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藏吴梅〈中国文学史〉》,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75页。,然而,考虑到吴梅早年与黄人的密切关系以及他这种《中国文学史》的相关论述与他此前《顾曲麈谈》、此后《中国戏曲概论》之间若即若离、互有详略的关系,这部著作对于现代散曲学的兴起而言,其实更具象征意义。
二、 群体突破:1919-1949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念很快压倒了传统的“杂文学”观念,并渗透到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中。1923年前后,凌独见、胡怀琛、谭正璧等人的文学史著作相继问世,明确标举“纯文学”的概念,更有甚者,直接以“纯文学史”标目,如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金受申《中国纯文学史》等。此后,各种断代文学史、分体文学史等如雨后春笋般涌出。
由于“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等等观念的广泛流播和广为接受(尽管关于其内涵和外延,向未达成共识),散曲文学的研究有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出现了一批研究者,如吴梅、郑振铎、赵景深、卢前、任中敏、傅惜华等,他们既是曲学的热好者,也在新文学或旧文学的领域内声名卓著,这大大提高了曲学的关注度;其二,大量散曲文献被整理、刊刻,如任中敏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卢前的《饮虹簃所刻曲》、《校印清人散曲二十种》《明代妇人散曲集》等等,为散曲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其三,出现了一批专门的散曲论著,如任讷《散曲概论》、卢前《散曲史》及《饮虹曲话》、梁乙真《元明散曲小史》等,不但对散曲进行了“史”的梳理,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框架或具体论断。
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依然对明代散曲表现出很多的漠视。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黄山书社1986年。统计,这一时期的文学通史著作有近百部,而为“明代散曲”列目的,却仅有9部,比例之低,耐人寻味。
事实上,随着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念以及整个学术语境的变化,整个学界“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文体分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诗、词、文、赋、戏曲、小说这些更符合“纯文学”观念的文体,构成了该时期文学史著作的主体。又由于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先秦诸子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各家文学史著述中的地位,被极大地凸显出来。因此,尽管曲体文学之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不可或缺,已经得到了较多的认同,但明散曲作为踵武元散曲之后的创作,尽管数量众多,它在有明一代的文学乃至整个明清文学中究竟居于何地位、有什么价值,却依然是疑问。
分析这9部为明代散曲留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6部著作的作者,曾经有从事曲学研究的背景,即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和《中国文学史大纲》、梁乙真的《中国文学史话》、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史新编》、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显然,将明散曲写入“中国文学史”,还只是一个人数相当有限的文学史家群体试图突破时俗观念的拘囿而做的一种努力。因此,我们注意到,这些写入明散曲的文学史著作,往往也别出新意,或是叙述对象上有作者独特的考虑,或是体现出某种不同流俗的文学观念。
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他书所未述及的,如戏文、诸宫调、变文、散曲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郑氏也给予了明代散曲大量的篇幅,对明散曲的发展历程作了阶段性分析,对各个阶段的代表性散曲家及其作品作了探讨,其中有许多曲家如杨循吉、王阳明、夏言,是前代的文学史从未提及的。作者还对《南词韵选》、《吴骚集》、《吴骚二集》及《南北宫词纪》所收作家及作品,作了分析、考证,列入其“参考书目”中的一些散曲集及散曲选本更为一般的文学史家们所忽略,这不但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明散曲提供了参考,也客观地展现了明代散曲的繁荣。
郑振铎是现代学术史上从事通俗文学研究的巨擘,他广泛搜寻、收藏通俗文学文献,常常为某一部通俗作品的发现而雀跃,甚而喜极而泣,同时也为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缺失而感到遗憾。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如是说:
如今还不曾有过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的呢。……不必说是那些新发见的与未被人注意着的文体了,即为元、明文学的主干的戏曲与小说,以及散曲的令套,他们又何尝曾注意及之呢?即偶然叙及之的,也只是以一二章节的篇页,草草了之。每每都是大张旗鼓的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难道几篇无灵魂的随意写作的诗与散文,不妨涂抹了文学史上的好几十页的白纸,而那许多曾经打动了无量数平民的内心,使之歌,使之泣,使之称心的笑乐的真实的名著,反不得与之争数十百行的篇页么?这是使我发愿要写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的重要原因。*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第1~2页。
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郑振铎先生的这一番表白显然主观性很强,似乎缺乏文学史书写者或许有必要先“预存”的一种冷静与客观,但另一方面,这种强烈的主观性,其实又是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平民文学”观念的自觉传承与发扬,更从一个角度凸显了当时中国文学史编写的一个普遍问题——重视正统文体而忽略通俗文体。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所谓“纯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但如何在各类“纯文学”领域内处理不同朝代、不同文体形态的创作,史家们依然在探索之中。对比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径直将散曲视为元明清三代诗歌的主流,宋以后只论散曲而摒弃诗、词,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反倒显示出另一份的客观与冷静了。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甚至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该书上卷成书于1939年,出版于1941年,下卷成书于1943年,1949年1月出版。作者深受西方进化论和文学社会学的影响,如认为文学史家的任务,在于叙述文学进化的过程与状态,又说“特别要注意到每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特色,和造成这种思潮的政治状态、社会生活、学术思想以及其它种种环境与当代文学所发生的联系和影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自序》第1页。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以社会文化为背景,以文学的进化为主线”*魏崇新、王同坤:《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西苑出版社2000年,第6页。正是这部文学史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明显的方法论预设,既体现为整部书的框架设计,也反馈于具体文学现象的论述,如在论述明代散曲时,作者将其纳入南曲、北曲两大分野之中加以考察,在分析南、北方的曲家及作品时,注意结合曲家的仕宦状态、文学思想及时代思潮等因素来阐释其内容、风格,这不但弥补了绝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中明散曲的空白,也为进一步探讨明代散曲之于整个文学史的地位、价值提供了基础。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解放以后曾三次修订,影响至为深远,甚至波及两岸对峙时代的台湾地区,因此,刘著的文体分布及其影响都值得作更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三、 片面阐释: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中国文学史”被纳入了新的教育制度和知识生产系统之中,由过去的“私人著述”、“市场选择”而转变为了“集体编写”、“体制决定”,观其体例和内容,也更多地由“彰显个性”的学术著作,而变为面对特定人群的“讲究共识”的教科书了。
1956年1月,高教部发布《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办法》,规定一般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材分别由高教部、教育部组织编写,然而在随后的“大跃进”风暴中,出现了两部名义上由大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即1958年问世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它们都强调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来研究文学史、作家及作品,故在论及明代散曲时,只追问诸如是否描写现实生活、是否运用了人民大众的语言、是否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是否批判统治阶级等,而几乎完全忽视其它问题。
到了1961年,为了应对“大跃进”所导致的文科教材危机,中宣部和高教部联合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三种“中国文学史”方面的全国性教材,即游国恩等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的修订版《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次会议其实标志着我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初创*傅颐:《“大跃进”前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眸——兼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初创》,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8期,第71页。,意义重大,时至今日,这三种“中国文学史”依然留有盛名,并持续发挥着影响,1990年代以来的“重写文学史”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史为参照对象的。
发掘古代文学的“人民性”,是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任务,也成为了这一代文学史的主要特征。因此,那些表现民众疾苦、揭露统治者、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以及那些与民间艺术形式有着渊源关系,或是积极向民间艺术学习的艺术形式,获得了文学史家们的重视,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刘著虽成形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且为个人撰述,但几度改写后,已经非常符合新社会的意识形态了。此处存而不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部分的第四章,单列一节论述“成化至隆庆时期”的散曲,肯定了明代散曲在数量上的繁盛,又认为明散曲在内容上“远远落在传奇之后”,其艺术风格亦“比不上元代”,这就从整体上对明散曲的价值作了否定;在具体分析时,亦多称赞一些“批判封建统治阶级及社会寄生虫”和“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897~901页。,很少关注明散曲的语言、意境等文学性特征。游国恩等人编著《中国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的第九章“明代散曲和民歌”中,将元明散曲进行比较,否定了明中叶以前的散曲作品,认为:“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部分在统治集团内部遭到排挤的作家面对现实写出了一些较有批判意义的散曲。”*游国恩:《中国文学史》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145页。
大体而言,明代散曲之所以被写入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并不是因为编写者们意识到了明代散曲在文学性、艺术性方面的独特价值,而是因为编写者们注意到一些明代散曲受到小曲(民歌)的影响,一些作品比较贴近民众生活,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能够折射出“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影响。
四、 探索争鸣:新时期以来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可谓日新月异,很多著作既是作为传授共识的教科书来编写的,也对学界的前言性研究作了综合或取舍,甚至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创见。特别是19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探讨以来,“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内容、体例和文风上,日益呈现出多方探索的格局。就明代散曲研究而言,上个世纪90年代也是大丰收时期,《全明散曲》出版以后,明散曲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反馈于各种文学史著述中,有关明散曲的书写总体而言,不但更为客观,且往往能推陈出新,呈现出争鸣的态势。由于明散曲研究总体而言是一个相对冷寂的学术领域,“中国文学史”类著作尤其是某些声名显赫、影响广泛的著作,是否重视明散曲、又是如何论述的,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界明代散曲研究的基本态势。
以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和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这是新时期以来最具影响的两部文学史。前者注意到明代散曲曲家、作品及曲论数量的庞大,认为明散曲整体受制于元散曲,成就有限,但也肯定了一些名家的优秀之作在发掘新的生活内容、深入表现人情世态等方面的发展。关于明散曲的发展,该书分为明前期、弘正年间、嘉靖前后、晚明四个阶段,然而,对比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明散曲分为明初、弘治正德年间、嘉靖以后三个时段,显示出很大的不同,值得关注。一种文体及其相关创作的划段分期,往往成为一个领域内相关研究的基础,具有“纲举目张”的统领作用,明散曲亦然,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这不仅对明散曲史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明代思想文化之于文学的影响,以及对相关文体发展演变的研究等,也具有一定启发作用。”*赵义山:《明散曲发展历程之重新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168页。
相比于划断分期,如何判断明散曲作为一代之文学现象其整体的价值、地位,更严重地影响到了各类文学史著述中明代散曲的位置。与绝大多数研究不同,郭英德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认为明散曲不但在数量方面超过元代,而且思想内容、艺术成就“亦足可方驾元人”*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页。。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该书进而分析了“一般人”印象中明散曲不及元散曲的两点原因,窃以为可移用过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文学史”著作常常偏爱元散曲而“歧视”明散曲,兹录如下:
一是元代诗词文皆不足称,而曲学特盛,故以曲为元代文学的代表样式,早成定论,所谓“唐诗、宋词、元曲”,真可谓妇孺皆知,约定俗成,几乎牢不可破了;二是从文体发展周期来看,青春期一过,后起者便难争衡,纵使后出转精,也难以引起读者的青睐了。*郭英德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明代卷》,第48页。
事实上,明散曲的地位和价值向来是在与元代散曲的比较中得以确立的。元、明散曲的优劣得失,或许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然而就曲家、作品数量而言,明代比元、清都要繁富,这显示出该文体在当时整个文学生产领域内的重要性;就题材而言,明代散曲相比元散曲有较大的拓展,这显示出该文体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就艺术形式而言,明代散曲出现了大量的南曲、南北合套和“集曲”,这显示出该文体自身的精微嬗变。因此,不管是关注文体发展的连续性,还是回归文学史的“原生态”,重视明代散曲都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遗憾的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对于明散曲的这些“别样风景”的关注,总体而言,落后于散曲专门研究者的探索。
五、 几点思考
何为“文学史”、“文学史”又该如何书写,学人的相关研究早已浩如烟海,本文不能深论;至于“中国文学史”类著作中应该如何处理各类文体比重的问题,相关探讨则较为薄弱,尤其缺乏针对具体文体分布情形的细密考察。事实上,任何“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在“一代有一代文学”观念的绾摄之下,文学史史家对不同时代之不同文体的取舍,便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或许就成为旁观者訾议的所谓“缺憾”了。
我们注意到,某种文体的创作者、创作数量与文学史书写篇幅“不成比例”的现象,并非明代散曲所独有;而且,除了像明散曲的这种数量庞大而书写篇幅极小的情况,也有反过来,数量极少而书写篇幅较长的现象。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流行的纯文学观,仅以小说、戏曲和少量的诗文流派来建构明代文学史,难免留下很多断层。大量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学史景观被忽略掉了,或视而不见。要想填补这些文学史的断层,仅凭推断和想象是不够的,而应尽可能地走近历史,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重返文学史现场也许只是一种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大量丰富的文学史细节和文学史景观,置之不理。”*陈文新、郭皓政:《明代状元别集文体分布情形考论》,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第60~61页。确乎真知灼见!这里主要是因“科举文体”的问题而引发的议论,其实,无论从哪种严苛的立场出发,要否认明散曲“纯文学”的性质,恐怕都是有困难的,因此,不能充分发掘明散曲之于整个明代文学生态的意义,未尝不是我国“中国文学史”类著述亟待弥补的一种缺憾。
之所以产生诸如此类的“文学史现场”与“文学史书写”的反差,除了文学史史家的文学观念、文学史理念以及学术语境等原因,或许也可从该文体自身的批评史、学术史那里,找到某些缘由。以散曲为例,明代散曲尽管多有新变,然而,自明中叶以来就“活”在元散曲的阴影之中,如李开先、王骥德、凌濛初等大家都极力推崇元散曲,其影响所及,便是晚近以来的散曲选本、文学史大多偏爱元散曲。然而,明人之推崇元曲,乃至整个明代曲学的复古倾向,其实另有“尊体”的深意*程芸:《明代曲学复古与元曲的经典化》,载《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1期,第163~168页。,并非只是对元、明二代散曲创作优劣的评骘,不能够成为今天的文学史可以忽略明散曲的有力论据。况且,今天的文学史书写固然应关注明代具体散曲作品的文学性、艺术价值,也更有必要挖掘明散曲作为一种整体现象所蕴含的更为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一方面明代散曲(乃至清代和近代散曲)的艺术成就、文学史地位固然仍有必要放到传统曲学的价值体系中加以估衡,另一方面,还需要纳入更开放的文学史理念中,加以重新的评判。
“中国文学史”著作跳出“一代之有一代文学”叙述范型的拘囿,虽是老生常谈,亦为当下之急。有理由相信,随着《全明散曲》之外更多明代散曲作品的发现*叶晔:《冯敏効〈小有亭集〉及其生平考略——兼补〈全明散曲〉48小令4套数》,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第66~71页;叶晔:《论李应策散曲及其散曲史意义》,载《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第79~89页;刘英波:《明代散曲家考补及曲作辑佚》,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年第4期,第54~56页;欧阳春勇:《〈全明散曲〉补遗——〈洗心亭诗余〉中的散曲》,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年第1期,第67~72页;汪超宏:《〈全明散曲〉补辑》,载《明清曲家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1~532页。,以及学人对其他明代文体(如词、骈文、辞赋、八股文等)研究的深入,明散曲所关联着的明代文学生态、“文学史现场”之多样性与复杂性,将在“中国文学史”类著述中得到更全面而合理的呈现。
●作者地址:程芸,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chengyunwuhan@163.com。
李艳华,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基金项目:2013年湖北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研究项目(2013006);武汉大学70后学者学术发展计划
●责任编辑:何坤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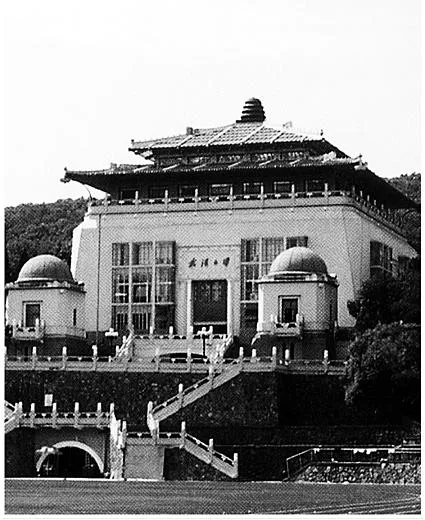
DOI:10.14086/j.cnki.wujhs.2015.06.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