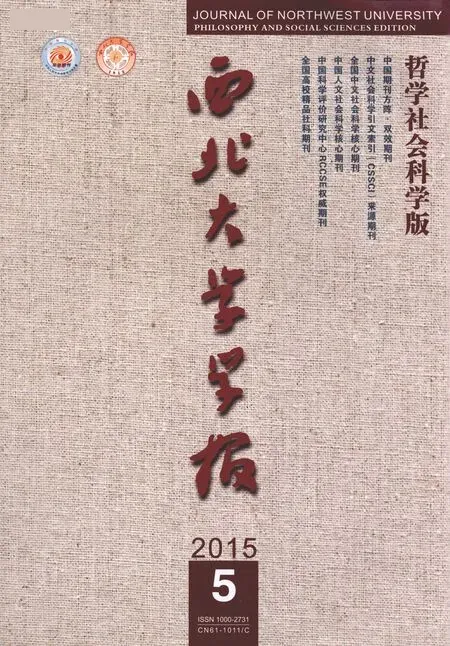论郑玄“仲春婚月说”解《诗》之未妥
魏启峰(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论郑玄“仲春婚月说”解《诗》之未妥
魏启峰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郑玄在有关《诗经》中《国风》和《小雅》九篇作品的笺释中屡申“仲春之月嫁娶”说。征诸文本语义,这些诗多与嫁娶无关,故其解未妥。郑说失当之成因有三:第一,对《周礼·地官·媒氏》的误读;第二,对阴阳学说的不当运用;第三,毛传“秋冬结婚”说的诱导。
关键词:郑玄;诗经;“仲春婚月说”;误读
东汉学者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兼通今文、古文经学,毕生孜孜矻矻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以解释儒家典籍的方式参与当时主流文化的构建,为汉代经学集大成者,受到了当世和后世的尊敬。编辑、订正、注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作《毛诗笺》,是郑玄治学成就的重要体现。
对这样一位卓然大家,后人怀着景仰之情研读其著述,为其深厚的学养和推陈出新的慧心所打动。但作为当代读者,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读其书,知其世;从其正,辨其误,不可全然为前贤说法所蔽。比如郑玄在《诗经》的《国风》和《小雅》九首诗笺中,屡言“仲春之月嫁娶”,似乎是说,男女在仲春之月结婚,是《诗经》时代的一个规定。事实是否如此,窃以为颇有可商榷处。
为了讨论之方便,本文将郑玄看法称为“仲春婚月说”。重新研读《诗经》文本,分析相关诗句后可以发现,以“仲春婚月说”解诗是未必确当的。
一、郑笺“仲春婚月说”之表述及所涉《诗》句解读
《召南·行露》第一章:“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郑笺:“厌浥然湿,道中始有露,谓二月中嫁取时也。言我岂不知当早夜成昏礼与?谓道中之露大多,故不行耳。今强暴之男,以此多露之时,礼不足而强来,不度时之可否,故云然。周礼: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行事必以昏昕。”郑笺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引自《周礼·地官·媒氏》,“行事必以昏昕”引自《仪礼·士婚礼》。
郑玄对《礼》研究精到,厥功甚伟,为古今学者所称道。但郑笺于此将诗句之“厌浥行露”与礼文“仲春之月”联系起来;将诗句“岂不夙夜”之“夙夜”与礼文“行事必以昏昕”之“昏昕”联系起来,以“夙”对“昕”,“夜”对“昏”,其对应看似有理,实则未必然。对这三句诗,郑玄之前的毛传指之为“兴”。郑玄之后的孔颖达疏:“毛以为厌浥然而湿,道中有露之时,行人岂不欲早夜而行也?有是可以早夜而行之道,所以不行者,以为道中之露多,惧早夜之濡己,故不行耳。以兴彊暴之男,今来求己,我岂不欲与汝为室家乎?有是欲与汝为室家之道,所以不为者,室家之礼不足,惧违礼之污身,故不为耳。以行人之惧露,喻贞女之畏礼。”[1](P80)毛传解诗时,将有的诗句标为“兴”,指出诗的表达法是其成就之一[2](P1333)。但何为“兴”?后世学者却有异见,南宋朱熹就认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3](P2)。笔者认为孔、朱两家之说都有道理,不可偏废。孔探后文而说,落实了兴句的涵意;朱就兴句在篇章中的位置而言,强调其修辞作用。既然置于篇章中,此兴句的含义虽不必如孔所说,却一定是有意义的。不论对“兴”的认识如何,毛传以为这三句是“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既然是兴,那就不必非得如郑笺那般以《礼》文说之,将兴句的“行露”一定要对应为“二月”。综观《行露》全诗,属比兴体,共三章,第一章是兴,后两章是比。第二章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第三章曰:“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首章以“行露”兴,二、三章以“雀”“鼠”比,加以“室家不足”“亦不女从”之句,女主人公拒婚之意毕现。就诗旨而言,当是一首拒婚诗。
《召南·摽有梅》第一章:“摽有梅,其实七兮。”毛传:“兴也。”郑笺:“兴者,梅实尚余七未落,喻始衰也。谓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则衰。”郑笺虽同意“摽有梅,其实七兮”是兴,但从其解释兴义“春盛而不嫁,至夏则衰”可以知道,他是根据《周礼》“仲春之月会男女”为说的。《摽有梅》是一首短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为了探求诗旨,不妨全部引出。首章三、四句:“求我庶士,迨其吉兮。”第二章:“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末章云:“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总体上看,这是一首女子急嫁之诗。以梅子熟落兴女子急于嫁人而不可暂缓的心情:梅子在树未落者始则“七”,继则“三”,终则全部落光,“顷筐塈之”。召南地区梅熟的季节在夏季,这位女子触景生情,发而成咏,读者正可以从梅子熟落的历程体味她情感的发展。笺以《礼》“仲春之月”说“摽有梅”,“仲春之月”即二月,那时还没有进入梅熟季节,其“务虚”不“务实”的倾向昭然。
《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郑笺:“有贞女思仲春以礼与男会,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时无礼而言然。”对于“有女怀春”,郑笺解为“有贞女思仲春以礼与男会”,仍是以《礼》文为据。而毛传释为:“怀,思也。春,不暇待秋也。诱,导也。”以秋冬为婚期,“有女怀春”意为有女子想着春天结婚。两家所解之不同在于:毛传谓女子想着春天就结婚,等不到他所认为一般用为婚期的秋冬季;郑笺谓女子思仲春与男会,诗句之“春”为仲春,符合其所谓《礼》规定的婚期。朱熹则解“怀春”:“当春而有怀也。”[3](16)只是直解,而未涉及婚期之说,但更为可取。古人有“女悲春,士悲秋”之说,女子怀春是一种因自然时令变化而发生的情感,不必硬与婚期拉扯到一起。
《邶风·匏有苦叶》第三章:“士如归妻,迨冰未泮。”郑笺:“归妻,使之来归于己,谓请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以昏矣。”以为这两句诗是说,士如果要行请期礼,就得赶在“冰未泮”的正月中以前,这样就可以在仲春二月办婚礼了。其说对婚事进程的规划不可谓不周到,对诗中女子心理的揣摩亦不可谓不细致。但果真那位女子就是这样想的吗?看看前后文。第三章共四句,前两句云:“雍雍鸣雁,旭日始旦。”郑笺:“雁者阴,随阳而处,似妇人从夫,故昏礼用焉。自纳采至请期用昕,亲迎用昏。”这还是以《仪礼·士婚礼》为依据所作的解释。笔者把这四句诗放到一起细细体味,觉得表达了一个与“时间”有关的意思:“雍雍鸣雁,旭日始旦”,表达重心在“旭日始旦”,雁鸣的时间在清早,以一天的时间长度作为参照,雁鸣得很早。“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表达重心也在后句“迨冰未泮”,盖结婚之期宜早,应赶在冰泮之前。婚礼用雁,郑笺解释了所以用雁的文化涵义———“随阳”,当然是对的,不过只适用于注《礼》,解诗时却要考虑具体语境。一则《诗》之作,至晚在春秋时,而《仪礼》成书晚到战国;二则一种思想之兴起与流行,有特定的历史确定性,不可拿后代之思想简单推想前代人之意识;三则一物之用,在此处与彼处可以不同,如同样是“雁”,用于诗和用于礼,因主体视角不同而意义有所不同。《匏有苦叶》全诗四章皆为女辞。此章女子以雁在“旭日始旦”的清早而鸣,兴起下二句“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表面似为“士”着想,实将自己急于嫁人之意,表达得至为直白。《诗》的时代,人们以歌达意,无所拘牵,有似天籁,所以孔子曾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4](15)试看看今之流行歌曲,有的歌词唯恐情意不显,极尽张皇之能事。凡开放时代,不论古今,情歌中适度的表达,实为人性正常情感的释放,都可以成为好的作品。
《郑风·野有蔓草》第一章:“野有蔓草,零露漙兮。”郑笺:“蔓草而有露,谓仲春之时,草始生,霜为露也。《周礼》: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根据郑玄对《周礼》这句话的解释,“令会男女”之“会”也应是结婚的意思,即郑笺所谓“嫁娶”。对不对呢?原诗接下来写道:“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毛传:“邂逅,不期而会,适其时愿。”以“不期而会”解“邂逅”,可谓得诗句之本意。毛传之“会”义,显然与郑笺“嫁娶”义不同。那么,这首诗写的是一次“会”,即诗所谓“遇”,郑笺“嫁娶”之“会”不可从。
《唐风·绸缪》小序:“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郑笺:“不得其时,谓不及仲春之月。”此诗第一章:“绸缪束薪,三星在天。”郑笺:“三星,谓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妇父子之象,又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焉。昏而心星不见,嫁娶之时也。今我束薪于野,乃见其在天,则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见于东方矣,故云‘不得其时’。”意为“三星”是心星,“三星在天”即心星见于东方,则是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这样的月份结婚,而不在仲春的二月,是不得其时,所以此作为“刺”诗。郑笺指“三星”为“心星”,以此为解释重点展开主观性言说。“三星”到底是什么星,毛传就有异说,认为指的是“参”星。但异中有同,二家都以星象对应时令,意在评论在此时令结婚的宜与不宜。换一下眼光,从文本出发重新审视此诗意蕴,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过分在意于“三星”具体所指,因为诗接着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皆为欢娱之辞,洋溢着无比喜悦之情,称对方为“良人”,结合古人举行婚礼在昏时的定说,可以认为此诗是在咏新婚,是一首美诗而非刺诗。诗中的男女是在几月份结婚的呢?依郑笺之说,也不在“仲春之月”。
《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毛传:“兴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郑笺:“杨叶牂牂,三月中也。兴者,喻时晚也,失仲春之月。”对此二句的解释,还是从婚期着眼定下调子,只是对毛传的婚季“秋冬”说作了修正,改为“仲春”。就诗作本身而言,这两句的信息有二:地点在“东门”;季节是暮春或初夏。毛郑两家热衷于挖掘诗句背后的意蕴,对本来显而易见的表面意思不屑置辞。《东门之杨》是《国风》中的短章,全诗共两章,每章四句。首二句之后,第三、四句云:“昏以为期,明星煌煌。”毛传:“期而不至也。”郑笺:“亲迎之礼以昏时,女留他色,不时行,乃至大星煌煌然。”“昏以为期”与“明星煌煌”两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毛传以为是转折关系,在解说中以“而”字表明,郑笺同意毛传之说,只是一简洁、一详赡而已。其实这两句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顺承或平列的:“昏以为期”是叙述,直接说出了时间背景;“明星煌煌”是描写,“明星”即启明星,“煌煌”为重言状态词。西方阐释学认为,一件作品成就之后,对它的阐释是开放的,随时而异,因人不同[5](3)。对这两句诗,也可以发挥赏读者的主体性而视为一首情诗,认为写的是男女约会时的情景。“昏以为期”之“期”,毛传、郑笺都解为“婚期”,我们释作“会期”,即约会之期。这首诗写了一次成功的约会,但以写景言之,含而不露,正符合中国诗论中的“情景合一”说。
《豳风·东山》:“仓庚于飞,熠燿其羽。”郑笺:“仓庚仲春而鸣,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显明也。归士始行之时,新合昏礼,今还,故极序其情以乐之。”《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6](550-552)根据《月令》对物候的记载,加上这两句之前有“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零雨”也是农历二月的天气特征,可以证明周公东征是在当年的仲春得胜西归的,此可为以诗证史之佳例。郑笺的说解,有对也有错:“仓庚仲春而鸣”说得对,但说这位战士结婚于三年之前的仲春,则未必有据;“熠燿其羽,羽显明也”才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后面两句是:“之子于归,皇驳其马。”西归的士兵在路上看到仓庚展翅露出的“显明”之羽,想起了他在家里的妻子刚嫁来时拉车的马儿“皇驳”亮丽———这将归士“勿士行枚”的喜悦之情刻划得多么传神而真切!《诗》之所以感人,于斯可见。两千年之后,我们还不禁为郑公此处体物之细、解诗之妙而击节赞叹。
《小雅·我行其野》第一章:“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郑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仲春之时,嫁取之月。妇之父,婿之父,相谓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岂其无礼来乎!责之也。”这首诗共三章,每章六句。首章最后两句云:“尔不我畜,复我邦家。”《我行其野》为弃妇诗,古今无异说。既然是弃妇所作,将“我行其野,蔽芾其樗”看作写当下情景,更为自然。妇人因丈夫“求尔新特”而被逐出家门,返回娘家,步履蹒跚,心情落寞,意绪萧然,借写景而出之,以乐景衬托出内心的悲哀。郑笺以为“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是弃妇回忆以往出嫁来时路途所见景物。“仲春”而“蔽芾其樗”,似乎也合理,但细加体味,设身处地为女主人公着想,则郑说未免隔了一层。就诗言诗,我们的看法与笺说之不同有二:就时间来说,这两句是指当下而言而非回忆从前;就表达功能来说,是表情而非达礼。此章中二句为责难,末二句道原因,都是直陈之辞,这是显而易见无需多说的。
二、郑笺“仲春婚月说”之成因
《诗经》郑笺中屡屡主张“仲春婚月说”,盖有三因,分述如下。
(一)对《周礼·地官·媒氏》的误读
对于上举《国风》《小雅》中九首诗中的相关诗句,郑玄都以仲春为婚月的观点予以解释。郑氏这种观点来自《周礼》。在给其中的两首诗作笺时,引了《周礼》的有关文句,其余七首诗无必要再引,只是根据自己的成见说诗。兹分析《周礼》文句所含的意思。
《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7](509-514)
细读此段,“媒氏,掌万民之判”是一个主题句,意为媒氏管万民的判合。由下文看,这个“万民”包括范围很广:有正常婚龄的“男”“女”,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的“男女”,有已经死了的男女,有“阴讼”的“男女”。可以看出,对婚龄的管理是媒氏职责的重点。所谓“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应将“男三十”“女二十”理解为男女嫁娶正常年龄的上限,意思是男子二十岁加冠[6](P64、1884),女子十五岁及笄[6](P1014),就算成年人,可以结婚了,从这时起到二十岁、三十岁这个年龄段,是适于结婚的时期。之所以有此规定,与古时生产力低下、依靠人力生产和打仗有关,因而重视人口繁衍。但对婚期安排在一年中哪个季节或月份,并没有事实上亦不必有硬性规定。“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应看作一个语意群,涉及当时针对超过婚龄的男女做出的一个规定———限定在“仲春之月”,时段集中,由媒氏主持,让超龄“男女”相会。此为硬性的义务,男女无正当理由不“会”,则要受“罚”。男无“家”、女无“夫”者都得“会”。目的是什么呢?亦须联系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状况才能理解:促进人民蕃育故也。史载孔子“野合而生”[8](1537),后人不解,以为于圣人是不名誉之事,其实正合于当时的礼。此“野合”即孔子之父叔梁纥和颜氏之女对“仲春之月,令会男女”的响应。而从另一方面看,亦可说官方对人性的需求考虑得颇为周到,用孟子的话说,算得上“仁政”了:在“仲春之月”天地阴阳二气相会之时,作为三才之一的人宜乎顺时而动,这符合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
从《周礼》对于“媒氏”职能的说明看,并无“婚月”的定制。“仲春之月,令会男女”面向的是过了最佳婚龄的男女,他们与占主体的适龄男女相较,毕竟是少数。郑玄之“仲春之月嫁娶”将“以会男女”之“会”理解为“嫁娶”,把专施之于超龄男女的“会”扩大到全部婚龄男女,乃是由乎误读《周礼》而致以偏概全、以权为经的主观之论。如上节所析,《诗经》中被郑玄解为“仲春之月嫁娶”的诗句,其实多与“嫁娶”无关。
(二)对阴阳学说的不当运用
《邶风·匏有苦叶》第一章:“匏有苦叶,济有深涉。”郑笺:“瓠叶苦而渡处深,谓八月之时,阴阳交会,始可以为婚礼,纳采、问名。”此处“为婚礼”的意思是为婚事进行一系列规定的礼节,具体指“纳采”“问名”两项。结合上引此诗第三章“士如归妻,迨冰未泮”的郑笺,可对其说有更为完整的了解:在八月行纳采、问名之礼,赶在来年正月中以前请期,就可以在下年的二月举办婚礼。
对于上引《周礼·地官·媒士》一段文字,郑玄注其中“(媒士)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曰:“仲春,阴阳交,以成婚礼,顺天时也。”[7](P511)
可以看出,郑玄无论注《礼》还是笺《诗》,都贯彻着阴阳思想,而且努力使体现人伦大端、合二姓之好的婚礼程序化,汲汲为之立法。当然其中有些说法是成立的,如谓八月、中春是阴阳交会的时期,虽然用了中国传统哲学术语,今人凭经验亦可以理解:农历八月气温转冷,仲春二月气温回升,这两个月份是天气变化的关节处。但将这种思想与诗硬性联系起来,却是不妥的。仍以此诗为例。《邶风·匏有苦叶》是《国风》中一首有趣的诗,作者当是一位女性。第二章云:“有氵弥济盈,有鷕雉鸣。济盈不濡轨,雉鸣求其牡。”其中首句、次句、第四句措意甚明,而对于第三句,以笔者所览,未见有发其意蕴者。试为之解:此句是一个反问句,承首句“有氵弥济盈”而来,可译为:渡口水满了不会湿了车轨吗?当然会湿着的。作者用的是隐喻思维———水喻男,轨喻女,用水触车轨喻男女相与。水湿车轨是已然(车正在水中,女诗人在渡口亲见者),雌雉鸣叫求雄雉是未然(还没有求到,只是听见者)。诗人用两个鲜活的比喻,道出了她的心曲。诗之语言微妙如此,还用得着搬来“阴阳”那一套高深的、那位作诗的女子不知道为何物的抽象概念吗?
(三)毛传“秋冬结婚”之说的诱导
《召南·野有死麕》:“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毛传:“怀,思也。春,不暇待秋也。”《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毛传:“兴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显然,毛传以秋冬为结婚季节。在《诗》的时代,婚礼是否一定举行于秋冬季节,甚至上引诗是否一定关涉婚事,都可能是另一回事。但既然毛传已有了婚季说,后起的郑玄便吸收了这种说法,只是对婚季在哪个月份有所修正而已。郑玄在笺诗之前已注过三《礼》,依据对《周礼·地官·媒氏》的理解,成就了自己的“仲春婚月说”,故在笺诗时,不免扩张己意以框诗旨。既然从毛传起婚期已经成为说诗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郑玄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开掘,比毛亨走得更远。
三、余论
如上所论,郑玄在笺释《诗经》中九首诗的相关诗句时,引入了《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说解会诗旨,而其说并不妥当。以一种经典解释另一种经典,当然是可以的,但又是要冒风险的。原郑说之失,除了对《周礼》经文的曲解、以战国时代兴起的阴阳学说牵合诗句之外,还与他没有充分认识或不愿正视《诗》与《礼》是两种不同的书写有关。《诗》尤其是《风》《雅》中的婚恋诗,是精神生命律动之表达,歌咏的是喜怒哀乐感受。而《礼》则是对社会中人们行为的规范,目的是为了社会群体之和谐。虽今本《周礼》不是西周初期的语言,但其体现的精神与周公治国有关,却是毋庸置疑的。既然《诗》与《礼》是两种文体,服务于人类生活的不同领域,那么郑玄根据自己对《礼》“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之说的独特理解笺释丰富多彩的《诗》句,便不免有省事之嫌。“诗言志”是中国诗史上一个有名的命题,我们有必要通过细心研读《诗经》,体会隐藏在《诗经》文句中普通民众之“志”,而不是简单两句“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所能概括得了的。因此笔者不揣谫陋,对郑笺中涉及的《诗经》九篇作品的相关诗句重新解析如上。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郑笺呢?经典之释解,因时而不同,此已为中外学者所阐明。明代学者钟惺精辟地指出:“《诗》,活物也。”[9](P347)肯定了《诗经》解读的多样性。在当代,西方阐释学被引进,强调因时为释,这是可以理解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尝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同样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学术都是当代学术。正是由于当下现实提供的课题,才激活了沉睡的经典,使它们重获了生命。各个时代由于关注的问题不同,而有不同的学术新得。我们对于古代学者,当有如是观。
以上就郑玄笺《诗》的“仲春婚月说”做了几点检讨,以期就教方家。有一点须特为申说:郑玄治学勤奋,熟于经典,属辞疏句,苦心经营,其解诗诸说,在当时极多创见,属于学术史上的正能量。拙文没有一点贬低前贤的用心。
参考文献:
[1]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龚抗云、李传书、胡渐逵整理.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3]朱熹传,赵长征点校.诗集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何晏注,邢昺疏,朱汉民整理.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郑玄注,孔颖达正义,龚抗云整理.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郑玄注,贾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9]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责任编辑刘炜评]
【历史研究】
On the Inappropriate Explaination of the Book of Songs by Using the Speculation that Mid-Spring is Wedding Month
WEI Qi-f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127,China)
Abstract:Zheng Xuan put forward the speculation that mid-spring is wedding month when explaining the nine poems in Guo Feng and Xiao Ya of the Book of Songs.This thesis does a textual analysis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for the related chapters,and finds that these lines are not about marriage.Then it explores the causes of Zheng Xuan'speculation that mid-spring is wedding month.They are,first,the misreading of Mei Shi of Zhou Li Di Guan; second,the abuse of Yin-Yang Theory; and third,Mao Zhuan'speculation that autumn and winter are wedding quarters was an incentive to Zheng Xuan.
Key words:Zheng Xuan; Book of Songs; the speculation that mid-spring is wedding month; misreading
作者简介:魏启峰,男,甘肃通渭人,西北大学博士生,从事训诂学和经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5-003
中图分类号:K224.06;I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