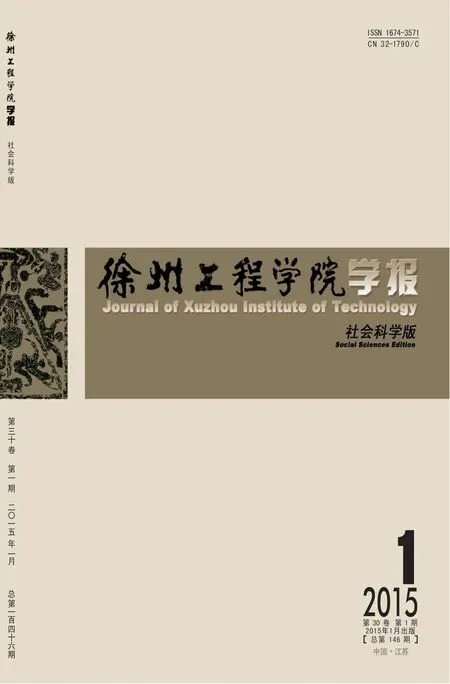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认同观
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认同观
陶国山,玄 博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 200241)
摘 要:晚近以来,传统的认同形式在主体身份破碎、流离的境况下逐渐被消解,人们开始面临各种“认同的危机”。英国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开展对认同的研究,他指出,文化认同是动态的,永远处于过程当中,就像一件随时都在生产,但是永远都没有完成、也不会完成的产品。因此,对文化认同的思考应该由传统的“我是谁”“我来自何方”转变为“我将会是什么样的”“我将要到何方”。这一转变对研究现代性流散、混杂的社会主体的文化认同具有较为深远的意义,也是我们探索现代性社会主体“文化认同”的一条重要路径。
关键词:斯图亚特·霍尔;后现代主体;文化认同;族裔散居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志码:A
收稿日期:2014-10-17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认同理论研究”(2011BWY0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文艺作品的阐释研究”(11YJC752019);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文艺思想研究”(13CZW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5批面上资助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陶国山(1974-),男,安徽天长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在职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理论、西方文论研究;玄博(1990-),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华东师范大学在读教育硕士,主要从事语文课程教学研究。
当代社会,全球化加速了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每个人都可能是移居者,在“故乡”与“第二故乡”,甚至是二者的混杂处徘徊。移居者主体的去中心化、内爆、认同的碎片化就像赛义德提到的后殖民语境下主体不断被流离一样。对自我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认同危机逐渐演化为一种群体性危机。每个人几乎都会有齐美尔所谓的那种“在内部又在外部”、“熟悉的陌生”的体验。这种看似地域上的差异实质是建立在文化差异的因素上的。1990年代中期,英国的开放大学以霍尔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围绕“文化认同”的主题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探讨了文化认同的各种问题,并对其提出质疑,引起了学界对文化认同问题的普遍关注。因为牙买加裔黑人的英国学者这种“两栖人”的独特身份,霍尔以自身经历而生发出对文化认同、族裔散居等问题的思考,将传统的对“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方”等追问转变为对“我们将会成为什么”的探索,为文化认同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理论资源。霍尔坦承自己“是以终生的文化研究为背景写作的”①Stuart Hall(1994):"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pora",in P.Williams and L.Chrisman,eds.,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London:Harvester Wheatsheaf)。,事实上,他也是公认的“当代文化研究之父”,他对文化认同理论的探讨正是在文化研究中展开的,后者本质上是一种针对现实的批评。在他看来,“(理论)其实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make it work for you)。我的朋友霍米·巴巴说他的工作就是生产理论,而我呢,则是运用理论。我不生产什么理论,就是运用”[1]。通过这种方式对文化认同理论的探究,不仅是对文化研究自身的一个突破性的贡献,也为当下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启示与支撑。
一、认同问题
霍尔对文化认同的研究经历了从对认同的思考逐渐转向对文化认同问题的重视。也即在对文化认同问题的思考中必然要对认同首先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尽管也有人认为是机器的出现推动了现代社会运动,但是,一般认为,是在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之间,开启了现代社会。“诞生了个人主义,现代催生了一种新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个人主义的形式,占据其中心位置的是一个叫做个人主体和它的认同这样一个概念。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前现代中没有个体的存在,而是在现代中它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被经历着、被概念化了。”①参见Stuart Hall,David Held,Don Hubert,Kenneth Thompson(1996),eds.,Modernity: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Cambridge,Mass:Blackwell)。这种现代的转变使个体从原来固定不变的,被人的身份、立场所遮蔽的传统和形式中解脱出来,是与过去的一种决裂。
然而,后现代主体再一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它正在被碎片化,不仅是与之前现代主体发展道路的疏远。更准确地说,它变成了一种混乱与错位,出现了霍尔所谓的主体“认同的危机”。在《谁需要“认同”》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认同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了一个研究领域,许多学科领域都一直对它进行解构拆析,因而由“身份有什么必要?谁会需要它?”这一问题展开论述,他提出了自己的认同理论问题。
在探讨是否有一个本质性认同的问题方面,霍尔认为,认同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一个策略性和定位性的概念。并且,关于这一理论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关于需要认知的主体理论,而是一个范围广阔、需要发散性实践的理论”②③转引自Stuart Hall(1996):"Who Needs Identity",in Stuart Hall and Paul du Gay,eds.,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Sage)。。从共识语言视角看,认同是一种建构,一个永远未完成的过程,它总是处于建构中,无所谓“是”与“不是”,想要完全融合实际上是幻想。借助德里达的一个概念,即认同是“异延的”,它不仅要承担自身建构过程中的活动,而且还要顾及“边界效果”的产生与互动,使外部事物内化进而再从内部改变过程的发展。因而,认同是一个缝合的过程,它是一种超定而非归类。从心理分析视角看,认同从一开始就是充满歧义的、矛盾的,例如弗洛伊德在恋母情结中提出的正反矛盾情感的共存,以及拉康认为儿童早期在“镜像阶段”对自我的认识就是从镜子中的“另一个”开始的。因此,认同是一种间际的关系,而非对传统中原初“我”的回归,相反,这种认同在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建构而成,有一定的未知性。因而,这时的认同是指向将来的。所以,霍尔提出探讨我们的认同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谁”“我们来自哪里”,不如说是“我们将会是什么”“我们将要去哪里”。
这一伟大转变针对的正是现代性的认同问题,它逆转了本质主义的概念,改变了所谓“自我身份”的含义。这样的认同是超越时间与历史而与“自我”保持一致的,即吉尔罗伊所谓的“变换中的同一”。其中,认同的具体形成过程则是通过差异与区别建立的,只有通过与另一方的关系、与非他的关系、与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的关系以及被称为它的外界构成的关系③,认同才能够被建立。所以说,“认同”是“主体”与“主体位置”的缝合,两方面都必须是“欢呼、质疑”对方的。因而,霍尔认为,认同是一个非本质性的概念,认同从前现代的一种主体到后现代社会在各种理论冲击下,人们因对自己是谁的不自信而被打破,进而呈现为多种去中心化的主体。
二、后现代主体的范式与认同
霍尔在《文化认同问题》中,参照了五种极具影响力的后现代主体理论,概述了“后现代五种去中心化的主体样式”④有关“五种后现代去中心化的主体观样式”的观点参见Stuart Hall,David Held,Don Hubert,Kenneth Thompson(1996),eds.,Modernity: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Cambridge,Mass:Blackwell)以及陶国山:《话语实践与认同建构———论文学话语下的认同建构》,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2012年9月,第39-44页。,并由此引发了对文化认同的思考。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表现为19世纪60年代那些被称为“西马”的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读与重新阐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西马结构主义学者阿尔都塞,他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人类创造了历史,但是,是在前人提供的基础条件上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独立创造的”,阐释为人类并不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他们只能够在原本存在的条件上作为。他把一系列社会关系(生产形式,劳动力剥削,资本回笼)等置于其理论的中心位置,而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关于人的观念。“马克思置换了现代哲学的两个关键的命题,即人的普遍本质以及具有真正主体的个体属性。”[2]40阿尔都塞则认为这两个命题是互补的、牢不可破的,但它们的存在和统一预示了一种理想的经验主义观点。通过拒绝使人成为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拒绝了这整个有机的命题系统。他不仅从政治、经济、历史、民族上,而且从哲学上对人进行了总结,他进而认为马克思这一观点是“反人文主义”的。阿尔都塞这一观点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了许多人类学理论的攻击,但是他的“理论化的反人文主义”确实在现代思想的许多流派上产生了重要的
影响,属于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的认同观的表现。
第二,“无意识主体观”,源于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发现。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身份、认同、性欲以及我们的欲望结构建立在精神和象征性的无意识加工过程中,它所依据的逻辑是一种“非理性”。它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代表的理性和一些固定、本质性的身份造成了“大破坏”,在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精神分析学者拉康指出,把自我形象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东西是婴儿需要逐渐、部分、艰难地学习才能形成的。它并不是在婴儿内部自行生长出来的,而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就像拉康在“镜像阶段”中所阐释的,自我形象是在“看”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中,孩子对父母的复杂情感,这些都是无意识的重要方面,它们使主体分裂。然而,尽管主体是分裂的,但是由于就像在镜像阶段中总是幻想自身是一个统一的“人”,它就在想象中经历了自身身份的被统一。
因此,身份实际是通过“无意识”过程形成的,并非与生俱来,它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总是在“过程”之中,总是在“被形成”中,关于它的同一通常是一种想象的结果。例如,男性自身的“女性”部分虽然不被承认,但是在成年后总是会以某种无意识的非理性方式表达出来。因此,与其说认同是一个完成的东西,不如把它当作一个进行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且认同绝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我们个人内部,而恰恰来自我们自身完整性中对它的缺失,它从外部“填充”我们,通过这些方法我们想象自己是被其他人看的。从精神分析学上看,我们之所以不断寻求“认同”,将自我不同的部分组合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想要获得这种“充满”幻想的乐趣。尽管无意识过程不易被检验,也不易通过心理分析技术来证明,但是它对关于主体和认同的思考产生了重大影响,破坏了传统理性的地位和对认同的稳固性想象。
第三,“语言学主体观”,这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有关。索绪尔认为,我们并不是自己的陈述或语言表达上任何绝对意义的“作者”,我们只有把自己置于语言规则和我们的文化系统下才能够用语言生产意义。语言是社会性的,而非个体的系统,它先于我们而存在。因而,我们不能成为任何一个甚至是极简单的意义的“作者”,说一种语言不仅是对我们内心想法的表达,它也是在激活那些已经存在于我们头脑深处的语言和文化系统的更广泛的意义。更进一步地说,词汇的意义并不是固定的与外界事物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产生于词汇间相似或不同的关系之中,就像我们说这是“晚上”,是因为它不是“白天”。相类似的,在身份认同中也有这样的关系。比如,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我知道了“我是谁,我不能是谁”。就像精神分析学的“无意识”一样,身份是像语言一样被建构出来的。此外,现代语言哲学家德里达,受索绪尔及“语言学转向”影响,认为无论一个人尽多大的努力,他也不可能最终使意义固定下来,这其中当然也包括身份的意义。而且,我们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会有“前”和“后”,那么,必然会有一个边缘的存在,这个边缘就是他者书写的地方了。所以,意义天生是不稳定的:它的目标是达到认同,但是中间总会不断地被差异性所打断。因而,它经常会从我们身边溜走,然后又会有新的含义补充进来,而且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它摧毁了我们要创造一个固定的、稳定的世界的企图。
第四,“权力主体观”,即福柯“现代主体的谱系学”中的主体立场。福柯发现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即在19世纪发展,于20世纪达到全盛的“训诫权力”(或规训权力)。训诫权力首先是对人种或人口的监视和管理,其次针对个体和身体。它的监控场所就是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那些机构,如工厂、军营、学校、监狱、医院等地方。训诫的目标是把人的生、死、活动、工作、痛苦以及个人的娱乐和他/她的精神以及身体上的健康、性欲甚至家庭生活都置于严格的规则与控制之下。让他们学习专业的知识,其基本目标就是要生产“一个温顺的身体”。在这种训诫制度下,个体性逐渐丧失。
第五,“新社会运动主体观”,这些运动包括学生动乱、反文化青少年运动、民权斗争、第三世界改革运动、女权主义运动等,它们都是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这个后现代的分水岭。这些运动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反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东方斯大林的集权主义,用怀疑的态度审视一切。每一个运动都有其支持者或对它的认同,比如女权主义运动吸引的是妇女,种族主义为黑人而斗争,反战主义要求和平等等。因而,它被认为是认同政治的形成。女权主义与去中心化更直接的联系是,她们质疑传统“内部”与“外部”的区分,“私有”和“共有”的区分。
这五种对后现代影响重大的理论勾勒出了有关主体认同概念的转变,即认同概念在从前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中已由一个被认为是固定的、稳定的认同(身份),变成了去中心化的,开放的,充满差异、矛盾的,永远处于完成过程中的破碎的后现代认同。然而,霍尔认为这并不是对主体的废除,而是使之重
新概念化,将它放在非中心的位置上来进行的一种思考。然而,这些也并非全部,但从中我们可以推论出认同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体现了文化认同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三、文化认同研究
霍尔认为,认同并不是透明的或没有任何疑问的,或许我们不应该把身份认同当作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事实,而应当把它当作一件“产品”,它永远没有完成,总是处于过程中,总是在内部而非外部建构起来。在《文化认同与族裔散居》中,霍尔指出,目前,关于“文化认同”有着两种基本的思考与立场。
第一种立场对“文化认同”的解释是,文化认同是一个隐藏在众多表面下的或是人为强加的“自我”背后的,对一个共享文化和历史、祖先的寻根。这种定义认为,文化认同反映的是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享的文化符码,这些提供给我们作为一个“人”有着稳定的、不变的和连续的参考和意义的框架,是一种“隐藏的历史”,他在许多社会运动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有着重要的作用。基于此,例如那些在殖民地和奴隶区到处分布的非洲散居族裔的人们,在他们文学、艺术作品中会体现出一种潜在的统一,有着对曾经历史的表现。同样在后殖民社会中,这种共享的、潜在的统一也被殖民者利用了。正如法侬提出的,殖民者不再满足于掌握人口和清空其民族思维的所有形式和内容,而是通过一种反常的逻辑转向被压迫者的过去,进而扭曲它、摧毁它。
第二种关于“文化认同”的观点认为,尽管这里有着许多的相似、相同之处,但是其中也有许多意义深刻的重大的不同、差异性。而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我们是谁”“我们将会怎样”。例如,对于加勒比人的文化认同,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经历的破裂与中断,我们就不能准确地为加勒比人的文化认同作表述。因而,在第二种关于“文化认同”的立场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关于“成为”和“将要是”的问题,它更多的是属于将来的问题而不是过去。它不是对那些已然存在的历史、文化的简单回归,而是超越了时间和地点。像所有事物一样,“文化认同”本身也是历史的,自然也要经历不断的转型,而不是永远规定在某一个本质性的、不变的过去。它注定是历史、文化、权力等不断上演的“戏剧”,在变化中保持着同一。
霍尔认为,只有从第二种立场才能更好地理解那些被殖民者的文化认同特征。那些被殖民者定位并服从于一种文化权力和标准下的统治制度,它不仅是赛义德《东方学》中所说的,他们在西方知识的分类下被视为“不同”或“其他”,而且就像福柯在“权力/知识”这对关键词中提醒我们的:这种制度是由权力形成的,进而通过知识从内部侵入。这不仅是用意志和统治力的强迫,而且是通过他们内心的被建构好的冲动(欲望)和主观性来构造规范。同样,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这种显示出来的差异性通过我们自身内部的冲动(欲望)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认同。例如“黑人就是黑人;就是说由于一系列的感情的迷乱,他在一个本应该把他从中赶出去的世界中定居下来”[3]2。从中可见法侬对后殖民社会中黑人与白人关系的评价。法侬介绍了族裔散居黑人的文化认同困境。
首先,是在语言上,说一种语言也就表示了对这种语言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的认同和接受。在法侬所描述的马提尼克岛上,人们甚至认为“到过宗主国的黑人是半个神”[3]10。“在学校里,年轻的马提尼克岛人学会瞧不起土话。人们谈论‘克里奥尔主义’。某些家庭禁止使用克里奥尔语,当孩子们使用这语言时,他们的妈妈以‘乡巴佬’相待。”[3]10孩子们被要求一定要说法语,说“法国的法语”,说“法国人的法语”,说“法文的法语”,甚至超越了以“貌”取人,直接凭借语言来显示他们的身份,甚至有“说得像个法国人”这样的评价来断定一个人的身份,因而也就产生了大量的讲着蹩脚法语的黑人。这正是因为他们虽生长在马提尼克岛上,但心中认定并渴望法国这个富饶之地是他们的祖国,渴望被这样一个高贵的地方所认可,从中找到自己的认同感。就像法侬所说:“必须从历史上理解黑人想说法语,因为这是可能打开那些五十年前尚且不准他进入的大门的钥匙。我们在那些进入我们描述范围的安的列斯人身上又看到一种对语言的微妙和非凡性的探求———这同样也是向自己证明符合文化的方法。”[3]25
其次,在《有色人种妇女和白种男人》一章中,有色人种妇女嫁给白种男人,其实质是自愿嫁给“蓝眼睛、黄头发和苍白的皮肤”。“他(白种男人)是主人。她不索取什么,不要求什么,只不过是想在她的生活中沾点白色。”[3]29她们不愿接受自己是黑人的事实,甚至想要使自己变白,为白人世界所接纳。然而,这种想要在新世界中找到认同的方式恰恰建立在不断回顾过去历史的基础上。一个学医的黑人大学生,他深深地感觉到由于肤色而不被器重,强烈的感觉到永远也不会为白人认作同行,被欧洲病人当作医生,直到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机会,工作中他是白人的领导,要他们尊敬他惧怕他。因此,无论是有色
人种妇女的对婚姻的过度补偿,还是黑人大学生得势后的报复,其实都是移民们试图摆脱过去记忆,在新的环境中寻求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的一种协调。
最后,法侬对勒内·马朗的小说《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人》的分析表明,主人公让·韦纳兹“他通过自己的聪明和刻苦勤奋学习,达到欧洲的想法和文化①②马朗:《一个同其他人一样的人》,转引自:[法]弗朗兹·法侬:《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译林出版社(南京),2005年5月。,却不能摆脱他的种族”[3]49。主人公爱上了白人姑娘安德莱·马里埃尔,但这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实现的。尽管与佩伊奥、纪德、伏尔泰等人的来往似乎消灭了所有这一切。“让·韦纳兹确实真心诚意地曾经‘相信这个文化并开始喜欢这一为了让他使用的被发现和赢得的新世界。他的错误多大啊!只要他年龄大了,去为被他祖先选择寄居的国家服务,就足以令他终于思忖是否他周围的一切背叛了他自己,白种人民不认他是他们自己的人,黑人几乎不承认他。’”②这就是他的情况,他既不属于白人又不属于黑人,换言之,他是个黑人却又有着白人的教育和思想,于是他不敢对那个白人姑娘说爱,即便是白人姑娘先向他表达了爱意,他也要等待一个白人对他的允许。他能够得到那个白人姑娘的条件是拒绝把自己看成是黑人,使自己相信这只是表象。但是,让·韦纳兹做不到,而同时他也想要是个同其他人一样的男人,尽管这是不可能的。他仍在寻求着,寻求白人世界给予他在白人世界中认同自我的希望。让的心中这两种精神总是在交叉搏击着,可是,事实上任何一种情感都不能取胜,而且让本身也不希望其中任何一种精神压倒另一种,他既希望加入白人世界中,害怕并愤怒被这个高贵的世界所排斥,却又不愿意也不能放弃过去的本质,因而在这样的夹缝中建立起了自身不断游离的、既防卫又寻求着的矛盾身份。黑人们正是在这种想要融入而被排斥,进而一次次尝试进入的验证中实现自我的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但无论怎样,在白人看来他最多是一个新型的人,而不是进入他们世界的新人,这是一种带着混杂身份的新人,而这一过程正是“他者”在复杂环境中寻求其文化认同形成的表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认同”并不是一个外在于历史、文化而保持不变的固定本质,它也不是深藏我们内部的根本不受历史影响的普遍或抽象性的精神,不是一次拥有就规定了永远的。因而,它不是一个我们最终可以做绝对性的返回的固定起源。当然,它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幻想,它有它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依据差异性建构出来的比真实更真的“真实”,是变化中的同一。
然而,第二种立场中较少的相似性或许会使人感到不安,如果认同不是有着一个起点,并在一个线性的、没有破裂的线索中前进,那么要怎么理解它的构成?其实不然,霍尔以加勒比黑人的“文化认同”为例认为,“文化认同”通常由两个向量共同构成,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显然“文化认同”是在这两个向量的对话关系中形成的。一个给予我们所根植的过去,另一个则是提醒我们在发展中的中断与差异的作用。又因为所谓的“过去”其实只是想象中的“过去”,我们是不能够真正返回的,所以,基于对这种“想象的过去”,加之“我”的“身份”在差异间不断被异延,最终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它比那种对想象中过去的回归形成的文化认同更“真实”。
这种关于差异的观点挑战了第一种认为“文化认同”有着稳定不变的本质的二元论观点,并且展示了认同是如何永远不能结束和被完成的,而是保持不断地运动去包围“他者”,补充“他者”的意义。因此,若没有差异的出现就不会有“文化认同”的产生。
结论
霍尔的文化认同研究与其文化研究的实践密切关联。作为新一代的左翼成员,他与早期左翼如雷蒙·威廉斯等人相比,差异在于他更多关注文化、媒体、生活。而且霍尔自己也逐渐意识到只思考单纯的文学是不够的,他所面临的认同问题根本上也是由文化所导致的。归根结底,霍尔认为认同困境最终是要靠文化理论来解决。因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运用霍尔文化研究理论解决的一个具体问题。
从霍尔的“文化认同”观点可知,“文化认同”是在过去“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与未来的对话之间不断建构起来的。虽然带着对“故乡”的想象,但更多、更主要的却是指向未来。它颠覆了曾经认为“认同”是一种本质性的、稳定不变的、具有连续性的观念,而转向了一种去中心化的、随时都在通过差异性建构的思考方式,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的破碎,边缘化的现象,即由前现代对主体的重视转变为对主体间的关注,更为突出差异与变化。就像霍尔解释的那样:“文化认同”就像一件随时都在制作,但总是处于制作、建构的过程中,并且永远
都不会被完成的“产品”一样。在后现代与后殖民的环境下,“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主体一次次被异延,不断被差异填充边缘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过程,这也正是霍尔所谓的“不做保证”的体现。
这一理论也合理解释了后现代流散人群的“认同危机”及其“身份焦虑”的问题。文化认同并不是对“所来自文化源”的完全“回归”,这也是不可能的,它早已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源头了,必然就会产生“认同危机”。真正的“文化认同”是在过去与将来的对话中,通过一次次的差异、碰撞,在不断变化中建构出来的“同一”,形成的“真正的现在的我们”。
参考文献:
[1]金惠敏.听霍尔说英国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访谈记[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2]陶国山.话语实践与认同建构———论文学话语下的认同建构[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法侬.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dentity of Stuart Hall
TAO Guo-shan,XUAN Bo
(Chinese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Recently,the traditional personal identity eliminated gradually with the broken main body identity,led to the Crisis of Self-identity.However,this was the specific aspect of Stuart Hall's cultural studies.Hall opened up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cultural identity.He argued that the Cultural I-dentity was dynamic,and was always in the producing but never completed process.Therefore,Stuart Hall pointed out that the way of thinking about Cultural identity,should be changed from the traditional"who am I""where I come from"into"What kind of person I will be""Where I'm going to".This shift on discussing about the social subject had great significance,and would be a new way for us to explore the"culture identity"of modern social subjects.
Key words:Stuart Hall;Postmodern Subject;Cultural Identity;Diaspora
(责任编辑张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