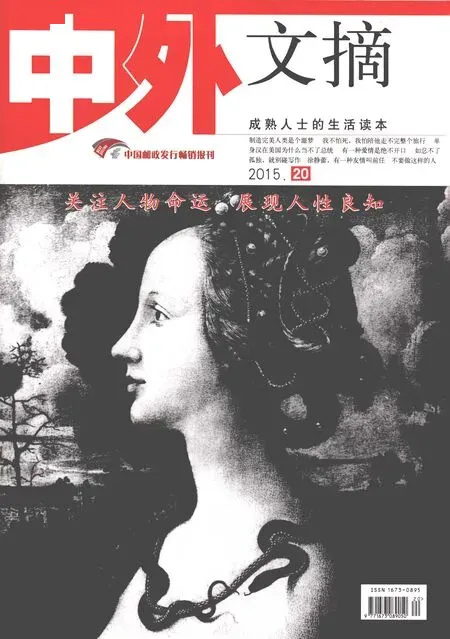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巡:点播电视
□ 崔小舟
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巡:点播电视
□崔小舟

1974年10月12日清晨,毛泽东的专列徐徐驶入长沙站。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走下专列,踏上了故土。他握住前来迎接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第一书记由华国锋兼任)的手说:“我这一次来这里,是来养病休息的。”
毛泽东有作重大决定之前出巡的习惯。此时,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在即,政治斗争异常激烈。7 月17日夜,他从北京火车站登上专列,开始了生前的最后一次离京出巡。这也是建国后他在家乡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
81岁高龄的毛泽东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身体每况愈下。由于腿脚不便,大多数时候只能躺在床上。运筹帷幄、掌控千里之余,看电视,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娱乐方式。为他安排好电视节目,让他能休息、放松,就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11月10日,45岁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文艺部戏曲组导演杨洁突然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电视台执行紧急任务,立刻出发。
杨洁出山
一头雾水的杨洁辗转两天,12日抵达长沙。一进湖南电视台的大门,她几乎被眼前的奇观惊呆了。
电视台里,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看样子都是演员,什么剧种的都有,唱京剧的,湘剧的,花鼓戏的,演话剧的,跳芭蕾的……有扮上了的,有没扮的,共有好几百人。
在这里,她见到了北京电视台仅有的两台彩色电视转播车(从德国进口)中的一台,还见到了之前神秘“失踪”的同事。同事见到她很高兴,说你可来了,这戏能转得像样了。
到这时,她才被告知了自己的任务:为毛泽东转播文艺节目。
以前毛泽东来湖南,都是直接为他演出,这一次,他已经不能坐在台下看戏了,只能通过电视台播放给他看。
由副台长王枫带队,北京电视台文艺部歌舞组负责曲艺、杂技的导演金元成等人先期开赴长沙。但到后才发现,毛泽东对杂技等曲艺节目不感兴趣,金元成无所事事。10月下旬,又派出文艺部歌舞组副组长齐清云,带着戏曲组切换导演宋洪等人,连同一整套设备,赶赴长沙。
齐清云出身好,政治条件过硬,但并不长于业务,而且是歌舞导演,戏剧、戏曲从没搞过,力不从心。
在文艺部,戏曲组导演杨洁钻研业务是出了名的。在他人还满足于“机器里有人就够了”的时候,她却买了电影学院的专业书来读,研究如何使用镜头语言,在转播戏曲节目时进行分镜头实验。
但就在当年,她才在反革命边缘徘徊了一圈。三八节那天,她担任导演,转播中国评剧院刚恢复的剧目《向阳商店》。本来她的指令是切3号机,但刚分来的切换副导演因为紧张,错切到了固定对准舞台中央的毛泽东像的2号机上,而当时刚好唱到“坏人面前”。当天晚上,大字报就出来了:杨洁恶毒攻击毛主席、三八节的反革命事件。她被停止工作半个多月,最后总算涉险过关。她一度心灰意冷,想调出电视台。之后虽然打消了这个念头,却决定,今后自调自切,不要副导演,因为她不能为别人的手指负责。
重任当前,在长沙坐镇的王枫听从大家的意见,决定调杨洁来接替齐清云。
“速归!”
11月17日,正在南京治嗓子的左大玢,接到了团里的加急电报:“速归!”
时年31岁的左大玢是湖南省湘剧院的台柱子。也是在当年,她主演的湘剧戏曲电影《园丁之歌》被江青说成“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批为大毒草,全国大批判,她被令专门去北京,在千人批斗会上作检讨。但湖南省领导对她诸多保护。张平化说,有什么错误我们省委来承担,跟演员没有关系。
这次毛泽东来长沙,点名调看了《园丁之歌》,鼓掌说:“好戏。”等于当场为这部影片平了反。当时,左大玢正随湖南省湘剧院在浏阳演出,“最高指示”传来,大家放了好多烟火。
在这之后不久,左大玢就接到“速归!”的加急电报。第二天,她又接到了第二封电报,依然是两个字:速归!
看到这两封加急电报,她心里有数:毛泽东来了。
1959年,16岁的左大玢为毛泽东演出湘剧《生死牌》,第一次受到他的接见。今年72岁的左大玢告诉记者,毛泽东见到她时,开玩笑地问道:“你姓左,为什么不姓右啊?”她想了半天,回答说:“我爸爸姓左,我就姓左。”
从此,毛泽东每次去湖南,她都会被派去给他演戏,或陪他跳舞、聊天。有时剧团在外地,会突然紧急集合回长沙。有一次,她在沅陵县演出,已经开演了,突然来了一个吉普车,让她别演了,下妆,戏让别人顶,赶快回长沙。
收到电报后,左大玢停止治疗,急匆匆坐火车离开了南京,11月20日晚回到长沙。第二天一早,就去湖南电视台报到。
到了湖南电视台,在一群一群不同扮相的演员中,她见到了一个干练的女导演,正指挥着工作人员录节目,她就是杨洁。
乡音难舍
为毛泽东提供电视节目的工作,由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挂帅,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振军、省文化局局长王庆章坐镇指挥。
湖南省湘剧院、花鼓剧团、京剧团、话剧团、歌舞团、曲艺团等省内主要文艺团体,全都参加了演出。节目主要是各剧种移植的“革命样板戏”,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杜鹃山》等。
节目由北京电视台和湖南电视台共同录制。杨洁担任导演后,转播很快上了正轨,不再出现“明明这个人在唱摄像机却找那个人”那种让人看不懂的情况了。她转播的节目,连演员都反映,比在剧场演出的效果都好。因为能“把你应该看的提供给你”,比舞台上让人看得更加清楚、真切。
生活条件是顶尖的。住的是最高级的湖南宾馆,杨洁一个人住一个房间——相比之下,她在北京一家五口所住的16平方米的小屋实在太过拥挤。一天包括夜餐在内,有四顿饭,顿顿大鱼大肉。
生活好,是为了更好地为这项重要政治任务服务。
毛泽东的作息昼夜颠倒,看戏通常在夜里11点以后。所有文艺团体每天都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一声令下,被点名的剧团就立刻上妆,进行直播。
毛泽东不喜欢看曲艺,话剧《枫树湾》演过一次,歌舞团待命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演出一场。他最常点的,是湘剧和花鼓戏。
湘剧和花鼓戏是湖南的两大地方剧种。曾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曾指示,湖南省要两条腿走路,用花鼓演现代戏,湘剧演古装戏。左大玢告诉记者,湘剧主要取材于《三国演义》等历史故事,毛泽东对背景和人物都深知,而且自己还会唱。
人老了,就喜欢乡音。常常准备好了别的节目,却临时被要求改播湘剧、花鼓戏。景片搭进搭出,总是乱哄哄的。
“你不能不安排节目,但你又不知道他要点什么。如果正播着《沙家浜》,他说我要看《红灯记》,那就得赶紧换。”杨洁说。如今已86岁的她身体不大好,全程插着吸氧机,向记者回忆了这段日子。
一天晚上,她转播完《智取威虎山》,并说了“再见”(文革开始后,就不再有出图像的播音员),“里边”却传出指示,点名要看《打虎上山》和《壮志凌云》(分别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里的唱段)。于是,只好让演员又将这两个唱段再唱一次。
当时,电视还没有进入家庭。截至1975年底,中国才有电视机46.3万台,其中国产彩色电视机4000台、进口彩电1900台。在长沙,只有一些单位才有电视,彩电更是凤毛麟角。即便这样,这种混乱的播出状况,还是引起了注意。
节目还没播完,电视台就接了好几个观众电话:“你们怎么搞的,没有节目播了吗?”他们只能推说:“安排失误,接受批评。”
但几百号人整天蜂拥在电视台里,总不是长久之事。12月20日左右,湖南省委决定,将所有人员和设备转移到宽敞的湖南剧场,用转播车录制节目,转到湖南台发射。
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长沙的这段时间里,每天早、晚,毛泽东总是由人搀扶着,沿门前草坪散步。他习惯边踱步,边吸烟,边沉思。思绪集中时,便停住脚步,一言不发地静静想事情。
虽然视力微弱、行动不便,他却时而要求坐车巡行长沙市内。酷爱游泳的他,五次秘密到市内湖南省游泳馆游泳。这时,他已无法再下到湘江去“中流击水”了。
如何体面地结束文革,成为他萦绕于怀的心事。l0月11日,就在离开武汉前往长沙之前,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这个文件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他的亲自过问下,贺龙等一批被打倒的老干部以及一些知名人士被“解放”出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各方都利用各种机会,频繁来长沙向他打报告。王洪文受江青等人的嘱托,来长沙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的状,结果,“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周恩来任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在长沙的近四个月中,毛泽东会见了六批外国政府首脑和政党领导人。尽管他表示,从明年(1975年)起,外宾一律不见了,对方要求见也不见了,但第二年元旦后,他仍见了两批外国客人。陪他会见外宾的中方领导人是邓小平(四次)、李先念(两次)等。
1974年12月23日,重病中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飞来长沙会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三次谈话。他告诉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他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还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2月26日是毛泽东8l岁生日。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当晚,约周恩来做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
28日,周恩来和王洪文带着经毛泽东审定的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决策,返回了北京。
“主席要看传统戏”
就在周恩来和王洪文离开的第二天,12月29日,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振军、省文化局局长王庆章急匆匆地找到杨洁:“杨导演,主席要看传统戏!”
“什么传统戏?”杨洁很惊异。传统戏是“大毒草”,绝对禁播。“就是京剧、湘剧、花鼓的旧戏。”
杨洁心里很高兴。八个样板戏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连主席都受不了了,这不正好吗?看来传统戏翻身有日。但她不多说话,“这种态是不能表的”。
播什么传统戏呢?谁都不知道。是播整出还是折子?“你怎么敢把整出拿出来?到时候又说,啊,我没让你拿出来,那你不就成了反革命了吗?那时候当反革命太容易了。”杨洁说。大家讨论决定,还是播折子。
是清唱还是扮唱?不扮上太难看,估计看的人不会高兴,遂决定扮上。唱什么呢?杨洁不熟悉湘剧和花鼓戏,只能提出几个京剧折子:取材自水浒故事的《打渔杀家》最有把握,《苏三起解》说的是受欺凌的妇女,也是保险的。《霸王别姬》,应该也可以。
敲定了四五出单人演唱的京剧折子戏后,湖南省京剧团立即组织演员上妆,加上班底伴唱。杨洁指挥着三个摄像师,成功地将“毒草”播给毛泽东观看。
第二天,上面的指示传达下来:“这样零碎的不行,要看整出的!”杨洁很兴奋,“整出的那就更来劲了”。
为了加强保密,省委领导决定,还是从湖南剧场搬回电视台。
当天晚上,在播音员说了“再见”之后,凌晨一点,电视台播放了湖南省京剧团演的全出《玉堂春》。
第二天,有观众给电视台打来电话:“反革命在传播传统戏《苏三起解》!”(《苏三起解》为《玉堂春》中一折)当向他解释说,可能是收到了香港台的信号,他说:“不可能!还有湖南电视台播音员张灵芝在报幕,说明电视台里也有反革命!”
事后才知道,这是个半夜里修理电视机的观众,刚好看到了。
一位“造反派”出身的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也得知了播传统戏的事,他带了一群人欲闯电视台:“有群众举报,你们在这里搞反革命活动!”湖南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紧张地向省委领导汇报:“怎么办?”汪东兴递出话来:“叫那个造反派回家去,少管闲事!主席要看,还是得播,其他的你们想办法。”于是,“造反派”被挡驾:“中办任务,任何人不得过问!”
进驻省委接待处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省委决定,改为有线电视播出。1975年1月11日,全体人员和设备,进驻湖南省委接待处。
转播车停在了与毛泽东所住的“九所”(有湖南“钓鱼台”之称)一墙之隔的地方,转播车上拉一根电缆,通到他面前的电视机上。
搬到接待处后,话剧团和歌舞团都撤了,只留下湘剧、花鼓和京剧团的演员。领导宣布了纪律:不许回家,不许请假,不许告诉任何人在哪里工作。
接待处的条件很好。群众演员三人一间,主角大多两人一间,有的老演员住单间。演出在礼堂进行。礼堂的舞台比普通剧场都大,但是座位少,只能坐两三百人。
不久,又传出指示,毛泽东要看湘剧和花鼓戏的传统戏。
毛泽东对湘剧院和花鼓戏团都很熟悉,亲自点了几个剧目,还点了彭俐侬、刘春泉、庄丽晶等几个老演员的名。
这些老演员,曾蹲了多年的牛棚,现在让她们出来演传统戏,都有顾虑。张平化亲自做大家的工作:“你们大胆一点,如果要你们游街戴高帽子,我就第一个去戴!”
老演员进组之后,立刻开排8个传统戏,如湘剧《柜中缘》《祭头巾》,花鼓戏《刘海砍樵》《打铁》《讨学钱》等。这些“毒草”多年不演,剧本丢的丢,烧的烧。演员们各自找个角落,几个人一对,台词就出来了。
杨洁对湖南话不熟悉,尤其是花鼓戏,说的是土话,听不懂,只能连蒙带猜。但声调和意境,却让她十分着迷。念台词时,拉长了声调,非常好听。8个戏都是喜剧,很有意思,她觉得最好的是湘剧《祭头巾》。
故事讲述的是一位老举人,赶考数次不中。“今天82岁,总共进了9次科场,科科未中,榜榜无名。”终于中举时,却因兴奋过度而溘然长逝。这虽是一部喜剧,但老演员的表演却让她几乎掉泪。
她以为让她选戏,就挑选了包括《祭头巾》在内的4个剧。可李振军告诉她:“所有的戏都是毛主席亲自点的,都要录!一晚上都要录完,因为不知道主席会点哪出戏。”
都录?《打铁》她就不敢录。这是一部滑稽戏。主人公姓毛,开了个毛家老店,善于吹牛皮,自夸打铁天下无敌。一个壮士故意刁难他,让他受到了教训。杨洁心里很喜欢这个短小喜剧,觉得滑稽得笑死人,又讽刺得一针见血。但多年来的教训,尤其是长期以来的派性斗争,让她不得不自我保护。她提出,别的戏她都能录,这个《打铁》,她不敢录。要录,主人公也必须改姓!
省文化局局长王庆章也不干:“录这样的戏,如果说是影射,责任谁担?”省委书记张平化亲自来做工作:“主席在,你们还怕什么?”王庆章还是不干,要求给他红头文件,“我不当这反革命”。最后,他还是管张平化要了个“手谕”。
当天晚上,杨洁录像一直录到3点。8个戏,白天看一遍,晚上录一遍,她有要累吐了的感觉。
第二天,“里面”传出话来:“主席看了哈哈大笑,还说这毛家的真是不可救药!”
但杨洁最看好的《祭头巾》,却没放给毛泽东看。不但如此,领队(北京电视台摄像、党员)文英光还是把录好的像给销掉了。“为什么销掉?那是一出最好的戏!”杨洁大为光火。文英光不紧不慢地回答:“销了就销了。”
“客散主人安”
湖南为毛泽东录传统戏的事,是华国锋和汪东兴亲自抓的,没有通过文化部。后来,江青知道了,让文化部部长于会泳在北京也组织了一班人马,由北京电视台导演莫萱担任导演,秘密录制传统戏。
杨洁的丈夫、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摄像组摄像师王崇秋参与了录制。他告诉记者,他们住在西苑旅社里,录制了不少京剧和河北梆子,比如《卧龙吊孝》《林冲夜奔》《空城计》《李陵碑》等。节目在北京录制完成后,用专机直送湖南。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五年之久,历尽周折。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2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毛泽东结束了在长沙岳麓山下长达114天的休养,启程东进,前往江西南昌。他本想再去家乡韶山,到父母墓前再祭扫一次,但由于健康状况,没能成行。临走时,他对大家说:“我在长沙住了一百多天,你们已经很辛苦了。客散主人安,我走后,你们好好过个春节吧!”
实际上,“客”散后,录制工作依然在持续,一直到当年6月,杨洁才回了北京。在北京,她又加入了西苑的摄制组,继续这项工作。
再赴长沙
1976年3月中旬,杨洁也从北京回来,再度担任导演。
这次录节目,与上次有所不同。因为毛泽东不在长沙,一切相对松散。大家每天正常工作,在规定的时间里将节目录好,由专机空运到京,不用再熬夜直播。
杨洁整日忙着发掘、搜罗各种传统剧目。后来实在是没戏可录了,就到株洲、邵阳等地,看地方上的花鼓戏。很多演员们把新中国成立后从来没有演过的“箱子底儿”都搬出来录制。“有的太低俗了。像《磨豆腐》,边磨边调情,到后面就太低俗了。”
她利用这个机会,录制了不少传统戏精品,如湘剧《追鱼记》、花鼓戏《刘海砍樵》。
左大玢在《追鱼记》里饰演观音,她的扮相一下被杨洁看中了。杨洁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以后我排观音的戏,一定找你来演!”
杨洁没有食言。6年后,她担任电视剧《西游记》的导演。左大玢没有试妆,直接成为观音的扮演者。
6月15日,湖南省湘剧院录完了《百花记》。随后,节目组封镜,全部工作结束。
后来,左大玢才知道,当时,病重的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想看小左和刘春泉的戏。”
她俩演的《百花记》,成为毛泽东点的最后一部戏。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26期)
——湘剧之形成与发展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