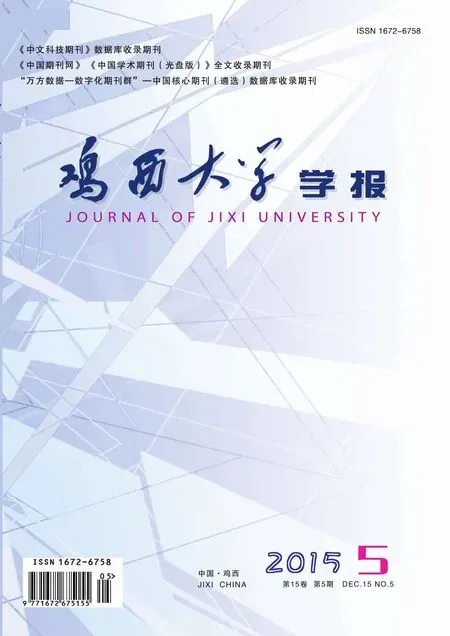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辨析
——东亚封贡体系形成理论研究之一
陈俊达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吉林长春130012)
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辨析
——东亚封贡体系形成理论研究之一
陈俊达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吉林长春130012)
通过学界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的认识和使用,从丽辽“关系”“朝贡”“遣使”的起止时间及阶段划分等三个方面入手,对上述三组概念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关系”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朝贡”强调的是“宗藩关系”,而“遣使”强调的则是“使者派遣”。三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同时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遣使分期”提出了新的划分标准与依据。并得出由于丽辽两国在1038年以后,朝贡制度与遣使制度实现了制度化,因此1038年以后的丽辽关系,应为东亚封贡体系之始的结论。
关系;朝贡;遣使;分期;东亚封贡体系
“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是在有关研究东亚封贡体系的论著中经常可以见到的词语,但三者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以及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等,却没有学者进行过专文探讨。甚至学者在研究东亚封贡体系相关问题时,多将此三组有着相对明确含义且差异较大的概念进行混用,尤其在探讨遣使问题时,多将遣使问题置于相关“关系分期”或“朝贡分期”下进行讨论,而不根据遣使的自身特点进行分期研究。因此,分清这三组概念之间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代王朝与边疆民族乃至邻国的关系,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封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此,笔者不惮鄙薄,试图从分析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三组概念入手,分析学界对以上三组概念的不同用法,探讨以上三组概念的异同,并兼及高丽遣使辽朝分期问题的探讨及东亚封贡体系形成时间的讨论。
一 学界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的认识和使用
学界目前暂无专门论述丽辽“遣使分期”的相关论著,现有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丽辽“关系分期”或“朝贡分期”的划分上。而在研究高丽遣使辽朝相关问题时,多将遣使问题置于相关“关系分期”或“朝贡分期”下进行讨论。最早对丽辽关系进行分期的是李符桐,其《辽与高丽之关系》一文认为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朝为辽丽关系的第一阶段,该阶段辽朝无暇顾及高丽,辽与高丽之间暂时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圣宗朝为第二阶段,该阶段辽朝国势发展至最高峰,对高丽发起多次大规模征讨,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兴宗、道宗、天祚帝三朝为第三阶段,该阶段辽丽两国关系日渐融洽,直至辽亡。[1]
金渭显在《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一书中,将辽丽关系划分为五期:第一期为公元926年之前,此时期契丹与高丽地界不相接,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只是维持一种平等交聘而已;第二期从926年至982年,这期间高丽一直在防备契丹;第三期从982年至1020年,期间契丹通过三次大规模征伐迫使高丽臣服,取得宗主权;第四期从1020年至1100年,认为高丽虽被迫臣服于契丹,但两国实际上仍处于对峙状态;第五期从1101年至1125年契丹为女真所灭。[2]然而之后金渭显在《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一书中,将丽辽关系分为初期交涉期、和战时期、和平时期,惜未对每时期作出明确的时间划分。[3]
此后学者对丽辽“关系分期”问题多持三分法。魏志江认为922年至992年为辽丽关系的前期,辽丽由睦邻平等变为敌对关系;992年至1020年为中期,辽通过数次武力征服,迫使高丽称臣纳贡;1020年至1125年为后期,辽丽朝贡体制全面确立,并随着辽的衰亡,两国关系趋于终结。[4]金在满认为993年之前为丽辽关系的第一阶段,该阶段两国一直维持着消极被动的外交关系;994年至1030年为第二阶段,此阶段契丹与高丽间的邦交才正式展开;1031年至1125年为第三阶段,此阶段两国处于和平交涉的时
期。[5]张国庆将辽丽关系分为918年至991年从友好到交恶时期,992年至1019年辽圣宗三征高丽时期,1020年至1125年正常化时期。[6]
上述这些论著对丽辽“关系分期”的划分应该说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其中比较突出的两点是认为丽辽关系的展开最晚不晚于922年,结束时间应为1125年,即辽被金所灭。这反映着学界在使用丽辽“关系分期”概念时存在的一种倾向。
对于丽辽“朝贡关系”的分期则相对比较统一,因为至今为止笔者仅见到付百臣主编的《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一书,对高丽向辽朝的朝贡进行了分期:高丽自993年始行契丹年号至1009年辽圣宗亲政为第一阶段,即高丽对辽朝贡的初期阶段。该阶段朝贡制度尚在完善中,贡期还不确定,贡物颇杂,且朝贡名目也较为混乱。同时受时局影响,这一时期高丽的许多朝贡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但双方的关系总体还是比较融洽的,双方使节往来频繁。1009年至1038年高丽行辽重熙年号为第二阶段,该阶段双方发生多次大规模战争,虽于1022年一度恢复朝贡关系,但随着辽圣宗去世,高丽重提辽退出保州城,拆毁鸭绿江浮桥等要求,双方关系再度恶化,高丽甚至单方面终止朝贡关系。1038年至1116年高丽对辽朝贡结束为第三阶段。该阶段,高丽对辽的朝贡稳定下来,并不断完善。[7]
以上即为学界关于丽辽“关系分期”与“朝贡分期”的代表性观点,但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学者对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异同做出明确的解释,而且在具体讨论丽辽“遣使分期”问题时多存在概念混用的情况。这一问题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学界对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三组概念缺乏准确、统一的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学界对相关历史问题缺乏深入探讨的结果。由此也为相关研究的深入带来了许多疑问。诸如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的各起止时间究竟是多少?其含义应该是什么?三者的关系如何,是否在某些方面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等等。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三组概念的具体含义问题,更涉及到如何准确认识高丽与辽朝的关系,进而如何准确认识中国历代王朝与边疆地方政权乃至周边邻国的关系,因此是很有必要对此加以正确界定和区分的。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试图分别从丽辽“关系分期”“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的各起止时间与阶段划分入手,以探求三者之间的差异与关系。
二 丽辽“关系”“朝贡”与“遣使”的各起止时间
关于丽辽关系的起止时间,由上文可知,丽辽关系的结束时间应为1125年,即辽被金所灭。这点学界已经达成了共识,分歧主要在于丽辽关系的开始时间。主要有三种观点:①辽朝建国说;②高丽建国说(918年说);③922年说。辽朝建国说首先被否定,因为此时高丽尚未建国。持918年说的学者,其依据多是《辽史》中的两条史料:神册三年(918年)二月,高丽遣使来贡;[8]三月,高丽遣使来贡。[8]而据《高丽史·太祖世家一》可知,高丽太祖王建于918年“夏六月丙辰即位于布政殿,国号高丽,改元天授”,[9]因此,前引《辽史》两条史料中记载的“高丽”,当为“泰封”之误。关于这点,前辈学者金渭显、[2]魏志江[10]等已有详细考证,此不赘述。故引用此两条史料作为918年丽辽交往开始的依据,显然是不正确的。
丽辽交往开始的时间当为922年。据《高丽史·太祖世家一》记载,高丽太祖五年(922年)“春二月,契丹来遗橐驼马及毡”。[9]此为丽辽交往之始。922年之前,高丽太祖王建忙于整顿内政,经略鸡林(新罗)地区,“先操鸡(林)后搏鸭(绿江)”,[9]无暇顾及朝鲜半岛以外地区。同时由于辽朝与高丽之间有渤海国相隔,“与高丽地界不相接,没有直接利害关系”,[2]直至922年,丽辽之间才开始真正交往。同时据《现代汉语词典》将“关系”一词解释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11]丽辽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从922年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朝灭亡。
关于高丽对辽朝贡的起止时间。首先,应界定“朝贡”一词的含义。朝贡即“君主时代藩属国或外国的使臣朝见君主,敬献礼物”。[11]在这里,《现代汉语词典》特别强调“藩属国”和“外国”。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在修史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大喜功的心态”及“中国君主‘君天下’思想的遗风”,[12]常将一些中国对其没有任何干预能力的国家遣使中国记录为“朝贡”。本文仅在藩属国与宗主国的关系下,使用“朝贡”一词。因此,“朝贡”一词在本文中的含义为“藩属国对宗主国按时进献礼品和方物,采用中国王朝年号、年历,以此表示臣服;而宗主国作为回报,则对藩属国进行回赐、封赏,用以体现天朝恩典”。[7]
理解了“朝贡”一词的含义,高丽向辽朝贡的起止时间自然迎刃而解。韩国学者徐荣洙曾对“朝贡关系”确立的标志有着明确的界定:“以政治臣属为前提,见于历法或年号的使用,以象征和表示从属关系”。[13]因此,丽辽“朝贡关系”的开始时间即为高丽成为辽藩属国的时间,结束时间即为高丽不再向辽称臣的时间。学界一般以高丽“始行契丹统和年号”[9]作为高丽成为辽藩属国的标志。然而关于这一标志的具体时间,由于《辽史》与《高丽史》中关于992年12月至994年3月间辽丽关系的记载存在一定出入,使得学界对这一问题存在争议。[14]笔者在拙作《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新探》中,考证这一时间应为高丽成宗十三年(994年)春二月。[14]因此,高丽朝贡辽朝应开始于994年。结束时间学界没有争议,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年)四月,“以辽为金所侵,正朔不可行,凡文牒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15]“高丽对辽的朝贡结束”。[7]
关于高丽遣使辽朝的起止时间,由于强调的是“使者派遣”,故只须考证高丽派遣出使辽朝的第一位使者与最后一位使者。高丽派遣出使辽朝的第一位使者当为监察司宪、借礼宾少卿李蒙戬。统和十一年(993年)八月辽朝发动对
高丽的征伐后,[14]于同年闰月攻破高丽蓬山郡。[9]辽朝东京留守萧逊宁(恒德)声言:“大朝既已奄有高勾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又移书云:“大朝统一四方,其未归附,期于扫荡,速致降款,毋涉淹留”。徐熙见书还,奏有可和之状。于是高丽成宗派遣“监察司宪、借礼宾少卿李蒙戬如契丹营请和”。[16]高丽派遣出使辽朝的最后一位使者为河则宝,据《高丽史·仁宗世家一》记载:仁宗元年(1123年)八月甲辰“遣河则宝如辽,自龙州泛海,不达而还”。[9]因此,高丽遣使辽朝自993年开始,终于1123年辽朝灭亡前夕。
按照同样的思路,辽朝第一次遣使高丽为922年,“春二月,契丹来遗橐驼马及毡”。[9]最后一次遣使高丽为1120年。“秋七月甲辰,辽遣乐院副使萧遵礼来”。[9]辽朝遣使高丽自922年始,终于1120年。
三 丽辽“关系”“朝贡”与“遣使”的分期
由上文可知,学界对丽辽“关系分期”的讨论最为激烈,分歧也最大。然而我们仔细研读各家观点后发现,虽然各位学者对丽辽“关系分期”的看法不同,但划分标准总体上还是一致的。
学界对丽辽“关系分期”多持三分法。前期,即初期交涉期,或平等交涉期。学者们皆注意到了这一阶段的整体特点是高丽与辽朝为两个平等政权,高丽还未成为辽朝的藩属国。学者们的分歧多集中在高丽与辽朝关系开始的时间与高丽成为辽朝藩属国的时间上。由上文笔者考证可知,922年至993年为丽辽关系的前期,即丽辽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展开。中期,即丽辽和战时期。学者们皆注意到了这一阶段的整体特点是和战不断,辽朝对高丽发起多次大规模征讨,最终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学者们的分歧多集中在辽丽大规模战争结束的标志上。笔者赞同将1021年辽圣宗改年号为“太平”作为丽辽大规模战争结束的标志,[17]此后虽丽辽之间仍有摩擦,但基本上保持和平交往的局面。994年至1020年为丽辽关系的中期。因此,1021年至1125年为丽辽关系的后期,即和平时期。
关于丽辽“朝贡”与“遣使”的分期,笔者认为,虽然高丽对辽朝贡与高丽遣使辽朝的起止时间不同,但在分期上,由于高丽对辽朝贡皆是派遣使者进行,因此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二者应该是相同的。黄纯艳在其《宋代朝贡体系研究》一书中,认为辽朝和高丽建立了典型的宗藩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辽朝和高丽之间有着制度化的使者互派体系,即不仅有稳定派遣的常使,也有临时派遣的泛使。[18]强调使者派遣的“制度化”是丽辽朝贡制度“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因此,关于丽辽“朝贡”与“遣使”的分期,笔者认为,皆应分为两个时期,即欠完善的前期与制度化的后期。
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笔者认为,应以1038年八月高丽“始行契丹重熙年号”,[9]作为前后期划分的标志。1038年之前,为高丽对辽朝贡、遣使辽朝的欠完善阶段,各种制度尚在制定完善中,贡期、贡物、遣使名目等皆较为混乱。同时这一时期无论是高丽对辽朝贡,还是高丽遣使赴辽,亦或是史书中没有高丽遣使朝贡辽朝相关记载的年份,更多的是高丽受到时局的影响,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正是由于朝贡制度的不完备,以及高丽朝廷的暧昧态度,丽辽两国在磨合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最终爆发了辽圣宗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战争期间,朝贡、遣使的制度化更无从谈起。后虽于1022年丽辽一度重新恢复朝贡关系,但随着辽圣宗去世,高丽重提辽退出保州城,拆毁鸭绿江浮桥等要求,双方关系再度恶化,高丽甚至单方面终止朝贡关系。显宗二十二年(1031年)十一月辛丑“金行恭回报契丹不从所奏,遂停贺正使,仍用圣宗太平年号”。[9]甚至在德宗元年(1032年)出现“契丹遗留使来,至来远城,不纳。遂城朔州、宁仁镇、派川等县备之”[9]的剑拔弩张的局面。这种局面直到1038年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038年以后,“高丽对辽的朝贡稳定下来,并不断完善。高丽对辽的朝贡名目固定的有:贺正旦、贺冬至、贺圣节、贺生辰、四季问候、问起居等。不定期的朝贡名目有:贺即位、吊慰、贺胜、进方物、告、请、谢、奏等”。[7]因此,高丽对辽朝贡的前期为994年至1038年,后期为1039年至1116年。高丽遣使辽朝的前期为993年至1038年,后期为1039年至1123年。辽朝遣使高丽的前期为922年至1038年,后期为1039年至1120年。
四 几点余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关系”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朝贡”强调的是“宗藩关系”,而“遣使”强调的则是“使者派遣”。从这个角度出发,丽辽关系应始于922年,终于1125年;高丽对辽朝贡应始于994年,终于1116年;高丽遣使辽朝应始于993年,终于1123年;辽朝遣使高丽应始于922年,终于1120年。
2.虽然学界对于丽辽“关系分期”存在不同看法,但殊途同归,其根本划分依据是相同的,即将丽辽关系分为平等交涉的前期、和战不断的中期、和平往来的后期三个时期。笔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丽辽关系的前期为922年至993年;中期为994年至1020年;后期为1021年至1125年的结论。
3.丽辽“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皆应以是否“制度化”作为分期依据。按照这个思路,笔者认为,高丽对辽朝贡与高丽遣使辽朝在1038年后实现了制度化。因此,高丽对辽朝贡的前期为994年至1038年,后期为1039年至1116年。高丽遣使辽朝的前期为993年至1038年,后期为1039年至1123年。辽朝遣使高丽的前期为922年至1038年,后期为1039年至1120年。
4.三组概念虽然差异甚巨,但在某些方面存在交叉点或相同点。三组概念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由于有明确记载的丽辽交往之始的事件为辽朝遣使高丽,故丽辽关系开始的时间与辽朝遣使高丽开始的时间相同;由于高丽对
辽朝贡皆是派遣使者进行,故丽辽“朝贡分期”与“遣使分期”在时间节点的选择上,二者相同等。
5.魏志江早在《辽宋丽三角关系与东亚地区秩序》一文中就指出:“辽丽朝贡制度,是一种以政治上臣属关系为前提的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认为高丽向辽表示臣属,具体体现在禀行辽朝的正朔、纪年,进而向辽朝履行贡奉(进奉、献方物)、告奏、谢恩、季节问候等臣属的义务。[19]杨军老师在《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以辽金与高丽的关系为中心》一文中认为“如果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在册封、使节往来频度、交往礼仪等方面都已经出现了制度化的规定,则可以断定,双方的关系已经由简单的封贡关系步入到封贡体系的模式之内”。认为“作为古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模式的封贡关系,其起源可以上溯至辽中期”。[20]而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丽辽两国在1038年以后,朝贡制度与遣使制度实现了制度化,故本文最后认为,1038年以后的丽辽关系,应为东亚封贡体系之始。
[1]李符桐.辽与高丽之关系[A].李符桐论著全集编委会.李符桐论著全集(第五册)[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2:177-179.
[2][韩]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契丹与高丽女真关系之研究[M].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171-178.
[3][韩]金渭显.高丽史中中韩关系史料汇编[M].台北:食货出版社,1983:103-122.
[4]魏志江.论辽与高丽关系的分期及其发展[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87.
[5][韩]金在满.契丹圣宗之进攻高丽以及东北亚国际情势之变趋[A].穆鸿利,黄凤岐.辽金史论集(第七辑)[C].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74-175.
[6]张国庆.辽与高丽关系演变中的使职差遣[A].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编.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四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3:150-155.
[7]付百臣.中朝历代朝贡制度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绪论,54-59.
[8]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1126.
[9]郑麟趾.高丽史第一[M].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昭和52年(1977年):12-220.
[10]魏志江.《辽史·高丽传》疏证稿[A].杭州大学韩国研究所编.韩国研究(第三辑)[C].杭州:杭州出版社,1996:35.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61,501.
[12]杨军,王秋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70.
[13]徐荣洙.三国南北朝交涉性格[A].东洋学研究所.东洋学(韩国)[C].首尔:东洋学研究所,1981:78.
[14]陈俊达.辽对高丽的第一次征伐新探[J].邢台学院学报,2014(3):104-106.
[15]郑麟趾.高丽史第二[M].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昭和52年(1977年):730.
[16]郑麟趾.高丽史第三[M].东京:国书刊行会株式会社,昭和52年(1977年):76-77.
[17]蒋非非,王小甫.中韩关系史(古代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69.
[18]黄纯艳.宋代朝贡体系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70.
[19]魏志江.辽宋丽三角关系与东亚地区秩序[A].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321.
[20]杨军.东亚封贡体系确立的时间——以辽金与高丽的关系为中心[J].贵州社会科学,2008(5):117-124.
On the Stage of relationship,the Tributary Stage and the Envoy Stage Between Korea and the Liao Dynasty——Formation Theory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East Asia
Chen Junda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12,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the Liao Dynasty in China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problems of the relationship stages;the tributary stages and the envoy stages.The starting and ending time of the relationship,the tributary and the envoy dispatching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division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is focused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orea and the Liao Dynasty,the Tributary system emphasizes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n and vassal;the Envoy stresses the envoy dispatching.These three concepts have different nature.The paper proposes a new division standard.After the year of 1038,the tributary system and the envoy-dispatching system had institutionalized.Therefore,the relation between Koryo and Liao Dynasty after 1038 sh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East Asia.
relationship;tributary;envoy dispatching;stages;tributary system in East Asia
K246
A
1672-6758(2015)05-0041-4
(责任编辑:蔡雪岚)
赵传兵,博士,副教授,洛阳理工学院。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教师教育。
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资助项目(省级课题)“新课程背景下的教师课堂行为研究(2014-JSJYYB-124)”阶段性成果。
Class No.:K246 Document Mar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