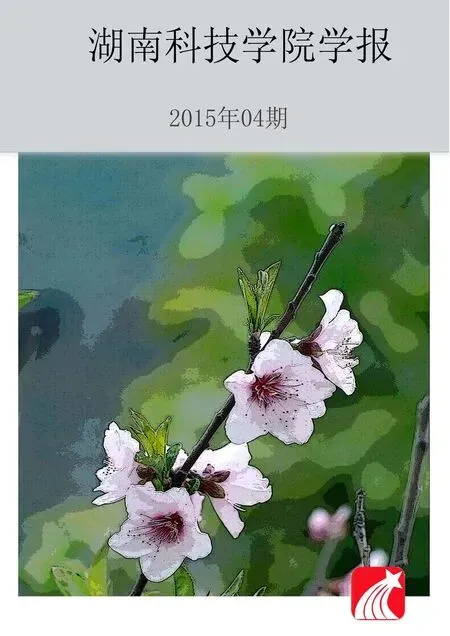在参差交错中求同存异
——对《看不见的人》中的多重原型解读
付 洁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在参差交错中求同存异
——对《看不见的人》中的多重原型解读
付 洁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看不见的人》是美国非裔黑人小说家拉尔夫·埃里森一部现代意义的长篇小说,拉尔夫·埃里森也因该小说而名声大噪。《看不见的人》在1952年已经出版之后,当即被誉为经典之作,文学评论界还将其视为二战以来美国最为重要的小说之一[1]。该小说的大获成功为拉尔夫·埃里森本人赢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学荣誉——美国国家图书奖,从此也奠定了作者在美国文学史上大家的地位。埃里森在该部作品中运用了广泛而丰富的文学、民俗及神话故事,这就使得原型批评理论已经成为众多评论家关注的一个方面。论文从原型的角度出发,解读作品中多重原型,引导读者透视现象中的本质,进而表现人物特征。
《看不见的人》;多重原型;拉尔夫·埃里森;神话原型
《看不见的人》是一部关注美国黑人处境和自我身份追寻的经典小说,具有超越种族的广泛意义。巴勒特曾断言该小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为整个二战后的一代作家提供诸多新的,有效的指导。多数评论家曾赞扬其小说超越了种族小说的界限及对人类普遍主题的探讨,但是该小说也让左 派评论家被小说中对美国左派组织描写所激怒,从而还使得它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黑人美学拥护者最为猛烈的抨击。该小说以“看不见的人”,一个无名、无身份的黑人青年为主人公,小说中“看不见的人”的原型被众多学者进行解读。笔者认为,“看不见的人”的原型并非单一的原型,而是多重原型复合的结果。本文就从多重原型对“看不见的人”进行分析,进而体现出美国黑人文化在美国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即求同存异。
一 引 言
《看不见的人》讲述了一个无名美国黑人青年在充满种族歧视和社会压迫中追寻理想而最终失败的故事,小说在内容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南方黑人大学中的学习、自由油漆厂的遭遇、哈莱姆区的经历。拉尔夫·埃里森作为黑人作家,其作品中充斥着黑人文学的传统,并且受到黑人文化、民俗以及西方文学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看不见的人》在写作手法上综合运用到了象征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多种元素。并且其多重原型的运用也提高了该小说的文学价值。
全书讲述了黑人男青年“我”成为看不见的人的经过。“我”本是美国蓄奴制南方土生土长的黑人大学生,在一次做错事后被校长推荐到美国纽约去谋生,在经历过校长欺骗和多次的拒绝之后,“我”最终被一家油漆公司雇佣,在一次街中漫步时,“我”看到黑人老夫妇被强行搬迁的困窘,因为“我”的气愤上前阻止和劝说:“黑人兄弟们,这不是办法,我们的民族是守法的,是不轻易发怒的。”虽然“我”的义愤填膺无济于事,但却引起了激进组织“兄弟会”的注意,最后被邀请到这个组织中参与活动,在这个组织中“我”发现我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是“我”发现这个组织的领导人知识浅薄,“我”常常被安排做一些我并不喜欢的事情,“我”重新获得的自我又逐渐地失去。在一次斗争中,“我”乔装打扮想要逃脱,不料却成了莱因哈特,同时获得了流氓、赌徒、情夫及牧师等多种身份,经过一系列的事情,“我”陷入了深思,开始意识自己到底是谁,究竟是什么身份。当外在的世界遗弃“我”之后,“我”开始将目光转向内心的世界,进而去发泄自我,发现自我,最后在一次偶然中,“我”在逃离险境时跌入一个地洞,从此便以地洞为家,并最终在自我的反省过程中反复思考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
二 原型概述
原型批评家弗莱曾指出原型是“典型的即反复出现的形象”,当某一自然现象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就不能把该自然现象定义成巧合,其反复的出现显示出了一种隐含的自然关系,而文学作品正是模仿这种关系去建构文本。并且弗莱还认为,神话作为一种具有具象意义的模型,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延续与发展。弗莱本人偏重于神话原型对文学的影响与作用,并且认为神话即是文学之母,又是文学的基本模式,其文学所有的体裁类型只不过是神话不同变体[2]。因为就神话本身来说,其自身就是多重的原型。
原型批评是上世纪西方文论史上较为重要的文学批评模式,曾一度被美国文学评论家韦勒克赞誉为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批评三足鼎立的国际性文学批评。弗莱把原型的定义从荣格的心理学范畴中移到了文学领域,并最终建立以“文学原型”为核心的原型批评理论,并且还认为是一种移位的神话[3]。弗莱本人还认为,文学性生成的来源便是对神话不同程度的移用,换句话来说,是在一个平常的和外部客观世界的逻辑、情理都相互一致的故事中加入神话移用,使得原本的故事因情节的怪诞获得一个抽象的文学性质。故事中引入神话能够表达出叙述者的同情,并且隐含作者的倾向与态度也能够寓于其中。神话具有超越世人的力量,能够表达出超越某一具体故事中最为一般的意义,即抽象主义。
三 《看不见的人》中的多重原型分析
(一)失乐园亚当原型的运用
作为《看不见的人》中多重原型之一,亚当的原型主要体现在“看不见的人”的天真与无知上。作者对该原型的运用体现出人类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那便是人从混沌状态到自我意识的觉醒。亚当本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尘土造成的有灵之人,并且用亚当的肋骨造就了夏娃,二人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之中,负责看护果树与动物。上帝告诉亚当:“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随意的吃,但是分别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最后,亚当与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分别善恶果树上的果子,犯下了原罪,被上帝逐出伊甸园。
其亚当的原型体现在“我”身上,既有自身的天真无知,也有对伊甸园大学的向往。在作品的前言中,“我”将自己看不见的原因解释为视力原因,而在当时的美国,文学作品中常常用视力弱和眼盲问题比喻天真与无知。并且“我”看不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我”周遭人眼疾的问题。在作品的第一章节中,埃里森特意强调了“我”对外部世界的信仰,在祖父临终遗言中,“我”发现对白人顺从的祖父竟然是叛徒和密探,尽管“我”的内心心存疑虑,但是仍然保持着天真的信仰。埃里森为了进一步强调“我”的天真,让“我”参加了集镇上在头面人物面前表演的格斗,此时此刻,“我”还无知地认为是让“我”发表毕业演说。在格斗前后,他们被迫观看穿着美国国旗内裤的金发女郎裸舞,在带电的地毯上获取假金币,虽然这些种种羞辱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可是“我”并没有感受到羞辱,反而以更加激情的态度去迎合白人的演讲。这些种种的细节,足以印证出“我”是一个同亚当一样的无知的少年。此外,亚当原型在“我”身上还体现在“我”对南方大学生活的向往。“我”作为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看似和谐的校园中自由自在地生活,并且作为一个老实的黑人,“我”愉快地接受生活给予我的一切,在这所校园里“我”生活得相当安逸,如同亚当生活在自己的伊甸园中一样生活在“我”自己的伊甸园中。但是一次意外的事件,“我”被逐出了学校,逐出了“我”梦幻中的伊甸园。事情起始于一次接待慈善家诺顿先生,因为“我”的老实与顺从,“我”按照诺顿先生的要求,无意间将诺顿带到学校附近黑人特鲁布拉德的家中,在特鲁布拉德与诺顿的交谈中,诺顿获知特鲁布拉德与自己的女儿乱伦并且导致女儿怀孕,这一事件使得诺顿大为震惊。并且这一些正是道貌岸然的校长布莱索博士所要一心掩盖的真相,却被“我”轻而易举地在无意中“揭穿了”。因为“我”同亚当一样都破坏了主人给予我们的忠告。因此,“我”也被逐出“我”的伊甸园了。原本无忧无虑的生活被剥夺了,“我”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各种痛苦与屈辱,并且,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抱有一个愿望,那便是回到“我”的伊甸园大学。最后当“我”拖着行李离开校园时,“我”看到了一条蛇,“我”看到一条毒蛇沿着水泥路面急速地向前蠕动,钻进附近的铁管子中[4]。显而易见,埃里森用“蛇”来戏仿《圣经》中亚当的故事。
(二)兔子和熊的原型形象
在《看不见的人》中到处都充斥着布鲁斯黑人歌谣以及不时闪现出的动物意象。但是如果读者自身缺乏对黑人文化特征及黑人文学史的了解,就会忽视这些重要的意象。事实上,文章中的动物意象倾注了埃里森很多的心血,这些动物意象隐喻在小说的结构中,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意义。早在上世纪,罗威茨就认为该作品参照了“兔子与熊”的原型故事模式,但是他本人对此并没有继续研究。如下就《看不见的人》中的兔子和熊的原型形象进行分析。
与原型亚当不同的是,《看不见的人》中兔子和熊的故事是一个美国黑人的民间传说,该传说故事的版本较多。美国著名的评论家梅森·布鲁尔曾在《美国黑人民间传说》中对兔子与熊的故事做过详细的论述。该神话故事是流传于非洲的恶作剧精灵的民间故事,作为一个黑人的民间故事,该神话故事道出了非洲神话对奴隶制的反映。美国黑人的民间兔子故事和非洲民间故事中的兔子角色相似,它用自己精明的诡计战胜了更为强壮的对手。黑人民间传说中的兔子故事,不仅只是具备单纯意义上的逗乐主义,该兔子实际上是象征了奴隶制度本身,拉尔夫·埃里森从美国黑人民间传说中寻找原型体现出作者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主题:“一个人越是意识到自己个人和种族及种族文化的历史,就越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
埃里森正是以兔子原型为出发点,将整个小说中“我”作为熊和兔子之间不停转化的角色。在作品开始的部分,“我”做任何事情都像熊一样笨拙,受尽了兔子(校长布莱索博士)的玩弄。布莱索博士拥有高等学历,如同兔子一样精明。在经历过特鲁布拉德事件后,他想办法把“我”踢出学校,而且还假惺惺地为“我”今后的工作生计着想,为“我”写了七封引荐信,但实际上这七封引荐信并不是帮“我”寻找工作,而是继续加害于“我”。在这第一轮的交锋中,“我”毫无疑问的失败了。在紧接着寻找工作的途中,“我”遇到了形形色色的“兔子”,其中对“我”这只笨熊最具杀伤力的兔子便是兄弟会的杰克。他千方百计地说服“我”加入兄弟会,“我”本以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事实上“我”仍旧被他们视为工具,只会靠演讲舆论来提供给他们帮助的工具。等到兄弟会遭到杀害后,“我”才顿悟过来,这次杀害并不是自杀,而是有组织筹划蓄谋的谋杀。而“我”却又在这次谋杀中充当了工具,“我”同时也在这场蓄谋已久的谋杀中受尽了摆布。
在作品的中间阶段,“我”因油漆工厂爆炸而住院,但是“我”自己的角色却因这次住院而发生了极其戏剧性的变化,“我”失去了原有的记忆和身份,只能记住的是之前唱过的关于兔子大哥的童谣。当医生用卡片提问“我”谁是兔子时,“我”对医生进行了嘲笑。事实上这是我在小说中第一次嘲笑别人,拉尔夫·埃里森巧妙地利用了该情节进行作品人物原型的过渡,“我”从笨拙的大熊一跃而成了机智诙谐的兔子,一度成为众人景仰的演说家。但是就兔子来说,不仅诙谐机智,而且还具有一项本领,那便是善于伪装。“我”同精明的兔子如出一辙也善于伪装,当“我”为了躲避拉斯的追赶,而精心的乔装打扮一番,但是其他人却把我当成了具有多重身份的莱因哈特。在故事的结尾处,当“我”终于变成一个“看不见的人”后,“我”在地下室生活,并且还盗用了电力公司的电,这一举动都意在说明“我”同兔子一样机智。
(三)探索者圆桌骑士的原型
除去亚当和动物兔子和熊的原型后,“我”还具有另外一个原型足以引起众人的思索,那便是“我”“探索者”的形象。世界上最早的探索者是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他们探索的是具有神圣意义的宗教信物圣杯[5]。有先知告知国王和骑士,英伦大地上最为优秀的骑士将能够重新发现圣杯,为争夺这一至高无上的荣誉,他们都开始寻找圣杯,尽管所有的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只有万众的宠儿才能获得圣杯,但是他们仍然毫不放弃的去寻找圣杯,这在一定的意义上也体现出来他们至高无上的信仰。对于这些骑士来说,无休止的探索才是生命长存的意义,作为一个骑士的生存方式,任何理由的半途而废都意味着失败和耻辱。
“我”如同骑士一样,在离开南方的学校后无休止地去寻找工作,并且在被布莱索博士七封引荐信欺骗后,“我”回归校园的梦想化为泡影。“我”为了生存在纽约,步履艰辛地穿梭在大街小巷,仍然找不到一个可供生存的工作。按照美国当局的规定,“我”既然是黑人,必定是看不见的,但是“我”想尽办法想要被看得见,但是事实上人们都不理会“我”的存在。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我”在油漆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好景不长,“我”在一次爆炸中受了重伤,在治疗许久之后,“我”终于出院了,但是却丢掉了工作。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被激进组织的头目所青睐,加入兄弟组织,“我”本以为自己曾经受到的种种苦难今天终于值得了,“我”获得了自由,获得了生存的价值。但是在一次暴乱中,“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是别人的一个工具,这个激进的兄弟会组织并不是帮助黑人改变生活的现状,而是利用黑人发展自己的事业。所以在一次暴动中,“我”在失望之余钻入修理管道最终成为了一个看不见的人。“我”离开南方后,试图在美国的工业社会中获得一席生存之地,“我”顺从过、反抗过,尝试过所有获得身份的事情,但是每一件事都不能使得“我”在美国的工业社会中被别人看见,当一切挫折过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失败的根源都归结于“我”黑色的肤色,因为“我”自身忍受不了作为一个“看不见的人”的事实,所以才躲藏起来。“我”如同亚瑟王的骑士一样,为了崇高的信仰而不止一次地探索。寻找“我”的黑人身份,在众多困难和艰难险阻之前,“我”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勇往直前。但是在最后的街头种族暴乱中,“我”彻底地顿悟了,靠一己之力是永远无法被看见的,只因为是黑人,“我”便成为一个无法被看见的人,“我”的希望被破灭,“我”的探索以失败结尾。埃里森此处的原型更能体现出“我”寻找身份之路的艰辛,也暗示身份如同圣杯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四 结 语
原型意象在文学作品中是极其常见的意象,作者通过对原型高度的重复和升华,引发读者的共鸣,并且引发深刻的感情[6]。拉尔夫·埃里森的成功之处,并不在于对原型的简单运用,他用自己独有的文学敏感性及独特的写作视角将众多的神话原型进行戏仿和传承,使之能够表达出作者创作小说的真正意图,同时也满足人们精神的需求。文学作品中原型的运用能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到不断延续的创新与发展,既为文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文学元素,也能够满足人们对文学作品不断变化的需求。
[1]陈晓菊.荒谬的极限处境与自我追寻——《看不见的人》之存在主义解读[J].宁波大学学报,2010,(5).
[2]郭利云.美国黑人文学的经典传奇——论拉尔夫·埃里森《看不见的人》的经典性[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 (4).
[3]石发林,邓彦东.对自由和身份的探求——论拉尔夫·埃利森小说《看不见的人》中的主人公[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3).
[4][美]拉尔夫·埃里森(伍绍曾,张德中等译).看不见的人[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5]王春芳.简析《看不见的人》中的原型[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与教学),2011,(1).
[6]易立君.论《看不见的人》的神话原型与作用[J].湖南社会科学,2007,(2).
(责任编校:呙艳妮)
I106
A
1673-2219(2015)04-0039-03
2015-01-15
广东省高职教育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改革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2013042)。
付洁(1973-),女,湖南岳阳人,硕士研究生,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