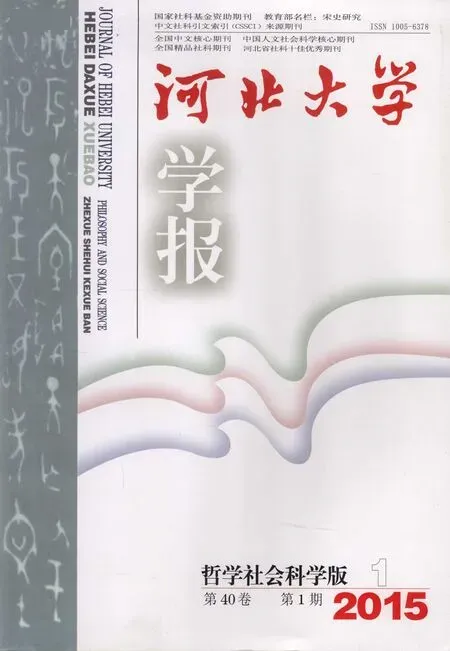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
赵志强
(石家庄学院 马列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与策略
赵志强
(石家庄学院 马列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35)
农村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难题的突破口,在当前的压力型体制下,农村互助养老工程的推进存在着选择性政策执行、数字式年度考核与乡村敷衍性应对、供给主体的责任缺失与乡村信任危机。推动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必须改变压力型体制,构建服务型政府;改变量化考核偏好,提高群众参与性;以农村互助养老为平台,农民养老需求为导向,构建整体性养老保障体系。
农村互助养老;压力型体制;乡村社会资本
农村老人特别是空巢、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各地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社会课题,各地地方政府和研究者不断研究和设计不同的方案,但成效甚微。2008年,邯郸市肥乡县前屯村创造性地建立了农村互助幸福院,主要特征是“集体建院、集中居住、自我保障、互助服务”,主要解决了经济有保障、身体健康的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河北省力图通过这一模式突破农村养老困局。2010年,河北省决定在全省推广农村养老“幸福工程”活动,明确用5年时间,即到2015年,全省实现农村互助幸福院基本覆盖的目标。2012年民政部开始推广肥乡模式,全国各地都在结合本地特点推行这一模式。
然而,在看到农村社会养老“幸福工程”建设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管理与使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的一些不足。在一些地方,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的热度与建成后的冷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些地方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建成后却无人入住,大门紧闭,几乎成了摆设,成了装点门面的“道具”,变成了应付上级检查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视角
1998年,荣敬本带领的课题组提出了“压力型体制”的概念。这一概念是指“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1]。杨雪冬在原来两要素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三要素结构,即:数量化的任务分解机制、各部门共同参与的问题解决机制、物质化的多层次评价体系[2]。“压力型体制”成为很多学者用以研究在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建设中政府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压力型体制为组织和个人提供了推诿责任的合理依据,在此体制下,基层政府关注的是对表面性政绩的考核,很难从乡村内在的真实需求出发,最终的结果是下级为迎合上级的评价标准搞数字游戏,强调表面数量或规模,不顾实际质量需求,也容易导致农村工作缺乏动力和活力。Polanyi在《大变革》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思想[3],但他的思想并不完善。1985年,Granovetter
对“嵌入性”做出了全新的解释[4],他以社会网为分析工具,论证了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密切关系,从而使嵌入性具有迁移性,为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嵌入性包括关系嵌入性和制度嵌入性两种类型。关系嵌入性是指人的行为受到其所嵌入的关系网络的约束;制度嵌入性认为行动者所在的网络是嵌入于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等结构之中的,即人的行为受到所嵌入其中的制度的约束。农村互助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农村养老模式,虽然产生于乡村的自发实践,但推广的主导者是具有压力型特征的政府。因此,农村互助养老必须嵌入压力型体制之中,地方政府和乡村社区要想完成好这一任务,习惯使然地要通过各种途径嵌入这种模式。笔者试图从“压力型体制”和“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就现行体制下的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发展困境问题进行分析。
二、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困境
在压力型体制下,政府是农村互助养老推广和发展的主导者,在农村互助养老的推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对于农村互助养老的推广、建设与发展方面,基层政府和乡村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迎合上级的精神,按照上级要求来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当前农村互助养老的爆发式发展路径,带有压力型体制产物的明显特征,其工作机制仍然属于自上而下的动员模式。之所以没有工作机制创新,一是政府行为的强大惯性使创新思维受限,二是压力型路径在限期完成任务时依然有效。
在各地迅速建设的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中,一些示范型幸福院能够按照规定的要求规范运行,但相当部分的农村互助幸福院存在着徒有其表、重建轻管、甚至无人入住等现象,表面上看是农民传统养儿养老观念及幸福院管理存在缺陷,其本质则是我国压力型体制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农村互助养老建设的过程可以分为确定任务指标、分解指标任务、派发指标任务、完成指标任务和评价等五个阶段。这一过程的主要特征是将任务和指标进行量化分解,从县到乡镇直到乡村,层层分解;评定的主要标准是完成建设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并与干部的评定、升迁挂钩,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5]。这种行政权力压力的指向同样是自上而下的,高度依赖政府的政治权威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度的管理。当前农村互助养老工程的建设基本就是遵循这一路径来实现的。
目前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要迅速发展就必须嵌入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之中。然而,压力型体制的弊端阻碍着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制度嵌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压力型体制下县乡地方的选择性政策执行
我国地方行政中已经形成了一种“选择性政策执行”的现象。所谓选择性政策执行,是指基层官员包括村干部在执行上级政府命令时倾向于“硬指标”,而忽视、冷处理“软指标”的现象[6]。农村互助养老建设成为农村社会建设的指标任务,乡村干部作为政策落实的执行者,必须按照要求去完成。据了解,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农村社会养老“幸福工程”的意见》,推动建设农村幸福院。按照河北省的规划,要求到2015年实现全覆盖,并列入地方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将这一工作列入年度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各地根据自身的实际和政绩的追求,都制定了提前完成的规划。在这种压力型体制下,乡村地方的选择性政策执行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互助幸福院工程的良性发展,并引发了各地不断刷新建设数字飙升的短期行为,甚至公然作假的行为。农村互助养老模式要良性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嵌入目前的行政制度环境,而基层政府和乡村社区的政绩工程与造假行为会对农村互助养老模式造成致命的危害,导致农村社区成员对农村互助养老的不信任。没有农民的参与,农村互助养老必然成为无源之水。
(二)数字式年度考核与乡村敷衍性应对
地方县乡两级政府在推行农村幸福工程的进程中,往往采取任务分解,层层签订责任状的压力动员方式。在压力型体制下,乡镇这一级的政权组织必须按照各种规章制度和组织程序进行专业化和非人格化的运作;但另一方面,每一层级的任务必须完成,每一项指标必须达到,每一批检查考核组必须应对,乡镇组织的重重压力可想而知[7]。乡村虽然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但在压力型体制下这种自治越来越表现出行政化的特点,乡镇政府的压力会通过种种形式传导到乡村一级。
乡镇政府的包村干部为了完成指标任务,会通过各种手段影响农村干部,甚至乡村两级干部结成利益共同体来应付指标压力,由此产生了重数量轻质量、重硬件轻内涵、重考核轻参与等弊端。县、乡、村干部在农村互助养老幸福工程建设中工作的重点不是要根本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而是形成数字的形式作为政绩向上级报告。在压力型体制下,乡村干部会形成一种自身的抵抗回应模式:一方面采用正式权力强行推行或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等方式完成指标任务,另一方面乡村干部采用造假和说谎的手段来应付上级的检查评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不可避免地妨碍农村互助幸福院的正常建设与效用发挥。
(三)建设供给主体责任缺失与乡村信任危机
农村互助养老属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保障空巢、留守老人弱势群体权益等需求的农村公共物品。农村公共物品的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中央、省、市政府应在农村互助养老供给中发挥主要作用,并承担政策制定和财政供给的责任。事实上目前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供给责任一开始就是由基层的县、乡政府部门承担,而建设责任则由乡、村来承担的。
按照农村互助幸福院的建设原则虽然建设主体是村集体,但由于村集体经济普遍羸弱,除一些集体经济比较雄厚的乡村外,每个互助幸福院投资3万元,再加上每年不菲的运营成本,对于不少集体经济薄弱的乡村来说,压力也是不小的。一些乡村也出现了互助幸福院开办了时间不长,就因为缺乏运营费用而被迫关门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是乡村干部责任意识不强,二是农村一事一议的财政补贴制度落实不到位,三是国家的建设主体责任缺失。一个只建设不运营的互助幸福院空有躯壳,摆在那里只会让老百姓寒心。在建设的时候没有征求百姓的意见,仅仅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结果只会是劳民伤财,更严重的是会进一步丧失村民信任,导致乡村信任危机。
三、压力型体制下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策略
(一)改变压力型体制,构建服务型政府
压力型体制造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目标任务承包系统,导致了农村互助养老发展的困境。省政府制定的互助幸福院2015年全覆盖的目标成为乡村的中心工作。这种来自于上级的强制性供给模式的潜意识认为,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是绝对正确的,是所有农村老人迫切需要的。而实际调查证明,由于农村养老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农村互助养老模式与乡村干部的观念以及农村实际养老需求存在着落差,导致相当的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徒有数字和建筑物,而没有形成实际的养老供给。因此,欲排除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性供需矛盾,就必须改革压力型体制,更新政府行政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确立以服务为核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其次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政府主导与社会组织协同、公民参与相结合的社会参与机制;第三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互助养老绩效评估机制。
(二)改变量化考核偏好,提高群众参与性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幸福工程的考核办法有其合理的一面,可以使上级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迅速传达到基层。但由于压力型体制中的考核目标设置主体单一,仅仅来自上级政府的任务下达,缺乏来自乡村组织和农民等多方主体的协商与合作,与乡村组织的实际条件不相匹配,并缺乏必需的反馈机制,造成了互助幸福工程数字成绩突出、实际效果不佳的现状。
发展农村互助养老是为了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难题,最有评价资格的是农村老人。因此,必需改变量化考核偏好,建立和完善新的综合性的互助养老实效评估指标体系,指标设置中引入有助于提升农村互助养老内涵的重要事项。同时,在对乡村基层政府的政绩评价方式上,应将建设互助养老幸福工程的绩效评判交给群众,由群众来考核乡村政府和干部建设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的政绩,从根本上改变“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的状况,将“单轨”运行的压力型体制改变为上下结合的“双轨”运行机制,才能扭转乡村信任危机。
(三)以农村互助养老为平台,农民养老需求为导向,构建整体性养老保障体系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养老模式,农民自己最有发言权。在目前阶段,并不是每一个农村都需要建设互助幸福院。传统的孝文化和居家养老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着人们对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的认同,毕竟农村老人理想的养老模式还是父慈子孝、儿孙绕膝。因此,可以以农村互助养老为平台,以农民养老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护理保险制度、老年人福利补贴制度、社会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农村养老保障法及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整体性养老保障体系。
[1]荣敬本: 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28
[2]杨雪冬. 压力型体制: 一个概念的简明史[J].社会科学,2012 ( 11):4-12.
[3]POLANYIK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M]. Boston, MA: Boston Press,1944.
[4]GRANOVETTERM. Economicaction and social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91(3):481-510.
[5]陈槟城.论压力型体制下的乡政困境[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5(6):22-25.
[6]KEVINJ,O'BRIEN,LIANJIANGLI.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J].Comparative Politics,1999,91(3):167-186.
[7]欧阳静.运作于压力型科层制与乡土社会之间的乡镇政权[J].社会,2009 (5):39.
【责任编辑 卢春艳】
Analysis on Dilemma and Strategy of Rural Mutual Pension Model Development
ZHAO zhi-qiang(Department of Marxism-Leninism Teaching,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5,China)
Rural mutual pension is the breakthrough to solve the rural old-age problem, but this mode must be embedded in the current pressure system. Under the pressure system, rural endowment project there are lack of responsibility and rural trust crisis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digital annual examination and rural perfunctory coping, the main supply.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pressure system,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ystem, reverse the rural crisis of confidence. To promote rural mutual pension development, we must change the pressure system,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changing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preference, improv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rural mutual pension as a platform, farmers pension demand oriented,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old-age security system.
rural mutual pension; pressure system; institutional embededness
2014-09-10
2013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社会资本与嵌入性:城乡一体化进程下河北省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与优化路径研究》(134576293)
赵志强(1970-),男,河北衡水人,石家庄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农村养老保障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D669
A
1005-6378(2015)01-0072-04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