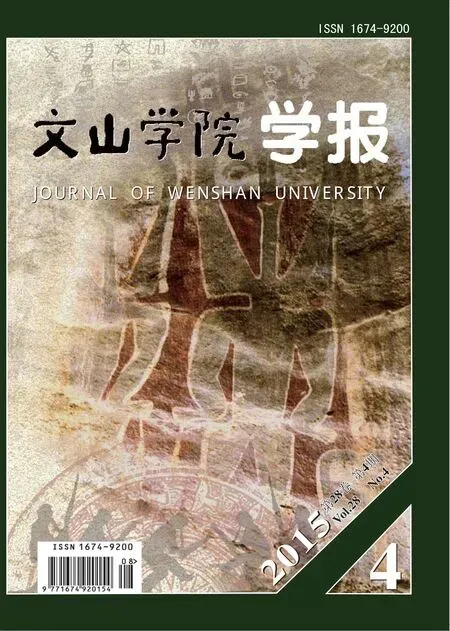试论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
方铁
(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试论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
方铁
(云南大学 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具有历史积淀深厚,总体特征鲜明,类型复杂多样,民族性与区域性的差异明显等特点。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可概括为爱国、宽厚、求实、企稳等方面。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受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云南与内地的关系、云南的民族关系等因素的复杂影响。
关键词:云南各民族;人文精神;群体性格
一、关于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
现今我国的省级行政单位,是在长期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形成的。省级行政单位的划分与确定,受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完整性,以及省区之间的差异性及其互补、协调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可否认,现今确定的省级行政单位,不仅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类型为基础,还涉及长期发展所形成的历史与文化的传统。[1]简言之,省级行政单位既是相对独立的社会演进与经济建设的单元,是资源配置和自然环境类型相对独立的单元,也是历史文化传统相对完整的人文单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省级行政单位的众多居民,必定有不同于其他省区的历史、文化乃至群体性格。
考虑到上述的诸多因素,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或称群体性格),必然表现出历史积淀深厚,总体特征统一而且鲜明,类型复杂多样,民族性与区域性的差异明显等特征。研究这一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云南各民族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扬长避短,注意改正或克服不利的方面,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云南省所具有的特点,在地缘关系方面,大致地处中国的西南部边陲,为联系相邻省区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枢纽,以及沟通邻邦与内地的门户。在社会结构与发展程度方面,主要是拥有众多民族,人口数量较多,但人口分布不平衡(坝子人口密集,丘陵地区次之,高山地区人口稀少),以及社会发展程度普遍偏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社会发展的水平差异甚大。
云南地区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云南地区便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以后与祖国内地的政治联系从未断绝过。七世纪南诏建立,以后初步统一云南地区。十三世纪元朝在云南地区建立行省,云南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辖下的一省。相邻的广西、贵州两省建省都比较晚,广西正式建省是在元代末年,贵州正式建省是在明代中期。若论历史之悠久和历史发展过程之复杂,在西南地区除四川盆地以外,当以云南地区为最。
在西南地区,云南是民族最多、社会和文化最为复杂多元的区域。现今人口在5000人以上的民族,在云南省有26个,支系在200个以上。历史上云南还曾存在过现已不存在的民族,以后被其他民族融合。受复杂的地形与气候条件的影响,云南地区存在坝子、山地相对的一种二元性社会结构,深刻影响了云南地区的发展。若进一步划分,云南还可分为高坝经济、低坝经济、坝子结合丘陵经济、坝子结合湿地经济、山地经济等不同的类型,云南民族、云南社会与经济的多元,由此派生出众多不同的文化类型。
云南是中国通往中南半岛和南亚地区的主要门户,也是西部开发较早、人口较密集的地区,西南地区历史上出现的两个边疆政权南诏、大理国,都以云南为活动中心。目前云南省有人口4600余万人,在云南、广西和贵州三省中是人口最多的省。
受以上因素的影响,云南各民族不仅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其人文精神在西部地区也堪称典型,值得深入探讨和总结。经多年研究,我认为云南各民族的人文精神,可以概括为爱国、宽厚、求实、企稳几个方面。
二、人文精神中的爱国精神
云南各民族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在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以及珍惜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这两个方面。
云南各民族对祖国有深厚的感情。总体上来看,云南各民族对国家和中央政府有深刻的政治认同,普遍有维护祖国统一和归属中国的观念,对中央政府怀有崇敬和遵从的深厚感情。这些观念和感情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对云南各民族于国家和中央政府有深刻的认同,可以用文化圈的理论来解释。[2]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圈,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是该文化圈中的亚文化部分,并受到中华文化圈的支配和影响。云南各民族的文化基本上属于农业文化,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内地的人口、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使原有的初级农业文化得到积累和提升,与内地华夏文化的差异也逐渐缩小。这些特点使云南各民族与内地文化有明显的亲近感,因此成为云南与内地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石。因此,云南文化圈与华夏文化圈两者虽有一定的差异并相互交叠,但内涵接近且处于同质演化的过程,或者说云南文化圈被华夏文化圈所覆盖及影响。
郭沫若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北方防御,南方浸润”,并解释“浸润”主要是文化浸润。[3]446郭老所说的“北方防御”,大致是指游牧民族不断南下,给中原王朝造成很大压力,双方的关系主要是前者南下侵扰和后者防御的关系,民族融合的特点,是发展中充满矛盾,融合过程主要表现为激烈的斗争。所谓“南方浸润”,则是指南方少数民族很少进入中原,而与中原汉族在文化上有较多的相通之处,双方的关系主要是南方民族为中原汉文化所浸润,民族融合呈现渐进式发展、嵌入式融合的过程。云南各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在南方民族地区堪称是一个典型。
由于与内地民族同属汉文化圈,以及历史上受到中华主流文明较多影响等原因,云南各民族认同祖国的归属感十分明显。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南子弟兵远赴东部的抗日战场,以惨痛伤亡为代价,取得全国称颂的骄人战绩。即便是在云南与境外地区均有分布的云南跨境民族,也普遍有认同祖国的归属感。他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在祖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侵犯时,云南的跨境民族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以鲜血乃至生命捍卫祖国的尊严。
以临沧地区的佤族为例。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占领缅甸,进而窥觇中国云南。云南佤族为保卫祖国的疆土与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严惩潜入云南的英国间谍,抵制英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班洪地区的佤族还提出“不准信基督教”的口号。1934年驻缅英军进入云南省的班洪、班老地区,当地佤族1000余人坚决抵抗并赶走侵略者。以班洪为首的17个佤族部落的首领,联合发出《告祖国同胞书》:“我佧佤山数十万户之民,宁血流成河,断不做英帝国之奴隶”,[4]12与班洪事件类似的事件,还有西双版纳傣族为反对清政府割让勐乌、乌得地区进行的斗争。这些史迹充分表现了我国跨境民族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其基础便是对祖国和中央政府的深刻认同。
云南各民族十分珍惜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明确了少数民族的法律身份,通过宪法和相关法规立法的途径,确认了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与平等地位,并在实践中努力贯彻和实施。同时,通过积极支持边疆省份的经济建设,予以边疆民族地区各项优惠政策和资金倾斜,有力地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为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左倾思想尤其是“文革”的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领袖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文革”结束后云南省很快走出阴影。改革开放以后,云南的发展回到正常轨道,党和政府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落实,这是云南省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的前提。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团结问题,开展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由于云南的民族关系较好,社会比较稳定,改革开放的各项措施得到切实落实,云南各民族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据媒体报道,近年相关机构进行调查统计,认为在各省区中云南人民的幸福感最强,这不是偶然的。可以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争取得到更大的发展,是云南各民族共同的心愿,也为进一步增进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人文精神中的宽厚精神
具备待人宽厚的群体性格,是云南各民族人文精神的另一个方面,具体表现在民族和睦、宽广包容两个方面。
关于民族和睦。具体来说就是云南各民族真心团结,重视营造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上述的这些特点,是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5]
云南传统的民族关系,大致有以下特点:一是各民族的关系比较和睦及和谐,长期以来各民族相互杂居、混同乃至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二是受云南复杂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多样性的影响,云南地区不仅民族的种类较多,同一民族内部支系亦较复杂,在各民族以及同一民族内部,普遍存在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存和互补互助的关系。三是在云南的民族关系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十分重要乃至起到主导作用。自汉朝在云南地区设郡县,先后有一些汉族人口迁居该地。汉族移民与云南少数民族的融合,大体上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汉族移民与原有民族的差别甚大,在经济文化形态和地域分布方面亦明显不同。随着外来移民逐渐融入原有民族,约在南北朝时形成新的本地民族白蛮。元代以后,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在数量和影响方面迅速扩大,民族融合的倾向转变为以汉族移民为主融合白蛮等本地民族。约在明清之际,以大中坝子和重要交通沿线为主要聚居地,逐渐形成云南新的汉族群体,并成为云南地区影响最大的民族。明清时期汉族在云南各民族中不仅力量最强,而且受到少数民族的普遍敬重。云南汉族对少数民族也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普遍视少数民族为骨肉乡亲。
云南各民族分布的状况,对民族关系也有重要影响。云南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在广大高原和山地间分布一些大小各异的坝子。云南各民族的居住分布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状况,不少民族习惯居住在特定海拔高度的地区,与其他民族形成立体插花状较稳定的分布格局。另一方面,受地形交通条件、民族分布与特定的地理生态环境有依存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各民族人口的迁徙活动,普遍呈现渗透式的扩展,速度十分缓慢,而且较少进入其他海拔高度的地区。从很早的时候起,云南地区的各民族便形成交错杂居、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云南基本上不存在因大规模迁徙导致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遗留的负面历史记忆。这是云南地区的民族关系友好共存、协同发展特点的一个重要条件。
前面说过,云南地区长期存在坝子、山地相对的二元性社会结构。由于坝子主要居住的是外来移民(以外来汉族人口为主,自元代起还有以军人、官吏身份移居云南的蒙古族和回族人口),以及受汉族影响较深的白蛮等本地农业民族;而广大山地则主要是彝族、哈尼族等主要从事游牧和旱地种植的少数民族居住。元代以前,云南坝子与山地发展的水平差距甚大,坝子与山地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不多。
自元代起,中原王朝加强对云南山地和僻地的经营,边疆、僻地与少数民族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逐渐形成坝子与山地的联系加强,以及坝子与山地协同发展的潮流,清代这一潮流达到一个高峰。清朝通过对边疆与僻地的大规模改土归流,对这些地区加强管理与开发,鼓励移民迁居边疆和僻地,加快了边疆与僻地的发展,坝子、山地相对的二元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两者关系中合作联系、互补的一面逐渐凸现,形成坝子、山地协调发展的趋势,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也逐渐缩小。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进而形成和谐、互补的民族关系持续发展的局面。
在云南历史上,出现过几次以吸收汉族移民为主的大规模民族融合,主要是汉晋、南诏和元明清时期。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亲密深厚的感情。在云南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占据主要和起支配作用的位置,由此决定了云南民族关系的和睦与和谐,以及与内地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拥有牢靠的社会基础和持续发展的稳定性。进入云南外来移民的来源,根据时间不同有明显差异。大体而言,元代以前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四川盆地,其分布以相邻的云南北部与云南中部较为集中。元明清时期的外来移民,主要沿元代开通由湖广经贵州进入云南东部的驿道迁入,初期散布在这条驿道及其支道的附近地区,以后逐渐深入到人口较少的广大山区和僻地。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云南各民族普遍有守土相安、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的传统;在分布方面亦彼此有别,以后经逐渐混杂才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因此,外来移民与云南原有民族的交往和联系,必然要经历长期的相互熟悉、磨合乃至融合的过程,由此减轻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接触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形成民族和睦传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云南历史上未出现过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也不存在因宗教、民族仇恨等造成的严重创伤。云南地区的宗教,具有种类众多、派系和演变情况复杂的特点,除傣族较普遍信仰上座部佛教外,其他民族未出现广泛信仰同一宗教的情形。云南的宗教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以及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等带原始宗教色彩的早期宗教。一般来说,白族信仰接受藏传佛教和大乘佛教禅宗教派影响的白族密宗佛教,信仰基督教的有彝族、苗族的一部分人口,以及云南西部的一些少数民族;信仰道教的民族有壮族、瑶族等民族。另外,有一些民族仍信仰或部分信仰祖先崇拜、神灵崇拜等早期宗教。在同一民族之中,不同的支系或部分居民分别信仰不同宗教,以及所信仰宗教混合其他宗教成分的情况十分普遍。云南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还有一个特点,即受经济文化发展有限及民族类别众多等的影响,信仰宗教很少出现盲目崇拜与宗教狂热的情形。因此,云南历史上未发生过因宗教冲突所引发的社会动乱。
应该指出,现今云南各民族长期和睦相处,是党和政府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及长期进行教育、积极营造团结氛围的结果。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核心。通过民族区域自治与民族平等政策,云南各民族实现了政治上的平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享受到党和政府的优惠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日益深入人心。
关于宽广包容。这是云南各民族群体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南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总体趋势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分逐渐壮大,汉族与少数民族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各地融合的途径与方式并非是单一的。云南少数民族与南迁汉人的融合,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过程。古代云南出现汉族移民与土著民族的渐进性融合,首先是由于这两个部分长期在较大范围相互杂居,互相影响。秦汉以来主要居住坝子的僰人,在不断吸收外来人口和发展较快的情形下,在南北朝时期形成新的民族群体白蛮。白蛮的发展水平较僰人要高得多,其中最活跃的部分由汉族移民的后裔演变而来。元代以后,迁入云南的汉族移民大量增加,民族融合的倾向转变为以汉族移民为主融合本地民族;约在明清之际,以大中坝子和交通沿线为聚居地形成云南的汉族群体。
汉族在云南被少数民族视为老大哥。在云南的民族关系中,汉族起到粘合剂与核心成员的作用。云南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与外族通婚,其中通婚数量最多的便是汉族;即便是少与外族通婚的民族,通常亦与汉族通婚。云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较好,是云南民族关系较为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云南汉族也吸收了大量的少数民族血统,少数民族也有一些是由迁来的汉族人口演变而来,由此决定了在云南地区,各民族普遍具有宽广、包容这一萌生于当地历史文化的人文精神。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历史上虽然也存在大民族统治小民族的情形,但由于总体发展水平相近,在较大范围内长期相互杂居,以及汉族在民族关系中起到凝聚剂的作用,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这对弘扬宽广、包容的人文精神也是有利的。
云南各民族普遍具有宽广、包容的人文精神,还与云南地区的宗教信仰处于较低层次有关。在同一民族乃至同一家庭中,不同成员信仰各种宗教的情形并不罕见,但相互之间相处融洽。主要原因是各民族信仰宗教,主要是出自与朋友聚会、希望得到相关团体在治病、扶助等方面的帮助有关。虔诚地信仰某一宗教,甚至愿意为宗教信仰献身的情况较少见。因此,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可以融洽相处。云南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普遍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即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顽强地得以保留,而各民族对彼此的传统文化又十分尊重,不仅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是这样,即便居住在同一村寨的不同民族也是如此,这是各民族具有宽广、包容人文精神的又一表现。
四、人文精神中的求实精神
云南各民族具有求实精神,主要表现在求真务实、踏实肯干这两个方面。
云南各民族具有求真务实的精神,首先,有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方面的原因。云南多山少平地,坝子仅占土地总面积的约6%。云南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十分闭塞。因此,云南大部分民族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社会阶段。云南地区的社会经济,虽可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型,但总体上发展程度有限,经济类型的特点相近,可称之为“初级复合型经济”。[6]初级复合型经济在云南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各民族以发展程度较低的农业为基础,积极经营畜牧业、养殖业、采集和狩猎。其复杂的经济成分和中原单一的农业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初级复合型经济发展的程度通常有限,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于动植物资源充足,人们果腹乃至温饱较为容易,但很难达到与内地比肩的发展水平。即便是发展速度较快的南诏、大理国时期,虽然初步实现了云南地区的局部统一,农业、畜牧业、冶金业和商业等也有较大的发展,但与内地的差距仍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下,各民族收获并积累的成果通常有限,若不务实肯干,日常的温饱便可能成为问题。
其次,在古代很长的时期,云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十分落后,直至明代前期还使用海贝充当货币。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各民族普遍认为种植方能果腹,很少有经商获取商业利润一类的意识。因此脸朝黄土背朝天、从土里刨食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很少设想有其他的谋生方式。从事农业需要的是埋头苦干,一个萝卜一个坑,思路活络、灵活经营则居于次要的地位。
由求真务实的性格,培养出人们踏实肯干的精神。具体表现是性格率真朴实,只知下死力干活,不会偷奸耍滑。若与爱国精神相结合,便表现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以云南军队参加抗日战争为例,[7]27,32,34,67,68,170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按照与蒋介石的约定,在云南曲靖举行誓师,云南第六十军奔赴北方抗日前线。1938年云南组建第二支抗日军队第五十八军,编制、武器和装备与第六十军相同。第五十八军在昆明举行誓师大会后,随即开赴抗日前线。以后,云南又派出新三军、老三军增援抗日前线。这几支云南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条山战役、武汉保卫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中浴血奋战,以生命和鲜血捍卫祖国,为中国抗日军队赢得崇高的声誉。出征北方抗日的云南军队,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形下,均未出现过投敌叛变的行为,始终保持了高尚的民族节操。
云南四个整军出征抗日,在当时各省抗日军队中,损失之大,付出代价之高,都是有目共睹的。在云南组建的四个整军中,除老三军外,其余的第六十军、第五十九军、新三军,兵力和物资均由云南本省补充。据国民政府国防部档案记载,自1937 年8月至1945年8月,中央政府分配云南的征兵任务是370496人,但实际征兵人数达381593人,超过11097人。云南军队先后从本省补充兵员,获得极为积极和迅速的支援。如第六十军在台儿庄战役中损失二万余人,数月之内便补充完毕。第五十九军、新三军在抗战中各伤亡近10万人,均从本省得到及时补充。为支持在前线抗战的将士,云南各界人民还组织经常性的慰问活动,有时由云南省政府出面组织募捐,有时由各界组织的抗敌后援会组织慰劳捐献。据估计,抗战八年中云南人民捐献的寒衣至少在200万件以上。1941年初,全国发起捐款购买飞机,云南抗敌后援会积极组织募捐,很快捐献出飞机30架,名列全国第一。为支援抗日战争,满足美国飞行员以牛肉佐食的需要,各地的耕牛被大量宰杀,几乎陷于绝种,但云南的百姓少有怨言。
又如修建滇缅公路。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国联系海外的交通线主要有三条:即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交通线,以越南海防港为中转站的西南交通线,以及经过甘肃、新疆联系苏联的西北交通线。其中运输量较大、作用显著的是前两条交通线。但这两条通道濒临中国南海,易被日本所阻断。因此。中国政府决定修建从云南通往缅甸仰光的滇缅公路。当年八九月,日本封锁中国东部海岸,中国海上交通几乎断绝。在这样的情形下,修建滇缅公路势在必行。滇缅公路全长959公里,除昆明至下关修通了土路外,需要新建从下关到芒市进入缅甸的548公里新路。这条道路跨越横断山脉及澜沧江等多条河流,施工难度极大。计划在一年内修成,许多外国人表示怀疑。经过动员,沿线17个县10个民族的20万民工,自带口粮和工具,翻山越岭奔赴工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修建。他们克服种种困难,仅用9个月就完成修建滇缅公路的任务,创造了世界公路修建史上的奇迹。
五、人文精神中的企稳精神
企稳精神主要指的是求稳怕乱的心态,大致包括注重稳定与容易满足两个方面。
一般来说,盼望稳定、注重稳定是好事,这是农业民族固有的心理。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后,实现社会稳定更成为人民群众的一致愿望。在这一方面,云南人民企求稳定,积极维护社会安定的局面,是一个积极有利的因素。但云南的一些居民因期盼稳定,进而形成胆小怕事、因循守旧的不良心态,甚至视必需的改革或变动为添乱,这就倾向于消极的方面。人们形成这一不良心态,首先与受云南自然环境与初等级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影响,云南人有容易满足的特性有关。
云南地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俗话说“插根扁担便会发芽”。发展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较容易。但云南的地貌大都是多山少平地,扩大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有限。又因云南地处边疆、长期封闭,给大幅度提高生产水平带来困难。因此人们谋生较容易,但经济发展水平则长期落后于内地。另外,云南的一些民族有温饱即安的传统,只要有饭吃、有衣穿便满足。由于有容易满足、生活欲望简单的特点,云南的一些居民小富即安,生活节奏缓慢拖沓,甚至懒惰不思进取。史籍称清末民初昆明城内的居民,“今日登山,明日玩水,有会必逛,有戏必看,”十足的自由和快乐。刷书匠虽工艺娴熟,但不乐于多做,每日做够买当日所饮大曲酒、所食饭肉及零花钱的开销,便停工歇手。[8]100如上所述的生活观念与习俗,在云南各地的城镇是较普遍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容易满足和懒惰拖沓的特性,使人们缺少开拓精神,固守成规而不思进取,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另外,人们普遍有求稳怕乱、容易满足及盲目顺从的心态,还有长期受土司制度影响方面的原因。[9]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存在600余年,成为联系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桥梁。由于实行土司制度,元明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明显深入,推动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实行土司制度,对稳定边疆和抵抗外国的侵略也起到积极的作用。土司制度深刻影响了边疆民族的思想与性格。在实行土司制度的地区,甚至形成土司文化,成为当地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土司制度也培养了土司及其百姓惧怕上司、顺从求安、不思进取等消极的惰性。在土司制度之下,各级土官、土司须看流官和上级官府的眼色行事,动辄获罪受罚,乃逐渐形成盲目顺从、愚忠愚孝的传统,这也是封建统治者所企望的。数百年间受土司制度的深刻影响,云南民族上层不同程度形成惧上惧官、因循守旧的传统,进而影响到云南整体社会。长期以来,一些人循规蹈矩乃至愚忠愚昧,固守成规不思进取,成为云南人群体性格的消极方面。
总体上来看,云南各民族具有的爱国、宽厚、求实、企稳的人文精神,积极的方面是主要的,是一笔宝贵的人文遗产,也是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重要动力。对于上面所说的某些弱点,我们应认真反省,改掉这些毛病,以便轻装前进,更好地走向未来。
参考文献:
[1]方铁.古代云南与周边地区的关系[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130- 137.
[2]方铁.跨境民族与文化圈[M]//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3]转引自邸永君.陈连开先生访谈录[M]//中国民族研究年鉴·2001年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4]段世琳.班洪抗英纪实[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5]方铁.云南古代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形成原因[J].社会科学战线,2013(7):130- 136.
[6]方铁.论影响云贵高原开发的社会历史因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49- 56.
[7]孙代兴,等.云南抗日战争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8](民国)罗养儒.谈六七十年前昆明人之生活[M]//云南掌故·卷四.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9]方铁.土司制度及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56- 61.
(责任编辑杨永福)
On the National Spirits of Humanities in Yunnan
FANG Tie
(Nationality Research Institut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spirits of humanities in Yunnan are characterized by profound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distinct overall features, complex types and distinctive national and regional features. It can be summarized as patriotism, lenience, realism and stabilization. It forms gradually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is infl uenced by production and living ways, relationship between Yunnan and inner regions, and relationship among nationalities.
Key words:Yunnan nationalities; spirits of humanities; group characters
作者简介:方 铁,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 - 04 - 21
中图分类号:K28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 - 9200(2015)04 - 0035 - 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