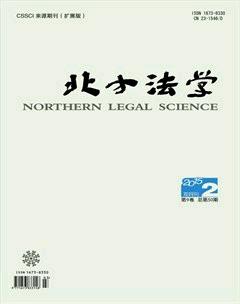国际投资间接征收的中国关切
摘要:21世纪初以来,国际投资条约出现了公益化革新的趋向,其核心是平衡投资者和东道国利益。间接征收是涉及利益平衡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双重身份,面临间接征收挑战。然而,中国已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条款存在严重缺陷,亟需改进。因此,必须认真关切间接征收问题,未雨绸缪。应该明确中国的投资协定政策定位,规范和完善中国投资协定的间接征收条款。
关键词:国际投资间接征收投资协定
中图分类号:DF9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2-0084-09
一、背景:投资协定的公益化革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加快走出去步伐。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这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新形势下,如何商签投资协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现行绝大多数的国际投资协定都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中心而构建的。晚近以来,因有关公益保护措施引发的国际投资争端的大量增加以及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漠视公共利益现象的频发,凸显了现行国际投资条约法对公共利益保护之不足及其保护公共利益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需要进行公益化革新。①因此,21 世纪初期以来,出现了平衡外国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趋势,不同国家和地区逐步调整立场定位,国际投资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②正如联合国贸发会(UNCTAD)所总结的,各国一方面进一步推动投资管理体制自由化,促进外国投资,另一方面控制投资,以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与自由化进程同步制订妥善的管理和体制构架。③为此,必须加强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层面,平衡国家与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确保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留出充足的政策空间,使得投资促进条款更加具体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④ 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实践越来越倾向于此。⑤
具体而言,需要对国际投资协定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进行改革,应根据每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确定保护外国投资与维持国内监管政策空间之间的合理平衡。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对政府政策空间的担忧问题、国家与投资者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并有效促进投资。为了保证投资保护义务与为发展留出的监管空间之间适当的平衡,国家可以通过仔细制定国际投资协定,清晰阐述协议中含糊的条款的含义和范围,以及运用具体的灵活机制,保护政府政策空间。在上述公益化革新中,就包括对“间接征收”条款的厘清与改进,⑥原因在于间接征收是一个事关投资者权利和政府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空间的重大问题,并且极易引发投资争端。
我国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也存在公共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必须进行公益化革新。在国际投资协定出现新的发展趋势的历史条件下,由于中国已经是资本输入大国、并且正在成长为资本输出大国,中国应该在投资条约实践中,平衡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的权益以及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权益。⑦在这一背景下,由于中国面临间接征收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关切。
二、挑战:中国面临间接征收问题
间接征收问题日益成为东道国、外国投资者乃至资本输出国共同面临的重要风险;成为既继续体现南北矛盾,又超越南北矛盾的复杂问题。⑧中国同样面临这一问题。
目前,中国在全球直接投资流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是资本输入大国,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1月,中国累计利用外资13900亿美元;2010年至2013年,中国每年利用外资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⑨年引资量位居世界前两位。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法治化程度仍然较低,目前又处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发展时期。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措施)很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外资企业,触动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并被指控实施间接征收。在现实中,已经发生构成间接征收事实的案例。⑩作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投资者诉诸国际投资仲裁的潜在风险不断增加。这将不利于我国的发展。
中国的海外投资已经和正在面临各种投资风险,存在被间接征收的可能,如何切实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利益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我国对外投资在迅速增加。2012年,在最大的投资国中,中国从第六位升至第三位,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14年1月,我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329亿美元。由于投资分布的国家和行业都很广泛,在东道国为保护公共利益或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采取国家规制措施时,中国的对外投资也面临着很大的间接征收风险。例如,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一些东道国政府采取特别措施,对我国企业的海外金融类投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平安公司—富通集团案”就是中国海外投资被间接征收的例证。2012年9月,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正式向ICSID申请仲裁,向比利时政府索赔228亿美元。随着我国海外投资的日益壮大,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利益已经成为我国投资保护协定的新课题。
总之,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仍将继续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因此必将继续大量吸引利用外国投资和推动对外投资。中国被外国投资者指控间接征收以及中国的对外投资被东道国间接征收的可能性都很大,间接征收事关国家和企业利益。因此,我们必须重视间接征收问题。
三、现实:有关条约规定存在缺陷
由于国际投资协定既事关我国作为东道国的权力和义务,同时对于促进和保护我国的海外投资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我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法律保证,所以,应分析和研究我国有关间接征收的条约规定,未雨绸缪。然而,现实是我国签订的投资条约中的间接征收规定存在诸多不足,表现如下:
(一)间接征收规定过于简单
从1982年中国与瑞典签订第一个双边投资条约以来,截至2013年底,中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有145个,其中双边投资协定128个,其他形式的国际投资协定17个。
我国缔结的第一个投资协定就规定了间接征收,但是规定非常简单,不仅定义模糊,而且没有规定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和方法,更没有规定不构成间接征收的例外。中国—瑞典投资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缔约任何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只有为了公共利益,按照适当的法律程序,并给予补偿,方可实行征收或国有化,或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这里的“采取任何类似的其他措施”其实就是间接征收。
与此类似,此后的投资协定均规定了间接征收,不过措辞不尽相同,如“其他类似效果的措施”、 “其他效果相同的类似措施”、 “其他效果相同的措施”、“其他类似措施”、 “其他等同措施”、 “或其他与国有化或征收有相同效果的措施”、 “或其效果相当于征收、国有化的任何其他措施”、 “或其他产生剥夺效果的措施”等。其表述方式,基本都是在“征收或国有化”之后,加上这些措辞。此外,还有其他的表述,比如,“任何缔约方不得直接地,或者通过与征收、国有化相当的措施间接地,征收或国有化 (以下称“征收”)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尤其是中国和德国2003年12月1日修改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第4条规定:“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直接或间接地征收、国有化或者对其采取具有征收、国有化效果的其他任何措施。”这一规定与NFATA第1110条对征收的规定基本相同。
经统计,我国签订的145个投资协定中,有138个(约占总数的95%)对间接征收的规定非常简单,均没有对间接征收进行概念性界定,也没有规定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和方法。这种状况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为间接征收概念与规则的不确定性是引发复杂的间接征收问题的原因之一,这些模糊的间接征收规定本身就隐含着发生间接征收纠纷的法律风险。
(二)新签投资条约仍有不足
目前,比较具体地规定了间接征收的投资协定,仅有近些年与印度、哥伦比亚、加拿大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与日本、韩国的三边投资协定,以及与新西兰、秘鲁、智利分别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投资章节或关于投资的补充协定。然而,这些数量有限的比较具体地规定了间接征收的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相关规定也存在许多不足。
1间接征收的定义及认定标准不一
2006年11月21日签订的中印双边投资协定第5条第1款规定:“缔约任何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投资不得被国有化、征收或采取效用等同于国有化或征收的措施……”中印双边投资协定议定书第3条规定:“关于对第5条中征收的解释,缔约双方确认以下共识:(1)除了通过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的形式进行的直接征收或国有化外,征收措施包括一方为达到使投资者的投资陷于实质上无法产生收益或不能产生回报之境地,但不涉及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而有意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2)在某一特定情形下确定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是否构成上述第一款所指的措施,需进行以事实为依据、各案进行的审查,并考虑包括以下在内的各因素: a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的经济影响,但仅仅有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这一事实不足以推断已经发生了征收或国有化;b该措施在范围或适用上歧视某一方或某一投资者或某一企业的程度;c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违背明显、合理、以投资为依据的预期之程度;d该措施或该一系列措施的性质和目的,是否为了善意的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以及在该等措施和征收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
美国2004BIT范本规定:“(a)在具体的事实情况中,确定一缔约方的一个或一系列行为是否构成间接征收,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的个案分析,并考虑其他因素:(1)政府行为的经济影响,但仅仅有一缔约方的一个或一系列行为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具有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尚不足以确定间接征收已经发生;(2)政府行为对明显的、合理的,投资赖以进行的期待的干预程度;(3)政府行为的特征;(b)除了在极少情况下,一缔约方实施的旨在、并且适用于保护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的非歧视管制行为,不构成间接征收。”
在我国30余年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中,中印双边投资协定第一次对间接征收的含义及认定做了明确规定。它同时还参考有关间接征收的仲裁实践以及新近其他一些国家的条约实践(如美国),规定了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和方法,并且有所创造:一是增加了一项认定标准,即“该措施在范围或适用上歧视某一方或某一投资者或某一企业的程度”;二是在“目的标准”上,不仅要求考虑措施的性质和目的,还进一步明确要求考虑措施“是否为了善意的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以及在该等措施和征收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这为究竟如何考虑措施的性质和目的提供了指引。国内有学者评价道,“虽然中国—印度BIT议定书第3条的内容基本上‘脱胎于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但前者似乎显得更具确定性,也更为谨慎,因为它包含着某些在后者中至今尚未直接、明确规定的内容:其一,对间接征收的界定更具体,即其指‘一方为达到使投资者的投资陷于实质上无法产生收益或不能产生回报之境地,但不涉及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而有意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第1款);其二,明确把是否存在歧视,尤其歧视之程度确立为认定间接征收的重要因素(第2款第2项);其三,不仅规定了特定政府措施的‘特征,并且明确规定了‘目的(第1款及第2款第4项),据此表明了‘目的因素在认定间接征收方面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在丰富、完善间接征收规则方面,较之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中国—印度BIT议定书第3条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008年4月7日签订的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就间接征收的定义、认定标准和方法也做了规定。具体规定如下:“1.除非一方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举措干涉到投资的有形或无形财产权利或财产利益,否则不构成征收。2.征收可以是直接或间接的:(1)直接征收发生在政府完全取得投资者财产的情况下,包括通过国有化、法律强制或没收等手段;(2)间接征收发生在政府通过等同于直接征收的方式取得投资者财产的情况下,此时,尽管其举措不构成上述第(1)项所列情况,但政府实质上剥夺了投资者对其财产的使用权。3.构成间接征收,政府剥夺投资者财产的行为必须为:(1)严重的或无限期的;并且(2)与公共目的不相称。4.在以下情况下,对财产的剥夺应被认为构成间接征收:(1)效果上是歧视性的,既可能是针对特定投资者的,也可能是针对投资者所属的一个类别的;或者(2)违反政府对事前向投资者所做的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承诺,无论此种承诺是通过协议、许可还是其他法律文件做出的”。
不难发现,在体例和结构上,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的规定更接近近年来美国的国际投资条约实践。在内容上,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第1条的用语和美国2004年BIT范本完全一样,第2条的规定也类似,但更明确,直接规定“政府实质上剥夺了投资者对其财产的使用权”;在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和方法方面,尽管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也是“效果”标准和“目的”标准并用(第3、4条),但却差别较大。第一,在“效果“标准上,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第3条第1款仅规定(影响是)“严重的”或(时间是)“无限期的”,较美国2004年BIT范本的规定简略,但范围上似乎宽泛一些,仅规定“严重的”而未明确限定经济影响,并且增加了“时间期限”这一考量因素;第二,在“目的”标准上则更具体,明确规定“与公共目的不相称”;第三,在这两个标准的基础上,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第4条明确在效果上是歧视的或者违反事前的书面承诺,则“对财产的剥夺应被认为构成间接征收”,这明确增加了“是否存在歧视”这一因素,而“违反事前的书面承诺”是就“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干预”而言,但内涵和范围要比“对明显、合理、基于投资的期待的干预”窄得多。相比较中印双边投资协定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的规定在体例和结构上差别较大,用语和表述方式也差别很大,但就间接征收的含义、认定标准和方法,在实质上基本一致,都采用了“效果”、“目的”、“歧视”和“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干预”四个标准。不同的是,除“效果”和“目的”标准外,中印双边投资协定议定书是“歧视”和“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干预”两个标准并用,而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是“歧视”和“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干预”两个标准选用。总之,比较而言,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的规定与美国2004年BIT范本更“形似”,与中印双边投资协定议定书的规定更“神似”。
中国—哥伦比亚投资协定第4条(“征收和补偿”)规定:“缔约双方一致认为:(1)由缔约一方采取的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构成的间接征收,尽管没有发生所有权的正式转移或完全夺取,但与直接征收具有同等效果;(2)确定缔约一方的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应逐案考虑并基于考虑以下因素的事实调查:a.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的经济影响;但仅有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对投资的经济价值产生负面影响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已经发生间接征收;b.该措施或一系列措施的范围及对投资的合理和明显期待的干涉。”
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附件一(“征收”):“二、第八条第一款提出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直接征收,投资被国有化,或通过所有权的正式转让或完全没收的方式直接征收。三、第八条第一款提出的第二种情形是间接征收,缔约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与通过所有权的正式转让或完全没收的方式直接征收具有同等效果。 (一)判断缔约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在具体事实情况下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需要在事实基础上对个案进行调查,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1.该措施的经济影响,虽然缔约一方的一项或一系列行为对一项投资的经济价值有负面影响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表明间接征收成立;2.该措施干预明显合理的投资期待的程度;以及 3.该措施的性质。”
此后,2009年4月28日签订的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附件9“征收”的规定与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的规定基本一致。然而,2008年11月22日中国与哥伦比亚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与上述三者的规定都不一样,可以说是“混合体”。 2012年9月9日中国和智利签订的自贸区投资协定中的间接征收规定与智利和美国于2003年6月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间接征收规定类似,采用了“效果”、“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干预”和“性质”三个标准认定间接征收。中日韩投资协定在间接征收的定义和认定标准上与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基本一致,主要区别是在认定间接征收的“性质标准”中,强调政府措施的性质和目的,并进一步明确对“性质和目的”的考察包括“措施是否与其目的成比例”,即增加了“比例”要求。中加投资协定在认定标准方面与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几乎没有区别。
可见,即便是比较具体地规定了间接征收的投资协定,其相关规定也存在明显缺陷:第一,相关规定不一致,甚至差异较大,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条约实践。第二,多数规定仍然比较简单。在间接征收的定义方面,多采用描述性的语言予以界定,没有突出间接征收的本质属性;在间接征收的认定方面,多数规定仍应加以进一步说明或适当的限制。
2间接征收的例外规定不一
从国际实践看,不构成间接征收的政府措施包括“治安权(police powers)”例外(将善意、非歧视、符合正当程序、合比例地保护公共利益的国家管制措施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和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例外。迄今为止,在中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规定了间接征收例外的投资协定仅有中印和中哥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投资协定、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中加投资协定和中日韩投资协定,但规定并不一致。
中印双边投资协定、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中加投资协定和中日韩投资协定规定了“治安权”例外。中印双边投资协定议定书第3条第3款规定:“除非在个别情况下,缔约一方采取的旨在保护公共利益的非歧视的管制措施,包括根据司法机关所作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裁决而采取的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或国有化。”相较美国投资条约的相关规定,其共同点主要是强调管制措施是“为了公共利益”和“非歧视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印双边投资协定的规定没有列举“公共利益”的具体类型,而且将司法裁决也包括在应予排除的措施之内。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附件13第5款规定:“除符合第4款的极少数情况外,政府为履行管理权而采取的、可被合理地判定为基于保护包括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在内的公共利益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不应构成间接征收”。这一规定无论是与美国式规定还是与中印双边投资协定相比,都有较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其解释和限定了“除非在个别情况下”的含义。它明确将“个别情况”限定为“符合第4款的极少数情况”,即政府措施在效果上是歧视性的或政府措施违反了事前对投资者所做的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承诺,从而构成间接征收的情况,应该说这是重大的不同。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治安权例外”规定与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完全一致。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中的“治安权例外”与前述投资协定中的规定有较大差异。中加投资协定和中日韩投资协定“治安权例外”的突出特点是都限定了“极少数情况”的范围,但又有所区别。中日韩投资协定指出,当“按照其目的政府措施非常严重或者不成比例”时属于“极少数情况”,而中加投资协定则是“按照其目的政府措施非常严重以至于其不能被合理地认为是善意地被采用和适用”。中国—哥伦比亚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治安权例外”规定与前述投资条约的规定不一样,该协定第4条第2款第3项规定:“缔约一方为公共目的或社会利益或为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采取的非歧视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但在特别情形下除外,例如以其目的来衡量该措施或一系列措施非常严重,以致不能合理地被认为是善意采取和适用的。”该规定将“公共目的”、“社会利益”以及“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并列,而不是用“公共目的”涵盖后者,并且增加了“社会利益”;对于“个别情形”的解释是以措施的“目的”与“效果”的比例来衡量。可见,关于“治安权例外”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各个投资协定的要求并不一致。
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附件一(“征收”)第3条第(2)款规定:“除极少数情况以外,缔约一方为保护正当公共福利目标,如公共健康、安全和环境,而规划或适用的非歧视性管理行为不构成间接征收。”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第8条(“征收”)第6款规定:“本条不适用于根据WTO 协定附件1C《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给予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强制许可”。
在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例外”方面,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第145条(“征收”)第5款规定:“本条不适用于根据TRIPS协定给予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强制许可。”中国—东盟投资协定的相关规定与此类似。中国—哥伦比亚双边投资协定的“强制许可例外”规定则与前述规定不同。该协定第4条第6款规定:“缔约方确认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0条和第31条发出的强制许可不因本条的规定受到质疑”。中国—智利自贸区投资协定的“强制许可例外规定”规定得更为具体:“本条不适用于强制许可的颁发或知识产权的撤销或限制,只要该撤销或限制和经适当修改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相符,或与双方皆为缔约方的其他知识产权协定相符。”整体而言,前述四个投资协定的“强制许可例外”规定大体一致。但是,中加投资协定的例外规定却就知识产权的例外做了扩大,不仅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强制许可的授予”,还包括“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其他措施”。遗憾的是,中印双边投资协定、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投资协定却没有规定“强制许可例外”。
可以看出,虽然个别投资协定较为明确地规定了间接征收的定义、认定标准和方法、“治安权例外”和“强制许可例外”,但却存在较大差异,这说明我国的有关条约实践还在探索中,也可能表明我国针对不同的缔约对象有不同的选择或者面对不同的缔约对象不得不作出不同的选择。无论如何,这种差异不利于我国相关条约实践的发展和条约的具体适用。这种内部不一致有可能引发条约适用的不确定性风险。如果不能有效克服这些内在规定的矛盾与冲突,对我国是大为不利的。
四、关切:改进条约中的间接征收条款
中国作为国际投资的重要参与者,作为间接征收问题的“利益攸关方”,必须关切间接征收问题和间接征收制度的塑造。笔者认为,在国际投资法的公益化革新浪潮中,我们应该明确我国的投资协定政策定位,以此为基础,规范和完善我国投资协定的间接征收条款。
(一)明确投资协定的政策定位
政策立场决定制度选择,只有具有明确的政策定位和立场选择,才可能较妥当地应对间接征收问题,作出明智的制度选择。顺应公益化革新趋势,在新时代的投资协定实践中,中国的投资协定政策应当是国内投资乃至经济社会政策的合理延伸,理应以自身利益为皈依,以自身实践为路径,并坚持对国际法的贡献。应该平衡考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和人权保障等不同价值,深入把握东道国主权及其管辖权和国家责任、外国投资者财产权利及其跨国责任、经济社会文化人权和非政府组织参与权。在具体做法上,中国的投资协定政策应与国内法的相关规定衔接;应当在重新评估投资协定功能的基础上,增强对外投资保护的有效性;应当实行投资协定政策和规定的更新与一致化;在投资协定实践中,不再亦步亦趋,应当基于前述立场,借鉴吸收各国投资协定的有益成果,提出自己的投资协定范本,强化对国际投资法制的贡献。
在国际投资法中,可以说,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各种利益和价值的载体,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的集中表现是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因此,上述政策立场可简单归结为: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平衡投资者利益与国家利益。当然,也不能忘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能忘记“在今后的投资协定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确保东道国有权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管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保留足够的政策空间,使政府能够在其签署的投资协定所确立的权利与义务框架内,灵活地运用这些政策。这显然有难度,因为保留过多的政策空间会削弱国际义务的价值,而过于苛刻的国际义务则会过度挤压东道国国家的政策空间。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是应当在投资协定的目标、结构、落实方式和内容上,保持有利于发展的平衡”。
(二)改进条约间接征收条款
基于上述政策定位,参考最新国际投资条约实践和间接征收仲裁实践,总结我国相关条约实践,建议改进投资条约中的间接征收条款,使间接征收规定一致与协调,并逐渐统一到国际投资协定中,实现国际投资协定相关内容的更新与一致化。
1改进国际投资协定的途径
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中国现有的投资协定有关间接征收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因此必须改进,以便在促进外国投资的同时,为东道国保留必要的政策空间,平衡东道国和投资者利益。我们应该利用多种途径改进国际投资协定,比如:缔约国可以澄清条约条款的含义(例如,通过作出权威性解释);修改国际投资协定(例如,通过修正案或议定书);以新的协定取代老的国际投资协定(例如通过重新谈判);或是终止国际投资协定(单方面终止或在相互同意基础上)。我们应根据不同时期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的具体情况以及其有效期的不同,区分不同的缔约国,采用合适的办法改进国际投资协定。
2国际投资协定的改进内容
我们应该通过上述途径,处理国际投资协定间接征收制度中的不一致性,完善间接征收的定义,明确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和方法,妥当规定间接征收的例外。
(1)完善间接征收的定义和认定
在间接征收的定义上,可基本采用中印2006年双边投资协定议定书第3条的规定:“除了通过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的形式进行的直接征收或国有化外,征收措施包括一方为达到使投资者的投资陷于实质上无法产生收益或不能产生回报之境地,但不涉及正式移转所有权或直接没收,而有意采取的一项或一系列措施”。
在间接征收的认定上,应该结合中印2006年双边投资协定和2008年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认定标准和方法,坚持多个标准并用,并且对各个标准予以澄清或加以适当的限制。例如,可规定为:在具体的事实情况中,确定一缔约方的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的个案分析,并考虑包括以下各因素:其一,政府措施的经济影响,这种影响应该实质性剥夺投资的根本性权利,但仅仅有一缔约方的一个或一系列行为对于投资的经济价值具有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尚不足以确定间接征收已经发生。其二,政府措施对明显的、合理的,投资赖以进行的期待的干预程度。这种期待应该是能客观证明的,区别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政府违反事前向投资者所做的具有约束力的书面承诺,如协议、许可、批准、保证或陈述等,使投资者的期待落空,可视作政府干预投资者合理期待的证明。其三,政府采取措施的背景以及政府措施的性质和目的,是否是为了善意的公共利益目标而采取,以及在该等措施和征收目的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
当然,还应加强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对有关标准的内涵、认定因素和使用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每一个标准的内涵、认定因素和使用,使之适当地细致和准确。
(2)合理利用间接征收的例外
在今后谈判和缔结投资协定时,应给我国对公共利益的管制保留适度的空间,以解决投资自由化的过度扩张所可能产生的纷扰,因此,应合理地利用和纳入间接征收的各种例外,如治安权例外和知识产权例外。具体如下:
第一,“治安权例外”。基于国家主权原则,国家当然享有“治安权”,有权采取旨在保护环境和公共健康等公共利益的管制措施。然而,这些管制行为有时也会对外国投资者或其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此时,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反对东道国的管制措施,指控这样的管制措施构成间接征收,并要求赔偿。如果国家对于这样的管制行为所造成的投资者损失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则将不当地限制国家的主权权力,限制国家采取措施保护公共利益的空间。为了避免国际投资协定的间接征收条款不适当地限制国家在公共利益领域采取管制措施的空间,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澄清和完善间接征收条款,规定“治安权例外”,详细解释和界定哪些管制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就是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选择。当然,也要防止国家滥用“治安权例外”,不当损害投资者权利。为了平衡东道国的发展利益和投资者权利,需要适当界定“治安权例外”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治安权例外”的适用条件。
在范围上,为保护公共利益,诸如环境和公共健康、人权、追求重要的社会和经济目标的管制措施是不需补偿的政府管制措施。在适用条件上,“治安权例外”的前提应该是在合法的“治安权”范围内,还应符合善意、非歧视、正当程序和最小损害要求。笔者认为,国际投资协定间接征收条款的“治安权例外”规则可规定为:对与国家的管制权力以及习惯国际法的治安权原则相一致,旨在、并且适用于保护或增进合法的公共福利目标,如环境和公共健康、人权和追求重要的社会与经济目的的善意、非歧视、符合正当程序的国家措施,国家不应承担补偿责任。如果这种措施对投资者造成了超出必要范围的损害,国家应该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
第二,知识产权例外。在间接征收视域下,强制许可的授予是一种对涉及知识产权的外国投资产生直接影响的政府行为。通过强制许可,政府可以授权政府部门或其他第三方使用知识产权,从而直接干预私人拥有的知识产权。根据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和方法,从法理上分析,强制许可可构成间接征收,而且国际投资协定提供的保护要高于TRIPS协定提供的保护,尤其是在补偿标准方面。这将促使投资者选择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索赔。这对授予强制许可的国家是极大的挑战,将使国家不敢授予强制许可(即使授予了也将承担巨大的成本),同时也是对国家维护公共利益的规制权力和能力的削弱。鉴于强制许可是为了防止专利权滥用,平衡权利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选择,间接征收将对这一努力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利益平衡的实现,因此,不能使间接征收规定适用于强制许可。换言之,应在国际投资协定中明确规定间接征收规定不适用于强制许可,或者强制许可不构成间接征收。除强制许可外,政府还可能对知识产权采取其他措施,同样可能引发上述问题,也需要将其排除在间接征收之外。当然,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人的权利,防止政府滥权,政府也应履行其负有的国际法义务,相关政府措施应符合有关国际知识产权协定。
因此,应在投资协定中将包括强制许可在内的对知识产权的政府措施规定为征收(包括间接征收)的例外。比较已有投资协定中的知识产权例外规定,中加投资协定中的规定更为可取。因此,建议按中加投资协定第10条第2款将知识产权例外规定为:“在给予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强制许可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符合缔约双方都是成员方的知识产权国际协定的范围内,本条不适用于该等措施”。这样不仅将强制许可排除在征收(包括间接征收)之外,也将政府采取的其他知识产权措施排除在外,国家在依据TRIPS等国际协定实施强制许可或采取措施时,即使干涉甚至剥夺了外国投资者的知识产权,也不会构成间接征收。
Chinas Concern over the Issue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ANG Xiao-lin
Abstract: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tend to innovate towards public interest protection with the core part of balancing interests between investors and host countries.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s one of central issues involved in balance of interest. In playing the dual role of capital-importing and exporting country, China is confront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However, serious flaws exist in indirect expropriation clauses of investment treaties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which require urgent improvement. Therefore, the issue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requires serious concern and considerate preparation. China should definitely establish the policy position, normalize and improve the provisions of indirect expropriation in relevant investment agreement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investmentindirect expropriationinvestment agreement
①张光:《双边投资条约的公益化革新》,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149页。
②王彦志:《中国在国际投资法上的身份转换与立场定位》,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134页。
③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2: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Overview,United Nations, pp23—24.
④前引③,p32.
⑤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Overview,United Nations , p15.
⑥前引③,pp34—36.
⑦参见曾华群:《论双边投资条约实践的“失衡”与革新》,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3—14页;韩秀丽:《后危机时代国际投资法的转型——兼谈中国的状况》,载《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6 期,第21—23页;前引②,第131—138页。
⑧陈安主编:《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⑨参见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资料来源于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3月3日。
⑩前引⑧,第160—161页。
李玲:《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缔约实践和面临的挑战》,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10年第17卷第4期,第122页。
参见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资料来源于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40218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3月3日。
梁咏:《我国海外投资之间接征收风险及对策——基于“平安公司—富通集团案”的解读》,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19页。
前引,第119页。
前引,第120页。
根据UNCTAD的统计,截至2012年底中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是145个,因为自2012年底至2013年底,中国没有签订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因此至2013年底中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仍然是145个。其中的其他投资协定是指除双边投资协定以外,含有投资章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系列协定中的投资协定。参见前引⑤,p230.
中国—日本投资协定第5条第2款。
中国—葡萄牙投资协定第4条第1款。
中国—澳大利亚投资协定第8条第1款。
中国—马耳他投资协定第4条第1款。
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第8条第1款。
中国和莫桑比克投资协定第4条第1款。
中国—肯尼亚投资协定第4条第2款。
中国—乌干达投资协定第4条第1款。
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第133条第1款。
前引⑧,第142—144、159页。前引⑧,第150—151页。
参见季烨:《中国双边投资条约政策与定位的实证分析》,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9年第16卷第3期,第199页。
前引,第196页。
前引,第196—201页。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3——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Overview,United Nations,2003,pp18—19.
[作者简介]王小林,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