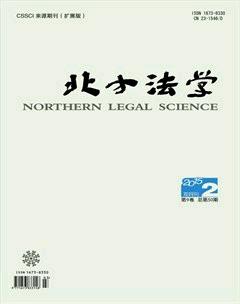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的理论反思
摘要:《劳动合同法》所确立的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有悖合同无效与合同解除的一般原理,难以对违法劳动合同作出有效规制。该制度的缺陷源自其基础理论的谬误。该谬误系相关学者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片面理解所致。应当在立法上排除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打破有效——无效的二元劳动合同效力结构,引入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劳动合同效力体系。
关键词:劳动合同无效解除无效劳动合同可撤销劳动合同
中图分类号:DF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5)02-0149-12
一、引言
1995年施行的《劳动法》首次对劳动合同制度作出了系统的规定。(该法于第三章“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以16个条文的篇幅,对劳动合同的概念、订立和变更、无效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的形式和条款、劳动合同的期限、试用期、劳动合同的终止和解除、解雇保护等方面作出了规定,在劳动基本法的层面上建立了劳动合同制度的基本框架。当然,由于理论储备和立法技术等方面的不足,该法亦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在劳动合同效力制度方面,《劳动法》采取的是有效—无效的二元制立法模式;①由于这一立法模式过于僵化,故学理上不乏反对意见;而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即是:应当增进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弹性、赋予当事人以更多的选择自由。②
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仍然沿袭了《劳动法》的有效—无效二元制效力结构。与《劳动法》的做法相同,《劳动合同法》亦未采纳“可撤销劳动合同”这一中间效力形态,而是将具有意思瑕疵的劳动合同(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直接归为无效。《劳动合同法》相对于《劳动法》的“突破”及“创新”之处则体现在“劳动合同无效解除”的设计,即将无效劳动合同纳入过失性解除的范畴;无过错当事人得享有“无效劳动合同”的解除权。应当看到,《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规定,旨在对《劳动法》所确立的相对僵化的二元效力体制作出缓和,扩大劳动合同当事人的选择空间。这一改进的大方向自然无可厚非,但具体的改进措施却是在维持原有的有效—无效二元效力体制的前提下、依“解除无效劳动合同”的思路而实行的,其结果必然是扭曲了“劳动合同无效”与“劳动合同解除”的本来含义,进而造成结构性的制度缺漏。本文将分析的焦点集中到劳动合同无效解除的理论依据上,以对该理论核心内容的辨析和纠正为基础,为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改进提供合理化建议。
二、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的含义及评价
(一)劳动合同无效解除的基本含义
《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第26条、第38条第1款第5项、第39条第5项)的含义(亦即所谓“特色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将无效劳动合同规定为可解除的劳动合同,置于劳动合同过失性解除制度之中。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在劳动合同因第26条第1款规定的情形③而无效、且无效原因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情况下,劳动者一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第5项的规定,在劳动合同因第26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情形(仅包括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而无效,且无效原因可归责于劳动者的情况下,用人单位一方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其二,将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权赋予劳动合同当事人。《劳动法》第18条第3款规定,“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即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权仅属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而第26条第2款则规定,“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依据该款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权实际上是由劳动合同当事人行使,只是在双方对无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从而产生争议时,才需诉诸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经劳动仲裁未引起诉讼的,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经劳动仲裁引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确认”。④
(二)学理上对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的争议
对于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的实际价值,学理意见存在分歧:
1 肯定说。
肯定意见认为,《劳动合同法》所设计的无过错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制度系采用授予特殊情况下对劳动合同无效无过错者以解除权的方式来替代可撤销制度,与劳动合同可撤销制度有异曲同工的效果;⑤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在当事人未行使解除权之前是有效的;对于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产生的病态契约,合同解除系一种在尊重受害人意思基础上的、具有相对性的否定性评价,类似于民事合同的撤销。在有解除权的一方行使解除前,劳动合同应理解为有效;《劳动合同法》虽然未引入可撤销合同的概念,但解除制度亦可发挥异曲同工的作用;《劳动合同法》的处理是恰当的,故而不应当“褒可撤销合同而贬合同解除”;无效合同适用解除与民法原理并不相悖;⑥就此类劳动合同而言,赋予劳动者解除权比赋予劳动者撤销权更有利于劳动者的保护。⑦
2 否定说。
否定意见认为,《劳动合同法》试图通过增加无效劳动合同在适用时的弹性,来改良原《劳动法》那种过于僵硬的劳动合同效力机制,然而立法机关对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宏观定位却模糊不清;⑧“无效劳动合同解除”制度在法理上存在着错误;如果将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作为可撤销劳动合同,则可避开法理上的障碍且实际效果更为合理,因为赋予受害方变更或撤销劳动合同的权利,受害方将占有主动地位:当事人既可选择维持劳动合同效力,以获得就业机会以及劳动合同法上的权利,亦可选择否认劳动合同的效力而将其撤销,进而适用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86条),令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⑨
(三)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的主要缺陷
依笔者观点,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在解决特定问题的同时,亦大大增加了适用方面的难度,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从运行的效果来看,颇有得不偿失的嫌疑。其缺陷主要表现在:
1 有悖合同无效与合同解除的一般原理
合同效力制度可被视为当事人意志与立法者意志的互动机制;合同效力形态的多样性,体现着法律对于当事人的合意所给予的不同评价。⑩合同无效,指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因严重欠缺生效要件,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赋予效力;合同无效场合得依法律规定(而非依当事人的意思),发生赔偿损失等法律效果。
而合同解除,则是指在合同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也是一种法律制度。合同解除制度的主要功能是解决有效成立的合同因主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提前消灭的问题;以有效成立的合同为标的,是合同解除区别于合同无效、合同撤销诸制度的重点所在。
合同无效与合同解除各自有着不同的涵义和功能:前者系法律对当事人合意作出否定性评价的结果,后者系法律为当事人提供的在特定条件下结束合同关系的退出机制;二者分别作用于合同关系的不同领域和阶段,在合同制度中既有严格区分又相互衔接。因此,所谓“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在概念使用上难谓严谨,在法理上存在错误;认为“无效合同适用解除与民法原理并不相悖”的观点难以成立。
2 存在结构性的疏漏
劳动合同无效解除的制度结构意味着,存在严重违法性的劳动合同难以得到有效规制。前已述及,依据《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权实际上是由劳动合同当事人行使。有学者将《劳动合同法》的这一规定解读为“有限确认原则”,即只有在双方对效力有争议时,才请求公权力介入裁判,公权力不得主动介入并确认劳动合同无效;认为“有限确认原则” 系对公权力作用范围的限缩,是私法理念回归的表现,有利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体现了劳动法律制度从强调国家管制向注重当事人自治过渡的趋势。而依笔者观点,第26条第2款的所谓“有限确认原则”,既不是所谓“私法理念”的回归,也不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而纯属劳动合同无效制度的结构性缺失,其后果是:劳动合同无效制度难以对违法劳动合同做出有效规制,有害《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的实现。
实际上,“劳动合同无效由当事人确认”(《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2款),与“无效劳动合同由当事人解除”(《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5项、第39条第5项)的规定具有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遵循合同无效的一般原理、沿用《劳动法》第18条第3款的规定而将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权仅赋予特定机关,那么由当事人来解除“无效劳动合同”的制度设计也就毫无实益了;劳动合同是否无效若由仲裁机构或法院来确认,当事人的“无效劳动合同解除权”又如何有行使的余地?如欲在此以“解除”概念来统合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法律效果,则只有将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权赋予劳动合同的当事人(排除“当然无效”),由当事人自主确定劳动合同是否无效;在当事人自行确认劳动合同无效之后,再由无过错的一方行使解除权。此即所谓“劳动合同的无效并不自然导致劳动关系的解除,只有在无过错方行使解除权并按照解除程序办理后续事宜以后劳动关系才被解除”。只有对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制度作出如此设计,“解除无效劳动合同”在逻辑上方能通顺。
依《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2款,假如当事人对劳动合同的有效性并无争议,不主张确认其无效,劳动仲裁机构及法院自然不得依职权主动确认劳动合同无效。这在仅有当事人意思表示形成自由受到妨害的情形(《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尚可成立,因为受错误、恶意欺诈或胁迫影响的劳动合同,虽然在缔约过程方面具有可责性,但其内容不一定是不当的,故而可将维持或消灭其效力的选择权交由当事人(如仅就《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第1项所规定的情形而言,或可承认“无效劳动合同的解除”在功能上相当于“劳动合同的撤销”)。但《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所规定的无效劳动合同类型不仅包括妨害意思表示形成自由的情形,还包括用人单位免除自己法定责任且排除劳动者权利的情形(第26条第1款第2项),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第26条第1款第3项)。该款第1项的规制范围仅为非法干预意思表示形成的情形,而后两项则涉及劳动合同内容违法(广义)的情形;尤其第3项系典型的合同无效事由(如与第3项几乎一致的《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以此为论,将无效劳动合同确认权赋予当事人的做法便颇值商榷了。
《劳动合同法》第28条规定:“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
以“杀人合同”、“贩毒合同”一类的极端例子来证明《劳动合同法》第26条与第28条的立法漏洞,似乎有小题大做的嫌疑,但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06年3月)对此却有着相对合理的规定。该草案第18条第2款将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权明确赋予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及人民法院。依据该草案第22条,“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有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的例外情形。遗憾的是,这样的合理规定最终却未被《劳动合同法》所采纳,导致第28条存在着如此明显的逻辑漏洞。对于一部“后发型”的法律而言,这样的错误其实完全可以避免。
《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2006年3月)关于劳动合同效力瑕疵规定(第18条、第19条、第20条、第22条)的优点在于:打破了有效—无效二元的效力体系,采纳了可撤销劳动合同这一中间形态,并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作出明确规定;将劳动合同无效的确认权赋予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在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效果方面,并未一刀切地规定报酬请求权,而是作出了合理的区分,将具有严重可谴责性因素的劳动合同排除在外,否认劳动者的报酬请求权。但上述内容均未被《劳动合同法》采纳。
前已述及,合同效力制度系当事人意志与立法者意志的互动机制;合同效力形态的多样性,体现着法律对于当事人的合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评价。具有意思瑕疵的合同,其负面因素有限(负面因素仅存于意思形成过程而不及于意思表示的内容),故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给予相对否定评价,将其定位为可撤销合同,得由当事人决定其最终效力。而违反法律秩序及社会公益的合同,其负面因素最为浓厚,故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给予绝对否定评价,将其定位为无效合同,不容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维持合同的效力。因此,无论如何强调劳动合同及劳动合同法的特殊性,无论如何强调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必要性,对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劳动合同,亦应绝对否认其效力。进言之,“合法”是订立劳动合同的基本原则,只有“依法”订立的劳动合同方具有约束力(《劳动合同法》第3条)。而《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2款的规定则意味着:即使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等具有严重违法性的劳动合同,只要相关当事人对其效力瑕疵并无争议,便可作为有效劳动合同而正常运行。结合第28条的规定可知,纵使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亦得毫无例外地享有劳动报酬的请求权,而无论该劳动合同是否具有严重的违法性。为了使“解除无效劳动合同”的逻辑能够得到贯彻,为了将“无效劳动合同”纳入“合同解除”的范畴,而背离了无效合同的基本理念,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具有高度反社会因素的劳动合同,纳入所谓“当事人自治”的范围,令此类劳动合同能够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有效”状态;此类合同纵使被确认无效,“劳动者”一方的报酬请求权亦毫无例外地不受影响。这样的制度设计,其合理性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三、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的理论基础——“无效解除说”
“劳动合同无效解除”的概念逻辑明显有悖法理,且相应的制度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疏漏,为何却能成为立法者最终的选择?立法活动离不开学理的支持,对相关学理意见的考察,或许能为《劳动合同法》采纳这一“特色”制度的原因提供解答。
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而论,“劳动合同无效解除”的相关主张,早在《劳动法》实施之前便已被提出:“劳动关系具有人身关系的特征,难以恢复原状,世界各国均避免因无效劳动合同而导致无效劳动关系。因此,我们只对无效条款作规定,劳动合同全部无效,通常也按照劳动合同解除处理”。出于表述方便的考虑,笔者将这一观点称为“无效解除说”。
“无效解除说”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民法上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法律效果即意味着“溯及既往”、“自始无效”,而“自始无效”的处理方式并不符合劳动关系人身性、继续性的特点。因此,对于有瑕疵的劳动合同,应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概念为基础重新进行制度设计,不应“跟在民法后面亦步亦趋”。
2 民法上合同无效制度所具有的“当然无效”的特点,亦不适用于劳动合同领域。
3 立法不应当采纳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是“从《合同法》简单照搬的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
其中,第1项与第2项,可以视为“无效解除说”的核心观点,即对“自始无效”与“当然无效”的否定;第3项则是针对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的具体反对意见。将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文与《劳动合同法》的正式规定相比对可知,上述三方面的观点基本被立法所采纳(当然,《劳动合同法》第28条的规定,仍然部分体现了“自始无效”的思路)。持“无效解除说”的学者亦认为,以解除概念统合劳动合同效力瑕疵制度,以及将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权赋予合同当事人的做法,正是《劳动合同法》较之于《劳动法》的“突破”之处。依笔者观点,这一理论在对民法基本概念的理解及论证逻辑的展开等方面存在问题;其立论依据难为合理,故有必要对该理论作出反思与纠正。
四、“无效解除说”在立论依据方面的问题
(一)对民法上无效及撤销效果的理解存在偏差
1 无效解除说的逻辑矛盾
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认为,民法合同无效理论并不适用于劳动合同法领域。其主要理由为: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制度,可以用“自始、当然、确定、永久”这八个字来概括;而民法上合同无效制度所具有的“自始、当然、确定、永久”的特点与劳动关系及劳动法的属性完全背离。在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看来,所谓“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制度”即等同于“自始、当然、确定、永久无效”:“合同无效制度的核心在于其合同无效直接后果的‘自始、当然、确定、永久,如果撇开了这些合同无效的要素,那么引入该制度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大多数学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对合同无效制度加以改良。但是无论如何改良,都无法回避或者舍弃合同无效的‘自始、当然、确定、永久。否则,无效也就不成其为无效了”;“溯及既往”、“自始无效”就是被部分劳动法学者所尊奉的“民法公理”;以所谓“民法理论”来设计劳动合同效力瑕疵制度,便意味着“溯及既往”、“自始无效”、“推倒重来”,是罔顾劳动关系人身性、继续性特点的错误安排。不仅如此,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认为,所谓“民法上”的合同撤销也意味着毫无例外的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应使撤销的效力溯及既往显然与无效的根本含义相悖,如果无效没有溯及力,那么其与解除也就没有区别,而解除与无效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范畴”;“解除与撤销这两个概念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只要受到损害的一方提出,两者也均要求终结劳动关系,区别只在于是否有溯及既往的必要”;对于有瑕疵的劳动合同,应以“解除劳动关系”的概念为基础重新进行制度设计。
由是观之,所谓“无效解除说”的逻辑在于:既然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及可撤销制度即意味着“自始无效”,意味着溯及既往地消灭合同关系,意味着不当得利返还的后果,不存在任何例外,这一处理方式与劳动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以及人身性合同的特点明显不符(已付出的劳动不能恢复原状,不利于保护劳动者利益),故而自当坚决否定。既然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法律效果仅等同于“自始无效”,那么,在劳动合同场合便应当排除民法上无效及可撤销概念的使用,而以“具有劳动法特色的无效及解除制度”取而代之。而在笔者看来,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及可撤销制度并不能简单地与“自始无效”划上等号,持此论的学者在逻辑起点上便存在问题,其结论的说服力自然有限。
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所引用的王利明教授的观点(合同无效系“自始、当然、确定、永久”地无效),是对合同无效所作出的一般意义上的阐述;仅凭这一句宏观层面上的论述,便将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制度贴上“溯及既往”、“自始无效”的标签并作为供批判的“假想敌”,进而证成己方相反的观点,则颇有以偏概全甚至简单粗暴的嫌疑。例如王泽鉴教授亦有类似的宏观层面上的论述:法律行为无效,意味着法律行为当然、自始、确定不发生效力;但王泽鉴教授同时亦指出了在继续性合同场合的例外情况,即:自始无效的例外在于,继续性契约,如劳动契约,合伙契约。主张无效者,惟得向将来发生效力;继续性契约,尤其是雇佣及合伙,在业已进入履行阶段的情况下,应限制无效或撤销的溯及效力,使过去的法律关系不因无效或撤销而受影响。如是观之,“无效解除说”的相关论点显然不够全面。
有必要指出的是,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同样援引了王泽鉴教授在《债法原理》一书中表达的上述观点来证明劳动合同的继续性特征,且认为“王泽鉴先生对继续性契约的特点分析是非常具有洞察力的”;但援引过后,却又言之凿凿地认为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及可撤销即意味着溯及既往、自始无效;认为“不应使撤销的效果溯及既往”便意味着“偷换了概念”。以此为论,一方面援引王泽鉴教授的著述作为论据,认为继续性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时的溯及力仅及于将来,另一方面认定民法上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效果便等同于“自始无效”。此处的逻辑矛盾相当明显。事实上,合同可分为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或称“一次性给付合同与连续给付合同”),所谓“自始无效”的后果系就一时性合同而言,于继续性合同并不适用;这是由两类合同自身的不同属性所决定的。无效或撤销的溯及效力,在劳动合同等继续性合同领域应当受到限制,无效及撤销的效果仅能及于将来。以上观点原本便是民法及合同法一般理论的应有之义,属学理上业已达成的基本共识。
应当看到,“无效解除说”的合理之处在于:劳动合同作为继续性合同,其无效或撤销的溯及效力应当受到限制,“自始无效”、“推倒重来”的立法模式(《劳动法》第18条第2款,《劳动合同法》第28条)确有改进的必要。笔者对这一点完全赞同。但这一目标完全可以在全面把握民法一般原理的前提下,运用既有的基本概念体系而达成,无需另起炉灶,重构一套具有“劳动合同法特色”的无效及解除概念体系。劳动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点,无需赘述,但仅因此便再搞重复建设,另外发明一套概念体系,恐属事倍功半、得不偿失。事实上,劳动合同效力瑕疵制度完全能够凭借民法的基本概念体系而有效运作。德国法上的“事实劳动关系”概念便是一著例。
2 “自始无效”的例外——德国法上的事实劳动关系概念
德国法上的事实劳动关系(faktisches Arbeitsverhltnis或译为“实际劳动关系”)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所谓事实劳动关系也称有瑕疵的(fehlerhaft)劳动关系:其所指涉的是雇员在缺少有效的合同基础关系的情况下提供了劳务的情形。事实劳动关系这一概念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合同缔结(Vertragsschluss)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必备的程序;换言之,劳动合同并非仅仅通过劳务给付而成立。
(2)事实劳动关系的原理意味着,在业已成立并开始履行的劳动合同因存在瑕疵而被确认无效或撤销的情况下,对无效的法律后果做出的目的性限缩(teleologische Reduktion);无效的后果原则上(自被确认无效之时起)只向将来发生(ex nunc)而非溯及既往(ex tunc)。过去曾实际存在的雇用是被作为有效的、无瑕疵的(fehlerfrei)劳动关系对待的,当事人得据此享有针对过去的、准合同意义上的请求权(quasi-vertragliche Ansprüche)。这一规则与民法典第142条(自始无效)的规定并不一致,其理由在于:信赖保护的需要与业已履行的劳动关系返还清算的困难。针对已经履行完毕的瑕疵劳动关系,在此期间内,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与有效成立的劳动关系相同(wie im wirksam begründeten ArbVerh)。雇员享有对约定报酬的请求权;如有必要(未明确约定报酬时),报酬的数额可以依据民法典第612条第2款确定。雇主则须遵守一切有关保护雇员的法律;特别是继续支付工资法(Entgeltfortzahlungsgesetz)与联邦休假法(Bundesurlaubsgesetz)。
“实际劳动关系”的译名,参见Immanuel Gebhardt/ Rotert Dübbers:《中国和德国劳动合同的无效》,载《中德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比较法文集》,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
Preis, Erfurter Kommentar zum Arbeitsrecht, 11 Auflage 2011 BGB § 611 Rdnr 145.
Müller-Glge,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6 Auflage 2012 BGB § 611 Rdnr 635.
Preis,aaO, Rdnr 147.
Müller-Glge, aaO, Rdnr 638.
前引, Rdnr 146.
参见前引董保华文,第28页。
(3)事实劳动关系原理并非无例外地适用于一切劳动合同无效及被撤销的情形;承认事实劳动关系不能与重要的公共利益(gewichtige Interessen der Allgemeinheit)相冲突。假如认定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禁令的重要性将被抹杀(BAG AP § 134 Nr 25 = NZA 2005, 1409; AP § 134 Nr 26 = NZA 2009, 663)的情形,即须排除事实劳动关系规则的适用。如果某一以行医为标的的劳动合同,因相关当事人既没有、也不可能被授予必备的开业许可而被确认无效,则不成立事实劳动关系;相反应依据不当得利的规定对已作出的给付进行返还清算(BAG AP § 134 Nr 25 = NZA 2005, 1409)。排除适用事实劳动关系规则的其他具体情形,例如: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有意违反刑法(BAG 254 1963 AP BGB§611 Faktisches Arbeitsverhltnis Nr2)以及劳动合同的内容严重违反善良风俗(BAG 14 1976 AP BGB§138 Nr34)。
德国法上事实劳动关系概念对我们的基本启示在于:首先,合同无效及撤销的法律效果系以有溯及力为原则(即所谓“自始无效”),但在继续性合同尤其是劳动合同的领域,考虑到此类合同自身的特性,应对溯及效力作出限制,将业已履行的合同关系视为有效;“视为有效”意味着劳动者得据此较为全面地享有相应的权利(合同权利、劳动基准权利以及社会保险权利均不受影响,而非仅得请求劳动报酬);其适用逻辑亦简洁明快。其次,对无效及撤销溯及力的限制须有例外:严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劳动合同则不能适用事实劳动关系的相关规则,不能将业已履行的合同关系视为有效。因具有效力瑕疵的合同毕竟属于受到法律否定性评价的合同(否定性评价的程度各有不同),对于可责性较高的合同,如不加区分地一概排除无效及撤销的溯及效力并“按照解除处理”,显然于理不合,同时也会造成效力瑕疵制度与解除制度的内涵双双被扭曲的结果。
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在论述劳动合同的继续性特征时,亦援引了德国学者Immanuel Gebhardt与 Rotert Dübbers在《中国和德国劳动合同的无效》一文中关于德国法上事实劳动关系(实际劳动关系)的一般阐述,以为佐证;但是其似乎再次忽视了上述德国学者在该文中对于民法典与劳动合同法之间关系的详尽阐释(与引用王泽鉴教授观点的矛盾情形几乎如出一辙):德国法中没有专门的劳动法,并且将劳动合同法看作是《民法典》中规定的民法的一部分。和所有其他的私法合同一样,劳动合同依照的也是法律行为的一般无效规定。法律行为理论一般原则的规定,也毫无疑问地适用于劳动法,这样就确保了劳动法和一般民法之间不存在裁定矛盾。裁判在德国的劳动法中具有特殊的作用。通过法官的法律发展,裁判改进了一般民法,并考虑到可能有的劳动法的特殊性。通过适用民法中关于劳动法的一般规定,劳动法也参与了一般民法规范的解释。民法中的经验可以在劳动法中适用,劳动法的经验也可以在民法中适用,劳动法还可以从民法其他部分中所获取的认识中获益。这种处理方式的优点是避免在几部法律中同时对同一个事实作出重复规定。合同何时生效、何时无效,只在《民法典》中作出一次性的规定,并适用于《民法典》所涵括的所有法律领域,包括劳动法。而且这样的做法还确保了诸如劳动法、一般民法或民事经济法等法律领域不互相交叉,确保整个法律制度不相抵触。
即便仅就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自己所利用的资料而言,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德国学者自然不会否认劳动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的不同之处,不会否认劳动法区别于民法的特殊地位,但也不曾因此便在民法典的基本概念体系之外另起炉灶,重搞一套体现“劳动合同法特色”的概念体系。“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自然意味着对合同无效和撤销的溯及效力作出限缩,体现了对具有继续性特征的劳动合同自身特性的肯认;但这一规则仍然是在民法典基本概念体系之内(法律行为的无效及可撤销)的操作,并不需要另外构建一套“劳动合同无效及解除”的概念取而代之。
(二)无效解除说对“当然无效”的反驳依据不足
如前所述,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认为民法上合同无效即等同于“自始无效”,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特点,故当批判。持此论者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合同无效制度所具有的“当然无效”的特点,亦不适用于劳动合同领域,同样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但是正是由于劳动法主体的不平等,劳动合同违反劳动法的规定不当然无效。……由于现代劳动法对劳动者之保护特别强调,因此在违反强行法时,仍需视其结果是否对劳工有利而定其效果,如果对劳工不利时,当然无效;对劳工有利者,则为有效。……在劳动法的实践中,即使当事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了劳动法的强行性规范,但是由此建立的劳动关系也不能判定‘当然无效。因此,对于融合了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的劳动法规范,不能因为劳动者的违反而导致劳动合同无效。……在违反的情况下,劳动法对于违法者的要求不是无效,而是必须按照命令性规范的要求纠正。因此,对于低于劳动基准的劳动条件约定,当然违法;但是劳动法处理的方式是按照劳动基准执行。比如劳动报酬的约定低于最低工资的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执行。就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形而言,劳动法上的处理方式是可以补充签订,而非宣布无效了之”。
笔者认为,相关论者对“当然无效”的理解,实际上存在着偏差。法律行为或合同的“当然无效”是指无效原因原则上“自动”产生效力;如果当事人的法庭陈述中包含无效原因,那么,即使被告没有主张合同无效,即没有以合同无效作为抗辩,法官也应对无效予以关注。易言之,“当然”一语的侧重点在于:对无效合同的审查系法院的职权,而无需当事人主张;法院对无效合同的确认系对合同无效这一既成事实的确认,而非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处理。在诉讼中,如果合同存在无效的原因,那么即使双方当事人均未作出合同无效的主张,法院亦得依职权迳行确认合同无效,令当事人承受法定的后果。而持“无效解除说”的学者以上论述所指称的情形是:不能仅因劳动合同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便“当然”认定劳动合同无效。实际上,这一内容属于合同适法性要件(《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劳动合同法》第1款第3项)的范畴,与“当然无效”的基本含义并无关系。依据民法的一般理论,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非“当然”无效;判断合同是否无效需要更加具体的考量,诸如效力规定与取缔(管理)规定的二分、特定规范目的及相应的利益衡量等等。我国现行法上亦有相应规定,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便明确规定,只有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后果。
可以看到,上述持“无效解除说”的学者实际上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方式来论证其观点,即:以劳动合同适法性要件的具体操作方式(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劳动合同不能“当然”被认定无效,而应进一步考察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并作出利益衡量)作为论据,来对合同无效确认主体意义上的“当然无效”(合同无效的确认权属于法院的职权,无需当事人特别主张)作出反驳;进而认为合同无效确认主体意义上的“当然无效”不适用于劳动合同领域。既然合同“当然无效”的本来含义不适用于劳动合同领域,那么劳动合同法自然要作出自己的“特色”规定,即将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权赋予劳动合同的当事人(排除“当然无效”),由当事人自主确定劳动合同是否无效。这样的论证逻辑,难谓合理。
(三)无效解除说对可撤销合同的具体理解有误
前已述及,“无效解除说”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认定民法上的合同无效及可撤销的法律后果即等同于“自始无效”,故当抛弃民法上的无效及可撤销制度。而针对可撤销合同制度,相关论者尚有更加具体的反驳意见,下文将就此作进一步阐释。
主张“无效解除说”的学者对劳动合同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的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从《合同法》简单照搬的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具体理由为:
法律的抽象化趋势本身便是立法技术进步的结果。古代法典所用概念多为单独概念,抽象性极低,由此构成的规则具有极大的具体针对性和刚性。其时的法典更像是具体案例的汇编。“例如,《萨利克法典》中有偷窃一头2岁的猪如何如何的规定;偷窃一头带着小猪的母猪如何如何的规定。至于偷一头4岁的猪该如何处置、偷一头不带小猪的母猪该如何处置,《萨利克法典》缄默不语”。不存在一般抽象法规的局面恰恰反映了当时人类思维能力以及立法技术的落后。只能为经验之内的事物立法,无法凭借抽象度高的规则来对经验之外的事物行使立法权,无法使法律保持足够的弹性以适应社会关系的不断变迁。参见徐国栋:《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1页。
首先,无效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界限难以区分。“例如,用人单位按低于最低工资法的规定确定劳动报酬,既符合劳动报酬低于国家规定的特点,也符合显失公平的特点,应当是无效合同还是可撤销合同?如果按照可撤销合同来理解,其实等于让这种现象合法化。如果确定一条无效劳动合同认定优先的原则,我们会发现纳入可撤销合同的范围本身会变得很不确定”。
其次,可撤销合同从民法借鉴过来的抽象表述并不符合劳动法的特点。“什么叫重大误解?什么叫显失公平?当两名做同样工作的员工拿不一样的工资时,算不算是显失公平?民法理论是将其交由法官事后认定。社会法其实本身已经有了更清楚、更具体的表述,如男女同工同酬、反歧视以及薪资政策要走一定的民主程序等等,法官已经有了更具体的审查标准,那种抽象表述的必要性已经大大降低”。
对于上述两点理由,笔者的反对意见如下:
首先,合同的无效与可撤销均意味着法律对合同作出了否定性评价,但否定程度有所区别:前者系绝对否定,后者系相对否定。在合同无效与可撤销出现重合的情形,应当取其重者,即按照无效的结果来处理;否则便等于人为减低了法律对相关合同的否定评价程度,进而导致无效制度的立法目的落空的结果。“用人单位按低于最低工资法的规定确定劳动报酬”的情形,毫无疑问应认定为劳动合同(部分)无效,并无“不确定”可言。
其次,所谓显失公平,是指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使一方遭受重大不利。其构成要件为:双方的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这种不对等违反公平原则,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限度。易言之,显失公平所描述的是同一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失衡的情形,在劳动合同领域即意味着在某一劳动合同当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显不对等。
再次,持“无效解除说”的学者认为,可撤销合同制度中“重大误解”、“显失公平”一类的概念,属于“没有必要”的“抽象表述”。笔者认为,举凡法律条文,必有抽象性;任何法律概念,必然属于“抽象表述”。从历史的角度言之,法律的抽象化趋势本身便是立法技术进步的结果。对法律条文中的“抽象表述”作出具体、明晰的解读,从而增强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系法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之一(解释论操作);如果说,“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属于没有必要的“抽象表述”,那么,作为劳动合同无效原因(《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的“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免除自己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一类的表述,是否也同样属于没有存在必要的“抽象表述”?单纯以某一概念是否属于“抽象表述”来判断其合理性的观点,恐难谓全面。
五、总结与思考
(一)应当在学理和立法两方面否定“无效解除说”
持“无效解除说”的学者认为,《劳动合同法》中解除无效劳动合同的制度设计,“是一个以解除的方式终结劳动关系的规定,意在不对已经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发生溯及既往的效力。这既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参见前引董保华文,第28页。)实际上,通过前文所作分析可知,无效及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自可达成排除溯及效力的目标,这种“无奈的选择”本来便是毫无必要的。
事实上,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中关于劳动合同解除协议效力的规定,亦可获知司法实务中引入可撤销合同制度的实际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法释〔2010〕12号)第10条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前款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情形,当事人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易言之,劳动合同的“解除协议”是可以依据可撤销合同制度来处理的。依据该司法解释制定机关的观点,本条规定的解除协议具有劳动合同和一般合同的双重属性,且在可撤销事由上与《合同法》存在一致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三)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
如鲁迅所言:“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前已述及,“无效解除说”的核心观点在立论依据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漏洞,相应的制度设计亦有缺陷。虽然其限制劳动合同无效及撤销的溯及效力的主张不乏合理性,但在不改变有效——无效二元体制的大前提下,以解除概念统合劳动合同效力瑕疵制度的做法,除了建立起一套“体现劳动合同法特色”的无效与解除概念之外,在功能上并无实际意义(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反而留下了难以规制违法劳动合同的漏洞,等于另一种意义上的“一刀切”)。此外,“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实际上造成了《合同法》与《劳动合同法》之间的概念冲突,引发了不必要的释义矛盾,人为地提升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不仅破坏了合同法律体系内概念和规则之间的和谐,而且极易成为涉外法律实践和对外学术交流的障碍。因此,在学理上否定“无效解除说”,在立法上摒弃“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应当打破二元制的劳动合同效力体系,引入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
在不改变有效—无效二元体制的大前提下,以扭曲基本概念的方式来增进劳动合同效力体系弹性的尝试,不仅无法有效地解决结构性问题,而且在学理上徒增困扰,实属“费力不讨好”的无谓之举。引入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并将其作为意思瑕疵劳动合同的规制手段,从而在结构上打破有效——无效的二元体制,构建多元化的劳动合同效力体系,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解决之道。
前文对“无效解除说”的相关评论已经证明了增进劳动合同效力体系弹性的要求与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将扩大当事人自主空间的立足点置于意思瑕疵之上,不轻易延伸至内容的可责性),且技术方面亦不存在任何障碍。在劳动合同效力体系得到结构性改进的前提下,德国法上的事实劳动关系(faktisches Arbeitsverhltnis)理论当可为无效及可撤销劳动合同的具体操作提供基本的、框架性的指示;而真正具有“特色”的裁判规则的形成和完善,则有赖于实务与学理共同的积累与沉淀。
(三)不应急功近利地强求部门法“特色”
《劳动合同法》所采纳的“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的确是一项独具“特色”的制度,但“特色”却未必一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当年的《民法通则》便曾采取了极具“特色”的模式,即以“民事行为”的概念取代传统的、中性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将“法律行为”等同于“合法行为”(《民法通则》第54条)。这一立法模式不仅区别于传统民法的通说,甚至与前苏联的立法模式与主流观点都有不同(针对法律行为概念的争论,即法律行为究竟是中性行为还是合法行为的争论,系源自前苏联早期民法理论,但立法机关始终坚持了传统民法理论对法律行为概念的理解);由此在学理上饱受诟病。此实可谓前车之鉴,故在进行制度创新的尝试时,不可不持谨慎的态度。
事实上,关于我国劳动合同理论基础的薄弱现状,劳动法学者已有清醒的认识,并对之作出了相当精到的阐述。如郑尚元教授所言,我国现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构建基本上是在无理论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的;“民法学界对该问题漠不关心,劳动法学界又未深入研究,而劳动立法又盲目操作”;“由于劳动法学界的学科弱势而使劳动合同理论一直处于初级水平”。劳动合同理论水平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劳动合同的制度打造欠缺民法契约法理论的支撑。在起草劳动合同相关的法律法规时,官方甚至学者很少关注传统雇佣契约理论,而民法学界对雇佣契约亦未曾提出过学术主张,更未有与劳动合同制度论战的成果献世。
依笔者观点,尽管“劳动合同”有着浓厚的国家管制的色彩并具有高度的社会化特征,但其本质毕竟仍是“合同”(《合同法》第2条第1款、《劳动法》第16条第1款);无论所谓“民事合同”抑或“劳动合同”,其订立和履行均须贯彻平等、公平、自愿、诚实信用等民法一般原则(《合同法》第3—6条;《劳动法》第17条、《劳动合同法》第3条);二者所受到的管制强度、相关当事人的自治范围虽有不同,但这仍然属于量的差别而非质的差别,并不影响对劳动合同基本属性的判断。总之,“劳动契约是法律行为、是私法契约,也是以劳务与报酬交换为内容的双务契约”。只要不去试图否认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决定性地位,纵使那些极力反对“跟在民法后面亦步亦趋”的学者,恐怕也难以断然拒斥“劳动合同的本质仍然是合同”这一基本判断。既然劳动合同与所谓“民事合同”的本质并无差别,那么,在概念使用以及制度建构方面,便不宜无视合同法的一般原理,而随心所欲地创造劳动合同法独有的概念体系。
前已述及,德国既没有独立的“劳动法”也没有独立的“劳动合同法”;规制劳动合同的框架性规范完全“寄生”于《民法典》之中,法律行为及合同的一般规定亦适用于劳动合同领域;可以说,任何一起劳动合同争议案件均离不开《民法典》相关规范的适用。但这样的“寄生状态”却丝毫不影响劳动合同法的特殊性,不影响劳动法作为部门法的独立性,不影响劳动法学科的自主性。德国模式的优势是易于实现民法与劳动法的良性互动;民法与劳动法的优势互补使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法律素材相对丰富。但其劣势在于劳动法的个别规定零散而不易查阅;法官法的透明度(Transparenz)不足,难于掌握。相比之下,中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构建和运作,本应具有某种后发优势:一方面,作为民事合同基本法律的《合同法》,立法水准相对较高,经过十余年的司法实践和学理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对丰富的成果与素材,可资利用。另一方面,劳动合同的基本法律框架系以独立的单行法——《劳动合同法》为表现形式,制度体系的可识别度较高,能够有效避免规范庞杂零散的弊端。但劳动合同法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现状,则很有可能将这一后发优势消弭于无形。
不论劳动合同法律规范是以所谓“社会法理论”、“劳动法理论”抑或“民法理论”为基础而建立,劳动合同立法所追求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体系严谨、合理可行的裁判规则,而不是刻意体现所谓“劳动法”、“社会法”特色的宣言书,更不是“外人禁入”的独立王国或自留地。“劳动合同法具有不同于民法的特殊性”自无疑问,但这并不意味着,劳动合同法必须着力打造出不同于民法的“特殊”概念体系方能彰显自身的独立存在。事实上,劳动合同法具有独到的价值取向、相对自足的规范内容及独立的法源,但需扎实耕耘,科学运作,所谓劳动合同法的特色即可自然浮现。“无必要的强求不同,只会降低体系的理性,升高运作的成本,最多换来一点精神胜利,实在不值”。
而对民法的所谓“扬弃”或“超越”,必以对民法相关制度有全面、深入的掌握为必要前提。实现民法学科与劳动法学科间的良性互动并促进二者的健康发展,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或许是一个较为艰巨的课题,但却是值得学界共同付出努力的正确方向。
(四)改进的基本面向
前已述及,《劳动合同法》所确立的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有悖合同无效与合同解除的一般原理,难以对违法劳动合同作出有效规制。该制度的缺陷源自其理论基础方面的不足。从立法论的角度出发,应当在立法上彻底排除劳动合同无效解除制度,打破有效—无效的二元劳动合同效力结构,引入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构建多元化的劳动合同效力体系。即一方面修正《劳动合同法》第28条中“自始无效”的一般性规定,在确立劳动合同无效无溯及力的一般性前提下、将“参照本单位相同或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作为特定情况下确定劳动报酬的标准之一,而非确定劳动报酬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删除劳动合同无效解除的相关条文,增设可撤销劳动合同制度。
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则可以考虑对《劳动合同法》第38条第1款第5项的规定作出目的性限缩,即仅将存在意思瑕疵的劳动合同(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而订立的劳动合同)纳入过失性解除制度的范围,令过失性解除制度在实质上能够发挥与可撤销合同制度类似的功能。而将违反强制性规定等严重有害社会公益的劳动合同归入无效制度的框架内,以此来克服现行无效劳动合同制度过于臃肿的缺陷,尽可能地纯化无效制度所涵括的范围,明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界限,克服劳动合同无效后果双轨制所带来的纷扰,避免法律适用的矛盾与混乱。除此之外,对于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限制,亦应通过类推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的方式,在解释上尽量予以明确。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ermination of Void Employment Contracts
WANG Shuo
Abstract:Regulations on termination of void employment contracts prescribed in the Labor Contract Law are contrary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void contracts and termination of contract, for it failed to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illegal employment contracts. The defects of this system originate from the serious fallacy of its fundamental theory. And the fallacy results from the improper understanding of fundamentals of civil law by related scholars. The regulations on termination of void contracts shall be eliminated in legislation and the rigid dual structure of validity of employment contracts shall be abandoned. Accordingly, voidable employment contracts should be introduced and a diversified validity system of employment contrac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termination of void contractsvoid employment contracts voidable employment contracts
①《劳动法》第18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劳动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确认劳动合同部分无效的,如果不影响其余部分的效力,其余部分仍然有效。劳动合同的无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②《劳动法》对于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设计过于僵硬,应当将劳动合同效力制度设计得更加精细且具有弹性。在我国合同法制度已实现多元制度安排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合同制度却一直坚持着简单的有效抑或无效制度,并且体现出的倾向是“尽量无效”。 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特殊性不应该是限制当事人特别是劳动者在效力选择上的发言权,而应该给当事人更大的选择自由。立法者不应越俎代庖,而应当将选择是否维持劳动合同效力的权利交给受侵害的当事人;应当确立劳动合同撤销制度,将因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劳动合同归入可撤销劳动合同的范围,劳动合同作为合同的一种形式,自然也可以通过可撤销制度使受害方当事人利益得到充分的保护;建立起包括无效劳动合同、可撤销劳动合同、效力未定劳动合同在内的多元化的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相关论述参见张渊:《劳动合同无效制度研究》,载《法学》2003年第2期,第83—86页;喻术红:《我国无效劳动合同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3期,第128页;冯彦君:《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应正确处理三大关系》,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6期,第27页。
③《劳动合同法》第26条第1款: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④关怀、林嘉主编:《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⑤参见王全兴、黄昆:《劳动合同效力制度的突破点和疑点解析》,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2期,第29页;洪宇光:《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与解除》,载《中国社会保障》2012年第8期,第61页。
⑥参见董保华:《劳动合同立法的争鸣与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510页。
⑦参见林嘉主编:《劳动合同法条文评注与适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前引⑤王全兴、黄昆文。
⑧参见许建宇:《我国无效劳动合同立法的成绩、缺失与重构》,载《中国劳动》2011年第11期,第15页。
⑨参见谢增毅:《对〈劳动合同法〉若干不足的反思》,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6期,第61页;王林清:《劳动争议热点问题司法实务指引》,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杨彬:《劳动合同效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⑩依崔建远教授的观点,合同的效力是法律评价当事人各方合意的表现,是国家意志的反映;同时也是当事人各方为满足其需要“寻找”法律的依据和支持,将自己的意思符合于已上升为法律的国家意志的结果。合同的效力作为法律评价当事人各方合意的表现,是复杂多样的:给予肯定评价,则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当事人各方承受合同条款固定的权利义务;予以相对否定的评价,则发生合同可撤销或者效力待定的效果,法律将最终决定权有条件地赋予特定的当事人,由其自主决定是否撤销或者是否追认合同;法律对当事人的合意给予彻底否定的评价,则合同无效,当事人各方仅能承受法定的权利义务。参见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96页。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8页。
参见前引⑤洪宇光文。参见前引⑤洪宇光文。
上海市总工会劳动法课题组:《劳动法课题研究总报告》,载董保华主编:《劳动合同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有必要指出的是,此报告完成于1993年。
相关论述参见陆胤、唐婵凤:《论劳动合同无效》,载前引董保华主编书,第208页;前引⑥,第499页;董保华:《口头劳动合同的效力研判》,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12期,第27页。
参见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13—214页。
参见前引⑥,第503页。
参见前引⑥,第498页。
王利明:《合同无效制度的问题——“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现场实录第173期》,资料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8694,转引自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09页;前引董保华文。
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05—208页。
参见前引董保华文。
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06页。
参见前引董保华文,第28页。
参见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9页。
参见前引,第482—483页。
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
参见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11页。
参见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05—206页。
相关论述可参见苏号朋:《合同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李永军、易军:《合同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97—198页;前引,第169页;前引,第86页。
参见前引,第109—110、118页。
必须特别指出,“对劳工不利时,当然无效”的相关表述,参见黄越钦:《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转引自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13页。
前引陆胤、唐婵凤文,第213—214页。
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63页。
参见前引⑥,第503页。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页。
学理上对于《民法通则》这一“特色性”立法模式的批评,可参见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8页;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180页;前引,第350页;尹田主编:《民法学总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参见郑尚元:《雇佣关系调整的法律分界》,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第88页。
杨通轩:《个别劳工法——理论与实务》,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62页。
Richardi, Arbeitsgesetzgebung und Systemgerechtigkeit, NZA 2008, Heft 1, S5.
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9页。
[作者简介]王硕,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