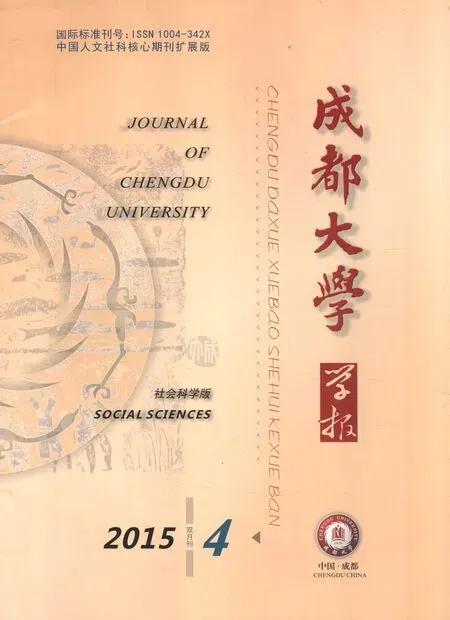钱基博与林琴南关于《技击余闻补》的一段公案辩正*
陶春军
(扬州大学 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江苏 扬州 225002)
·文艺论丛·
钱基博与林琴南关于《技击余闻补》的一段公案辩正*
陶春军
(扬州大学 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江苏 扬州 225002)
林琴南发表武侠题材文言短篇系列小说《技击余闻》后,钱基博仿其体例,撰写《技击余闻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钱基博仿写有“文人争名”之嫌,文章认为钱主观上是“逞强好胜”,客观上“补其阙略”,钱林之争反映了古代文人固执性格的趋同与对立。
《技击余闻补》;公案;辩正
文坛上与林琴南有过芥蒂的名士不乏其人,严复、章炳麟等赫列其位,其中是非曲直,论者已有广泛争论,但钱基博与林琴南关于《技击余闻补》的一段公案,却鲜有人关注。在这段公案中,作为长者的林琴南与晚辈的钱基博由于当时名气和实力的悬殊,只是近代文坛上一段低调的口水战。这段公案的结果是“双输”:钱基博失去了进高等学府北京师范大学任职的机会;林琴南出了一口怨气却输了名声和口碑。这段公案,在时人及后来研究者中也有不同的看法:支持林琴南一方认为,钱基博的续写有沽名钓誉之嫌,是淌了浑水的“文人争名”之举;而力挺钱基博的另一方则坚持,钱基博的续写是出于公正之心,纯属“补其阙略”行为。那么钱基博的仿写究竟是“文人争名”抑或“补其阙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看待这一段公案?
一、仿写引发一段公案
林琴南1908年发表了武侠题材的文言短篇作品《技击余闻》①,拉开了近代笔记武侠小说的序幕,并引起了社会对武侠题材小说广泛的阅读兴趣。林琴南何以能够创作出《技击余闻》?中国古代传统“义”、“侠”文化的影响功不可没。古代“义”、“侠”文化成形最早可上溯至西汉。西汉司马迁首次较清晰地解释了何为之“侠”,他在《史记》中替游侠、刺客立传,以“义”为核心,提出了侠德、侠品的规范。武侠小说史研究学者徐斯年先生曾指出:“至《史记》出,方有真正体现侠者立场的‘立言’。”[1]此后,唐代传奇如《虬髯客传》、《昆仑奴》、《霍小玉传》中也有侠的影子。这些侠客出神入化的技艺及高尚的侠德、侠品对林琴南《技击余闻》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除此以外,林琴南《技击余闻》的创作还有着近代中国社会深刻的“武侠”思想土壤。晚清以降,中国深受外敌欺压侵略之害,当时思想、政治等领域的有识之士,沉痛思考屡挫于外虏之教训后,渴望弘扬孱弱的中华民族庶几消失的“尚武”精神,自此君子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等激进思想大行其道,《技击余闻》这类武侠小说的创作正契合了这样的时代精神。《 技击余闻》与林琴南后来结集出版的《林琴南笔记》、《畏庐琐记》、《畏庐漫录》里面收录的武侠作品,塑造了众多形态各异的侠士,既生动形象又真实可信,时人评价他“所记多趣语,又多征引故实”[2],尤其是《技击余闻》,今天读起来仍令世人精神振奋、叹为观止。
林琴南发表《技击余闻》一炮走红,并在近代文坛引起模仿和续写热(见表1)。1914年, 钱基博步林琴南后尘,仿写了《技击余闻补》,在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第5卷第1期开始连续登出。1915年朱鸿寿推出了同名的《技击余闻补》在《小说新报》第1卷第10期开始连载。1916年江山渊发表《续技击余闻》在《小说月报》第7卷第11期登载。在模仿和续写诸作中,又以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连载时间最长,篇幅最多(见表2),影响最大,并引发了与林琴南的一段公案。

表1 《技击余闻》及续写诸篇一览表
二、“文人争名”之辩:主观逞强好胜,客观“补其阙略”
钱基博在《技击余闻补》开篇《窦荣光》中即言明:“友人以林侯官《技击余闻》相赠”[3]。钱基博是由朋友赠阅林琴南《技击余闻》小册子才萌发模仿和续写念头的。毫无疑问,他的模仿创作是主观有某种意愿才为之。此外,“叙事简劲,有似承祚《三国》。以余睹侯官文字,此为佳矣”[4]从钱基博对林琴南《技击余闻》的评语结合后面钱基博自述创作目的时相互矛盾的言论,可以推测作为晚辈的钱基博对《技击余闻》言不由衷仅为面子上的溢美之词,而真实的想法应是“此小说不过尔尔”。但此想法对文不对人,钱基博对作为长辈的林琴南本人敬重,对其古文方面的造诣钦佩,这个前提应该肯定。钱基博此前曾称林琴南是“以高名入北京大学主文课”,并肯定林琴南所著古文追慕者众多,极具影响力,“当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琴南为师法”。

表2 《小说月报》1914年第5卷1-12期连载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
既然钱基博肯定了林琴南其人其文,那么续写岂不是有掠人之美,“文人争名”之嫌?凭心而论,从《技击余闻补》发表后比《技击余闻》更胜一筹的影响来看,有这样的嫌疑不是没有道理,但笔者认为当初钱基博创作主观上更多的是作为“血气旺盛”的后辈“逞能”之举。在《窦荣光》序言中钱基博流露出这种“逞能”的豪情,“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私自谓佳者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也。”[5]钱基博年轻气盛,他觉得自己也能写好这类武侠题材,但没想过要把林琴南比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仅止于“爰撰次所闻,补其阙略”。
那么《技击余闻补》是否如钱基博所说“补其阙略”呢?林琴南的《技击余闻》涉及的大部分是福建一带的武林掌故,钱基博续写的《技击余闻补》把武林故事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他家乡江苏无锡一带,所以钱基博的说法基本是可信的。而且作为“血气旺盛”的后辈钱基博“逞能”之举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底气和保障的,理由如次:(一)历史上,模仿原著之作如归锄子著《红楼梦补》、陈忱著《水浒后传》、酉阳野史著《续三国演义》、董说著《西游记补》等,超过原著者寥寥无几,所以钱基博的仿写是要冒着巨大风险的。林琴南的《技击余闻》毕竟有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想要超越,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钱基博对自己文笔的自信。(二)清末民初,受日本影响的文言笔记武侠小说的创作因为贯穿激进知识分子强身健体、保家卫国的君子思想而大行其道。钱基博应该不是简单地抄袭和模仿《技击余闻》,他同样热衷在笔记小说中讲述武侠故事和神奇武功。他在恽铁樵主编的《武侠丛谈》跋中曾有过详细的说明,他赞扬中国自古以来“勇于持刺,为大国之风”,并认为中国的武术应像日本的柔术与瑞典的击剑术一样,发扬光大。(三)《技击余闻》开近代笔记武侠小说创作之先河,尽管其初始发表为大多数读者所欢迎,但仍不被一些评论者所看好。例如蒋瑞藻在《小说考证》中认为:“林氏自著之书,有《技击余闻》一种,为笔记体,计二十余首。首纪一人,自无结构可言,文采亦不若其翻译诸作之绚烂,无甚意味。”[6]而郑振铎先生对林琴南包括《技击余闻》在内的自创小说评价不高,他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指出:“他自作的小说实不能追踪于他所译的大仲马、史各德及狄更司诸人之后”[7],甚至更严厉批评,“林琴南先生自己的作品,实不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文坛上站得住一个很稳固的地位”[8]。从读者接受视角来看,自《小说月报》连载《技击余闻补》后,有读者通过文本阅读比较,力誉钱氏笔墨劲峭苍古,在林琴南之上,他们认为《技击余闻补》“‘行文高古,吐语尔雅’,摹态传情,亦时有可观”[9]。在语言技巧、人物塑造、文章结构等方面,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确实要比《技击余闻》更胜一筹。
由上所述,《技击余闻补》客观上确实起到了“补其阙略”的作用,但关于钱基博主观上“文人争名”之说是不符合常理逻辑的。钱基博续写《技击余闻补》是在1914年,而其在1905年16岁时就写出了《中国舆地大势论》②这样非常有思想的文章,已具文名。他在自传中曾有言“博苟卓然有以自立”[10],“平情而论,胸中未尝有不平之气”[11]。确实从主观创作动机上看,他年轻时已有所作为,不想借林琴南成名之说基本是可信的,也在情理之中。作为晚辈,他也无意于冒犯长者林琴南的权威,只是后来的冲突是钱基博始料未及的,这是他年轻气盛付出的代价。
如果模仿对象不是林琴南,钱基博的模仿也就算不得一件大事,即便模仿对象是林琴南,钱基博如果低调行事,也不至于引发冲突。况且模仿林琴南《技击余闻》的还有朱鸿寿、江山渊等人。不同的是,朱鸿寿的《技击余闻补》与江山渊的《续技击余闻》影响与成就都不及钱基博的《技击余闻补》,并且两人对林琴南礼节谦恭,对《技击余闻》推崇备至。江山渊曾在《技击余闻补》篇首对林琴南及其《技击余闻》表达了这样的敬意:“林子畏庐,善为古文辞,播声四方,其撰《技击余闻》,虽寥寥短简,实足以淬民气而厉儒风……余窃私其意,博取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最而录之,以续林子之书,自愧味道懵学,文不加采,珠玉火翟烁,王与王武无光,方之原作,自惭弗逮。”[12]钱基博在言辞和态度方面与江山渊谦恭示弱相比,明显锋芒毕露。
三、“钱林相争”之因:固执性格的趋同与对立
《技击余闻补》尽管客观上起到“补其阙略”作用,但因钱基博主观上逞强好胜,而给时人及研究者留下掠人之美、“文人争名”的不好印象,这也暴露了钱基博年轻时的固执性格。固执性格的人具有坚持成见、对侮辱和伤害耿耿于怀、自我评价过高、不懂变通、不接受批评、易冲动等特点。钱基博因说出许多逞强好胜、无意间冒犯林琴南权威的言论而招致猜疑,与他的固执性格不无关系。而林琴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一点上,他们性格具有趋同性。林个性独特、自视甚高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陈衍批评他的诗文而招致他的反击。他的同乡好友陈衍(石遗)是写诗行家,掌故大王郑逸梅先生对陈衍批评林琴南诗稿经过有这样记载:“林琴南不以诗名,偶有所作,得数十首,以示陈石遗,石遗谓工者十之二三,不工者十之七八,劝其大加删汰。”[13]林琴南本想拿着诗稿去朋友处获取一番赞美之词,却被如此评论,觉得羞愧难忍,争辩不服。而事实上,林琴南诗文成就是不及其古文的。后来陈衍又批评其文,使其全面失态,奋起反击。《林畏庐先生手札》中曾记载这样的忿忿言辞:“石遗(陈衍)言吾诗将与吾文并肩,吾又不服,痛争一小时。……六百年中,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诚然,陈衍以林诗与其文相提并论,肯定不妥,但林琴南推崇桐城派古文的章法,并在前后六百年中,他仅膺服明朝桐城大家归有光,而以天下文章第二自居,这在时人眼中,是属于顽固迂腐且“自大成狂”的。因此在白话文运动中,遭到北京大学推崇新文化的学者、教授们的反对。在古文一派中,又遭到另一位古文大师章炳麟的诘难。在章炳麟看来,林琴南认为唐以前的古文不可学,实在是可笑之极。张俊才先生在其所编的《林琴南年谱》中记载了林琴南对章炳麟等的反击:“本年(1913年)林琴南与姚永概因与京师大学堂中魏晋文派势力不相合睦,遂一齐辞去大学堂职务……之后不久,又致书姚永概,对推崇和学习章炳麟古文的人,大加挞伐。”[14]林琴南因为有这样的固执性格,所以对钱基博模仿《技击余闻》一事也就不会漠然置之的。“决不让侯官出人头地”不单纯是钱基博的调侃之言,更是他对自己创作才能极度自信的表现,这足以让林琴南心中产生芥蒂。
可能林琴南认为以他当时的成就和声誉,不应该受到这样的挑战。事实上,尽管林琴南的译作及创作存在很多问题,但一般极少有人对他发难。郑逸梅先生在其《艺林散叶》中曾记载吴县文人陆澹安欲修改林琴南译文而终放弃一事:“林琴南译《茶花女遗事》,语挚情深,为时所称,陆澹安却认为语多疵累,为之窜改,友以徒劳无益劝止之,乃中辍。”[15]
由此可见,林琴南难以接受异己的意见绝非一般。心理学上认为,性格同样固执的两个人相处,容易产生矛盾、隔阂,甚至对立。钱基博的续写,在林琴南看来,属于冒犯长辈的无礼之举。《技击余闻补》让他很难保持谦谦君子之风,他进行了异乎常规的反击,甚至行为失范。林琴南的反击措施主要有三:(一)写信给商务印书馆高层以不愿再继续供稿为要挟:“此后愿让贤路,不再贡拙。”[16]碍于面子,林琴南没有直接跟晚辈钱基博论战交锋,而是以退为攻,先将大东家商务印书馆抬出来,逼其不再登载钱基博的武侠小说。此招非常有效,当时林译英美等国言情小说在中国读者中炙手可热,林琴南与别人合译之《双雄较剑录》、《想夫怜》等小说连载在《小说月报》上,且占据较重要的份量。商务印书馆高层高梦旦等人估量轻重,以报刊发行的商业利益为旨归,选择“弃林保钱”偏向于林琴南(此语疑有误,当是“弃钱保林”)。钱基博被“封杀”后《小说月报》上的武侠小说改由他人撰供,所以《技击余闻补》在《小说月报》上登载到第5卷第12号便不再连载。(二)让商务印书馆不再出版钱基博的著作。在《钱基博自传》一文中,钱基博提起十五六年前与林琴南结怨的事情,说林琴南“不胜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戈矛,儒林沦于市道,属商务不印拙稿”[17]。(三)阻挠钱基博到北师大任教。
这三条制裁措施基本都奏效了,尤其是北师大任教职而未成行更引起了钱基博强烈的对立情绪。钱基博视林琴南此举为小人(臧仓)行径,多年之后,钱基博在其《自传》中回忆到这一段仍难以释怀:“有友人介绍博任北师大国文讲座,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气焰炙手可热,亦作臧仓,致成罢论。”[18]但作为后辈的钱基博对于林琴南的过分之举无法正面唇枪舌剑抗衡,而且钱氏没料到步林氏创作后尘,竟引起林氏如此强烈的反应,当时主观上可能亦有自责之意,故面对林琴南咄咄相逼的气势更多的是隐忍退让。只是后来,他在《钱基博自传》中,曾有过这样的抱怨:“畏庐六十老翁,不能宏奖后进,而党同妒道若是!胜我不武,不胜见笑!”[19]林琴南比钱基博整整大35岁,钱基博认为林琴南作为长者,应当提携后进,而不应该气量如此狭小。所以他早期对作为长辈的林琴南本人敬重、对其古文方面造诣的钦佩态度在后来发生了逆转。从钱基博对林琴南的所有评价来看,笔者认为至少有两点反映这种态度转变。一是他对林琴南翻译的言情小说颇不以为然,他在《钱基博自传》中借李详之口表达出了这种声讨和谴责:“观其所译小说,重在言情,纤禾农巧丽,浮思古意。三十年来,胥天下后生,尽驱入猥薄无行,终以亡国,昔人言王、何之罪,浮于桀、纣。畏庐之罪,应科何律!”[20]二是林琴南在古文方面,废黜百家,独尊“桐城”,这是钱基博所不苟同的。他认为“桐城之文,尚澹雅而薄雕镂。而畏庐则刻削伤气,纤禾农匪澹,于桐城岂为当行!而气局偏浅。”[21]《钱基博自传》是事情隔了十几年后所撰,但正是因为钱基博对林纾不满主观因素存在,他在言辞方面与先前对林琴南的态度相比,明显前恭后倨。
在这段公案中,钱基博和林琴南在性格固执上具有趋同性,并最终对立,在对立过程中,便显出林琴南作为长者气量缺失,而钱基博作为晚辈谦逊不足。
古代文人的固执性格,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存在而具有普遍性,不仅仅在钱林身上体现,在《小说月报》主编的恽铁樵身上同样得到体现。面对商务高层“保林弃钱”片面追求商业利益的不厚道做法,恽铁樵心中很为钱基博不平,“他对于梁溪钱基博(子泉),有一事颇感歉仄”[22]。这种不平同样通过倔强固执性格表现出来: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甚至不畏林琴南这样的权威。我们通过恽铁樵主编的《武侠丛谈》③一书,可以窥其端倪。恽铁樵编辑《武侠丛谈》,并为之作《序》,但文中闭口不提林琴南。《武侠丛谈》作为武侠小说合集,竟连名噪一时的林琴南一篇作品都没有收录,却将书的三分之二的篇幅给了钱基博,这或许正体现了恽铁樵的立场:处事公道,不偏袒于强势一方,更没有与强势一方结党联营。顶着商务高层的压力,恽铁樵坚持己见,但又有所节制,对钱基博和林琴南没有公开地声援和讨伐,他的做法与钱基博相似,都是低调固执。低调固执而不失君子坦荡之风契合恽铁樵在《小说月报》任主编时的办报理念:“本报宗旨,不主张骂人,含沙射影,尤所深戒。”[23]
四、结语
综上所述,钱基博撰写《技击余闻补》,主观上是逞强好胜,客观上“补其阙略”,而“文人争名”的嫌疑加在钱基博头上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当时客观事实的。“钱林相争”是古代文人固执性格而引起的对立。林琴南撰《技击余闻》与钱基博撰《技击余闻补》此类笔记武侠小说,都不能算作是他们著作中的主要成就,林琴南以翻译言情小说而蜚声近代文坛,而钱基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国学方面造诣深厚。换言之,他们在笔记体技击小说创作方面,算是业余、副业,所以两人在此方面的争执,不是各自的专业成就之争,而最终没有影响他们在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注释:
①《技击余闻》版本,据林琴南弟子朱羲胄编《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世界书局1949年版)之二《春觉斋著述记》所述,他在宣统初年见到铅印本,但找不到此版本,故以1913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为始。林琴南研究专家张俊才先生在《林琴南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所撰《林琴南著译系年》,沿用朱羲胄《春觉斋著述记》中所述。学者林薇在《林琴南自撰的武侠小说〈技击余闻〉最早版本辩正》(见林薇著《清代小说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299页)一文辩正,商务印书馆绣像石印本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版(1908年)确已存在,商务印书馆于1913年再版。《技击余闻》中共收短篇小说46篇,其内容主要是写江浙闽粤沿海及台湾的武林故事,有7篇涉及京陕齐鲁中原武林琐闻,还有西方“技击”传闻“转载”,例如《巴黎力人》、《巴黎技师》等。
②《中国舆地大势论》刊于《新民丛报》第64至67号,分别连载于1905年3月6日、3月20日,4月5日、4月19日;又转载于《广益丛报》1905年7月22日第77号。
③恽铁樵(冷风)所编的《武侠丛谈》一书,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海书店1989年3月影印再版。该书共48篇,选录了钱基博小说32篇,另有许指严、江指厚诸人作品。
[1]徐斯年.侠的踪迹——中国武侠小说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2]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3][4][5]钱基博.窦荣光·序[J].小说月报,1914(5).
[6]蒋瑞藻.技击余闻第四十九·小说考证·续编卷二[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7][8]王俊年.1919-1949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柯灵,张海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笔记文学集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
[10][11][17][18][19][20][21]钱基博.钱基博自传[J].江苏研究,1935(8).
[12]江山渊.续技击余闻[J].小说月报,1916(11).
[13][15]郑逸梅.艺林散叶[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4]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16]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22]郑逸梅.恽铁樵奖掖后进.郑逸梅选集(第二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23]恽铁樵.某三·编者跋语[J].小说月报,1915(7).
(责任编辑:刘晓红)
Discrimination on the Detective of Supplement About Fighting That I Listened between Qian Jibo and Lin Qinnan
TAO Chunjun
(Post-Doctoral Mobile Station of Ar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2)
Lin Qinnan published the classical Chinese short stories with knight-errant theme Fighting That I Listened,Qian Jibo paced its follow,wrote Supplement About Fighting That I Listened and it was continuously published in Short Story Monthly,which made the suspicion of fighting for reputation.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Qian “seeks to prevail over others" subjectively and “filled the omitted story" objectively.The conflict between Qian and Lin reflects the convergence and opposition of ancient literati's stubborn character.
Supplement about fighting that I listened;detective;discrimination
2015-04-2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规训与突破”(10BZW013)阶段性成果。
陶春军(1973-),男,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博士,扬州大学博士后。
I207.419
A
1004-342(2015)04-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