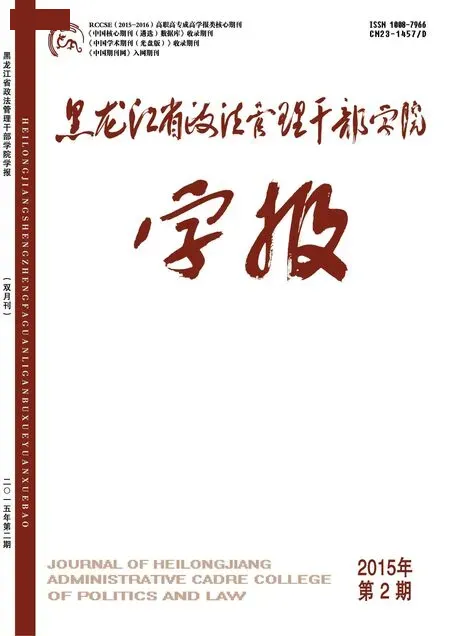公共场域中媒体跟拍娱乐明星隐私的法律分析
——以第四权理论为视角
马树同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银川750021)
公共场域中媒体跟拍娱乐明星隐私的法律分析
——以第四权理论为视角
马树同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银川750021)
学界对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中的隐私权存有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能否享有隐私权;二是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隐私的界限是什么。争议的出现,概因对于娱乐明星是否属于公众人物的范畴有不同的认识。根据公众人物这一概念的起源、类型及判断标准,娱乐明星当属公众人物的范畴。在公共场域中,作为公众人物的娱乐明星,其隐私权不是当然受到限制,只有娱乐明星的隐私涉及公共事务,或能引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需要媒体对政府权力监督的时候,其隐私才会受到限制,这是第四权理论下,媒体于公共场域中跟拍娱乐明星隐私不为侵权的法律依据。
跟拍;隐私权;公众人物;公共场域;第四权力
基于文字的缺陷,媒体对欲报道的事件以图片、影音等更直观的方式进行传播,是其吸引受众必然选择的一种方式。这些图片、影音等资料的来源,除了对相关事件、人物的采访报道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跟拍。当然,基于新闻本身的特性和私权利的保护,对一般普通民众的跟拍并不具有必要性和合法性。有学者在微博上指出,“相比法治、腐败、环境和民主问题,中国的年轻人更关注明星的私生活”[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体报道领域的一种现状。问题是:媒体为了满足受众的猎奇心,对娱乐明星私生活进行报道时是否侵权,特别是在公共场域中,媒体跟拍娱乐明星隐私的行为是否有法律依据,在何种情形下,媒体的这种行为可以获得法律的支持。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公众人物的隐私应受保护,但较之普通民众需受到较多的限制。但对娱乐明星是否为公众人物?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的隐私是否应予以保障及保障的依据尚有争议。对这些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新闻法治的推进和媒体自律的提升,对娱乐明星的个人权利亦是一种保护,这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娱乐明星是否为公众人物
虽然在媒体报道中,经常将娱乐明星涵盖在公众人物概念之中,但学界对娱乐明星是否为公众人物却存有争议①具体可参见孟卧杰:《论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载《政法学刊》,2009年第3期;孙欣、杜智娜:《想灿烂,就别怕曝光》,载《法律与生活》,2003年1月下半期。。
(一)公众人物的概念
公众人物的概念起源于美国,1964年《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首次确立了“公共官员”的概念。在三年后的巴茨案件中,法院正式提出了公众人物的概念。本案中,首席大法官沃伦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其在关系到公共问题和公共事件的观点与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常常与政府官员对于相同问题和事件的态度和行为上涉及公民的程度相当。”[2]93但同时,大法官在本案判决书中也提及,所谓公众人物者,即“因其地位特殊,或因其主动卷入特定重要公共争议之行为,而使社会大众对其一举一动产生相当之兴趣,且其具有可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工具,以澄清不实报导之能力”。以及,凡“密切涉及如何解决重要之公共问题,或其盛名即足以影响社会所关切事务之发展者”,即属公众人物[3]101。可以说,公众人物本身既不是一个政治概念,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限制人格私权而创制的一个概念。要对公众人物下一个完整的概念不仅有难度,而且也是不理性的,即便在公众人物概念起源的美国,对公众人物的概念界定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只是通过法院的判例界定了公众人物的范围。所以,为了对公众人物的概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有必要对其类型的划分②对公众人物类型的划分,本文采用的是学界比较通行的标准,具体可参见,王利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做一交代。
一是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 forallpurpose),主要指在政府机关担任重要公职的人员。此类人物或拥有极大的权力、影响力或特殊之社会地位,或获有普遍的声誉或恶名昭彰,或在社会事务上扮演特别醒目的角色,或完全暴露于媒体持续性的注意下。法律通常更对他们所为有关执行职务或出于自辩之言论,特别予以不罚之保障规定,因此他们实具有远高于常人之机会去澄清辩解错误之报道或批评,而他们的活动、言行都关系到公众“知的权利”的问题,故对他们的人格私权应做必要的限制。在一些案例中,法院认为,这些人在社会事务中具有特别出众的作用,他们都是一些著名的、有影响力的人,因此必须要由其举证证明侵害人具有真实恶意或重大过失,才能对其名誉损害进行补救。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公职人员的隐私都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某人的职位过低,也没有必要把他当成公众人物对待①有学者质疑存在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其理由是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得不到保护。根据西方的传统,高官无隐私,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完全目的的公众人物无隐私。。
二是自愿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s voluntarily),也称为“有限目的的公众人物”(limited purpose public figure)。这些人的行为涉及公众的兴趣和娱乐生活,这种公众兴趣虽然不是公共利益,但涉及公众的利益,或自愿投入特定的公共争议,或在公共问题的解决中特别突出,或把自己放置在特定公共议题的最前线,以便影响该议题之解决者。因此在法律上也有必要从维护大众的利益考虑对其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进行限制。影视明星、运动明星等即属此类之公众人物[2]93。
三是非自愿的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s involuntarily),指某些人本身不是公众人物,不会引起公众兴趣,更不会涉及公共利益,但因某些事件的发生而偶然卷入其中从而成为“公众人物”。偶然的公众人物具有暂时性,随着这些事件的“降温”,这些公众人物又回归到普通人物的行列了。在美国法中,公众人物可以是偶然的,他们由于莫名的运气偶然地卷入某公共事件,这些人为数通常极少。而且,这种非自愿的公众人物,并非都丧失其隐私权[2]93。
(二)公众人物的认定标准
从公众人物概念的起源看,公共利益是公众人物的核心要素,但如果以此来认定公共人物②有学者主张判定公众人物的标准应为:一是社会知名度;二是与公共利益相关,具体可参见孟卧杰:《论公众人物及其隐私权》,载《政法学刊》,2009年第3期。,则并不恰当。如果以公共利益来判定公众人物,会在现实中产生灰色地带,对一些人物是否为公众人物难以认定③对公众人物类型的划分,本文采用的是学界比较通行的标准,具体可参见,王利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2期。。判定公众人物除了应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还可以参考以下标准:一是该人物是否能比其他人更有接近媒体的管道;二是在相关公共事件中,该人物是否自愿担任某种特别显著角色,并且促进大众承认或认同其担任角色;三是该人物是否设法影响特定争议的解决方式与结果,及其在争议解决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四是媒体是否持续对其采访、报道,及相关该人物的新闻事件曝光时间的长短[4]43。
就上述公众人物概念的起源、类型及判断标准而言,娱乐明星无疑属于公众人物的范畴。从类型划分来说,娱乐明星当属自愿型的公众人物;从公众人物认定标准来说,娱乐明星除了社会知名度这一因素外,且比普通民众更有接近媒体的管道。
二、娱乐明星的隐私范围
作为公众人物的娱乐明星拥有什么样的隐私权?他们隐私权中的隐私具体内容是什么?特别是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中隐私的界限为何?对这些问题的梳理,有助于明确媒体跟拍权的行使和娱乐明星隐私权的保护。
(一)隐私与隐私权
“隐私”与“隐私权”在人们的口语使用中往往不太区别,两者可能都指的是生活中的一种防护样态。当欲借此而有所主张的时候它应该是一种权利,始得主张[5]68。
一般而言,隐私“是指不愿告人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6]1626。可以说,隐私是随着人类群居,社会组成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在先民裸体而居,与恶劣生存环境抗争的年代,是不存在隐私一说的。所以,隐私虽依附于个人、社会、环境,其本质却总是与之对立。隐私之所以“隐”,是为了避免他人或群体探知、观览或干涉,因此隐私的追求,逻辑上势必与他人、群体(总之是自我以外的任何他人)产生紧张或甚至冲突的关系[5]68。从现实生活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都在吞食他人的隐私,每天的新闻、杂志、电视、广告连续不断的报道各种关于他人事物的新闻事件或娱乐节目,以满足读者或观众想窥悉他人隐私的本能或欲望。在重大意外事故、经济犯罪或政治丑闻、名人自杀或猝死事件发生时,人们都想知道谁牵涉其中,如何发生,当事人的家人是谁,有何反应,有无不可告人之事。社会集体有窥悉他人信息的兴趣,大众媒体搜集、储存、传播、公开提供各种消息,在言论自由的市场大量地消费他人的隐私,造成了隐私保障与表见自由的紧张关系。”[7]3
“相较于单纯概念描述的隐私,隐私权便是隐私这样一个概念在法律面前如何被认识、看待与评价的问题,并且是进而可以成为在侵权法律关系的求偿上、在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清单里,作为界质的一项权利。”[5]69
对于隐私权概念的探讨,最早最系统的是1890年美国两位法学家布兰戴斯和沃伦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论隐私权》一文。他们强调任何人都有独处而不受干扰之权利。该文主张:隐私权是为了因应新闻自由之持续扩大滥用趋势,而必须对于特定私人因此所遭受不当而过度剧烈之心灵痛苦予以保障,所应予独立提出之权利类型。他们从社会新的发展产生了对新权利的需求开始谈起,认为个人的权利从最初的身体方面扩及名誉方面,最后不可避免地会扩及情感、精神方面。由于摄影技术的进步及报纸的兴盛,导致对私人及家庭生活造成侵害。报纸的报道逾越了社会礼仪的界限,将闲话(gossip)转化成为商品(trade),以满足大众粗俗的品味[8]15-16。
同时,他们二人在文章中也讨论了隐私权的界限,在下面几种情形中,隐私权不受保障:一是涉及公众或一般利益事物(any publication ofmatterwhich is ofpublic orgeneral interest)之出版;二是虽然所发布的事物本质是具有私人性的,但依照法律把它当成是具有传播特许(privileged communication)者;三是口头之散布(oralpublication)而未造成特定的损害;四是由本人散布的事实或经其同意者;但散布真实之事及散布者没有恶意(the absence of“malice”)并不构成其行为合法的抗辩事由[8]16。
此后,隐私权及其保护便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和攻击。”被认为是隐私权最重要的人权法渊源。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也做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有关规定。
虽然学界至今对隐私权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对妨碍隐私权归纳出两个诉求:其一是干扰他人私生活;其二是未经本人同意。同时符合此二要件,极可能就可以认定侵犯了个人隐私权[9]61。
(二)公共场域中娱乐明星隐私的界限
根据前文所述隐私与隐私权的起源、范畴等方面的内容,应当认定在公共场域中,隐私权仍有得以主张的空间。既然公共场域仍有隐私权主张的空间,那么,在媒体跟拍娱乐明星所引发的隐私权冲突中,对隐私的范围应如何界定?笔者拟从娱乐明星这一主体出发,以所涉议题、手段以及非物理性侵入三个方面做一简单阐述。
特定人物和特定议题,可以说是新闻报道之所以吸引民众关注、讨论的元素,欠缺其一,或甚至两者均无,则无法引起他人兴趣。例如:某当红女星独自驾车,一路循规蹈矩回家(没有价值的议题);车站的一对情侣(非公众人物)相拥吻别的身影(寻常普通的画面);等等,这些情景本身就不具备任何新闻价值,对记者而言完全欠缺猎取画面的动机,成为冲突点的机会将趋近于零,讨论其隐私也就缺乏现实基础。但若情况与此相反,一位当红娱乐明星与绯闻对象街头激吻;或夜店吸食毒品,这样的人物与议题,出现在公共场域,便难以完全主张其隐私权,并拒绝记者或一般民众的拍摄。毕竟身为公众人物,虽然处处受到瞩目,但是于特定场域呈现特定行为,仍有其个人充分选择的余地[5]141。
在公共场域里,因为高科技器材的采用,即使不着痕迹却也可能构成对隐私的侵犯。例如:采用高倍数望远或透视等器材拍摄远距离特定人与他人的互动。不过,是否当然构成对隐私的侵犯,笔者仍持保留的态度,并以为须以场所隐蔽特征的强弱来加以衡量。一般来说,隐蔽特征不高的场合,采用高倍数望远镜头拍摄,其实应属于避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现场产生不快,甚至冲突的方法,也是调和双方冲突的途径之一;但相反,若隐蔽特征相当高,隐私的权利人清楚的释放出控制注视的人群范围时,利用高倍数望远镜头或具备透视效果的器材加以猎取画面,即便并未加以利用,光是取得行为本身便已经构成隐私权的侵害[5]145。
另外,相较于容易理解的物理性侵入,非物理性的侵入往往是公开场所中最不容易划分,却也是经常发生的侵害型态。离群索居毕竟非人类生活的常态,群居生活所必然付出的代价便是个人生活不可能完全不受到他人干扰。个人身处公共场域,面对非物理性侵入的跟拍时,若不是确属受高度关注之公众人物,亦非刻意以特别方式引起他人注意,例如相对清凉的穿着、大声叫嚣之言论、动作,原则上应可期待能隐没、融入于人群、场所之中,则可主张隐私权之受保障[5]147。同时,新闻跟拍是一种人力资源支出的沉重负担,从市场经济理性选择的角度而言,除具有新闻价值的公众人物外,一般也不会存在这种新闻追踪方式。
综合上文所述,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隐私权之所以受限,除了因为娱乐明星是公众人物这一主体因素外,还受到新闻所涉及的议题、报道的手段、是否采用非理性的方式的影响。与普通民众相比,娱乐明星可能更多地涉足公共领域,其个人事务更多地会与公共利益发生联系,因而受保护的隐私少于普通人,但无关公共利益部分的隐私,也应给予与普通人同样的保护。也就是说,公共利益是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隐私权受限的边界,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不受隐私权保护。但问题是:在公共场域中,媒体对娱乐明星隐私的跟拍如果和公共利益相关,其法律依据何在?
三、媒体跟拍娱乐明星隐私的法律依据
(一)跟拍的定义
“跟拍,从字义来说明,包括了‘跟追’与‘拍摄’,即为了达成拍摄特定画面的目的而采取跟追行为的方法加以拍摄,是新闻采访须采用的方法之一。”[5]18“跟追”,系指以尾随、盯梢、守候或其他类似方式,持续接近他人或实时知悉他人行踪,足以对他人身体、行动、私密领域或个人资料自主构成侵扰之行为。若从此定义,则跟追所指涉的行为态样相当广,无论是动态的尾随,或者静态的盯梢、守候,都包括在内。固然得收有对被跟追人较完整保障之效,却也更容易形成与跟追者的冲突[5]18。
跟拍既属新闻采访手段之一,为公众提供信息,自应为新闻采访自由所保障。根据学界通行的观点,新闻自由是包含采访自由的。新闻采访自由的讨论往往置于新闻自由的讨论之下,新闻自由受到保障,作为新闻自由下位概念的新闻采访自由自然也在保障的范围之内。所以,笔者将以新闻自由的理论基础——第四权理论——展开讨论。
(二)第四权理论
1974年11月2日,美国联邦大法官Stewart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发表演讲,根据新闻媒体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功能,提出了第四权理论。Stewart大法官认为,宪法之所以保障新闻自由,目的就在于保障一个有组织的新闻传播媒体,使其能成为政府三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以便监督政府,防止政府滥权,发挥制度性之功能[10]159。
Stewart大法官之所以会提出第四权理论,主要是因为观察到他当时所处美国社会中,新闻媒体所担任的角色功能而引起。他观察到新闻媒体在越战时期所作的调查性报道以及与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相抗衡的角色功能,开始受到美国人的注意。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锲而不舍追踪调查及报道,导致尼克松总统的辞职下台,更使人们深切地认识到新闻媒体在担任监督政府功能方面所能发挥的效果。同时,他也观察到,虽然民众欢迎媒体揭露并监督政府官员不法的行为,但也对媒体在发挥该功能时,所行使的权力是否合法正当,感到疑惑。Stewart大法官于是提出第四权理论,说明新闻媒体担任监督政府的功能,正是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新闻自由”所设之目的[11]74。
根据该理论,宪法之所以要保障新闻自由,是为了保障新闻媒体的独立性及完整性,维持新闻媒体的自主性,以便能够提供未受政府控制或影响的信息、意见及娱乐,促使人们加强对政府及公共事务的关心,并引发公众讨论,形成公众意见,帮助公众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对政府的监督,虽然在理论上或事实上,最后仍需借由民众的舆论或公意,并经由选举时的投票、或消极的不遵守政府的法令、或甚至以极端激进的革命手段等压力,使政府能接受人民的监督。然而,民众的监督力量,往往是相当分散的,要整合汇集人民的力量并不容易,而且人民也缺少政府所拥有的强大资源,例如机关组织、专业人员、信息情报等,由新闻媒体作为监督政府的媒介,其重要性由此就可以体现出来[11]79。
(三)公共场域媒体可否跟拍娱乐明星隐私
根据第四权理论,媒体享有新闻自由,是因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媒体发挥的制度性监督政府权能所需。跟拍作为媒体获取资讯的一种方式,当属采访自由之内容,只要符合媒体监督政府权能之发挥,就不应限制。而媒体在公共场域跟拍娱乐明星隐私之行为,是否必然属于应限制行列,则须根据不同情形予以对待。
当娱乐明星出现在公共场域时,其隐私权的保护就必须和第四权理论中媒体监督政府的权力相权衡。甚至,当娱乐明星參与了受到民众瞩目的重要新闻性事件时,是无法向法院要求免于引起大众注意的(avoid publicity)[9]76。虽然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仍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但其隐私权的范围显然取决于參与公共事务程度之深浅,以及该事务受到大众瞩目的程度。
另外,娱乐明星作为公共人物这一主体特性也决定了其介入公共生活领域可能性较大,其言行举止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色彩。因此,媒体在公共场域进行跟拍时,基于维护公众资讯利益之权利,参与公共事务之讨论,娱乐明星的隐私权应受到明显的限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娱乐明星在公共场域一定无法保护其隐私权,媒体在跟拍的过程中,如果将娱乐明星的不雅谈话或尴尬画面,比如某当红明星与第三者的亲密情形摄入镜头并报道出来,则视个案情节,有可能构成隐私权的侵犯。换而言之,依据第四权理论,媒体为履行监督政府之权能,需提供多元化的资讯,包括娱乐资讯,以引发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进而发表公共意见,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如果媒体所提供的娱乐资讯涉及新闻当事人的个人隐私,且与公共事务无关,无助于对政府权力的监督,这种媒体跟拍娱乐明星隐私的行为就应该受限。
[1]《港媒:演员八卦盖过“严肃”新闻不是件好事〔DB/OL〕: http://new s.xinhuanet.com/world/htm.
[2]王利明.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和保护[J].中州学刊,2005,(2).
[3]法治斌.论美国妨害名誉法制之宪法意[J].政大法学评论,1986,(6).
[4]吴佳颖.平面媒体对于公众人物采访与报道自由之研究[D].台北:台北教育大学,2012.
[5]蓝宗煌.跟拍采访之基本权利冲突研究[D].高雄:高雄大学,2013.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26.
[7]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上)[J].比较法研究,2008,(6).
[8]詹文凯.隐私权之研究[D].台北:台湾大学,1998:15-16.
[9]陈仲妮.论新闻自由与公众人物隐私权之冲突与调和—以欧洲人权法院卡罗琳公主诉德国案 (VON HANNOVER v.GERMANY)为中心[D].台北:东吴大学,2008.
[10]马树同,刘小冰.论我国突发事件中的新闻自由[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11]林子仪.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
[责任编辑:李 莹]
①比如某些娱乐明星,虽然为公众所知,但与公共利益并无直接的联系,而且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性很强的概念,这样对一些娱乐明星是否为公众人物的认识就会产生分歧。
DF2
A
1008-7966(2015)02-0013-04
2014-11-01
马树同(1982-),男,宁夏固原人,法学硕士,教师,主要从事宪法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