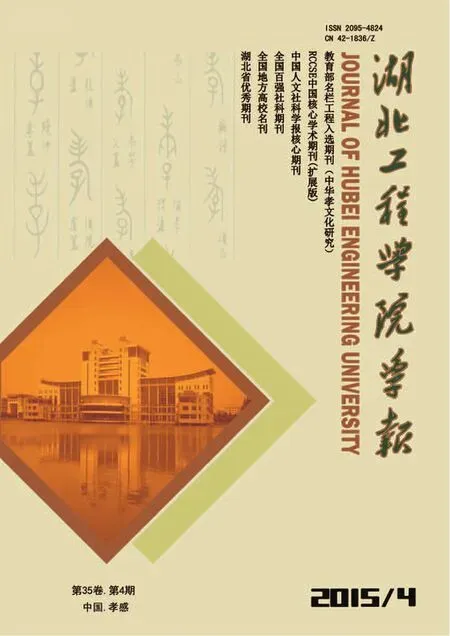崇孝与尊老
——西汉诏令中的“孝”伦理思想探究
王传林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
崇孝与尊老
——西汉诏令中的“孝”伦理思想探究
王传林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875 )
秦亡汉兴,“孝治”确立。从西汉诏令凡涉“孝”的内容来看,“孝”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理念贯穿于整个西汉王朝。从“孝”的“呈显”与“发用”来看,“孝”之于政治似乎存在一个向人伦至情回归的逻辑向度与价值向度,即“孝”始于“情”,发用于“事”并在发用于“事”时回归到“情”本身。从西汉历史之维看,“孝”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理念在西汉政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所彰显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关怀与人道精神,而且也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人伦至情与终极性的伦理情怀。
《西汉诏令》;崇孝;尊老;价值向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诏令”是最高统治者即皇帝颁发的命令,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文化、军事、外交政策等诸多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帝国的“诏令”不仅仅是那个时期的重要史料,而且对于研究王朝兴衰、制度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矛盾、社会矛盾、伦理文化与价值取向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人云:“两汉诏令,最为近古,虙等采辑详备,亦博雅可观”;“诏令之美,无过汉唐”;“《两汉诏令》虽取之於‘三史’,然汇而聚之,以资循览,亦足以观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之遗”。[1]495愚观西汉所制诏令特点鲜明:内容文实相兼,行文典雅而凝重,气韵温润而浑厚,足为后世之典范。凡考,《西汉诏令》为宋时“吴郡林虙德祖编。采括志传,参之本纪,以示信安程俱致道。俱以世次先后各为一卷,差比岁月,纂而成书,且为之序”[2]133。“《东汉诏令》十一卷宗正寺主簿鄞楼昉旸叔编。大抵用林氏旧体,自为之序。”[2]133由此可知,《西汉诏令》与《东汉诏令》原为两书,各自为卷。宋室南渡后,楼昉依林虙之体,编《东汉诏令》以续之,并在嘉定十五年(1222)作《自序》。至此,《西汉诏令》与《东汉诏令》“编合为一书,题曰《两汉诏令》,而各附原《序》於后。其首又载洪咨夔所作《两汉诏令总论》一篇”[1]495。也就是说,南宋之末,两书珠联璧合,合而为一,始成《两汉诏令》。时至清代,清朝官方编纂《四库全书》时,从之。又考,《西汉诏令》成书于北宋之末(1109年),成书不久即付之版刻。其证据是《西汉诏令》目录后有大观三年(1109年)程俱、林虙、蒋瑎三篇序言和林氏的发刊识语。林虙所辑《西汉诏令》,凡涉诏令内容均直引《史记》与《汉书》,收录西汉高祖至平帝,凡十一帝与一后(吕后)所颁诏令凡计“四百一章”(即401道诏令),以世次先后编成十二卷。该书是一部收录完备、编次讲究的西汉诏令总集,同时也是古代诏令编纂史中的重要成果之一。
循历史之维,探儒术之用。本文试图通过对《西汉诏令》[3]中“孝”伦理思想的梳理,以探寻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在西汉政治中所凸显的伦理理性、伦理范式与价值向度。
一、“孝”思想在政治中的确立
秦亡汉兴,“孝治”初立。汉初,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更好地建设新政权的需要,上至皇帝下至学者都对秦朝的成败得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与总结,前有陆贾与刘邦的“十二论”,后有贾谊的“过秦论”。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中,儒家的孝悌仁义思想受到广泛的重视。当然,“孝”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还反映在皇帝本人对“孝”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推崇。史载刘邦当上皇帝后,于高祖六年五月颁《尊太上皇诏》,此《诏》可谓是汉朝确立“孝治”为其政治伦理理念的重要标志。继而,在家国同构的政治间架下,“孝”的理论边界被突破,逐渐由家庭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1.反思“秦弊”。面对秦时“不施仁义”而最终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陆贾向刘邦进呈的“十二论”,大谈“仁义”的重要性,他说:“圣人怀仁仗义,……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4]可以说,陆贾的“新语”为刘邦接受儒家仁义孝悌提供了理论依据。客观地讲,法家的政治哲学对处于战时状态中的秦国而言,有助其迅速实现政治层面的从无序到有序之变,有助其迅速实现经济层面的从穷困到富裕之变,有助其迅速实现战争层面的从无力到勇猛之变。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法家的严刑峻法之弊、急功近利之弊与仁义不施之弊。贾谊曾以《过秦论》细数秦之利弊,在他看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5]由是观之,贾谊以“仁义不施”画龙点睛式地概括出了秦亡的症结,凡此在某种程度上为儒家伦理之于西汉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基于历史经验的精辟论证。其实,司马迁对秦的短暂宿命与严刑峻法的弊端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思。例如他在《史记》中云:“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6]2236司马迁更是借商君之口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6]2236-2237又如,《史记》记载:“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6]2156;李斯更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6]2563凡引可见,法家之法使人噤若寒蝉,即便是曾贵为立法者,有时也难免其害;法家用刑之深,不仅扭曲了人性而且淹没了人情,更疏离了正常的人伦关系与社会交往。
2.确立“孝治”。秦亡汉兴,“孝治”初立。随着“孝”伦理观念进入到政治,原本冰冷而血腥的政治似乎多了几丝温情。这其间或许是因为政治的需要,但也是伦理亲情之于政治层面的一种彰显。
很显然,“孝”在西汉政治中的确立与皇帝们对“孝”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推崇是分不开的;“孝”在政治上的重要表现还反映在皇帝本人对“孝”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推崇,例如刘邦当上皇帝后,将其父封为太上皇。史载,高祖六年五月颁《尊太上皇诏》,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7]62由是观之,此诏不仅体现了刘邦内心流露出的基于血亲关系的至亲之情,而且也确立了汉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理念。又如,孝惠帝毁“复道”之事,更是反映出即使身为皇帝也必须遵守“孝道”,不敢贸然有违。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另据史载,汉文帝本人也曾以孝闻名,对此袁盎赞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6]2739上引可见,儒家“孝”伦理思想在西汉政治中的规约性与影响力。同时,汉文帝为母尝药尽孝之事被世人传为美谈,“当时天下咸祢颂帝之仁孝”。此外,“孝”在西汉前期政治中的重要性还表现在皇帝们的谥号多追加“孝”字。根据《史记》本纪记载,西汉前期诸位皇帝多以“孝”为尊,例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皆以“孝”为谥号。这一现象侧面反映出汉初诸位皇帝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认同与推崇,同时也折射出“孝”作为一种基于家庭亲情关系的伦理范式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尽管西汉初年官方在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大力推崇黄老之学,但是在具体的家庭生活与社会伦常中,儒家伦理哲学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儒家推崇的“孝”伦理思想不仅成为维系家庭伦理关系的枢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维系政治伦常秩序的关键。
由上观之,西汉王朝确立“孝治”为其政治伦理理念既有对历史的反思与回应,又有迫于维系现实尊卑关系的理论需求;同时也反映出人伦至情从家庭领域向社会与政治领域扩展的新动向。换言之,西汉王朝确立“孝治”为其政治伦理理念有历史、现实、伦理与文化的背景和基础。通考《西汉诏令》,我们发现“孝”或“孝治”作为政治伦理理念在诏令中有比较集中而又普遍的体现。
二、“孝”思想在诏令中的体现
在儒家所描绘的“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的伦理理念与美好蓝图的吸引下,西汉初期的诸位皇帝也多是“以孝治天下”而自居。如前所述,无论是刘邦所颁的《尊太上皇诏》,还是其他诸位皇帝的谥号加“孝”,足见他们对儒家“孝”伦理思想的认同与推崇。对于“孝”或“孝治”作为政治伦理理念在诏令中的体现,我们可以从诏令“孝悌”、诏令“尊老”与诏令“废刑”三个维度略加缕叙。
1.诏令“孝悌”。尽管西汉初期迫于经济与政治的压力,中央政府大力推行黄老无为之策,但是儒家政治哲学尤其是伦理道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较强的适应性与生命力。自从刘邦在《尊太上皇诏》中为汉家确立“孝治”政治伦理理念后,西汉诸位皇帝在诏令中对“孝治”亦多有体现,今据《西汉诏令》兼参《史记》与《汉书》,摘要兹录如下。
例如,汉文帝十二年(前168)的《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云:“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 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7]124又如,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四月颁《复高年子孙诏》,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3]994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颁《诏议不举孝廉者罪》,诏曰:“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3]998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四月颁《遣谒者巡行天下诏》,诏曰:“朕闻咎繇对禹,曰在知人,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盖君者心也,民犹支体,支体伤则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流货赂,两国接壤,怵于邪说,而造篡弑,此朕之不德。《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已赦天下,涤除与之更始。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3]1000-1001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五月颁《诏策贤良》,诏曰:“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3]996另说,此诏颁发时间为建元元年五月,姑且存疑。由上观之,“孝悌”一词在汉武帝的诏令中频繁出现,这或许与儒家伦理思想经过公孙弘、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后,业已成为汉武帝治理国家的重要思想有关。其中,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7]726可谓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正式被汉朝官方确立的重要标志。
时至汉宣帝、汉元帝时期,随着儒学在政治中的扩散,儒学逐渐占据了政治与文化的主流地位,因此“孝悌”思想在诏令中出现的频次有增无减。例如,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颁《举孝弟等诏》,诏云:“……《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於乡里者各一人。”[7]260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三月颁《凤皇甘露诏》,诏曰:“…… 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3]1018汉宣帝元康三年三月颁《神爵集宫苑等诏》,诏曰:“……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屡获嘉祥,非朕之任。其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鳏寡孤独各一匹。”[3]1020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春二月颁《吏有丧勿繇事诏》云:“导民以孝,则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绖凶灾,而吏繇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3]1017又如,汉元帝永光二年(前142)春二月颁《赦天下诏》,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晻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3]1030-1031汉元帝颁《敕谕东平王宇玺书》(此诏具体颁布时间不可考,疑为初元至永光年间),诏曰:“盖闻亲亲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义莫大于忠,故诸侯在位不骄以致孝道,制节谨度以翼天子,然后富贵不离于身,而社稷可保。今闻王自修有阙,本朝不和,流言纷纷,谤自内兴,朕甚憯焉,为王惧之。诗不云乎?‘毋念尔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褔。’朕惟王之春秋方刚,忽于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纳,故临遣太中大夫子蟜谕王朕意。孔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王其深惟孰思之,无违朕意。”[3]1034-1035
时至西汉晚期,随着儒术地位在政治中的巩固,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业已渗透至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具言之,儒家宣扬的孝悌仁义甚至成为诸侯大臣获得分封或去职削爵的重要标准,这一点在汉成帝、汉哀帝与汉平帝的诏令中多有体现。例如,汉成帝建始年间颁《复东平王削县诏》,诏曰:“盖闻仁以亲亲,古之道也。前东平王有阙,有司请废,朕不忍。又请削,朕不敢专。惟王之至亲,未尝忘于心。今闻王改行自新,尊修经术,亲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传不云乎?朝过夕改,君子与之。其复前所削县如故。”[3]1037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六月颁《封楚王嚣子诏》,诏曰:“盖闻‘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楚王嚣素行孝顺仁慈,之国以来二十馀年,孅介之过未尝闻,朕甚嘉之。”[3]1039汉成帝永始二年颁《册免薛宣》,诏曰:“君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无闻焉。……罢归。”[3]1043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二月颁《立皇太子诏》,诏曰:“…… 定陶王欣于朕为子,慈仁孝顺,可以承天序,继祭祀。其立欣为皇太子。……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3]1045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颁《策免何武》,诏曰:“君举错烦苛,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无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印绶,罢归就国。”[3]1048由上可见,“孝”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为人与出仕的重要条件,换言之,孝或不孝既可成为一个人获得仕途机会的基本条件,亦可成为一个人失去仕途机会的借口。同时,“孝”也成为立太子的道德标准。又如,汉平帝元始年间颁《授四辅等诏》,诏曰:“太傅博山侯光宿卫四世,世为傅相,忠孝仁笃,行义显著,建议定策,益封万户,以光为太师,与四辅之政。车骑将军安阳侯舜积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冲万里,功德茂著,益封万户,以舜为太保。左将军光禄勋丰宿卫三世,忠信仁笃,使迎中山王……”[3]1067此外,汉平帝的《九锡策》也曾论及孝,策云:“诗之灵台,书之作雒,镐京之制,商邑之度,于今复兴。昭章先帝之元功,明著祖宗之令德,推显严父配天之义,修立郊禘宗祀之礼,以光大孝。是以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渐化端冕,奉珍助祭。”[3]1060由此观之,即便王莽有不臣之心,其仍然需要从道德层面赢得大家的认可,尤其是皇帝及朝廷的褒奖。在此,我们甚至可以说道德业已成为通往政治及权力之巅的铺路石,“道德”的本质甚至被政治与权力所“异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西汉中央政府对儒家“孝悌”伦理思想的认同与推崇。
2.诏令“尊老”。 西汉诏令的尊老与崇孝互为表里,“尊老”作为政治伦理理念从家庭到社会、政治甚至到外交,层层扩散,贯穿西汉。汉初,汉高祖颁《谕诸县乡邑》“除去秦法”[6]362,又颁《赦天下》以示“尊老”。时至文景,汉文帝元年(前179)三月颁发的《养老诏》云:“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7]113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颁《颂系老幼等诏》,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7]1106汉景帝元年(前156)冬十月,颁《文帝庙乐舞》,诏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胜识。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亲行之。”[7]137凡引可见,诏令"尊老"映现出西汉前期政治哲学中的儒学底色,以及政治权力儒家化的倾向。
时至宣元,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春正月颁《遣太中大人循行天下诏》,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暴逆之心,今或罗于文法,执于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3]1020汉宣帝神爵五凤年间(神雀四年夏五月)颁《裒黄霸诏》,诏曰:“颖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乡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3]1023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正月颁《改元神爵诏》,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厥理。……东济大河,天气清静,神鱼舞河。幸万岁宫,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惧不能任。其以五年为神爵元年。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3]1020-1021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四月颁《遣光禄大夫循行天下诏》,诏曰:“朕承先帝之圣绪,获奉宗庙,战战兢兢。间者地数动而未静,惧于天地之戒,不知所繇。方田作时,朕忧蒸庶之失业,临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困乏失职之民,延登贤俊,招显侧陋,因览风俗之化。相守二千石诚能正躬劳力,宣明教化,以亲万姓,则六合之内和亲,庶几宓无忧矣。”[3]1026同时,汉元帝又颁《诏关东今年毋出租赋等》,诏曰:“关东今年谷不登,民多困乏。其令郡国被灾害甚者毋出租赋。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赐宗室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3]1026汉元帝初元五年(前44)四月颁《罢角抵宫馆等诏》,诏曰:“……博士弟子毋置员,以广学者。赐宗室子有属籍者马一匹至二驷,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鳏寡孤独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3]1029汉元帝建昭四年(前35)四月颁《遣谏大夫博士诏》,诏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栗栗,惧不克任。间者阴阳不调,五行失序,百姓饥馑。惟烝庶之失业,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问耆老鳏寡孤独乏困失职之人,举茂材特立之士。相将九卿,其帅意毋怠,使朕获观教化之流焉。”[3]1033此外,汉宣帝与汉元帝多次颁《赦天下诏》,汉成帝河平年间颁《减死刑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正月颁《诏举孝弟等》,汉平帝元始四年正月颁《诏勿击老弱》等诏令亦多反映西汉后期官方对“孝”的重视与“尊老”程度。其中,汉平帝的《诏勿击老弱》颇具代表性,诏曰:“盖夫妇正则父子亲,人伦定矣。前诏有司复贞妇,归女徒,诚欲以防邪辟,全贞信。及眊悼之人刑罚所不加,圣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系犯法者亲属,妇女老弱,构怨伤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它皆无得系。”[3]1057综上可见,西汉自汉高祖至汉平帝无一例外地皆强调“尊老”,重视弱势群体,因此他们的诏令不仅言语恳切,而且亦彰显一种政治关怀与人伦精神。换言之,从西汉诏令来看,“养老”是以最高命令与法律形式确立的,既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又具有道德的约束力。从诏令强调的重点来看,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要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高年群体进行帮扶与赡养,而且要在政治上对高年群体予以应有的尊崇即赋予高年老人一定的政治特权——“无侮鳏寡,惠此茕独”。凡此可见,诏令尊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优抚老人,其旨在建立一个政治伦理制度或以政治意志为主导的养老制度。
3.诏令“废刑”。 如果说西汉诏令中的崇孝与尊老是互为表里的,那么崇孝在另一个层面的体现则相对较隐蔽——诏令“废刑”。愚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崇孝”在诏令“废刑”中是有所体现的,而且贯穿于整个西汉王朝。史载,汉高祖元年(前206)十月,颁《谕诸县乡邑》,诏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6]362汉高祖六年(前201)十二月颁《赦天下》,诏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7]99尽管“刘项原来不读书”,且曾“戏儒简学”, 凡此亦足见其对儒家孝悌仁义思想的接受与应用。
时至文景,淳于缇萦因代父受刑而书奏汉文帝,文帝怜悲其意,于汉文帝十三年(前167)颁《除肉刑诏》,诏云:“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7]1098此外,汉文帝二年五月颁发的《除诽谤法诏》废除了诽谤罪,汉文帝二年(前178)颁发的《诏议犯法者收坐》废除了连坐罪,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夏颁发的《除秘祝诏》废除了因灾异而刑于百姓的做法。又,汉景帝元年颁《减笞诏》,诏云:“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7]1100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又颁《减笞诏》,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7]1100凡引可见,西汉文帝、景帝之仁厚以及其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认肯与推崇。
时至武帝,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三月,颁《赦汾阴等诏》,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7]195汉武帝元朔元年三月的《赦天下诏》,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7]169
时至宣元,汉宣帝元康二年(前164)五月颁《察吏诏令》,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繇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3]1019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颁《议律令诏》,诏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3]1026此外,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十二月颁《置廷平诏》,汉宣帝地节四年五月颁《子首匿父母等罪勿坐诏》,汉宣帝与汉元帝多次颁《赦天下诏》,汉成帝河平年间颁《减死刑诏》等诏令亦反映出西汉中央政府对“法”、“刑”与“罚”的弱化。
综上,我们认为,西汉时期的“崇孝”在诏令中的反映是多层面的,贯穿于整个西汉时期。换言之,从西汉之史来看,“孝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贯穿于整个西汉王朝,同时也是一个由亲情伦理向政治伦理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对政治伦常起到了规范作用,而且还影响了西汉政治哲学的走向及其伦理价值的取向。同时,“孝”作为政治伦理理念反过来又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家庭的伦理关系。这一点在诏令尊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诏令尊老使得“孝”本身的规约力被拓展,从而具备了法律的强制力。
三、诏令“崇孝”的价值向度
纵观《西汉诏令》,涉“孝”之诏令凡计约百,足见西汉王朝对“孝”的推崇。当然,“孝”在《西汉诏令》中的价值向度也是多维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向度略加诠释。
1.诏令“崇孝”的政治价值。对于诏令“崇孝”的政治价值,我们则可从以“孝”治国、以“孝”选才与以“孝”外交三个层面略加剖析。
(1)以“孝”治国。如前所论,自从刘邦颁《尊太上皇诏》确立了以“孝”治国的政治伦理理念后,继任者无不“崇孝”。正是在西汉诸位皇帝的推动下,“孝”作为政治伦理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散,逐渐渗透至社会、政治与文化等诸多领域。因此,我们认为西汉时期可以说是“孝”思想占据政治主流位置的历史时期。这种现象反映出“孝”作为人之至情既适用于治家,在家国同构的政治间架下也适用于治国;同时也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中政治与伦理的内在相通性,即政治统治并非完全排斥伦理与道德。因此,当源于家庭领域的“孝”进入政治后,它必然会彰显出自身的伦理温情与人文关怀。简言之,诏令“崇孝”的政治价值就在于此。
(2)以“孝”选才。如前所论,“孝”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皇帝选拔人才、分封或废黜诸侯大臣的重要依据。西汉王朝不仅开创了“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而且以诏令的形式诏告天下不举孝廉、不劝孝廉者有罪,例如汉武帝曾颁《诏议不举孝廉者罪》。从历史的维度看,以“孝”选才在汉成帝、汉哀帝与汉平帝的诏令中多有体现。例如汉成帝建始年间颁《复东平王削县诏》,汉成帝河平四年(前25)六月颁《封楚王嚣子诏》,汉成帝永始二年(前15)颁《册免薛宣》,汉成帝绥和元年二月颁《立皇太子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16)颁《策免何武》,汉平帝元始年间颁《授四辅等诏》,汉平帝颁《九锡策》等等。由上可见,“孝”不仅成为一个人出仕的重要条件,而且成为一个人擢升或罢黜的凭据。从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二月颁《立皇太子诏》中,我们发现,“孝”甚至成为立太子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成为评价皇帝的重要标准。例如汉哀帝建平三年(前4)十一月颁《令太皇太后诏有司》,诏曰:“皇帝宽仁孝顺”[3]1061。也就是说,“孝”作为伦理规范不仅对普通百姓有约束力,而且对太子与皇帝也有一定的约束力。凡此,我们不难想到,西汉官方对“孝”的重视程度,儒家伦理思想在西汉政治中的影响力。
(3)以“孝”外交。在此,我们讲以“孝”外交主要是指西汉诏令中凡涉外交的诏令体现了“孝”思想。这一点,在汉文帝时期的《遗匈奴书》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例如,汉文帝前六年(前174)的《遗匈奴书》曰:“…… 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6]2897又如,汉文帝后二年(前162),《遗匈奴书》曰:“…… 圣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6]2902-2903由是观之,内涵几乎完全相同的尊老与崇孝思想已经从家庭领域扩散到政治领域,再经由政治领域扩散至外交领域。汉文帝提出的“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与“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的外交主张可以说就是“孝”思想的一种具体化。换言之,汉文帝试图以“崇孝”与“尊老”的政治伦理理念去影响或改变“匈奴俗贱老”[6]2899的陋俗;同时以期基此去改善多年以来的时战时和的汉匈关系。
2.诏令“崇孝”的伦理价值。在农耕文化与宗法社会中,“孝”作为基本的伦理范畴无论是维系家庭伦常关系还是维系社会伦常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诏令崇“孝”的伦理价值还体现在政府的政令化、制度化养老,即诏令崇“孝”不仅有助于养老制度的形成,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政治伦理氛围。同时,“孝”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还体现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一种人文关怀与终极关怀。(1)彰显人伦关怀。如前所论,诏令“孝悌”、诏令“尊老”与诏令“废刑”皆从不同层面彰显西汉诏令崇“孝”的伦理价值与人伦关怀。从儒学学统看,先秦儒家对“孝”所蕴含的人伦关怀曾有论述。例如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孝经·孝治》)等等。也就是说,“孝”作为个体本能地改善与祖宗、父母之人伦关系的伦理规范有其不同的理论指向。比如说,在事亲与事亡方面,“孝”则主要体现在敬亲、哀戚、守丧等层面,凡此在西汉诏令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汉哀帝建平二年(前5)六月颁《葬丁太后诏》,诏曰:“…… 孝子事亡如事存。”[3]1049(2)改善人际关系。诏令“崇孝”的伦理价值还体现在改善人际关系中,“孝”作为衡量人之为人的伦理规范与道德标准,它具有明确的指向——“我”。也就是说,“孝”作为一种始于情、发于行的道德律令,它具有“自律”的性质。具而言之,“孝”之于改善人际关系主要有三个基本层面:一是家庭内部的长幼人伦关系;二是社会层面的人我关系;三是政治层面的君臣关系。凡此,在刘邦的《尊太上皇诏》中均有体现。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够做到“孝”,那么那个社会必然会是风气纯朴、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反之,当一个社会反复提倡“孝”时,则意味着那个社会可能出现了道德难题。因此,西汉王朝在诏令中反复提到“孝”,一则反映后继者对汉初以“孝”治国理念的继承,二则反映他们自身对“孝”的认肯与推崇,三则反映出“孝”之于理顺政治秩序与化解社会道德难题的重要性。
3.诏令“崇孝”的文化价值。在此,我们可从两个基本层面来讨论诏令崇“孝”的文化价值:
(1)树立道德典范。上行下效,君为民师。当基于血亲关系的“孝”被统治者放大后,无论是出于血缘亲情与人之本性,还是出于效法人君与迎合政治,老百姓对“孝”伦理思想均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与推崇。从发生在西汉文帝时期的“淳于缇萦代父刑罪”(见《史记·孝文本纪》)一事中可见“孝”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淳于缇萦”甚至被视为“孝子”的典型。史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6]2796。淳于缇萦的“求赎父刑”不仅得到了汉文帝的认可与表彰,而且还促成汉文帝颁发了《除肉刑诏》。如前所言,汉文帝本人也以“孝”著称,对此袁盎赞曰:“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6]2739据说,汉文帝为母尝药尽孝之事,“当时天下咸祢颂帝之仁孝”。凡此,不难发现道德典范的影响力,以及“孝”思想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2)净化社会风气。如上所言,“孝”具有改善人我关系与君臣关系的功能与价值。因此,当“孝”作为政治伦理理念被官方所弘扬时,它必然会对社会风气起到净化之作用,并且通过自身特性的彰显向社会释放出正能量与正价值。“孝”以其至情使人我关系、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回归到真情本身,回归到没有功利目的的伦常关系中。可以说,正是因为“孝”之情的质朴与至真,社会风气在其影响下才可能得以净化并归于淳朴与和谐。换言之,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人都讲“孝”、行“孝”,那么这个社会必然会是风气淳正的社会,人我关系、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也必然会是和谐而有序的。
总的来看,诏令“崇孝”的价值体现是多维度的、多层次的。也就是说,“孝”不仅仅是一种家庭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也是维系君主专制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手段和道德价值导向。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孝”治家与以“孝”治国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向度上是相通的,因为“孝”的伦理精神实际上统驭着“三纲”中的“二纲”,即“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
四、小 结
综上所论,从“孝”在《西汉诏令》中的多维度体现来看,“孝”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理念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理论边界即由家庭领域进入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同时也突破了学术派别与政治派别的纷争以及时间的界限。换言之,“孝”伦理思想的突显不仅为西汉政治注入了新思想与新理念,而且为儒学在西汉政治中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从“孝”的“呈显”与“发用”来看,“孝”之于政治似乎存在一个向人伦至情回归的逻辑向度与价值向度,即“孝”本源于子女与父母的血亲至情,尽管它一度越过了原有的边界进入社会与政治领域,但是其作用与价值的彰显则又使诸种关系的处理回到“至情”本身。也就是说,“孝”始于“情”,发用于“事”并在发用于“事”时回归到“情”本身。其实,“孝”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人伦规范与伦理精神,从历史的维度看,它具有贯穿人类发展史始终的永恒性、超越性与客观性;从个体生命的历程看,它又具一种贯穿个体生命始终的天然性、主导性与规范性。从“孝”至“孝治”,尽管其有不同的伦理范式与价值向度,但是其自身所彰显的伦理精神却不会为政治、时代与文化所局限或消解,它必将以其自身特有的伦理关怀与价值向度伴随人类社会与个体生命之始终。
纵观西汉诏令,我们发现:“孝”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贯穿于整个西汉王朝,并逐渐成为西汉王朝的重要伦理范式,同时也彰显出其自身的伦理价值。也就是说,“孝”作为一种政治伦理理念在西汉政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它所彰显的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关怀与人道精神,同时也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人伦至情与终极性的伦理情怀。
[1] 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林虙.两汉诏令[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971-1061.
[4] 陆贾,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25-30.
[5] 贾谊,阎振益校注.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3.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责任编辑:祝春娥)
2014-12-16
王传林(1978- ),男,安徽阜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B82-052
A
2095-4824(2015)02-0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