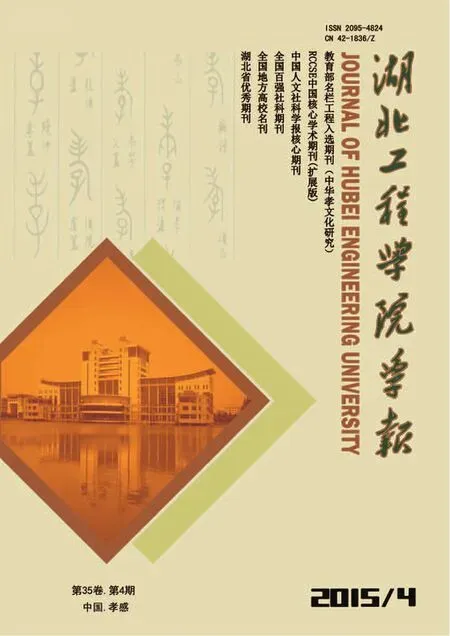炫技、交游与唱和
——清词中兴成因新探
祝 东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炫技、交游与唱和
——清词中兴成因新探
祝 东
(兰州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关于清词中兴问题,学界前辈时贤多认为其与明清易代的政局相关,特别是与当时勃兴的文字狱关系密切。然而,考察清代文字狱研究史料可知其并未达到如此夸张残酷的地步,不足以直接引发词体文学之复兴。清词中兴应与文人间互相比拼才情、夸饰技艺的风尚有关。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清代,传统诗歌平仄格律已不能满足文人士子的需要,而格律音韵相对复杂的词则更能显示文人们的才情。由此,清人对词体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学圈内的交流酬唱则直接促成了清代词体文学的复兴。
清代词学;文人兴趣;文学场;清词中兴
词体文学发轫于唐季五代,兴盛于两宋,元明相对衰微,复振于有清,已成学界共识。昔日王观堂论文学一代有一代之盛,那么一度衰微的词体文学为何会复兴于清代?学界前辈时贤多从社会历史关系入手,认为清词中兴是“文祸”促使下以词写心的避难策略。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完全以社会历史决定论来探究文体兴衰,而相对忽略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群体,则未免有失偏颇。本文试从文人唱和与文学场之关系来探讨清词中兴的具体成因。
一、“文祸”中兴成因说与清代文祸实况
传统清词中兴成因的观点,一般将其与明清易代的特殊政治背景联系起来思考,在方法论上即是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联系明清之际的政治文化背景来考察,特别是文字狱事件对清人心态的影响。民国时期的王易是较早将文禁时局与清词中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学者,他认为易代之后,文人之所以选择以填词的方式吟风弄月,目的在于避祸,即避免文字狱的迫害[1]274,开清代词学复兴探究之风,此后学者们在探讨清词复兴的原因时大抵都采纳这一基本观点。如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论及清词中兴成因时联系清初文字狱对士人心灵的震撼和控制作用,指出:“从来被人们视为‘小道末技’的词却正好在清廷统治集团尚未关注之际应运而起,雕红琢翠,软柔温馨的习传观念恰恰成为一种掩体,词在清被广泛地充分地作为吟写心声的抒情诗之一体日趋繁荣了。”[2]孙克强先生在《清代词学》中亦曾指出,清代文字狱重点关注打击的对象是诗人,“而无一例为词”[3],因为自古就有“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故文人士子喜弄笔填词,抒情释怀,由是造成了清词的中兴之盛。这种观点经过学者们的不断揄扬,逐渐成为通论,学界在论及清词中兴成因时大都会从此论点出发,进行延展。
既然学界皆将词学中兴与清初政治特别是文字狱联系在一起,那么很有必要检视一下清代文字狱的具体状况。据胡奇光《中国文祸史》一书统计,清代顺治朝18年文字狱至少有5起,康熙朝61年大约11起,雍正朝13年大约25起,而乾隆朝60年大约有135起,总而言之,顺康两朝文字狱实宽,而雍乾两朝则趋严。[4]185-186但清代词体文学在顺康两朝就已经形成中兴之势了,而雍乾两朝词体文学实际上是相对衰落,因此雍乾两朝文祸不能作为词体文学复兴端绪之因由。再来看顺康两朝的文字狱情况,其打压的主要对象是在意识形态上公开唱反调或者在政治态度上公开不合作的士人,如黄毓祺案、庄廷龙《明史》案皆是如此。此外还有部分文祸实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文人文字罹祸乃牵连所致。如僧函可的《变纪》书稿案即为巴山与洪承畴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张缙彦诗序案则是清初汉族官僚集团之间党派斗争酿成的悲剧。真正因诗文罹祸的文字狱案件并不多,“康熙朝仅有何之杰、陈鹏年两人因诗得祸,也均从宽发落”。[4]140可见单纯写诗作文并不一定就会遭受文字横祸,清初统治者也绝非昏庸糊涂之辈,况无故乱起文字狱遭致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感,于满族王权统治也无益。胡奇光先生指出:“顺康雍三朝文字狱打击的主要对象是官绅、名士,即‘钦定’的政治上反对势力及思想上有反满倾向的士大夫。”[4]87这个结论发人深省。清代有文字狱是实,但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不服从满清统治的文人士大夫,特别是江南士子,因为“这些地方是人文渊薮,舆论的发纵指示所在,反满精神到处横溢”。[5]遭受文祸者多是因为政治上公开反满,而对于政治上已经迎合清朝,即便此前有过反清复明举动者,也是既往不咎,如陈维崧、朱彝尊诸人,在易代之际或明或暗从事过反清活动,但后来皆入博学鸿词科,可谓政治上“投诚”了,他们诗文中的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虽多处可见,却并未因此遭受打压,因此文人士子写诗作文动辄罹祸的观点有待商榷,“文祸”并非词体文学复兴的直接原因。
同样,认为词体文学是小道末技,并未引起清初统治者的注意也不太恰切。康熙朝词体文学两次破天荒地立了“国家级重点课题”,即《历代诗馀》和《钦定词谱》,此二书从立项到完成,皆受到康熙帝的关注与重视,并且亲自御制序文进行阐发:
朕万机清暇,博综典籍,于经史诸书有关政教而裨益身心者,良已纂辑无遗。……宋金元明四代诗选,更以词者继响夫诗者也。乃命词臣辑其风华典丽,悉归于正者,为若干卷,而朕亲裁定焉。……苟读其词,而引申之,触类之,范其轶志,砥厥贞心,则是编之含英咀华,敲金戛玉者,何在不可以“思无邪”之一言该之也![6]
从序言中可以看出玄烨早已将词与诗比肩,纳入诗教传统中了。此亦足以证明满清统治者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词体文学亦在清代文网之内,如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中就有清初词学选本《瑶华集》(这部词选因以词存史,多及易代时事,内容上有违碍,故遭禁行) 。[7]因此词并非如前辈学者所言,因是小道末技不被重视。只要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犯禁,不管诗词,俱会遭禁受罚。
因此,总体而言,清初文祸并非胡乱打压汉族士子,而有其针对性,清初文祸也不单是诗文罹祸,而与政治斗争、朋党倾轧关系密切,文人往往充当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既然文祸高压并不是清词复兴的端绪,清词缘何复兴?笔者认为可以从清代文人生态环境进行考察,特别是文人兴趣嗜好的转移入手进行观照。
二、夸饰才情与词体复苏
在以往文学研究中,人们过于重视社会历史对人的影响,忽视了创作主体的个性特征。在同一社会条件下,作家选择这一文体而非另一文体,不仅与历史现实相关,而且与作家的才情、兴趣、爱好及师友交游酬唱等文人生态环境有关。
清代文化经数朝之积累,已成造极之势,文人士子多饱学,杜甫所云“读书破万卷”的事情于清人来说已经很平常了。为了超越前人,甚至出现了“竹垞以经解为韵语,赵瓯北以史论为韵语,翁覃溪以考据金石为韵语。虽各逞所长,要以古人无体不备,不得不另辟町畦耳”[8]的文坛景观。文人在一起交游唱和时喜欢夸饰才情文笔。如王晫《今世说·赏鉴》中记载浙江的鉴湖社,参与者把诗文糊名誊抄,然后进行评比,“一联被赏,门士胪传,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赉”[9]58。此足见文人之间争奇斗艳的风尚。况且清代词人亦多兼为学人,故能摒弃明词空疏淫艳之习,学人弄笔填词者亦盖过两宋。这个现象晚清词学家谭献、今人钱仲联亦多有关注:“清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雄者,多为学人……盖清贤惩明人空疏不学之敝,昌明实学,迈越唐宋。诗学家称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词学家亦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合。而天水词林则不尔,周、程、张、陆不为词,朱熹仅存十三首,叶适一首而已。以视清词苑之学人云集者,庸非曹郐之望大国楚乎?”[10]清代词人的双重身份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传统诗歌格律对他们来说已不足以显示才情学问,于是需要有新的文体来夸耀才情炫示学问,“词有定格,字有定数,韵有定声”,其繁琐的规则难以把握,相对于格律诗来说,词体文学是一种形式更为考究、限制更为严格的文学样式,如谢元淮言:“词之为体,上不可入诗,下不可入曲。要於诗与曲之间,自成一境。守定词场疆界,方称本色当行。至其宫调、格律、平仄、阴阳,尤当逐一讲求,以期完美。”[11]其规矩讲究比诗歌和曲子严格得多,于是自然成为一种能够夸耀才情的文体,由此在明人不遗余力的诗歌复古革新运动失败之后,清人重新“发现”了词体文学。此可在李渔的《耐歌词自序》中得到印证:
三十年以前,读书力学之士,皆殚心制举业,作诗赋古文词者,每州郡不过一二家,多则数人而止已;余尽埋头八股,为干禄计。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此后则诗教大行,家诵三唐,人工四始,凡士有不能诗者,辄为通才所鄙。是帖括时文之世界,变而为诗赋古文之世界矣。然究竟登高作赋者少,即按谱填词者亦未数见,大率皆诗人耳。乃今十年以来,因诗人太繁,不觉其贵,好胜之家,又不重诗而重诗之馀矣。一唱百和,未几成风。无论一切诗人皆变词客,即闺人稚子,估客村农,凡能读数卷书、识里巷歌谣之体者,尽解作长短句。[12]
序文写作时间为康熙戊午中秋前十日,即康熙十七年(1678),往前推三十年则是明末清初之际,明代文人以攻举子业为尚,易代之后,政局混乱,故明举业告退,士子转而为诗,但诗太简单,不足以展示才情,作诗“为通才所鄙”,文人为了争奇斗胜,转而填词,词填得好,亦可给作者带来巨大的声望。如王士禛《蝶恋花·和漱玉词》中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的句子,“长安以此遂有‘王桐花’之目”[9]49,影响之大可以想见。由是改变了文坛风尚,诗人皆变词客,而文坛风向一旦改变,则会引起文人们的群起效仿,此或可谓之“蝴蝶效应”。如顾贞观《与陈栩园书》中所言:“而余因窃叹天下无一事不与时为盛衰,试即以词言之,自国初辇毂诸公,尊前酒边,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托,久则务为谐畅。香岩、倦圃,领袖一时。唯时戴笠故交,提簦才子。并与燕游之席,各传酬和之篇。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竟起,选者作者,妍媸杂陈。”[13]975由于有才学之士以词写心,改变了以诗言志的套路,使得一直萎靡不振的词坛得到了一个发展的契机,于是习词填词者渐多,最后到了“吴越操觚家闻风竟起”的地步,填词蔚为风气。有文人甚至受到当时词坛风气影响由攻诗转为专力为词,据蒋景祁《陈检讨词钞序》记载:
其年先生幼工诗歌,目济南王阮亭先生官扬州,倡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麓、曹秋岳诸先生主持之,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迨倦游广陵归,遂弃诗弗作。[14]卷二
陈维崧为清代词坛大家,填词两千余首[15]98,当之无愧的词坛第一作手,但他起初是主攻诗歌的,少时还师事陈子龙、昝质名流学诗,至顺治七年(1650)才始学填词,据其《任植斋词序》中所云:“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籍旗亭北里间。其在吾邑中相与为倡和者,则植斋及余耳。”[15]53后来游历广陵,结识王士禛等人之后,受其影响才专力填词。正是由于当时文坛风尚的转变及与师友酬唱交流的影响,才成就了陈维崧这位词坛巨擘,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文人生态问题,即是文人之间交流唱和对词体复兴的影响。
三、交游酬唱和与跻身“圈内”
明清易代,面对神州陆沉,有皈依新朝者,有反清复明者,有持观望态度者,有甘作遗民隐士者,不一而足。易代致使诸多士子或失业,或失去生活来源。赋闲的困顿使文人士子不得不游走于仕宦之间,旅食他乡,游幕成为当时文人生活的一道风景线。如尚小明言:“众多才华横溢却屡踬场屋、难入仕途的贫寒士人,为求得一谋生之路和读书治学的环境,亦纷纷投至各级官员幕下。士人游幕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对清代学术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16]为维持生计,很多文人不得不放下身段,游身乞食,或依傍名流大佬,靠他们的接济维生,如清初词坛大家朱彝尊就一度靠游幕维持生计,陈维崧依靠冒襄度日竟长达8年之久,京华落魄文人被龚鼎孳接济的更是不可胜数。
由于文人交游频繁,逐渐形成文人圈子,文人要想进入圈子,需要一定的条件,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观点来说,圈子即场域,进场必须携带一定的资本作为“入场券”才行,由此我们引进了布迪厄所云的“场(field)”的观念:“从场的角度思考就是从关系的角度思考。”[17]一般来说,一个文学圈子里的主盟人物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能给文人雅集提供足够的空间和物质,而要进入这个场域的文人,必须携带相应的文化资本。并且,“场域中的权力、资本的分配结构,决定着位置与位置之间的关系,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或结构上的对应关系”。[18]文人要进入圈子,依附于拥有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来谋求生活资源,在场域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为了保持其在场域内的位置,他们必须积极贡献自己的文化资本,比如场域中处支配地位的人物有词作的话,那么被支配者必须竭力唱和,以保证其在场内应有的地位,否则可能会“出圈”。故而我们会在清初词坛上看到诸多大型唱和的文学景观。如康熙元年(1662)王士禛主持的虹桥唱和,就曾经是清初词坛上的一次盛举。据王士禛《红桥游记》所言:“壬寅季夏之望,与箨庵、茶村、伯玑诸子,偶然漾舟,酒阑兴极,援笔成小词二章,诸子倚而和之。箨庵继成一章,予亦属和。”[19]另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当时参与唱和的文人有杜濬、陈允衡、丘象随、陈维崧等十人,时王氏为扬州推官,雅好诗文,“总持风雅”,“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他自己率先作了三阕《浣溪沙》为“虹桥唱和集”[20],王士禛在扬州任上,主盟文坛,对词坛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纳兰容若在京师主持的词坛,亦吸引了众多旅食者,“吾友容若,其门地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13]975,容若以其贵戚身份,雄厚财力,足以能够承担穷途文人们所需的生活补助,故而流寓京师的文人多趋之,“海内名为词者皆归之”[21]如严绳孙、顾贞观、陈维崧等多曾从其游,主客唱和,彬彬称盛。
此外,康熙四年(1665)曹尔堪、王士禄、宋琬等人的江村唱和,康熙五年(1666)曹尔堪、王士禄主持的广陵唱和,康熙十年(1671)曹尔堪、龚翔年等人在京师的秋水轩唱和,皆是一唱百应,蔚为风气,参与唱和的成员大抵皆是能够跻身“圈内”的人物。康熙十二年(1673)陈维崧在家乡宜兴与蒋景祁、徐喈凤等16人修禊东溪,参与者皆有词作唱和。而释大汕在康熙十七年(1678)为作《其年填词图》后为陈维崧携至京师,在京名士梁清标、王士禛、彭孙遹、朱彝尊、毛奇龄等三十余人多有题咏,蔚为风气,堪称壮观,据马祖熙先生《陈维崧年谱》所考:“《迦陵填词图》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朝,历一百五十年,续有题咏”[22],足见这种唱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世亦引起广泛关注与参与,可谓流风余韵,不绝于缕。陈维崧不仅为此获得了巨大的荣誉,而且此等盛况也应极大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这件雅事在词坛引起的震动与追慕亦不容小觑。而庄澹庵评康熙十九年(1680)所刻王晫《峡流词》中《满江红》词时云:“此调和者如云,几累千百。”[23]卷下这首词是追和江村唱和《满江红》而作,江村唱和在士人圈子中的影响自不必云。
可以这么说,清词的中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人之间的交游唱和引起的群体效应。而唱和又容易刺激文人之间争奇斗胜的创作欲望,促进词体文学的繁荣。清初浙西阳羡词体巨擘朱彝尊、陈维崧莫不如此。这样他们在交游或游幕中,既多了闲暇的时间从事创作切磋,又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文人圈子,如以王士禛为中心的广陵词人群体,以曹尔堪为中心的柳州词人群体,以纳兰性德为中心的京华词人群体等。文人在一起可以喝酒写诗作文,是为诗酒风流,同时可以夸耀才情。文人进入“词学场”内,不仅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资源,还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名声与影响,名利双收,而由此带来的文学景观则是词体文学的复苏。
四、小结
清词中兴固然与明清易代下的文字狱有一定的关系,但清初文字狱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荒唐,它的打击对象是有针对性的,对词学复兴并未起到关键性作用。清代词体文学的兴盛与清人的兴趣爱好及生活境况有关。文人之间的交游唱和及夸耀才情的需要,使得他们不自觉选择了在格律音韵上更难把握的词体文学,因为此时词体文学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长短不葺的新体格律诗。但这种文体的文类等级地位不高,故而清代词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扬词体。清代词学中不断出现的辨体与尊体工作,与文人的兴趣转移相关,正如江晓原所言:“文人们从来不缺乏为自己的兴趣寻找正大理由的动力,能找到的理由还总能与时俱进。”[24]
一种文体的兴衰,并不是个别作家能够左右的,它必定会受到群体力量的影响,文人之间的交游酬唱,以及夸饰才情、谋食糊口等,都会对文体的兴衰产生具体的影响。研究文学史,不能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应该把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的过程之中,以生活在历史之中的作家活生生的物质、精神需求等来作为考察依据,由此来研讨一定的文学现象,丰富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于诗文词曲皆如是。
[1] 王易.词曲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274.
[2] 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9.
[3] 孙克强.清代词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9.
[4] 胡奇光.中国文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16.
[6] 康熙.历代诗馀序[M]//沈辰垣,等.历代诗馀.上海:上海书店,1985:3-4.
[7] 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59,74.
[8] 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一[M].光绪八年刊本.出版者不详,光绪八年(1882).
[9] 王晫.今世说[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
[10] 钱仲联.全清词序[M]//程千帆.全清词:顺康卷.北京:中华书局,2002:2.
[11] 谢元淮.填词浅说[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2509.
[12] 李渔.李渔全集·册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377.
[13] 顾贞观.与陈栩园书[M]//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 陈乃乾.清名家词[M].上海:上海书店,1982.
[15] 陈维崧.陈维崧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6]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1.
[17] 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41.
[18] 张意.文化与权力符号: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73.
[19] 王士禛.渔洋山人自撰年谱[M]//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8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207.
[20] 李斗.扬州画舫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220-221.
[21] 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6.
[22] 马祖熙.陈维崧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14.
[23] 王晫.峡流词[M].刻本.霞举堂,康熙十九年(1680)
[24] 江晓原.从《诗》三百到《夹竹桃》:艳情诗之中国篇[J].万象,2008(1).
(责任编辑:李天喜)
Showing off, Making Friends and Chiming in with Others:A New Study on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Zhu Dong
(SchoolofInternationalCulturalExchang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China)
About the issue of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Qing dynasty,most academia seniors thought it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especiall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riting prison. However, by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writing prison in the Qing dynasty, it was found to be not so exaggerating or cruel. Hence it might not directly lead to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Instead,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might be brought on by the fashion of literati competition with each other and exaggerating accomplishment. When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developed up to the Qing dynasty, pingze and rhythm couldn’ 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iterati, but Ci poetry's metrical phonology wa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could more commendably display the literati’ s artistic talents. Hence the literati in the Qing dynasty developed a strong interest in Ci poetry. And The communication and singing in literary circle directly facilitated the revival Ci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Ci study in the Qing Dynasty;literati interest; literature field; the revival of Ci poetry in Qing Dynasty
2015-05-23
祝 东(1982- ),男,湖北孝感人,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I207.23
A
2095-4824(2015)04-005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