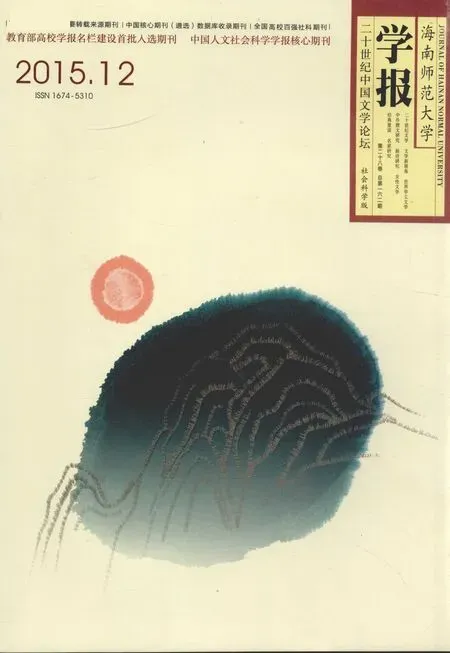《黄色墙纸》的女性哥特解读
郑朝琳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0)
《黄色墙纸》是美国著名女权运动家和作家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的短篇小说佳作,长期被淹没在美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之中,直到20 世纪70 年代才被重新发现和认识。1973 年,女权主义出版社对《黄色墙纸》再版,评论家伊莱恩·R·赫基思认为评论家对其研究过于狭窄,且缺乏女性主义视角,“没有人将疯癫与女主人的性别或者性别角色相联系,也没有人研究文本中的性别关系”[1]。此后,学者们从女性主义、语言学、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种角度挖掘作品复杂深刻的内涵。如今,吉尔曼和《黄色墙纸》在美国文学史尤其是女性主义文学史和批评史中重新获得了地位和价值。《黄色墙纸》内涵丰富,寓意深刻,风格多元,既可以是女性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还可以是后现代主义的。本文从女性哥特主义出发,对这部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力求领略吉尔曼在制造恐怖、设置悬念的精妙技巧之外,深入地把握作者对自我经验的书写、女性身份危机的焦虑以及在构建新女性形象方面所做出的思考和努力。
一、“黄色墙纸”的原型
西方文学源远流长,“黄色墙纸”在19 世纪以前的文学中很难找到文学原型,或许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更好地探索“黄色墙纸”的原型意象。在全文中,墙纸的关键词是黄色,因此理解“黄色”这个词语能够更深入地把握作品的内涵。认识语言学认为:“原型(prototype)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所有概念的建立都是以原型为中心。”[2]“黄色”作为颜色词,在各国文化中相差无几,但“由于受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同一种颜色表达不同的文化心理,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3]。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黄色象征尊贵、地位、荣耀和权力,被视为“天子之色”,普通的百姓不敢跨越界限染指。在西方文化中,黄色与祸害、落后、下流等相联系,具有负面的意义。这种内涵具有深刻的文化渊源,在19世纪中后期,大众把品位低级的报纸称为“黄色报纸”。美国民族中的亚裔形象也被称为“黄祸”,甚至在19 世纪末美国出现了“黄祸论”,背后折射出美国对东方民族的刻板印象、种族歧视和文化优越感。在19 世纪中后期到20 世纪前期的美国文化中,黄色成为了疾病、怯懦、肮脏、腐朽等的代名词。
吉尔曼沿用了黄色的原型意象,却在具体的写作中,扩展了黄色的引申义,增加了象征意义。文本中,黄色多次出现,叙述者“我”认为这是一种“郁闷的模糊不清的黄颜色”,而且“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恶心”。[4]71黄色承袭了西方文化中的含义,具有混乱、模糊等负面意义。这种黄色又富于变化,有时是单调俗气的桔黄色,有时是阴沉黯淡的黄绿色。随着故事的进展,“我”看到墙上布满了各种色调的黄颜色,这种颜色奇怪、丑陋、肮脏,甚至散发出黄色的气味,“我”对黄色的憎恨程度越来越深。最终,“我”撕掉了这些令人恶心的黄墙纸,“我”也彻底变疯了。黄色在“我”的叙述中具有三个特点:首先,黄色让人恶心,能够激发“我”的各种负面情绪,“我”因为黄色而情绪焦虑、焦躁,甚至最后疯掉;其次,黄色具有可变性,它甚至能变成气味,渗透到整个房间,而且这种气味难以消散;最后,黄色具有“生命力”,它能够在墙菌的新芽上生长,以至于多得“我始终数不清它们有多少”[4]83。黄色不仅是腐朽、落后,和“我”之间形成了对立的关系,它是压迫“我”,逼“我”发疯的罪魁祸首。吉尔曼作为美国第一阶段女权主义运动的主要活动家和作家,她对黄色的选择和定义,折射出自己对于父权制社会的深入思考。父权制社会是压迫女性的主要力量,它僵化、落后,却又十分强大,在这种困境下,女性应该如何行动才能摆脱父权文化的桎梏和压迫,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人呢?此外,颜色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符号体系,必然要受到一定社会环境的建构,作家对黄色的使用也表现出19 世纪末期美国文化对于黄色所赋予的内涵。鉴于黄色又与西方人对东方人的称呼有关,因此苏珊·兰瑟在“种族忧虑”的语境中解读《黄色墙纸》,认为作品字里行间都反映出吉尔曼的种族歧视思想,是“作者思想深处的政治无意识”[5]。任何一种女性主义作品或者女性主义理论都不会是普世化的,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女性主义既是世界性的,又是民族性的;既要“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文化和经济条件考虑妇女解放的重点和策略”,又要达到“旨在把妇女从一切形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促进各国妇女之间的团结”[6]之目的。
除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黄色墙纸》的素材来源外,我们也不可忽视作者自身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作者自身的经历就是这部作品的原型。吉尔曼与斯托夫人姐妹、凯瑟琳·比彻接触频繁,受到她们女性主义观念的影响,这使《黄色墙纸》充满了女性的“声音”。童年时期父母分离,导致吉尔曼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孤独和痛苦,并使她对婚姻怀有一种复杂的心理,就如同作品中“我”对丈夫的矛盾心态一样;她热爱写作,喜欢读书,小说中“我”也是偷偷地写作,并借助黄色墙纸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她患了产后忧郁症,不得不接受当时著名医生米切尔的“休息治疗法”,但是这种方法没有减轻她的痛苦,反而加深了她的病情,于是她将经历诉诸于文字,形成了《黄色墙纸》,直接将矛头指向了这种医疗方法。吉尔曼以否定“休息治疗法”为起点,直指性别权术,多角度批判了父权文化对女性身体权、话语权和写作权等的压制与扼杀,发出了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女性解放道路思考的强烈声音。
二、女性哥特传统与身份危机
西方文学中,一直存在着女性哥特的文学传统,却被菲勒斯中心主义长期淹没在地表之下,只有零星的几位作家为文学史和社会所认可。艾伦·莫尔斯在《文学女性》中提出了“女性哥特”这个词语,视其为“女作家采用哥特文体所创作的作品”[7],并发掘出一个漫长复杂的女性哥特传统。许多学者认为,男性哥特小说的主人公多为社会秩序的僭越者,他们独自与各种社会体制对抗,而且通过描写死尸、谋杀、强奸、乱伦等来刺激读者的感官,营造恐怖气氛。而女性哥特则弱化感官场面,更多地聚焦于女主人公对于恐怖的感受和体验,是“一种表达女性内心隐秘的抗争、幻想和恐惧的文学体裁”[8]。在女性哥特文本中,女主人公恐怖感的产生往往伴随着自己对自我身份的探寻与确认。
吉尔曼虽然大体沿用典型的哥特式框架,却改变了其中的一些关键元素,使这部作品体现出更多的女性主义色彩。小说是以“我”来讲述的故事:“我”不再被囚禁在昏暗的古堡或者地下室中,而是被丈夫以养病为名囚禁在四面带窗的“圆形监狱”中,无时无刻地受到“权力的眼睛”的监视;“我”不再被恶棍英雄所虐待或强奸,而是被丈夫温情地称作小傻瓜。不管女性哥特风格如何多元,贯穿始终的是对性别等级制度的反抗。在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说中,女主人公伪装成柔弱者来进行抗争;在《简爱》中,女主人借伯莎之手来对父权制实行报复;在《黄色墙纸》中,“我”是通过自己身份的追求和确认来反抗父权制社会的规训权力。
小说开始的“我”就是多元社会身份的合一:“我”是母亲,因不能履行父权制社会期待的“母职”,而被丈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被迫接受“休息疗养法”。这种在当时颇为盛行的医疗方法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因为它只用于女性身上。“我”是病人,必须接受医生的话语权威。丈夫以医生的口吻命令“我”不准写作、不准胡思乱想、不准外出探访亲友,只准按时服药、安静休息、准时吃饭。“我”是妻子,因不符合男性心中“驯服的肉体”,而被丈夫禁锢在固定的房间之中。在这充满着男性权威的空间里,“我”由于不能很好地完成母职、妻职,而遭受到以丈夫所代表的父权规训力量的压迫。在这种窒息的空间内,“我”的每个身份都是由父权社会所指定的,每一种身份都处于被压迫、边缘化的位置。“我”是妻子、母亲和病人,唯独不是我自己。在这种生存困境下,“我”的态度和观念产生了变化。最初“我”接受父权社会的规训力量,希望能够尽快好起来,呈现“超我”的一面,成为父权社会的“家庭天使”。但是“我”的“本我”却不断地促使“我”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确认自己的个体身份。“我“向丈夫解释病情,他却要“我”服从医生的权威,所以“我”不得不沉默;“我”又觉得照顾小孩使我神经紧张,自己“没法跟他呆在一起”。“我”陷入了“本我”和“超我”的争斗危机中,“本我”无法很好地协调二者,“我”逐渐陷入了疯癫之中。在疯癫中,“我”找到了“我”作为个体的人存在的价值,为自己确定了身份:作家、读者和拯救者。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笔”代表着男性的话语权,女性作家被“禁闭”在菲勒斯文化中,常常会有影响的焦虑,如何建立女性文本成为她们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我”也不例外,“我”的写作权虽然遭到丈夫的压制,“我”也曾经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可是“我”还是偷偷地写作,因为写作是“我”发出“声音”的一种渠道。除了写日记之外,“我”还利用黄色墙纸写出了虚拟的文本。这个时候,“我”既是作家又是读者,在阅读黄色墙纸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它。在丰富的想象中,“我”将毫无美感、混乱模糊、让人恶心的黄色墙纸创造成了一个压抑、桎梏女性的抽象符号。在黄色墙纸的背后,“我”发现了生命的存在:一个或者多个爬行的女人。为了将她从墙纸中解放出来,“我”成为了一个拯救者。“我”搬走婚床、拆除栏杆、撕掉大部分墙纸,好让墙纸后面的女性能够顺利地爬出来,得到自由。最终,墙纸被撕掉了,“我”也获得了自由,再也不会担心被丈夫赶回到墙纸之内。“我”在疯癫中获得了话语权和写作权,在疯癫中驰骋了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疯癫中表现了自己的判断力和行动力。“我”终于不再是衣着干净、驯服善良、温声细语的母亲和妻子,“我”终于摆脱了性属特征,重建了新的身份,成为了一个自由的、拥有主体性的人。克里斯·威登指出:“在当代女性主义强调妇女说话的重要性背后,其重要动机是表达妇女的主体性。”[9]《黄色墙纸》中的“我”不仅是叙述者,而且是行动者;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社会家;不仅重建自我,而且关注其他女性,希望建立女性之间的联合。“我”抵抗住了男权社会强有力的规训力量,在疯癫中建立了新的自我,这样的“我”不正是一位集言说主体、审美主体和行动主体等为一身的“人”吗?
三、密闭“空间”与矛盾心态
在哥特小说中,哥特空间往往是故事发生的核心场景。在女性哥特文本中,哥特空间可以是有形的、具体的场景,也可以是无形的符号,如家庭或者人物主观的体验等。吉尔巴特认为密闭空间“反映女性作家自身的痛苦、无助感、由于身处陌生并无法理解的地域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及其对19 世纪性别领域划分意识形态中蕴含的非理性成分越来越强烈的质疑”[10]84-85。艾伦·莫尔斯认为古堡在女性文本中物化为婚姻家庭关系、社会性别观或者价值观,如“性别角色的禁锢性规定以及以性别为导向的人际关系、女性空间的束缚,特别是父权社会的家庭关系和婚姻制度等”[11]。女性哥特小说中的哥特空间象征着男性的空间,女性被囚禁在那里,意味着被父权制社会压制和异化。女性只有打破这种幽闭的空间,才能获得自由。不少学者都认为女性与“空间”之间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性别关系的体现,实际上正如女性哥特小说内涵的多元、复杂和开放一样,许多哥特文本中女性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绝对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充满了依附与反抗、接纳与摧毁之间的矛盾张力。
《黄色墙纸》中的哥特空间表现为多种层次,由外至内依次为:远离公路的大厦、带栅栏的楼房、分层的房间、贴满黄色墙纸的阁楼、有栅栏的窗户等。层次虽然多,却并非无序杂乱。荒凉的大厦原是某家族的世袭产业;带栅栏的楼房是普通的家宅;“我”和丈夫分别住在上下层的房间中;“我”被安置在带有黄色墙纸的顶楼房间内,这个房间原是育儿室;房间内有张笨重的婚床,窗户上安装了许多保护儿童的栏杆。任何层次,均指向同样的元素:家庭。“我”被迫离开原来的家庭,被带入到另外带有哥特气氛的家庭中。在这里,“我”经历了身份危机,最终得到了疯癫式自由。同样是家庭,同样是父权制囚禁女性的牢笼,为什么女主人公能在后一所房间中重塑新的自我呢?吉尔曼这样的设计颇为精妙,传达出多方面的含义:首先,女性离开家庭,走进家庭,甚至走出家庭,都不是自己的主动行为。女性的人生可谓是一部不断地沦陷于家庭之中的历史。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提出家庭“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的首长,用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对她们握有生杀之权”[12]。从家庭出现的那一时刻起,女性就被迫从属于男性,处于被动地位。其次,女性在家庭中必须要履行妻职、母职,因其性属特征,她成为欲望的客体、生育的工具。父权制通过家庭来实行对她的“社会历史性”压抑,所以,女性如果想找到自己,必须走出家庭这个“幽灵塔”。在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总是伴随着对家庭性别角色的不满、否定和反叛。由于“我”不能成为“家庭的天使”,而被丈夫带到一个具有鬼魅色彩的房间之中。丈夫表面是为“我”治病,实际上是对“我”进行精神上的惩罚。在这个哥特房间内,“我”被丈夫、妹妹、女佣等男权社会的代表者或者驯化者所监视,被剥夺了自由和权利,所以“我”必须反抗。但同样在这个房间内,“我”不需要以家庭女主人的身份来履行家庭职能,所以“我”具备塑造自我身份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和哥特式家庭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正常的、秩序井然的家庭只会迫使“我”沦为生物性的存在,而非常态、反常的家庭在桎梏“我”的同时又客观上对“我”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这种矛盾的心态还体现在“我”对母职的认识上。在小说开头,“我”因为成为“母亲”而患上了“精神抑郁症”,于是被丈夫带来治疗休养。“我”无法同自己的孩子呆在一起,因为他让“我”感觉到精神紧张。这些叙述表明了“我”不愿成为散发着母性光芒的社会既定形象,而且有意将自己从母亲的家庭角色中剥离出来,拒绝沦为生育工具。但是,“我”又会想起可爱的小宝宝,庆幸他不用住在糊满墙纸的房间内,又流露出“我”对孩子的思念以及想要成为一个好母亲的渴望。吉尔曼对“母职”的观念,相对于妻职来说更为复杂,表现了作家对女性与母亲角色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她在以后的作品中也继续探索着这一问题。在19世纪文坛中,许多女作家往往会采用“反家庭”的叙述形式,以此来表明对女性命运的忧患和父权制家庭的否定,但是由于女性所处的家庭环境、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的不同,对父权制的抗争和否定又表现出程度和形式上的差异。《黄色墙纸》中对父权制的态度是模糊的,在反抗的同时又夹杂着少许的留恋,这种矛盾之间的张力也增强了文本意义的衍生性。
四、怪诞与真实
怪诞是哥特小说的审美范畴,特色在于“把人和非人的东西的怪异的结合”[13]。怪诞意味着幻与真的完美结合,“幻”使审美主体意识到与客体之间的距离,进而产生崇高的审美快感。“真”使审美主体能够切身体验到客体,从而使情感得到净化。18世纪以前,怪诞多意味着与人类生活经验相异,包含奇特、荒诞、滑稽等含义。18 世纪后,随着启蒙时代对真理的追求,更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怪诞还包含有一定的现实和真理成分”[14]。汤姆森认为怪诞在本质上是自相矛盾、对立冲突的,“是人类生存本身那种困境作的恰如其分的表述”[15]。怪诞只有与现实相连,才能彰显其特质。哥特小说是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形处理,所以虽有怪诞的形式,却有真实的内容。正是在亦假亦真的情境中,人们发现熟悉的东西陌生化,产生莫名的恐怖,获得审美上的愉悦。《黄色墙纸》正是一篇怪诞佳作。除了以上论述恐怖的场景、幽闭的空间、疯癫的女人、怪异的黄色墙纸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即疯癫叙事和象征手法。小说的叙述者是“我”,“我”是一位精神从抑郁、焦躁至疯癫的女性。吉尔曼设定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通过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她的精神变化历程。“我”的叙述十分主观和片面:“我”会经常产生幽灵的遐想,会觉得每个人都在监视自己,会对墙纸生气,会看到墙纸中的女人,甚至会通过牙咬的方式去抬床。“我”的语句也不连贯、流畅,而是充满跳跃、重复、间断等。于是,《黄色墙纸》就成为了一名疯癫女性的疯言疯语。那么,读者如何来相信一名疯子的言说呢?也就是说,读者怎么找到怪诞之中的真实呢?
西苏说:“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16]。吉尔曼将自己写入了小说,《黄色墙纸》成为了一篇自传色彩的虚构小说。“我”的叙述视角使读者更容易感受到人物的内心,易于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也容易达到吉尔曼的写作意图。除了自传性外,叙述的深层结构更是加强了文本的真实性。即使“我”对自己、他人和事情有着错误的读解,叙述的整体效果却是真实的。吉尔曼在散漫的情节、丰富的物象、杂乱的语言之下,贯穿一条主线:即对女性对自我的追求,这是美国时代精神文化的反映。19 世纪末期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更多的妇女不仅获得高等学历,而且进入许多传统的男性职业领域。不同阶层的女性还联合在一起,建立了俱乐部和救济组织等机构,显示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女性作家群体开始涌现。她们不仅在作品中表现女性问题、关注女性命运,而且着力于建立“新女性”。“新女性”这个词语由19 世纪末的英国女权主义出版社发明,随后被广泛用于指代那些有新思想的、有自我意识的年轻女性。女作家开始质疑或者摒弃旧的女性标准,希望在作品中定义或者描绘那些正在改变的女性形象。吉尔曼也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中探讨了新女性的形象。《黄色墙纸》中的“我”在自我牺牲和自我实现之间选取了后者,也就是说“我”不愿迎合男权文化的需要成为自我牺牲的妻子和母亲,而是乐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建立新的自我。于是,“我”借助写作和阅读建构了一个掩埋在墙纸中的虚幻女人。在“我”的努力下,“我”最终和她融为一体,建立了“新我”。小说最后的“我”是这样描述“新我”的:“我”撕掉了大部分的墙纸,“到底还是出来了”;“我”在房间中爬行着,每次都得跨过丈夫的身体。这样的“新我”在他人眼中是疯癫的,以致于丈夫惊呆了,并昏了过去。这样的“新我”是让“我”高兴的,以致于“我爱怎么爬就怎么爬,多叫人开心呀!”[4]89女主人公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胜利。她不是男性霸权文化的逆来顺受者,而是成为了反叛者,对现行的社会性别政治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和有力的威胁。女主人公新的形象是通过艺术的方式来完成的,表明了女性在职业身份和家庭角色之间所做出的选择。女性在职业和婚姻中选择了前者,表明了这时期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的独立个性,她们将职业而不是婚姻作为展现自我、完善自我的道路。吉尔曼虽然塑造了新女性的形象,但是她对独立女性的处境并不乐观。小说结尾中“我”只能像婴儿爬行,象征女性解放道路的漫长和艰辛。“我”只能囿于房间之内,暗示了父权文化的强大。“我”得到的疯癫式自由,表明了女性若要获得解放和自由,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小说中的时间安排也颇有意味,“我”在房间中度过了美国的独立日。这篇小说创作于19 世纪晚期,在美国独立后的一百多年,女性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还没有享受到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这难道不是对主张人人平等的美国独立精神的嘲讽吗?作品虽然有怪诞的形式,却在内容和时代精神与社会文化变化相呼应,从而怪诞背后有了真实的支撑,而且使虚构和真实得到了统一,印证了我国文学家袁于令所说的,“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17]。
综上,吉尔曼运用了哥特小说中分裂的身份、幽闭的空间、怪诞的情境、恐怖的效果等元素,使《黄色墙纸》呈现出浓厚的女性哥特风格。正如女性哥特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衍生性一样,《黄色墙纸》也具有丰富的言说空间,因为它讲述的不仅是吉尔曼自己的故事,也不仅是疯癫的“我”的故事,而是讲述了“所有的文学女性,如果她们能够说出自己无言的痛苦的话,都会讲述的故事”[10]89。
[1]Elaine R Edges.“Afterword to The Yellow Wallpaper”,The Captive Imagination:A Casebook on The Yellow Paper[M].Femimist Press Edition,1973:125.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4.
[3]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75-176.
[4]〔美〕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黄色墙纸[M]∥文忠强,译.钱满素,选编.我,生为女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5]Lanser Susan S. Feminist Criticism,The Yellow Wallpaper,and the Politics of Color in America[J].Feminist studies,fall,1989:7.
[6]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M].北京:三联书店,1995:19.
[7]Ellen Moers.Literary Women[M].New York:Oxford Up,1976:90.
[8]Punte David.Glennis Byron.The Gothic[M].Malden:Blackwell,2004:278-279.
[9]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246.
[10]Sandra M.Gilbert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en in the Attic:The Wome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ture Imagination[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11]林斌.西方女性哥特研究——兼论女性主义性别与体裁理论[J].外国语,2005(2):72.
[12]〔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3.
[13]〔德〕凯泽尔.美人和野兽文学艺术中的怪诞[M].曾忠禄,钟翔荔,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14.
[14]李伟昉.怪诞:英国哥特小说与六朝志怪小说审美比较论[J].英语研究,2006(3):11
[15]〔英〕汤姆森.论怪诞[M].孙乃修,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37.
[16]〔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M]∥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88.
[17]慢亭过客.西游记题辞[M]∥黄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