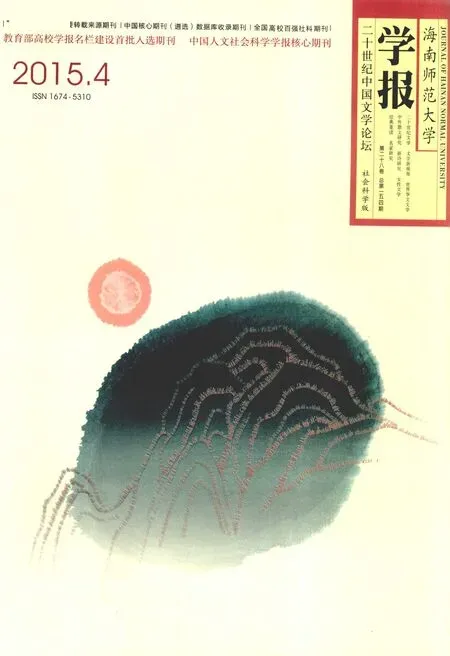《纸爱人》多重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解读
宋晓英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纸爱人》多重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解读
宋晓英
(济南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22)
施玮的小说《纸爱人》含义多重:全知全能的视角陈述了一个世俗的故事,主人公的内视视角以意识的流动推动人物命运的逆转,批评者冷眼旁观到了“他者就是地狱”,隐含的回望视角预示了大的悲凉。其所揭示的存在主义的荒谬在于:人物以“娜拉”式的行为演练了“秋菊”式的反抗,无力反抗的人拒绝了世俗的温暖。其“纸爱人”的意象证明:“文明”与“理性”的外表下,权力与利益,施虐与受虐,劝降与投诚等“游戏”时时上演;城市人如“纸片似的偶人”游走于舞台;“现代人”的灵魂被放逐,心无归处。
施玮;《纸爱人》;多重视角;存在主义
北美华人女作家施玮的小说往往含义多重,中篇小说《纸爱人》是一个典型:既有世俗的关怀,也有人文的深思,阅后久久萦怀的回味里既有时光不复,永失我爱的伤逝,也生发出种种存在主义的哲思。
悲剧与荒谬以旁观者的镜头、夫妻的抱怨、伤逝的回忆、哲学理念的透析一层层揭破。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种视角:一,虽交替以第一人称叙述,但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在不偏不倚貌似调侃地陈述事件。这个语言是充满了世俗温暖的,轻喜剧似的,家长里短地谈论着一个普通家庭捉奸与离婚的闹剧。二,男女主人公的内视视角,主观性较强,五味杂陈,愤慨、犹疑、依恋与决绝时而暴露,时而隐忍。这种情绪的流动推动着人物的行为、情节的发展甚至命运的逆转,从偶然到必然,又从必然到偶然。“一切事情的发展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只在一眨眼的功夫结果便出来了。并且不等你看清楚,这‘结果’又跑出去好远。”[1]78终于,一出喜剧,一个闹剧最后成为悲剧。三,故事隐含的回望视角。悲剧的意义在情节中表面是一个“短痛”,或说这种“短痛”是一件好的事情,戛然而止的结局似乎在预示着女主人公的“新生”。但就人物“质本洁来”的虚妄、“多余的人”的软弱、知识分子的忧患等多重性格去看,这个结局会在多年后成为一种“长痛”,不算是永失我爱,很可能是“永失我伴”。此种意义上,读者会回味出“伤逝”的悠远。四,批评者,或说事件评判者所带来的分析立场,或意义视角。这个冷眼旁观者看到了“他者”就是敌人,就是“自我实现”的障碍等存在主义蕴涵,看到了人类渴望交流与温暖,却相互间筑起不可跨越的鸿沟。其结局的荒诞性在于,女主人公以“娜拉”式的行动演练了“秋菊”式的反抗,其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以滑稽的闹剧与鲁莽的行为草草收场。最终,孩子与脏水一道泼出,孤行的人可能会更加“孑然一身”,行走在虚无的荒漠之中。
这样的判定源于现实的基础与性格归因。小说中一再强调男女主人公是“一类”的人,事件是性格的“必然”,结局是情绪所引发的“偶然”。男主人是一个“作家”,虽个人生活上“玩世不恭”,但也有“助人为乐”、“伸张正义”的职业行为,此番的“出轨”是放浪生活的最后一次,是一种“告别”性演出。女主人公“淼”在生活与工作中委曲求全、忍而不发。这种“多余的人”的萎顿积年已久,丈夫制造的这次“外遇”,女友逼迫的这次“捉奸”强加于她一个行动的“事由”。
与许多把情节、关系、情感、生命简化为肥皂剧的写法不同,小说的意识流手法极大地展示了命运的偶然与必然间的张力。通奸者的床前,女人对自己必须要扮演的“受害者”角色不堪重负:“我在哪里?”“我在做啥?”在她的“自省”意识中,无论对眼前的男女双眠图,还是对他们将要共同起身穿上一切的琐碎,自己似乎都是一个局外人。愤怒为什么没有喷涌,甚至积蓄?长久以来,她似乎丧失了对任何事情产生强烈情感的能力,她性格的悲剧,命运的荒谬似乎不在这里,而在于她从来不是一个“秦香莲”,此刻却要扮演“怨妇”的角色。她爱这个男人吗?不爱。此刻他的一举一动,如指向旁边的这个女人,好像对她说“你看着办!”就应该是一个抗议的姿态。
女人在这里不明就里,扎手扎脚。以什么样的姿态“捉奸”不只关系到她的形象,还关系到她对历时10年的婚姻的定义。于前者,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定要表演出“眼里揉不进砂子”;于后者,她不想负责,无力行动,尽量地拖延着这个过程。“延迟行动”,是存在主义意义上“多余的人”、“反英雄”形象的典型表现。
小说在两个地方对她“多余的人”的人格做过铺垫:接到女友告知真相,她懊恼:“就像是一种专利被人占了,或是原本我的角色被她抢着演了。”[1]68当然,这是隐含的情节伏笔,但她既不想追究女友对此事过于关注的原因,也不愿承担此事所带来的荒谬。“世界的错误不应该由我来承担”,是“反英雄”的共有心态。另一个佐证是出差途中她与“女同事”的虚与伪蛇。“女同事”只是助手,“机械工程师”与“业务代表”是自己。当设备安装与培训基本完成,自己不得不提前返回,庆功宴送行礼归于“女同事”,她却表演了一连串的勇于承担、替人分忧的“仗义”行为。“我”司空见惯地应付着,不仅因为她是“领导的人”,还在于“我”一贯的原则:不与人计较,“一任群芳妒”。这些委曲求全的人格根源一方面在于“延迟行动”、“无力反抗”,另一方面是“悲剧性抵御”:出于自然与本性坚守自己的灵魂禁地,拒绝他人入内。所以,夫妻博弈的回合中,她隐约觉得自己是“有错”的:“施虐”的行为大多有“受虐”者参与,自己“一如既往”的“清高”可能早已“犯了众怒”,这个男人被她“冷遇”得够了。此处的人物有多重角色:一个在世俗温暖与精神高洁间举棋不定的人,一个内省者,一个冈察洛夫笔下《奥勃洛摩夫》一样“畏缩”的人。
女人意识到自己的“抗议者”角色应该上场了。她拉开窗帘,让日光之箭刺向这一对男女。男人“将手臂屈着挡在头上,一副挨打的样子。他的手臂苍白,毫无血色,像一截石膏”。“我”幻想着“他的身体一截截遇着阳光,并一截截变成石膏。最后这具男性的身体,就成了一尊毫无性感的石膏像。”[1]73“男人”的形象被“物化”了。在她的“象牙塔”中,他本来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一个“作家”,他在“我”看来本不缺乏灵魂,应该是我的同类,但此时,“他”被“物化”了。他本来就是“物化”的,还是自己一直在“参与”这种“物化”?她有点底虚。男人“抗议成功”的姿态才刚刚上演,“我们离婚吧”,“台词”说出去的时候两个人都像演员。男人试探着问:“我们今天就去?”语气中报复的欢畅多于惶然,进一步警醒她,应该把“愤怒者”的角色扮演到底。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种角色表演感是全知全能的叙述语言所阐释的,也是女主人公“自省者”角色所认知的。一方面,她对自己的一贯清高、冷落他人有所忏悔,另一方面,她的宽容也很茫然,因为自己对家庭与社会同样积怨已久:“我”难道不是一直在“完成一个做妻子的过程,尽可能地尽善尽美”[1]67?一个本我的自清者,于人何害?单位里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加班加点,业绩不比别人少,但更多地感到疲惫与厌倦。这“厌倦”达不到萨特的人物《恶心》的强度,如面对床上的通奸者,精神洁净如她,灵魂高蹈如她,为什么不“恶心”,甚至不“愤怒”?
女人的“延迟行动”,不仅在于她的“自省”,还出于她对现实的考虑。离婚路上的街景与“机关”建筑的强大都暗示了自己的渺小,两个“小人物”被挤压得更渺小。“区委”“骤富”,因为已经与“××房地产公司”“强强合作”;办事处人的嘴脸冷漠无情、斩钉截铁:“今天不办离婚!”在“自我”之中待得太久,完全忽略了社会的强大,忘记了“家”这个小小的巢穴的保护作用。强大的世界一直对于他们来说是“共同的敌人”,两个“同盟”交流着“小人物”意会的眼神。他们已经习惯了面对外界的“铁律”或“冷漠”“握爪”,自己已经准备好对这个世界“孤身对抗”了吗?他们习惯了两个人相伴,脱掉身上的毛刺,对许多事情不抵制,就是眼前走在离婚的路上,尚懒得思考,期盼有个偶然的因素给自己一个明确的暗示:“离还是不离?”两人对于将在这个混沌的世上恢复独身有隐秘的畏惧。
离婚路上的冷暖自知、社会批判、自我反省说明她除了是一个清高自许的女人,还是一个反思者。这个知识分子的“超我”看到了更多的世界的灰色与污浊,感受到了自我的无力:在这个强大的社会里,一个软弱的人无资格谈爱情,无资格谈离婚,又什么时候坚持过原则?世界是按照强权的规则而确立的,“他们创造出这么庞大、精微、环环相扣又妙不可言的所谓文化”,[1]77还不是为了巩固霸权,管理弱者,比如,婚姻市场上的女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嫁给谁都一样,在那里工作都一样,作为弱势,自己似乎只有“修善自我”,训练成为这种文化之“附庸”的功能。“冷眼旁观者”借二人的心理展开讽刺:“大肆贪污”、“物价飞涨”、“治安混乱”均不是“大事”,其它“无可估量的罪恶,肉体与精神侵害”都不算什么,而“丈夫与另一个异性做爱”是“头等大事”!因为于前者,你无力反抗,所以于后者,你就算怕强凌弱了,不过借“捉奸”与“离婚”一改“小人物”形象,将“正义与权益”表演在“捍卫”这个无爱的婚姻的“神圣”上。不过是一个怨偶,一个委屈的“娜拉”,顶多算是一个“秦香莲”,却弄出一种“秋菊”的姿态与“窦娥”的力量,岂不是一种“避重就轻”、“小题大做”?小说借清高小女人的独白在女主人公的身体里栽种了一个悲观绝望的知识分子形象,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尼金》,与《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承担着对命运的反思、对时代的批判。
像一切悲观厌世的人都必须靠俗世的温暖来呼吸与活着一样,两个孤单的“小人物”,“人民内部”的队友,在“离婚”的猫鼠游戏中产生了惧怕。情节的一波三折来自于双方都不乏依恋但又都想对方让步。但“偶然性”的因素出现了:难办的离婚手续竟让“他”所托付的一个急于“报恩”的人办成了!在这一瞬间,女人对这种“必然”释然了,倔强反抗的“尊严”复苏了。她决绝地走出了家门,一个勇于“翻篇儿”,勇于走向新生的“我”诞生了。
“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是施玮常用的句子。意思是“现代”社会,人人拒绝责任,规避良知,避免沉重。与“乾坤特重我头轻”、“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英雄”们相比,他们解构了崇高、价值、忏悔意识与批判精神,“方寸之间的”、“鼻子底下的”的可怜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日常生活”一定比“宏大叙事”要重要得多。在这个“真实的人生中”,他们既失去了创造与自新的勇气,规规矩矩地守着可怜的“巢穴”,懒得看外面的世界,但他们过的是“日子”,真正的爱与不爱,无力去追究了。小说的主题是:失去了“爱”的勇气的人们仿佛没有生命的纸壳儿,晃着轻飘飘的身子继续过着无穷无尽的毫无意义的“日子”。
艺术上,小说的心理结构曲折变化,如太极拳的推手般玄妙多端。人物的言语是克制的,心理是隐含的,情节是流动的,作家的笔一点点揭破事件层层的细纱,文学功底在此,哲学的深邃在此,存在主义的荒谬、“多余的人”的无力与“他人即地狱”的含义昭然若揭。逻辑的荒谬在于:男人在试图“洗手不干”的时候被女人的“女友”揭发;女人在离婚的路上意识到外部的世界如铜墙铁壁,自己需要一个“小家”的保护;见证了结婚办事人员所代表的强权,才给家里这个小的“他者”赎罪的机会。他妥协求饶的行为是,建议吃一顿女人爱吃的红房子,而不是他爱吃的路边摊儿。她尚在犹豫不决、欲迎还拒的当口,男人找到了脱逃的机会。丈夫两天没回家,自己两天没上班,“巢穴”的空虚与社会角色的“失职”使她深悟虚空。“浪子”归来,这一次应该是彻底地归来,因为在“逃跑”的路上、“背叛”的路上,他显然疲累了,流浪得够了。“他往那儿一坐,屋里的一切死东西都活了起来,变得柔和了。”[1]87他想以一场酣畅淋漓的亲密来证明10年的温存,来抵御手中的“一张纸”,女人同意了。但心有洁癖的女人怀着温存的回味和团聚的欢欣收拾着这个家的当口,发现了这个“纸团”——他托人办成的“离婚书”。
一个揉皱了的因为当事人没有到场事实上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纸团唤醒了决绝的她,那个不愿意妥协的“新我”。对“你回来时希望我在吗”的恳求断然拒绝,她走出家门,切断了10年的维系。这一刻,她的心似乎勇敢起来:这个“物化”的、生理的男人给她的“陌生感”太强烈了,无论“皮相的温暖”①余华在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中借少年孙光林的命运定义人生就是在孤独的无依无靠的雨夜里发出求助的呼声。但在空旷的荒漠的世界里找不到真正的温暖,仅有一种“皮相的温暖”,而不是刻骨的温暖,或灵魂的温暖,来自于互惠,或者一种利益需要,并不是对你的“呼喊”的回应。存留了多久,他们间的维系也可能像手中的这张纸一样的脆弱。生命的“真我”不应该像这样被揉皱成一团,她不再容许别人对自己的委屈全不放在心上,她的“浊其源而求其清流”,精神尊贵,都是对自己的负责。她走出了家门,“灿烂的星空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喜悦,我突然就有了购物的欲望。”[1]89
人物的命名有隐喻的意义:“石”与“淼”,清灵如水与顽石沌根,就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性别间沟壑林立,人与人隔着保护膜,肌肤相亲的人关系也孱弱如丝。现代社会的情爱关系已失去了惟一性,人人自以为有了更多的选择,无论是骨肉血亲还是亲密爱人,无论怎样的唇齿相依或狼狈成奸,都在世界性流动中失去了关系的固性。在“文明”与“理性”的外表下,“现代人”逐渐失去了本性、真纯,多了“猫鼠游戏”的权衡。权力与利益,施虐与受虐,劝降与投诚天天在表演:纸片似的偶人游走在舞台,血肉之躯被放逐了,精神灵魂被放逐了,“现代人”心无归处。
[1]施玮.纸爱人[C]//新城路100号·小说卷第一辑(下).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毕光明)
An Existent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 ulti-meanings of Paper Lovers
SONG Xiao-ying
(School of Literature,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250022,China)
ShiWei’s novel Paper Lovers is ofmultiplemeanings,as is shown in the narration of a secular tale in the view of an omniscient narrator;the reversal of characters’destiny conducted through the flow of consciousness by way of the protagonist’s internal-visual-angle;the witness of a critic to the phenomenon—“the other is a hell”;and the presage of some tremendous desolation via the implied view of retrospection.As revealed in the novel,the absurdity of existentialism is shown as follows:instead of resisting against social suppression in a Quju’s style desired by the heroine as an intellectual,she has behaved like Nora and rejected the worldly warmth—one of a few sustentations in her lengthy life.The images of“paper lovers”are indicative of the constant performance of such“games”as power and profit,sadism andmasochism,capitulation and surrender beneath the surface of“civilization”and“rationality”,with city dwellers performing like“paper puppets”on the stage and the soul of“modern people”having been in exile.
ShiWei;Paper Lovers;multiple perspectives;existentialism
I106.4
A
1674-5310(2015)-04-0046-0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编号:11BZW113)
2014-12-24
宋晓英(1961-),女,河北威县人,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英国爱丁堡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美国陶森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世界华人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浅析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评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