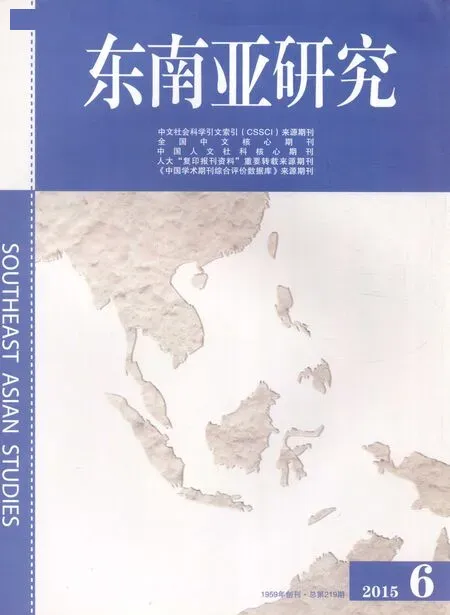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杨 勉 张 乐
(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100024)
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截然不同处置结果的背景与原因分析
杨勉张乐
(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北京 100024)
[关键词]中缅边界;中印边界;争端解决方式;和平解决;武力解决
[摘要]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是中国最早与邻国着手解决的陆地边界问题。二者历史起源相同,问题属性相似,但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中印边界则爆发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形成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文一武”两个范例。在近年中国与海洋邻国岛屿归属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日益尖锐的背景下,对比分析导致中印和中缅边界问题情况相似但处置结果和走向截然不同的原因,既是重要的历史经验总结,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Determinants in Resolving Sino-India and Sino-Burma
Border Disputes:Background and Reason
Yang Mian & Zhang Le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China chose India and Burma as a start to work with its land border disputes. These two border disputes were of the same kind and shared similar origins. However, the Sino-Burma border dispute reached a peaceful solution while the Sino-India border dispute ended up with a war, creating two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territorial dispute resolving—military solution on one hand and peaceful s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the deteriorating situation of the disputed islands with marine rights and interest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s, it is important to compare and reflect on the determinants which led the two disputes to different results.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面临的边界局势是与所有邻国都存在着不同种类和程度的争端。20世纪5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着手边界问题的解决。首先处理的是中缅和中印两个边界问题。二者历史起源相同,争端问题相近,但最后中缅边界争端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而中印边界则爆发战争,至今仍未得到解决,由此形成中国解决领土争端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文一武”两个范例。“中印、中缅边界划分问题是新中国边界谈判实践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特例。中印边界的划分至今悬而未决,而中缅边界的划分早已成为中外边界谈判的楷模”。近年来,中印边界形势曾屡屡紧张,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而缅甸临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内战不断,双边关系却因边界问题早已解决而波澜不惊。近年中国与海洋邻国的岛屿归属争端和海洋划界争端日益尖锐化,因此,回顾和对比分析导致中印和中缅边界两个案例不同结果走向的背景与原因,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中缅边界与中印边界争端的相似性
(一)都有涉及相当面积的三段边界领土争端
1.中缅边界三段争端
中缅两国之间有着2000多公里长的边界,但在中国强盛的藩属体制时代,中缅之间并不存在一条近代意义上的国界线,边界长期处于一种游移状态,中缅之间正式划分国界是在英国占领缅甸以后。缅甸与中国存在争议的领土分为北、中、南三段。
北段:指西藏察隅以南、尖高山以北、高黎贡山以西、印度阿萨姆以东地区,此段边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清朝末期,中英两国分别于1894年和1897年签订《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和《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对尖高山以南的中缅边界作了明文规定,但双方在尖高山以北边界划分上分歧巨大,遂规定“北纬25度35分之北一段边界,俟将来查明该处情形稍详,两国再定界线”。尖高山因此成为中缅边界“北段未定界”的起点。
中段:勐卯三角地,也称南畹三角地,指南畹河与瑞丽江汇合处的一块地区,约220平方公里。1897年的《续议缅甸条约附款》规定勐卯三角地属于中国,英国则以“永租”的名义取得对该地区的管辖权,每年向中国支付1000卢比租金。1948年缅甸独立后从英国继承了这一“永租”关系。中华民国政府拒绝接受缅甸政府缴纳的“租金”,以示不予承认,但因忙于内战无暇收回该地。
南段:通过1894年、1897年两次边界条约,清政府与英国划定了尖高山以南的滇缅边界。1897至1899年,中英两国先后三次派员实地勘划中缅边界,但由于条约约文、附图的矛盾与错误,到1900年4月实地勘界结束,镇边厅阿佤山区一段的边界也没能达成协议,导致从南帕河与南定河汇流处起至南马河流入南卡江处一段成为中缅边界的“南段未定界”。1941年英国制造“1941年线”,将中缅边界线向中国方向东移几十公里。
2.中印边界三段争端
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历史上从未正式划定。争议地区分东、中、西三段,争议面积约125,000平方公里。
东段:即中国所称“藏南”地区(印度在此非法成立了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西起中国、印度、不丹三国的交界处,东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的交界处,争议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
西段:指中国新疆南部和西藏东部与印度接壤的边界地区。印度对新疆阿克赛钦地区的大部分和西藏的巴里加斯地区提出领土要求,总面积达3.35万平方公里。阿克赛钦地区位于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巴里加斯地区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狮泉河河谷地区。上述两地历史上历来属于中国。
中段:从西藏阿里地区与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和印度的交界处起,到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为止,争议地区分为四块,总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包括巨哇、曲惹地区;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中印中段边界与东段和西段一样,两国之间未订立任何条约和协议,从来没有划定过。但依循历史沿革的管理范围,双方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线。
(二)都是英国殖民侵略的遗留问题
中缅、中印边界问题都是英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849年,英国完全侵占印度。1885年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清政府默认了英国对缅甸的统治,签订《中英缅藏条款》,规定“缅甸循例向中国十年一贡;中英派员会同勘定中缅边界,边界通商另立专章”。中缅边界问题由此产生。中印边界问题也是源自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制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和“约翰逊线”,独立后印度政府的“西藏缓冲区”设想和“边疆前进政策”也都继承自英印殖民当局地缘政治战略。
1.英国在中缅边界地区的侵略
(1)英国军事蚕食尖高山以北未定界地区。
1894年和1897年的中英边界条约规定了尖高山以南的中缅边界,对尖高山以北边界的划分因分歧巨大,双方本决定留待将来再议,但英帝国主义不断在争议地区蚕食鲸吞。1911年1月英国占领片马,制造了“片马事件”。英国的侵略行径遭到当地傈僳族、景颇族人民的激烈反抗。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英国政府停止了与中国政府的交涉,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实现其边界要求,1927年先后武力侵占中国的古浪和岗房等地区。片马、古浪和岗房地区(简称“片马岗地区”)面积约为153平方公里。此后英国虽然不得不承认片马、岗房、古浪属于中国,但仍保持对片马岗地区的占领。1914年英国在坎底设置葡萄府;1926年趁中国北伐战争,出兵强占恩梅开江和萨尔温江之间的江心坡地区。到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英国实际上将高黎贡山变为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实际控制线。缅甸独立后把上述地区划入克钦邦,延续英缅政府时期的各项行政设施和管辖。
(2)英国武力炮制“1941年线”,侵占阿佤山大片地区。
在中缅“南段未定界”,英国侵略者于1927年非法进入云南沧源地区秘密勘探矿藏。1933年英国开始修筑通向矿区的公路,1934年1月派兵侵占班洪、班老和永邦三个佤族部落共管的炉房银矿,激起佤族人民的愤怒。班洪王与班老王邀集周围部落,组成三支武装抗击英军,最终击退入侵者,收复了失地。但英国并不死心,借中国抗日战争急需陆路对外通道之际,以封锁滇缅公路相要挟,于1941年6月18日,与中国以政府换文的方式划定阿佤山区边界,将72%的阿佤山地区,包括部分班洪和全部的班老地区划给英属缅甸,史称“1941年线”。所谓的“1941年线”将中缅边界线向中国方向东移了几十公里。但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英双方都没来得及实地勘测和树立界桩。缅甸联邦独立后将班老、班洪地区划入掸邦。1952年中国军队为追击败退到缅甸的国民党军已经越过“1941年线”,并在当地驻扎下来。同时,缅军也在南北两段未定边界上向前推进,抢先占据有争议的地方。
(3)英国名义上“永租”,实则“永占”中国猛卯三角地。
1894年《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签订之前,英国借口勘察两国边界,未经中国同意就修建了从八莫到勐卯三角地的公路。1897年2月,英国殖民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其中第二条规定:“……南碗河之南那木喀相近有三角地一段,西濒南莫江支河及蛮秀岭之垒周尖高山,从此尖高山遵岭东北至瑞丽江,此段地英国认为中国之地,惟是地乃中国永租与英国管辖,其他之权咸归英国,中国不用过问,其生年租价若干,嗣后再议。”此后,英国便以“永租”名义强行占领了中国的猛卯三角地。
2. 英国在中印边界地区的侵略
(1)私划所谓“麦克马洪线”,觊觎中国藏南地区。
中印东段边界争议产生的原因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麦线)问题,这是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问题。中印边界原本是一条传统习惯线。1913年11月,英国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了中、英、藏三方代表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会议期间,英国代表亨利·麦克马洪背着中国政府,私自划定“麦克马洪线”作为所谓的“印藏分界线”,威胁利诱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于1914年3月24日签订所谓的《西拉姆条约》,并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将“麦克马洪线”插入到换文地图中,此线将藏南地区9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英属印度,对此历届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英国也做贼心虚,秘密换文后一直不敢公布,也不敢改变地图的历来划法,印度官方地图直到1937年才以“麦线”显示所谓的“边界”,但仍注明“边界未经标定”。在印度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初,中印边境地区按传统习惯线划分的格局从来没有打破。
(2)私划所谓“约翰逊线”,觊觎中国阿克赛钦和巴里加斯地区。
19世纪,中国新疆地区逐渐成为英俄角逐中亚的前哨阵地,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中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1865年派遣英属印度测量局官员W·H.约翰逊潜入南疆地区,从其侵占的拉达克地区进入阿克赛钦,最后到达新疆的和田。约翰逊通过所谓的“勘察”,绘制了一条所谓的“约翰逊线”(简称“约线”),此线将中印边界从喀喇昆仑山推进到昆仑山,将中国阿克赛钦和巴里加斯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英属印度版图,企图将上述地区变成英属印度克什米尔的一部分。阿克赛钦地区隶属中国新疆,总面积约4.3万平方公里,其中中印争议地区约3万平方公里,巴里加斯地区位于传统习惯线中国西藏一侧,包括基古纳鲁河、乌木隆、碟木绰克(典角)、果洛4块地方,面积约1900平方公里。但英国政府并未知会当时的清政府。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建了新藏公路,印度政府得知后,于1958年10月18日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向中国提出对阿克赛钦的领土声索,中印西段边界争端由此产生。但是,阿克赛钦地区始终处在中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而巴里加斯的部分地区被印度侵占*印度称巴里加斯地区为碟木绰克,隶属印控“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地区列城县”。。
(3)不断武力蚕食中印边界中段的藏民村庄和牧场。
中印边界中段中国边界以南地区,原属尼泊尔管辖。英国以武力割占尼泊尔与克什米尔之间的大片地区后,英属印度才在这一地区与中国西藏接壤。得寸进尺的英印殖民当局把喜马拉雅山山脊视为此段中印边界的“理想界线”。一些山口西面或南面的藏族村庄和藏族牧民的传统牧场,被不断向前推进的英国殖民者蚕食,单方面划归英属印度。中段边界争议地区中的桑、葱莎地区较早为英国侵占。印度独立后派兵进驻上述地区,又陆续蚕食乌热、然冲、香札、拉不底、波林三多、巨哇、曲惹等地。
(三)中缅、中印双边关系属性的相似性
1.缅甸和印度都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首批正式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
(1)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中缅睦邻友好关系有着深厚的基础,两国山水相连,人民自古和睦相处。两国近代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持,共同修筑长达100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是二战期间至关重要的国际援华物资战略通道;中国10万远征军将士曾赴缅抗日,可以说中缅友谊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关系揭开新的一页。缅甸于1949年12月16日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希望建立外交关系及互派使节。缅甸成为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并于1950年6月8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2)印度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两个最大的文明古国,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国有文字记载的交往始于公元前2世纪。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曾到印度求经,印度高僧达摩曾来华传教,带动了两国之间的文化思想交流。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处于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艰苦时期的印度国大党,在自身条件也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给予中国人民帮助。尼赫鲁在1936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抨击“不抵抗”政策,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他还曾发起募捐,动员印度民众捐钱捐物支持中国抗战。前来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曾任八路军医院外科主治医生、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1942年12月因病逝世于河北唐县。印度1947年独立,1949年12月30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4月1日与新中国建交,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1954年,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成为新中国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首脑。当年北京的机关学校全部放假,几十万市民从机场到宾馆夹道欢迎尼赫鲁,盛况空前。随后周恩来回访印度,中印关系一度进入了“Hindi-Chini Bhai-Bhai”(中印人民亲如兄弟)的蜜月时期。“1954年双方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解决了英国遗留的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此后两年,在内地至藏公路修通前,中央驻藏军政人员供给大半由印度进入”。
2.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缅、中印双边关系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基本处于同一友好水平,三国在国际反殖、反帝斗争中并肩协作。缅、印两国都支持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拒绝加入并谴责以围堵新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1955 年印尼万隆的“亚非会议”上,缅、印两国都曾为新中国与亚洲有关国家结交朋友做出了各自努力。
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底,中国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12月3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1954年,周恩来又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并分别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印、缅三国一起将五项原则的精神带到亚非会议上,深刻影响了“万隆精神”十项原则的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在措词上作了修改,“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即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合作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赞同,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基本原则。
二截然不同的争端处置方式和结果
(一)中缅边界争端和平解决
1.和平谈判签订边界条约
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友好协商与互谅互让的精神,经过长期谈判,中缅双方于1960年1月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6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成立,仅用三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对边界的勘查、划定和边界条约的起草工作。10月1日,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努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
2.中缅边界解决方案
条约规定中缅三段争议领土的解决方案如下:(1)北段边界: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等于中国承认旧地图上划在中国境内,但并不实际控制的江心坡地区属于缅甸),缅甸将片马、古浪、岗房地区归还中国(今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2)中段地区:鉴于中缅两国的平等友好关系,废除缅甸对猛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而中国考虑到缅甸交通的实际需要,将该地主权移交给缅甸;(3)南段边界:基本保持“1941年线”,但作为对猛卯三角地的交换,同时为了照顾历史关系和部落的完整,把“1941年线”划给缅甸的班老、班洪部落辖区归还中国。而且,为了便于双方各自的行政管理,照顾当地居民的部落关系和生产生活上的需要,对“1941年线”的其他部分做出一些公平合理的调整,双方商定调整六个骑线村寨的归属:将缅甸管辖的永和和龙乃两个寨子划归中国;将中国管辖的羊柏、班孔、班弄和班歪四个寨子划归缅甸,使这些骑线村寨不再被边界线所分割。此外,中国政府根据反对外国特权和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一贯政策,放弃1941年中英换文中规定的中国参与经营缅甸炉房矿产企业的权利。勘界后的中缅边界线总长2184公里,其中西藏段长187公里米,云南段长1997公里,在边界线上竖立了400余块界碑。
(二)中印边界爆发战争
1.印度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的“前进政策”
印度在中印边界争议地区采取所谓“前进政策”,设置哨所,蚕食领土。在东段,印度利用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无暇西顾之机不断向北推进,1951年2月,印度军队占领达旺,到1953年印军完成了对藏南地区的实际控制,并于1954年在该地区成立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印度当年出版的官方地图将边界东段“麦克马洪线”和西段“约翰逊线”都标为已定界。在中段,趁中国边防部队尚未到达之际,印度政府派军队侵占了中国的波林三多、乌热、然冲、拉不底等地区。到1958年,印度已经侵占了中段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西段,印度于1958年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正式提出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
2.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1959年,中印于8月和10月发生东线的朗久事件和西线的空喀山口冲突,中印边界局势紧张升级。1962年10月12日,尼赫鲁发表公开讲话,命令印度军队“清除”边境上的中国军队,印军先后在中印边界的东西两段发动炮击,10月20日中国实施反击,发动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战事分两个阶段,前后进行了大约一个月。中国参战部队约3万人,以伤亡2400余人的代价歼灭印军近万人。在西段地区打掉了印军的入侵据点,在东段地区把印军赶回了传统习惯线。在完成痛击印军的既定战役目标后,1962年11月21日,中国突然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将缴获的印军物资和俘虏的印度战俘归还印方,随后中国军队撤出了在藏南攻克的地区,一直退到冲突发生前的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处。但在中国撤军之后,印军旋即重新占据了绝大部分藏南地区*1972年印度将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改为所谓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1986年底印度议会两院立法又将此地升格为所谓的“邦”。翌年,印度正式宣布成立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严正声明印度的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而在西线的阿克赛钦地区,印度在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面前未敢再次染指。
三影响中缅、中印边界争端不同处置路径的背景和原因
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出中缅、中印边界问题在边界属性、争端起源和国家关系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截然不同。中缅边界秉承互谅互让原则迅速得以解决,成为新中国妥善解决领土边界问题的范例,而中印边界争端走向战争,至今未得到解决,给两国关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下因素可以解释中印、中缅边界争端为何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
(一)印度霸权式的地缘战略和扩张性的领土政策
1.尼赫鲁的“大国”梦和欲变西藏为中印之间“缓冲国”的幻想
印度无论从人口还是面积上都是南亚次大陆最大的国家。尼赫鲁在其《印度的发现》一书中宣称:“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印度将发展成为印度洋、东南亚,直至中东地区的经济政治活动中心”。“大国情结”与印度民族主义一样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巨大影响。在印度决策者的认知系统中,如果接受中国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主张,那就等于屈从中国的压力,损害印度的大国形象……基于这种认知,拒绝中国有关边界谈判的建议就是一种必然的逻辑结果。
印度继承自英印政府的地缘野心是中印边界争端的根源,其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印关系恶化乃至影响边界问题解决的重要原因。在地缘安全战略方面,印度沿袭了英印殖民政府的思维,将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南亚邻国看作印度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同时希望西藏能够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1951年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印度“缓冲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驻军使中国从“潜在的威胁”变成“眼前的威胁”,于是印度政府开始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暗地里支持怂恿“藏独”。对此周恩来指出:“印度一部分上层人士希望西藏落后的制度不变,保持西藏‘缓冲国’的想法,在西藏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作用。西藏反动分子纷纷到噶伦堡去,他们同蒋介石、美国、英国的特务来往活动,没有印度的许可是搞不成的。”1959年3月,西藏上层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4月达赖出逃印度,印度不但给予庇护,还拨出达兰萨拉给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留驻,同时指责中国政府违背了西藏自治的承诺。在中国政府看来,印度干涉中国内政、试图分裂西藏是“美印苏反华同盟”弱化中国的首要手段,必须采取有力的反击。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削弱了双方的互信,损害了两国原有的睦邻友好关系,并最终导致两国的敌对与边界战争。中国发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为了教训印度怂恿和庇护“藏独”的行径以及震慑达赖集团。过去中国学界在这一点上的关注和论述不够,但印度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和强调这一点。
2.印度拒绝谈判和妥协、一味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扩张性领土政策
印度不但否定领土争端的存在,还多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一味谋求领土利益的最大化。印度政府拒绝谈判妥协,拒绝冻结现状,拒绝脱离接触,也拒绝“以东换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事后受命研究总结印度失败原因的内部报告指出:“尼赫鲁政府决定通过另外一个方式解决此问题,即是单方面研究并决定印中边境的合适的分界并拒绝和北京谈判。除非北京不可思议地接受印度单方面随意地对中国边界施加影响并侵占其领土的行为,尼赫鲁必然导致冲突。”英国学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如此评价印度的边界政策:印度“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赛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否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尼赫鲁政府拒绝承认中印边界存在争议的事实,认为在1954年的《中印西藏协议》中就已经解决了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1959年3月,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要求将有争议的12.5万平方公里领土全部划归印度。
印度推行所谓“前进政策”。从1961年开始的印度“前进政策”,不但向中印边境增调军队,甚至到中国边防军的后方设置据点。中国一直警告如果印度不停止它的扩张行动,中国军队将被迫反击。1959年中国平息西藏叛乱之后,印度开始大量增加军费,购买外国飞机、坦克、导弹等先进武器装备,积极扩军备战。同年8月和10月,印军挑起东线的朗久事件和西线的空喀山口冲突。
印度拒绝中国提出的冻结现状的危机管控方案。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承认实际控制线。1959年中印边界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周恩来正式向印度提出双方从边界实际控制线各后撤20公里,建立非军事区以避免冲突的建议,这就是1959年11月7日双方控制线的来历。这条控制线,在中印边界东段就是麦克马洪线;在西段,是中印传统边界线。1960年,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商谈边界问题,再次提出双方边界守军从各自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的建议,在遭到印度拒绝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单方面执行了这项提议。
在中印领土争端中,“印方采取了‘寸土必争’的方针,多次拒绝中方提出的建设性提案”,顽固谋求己方利益最大化,对中国递来的橄榄枝不屑一顾。1960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外长陈毅访印,向印方提出“以东换西”(即东段争议地区换取西段争议地区的“弃东保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如果印方接受,中印局势势必得到缓和,为日后和谈创造条件。但尼赫鲁不接受中方的建议,认为“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坚持索要西段的阿克赛钦地区,致使中国政府的这一巨大让步没能达到预想效果。印度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拒绝“以东换西”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无视中国的底线,错失和平解决的良机,最终导致事情滑向最坏的方向。
印度政府还极力图谋将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为了在国际社会上先声夺人,印度将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照会、声明、信函公之于众。1960—1962年的“照会战”将中印边界问题国际化,把两国间的谈判内容公诸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首先,边界争端细节的公开助长了两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寸土得失都会被上升到国家尊严层面的舆论氛围下,两国政府政策转寰的余地都大大受限,加大了双边谈判的难度。其次,“在‘照会战’、‘宣传战’中,中印双方均将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态度公布得清清楚楚,一览无遗,使得国际社会对边界的走向和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了如指掌。事到如此,任何一方的妥协、让步都意味着国家尊严的丧失、民族自尊心的伤害,这无疑将中印双方逼到了非开战不可的地步”。
3.尼赫鲁的自负、误判和投机
尼赫鲁自以为可以制造既成事实迫使中国接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印度一方面及早与中国建交,发展友好关系,同时又悄悄地向麦克马洪线不断推进,在外交交往中则不提边界一事,以期让中国接受既成事实。
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浮出水面之后三年间,恰逢中国国内因大跃进失败和严重自然灾害导致的“三年困难时期”,海峡对岸台湾当局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国际上中苏分歧加剧,“美国在中南半岛升级对越南的战争”。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正处在美苏的双重压力之下,乘此时在边界问题上逼中国做出相应的让步和妥协是可能的”〗,“1961年出兵葡萄牙属地果阿的成功事例强化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认知,即坚持推行‘ 前进政策’,只要把中印边界全线推进到自己认知的边界并造成既成事实,中国就不得不接受边界现状”。尼赫鲁认定在中国内外交困之时,正是把喜马拉雅山山脊变成其“理想边界”的好机会,严重低估新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与能力,误判中国不会对印度的“前进战略”做出强硬反应。正如印度专家战后分析的那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及他的国防部长V·K.克里什那·梅农(V.K.Krishna Menon)自以为是地相信即使印度奉行‘前进战略’,中国也不敢进攻印度。前进战略和对中国不会作为的判断得到了当时的情报局长B·N.穆利克(B.N.Mullick)的坚决支持。不幸的印度前线的军队被命令扫荡比自己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很快他们就认识到:如果尼赫鲁宣布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不会坐以待毙。”
尼赫鲁借召开万隆会议和发起不结盟运动在第三世界树立起较高的威望,自以为是不结盟运动的的领袖,国际同情和支持在印度一方,甚至某种程度上还自恋有恩于中国;自恃印度军队作为英军的一部分参加过二战,并取得过不俗战绩;仗恃印度作为两大阵营的调解人与美苏都有良好关系,而中国与美关系敌对,与苏关系破裂。因此,斗胆挑衅,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尼赫鲁以麦克阿瑟式的狂妄,低估了中国的决心和能力。尼赫鲁以己度人,投机取巧,想借中国“内外交困”大捞一把,结果没想到被对手毛泽东将痛击印度当成“解困脱套”的一招棋,趁着美苏缠斗于古巴导弹危机而无暇顾及,结结实实地给了印度一个又狠又痛、印象深刻的教训,并为其正在酝酿的中国内外政策重大调整提供了根据。战争失败后两年,年事已高、郁郁寡欢的尼赫鲁就因病去世了,为自己的自负、误判和投机付出了代价。
4.大国势力的挑唆和印度的挟洋自重
20世纪50年代,遏制中国、证明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性是美国发展对印关系的一项重要考虑。美国希望通过援助,帮助印度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胜出,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封堵共产主义跨越中国边界继续南下的路,保障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与影响力。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任内,美印之间的经贸关系、军事合作以及科技文化交流都有相当水平的提升。据统计,1959年至1962年,美国答应给予印度的援助增加到40亿美元,比此前12年间总和的2倍还要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美国向印度提供了9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包括轻型山地炮、防空雷达、通讯设备、运输机和直升机等武器装备。
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把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视为其与第三世界国家友好关系的核心以及苏联南亚政策的基石。1959 年8 月,在印度挑起第一次中印边境武装冲突的“朗久事件”后,赫鲁晓夫认为“是毛(泽东)本人挑起同印度的纠纷”,“正义和真理在印度一边”塔斯社则发表声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试图阻挠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在赫鲁晓夫访美日程刚刚敲定之际“使局势复杂化”。“塔斯社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明显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不是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印度发动的武装挑衅,而是谴责面临挑战的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一致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尚属首次。”苏联还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即中苏边界与中印边界都涉及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苏联担心中国随后也会对在沙皇时期丧失的土地提出要求。
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1959年9月10日,塔斯社声明中称中印边境事件是“可悲”的,含蓄地表达了反对中国的立场。9月30日,赫鲁晓夫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表示,“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10月2日,中苏领导人会谈中就中印边界冲突发生了激烈争吵,赫鲁晓夫蛮横地表示:“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赫鲁晓夫回到海参崴后随即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中国“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在10月31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境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抹杀印度挑衅的责任。“11月7日,赫鲁晓夫在同印度《新世纪》周刊记者的谈话中进一步表示,中印边境事件是‘一件不愉快和极其愚蠢的事情,没人知道边界在哪里,而且争吵的地区是无人居住的’。他还引用苏联同伊朗解决边界问题的例子说,‘我们就是通过得少给多的办法来解决我们同波斯的争执的。但是,多这几平方公里或少几平方公里,对像苏联这样的国家又算得什么呢’,以此暗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领土,满足印度的要求。”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升级,苏联加大对印度的援助力度。1959年,苏联给予印度近30亿卢比的贷款,供其开展第三个五年计划,到1963年,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共计达到50亿卢比。苏联还从1960年开始,多次与印度签署协议,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或出售技术先进、规模庞大的武器装备,包括米格-21型战斗机和安-12型运输机。
美苏的介入增加了印度无理边界要求的不妥协性,同时导致印度挟洋自重,漠视中国的和谈诚意与警告信号,在边界问题的立场上越来越强硬,不断挑战中国的底线,结果遭到迎头痛击。
(二)缅甸现实主义的地缘认知和维护现状的领土政策
1.缅甸基于现实主义的地缘认知主动与中国修好
缅甸当时也对新中国怀有疑虑,担心中国向缅甸输出革命和进行领土扩张。吴努总理在其第一次访华时表示:“中国好比大象,缅甸好比羔羊。大象会不会发怒,无疑会使羔羊提心吊胆。”独立后的缅甸,一方面国内面临着少数民族的分离要求;另一方面,缅北地区盘踞着从中国流窜到此的国民党残军93师,这些因素让缅甸意识到,与新中国建立发展友好关系对缅甸的国家统一和国内安全至关重要。缅甸对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和力量对比有着清醒的认识,缅甸政府和领导人积极发展缅中关系,持续的友好往来和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访,使中缅双方的友谊与信任不断增强。195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缅甸时,缅甸总理吴努首先向中国提出了早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愿望。经过友好商谈,双方达成协议并于6月29日发表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中两国总理“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2.面对冲突,缅甸接受中国管控危机的合理建议
1954年中缅开启边界谈判。谈判中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中方认为中缅边界南、北两段都存在问题,而缅方认为“北段是未定界,南段的边界已定”,欲让中方接受南段“1941年线”的既成事实。1957年,缅甸总理吴巴瑞曾直接给周恩来写信,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缅甸独立时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边界状况,即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在中段把勐卯三角地无条件地交由缅甸支配。仅有的修正是,在北段把包括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50平方英里土地交还中国。
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追击国民党军队的过程中进驻了“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1955年11月,中缅军队在“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了武装冲突,缅甸亲美的《民族报》发表头条新闻,说中国军队正向缅北侵犯,西方国家媒体也大肆炒作中国侵略。该事件震动了中缅两国政府,双方都认识到,合理解决边界领土问题刻不容缓。为了和缓气氛,中方建议,中方先从有争议的“1941年线”以西地区撤回所驻部队,但缅甸军队不得进入;作为交换条件,缅方也要从北段连英国也承认主权属于中国的片古岗地区撤军,中国军队也同样不能进驻。缅方接受了中方这一管控危机的合理建议,中缅边界紧张局势得到缓解,为谈判互信创造了条件。
3. 缅甸赞成和平解决边界领土争端的原则,同意与中国互谅互让,一揽子解决问题
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政府希望将解决中缅边界模式树立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典型,缅甸政府对此给予了响应。在原则上,两国在边界问题中采取了和平谈判、互谅互让、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的态度;在技术上,双方采取了适合中缅边界情况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考虑到中缅三段争议边界每一段的单独解决都有相当难度,周恩来向缅甸提出三段边界一揽子解决的方案,缅甸同意接受此种方案。事实证明,一揽子方案有利于双方利益的相互调整,双方秉持互谅互让、有舍有得的精神,承认彼此的利益存在和利益要求,而不强求单方面利益的最大化和边界诉求的百分之百实现,最终取得了双方都较为满意的成果。中方在北段未定界、“1941年线”、勐卯三角地等问题上做出让步,缅方则将英国侵占的片古岗地区和班老、班洪部落归还给中国。
4.缅甸坚持双边谈判框架,受国际因素干扰较小
相比中印,中缅边界问题较少受到国际干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缅边界发生黄果园冲突时,美国和西方曾趁机挑拨中缅关系,给冲突事件贴上“‘弱小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等标签,但缅甸政府对美国的声援不为所动,拒绝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继续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中缅在谈判过程中也曾遇到波折,例如1958年由于缅甸内政原因双边谈判搁置、印度曾试图联合缅甸在“麦线”问题上施压中国,但缅甸很少采用错误的地缘政治思维来鼓吹中国威胁,能够及时安抚国内的反华情绪而不致影响双边关系,更不曾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这些都是双边关系实现友好互信、和平谈判稳步推进的重要原因。而且,缅甸在谈判遭遇挫折时,也不曾像印度一样发起“照会战”,单方面将双边谈判内容公之于众,自然也就不会招致过多的国际关注与干扰。
(三) 中国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的原则和睦邻友好的地缘政治方针
1.新中国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与稳定周边、争取有利环境有机结合
边界划分的实质是国家利益的划分与调整,除了现实意义上的领土、人口、资源等直接利益,还会考虑长远的边境地区安全环境、两国关系未来亲疏、经济贸易交往发展、国家声誉与形象塑造等潜在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处于冷战环境,因此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时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不仅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要考虑到安定四邻、稳定周边,争取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和平环境。因此,新中国一开始就确定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与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基本原则。在原则上,不承认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在现实中,可以以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基础通过谈判互谅互让和平解决边界问题。
因此,新中国将现实与长远、直接与潜在利益相结合,当对方仗恃武力谋求其边界领土诉求时,中国态度就针锋相对,不排除必要时以打促谈,动用适度武力迫使其接受中国的和平协商主张;反之,如果邻国同样采取谈判妥协,互谅互让的边界领土政策,中国就会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在明辨历史的前提下,尊重边境现状,宽和对待邻国的划界要求。中国学者聂宏毅和李彬将其特征归纳为“强硬对扩张,宽和对现状”,即如果邻国奉行扩张性边界政策,中国的态度就趋于强硬。反之,如果邻国奉行维持现状的边界政策,则中国的政策选择则倾向于宽和。“对扩张国态度强硬的弊是可能短期内出现严重军事对抗,利是遏制其扩张野心。对现状国宽和,虽然可能出现局部边界调整和牺牲,但是,这种宽和可以消除其恐惧感和威胁感,防止其与其他国家结盟,有利于中国边界的长久和平。”“实践证明,互谅互让各有所得,边界问题容易解决。而得寸进尺,寸土必争,斤斤计较,这只能使边界问题陷入僵局。”
2.中缅边界问题的和平处置确立了互谅互让、一揽子解决的范式
在新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历史遗留的与邻国间的边界问题中,首先解决的是中缅边界问题。当时周边不少新兴独立国家对新中国怀有疑虑,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刻意挑拨离间,散布中国侵略扩张,输出革命的舆论。“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根,发挥自己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必须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建立睦邻关系。从国际战略的全局出发,新中国政府提出以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为契机,为解决与邻国存在的其它问题积累经验。”周恩来总理1957年多次谈到中国解决缅甸边界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示范作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一些亚洲国家担心,认为大国必然扩张。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争取和平共处,在10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陆续解决,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尽快以和平共处精神同缅甸解决边界间题,这对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无疑是釜底抽薪,对缅甸这类不受帝国主义唆使的友好国家,也是一个鼓舞和支持”;“我们把中缅边界谈好,使四邻相安,这样可以起示范作用,争取亚洲国家和平共处,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使我们国家强大起来,这是最基本的要求”。“由此,可清楚地看出,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符合我国国际战略的总体利益。中缅两国都把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作为各自实施整体国际战略的重要步骤,这就能使双方超脱一田一水、一村一寨的‘斤斤计较’,从全局的高度来对待和实施‘互谅互让’,从而使边界谈判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
缅甸认同中国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则,不利用边界问题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同意在一揽子的框架内相互调整利益,使中国的善意与让步得到应有的回馈。双方在谈判中互谅互让,一起为边界争端的缓和与最终解决创造了条件。周恩来总理“将中缅边界问题‘当作麻雀来解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主持中缅边界谈判,并探索出了一套‘鉴定争端——维持现状——互谅谈判——签定新约’的解决模式”。所谓“‘互谅互让’实质上就是利益上的互谅互让,只有彼此间承认对方利益的存在,在得到一定利益的同时也让出一部分利益,才能使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否则,边界问题就难以解决。”
“中国从自身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在中缅边界谈判中较好地照顾到了缅甸的利益也是中缅边界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在谈判中提出的划界方案是:中缅边界北段,从伊索拉希山口以北到底富山的部分,可以按照习惯边界线为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古浪、岗房应该归还中国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划定边界,其分水岭即高黎贡山及其支脉姊妹山、狼牙山。但是此划界方案与旧中国地图上的中缅边界画法差距巨大。当时,中国国内许多人据此认为“失地太多”、“吃亏太大”,希望“改变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周恩来总理在详细调查研究和勘察考证的基础上,对旧中国地图上中缅边界北段画法与实际控制的现实的差距作了客观分析。为了澄清事实和安抚国内舆论,周恩来在1957年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回顾了中国地图对中缅边界画法的变迁。清朝道光和光绪年间的官方地图上,所标边界均在高黎贡山脉处。到民国时期,由于受到片马事件的刺激,1917年出版的《中国新舆图》把江心坡划入中国版图。1942年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地图,在南段承认“1941年线”,北段则把边界划到了枯门岭,但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并未控制高黎贡山以西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图出版社1953年委托私人出版的地图也把边界划在高黎贡山以西,但声明“南北两段边界都是未定界”,且“地图未经政府审定”。周恩来表示,这五张图的变化“说明我们(的)地图是一件事,实际的情况是一件事,交涉又是一件事。这三件事并不吻合”。对于地图则“不能追溯得太远”,而应“以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资料作为重要参考”,还要区别其真伪及可靠程度。国民党当年在英国的压力下承认了南段的“1941年线”,但为了掩饰其退让,又在地图上弄虚作假,“把北段的未定界尽量往西划,扩大了7万多平方公里,其实这些地方中国的统治一向未到达过”,因此1942年版地图不能作为划界的根据。在互谅互让问题上,周恩来赞扬了地方政府和群众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同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爱国主义立场,认为“与帝国主义必须寸土必争”,但也指出要争取已经独立而且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民族主义国家缅甸,防止帝国主义挑拨离间。“我们提出的解决北段的要求不能过高。我们的历史根据和政治理由必须结合起来,取现实的态度来解决。”“做到使双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而不在于我们必须多占一点地方。”“中缅边界谈判时中国不仅面临着迫切的建设任务,而且在国际上受到美国的封锁和包围,谈判期间中苏关系和中印关系的恶化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外交上的困难。为了打开外交局面,争取国际形势与周边安全形势的和缓, 中国在与缅甸的边界谈判中始终秉持宽宏大量,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对缅甸作了一些让步”,然而这一让步是实事求是的。中缅边界划定的结果表明新中国对周边邻国并不存在领土野心,中国政府追求的不是扩大领土和天然屏障,而是边界的划定和与邻国的和平共处,从而消减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扩张”的疑虑;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的大国风范与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真实性。“中缅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现代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准则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新范例。”
3.中印边界问题的武力处置确立了捍卫底线、正当防卫、教训震慑的范式
在中印问题的案例中,中国对印度原本奉行的也是和平谈判方针,能和平解决绝不动用武力。1959年5月,毛泽东曾向尼赫鲁捎话透底,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具有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以中国大使潘自力名义致印度外交部的书面谈话指出“中国不能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同年9月,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也全面阐述了中方立场:“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
但是反观印度,它执行庇护藏独、试图建立“缓冲地带”的地缘政治战略;它不尊重实际控制线、推行武力打破现状的“前进政策”;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无视中国“以东换西”方案做出的巨大让步,坚持“无需谈判”的不妥协立场;它挟洋自重,利用中国内外困难频频挑衅的机会主义做法……最终突破了中国核心利益的底线,把中国逼到了墙角。毛泽东在战后谈到中印冲突时说:“印度整了我们3年,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有4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使它知难而退,才可以暂时和缓。”
1962年的中印边界反击战中,中国军队主要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并没有深入印境,反击成功后乘胜即收,主动撤兵,又回到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之内,并要求印度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一举动再次向世界昭示了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立场。中方虽然坚持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拥有主权,但没有占领一寸土地,依然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的政策,将军事行动的目标严格控制在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上,体现出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和掌控局势的灵活性。
发动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目的并非是中国要以武力来解决边界领土问题,而是在所有和平渠道被堵塞的情况下,不得不以有限的反击行动来惩戒和遏阻印度的玩火行为,促使其悬崖勒马,重新回到和平谈判的轨道上来。应战是和平手段用尽情况下的唯一选择。“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政治而不在于军事,但是军事上的胜败却是政治和外交上是否有利的必要条件。中国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胜利,既将印度打狠打痛,更将其打醒打怕,使其认识到:用武力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行不通的,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得到的只能是沉重的打击。”
中方之所以实施单方面撤军,主要还是根据既定战争目标行事。因为中国军队进行自卫反击战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为了收复被蚕食的领土,而是为反击印度的边境挑衅。在通过有效的军事行动,把印军推回去后,预定的目标已经达到。对于中印边界之战,毛泽东评价说,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30年的稳定。中国“以将对手‘打狠打痛’的方式给其教训,争取了西部边境长期的安定’”。“对印实施反击作战的经过,体现了毛泽东处理边界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在采取外交方式阐明中国力求维持现状的立场时,必要时也以武力向对方传递信号。使用武力的方式又分为威慑、实战两种,分别视危机的严重程度而定,同时严格限制其升级。随后,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措施,证明化解危机的努力基本还是成功的。”从1962年迄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尝到了血的教训的印度未敢再猖狂“前进”。
中印边界反击战带有教训、惩戒、震慑、迫和的作用,主要目标是以打促谈,以攻为守。近年来对中国主动后撤的原因反思研究颇多,都有其合理性,但较少与当初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联系起来考量。1960年中国方面向印方提出的“以东换西”方案,是以中国宣布的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基础提出的。1962年边界战争中,中国军队在占领了“麦线”以南,中印传统习惯线边界以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情况下,全部撤回到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以北20公里,是要再次表明中方不打算以武力改变实际控制线现状的真诚立场,并打算以此为基础,重开中印边界谈判,尽早解决边界问题。但遗憾的是,认为遭到“奇耻大辱”的印度当局为了面子,当时仍旧不肯走上谈判桌,直到十多年后才终于明白和平谈判是唯一出路,姗姗来迟地走到谈判桌前。
1976年中印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1988年12月,印总理拉·甘地访华,双方表示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和条件。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为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先后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宣言。1993年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6年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明文规定“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2005年签署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实施办法的议定书》;2012年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2013年签署了《中印边境防务合作协议》。目前,中印边界领土问题虽然尚未解决,但两国都表示同意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正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最终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不过,双方对具体解决方案还存在很大争议,边界矛盾也时有发生,中印边界问题的彻底解决还需要时间。习近平主席2014年9月访问印度时指出:“在边界问题上,双方要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寻求公平合理、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前,共同管控好争议,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发展。”印度总理莫迪回应说:“印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管控好边界争议,加快推进边界问题谈判,早日找到解决方案。”在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以及双方的联合公报都再次谈到中印边界问题需要妥善处理与和平解决。
4.“一文一武”两种处置范式是中国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宝贵财富
处理中印、中缅边界争端“一文一武”的两个案例,为以后中国与邻国的边界领土争端的解决提供了范式。这种从上述处置范式中提炼出的决策模式,被应用于中国与其他邻国边界领土争端问题的处置和解决中。秉持中缅边界和平解决范式的政策与策略,中国先后同尼泊尔(1960年)、蒙古(1962年)、巴基斯坦(1963年)、阿富汗(1963年)、朝鲜(1964年)等国家和平谈判,互谅互让划定了边界。对曾采取类似印度对华边界政策的前苏联和越南,中国都进行了“边界自卫反(还)击战”。而20世纪90年代后又陆续与曾经武力相向的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前苏联国家互谅互让和平谈判解决了边界问题。曾经进行边界战争长达十年的中越之间,最终也是通过和平谈判互谅互让解决了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上划界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邻国海岛主权与海洋划界争端加剧,关于中国当年处置解决中缅中印边界问题的回顾与反思不断,有中缅边界最后解决方案对缅让步太多和中印边界战争胜利后不该撤军的多种议论,但以今天中国的崛起力量和国际环境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当时的情况是强人所难和违背历史客观的。世界格局是逐步演变的,国家力量对比是不断变化的,人们的认识也是不断前进的,解决问题的模式也不能一成不变。今天中国处置和解决海洋争端的模式不可能完全照搬当年解决陆地争端的模式,但中缅中印模式中包含的被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方针与原则、政策与策略、理论与实践,仍旧是中国处置和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宝贵财富。
【注释】
[1][14][16][18][40][41][45][47] 赵磊:《中印、中缅边界问题比较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第577页,第483页。
[4]《周恩来总理会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谈话纪要(1956年8月25日)》,中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5-00307-03(1)。
[5]张植荣:《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反思——杨公素大使访谈录》,《当代亚太》2000年第8期。
[6][7]〈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7页,第356页。
[8][19] 随新民:《印度对中印边界的认知》,《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
[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72页。
[10] Pravda,ThetruthabouthowtheleadersoftheCPSUhavealliedthemselveswithIndiaAgainstChina,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Peking,1963,p.72.
[11] 《1962年中印战争印方最新观点》,中华网,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dljl/zhongyin/01/11045907/
[10]20060405/13222976.html
[12] 〈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郑经言译《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南亚研究》2000年第1期。
[13][38] 聂弘毅、李彬:《中国在领土争端中的政策选择》,《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
[15] 〈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第179页。(作者与注[12]是同一人,但译者介绍的作者的国籍不同)
[17] 邱美荣:《边界功能视角的中印边界争端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2期。
[20]《印度将军的反思:1962年边境战争为什么输给中国》,2010年8月6日,http://bbs.tiexue.net/post2_4401495_1.html
[21][22] 张敏秋:《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57页,第264页。
[23] 邱美荣:《1959—1962的中印关系: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6页。
[24] 〈苏〉赫鲁晓夫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市政协编译组译《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466-468页。
[25]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5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14页。
[26] David Floyd,Maoagainstkhrushchev-AshorthistoryoftheSino-Sovietconflict, New York:Praeger, 1963,p.74.
[27] 关培凤:《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缅边界谈判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8] 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266页。
[29]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30]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3页。
[31] 人民日报编辑部:《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页。
[32] 《瑞典舆论对中国同印度边界问题的反应(1959年11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10-00825-02 (1)。转引自关培凤《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对中缅边界谈判的影响》,《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
[33] Bimal Prasad,Indo-SovietRelations, 1947-1972:ADocumentaryStudy,Allied Publishers,1973,p.143.
[34] Rajesh Rajagopalan,TheSino-IndianBorderConflictof1962:AStudyofIndia’sStrategyandDiplomacy,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Dissertation,1988,pp.54-55.
[35][62][63] 徐焰:《解放后我国处理边界冲突危机的回顾和总结》,《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
[36]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37][49][51] 金冲及:《周恩来传》(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88页,第1182页,第1181-1184页。
[39] 聂弘毅:《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57页。
[42][43][44] 裴坚章:《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97页,第96页,第97页。
[46] 朱向春:《试论影响中缅、中印边界问题解决的因素》,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内容提要、第12页、第31页。
[48][53] 关培风:《中缅边界谈判研究》,《史林》2014年第1期。
[50] 于海洋:《〈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始末》,《党史天地》2001年第1期。
[52] 周恩来:《中缅边界的报告》,《人民日报》1957年7月10日。
[54] 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4页。
[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
[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年,第376页。
[57]《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人民日报》1959年9月10日。
[58] 《阴法唐将军讲述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亲历记》,凤凰网资讯,http://news.ifeng.com/mil/media/detail_2010_04/07/513362_0.shtml
[59] 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上的发言,1962年11月24日,转引自廖心文:《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对策方法——老一辈革命家与边界问题研究之三》,《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
[60][61] 王学军,赵力兵:《透析1962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政治战本质》,《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
[64] 江涛、陈莎:《中塔与中印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65] 《中印签署〈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17/c_111445915.htm.
[66] 杜军帅:《辛格访华成果丰硕为两国关系注入新活力》,国际在线,http://gb.cri.cn/42071/2013/10/25/7211s4297792.htm
[67] 《习近平亚洲之行亮点纷呈从A到Z逐个数》。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920/c1002-25699417.html
【责任编辑:邓仕超】
Keywords:Sino-Burma Border; Sino-India Border; Method in Dispute Resolving; Peaceful Solution; Military Solution
[中图分类号]D8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5)06-0043-13
[作者简介]杨勉,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乐,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