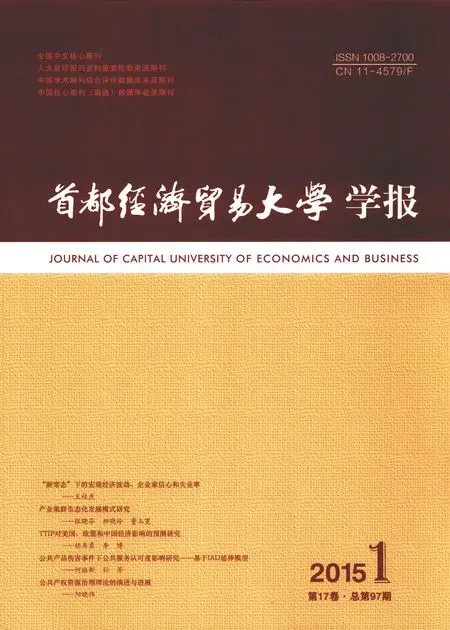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中的应对策略
穆丽霞,胡敏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 青岛 266580)
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中的应对策略
穆丽霞,胡敏敏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东 青岛 266580)
在国际碳交易中,中国缺乏核证减排量(CER)的定价权,主要由于国内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弱、碳交易项目类型过于单一、碳交易项目受制于欧美发达国家对CER的需求、国内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滞后。因此,中国应当采取在国际碳交易定价中的积极应对策略,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确立自愿减排和配额相结合的交易机制,发展碳金融衍生品及其服务,战略性储备碳排放权资源。
碳交易;定价权;项目交易;配额制
引言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允许采取的四种碳减排方式中,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清洁发展机制(CDM)与发达国家进行相关项目合作,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目前,中国已经成为CDM一级市场的主要供应方。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所提供的数据统计,截至2014年8月31日,中国已注册成功了3805个CDM项目,向买家签发了6.27亿吨当量CO2的初级核证减排量(pCER),注册CDM项目量和pCER签发量均排名第一[1]。据联合国EB官网数据,2014年5月28日,世界银行《碳市场现状与趋势2014》报告,全球有39个国家和23个地区已经或者计划实施碳定价工具,包括排放权交易系统和碳税。全球的排放权交易系统价值约300亿美元,其中中国已在布局全球第二大碳市场,覆盖了11.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银行集团及其他参与者鼓励各国、地区和企业加入并联合支持碳定价。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只是参与CDM项目的初级市场,并且缺乏核证减排量(CER)的定价权,因而处于CDM产业链的价格低端,难以在CDM项目中获得丰厚的收益。因此,分析国际碳交易定价的影响因素,争取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定价权,对于中国CDM项目企业利益的维护以及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的定价
在经济学中,碳交易定价的方法有总量管制及贸易体系、碳税、基准与排放额度、项目机制等。总量管制及贸易体系(cap-and-trade system)是一种取决于环境容量的碳定价机制,对碳排放总量进行绝对的控制,具体地说,就是先针对特定环境区域设定总的碳排放限额,然后再决定本环境区域内的碳排放单位的碳排放许可证数量。实行这一体系的主要有:美国东北部的州电力部门、欧盟EU-ETS、新西兰经济体。碳税(carbon tax)定价的实质是将碳排放的外部经济成本转化为内部经济成本,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税的碳定价机制是基于价格控制而形成的。实行这一体系的主要有:加拿大BC(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挪威离岸工厂、澳大利亚。基准与排放额度(baseline-and-credit)是对总量通过项目形式进行相对的控制。若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低于预先设定的排放基准,就可以获取相应的碳信用。项目机制(project mechanism)开展碳减排项目,如项目的减排效果强于基准排放量,则发放核准的碳信用。碳信用可在总量管制体系中作为履约工具使用[2]。
目前中国碳交易活动主要是通过清洁发展机制来进行,具有国际减排承诺的发达国家为了降低本国的自主减排成本,以技术转让或资金援助的形式,与发展中国家达成协议,由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实施各种环保项目,形成可以买卖的CER,以实现发达缔约国履行议定书的减排承诺。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的CDM项目会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流通。在CDM一级市场上的交易主要表现为远期交易,交易双方共同约定在特定时间、以特定价格交易特定数量的pCER。在CDM二级市场上的交易是在远期合约签订之后,或者联合国执行理事会签发后,交易标的为sCER。sCER属于标准化合约,价格透明,在CDM市场上占据主导位置[3]。
二、国际碳交易定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碳交易中定价的商品就是碳排放权。碳排放权是一种无形的虚拟商品,只有通过特定权威机构的核证才能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商品,因而,这类商品的成本价格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生产成本,其交易成本和风险成本才是主要的成本价格。
1.需求与供给因素
供求关系是商品交易过程中基于诸多因素制约而形成的,它直接影响着商品的价格。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曾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主要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通过供需双方的相互牵制,建立起均衡价值论[4]。从经济学视角讲,碳市场中的碳排放定价权取决于碳排放权的供给者和碳排放权的需求者之间的利益博弈。遵照2008年《京都议定书》的排放量削减规定,2008—2012年发达国家应进行5.2%的温室气体削减。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结束。在2010年坎昆会议上,发达国家在影响既得利益的实质性问题上不肯做出让步,拒绝或敷衍发展中国家的合理要求。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形成决议,实施《京都议定书》中商定的第二承诺期,以发达国家的资金投入为前提,及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以推动碳减排。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确定2013—2020年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是,面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到来,发达国家却不愿意为绿色气候基金的设立承诺具体的投入资金数额。2013年华沙气候大会强调了落实巴厘路线图成果的重要性,并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希望提高2020年前的碳减排力度。每年的国家气候大会协议都会对全球范围内的碳交易发展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也直接影响碳交易的供需关系。
2.各国的利益博弈因素
在每次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各个国家都谋求着各自利益最大化。在后哥本哈根时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为碳减排行动中的两大对抗性阵营,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遵循《京都议定书》中各国的碳减排承诺?如何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减排的平等?在后京都时代,供需双方的谈判表面上是关于温室气体排放额度的谈判,但其实质是国际碳交易定价权的一场博弈。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找到最优的策略,这种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必然影响国际碳交易定价权的制定。
3.国际价格及投机因素
国际碳交易市场定价很大程度受到欧盟排放交易市场的影响。该市场碳排放权衍生品的价格风险通过EU-ETS市场直接传导至CDM市场。国外的投资机构通过在中国参与CDM项目,将项目获得的碳减排量转移到欧洲的CDM二级市场进行投机性交易,赚取更多差价。从世界银行《2007—2012年碳市场现状与趋势》报告中可以看出,CDM一级市场交易额变化并不大,但CDM二级市场的交易额在剧增。CDM一级市场从2005年的24亿美元交易额到2011年的30亿美元的交易额,增长了25%;而CDM二级市场从2005年的2亿美元交易额到2011年的223亿美元的交易额,增长了110倍[5](见表1)。
4.能源价格因素
碳交易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还有能源价格,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的增加和碳排放量的强制削减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所以,碳交易价格通常会随着能源价格的涨跌而随之发生相应变化。所以,要保证碳交易价格的稳定和适度增长,应当建立建全能源定价体系,适当提高能源价格,降低能源的市场需求[6]。
三、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中失语的原因分析
1.国内企业的议价能力较弱
中国是国际CDM项目的最大供应方,但是,由于中国国内企业主要通过CDM项目运作分散地参与国际碳交易,在成本核算、国际碳交易价格及走势方面的信息缺乏;同时,这些企业也把CDM项目视为一本万利的项目,自己不需要支付经济成本,而未来碳减排资源的转让收益就是自己项目的额外收益,缺乏未来面临高价回购的风险意识。在缺乏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平台的前提下,CDM项目的区域性明显,使得中国CDM项目企业处于国际CDM产业链的底端。而国际上的买家在低价购买后,通过注册、签发,转入CDM二级市场,包装成碳金融产品进行流转,获取更大的收益。
数据来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的CDM项目数据库系统。
2.碳交易项目类型过于单一
中国目前已经注册成功的项目主要集中在风能、水电、沼气等节能和高能效的低端领域,这些资源利用型项目多为技术含量低、收益稳定[7];而其他升级改造项目由于减排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的却鲜有问津。但大量资料表明,单纯的CDM项目不能成为引导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市场机制[8](见表2)。
3.碳交易项目受制于欧美发达国家对CER的需求
CDM项目是基于《京都议定书》协助发达国家履行碳减排承诺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对碳减排配额制的一种有效补充方式,因此,在CDM市场交易价格博弈中,欧美发达国家的CER买方市场始终是占据主导地位。2011年欧盟碳排放权配额占全球碳市场交易额的84.03%,这原本会给予发展中国家CDM项目发展带来机会,但发达国家为了控制CER交易总量,限制了ERU与CER之间的替代性,更进一步控制着CER定价权。《欧盟排放指令》规定了抵消机制,使得《京都议定书》中CDM项目下产生的CER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强制减排下分配的ERU可以抵消使用[9]。同时,欧盟确定,在2008—2020年间抵消减排量不能超过整个欧盟范围总减排量的50%,参与者考虑到原有排放设施和这段时间内可能新建的设施,最多可以购买配额11%的碳信用来抵消多余排放量[9]。
4.国内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滞后
中国经联合国核准的节能减排项目卖给西方国家的碳排放指标均为现货,而能够作为期货销售的产品基本不存在。由于缺少金融业的介入,在现货交易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更是没有碳期货、碳基金、碳证券等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务的支持,导致国内企业在谈价格谈判中缺乏定价的参照系。
四、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行动中的积极应对
进入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的诸多变数使得中国开展CDM项目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前景难以预估。对此,要实现碳减排目标,把握中国碳市场未来发展主动权,必须谋求国际碳交易定价权。
1.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2013年6月19日重庆碳交易所正式开市交易之时,中国的七个试点的配额总量达到约12亿吨,控排企业约纳入2 000余家,成为继欧盟之后的第二大碳配额交易体系。截至2014年5月30日,深圳碳市场共成交超38万吨,总成交额为2 744万元,占全国成交额的19%,成为全国交易量最大的碳市场[10]。虽然轰轰烈烈,但与欧美国家的碳交易市场相比,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分散而隔离,不论是在功能上还是在规模上都与国际市场有很大差距,因此,在中国组建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迫在眉睫。
2.确立自愿减排和配额相结合的交易机制
碳减排法律制度框架的搭建,从规划、制定到实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经历了数年的省级碳交易试点,但中国碳减排领域的减排模式比较单一,更多还是以自愿减排作为主要的减排模式。因此,以目前的试点经验为基础,可以借鉴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经验,构建中国的自愿碳减排标准。作为全球第一个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交易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二大碳汇贸易市场,也是美国唯一认可CDM项目的交易系统。2006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制定了《芝加哥协定》,该协定明确了建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目标,确定了协定的覆盖范围。该交易平台有可操行性强的制度框架及交易细则,拥有覆盖范围广泛的会员实体以及结算迅速、价格透明公开的交易系统。在具体操作上,要求政府对企业碳减排需要增加的经济成本予以一定量的补偿,并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效益补偿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的多重作用下,提高企业自愿参与碳减排交易的能动性[11]。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应当改变目前单一的碳减排模式,构建具有一定强制性或者自愿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碳交易运行机制。应当尽快搭成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平台,在强制性碳交易运行机制中,设定具有强制性的碳减排标准,对不同类别的行业确定不同的碳排放强度,逐步调整并扩大强制性减排机制的适用范围;逐步将国内碳交易市场和国际碳交易市场接轨[12]。
3.发展碳金融衍生品及其服务
中国在国际CDM项目定价中缺乏话语权,主要是因为缺少基本的碳金融工具。碳金融衍生品具有明显的价格发现、风险转移和提高市场流动性功能,可以通过对碳市场的参与调节碳交易价格。通常的国际惯例看,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产生,一方面取决于一级市场的供需,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二级市场的流动性。碳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变市场单边运行状态,使碳排放价格随着投资需求变化而变动,有效改变一级市场的供需关系,形成平衡的供需市场。因此,具有社会责任感的金融机构应当及时更新观念,开展与碳交易相关的金融活动,设立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平台,开发以CER为基础的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价格发现机制,以有效应对后京都时代全球碳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13]。
4.战略性储备碳排放权资源
将中国碳排放交易资源进行一定规模的战略储备,以国家战略投资形式收购碳排放交易,以便争取在国际碳交易定价中的话语权。在这方面,印度以政府为主导的CDM单边碳策略可供中国借鉴。从2005年起,印度采取了“单边碳策略”,把注册成功的CDM项目所产生的CER进行国家战略储备,以供未来承担国际强制性碳减排义务时使用或者选择合适的价格出售,以此控制碳市场价格,减低未来的碳减排成本[14]。在实施碳储备之时,要合理确定碳排放储备的量。储存量的过大或过小都不足以对碳排放价格形成有效的控制,会妨碍碳储备的碳交易定价调整功能的发挥[15]。
五、结语
全球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更高的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对碳排放权的需求会在相当长时期处于增长态势。因此,应看到碳交易市场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碳排放交易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实现与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对接,以争夺在国际碳交易中的定价话语权。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CDM项目数据库系统[EB/OL].[2014-08-31]. http://cdm.ccchina.gov.cn/NewItemTable9.aspx
[2] 杨帆.国际碳定价机制研究及其启示[J].商业时代,2012(4):131-132.
[3] 郇志坚,梁艳.中国碳市场发展及其定价策略研究.金融发展评论,2011(3):143-152.
[4] 马歇尔的均衡价值论[EB/OL].[2008-08-24].http://wiki.mbalib.com/wiki/.
[5] 世界银行《2007—2012碳市场现状和趋势》报告[EB/OL].[2012-06-01].http//cn.chinagate.cn/worldbank/2012-06/01.
[6] 胡小娟,赵倩.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方式碳排放——基于投入产出法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4):22-26.
[7] 高山.碳排放交易价格问题研究[J].市场经济与价格,2013(2):16-19.
[8]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的CDM项目数据库系统[EB/OL].http://cdm.ccchima.qov.cn/.
[9] 邹伟进,王向东,朱冬元.碳交易定价问题研究进展[J].理论月刊,2014(3):149-152.
[10] 杨晓华,张宏艳.印度碳市场构建对我国谋求碳交易定价权的启示[J].特区经济,2011(11):122-123.
[11] EU Linking Directive. Directive 2004/101/EC,OJL338/18[EB/OL].[2012-05-15].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
[12] 邹亚生,孙佳.论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11(7):124-134.
[13]王梦夏.低碳经济理论研究综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3(2):106-111.
[14] 李曼莉,王晓.论碳交易定价的域外经验及我国的实践[J].求索,2012(8):11-13.
[15] Wor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R].Washington,DC,2010.
(责任编辑:蒋 琰)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Trade Pricing
MU Lixia,HU Minmin
(College of Arts,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trading, China lacks the pricing right of CER, due to the weak bargaining ability of domestic enterprises,the simplex of carbon trading type, the subjection of carbon trading project to demand for CER of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developed countries,and the lagging of domestic carbon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refore, positive cop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adopted in international carbon trade pricing to set up a unified national carbon trading market and establish the trading mechanism combining 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 and quota. In addition, China should develop carbon financial derivatives and services and reserve carbon emission rights resources to ensure more pricing right of CER.
carbon trade; pricing right; program trading; quotas
2014-10-20
穆丽霞(1965—),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硕士生导师;胡敏敏(1991—),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硕士研究生。
F752.7
A
1008-2700(2015)01-005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