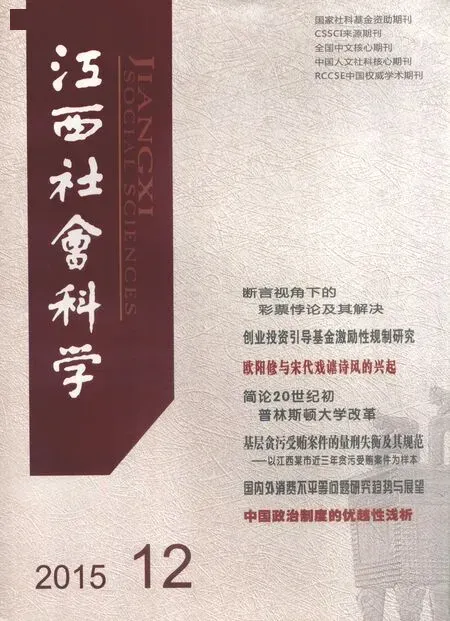死者名誉之刑事救济:间接诽谤的视角
■胡 杰
死者名誉之刑事救济:间接诽谤的视角
■胡 杰
“权利”与“法益”的概念需要予以区别,死者没有名誉权,但却拥有社会生活中的利益,对其社会评价也应当予以刑事救济保护;死者的名誉,更多的只是宗教立场的结论,刑法上对于死者名誉的保护,本质上是对遗族虔诚感情的保护;在死者的社会评价受到他人诽谤的场合,从间接诽谤的角度来说,同时可以认为是对死者近亲属名誉的损害,满足诽谤罪的犯罪构成。
死者名誉;诽谤罪;间接诽谤;法益
胡 杰,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江苏无锡 214064)
现代社会传统价值在道德层面的法律救济似乎稍显滞后,死者名誉的刑事救济途径的缺失就是一例。生存在世界上的人都具有名誉,那么死者是否具有名誉,却是刑事法理论上一直以来极具争议性的问题。[1]本文拟就死者名誉刑事救济的必要性、死者名誉刑法规制的理论基础、通过间接诽谤理论对死者名誉进行刑事救济以及制度设计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一、死者名誉刑事救济的必要性
在我国,对死者名誉权的民事救济,经过学界激烈的讨论,在学术界与实务界对死者名誉的民事法律保护已有定论。[2]然而,在我国,对死者的诽谤行为一直未作为犯罪予以规定,对死者名誉的刑事救济的学界讨论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名誉权在网络时代受到史无前例的侵犯与践踏,公民对名誉权的法律救济的需求也同时呈现上升趋势,在刑事法中对公民名誉权进行全面、深入保护是必须重视的问题,这其中也自然包括对死者名誉的刑事法律保护。
诽谤罪的“他人”如何理解,也就是诽谤罪的对象范围的界限,直接影响着诽谤罪是否成立。对诽谤行为,“人”显然是其对象。对活着的人来说,名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生命更为重要,它具有独立性和私有性。每一个新生的生命都会获得其社会地位,除了自己,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获得自己名誉的任何组成部分。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的名誉都是独有且与生俱来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元素,会在之后的生活中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成长与表现获得各种不同的变化。因此,法律对名誉权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名誉权作为公民人格权的组成部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法律必须予以有效保护。
对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一般来说,死者是没有名誉权的。所谓名誉权,生存是必要的前提,与人的死亡一起所有的权利也一起消失,名誉权作为死者一生专属的权利,继承他人的名誉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死者的诽谤行为,并没有侵害死者的名誉权这一法益,无论是与生俱来的名誉权还是通过自身努力所获得的名誉权,都会随着人的死亡而一起进入坟墓。这也是刑事法律对死者诽谤不予以刑事救济这一观点最为重要的支撑点。
死者固然没有作为人格权组成部分的名誉权,但是,对死者名誉的救济,将死者的名誉权保护与死者社会评价的保护进行概念的模糊与置换理解,是不合适的。具体来说,死者虽然自身没有名誉权,对死者名誉损害的行为,却是侵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行为。名誉作为对人的社会评价,在人死后依然存在他人的记忆之中。名誉在以社会评价形式出现的时候,往往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法益,未必以法律上的规定为限定,作为应当保护的价值,生活中的必要利益也应当成为法律上的所保护的权利。因此,在人死后所残存的社会评价作为一种法益是不能否定的。这种价值不仅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而且也具有物质意义上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种“社会评价”价值的保护,并不需要区分评价的对象是否具有现实的生命。因此,对社会评价这一法益来说,并不会因为评价对象的去世而失去社会价值。
在法律中,“权利”与“法益”的概念应当予以区别。作为法律上的“人”,权利能力从人的“出生”开始,并随着人的“死亡”而终结。出生之前的“胎儿”、死亡之后的“尸体”并不能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主体。权利的实体意味着具有法律上的“地位”,而法益的实体更多地意味着生活中的“利益”。因此,作为权利,有关其归属的主体,必须具有法律上的资格,也就是具有所谓的权利能力。但是作为死者,虽无权利能力,却拥有“法益”。所谓“法益”,作为社会生活上的利益,并不以拥有法律主体的地位为必要前提。“社会生活上的利益,并非法律上的资格的问题,某一主体是否具有社会生活上的利益的享受,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事实的问题。”[3]因此,死者虽然不能作为法律保护的主体,但是,对死者名誉的毁损,作为对法律所保护利益的侵害,同样也是损害刑法所应当保护法益的行为。
作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普通公民名誉的利益与死者的社会评价的利益,并没有本质区别,公民社会评价的利益并不会因为其去世而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法律对公民社会评价利益的保护与死者社会评价利益的保护应当是同样标准上的保护。因此,理论上对公民名誉权可以从刑事法层面进行救济,现实中却不允许对死者社会评价侵害的行为进行刑事法层面的救济保护,这是不合逻辑的。对死者名誉的诽谤行为,同样也是侵犯刑事法律的行为。对死者社会评价的侵害行为也是侵害刑法所保护社会关系的行为,也应当从刑事法角度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二、死者名誉刑法规制的理论前提
对侵害死者名誉的行为的理解,最初的思路是直接将死者的名誉权直接作为法益进行解释。具体来说,人在生物学上的死亡并未使一切人格关系全部消减。特别是在宗教表象的世界中,将死者的人格作为祭祀的对象是其显著的表现,[4](P269)但是其未必就限于宗教表象的世界中。社会学的名誉在人死后仍然是存在的,也是可以毁损的,与此相关的死者人格的存在,也需要法律上的保护。因此,死者的名誉在死后仍然是存在的,而在法律上予以保护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如前所述,死者本身是没有权利的,死者直接作为法益的主体从上述的解释中并不能得到“死者可以作为法益主体”的直接结论。
为了避免上述解释的困境,将死者的名誉理解为一种公共法益,而非个人法益,这样可以避免如何回答法益主体的问题,成为学者思考的途径。也就是说,死者的名誉,在其死后以社会一般追忆的形式存在。这种社会的评价应当作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应当予以尊重并保持,这种应当作为一种法益予以解释。因此,这种法益并不属于特定的人,应当属于一种公共法益的性质。[5]将死者的名誉理解为一种公共法益,这种解释虽然可以回避法益主体的问题,但是,诽谤罪作为有关个人权利保护的犯罪,有关死者的诽谤罪以侵犯公共利益作为解释是否恰当仍然有待进一步论证。
相似的思路,将法益概念作为一个一般的平均的利益,或者一种客观的价值来理解,可以得出死者自身的名誉作为法益的结论。[6](P196)具体来说,国家的法益相关的犯罪或者在社会的法益相关的犯罪的场合,“权利主体性”“权利能力”以及法律上的“人格”并非法益的必然的要素。因为死者不具有权利主体的性质,所以不能具有名誉这一法益,从而对死者的名誉不能进行毁损并没有根据。一方面承认死者是不能作为法益的直接主体的,另一方面也认为,法益的主体性并非法益的必要要素,从这个角度论述死者的名誉也是需要保护的。
死者并非作为“人”的存在,死者并没有完全的人格,这种对死者名誉的保护,是作为法体系上非常例外的规定。这种例外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只是因为死者的名誉在社会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利益的缘故。[7](P33)事实上,死者的名誉作为法律保护的法益,仅仅是法律体系上一种例外的特别规定,死者没有人格权、死者本身不能拥有名誉权以及死者不能作为法益的主体都是毋庸置疑的。“法将死者作为法益归属的主体的考虑,与全法体系不相容。死者的名誉虽然确实可以作为侵害的客体,但是其自身并不能作为法益。”[8]因此,上述将死者直接作为名誉权保护的主体的解释,从根本上来说,是存疑的。
直接将死者解释为刑法上的侵害的对象,从法哲学角度或许存在某些合理性,但是,这种理解仍然与普遍的社会伦理相违背。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对死者名誉毁损罪的法益,并非仅仅指死者的名誉,同样也指家族的名誉成为较有说服力的观点。家族的名誉并非单个的家族成员的名誉,更多的是作为团体的家族的名誉。对死者的名誉侵害,因为死者本身是没有名誉权的,所以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实际上是对活着的人的侵害,且是对死者的家族团体的名誉侵害。从德国刑法第189条来说,死者的名誉与家族的名誉是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家族的名誉同样属于法律应当保护的法益。对死者诽谤的行为所保护的法益,并非仅仅是对死者名誉的侵害,同样是对家族名誉的侵害。家族名誉并非单个家族成员的名誉,更多的是一种作为团体的家族名誉的理解。[9](P134)如果仅仅考虑所谓团体的 “社会功能”的作用,家族是符合团体的定义的,家族作为受益于名誉的一个整体,它是所有组织中最富有凝聚力的。同时家族的名誉无论是对家族的每个成员,还是对家族本身,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然而,家族作为诽谤行为所侵犯的对象,在法律上却存在着诸多的问题。首先,家族的范围并不确定。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主体,团体的组成人员必须有明确的范围,但是对家族这个概念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具体的标准来判断家族的范围。因为,这样一个团体很难被认为具有法律上的意义。此外,家族本身并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家族作为一个团体,是相对松散的,家族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团体,很难通过家族本身的名义对外进行活动。由于并不拥有法律上所赋予的权利,也不承担必要的义务,家族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地位。最为重要的是,家族本身并没有经济价值,也不存在经济上的损失问题。一般来说,名誉毁损行为诉诸法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经济上的补偿,但是家族本身是没有经济价值的,也就更谈不上所谓的经济损失问题,失去经济损失这种量的衡量标准,家族的名誉本身也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德国刑法上,将个人名誉的保护作为原则,而团体的名誉仅仅只是以法规上明确规定的场合为限予以保护。也就是说,德国刑法中虽然有对团体的名誉予以保护的例外规定,但是仅以法律规定为限。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团体,并不能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因此,家族的名誉说同样存在瑕疵。
事实上,对死者名誉的毁损行为,虽然诽谤行为的直接对象是死者,但是这种行为同样也对死者的近亲属的感情造成损害,也就是将死者的遗族对死者敬虔的感情作为法律保护的法益成为德国学者的通说。[10](P98)“敬虔的感情”来自于德国刑法条文第189条的 “死者的追忆”的条文描述,由此,将死者的名誉毁损的保护法益,解释为死者敬虔的感情。同时,对死者追忆的诽谤,具有告诉权的人限制在死者的父母、子女、配偶以及兄弟姐妹之内。所谓遗族的名誉也就是敬虔感情作为法益予以保护。[11](P141)这样被害人可以解释为死者的近亲属,避免将死者直接作为被害人解释上的困境。但是,直接将“感情”作为法律所保护的法益进行理解,严格来说,“感情”仅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根据每个人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这种存在多义解释的感情予以保护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待商榷的。
三、死者名誉救济的基石:以间接诽谤理论为基础
所谓间接诽谤,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言论在直接导致某一公民名誉损害的时候,对其他公民的名誉也间接造成损害的情形。例如,指称一个孩子智力存在问题的言论,不仅仅损害孩子本身的名誉,对孩子的整个家庭都是很大的伤害。在传统刑法理论中,一般来说,行为的被害人是不能扩大的,例如,盗窃了甲的财物,虽然该财物可能是甲的家庭的共同财产,但是不能认为被害人是甲的整个家庭。同样的,在这里是否应当对被害人进行限制也是有争议的。在日本,学界通常认为,对这种间接诽谤,原则上是不能认可的,有关诽谤罪的对象,应当严格限定在直接诽谤的对象[12](P282)。名誉是有关个人存在的权利,因此,对近亲属的名誉毁损的行为,并不能认为是对本人名誉的毁损。例如,仅仅指称妻子具有通奸等行为,并不能认为是对丈夫的名誉毁损。
一般来说,所谓的间接诽谤多发生在涉性名誉受到侵害的情形。例如,某甲男与某乙女通奸的言论,对甲男、乙女自身的名誉造成伤害自不必说,对甲男的妻子、乙女的丈夫的名誉同样也造成了损害。甚至可以说,对甲男、乙女的近亲属的名誉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害。间接诽谤在认可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间接诽谤的对象范围如何界定。如果认可甲男的妻子、乙女的丈夫的名誉毁损,那么甲男的近亲属、乙女的近亲属的名誉是否应当予以保护?如果不保护,这种限制性保护的理由并不充分,很难界定乙女的丈夫与乙女的父亲谁的名誉受到的损害更为严重;如果对近亲属都进行保护,这一权利损害的对象的范围又过于宽泛,对间接诽谤的认可就会受到更多的质疑。因此,在德国,对这种有关性的名誉毁损的问题,“只有当该行为不属于通奸罪的构成要素,根据其行为的具体性质和对女伴丈夫表示出的蔑视行为,才能够认为是一种名誉毁损的行为。”[10](P95)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不是间接诽谤的情形,而是一种直接的诽谤行为。如果有关言论在论及受害人的同时,对其某个家人的名誉也一并进行损害,这个时候应当认为是行为对该家人名誉的直接伤害。
但是,对间接诽谤一概地不予承认,在下述情形下也会存在问题。
首先,如果作为诽谤言论的直接被害人不进行法律上的救济,诽谤罪作为自诉案件,当被害人的近亲属名誉也受到毁损时,也就无法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救济。例如,上述的某甲与某乙通奸的言论,虽然甲和乙两人之间是非常简单的朋友关系,并没有所谓的通奸行为,甲和乙自身对这些言论非常不在乎,害怕通过诉讼程序反而将原来并没有的事实变成传播更为广泛的谣言,并未进行任何法律上的救济,这些言论对甲男和乙女的正常生活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但是,乙女的父亲丙得知有关情况后,作为父亲的社会评价自然受到影响,自己的名誉感情也受到很大的伤害,决定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作为老父亲的丙在整个事件中,名誉受到的伤害同样是非常严重的,但是由于其并不是直接的当事人,如果不认可间接诽谤的成立,对丙的名誉是不能进行救济的。
其次,有关法人的间接诽谤问题。法人虽然是作为法律上的拟制的人,但是法人的日常运转的行为仍然需要法人内部的自然人来完成,因此,有关名誉的保护上法人与自然人还是有些许差别。也就是说,作为自然人,有关社会评价的获得直接来自于自身的客观行为;而作为法人,法人的名誉的获得虽然也是来自于法人自身的行为,但是真正的行为人是法人内部的自然人。因此,在特定的情形下,作为法人的名誉以及作为法人内部自然人的名誉,可能会发生重合。具体来说,作为法人内部的自然人,如果是拥有特殊职位的情形,对自然人的名誉毁损,同时也可能是对法人的名誉毁损;而对法人的名誉毁损,在特定的情形下,也可能是对特定的自然人的名誉毁损。例如,某公司甲的财务报告有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的行为,对甲公司的名誉固然是造成伤害,对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的个人名誉也是一种间接伤害言论。再比如,“某上市公司丙的董事长丁以权谋私,侵吞公司财产”,该言论直接针对的对象固然是丁的个人名誉,但是这种言论对上市公司丙的社会评价也会造成很大的损害,可以说,丙自身的权利也会受到损害。对法人来说,通常法人的名誉与法人中的自然人的名誉是彼此独立的。但是,在上述存在间接诽谤的特殊情形下,如果仅仅限于对法人的名誉保护或者限于对法人内部自然人的名誉保护,可能都会有所欠缺,对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的权利都未能进行充分的保护。
最后,作为被害人的当事人在受到他人的诽谤后由于各种原因去世了,因为名誉权属于个人一生专属的权利,随着当事人的去世,名誉权也就不再拥有。在这种情形下,若侵犯名誉权的行为已经发生,当事人的去世固然并不影响犯罪行为的成立,但是,在诉讼中认定人的主观名誉感情受到的损害就很难进行。当事人的去世是否因为主观上的名誉感情受到的伤害,如果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很难说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名誉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是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的。无论是生命权、身体权,还是财产权、知识产权,对权利造成的损害都是不能扩散的,但是,名誉无论是社会评价,还是主观上的名誉感情,都是具有扩散性的。社会对女儿评价的降低,父亲的评价肯定也会受到影响;女儿的名誉感情受到伤害,作为父亲的名誉感情同样也会受到伤害。在这个意义上,名誉的法律保护本身并没有任何不当。而在刑法中,之所以需要限制诽谤罪的对象,一方面,承认这种扩散性,就好比一滴墨汁滴到海里,这种扩散性的界限是难以界定的,另一方面,这种扩大保护在诉讼程序上的界定也存在着诸多困难。但是,如果出现当事人的权利无法救济,或者放弃救济时,以及有关法人的名誉保护问题时,在特定的情形下,应当考虑允许间接诽谤的成立。
死者本身是没有名誉权的,死者直接作为法益的主体,从法益主体的角度解释存在很大的困难,“死者具有名誉,但是没有名誉权。刑法上对死者的名誉毁损的保护,只是对遗族的名誉权侵害的保护”[13]。名誉这一概念,有关法益的负担者,只能是生活的人类能够拥有。作为死者,并不是权利的主体。因为死者没有人格,也就不能作为名誉的主体,死者的名誉毁损,实际上只是死者的亲族或者子孙(也就是遗族)的名誉毁损。在这一意义上,德国刑法有关死者的名誉毁损的规定,更具说服力。死者的名誉,更多的只是宗教立场的结论,刑法上对死者名誉的保护,本质上是对遗族虔诚感情的保护。
四、我国死者名誉刑事救济的制度设计
我国刑法既没有有关死者诽谤罪的规定,也没有对死者遗族名誉的保护,对这种行为没有相关的刑法条文予以规定。在现行法律未变的前提下,有条件地允许间接诽谤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弥补这种法律缺陷与漏洞的。
在死者的社会评价受到他人诽谤的场合,从间接诽谤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是对死者近亲属名誉的损害,同样符合诽谤罪的犯罪构成。通过这种解释,一方面避免直接将死者作为行为对象存在的刑法解释上的困境,死者的近亲属作为直接的受害人,可以提起自诉维护自身以及死者的权利;另一方面,间接诽谤的理论解释,也与诽谤死者现实的危害性相一致,也就是说,对死者的诽谤,现实层面主要是对死者近亲属名誉的直接危害,这种法律解释也与现实的法律诉讼需求相吻合。
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可以被认为是死者近亲属自身的名誉受到损害,借用诽谤罪的规定,对行为人也可以追究相应的责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是这种对死者名誉的保护,仅仅限于对死者近亲属权利的保障,不能肆意扩大,保护的范围必须予以限定;二是对死者名誉的损害,必须同时考虑死者的社会评价的损害、死者近亲属社会评价以及名誉感情的损害,必须同时满足上述条件;三是行为人必须是虚假的事实对死者名誉进行损害,因此,如果被告人能证明事实的真实性,可以免除处罚;四是对死者名誉的救济,也必须满足“情节严重”的标准。
对死者的诽谤行为,根据间接诽谤的理论,死者近亲属的名誉受到损害,其可以提起刑事诉讼,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情形。同时,如果对死者名誉损害的行为已经损害到公共利益,死者的近亲属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当事人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提起诉讼的,司法机关可以直接立案审查。刑事法律的这种制度设计,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死者名誉保护的难题。具体来说,自然人死亡后,如果其名誉受到他人损害,其近亲属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但是,如果其近亲属并未提起民事诉讼,根据民事法律中不告不理原则,这种情形就无法追究行为人的责任。近年来,在网络中充斥着诸多对去世的革命先烈、领袖伟人、演艺名人等公众人物名誉损害的言论,但是由于民事法律对死者名誉保护的缺位,如果无人对此提起民事诉讼,就无法及时有效遏制此类言论的恶意捏造与肆意传播。在这种情形下,刑事法律的合理介入,国家公权力的保护弥补公民私权利救济的困顿,对有效规范公民的正当言论,合理保护公民的名誉权,不失为解决此类问题可探讨的合理方向。
[1]陈慰星.信访激励的法经济学分析[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2]杨立新,王海英,孙博.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J].法学研究,1995,(2).
[3](日)杉山博亮.死者の名誉毀损[J].现代刑事法,1987,(4).
[4](日)小野清一郎.刑法に於ける名誉の保护[M].东京:有斐阁(增补版),2002.
[5](日)中野次雄.名誉に对する罪[J].刑法讲座,1993,(4).
[6](日)木村龟二.刑法の基本概念[M].东京:有斐阁,1969.
[7](日)植松正.再记刑法概论II各论[M].东京:劲草书房,1975.
[8](日)植松正.名誉に対する罪[J].刑法讲座,(5).
[9](德)Binding.Lehrbuch des Gemeinen Deutschen Strafrechts.Stuttgart:W.Engelmann,1902.
[10](德)Hermann Blei.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 Stuttgart:Gieseking,1983.
[11](德)Reinhart Maurach.Deutsches 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Stuttgart:Teilband,1964.
[12](日)宗宮信次.名誉权论[M].东京:有斐阁,1961.
[13](日)日高義博.死者の名誉毀损[J].专修法学论集,1978,(31).
【责任编辑:胡 炜】
D924.34
A
1004-518X(2015)12-014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