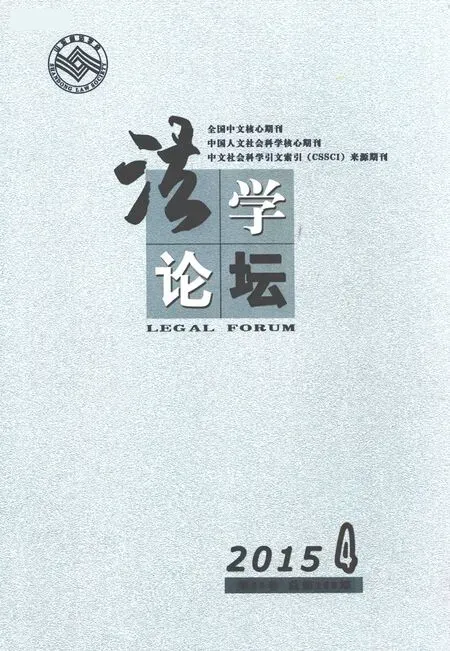环境维权“民告官”的困境与出路
——以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为分析对象
李少波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环境维权“民告官”的困境与出路
——以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为分析对象
李少波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是私权模式的阐释和捍卫,重在保护私主体的人身、财产等传统权益不受行政行为的侵犯。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欲保护的利益,往往是非原告所专有的审美、娱乐、环保以及精神享受等非物质性利益,被诉行为往往不限于行政行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与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的现实冲突,要求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应从私权模式转向公共价值模式,拓展被诉行为的范围与法益保护的范围,以适应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的客观要求。
原告资格;私权模式;公共价值模式;新兴利益形态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2月20日,饱受雾霾之苦的石家庄市民李贵欣经过长达三个月的“酝酿”,将石家庄市环保局诉至该市裕华区法院,要求石家庄市环保局依法履行治理大气污染职责并赔偿损失1000万元。此事件经媒体报道之后立刻引起各界关注,法律界也热议起诉的重要性和立案的可能性。*参见刘岚:《省会市民状告环保局引起各界共鸣》,载《燕赵都市报》2014年2月25日。其实,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加剧以及环保局的屡屡不作为,类似李贵欣的“民告官”壮举屡屡见诸报端:80后女孩陈立雯先后将广州市环保局、杭州市环保局和四川省环保厅告上法庭,*参见焦东雨:《状告环保局的80后女生》,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43&id=7034北京市朝阳区万象新天小区业主杨女士将北京市环保局告上法庭,*参见王殿学:《诉环保局违法居民被判无资格》,载《新京报》2010年5月24日。业主因不满市规划委核发许可证的行为而将其告上法庭,*参见于平:《建筑规划审批能否引入社区审查》,载《新京报》2004年10月27日。安徽农民因质疑环保厅违法审批污染企业而将环保厅告上法庭,*参见冀强:《安徽农民“叫板”环保厅》,载《山东商报》2013年5月27日。杭州市民金喜奎状告杭州市规划局案*参见陈思:《金奎喜诉杭州市规划局案》,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11/id/93681.shtml.……而江苏省高院发布的2012年以来审结的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中,环境诉讼“民告官”明显增多。*参见陈月飞:《环境诉讼,“民告官”多了》,http://news.sina.com.cn/c/2013-12-12/064028961787.shtml.在这众多的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中,既有维护个体私益者,也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者;既有维护传统意义上的人身、财产权益者,也有维护娱乐、审美、环保等新兴利益形态者;既有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也有针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案件。不管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维护的利益性质如何、形态怎样,因当事人适格问题而被法院拒之门外成为大多数案件的共同宿命。“2013年中国十大公益诉讼”中的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诉福建省林业厅向“归真堂”公司活熊取胆违法颁发许可证案,正是被法院以“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不足”为由而拒绝受理,*2013年4月11日,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换机加工研究所依法向福建省鼓楼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福建省林业厅撤销其为“归真堂”活熊取胆所颁发的“驯养繁殖”和“经营加工”许可证。法院的答复是“原告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不足”。参见黄庆强、杨子强:《破除行政公益诉讼的“门禁”》,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6日。而在杭州市民金喜奎状告杭州市规划局一案中,法院也是以“金喜奎与在建的浙江老年大学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为由不予立案。*参见魏华兵:《西湖风景区建无关项目市民打公益官司告规划局》,载《青年日报》2003年3月28日。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是对私权模式的阐释和捍卫,重点在于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安全,人身和财产权益之外的其他新兴权益并非其保护的对象,因而无法适应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日益增长的现实需要。本文以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为例,详细探讨环境维权“民告官”背景下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困境与出路,以便为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适用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二、我国《行政诉讼法》上的原告适格规则
原告资格(standing to sue)是指当事人为获得某一纠纷的司法解决而在该司法争端中所具有的充分利益,*参见Black’s Law Dictionary, 5th Edition, 1260 (1979).是对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利害关联的描述,*参见陈亮:《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76-79页。是对抗制模式之下法院用以确保当事人为其案件进行热心辩护的制度设计。*同④。原告适格规则(the law of standing)则是指用以判断当事人是否是适格当事人的一系列规则的总称。*参见Australian Law Reform Commission, Standing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Report No.27(1985), at.3.
我国关于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规定,是以现行《行政诉讼法》第49条第1项和第2条为主体,第12、13、25条为补充的规则群。根据该规则群,可以剥离出判断行政诉讼原告是否适格的四项标准,包括适格原告须符合行政诉讼当事人能力的一般性规定、适格原告须因行政行为而受到影响、适格原告合法权益可能受到被诉行为影响以及适格原告须是受影响的合法权益的享有者。
(一)适格原告须符合行政诉讼当事人能力的一般性规定
在大陆法系中,当事人能力和当事人适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事人能力是指能够成为诉讼当事人的一般性资格,“当事人能力不以具体案件为前提,而是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对某人能否成为诉讼当事人加以考察和确认。这种能力和资格并不以具体案件的不同而转移。”*王彦:《行政诉讼当事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与之不同的是,当事人适格则是以特定案件为前提,具体地、个别地讨论某人能否成为该案件的诉讼当事人。*参见[日]中村英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锋、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从二者关系上来看,当事人能力是当事人适格的前提,两者是共性与个性,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参见王锡三:《民事诉讼法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页。职是之故,行政诉讼适格原告必须符合行政诉讼当事人能力的一般性规定。
这一要件的功能在于划定行政诉讼适格原告的属人范围。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可以纳入这一范围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就是说,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适格原告首先必须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除此之外的其他主体不能成为适格原告。
(二)适格原告须因具体行政行为而受到影响
“具体行政行为”是贯穿我国原《行政诉讼法》全文始终、被频繁使用(总共出现32次)的核心概念。它与德国法上的“行政行为”概念一样,是诉讼法律保护适法性的核心概念,决定着是否以及怎样提供行政法律救济的问题:一旦某个行政活动被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提供行政法律救济的问题随之解决;同时,行政行为对随后“如何”提供法律保护的问题也具有意义,即有助于确定诉权、诉讼类型、诉讼期限以及前置程序的必要性。*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等著:《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3页。
尽管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取消了“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术语,代之以“行政行为”,但是“适格原告须因具体行政行为而受到影响”这一要件并没有因为“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术语的消失而改变。按照修法者的初衷,之所以用“行政行为”取代“具体行政行为”,是因为原《行政诉讼法》第11、12条对可诉范围已作了明确列举,无需再借助“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概念来限定行政诉讼的可诉范围。*参见陈丽平:《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有新修改 可诉条件取消具体行政行为限制》,载《法制日报》2014年8月26日。反观现行《行政诉讼法》第12条和第13条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与原《行政诉讼法》第11、12条的规定并无本质差异,仍然将被诉行为限制在“行政主体针对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就特定的具体事项而作出的有关该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本质上仍属于我国行政法学理上所称的具体行政行为。
换句话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换汤不换药”,通过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之外,同样达到了原《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所要实现的目的,即将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制定、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被诉行为之外,凡是受这类行为影响的原告均不能作为适格原告。
(三)适格原告受被诉行为影响的须是合法权益
该要件的功能在于限定适格原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法益范围,即只有合法权益受到被诉行政行为影响的原告才是适格原告。对于“合法权益”,学界曾有“法律未禁止或反对的”、“法律确认的”以及“法律明确规定的”三种解释路径。从相关规则之体系解释出发,“合法权益”应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权益。*参见沈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裁量的空间与限度》,姜明安、沈岿、张千帆主编:《润物无声:中国宪政之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69-272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合法权益”以人身权、财产权为主,人身权、财产权之外的其他权益,须以法律明确规定为限。*参见周汉华:《论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审查》,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6期。
有学者指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经历了从无标准时期到法律规定标准时期,再到合法权益标准时期,进而发展到利害关系人标准时期。*参见黄学贤:《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学》2006年第8期。这是否意味着这一要件中的“合法权益”应由“法律上利害关系”取而代之。事实并非如此。“法律上利害关系”一语,并非关于法益保护范围的规定,而是对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关系的描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引入“法律上利害关系”这一术语,旨在扩大起诉人的范围,纠正当时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所流行的“原告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错误观点。*参见陈亮:《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201-202页。就“合法权益”与“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关系而言,合法权益的存在恰恰是其受具体行政行为影响,并进而可能形成“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前提,*参见张旭勇:《“法律上利害关系”新表述——利害关系人原告资格生成模式探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起诉人与被诉行为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则应理解为起诉人的人身权或者财产权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权益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而不论该起诉人是否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四)适格原告须是受影响的合法权益的排他性享有者
该要件的功能在于厘清原告与被侵害的法益之间的权属关系,意在肯认行政诉讼原告不得主张第三方权益的原则。当然,这一原则并非绝对,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权益属于原告标准仍有两个例外:一是原告资格的转移;二是合营企业各方可以原告身份起诉侵犯合营企业权益的行政行为。*参见沈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司法裁量的空间与限度》,姜明安、沈岿、张千帆主编:《润物无声:中国宪政之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除此之外,我国法律并不存在允许行政诉讼原告主张第三方权益的情形。
三、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下环境维权“民告官”的现实困境
“民告官”是行政诉讼的俗称,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针对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诉讼。环境维权“民告官”则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就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环境行政行为而提起的环境行政诉讼。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面临的最大障碍是原告资格问题,因为原告资格是接近正义的第一步,对于当事人能否利用法院解决其司法争端具有前提性意义。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经由第2、12、13、25条和第49条第1项所建构的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是我国法院据以判断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当事人是否适格的基本规则。这一规则是对私权模式的阐释和捍卫,以维护个体自由和财产安全为己任,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的现实需要。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与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的现实之间存在下述冲突。
(一)裁判模式的冲突
美国学者根据法院作用的不同,将裁判模式分为纠纷解决模式和公共价值模式:纠纷解决模式将法院作用限制在解决纠纷这一传统作用之上,而公共价值模式则主张法院应在公共价值的形成方面发挥其应有作用。*参见Evan Tsen Lee, Deconstitutionalizing Justiciability: The Example of Mootness, 105Harv. L. R. 603, 625-27(1992)纠纷解决模式以既定法律规范的违反作为司法干预的前提,强调当事人与纠纷之间的利益关联,强调权利与救济之间的相互依存,是高度个人主义化的。*参见陈亮:《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122页。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是纠纷解决模式的阐释和捍卫。首先,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对合法权益的强调,实际上是将现行法律、法规的违反作为司法干预的前提,是对“以既定规范的违反作为司法干预之前提”的纠纷解决模式特征的反映;其次,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要求适格原告的合法权益须受被诉行为影响,实际上是要求原告证明被诉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对纠纷解决模式“强调权利与救济相互依存”这一特征的再现;最后,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要求适格原告须是受影响的合法权益的排他性享有者,原告不得主张包括公共利益在内的他人的权益,这既是对纠纷解决模式要求当事人与纠纷之间存在利益关联这一特征的回应,也是纠纷解决模式高度个人主义化特征的题中之义。
作为纠纷解决模式之阐释与捍卫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以保护个体私益为己任,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的社会现实。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中的环境利益损害,大多是广大区域内的居民共同的利益损害,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正如日本环境法学者原田尚彦所言:“环境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受到的环境上的利益损害,是广域区域内的居民共同的利益损害,是公共利益而不能称作个人利益,即使评价其为个人利益,对于原告个人也不会被当做那种严重程度的损害认识,往往被解释为不符合需要由停止执行来加以保护的紧要的个人利益。”*[日]原田尚彦:《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既然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中的环境利益损害属于公共利益损害,那么以保护个体私益为己任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就无从适用。
(二)被诉行为的冲突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由此导致各地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解决步骤各有不同。国家制定的适用于全国范围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因其过于抽象原则而无从适用,授权地方立法机关或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地方性环保法规和规章就成为我国环保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环境行政管理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些地方性环保法规或规章,要么设定行政处罚,要么设定行政许可,要么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皆有可能因违法而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比如西安市以环境保护、交通安全等之名实行的禁摩令,*考虑到摩托车污染环境、不安全和阻碍交通等因素,2000年6月,西安市交警支队在未经任何调研、论证、咨询、听证程序而径直宣布,从当年7月1日开始,西安市摩托车包括轻骑车一律不准在城墙内通行,外地摩托车一律不准在二环路内通行。此禁令一出,反响强烈。参见刘莘主编:《法治政府与行政决策、行政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正是以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方式进行环境行政管理进而损害公民、法人及其经济组织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
以制定规范性文件形式进行的环境行政管理行为属于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相较于具体环境行政行为,这种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的特点在于其适用对象的普遍性、适用效力的普遍性和持续性。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其影响远远大于具体环境行政行为。抽象环境行政行为一旦违法,将给众多人造成损害,并且这种损害会在一定范围内连续发生,从而使更多的相对人蒙受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抽象环境行政行为具有更大的破坏性,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不可估量性和大面积性,更应纳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参见席正清、梁永辉:《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构建》,载《检察日报》2009年11月9日。
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要求原告须受具体行政行为影响,从而将针对一般大众作出的、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外。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这一要件给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许多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正是由于被诉行为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而被法院拒之门外。北京私家车车主刘工超因未安装北京市环保局、交通局及公安交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对具备治理条件轻型小客车执行新的尾气排放标准的通告》(以下简称“513号通告”)所指定的尾气净化系统而未能获准年检。刘工超经行政复议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3被告联合作出的“513号通告”有关内容违法,受案法院正是以“513号通告”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抽象行政行为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参见汲传排:《私家车主状告3局垄断一审败诉》,http://www.people.com.cn/GB/channel1/11/20001221/357909.html.
由此可见,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关于“适格原告须受具体行政行为影响”的规定,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环境行政管理的现实需要,给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
(三)法益范围的冲突
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保护的利益具有多样性,既有人身、财产利益,又有非人身、财产利益;既有个体私益,又有环境公益;既有合法权益,又有法外利益。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中这些性质各异、种类繁多的利益,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所保护的法益范围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具体而言,这些冲突体现在:
1、利益形态的冲突。 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欲保护的利益,既包括人身、财产利益,也包括非人身、财产利益,而且绝大多数体现为审美的、娱乐的、环保的以及精神享受等非物质性利益,杭州市民施建辉、顾大松诉南京市规划局违法行政案正是原告请求保护人身、财产利益之外的非物质性利益的典型代表。2001年,南京市中山陵园管理局于中山陵风景管理区紫金山兴建“南京市紫金山观景台”,此事经当地媒体披露后,引起南京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同年10月 17日下午,东南大学施建辉、顾大松两位教师,以南京市规划局在对观景台的规划许可中未依法行政,致使观景台的建设给紫金山的自然风景造成破坏为由,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南京市规划局撤销对紫金山观景台的规划许可。*参见路国莲:《论行政公益诉讼——由南京紫金山观景台一案引发的法律思考》,载《当代法学》2002年第11期。此案中原告所欲保护的自然风景,显然不属于人身、财产利益的范畴,而是审美、环保以及精神享受等非物质性利益。
无独有偶,上个世纪70年代发生在美国的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Sierra Club v. Morton),也证明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欲维护的利益往往是人身、财产利益之外的非物质性利益。在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以“一个对自然公园、猎物避难所和乡村森林的保全和正确维护有特殊兴趣的”公益团体的名义,对林业部批准沃特·迪斯尼在“矿王峡谷”(Mineral King Valley)兴建综合游乐场的决定提起诉讼,主张该游乐场的修建将破坏或影响国家公园的美景、自然与历史景观以及公园内野生动物的栖息,从而损及后代人享受该公园游憩的利益。*参见Sierra Club v. Morton, 405 U.S., 727 (1972)在该案中,原告塞拉俱乐部并没有主张被诉行为影响了俱乐部本身或其成员的人身、财产利益,而是主张被诉行为有可能对该地区的美景或生态造成不利影响。这又再一次证明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欲保护的利益往往是人身、财产利益之外的非物质性利益。
由此可见,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欲保护的审美的、娱乐的、环保的以及精神享受等新的利益形态,与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所欲保护的利益形态之间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的立案困难。
2、利益归属的冲突。 环境损害往往具有广泛性,这主要体现在受害地域和受害对象上。环境行政行为所损害的利益,往往是广域区域内广大居民的共同利益,是为不特定公众所共有的共同利益,而非专属于某一个体的私人利益。职是之故,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欲保护的利益,通常超出个体私益的范畴,大多体现为环境公共利益。
按照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要求,适格原告须是受影响的合法权益的排他性享有者,原告不得主张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第三方的利益。这一要求为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许多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正是因为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缺乏利益关联而被法院拒于门外。在杭州市民金奎喜诉杭州市规划局一案中,法院正是以“金奎喜与在建的浙江老年大学没有利害关系”为由,拒绝承认金奎喜的原告资格。*参见魏华兵:《西湖风景区建无关项目市民打公益官司告规划局》,载《青年日报》2003年3月28日。
事实上,环境公共利益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所享有,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环境公共利益不值得通过司法程序加以保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不无正确地指出:“与经济利益一样,美学和环境利益也是我们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定利益由许多人而非少数人共享这一事实并不会使这些利益更不值得通过司法程序加以保护。”*参见Sierra Club v. Morton, 405 U.S., 727,734 (1972)
四、环境维权“民告官”背景下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应然构造
行政诉讼适格原告条件的放宽业已成为各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理论界的基本共识。遗憾的是,对于世界各国的这一发展趋势和我国理论界的这一基本共识,我国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笔者认为,为适应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的需要,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从理念追求到制度构建都应进行调整。具体而言:
(一)理念追求:从私权模式转向公共价值模式
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原告适格规则的构建具有前提性意义,包括原告适格规则在内的所有可裁判性规则的形成与变迁,本质上都是对不同裁判模式的反映。*参见陈亮:《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在私权模式或者纠纷解决模式之下,“纠纷解决者被置于一个类似辩论赛裁判的位置上——他并不关注讨论问题的本身,而只是客观地专注于法庭辩论技巧的展示”,而决策者仅需作出有利于在法庭辩论中取胜的当事人的判决。*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在这种裁判模式之下,当事人的地位至关重要,主导着包括诉讼启动、存续、争点的形成、事实的发现乃至判决的做出等整个诉讼程序的运行。*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202页。为适应当事人在传统裁判模式中的主导性地位,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不得不采用私权模式的原告适格规则,将既定规范的违反作为司法干预的前提,强调当事人与诉争之间的利害关联,其根本目的在于利用当事人的利己心,促进当事人为其案件进行“热心辩护”,以提供法院裁判案件所必须的信息。*参见陈亮:《美国关于原告资格功能之争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7期。
与之不同的是,公共价值模式则以公共价值的维护或公共政策的形成为己任,官员控制着包括诉讼的启动与终结、争点的形成与事实的发现等在内的全部诉讼程序,当事人仅仅是官员们作出正确决策所需的信息来源之一,而非全部;*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249页。法庭竞赛中取得优势的论点或者程序参与者的愿望不再是决定裁判结果的唯一因素。*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页。公共价值模式中当事人地位的变迁,使得公共价值模式无需再倚重当事人的利己心来为案件进行热心辩护,从而也就无需强调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的利害关联了。
环境维权“民告官”,往往并不限于维护公民个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广域范围内的众多民众的娱乐的、审美的、环保的以及精神享受等新兴利益形态,这些新兴利益形态蕴含浓厚的公益意味。以传统私权模式为指引构建的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已经无法适应保护新兴利益形态的现实需要。我国必须以公共价值模式为指引,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
(二)被诉行为:承认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往往针对环境规制行为。环境规制行为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它往往并不直接针对某个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或财产,而是针对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以维护公共利益之名,通过发布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来实施,其效力及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也就是说,环境规制行为以促进环境公共利益为宗旨,大多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将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纳入被诉行为的范畴,可以大大提高环境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在抽象环境行政行为不可诉的情况下,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根本不必担心因其文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而受到起诉,从而放松对规范性文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如果抽象环境行政行为可诉,那么环境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者将会全面考虑其文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免卷入不必要的诉讼之中,从而提高环境规范性文件的质量。
将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纳入被诉行为的范畴,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在环境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情况下,每一个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受害人,只能等到环境执法部门据此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后再提起诉讼,由此导致各地法院的重复审查,导致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纳入被诉行为之后,可以大大避免各地法院的重复审查,从而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在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环境规制的当代中国,将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被诉行为的范畴,既可以大大提高环境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又可以有效节约司法资源。因此,我国在重构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之时,应将抽象环境行政行为纳入被诉行为的范畴。
(三)法益范围:将娱乐、审美、环保等新兴利益形态纳入保护范围
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所欲保护的利益,往往是娱乐、审美以及环保新兴利益,与传统意义上的私人自由与财产大异其趣。如果严格遵循以维护个人自由与财产的传统原告适格规则,那么大量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最终将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换句话说,传统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与财产,不应成为判断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原告适格与否的唯一标准。正如理查德·B·斯图尔特所说:“政府活动的迅速增长,已经使普通法上的自由和财产权利这一准绳,成为在确定有资格寻求司法干预以抵抗非法行政的私人利益方面不适当的衡量标准。”*[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80-81页。正因为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2年审结的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中首次承认和保护审美、环保等非经济利益。*参见Sierra Club v. Morton, 405 U.S., 727,734 (1972)自此之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各类原告资格,如保护自然资源、风景、历史文物等公民团体的原告资格,都渐次获得美国法律的认可。*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437-438页
娱乐、审美以及环保等新兴利益,在我国民众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国应顺应历史潮流,在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之时,将非属于人身与财产的新兴娱乐、审美以及环保等利益形态纳入其保护范畴。
(四)具体规则
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具体构建,“既要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大量原告开启正义之门,又不能因原告适格规则的自由化而害及我国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转,同时还要考虑被告的利益”*参见陈亮:《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版,第224页。新构建的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须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应以公共价值模式为指引,淡化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的利害关联,并在被诉行为和法益范围方面进行拓展以适应环境维权“民告官”的现实需要。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引入澳大利亚的“好事者”标准,即在行政诉讼中,任何人都享有原告资格,除非法院能够认定原告仅仅是“为了骚扰”才提起诉讼。*参见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Australia,Standing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5),at 26.在具体操作该规则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好事者”标准并未废除“原告必须具备原告资格”这一要件,仍然保留了原告资格要件及其所发挥的功能。也就是说,原告欲让法院就其案件实体问题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仍然必须具备原告资格,以确保原告资格要件的功能得以发挥。
2、“好事者”标准是对原告资格的推定,即法院首先推定提起公益诉讼之人均具备原告资格,然后由被告举证证明原告起诉是否仅仅是为了骚扰。只要被告能够举证证明原告起诉仅仅是为了骚扰,那么法院便可以原告缺乏原告资格为由驳回诉讼。
3、原告是否是骚扰者,并非根据现行原告资格所要求的利益种类、被诉行为以及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利害关系来判断,法官须结合原告的诉讼请求等作出原告是否适格的判断。
这一标准改变了传统原告适格规则以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评价原告是否适格的标准,淡化了原告与诉争案件之间的实体利害关联。这一原告适格规则,不仅可以对私权模式原告资格和公权模式原告资格作出统一说明,而且淡化了被诉行为与法益保护范围在判定原告资格方面的决定性作用,是公共价值模式的阐释与捍卫。在我国环境民权“民告官”案件日益增多、利益形态和被诉行为日趋多样化的现实背景下,这一原告适格规则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五、结语
环境维权“民告官”案件的质量,是我国环境法治的“晴雨表”,关乎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最终实现。传统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在价值追求、被诉行为以及法益范围等方面的固有缺陷,使其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环境维权“民告官”的现实需要。重构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以降低环境维权“民告官”的制度门槛,是我国制度设计者们当前面临的难题之一。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重构,应以公共价值模式为其理念追求,不仅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被诉行为范畴之内,而且应拓宽其法益保护范围,将审美、娱乐、环保等新兴利益全部纳入其中。为此,澳大利亚的“好事者”标准不失为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规则的明智选择。
[责任编辑:刘加良]
Subject:Public Right Protection in Environment Cases: Its Dilemma and Way-out: Focusing on the Required Condition Rules of Litigant in Concerning Administrative Lawsuit
Author & unit:Li Shaobo(School of Law, Zhongnan Minz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The required condition rule of plaintiff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 is a regime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rights, focusing on the free of infringement of private human body and his or her property by the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The interest concerned in the environment lawsui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re always related with non-physical interest such as aesthetical, amusement, environmental and spiritual ones, and the accused activities are not confined to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ivities. The present conflicts between the required condition rule for the plaintiff in administrative lawsuit and the environment lawsuit concerning the public against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demands the said rule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private right protection mode to public value mode, which could expand the protection range of the accused activities and legal interest so as to meet the objective requirements of public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suit against the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required conditions of the plaintiff; private right protection mode; public interest protection mode; forms of newly emerged interest
2015-05-06
本文系教育部2013年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社会管理法治建设》(IRT13102)的部分成果。
李少波(1975-),男,湖北赤壁人,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治理法治化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法,行政诉讼法。
D925.3
A
1009-8003(2015)04-013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