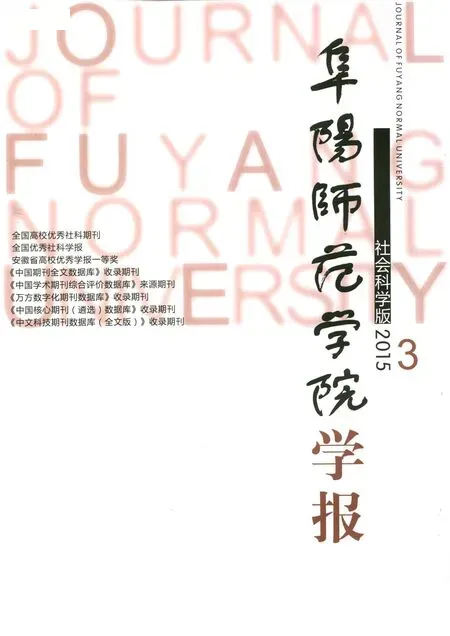张载“相感说”之三层次探析
李文斌(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张载“相感说”之三层次探析
李文斌*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本文从“虚气相感、阴阳相感、心物相感”三个层次对张载的“相感说”加以分析,通过“相感”分析虚气关系,明确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点是虚气相感不离,宇宙论和本体论同时并建,并从天到人,尽性穷理,从而使宇宙本体论与人生修养论贯通为一,完成其整个天人哲学的思想建构。
张载;太虚;气;相感
关于张载哲学思想中“相感说”的论述,在过去的研究中往往被人们当作旁枝末节的东西忽略,近年来才开始有相关的论文专门讨论,主要有杨立华教授对“感”本身的详细分析;王英博士上溯“浩然之气”,把“神”纳入到太虚之气中探讨“气与感”之关系;郭胜则从“太虚本体”出发,探讨张载贯通天人之际的感通思想。但纵观这些探究,对于用“相感”来把握张载思想的核心点却有不显之处。本文着重从“虚气相感”“阴阳相感”与“心物相感”这三个层次分析张载的“相感说”,尝试通过“相感”来把握张载哲学的思想理路。
一、虚气相感
张载《正蒙·太和篇》云:
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 是生 絪絪、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起知于易者乾乎!效法于简者坤乎!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不如野马、 絪絪,不足谓之太和。语道者知此,谓之知道,学《易》者见此,谓之见《易》。不如是,虽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称也已。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人们传统的看法就是将它当作“气化宇宙论”来理解,这种看法从前面一句来看或许并不错,然而却没有注意下面的两句。从行文来看,“其”在这里就是指上句的太和,以此观下面的几句,意思就是太和是几微易简和广大坚固、起知之乾与效法之坤、散殊而可象为气和清通而不可象为神的统一。如果说将太和理解为气,那么这句话简直就无法理解了,“气”作为形而下的东西怎么也不可能是散殊而可象为气和清通而不可象为神的统一,“因此这里的太和只可能是形上太虚和形下的气的统一”[1]。当然从这句话本身并不能看到“太虚”的存在,然而这句话说的是太和之性,太和又是虚与气的统一,所以“气”的变化之中也就自然包括了“太虚”。
上面这一章是《正蒙》开篇第一章总述太和之道,形上之太虚与形下之气统一于太和,这为张载哲学中的虚气关系定下了一个基调,紧接着的下一章对虚气关系就说得非常明晰了。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至静无感,性之渊源,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2]7
太虚为气之本体,即太虚与气分属形上形下两个层面,太虚为形上之本体,至静无感;气则有聚有散,为变化之客形。太虚至静无感,则何以与气相感?然《正蒙·乾称篇》云:
无所不感者虚也,感即和也,咸也。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2]63
由此可知“太虚”无感又无所不感,就“太虚”本身而言,其至静无感,然有“气”则无所不感之太虚自然感之,此感是由无感向无不感的一个转化,这种转化是自然而然的。“太虚者天之实也”[2]324,“然天之感有何思虑?莫非自然”[2]107。虚与气相感,由此而知即是一种自然地相接,此种不形与形下之气的自然相互连接在《横渠易说》的另一段论述中说得更为详细:
凡不形以上者,皆谓之道,惟是有无相接与形与不形处之为难。须知气从此首,盖为气能一有无,无则气自然生,气之生即是道,是易。[2]207
他在这里说:“盖为气能一有无,无则气自然生,气之生即是道,是易。”这句话的意思是气能够将形下与形上都集中于自身,气之本身是能内在地存有无的,无在这里就是气自然生的形上依据,气之自然生就是道,是易。这就是说张载认为形上存在是贯穿于气之存在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相接,太虚于气是既超越又内在。
上面谈论了虚气之自然相感“一之”,然而谈论至此,关于虚气相感之探讨却并没有结束,因为上面还提到无感无形之太虚与客感客形之气,惟尽性者“一之”,因此下面有必要对此展开一番讨论。这个“惟尽性者一之”已然不同于虚气自然“一之”,此处“一之”是指天人之相沟通,是整个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点所在。因为若不能沟通天人,那么就会跟汉儒犯同样的毛病,就是张载认为的“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此秦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宋史·张载传》)。在这里张载鲜明地提出了他的观点,认为汉儒只知人而对于形上之天却没有探求,没有沟通天人,打通有无,致使汉唐儒学陷入经学的繁琐与枯燥,并且没有了形上的根据,也让儒学失去了能够感召人心的理想的超越追求,这样就使得经学不可避免地衰微了。同时儒家也越发衰落,以致“大道精微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谈”[2]4。张载面对儒家这样的一个现状,自觉地承担起了为儒学造道的责任。要为儒学造道,就必须摆脱汉儒之蔽,为儒家建构一个形上的本体,并与形下贯通,天人合一,也就是张载所说的“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惟尽性者一之”,要落到个体生命当中去,即将太虚之全体贯穿于客感客形中,使人之生命得以充实,因此尽性成为沟通天人之大关节。
那么何以尽性呢?《正蒙·乾称篇》说:“有无虚实通为一物者,性也;不能为一,非尽性也。”[2]63反过来说,尽性就是要将“有无虚实通为一物”,此有、实自然指万物有形之存在,无、虚指形上之太虚本体。关于这二者通为一物,张载还有这样的论述:“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顾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从来,则深于易者也。”[2]8这里可看出尽性便是要打通虚气、有无、性命,认识到自然相感之奥秘,体万物而不遗,推本究源,便可深于《易》也,所谓“天所自不能已者谓命,不能无感者谓性”[3]316,只要尽此性,就能够体此“自然”,通有无虚实为一。到了这里性的概念就出来了,并且如何尽此性也就随之而来了。首先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说:“性者万物之一源也。”[2]21从这个角度来说,性就是天地万物的根源性存在,张载在论性的时候,是分开两说的。性在天来说就是天性,亦即天所性,“天所性者通极于道,气之昏明不足以蔽之”[2]21。性在人而言就是天地赋予人的天地之性,其实二者也可以说是通一的,只不过是角度不同,分在天在人而已。“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性即是乾坤、阴阳相感的统一,天性包含乾坤、阴阳二端,“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2]63,这二端乾坤、阴阳即分指太虚与气,虚气相感而已。张载在《横渠易说·上经》里说:“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则有体,言乾坤则无形,故性也者,虽乾坤亦在其中。”所以这里的无形乾坤可为太虚在天地中的另一种表达,太虚与气相合,则就是前面所说之“太和”,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太和就是天性的另一说法。张载又说:“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这样性与天道、太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相通了,前面说的虚与气在太和中相感在这里也就更加明确了。
另外张载从人的角度论性,还提到一种与天地之性相对的气质之性,《正蒙·诚明篇》云:“性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2]23这种气质之性是形而后有的,也可以说就是可以形的气性。《正蒙·太和篇》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又在《正蒙·诚明篇》说“性气总,合两也”,也就是性就是太虚之性和气性的相整合。张载关于性还有这样的论述:“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惟屈伸、动静终始之能一之,故所以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2]63这里张载说“体万物而谓之性”,即是把性内化在了万物之中,也是把天性与气性内化于事物之中,感的意思在这里就是性之神妙不测,性是感之能成的基础,惟有屈伸、动静、终始能一,故体万物而谓之性。“能一之”,这里就是太虚与气能一,亦即天性与气性能一,所以这里太虚与气也是从始至终贯穿为一的,“感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2]9,虚气相感通而为一。因此我们发现虚气相感就是张载哲学的核心,贯穿整个性之论述。
还有一个问题未解决,那就是如何尽性。《正蒙·诚明篇》说“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心能尽性”在这也是对“人能弘道”的另一种表达,所以说尽性就是要人能弘道,而“性即道矣”,尽性即是弘道也。而“性于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所以这里的尽性也就是要变化气质,努力使气质之性向天地之性转化,与天性为一,从而完成张载所说的:“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2]65天人合一也是张载哲学思想的最终归宿,是其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并建方向,而且更是其人生修养论和宇宙本体论的统一。因此从上述来看,张载要完成天人合一而不二本,虚气关系就成为其中的核心,而虚气相感不离则就成了虚气关系的核心。只有虚气始终相感不离,其天人合一才能得以展开论证,其宇宙本体论与人生修养论才能贯通为一,所以要厘清张载哲学的脉络,就始终不能离开虚气相感这个核心,“无所不感者虚也,……所谓性即天道也”。至此则虚气相感不离,天人相合不分,张载哲学的构架也就由此建立起来了,而“相感”在这里的意涵也就比较明确了,即相合不离而感通感应,虚气终始不离,相感相通神妙于万物。到了这里,我们理解张载哲学也就有了一个极总之要,在此基础上,阴阳气的相感也就更好地展开了。
二、阴阳相感
上面已经提到虚气相感不离,因此在下面论述阴阳二气相感时太虚始终是贯穿其中的,这里可以说虚气关系就是体用关系,阴阳二气相感变化就是太虚之发用流行处。
《正蒙·乾称篇》云:
太虚者,气之体。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气散无数,故神之应也无数。虽无穷,其实湛然,虽无数,其实一而已。阴阳之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则混然,人不见其殊也。[2]63
气分阴阳,阴阳二气屈伸相感变化无穷,故其神之应也无穷,神在这里张载有解释,“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2]16。阴阳相感,即阴阳合一之不测其神妙也,感在这里也是其阴阳变化无穷的一个基础,阴阳二气相感变化虽无穷、无数,其实湛然为一。“阴阳二气,散则万殊,人莫知其一也”,此即可指阴阳二气相感之神妙不能知,也可指阴阳二气中始终贯穿着太虚本体,此则这章首句之所谓“太虚者,气之体”。
张载又说:
气 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 絪絪,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结,糟粕煨尽,无非教也。[3]41
阴阳二气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行,化生天地万物,这是张载对阴阳二气相感化生万物作的一番考察。他首先明确阴阳之性,并根据阴阳的性质特点进一步为万物生成作了说明。“阴性凝聚,阳性发散,阴聚之,阳必散之,其势均散。阴阳为累,则相持为雨而降;阴为阳得,则飘扬为云而升。故云物班步太虚者,阴为风驱,敛聚而未散者也。”“凡阴气凝聚,阳在内而不得出,则奋击而为雷霆,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其聚有远近虚实,故风雷大小暴缓。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曀霾;阴常散缓,受交于阳,则风雨调,寒暑正。”[2]12这也是张载对其宇宙论的进一步论证。在这里阴阳二气所以能化生万物者,中间正是有感也,感则聚为有象,阴阳二端故有感,阴阳相感以成天地万物。相感在阴阳二气中就有这样一个连接的纽带作用,且其发生作用也是神妙不测的,所以相感在这里也就贯穿在阴阳、虚气之不离相互间,并由此张载将本体论与宇宙论同时并建,形成他宏大的宇宙本体论,即虚气、阴阳相感中确立了他的宇宙本体论。然张载论天是不离人的,那么下面就要进一步论述相感在人与阴阳所化之万物中间发生的作用了。
三、心物相感
“有识有知,物交之客感尔”,人生活在宇宙万物之中,就必然要与物相接,而相感就有这样的连接人与物的功能,也就是人的心通过相感与物接触,从而认识世界万物,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关于张载心物相感的思想。
《正蒙·中正篇》云:“无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诚也;计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2]28意思是相感必须要得以真实的发生,否则就是妄,因此心物相感必须在人心与物之间得以真实发生,不能无物空感。《张子语录》云:“若是见闻为心,则止是感得闻见。亦有不闻不见自然静生感者,亦缘自昔闻见,无有勿事空感者。”[2]313这句话也是说明不能以空为感的内容,有事是所感必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方能感也。此感便是心与物相感,心在张载这里有明确的定名,《正蒙·太和篇》曰“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此心即是有知觉的人心。人心在《正蒙·大心篇》里有述:“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2]24张载在这里依见闻将心分为圣人之心和世人之心即凡人之心,“圣人尽性”“心能尽性”,圣人心尽性,而世人之心以见闻为狭,未尽其性也。因此心物相感在此基础上也有所区别。
《正蒙·乾称篇》曰:
天包载万物于内,所感所性,乾坤、阴阳二端而已,无内外之合,无耳目之引取,与人物蕞然异矣。人能尽性知天,不为蕞然起见则几矣。[2]63
天包载万物,所感者“乾坤、阴阳二端而已”,乾坤、阴阳二端所感则是无内外之合,无耳目之引取的。乾坤、阴阳在前面的论述中已有分析,因此乾坤、阴阳二端所感即是虚气相感也,此感与人物即心物相感异也。心物相感有内外之合、耳目之受也。所以从上面的这两句话中我们能够发现心物相感可分为不以见闻所止相感和以见闻为狭相感,前者可以说就是圣人心与物相感,后者则是世人之心与物相感,二者有分矣。
《正蒙·天道篇》云:“圣人有感无隐,正犹天道之神。”[2]15圣人之心感物,无有隐也,就像天道之神一样,“无所不感者虚也”,圣人亦是如此。《正蒙·大易篇》言:“神德行者,寂然不动,冥会于万化之感而莫知为之者也。”[2]49此神德行者就是圣人的另一种表达,故可以说圣人之心感物,无所遗,亦冥会于化而莫知圣人之为也,此感非有意也,自然所生感矣。世人之心感物则是不同于圣人,世人止于见闻,故其心与物相感则纷杂烦乱,被物所牵,蕞然异于圣人。
凡饮食男女皆性也,但己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举动,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梦而死者众也。[2]187
此即世人之心与物相感,不仅感而蕞然且心又不求,不知尽性知天求为圣人,所以最后只能醉生梦死。
除了上述心物相感之论张载还有梦寐所感与乐感人心。《正蒙·动物篇》云:“医谓饥梦取,饱梦与,凡梦寐所感,专语气于五藏之变,容有取焉尔。”此处梦寐所感也是由气在人身上的变化而言,饿了在梦中则自取,饱了在梦中则自与,这是说人与外物相接触,所感受到的在梦中就会显现出来,然而在梦中取与与,不可认为在梦中实有物。《正蒙·太和篇》云:“魂交成梦,百感纷纭,对寤而言,一身之昼夜也;气交为春,万物糅错,对秋而言,天之昼夜也。”[2]10寤梦相感只是在梦中发生,但引起梦寐相感者则在外,使人在梦中百感纷纭,但这纷纭繁多却不是于梦中实存。乐能感人心,此乐指雅乐,《经学理窟·礼乐篇》云:“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后之言乐者止以求哀,故晋平公曰:‘音无哀于此乎?’哀则止以感人不善之心。”[2]263以雅乐感人,可以培养人的德性中和之气,可以感化人心向善,此是乐感人心。上面的寤梦所感与乐感人心,都是于人心处所发于物相感,所以都可以归结为心物相感。
以上三部分就是本文关于“相感”的论说,“感”前用“相”,是为强调“二端故有感”,“感”也是在二端间发生,二端不相离,所以“感”是超越个体局限而与它者建立关系并发生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感”自身拥有一种超越性,但这种超越性又实然在万物间发生着,“无须臾之不感”,这也正应了太虚即超越形上,却又与气无所不感,虚气不相离也。从而也在侧面印证了张载哲学的核心虚气相感不离。同时张载还用“相感”来批“释”,《横渠易说·下经》云:“释氏以感为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者,皆不足道也。”张载希望用相感的真实性从思想上破除释氏的以感为幻妄。这也体现了儒家跟释氏对待人类社会的不同之处。
综上所论,可看出“相感”的思想在张载哲学中贯穿始终,从“虚气相感”到“人之相感”,是从天到人的一个宇宙本体论和人生修养论的统一。张载又从立志开始,“思知人而不可不知天,尽其性然后能至于命”[2]21,从而由人至天,这样从天到人,从人到天,张载的哲学建构也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虚气相感”始终是张载哲学的核心所在,也是其“造道”之关键所在。
[1]丁为祥.张载虚气观解读[J] .中国哲学史,2001,(2):46-54.
[2]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3]林乐昌.正蒙合校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Analysis of Three Levels of Zhang Zai’s Idea of “Sensing”
LI Wen-bin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710119)
This article analyses Zhang Zai’s idea of “ a sense of three levels” from the "virtual gas sense, yin and Yang with heart phase sense" and analyis of the false gas relations through a sense of clear. It points that the core philosophy of Zhang Zai's virtual gas sense means not to leave, it means the building of cosmology and ontology at the same time , and it means from sky to people until the eternity , so that he formed the unity ontology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through a complete whole philosophy of heaven and man.
zhang zai;void; gas;sensing;
B244.4
A
1004-4310(2015)03-0097-04
10.14096/j.cnki.cn34-1044/c.2015.03.023
2015-02-23
李文斌(1991—),男,甘肃天水人,在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