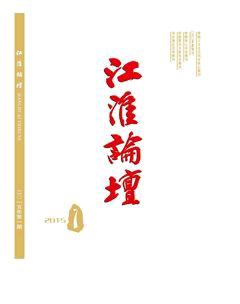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脉络及其规律探析*
李 净 戴钢书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成都 611731)
马克思指出:“人在把成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进行估计,赋予它们以价值或使它们具有‘价值’属性。 ”[1]409价值就是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的效益关系。价值意识伴随人的主体意识产生发展而逐渐生成发展,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经历由自在到自为的发展,价值意识也经历自发到自觉、自省的发展。从历史的纵向坐标审视,表现为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萌芽、生成、同构、演进及现代转化过程。而以传统价值观为深层结构演绎的传统文化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因,那么,厘清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历史演进脉络及其规律对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实践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原始社会:混沌意识与前价值观念萌生
人类的价值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随着生产、生活实践的开展,伴随文化创造与积累,经历前价值观念到价值观念的发展。从“人猿相揖别”时起,反应主客体关系意识的价值意识就萌芽了,只是此时的价值意识还是混沌、模糊的,是处于前价值观念状态的。所谓前价值观念,“主要是指人类童年状态的模糊价值意识,或者说是人类非逻辑的史前价值观念”[2]55。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先民们所能产生的价值观念并非是理性价值抽象与判断的思维形式,而只能是一种在与外界作用后被动、消极地形成的一种非理性的、非逻辑的价值思维形式。归而言之,原始社会人类的价值意识经历了从无到有,再从埋没个体于整体的集体价值意识到个体价值意识萌芽的发展过程。
大约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后,采集和渔猎范围得到一定扩展,原始先民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得到加强,人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一定发展,他们已经能够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幻想实践。原始先民逐渐认识到许多自然现象与他们的生活有紧密的联系,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他们仍然很软弱,对于许多自然现象仍然无法解释,对于自然灾害的威胁压迫也束手无策,于是他们逐渐把生活中的成败得失归结于某种自然力,认为一切都是自然的恩赐或惩罚,错误地将自然力超自然化,幻想自然现象是受某种神秘力量控制,进而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心理。以捕鱼为生的部落则主要崇拜海龙王,以捕猎为生的部落则主要崇拜山神、猎神。应该说此时原始先民的思维才逐渐将自身与自然界区分开来,才逐渐有了朦胧的主体意识,这是价值意识发展的必要前提。
图腾意识、图腾崇拜的出现才是原始先民开始认识自我的表现,第一次将眼观转向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身。图腾崇拜,盛行于母系氏族社会,意指以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为“图腾”,也就是作为本氏族的标志或象征,加以崇拜、信仰。如神话传说中,少皞氏以鸟为图腾,禹部族是以薏苡即苤苜为图腾,伏羲这个部族是以无生物——风、雷、彩虹为图腾。图腾崇拜是原始先民群体主体意识的朦胧发展。图腾是维系氏族部落秩序的纽带,是各成员的共同意识和精神支柱。图腾崇拜之下萌生的集体主义价值意识具体也规范着氏族部落各成员的日常活动,它引导本氏族部落成员间要团结、互助、关爱、平等,虽然这些意识并不是个体价值理性、自觉思维的结果,但这些是价值意识生成的发酵要素。自然在生产力仍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这种集体主义价值意识灵光还仍然具有巨大局限性,实际上,它仅限于本氏族部落成员间,只要跨出这个范围,便是为了生存竞争而产生的生死搏斗、厮杀抢掠,而“勇敢”则成了野蛮的美称,“正义”成了一部落占领另一部落的荣耀。也可以看出此时的先民们从集体价值意识本位出发形成的“勇敢”、“正义”价值意识也并非理性反思思维所致,仍然是一种非理性思维的价值意识表现。图腾崇拜下生成的集体价值意识还具有埋没个体于整体的价值趋向。面临各种蛇虫猛兽、自然灾害的威胁,原始先民为了求得生存,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3]45,此时,个体是绝对从属和服从于集体、氏族、部落的。
个体作为意识的主体和具备个体价值意识是源于祖先崇拜的出现,而祖先崇拜的出现却得源于父系制的建立。父系制阶段,男性的生产劳动作用得到加强,再加之氏族首领和家族长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人们产生了畏惧、崇敬和顺从心理,致使他们相信男性祖先的鬼魂有着强大的神力,能够保护活着的子孙后代,从而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在这种原始迷信思想下,一些氏族内部逐渐形成了对那些曾经为本氏族的发展做过巨大贡献的已故男性祖先的崇拜,并通过追掉、安葬、祭祀等仪式以表敬畏、尊敬。对祖先的崇拜起初其对象主要是父系氏族的共同祖先,后来又增添了家族其他祖先,再后来发展至对首领、对英雄人物的崇拜、敬仰。祖先、首领、英雄崇拜等已不再是物,而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崇拜对象被崇拜的原因不仅在于与崇拜者有无血缘关系,更在于是否对本氏族、本家族有无重大贡献,即“祖有功,宗有德”,体现的其社会原因。可以看出,此时,对人的崇拜已经占据支配地位,说明人类的价值意识特别是个体价值意识已经发酵萌芽。而价值意识也逐渐从自为到自觉的发展,价值思维也逐渐从非理性认识判断到理性认识判断的转变,即开始萌生以个体的利益诉求而进行价值反思实践。如《尚书·皋陶谟》曾记载,“舜帝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可以看出,在尧舜禹时期,已经初见维护社会秩序需以民众为本位的价值思想取向,这也是以人为本位进行价值思维的先例。虽为神话传说,无法考证是否属实,但从夏尊命、商尊神到周的尊礼,敬德的价值主体转换,可以追溯原始社会末期存在着以人为价值本位的思想萌芽。
二、奴隶社会:传统价值观生成与多元化发展
(一)由夏尊命、商尊神到周尊礼之价值主体转换——传统价值观的生成
《礼记·表记》言:“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可知,在奴隶社会的诞生和上升时期,即夏商西周时期,社会的价值观念经历了从夏尊命、商尊神再到周尊礼之价值主体转换的发展过程。夏尊命,即夏尊奉天命。天就是自然,命就是规律,尊天命就是要尊奉自然规律。夏尊命,自然不太相信鬼神之说,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其认识能力无法达到科学解释鬼神事宜,又要利用鬼神进行政务管理,因此不愿意,也不能够否定鬼神的存在。所以既“事鬼敬神”,但又略有意“远之”。商则尊神,乃对天神、地祇、祖先等进行崇拜,于是“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是殷商时期的主要价值取向。殷人认为,神灵鬼怪主宰着人的一切祸福,人的需要的满足,自然要祈求神灵的恩赐,鬼怪的庇佑。无论是夏的尊命还是商的尊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被动的进行价值思维,并未清晰认识到人才是价值主体,而将价值主体定位于自然、神灵、鬼怪之上,视它们为价值创造之源。在周人灭商、推翻殷统治,建立周政权以后,才逐渐实现价值主体由自然、鬼神到人的转换,把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虚无缥缈的天上拉回到现实的人间。周人承认鬼神是重要价值来源,但怀疑其恒长性,认为“天命靡常”、“天不可信”。周人认为,任何人把自己的需要的实现即价值满足唯一地寄托于鬼神,是靠不住的,而人的主观因素、主观能动作用,则对需要的满足,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们倡导尊礼。礼就是行为规范。而周人所尊之礼,非一般之礼,它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其形式表现为礼仪、仪式,其内容则表现为贯彻血缘宗族和政治等级原则的“亲亲”和“尊尊”。“亲亲”乃对殷礼“亲亲”的继承,强调宗族血缘关系,而“尊尊”则是周礼的核心,强调阶级关系。因此君权、父权、夫权在周礼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如君至尊、父至尊、夫至尊等,这也是汉代提出的“三纲”价值观念的雏形。周强调“尊尊”,乃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并非血缘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周人尊礼,事鬼敬神而远之,说明周统治者并不相信鬼神,但他们从理性的角度认识到利用鬼神可以服务政治统治。实际上,正如《论语·为政》记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殷商周的价值发展轨迹是一个批判继承的辩证发展过程,也是一个螺旋上升过程。而不论是尊命、尊神还是尊礼都是一种核心价值取向,围绕此核心价值取向而生成着一系列价值规范,从而延伸出一套相应的价值体系,但就周尊礼价值取向实现的价值主体转换而言,才可谓周的尊礼价值体系的构建使传统价值观真正得以生成。具体而言,周礼的内容和形式统一而形成了一套“别贵贱,序尊卑”的价值观念体系,这也是影响我国传统社会始终的的正统价值观念要素。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价值争鸣——传统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衰落和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这一时期是大变革、大动乱的时期,周礼的贵贱有别、尊卑有等、亲疏有则、上下有序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法继续维持。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提出不同的价值诉求,可以说,这是多元价值体系建构的时代。它是人的价值意识自觉发展的结果,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在诸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数儒、道、墨、法四家提出的价值观念体系最为显著。具体而言,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价值取向构建了一套以“君子”人格和“仁政”社会的为价值理想追求和以“重义轻利”为价值判断的价值观念体系。儒家的价值观念体系很明显是对周 “尊礼”,“敬德”价值观的进一步发展。道家则以“自然无为”为核心价值取向构建了一套以“至人”人格和“至德之世”为价值理想追求和以“无为而治”为价值实现途径的价值观念体系。代表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墨子创立的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价值取向构建了一套以崇尚“兼士”人格和“尙同”社会为价值理想和以功利价值取向为价值判断的价值观念体系。墨家构建的这些价值观念都典型地反映出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的价值心理。法家则以法治、权力为核心价值取向建构其一套以“法术之士”和法治社会为价值理想追求和以“功利尽举”的价值标准和“尽力务功”的价值实现方式的价值观念体系。除了儒、墨、道、法几家的价值观体系外,阴阳家、农家、名家等建构的价值观体系在当时影响也非常大。阴阳家持阴盛阳衰,阳胜则阴衰的价值理念,运用阴阳消长来论证社会人事兴衰;农家主张统治者应与民同耕、同食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名家则崇尚名而轻实的价值取向。而不论是从儒、道、墨、法各家还是从阴阳、农、名等各家的价值观体系来看,其间都贯穿着一条红线,突出着一个主题“天道远,人道迩”,也就是说,对人自身的关注的增强和人自身价值得到提升。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而构建起来的多元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理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封建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同构、反思、复归、没落
封建社会经历了秦汉时代“三纲五常”价值体系确立而实现传统价值观的同构到魏晋南北朝多元价值观冲突、震荡与隋唐儒释道三位一体的价值观融合而催使传统价值观的反思,再到宋元明时期“存天去欲”价值体系营建而促成传统价值观的复归,最后到晚明至清中后期启蒙价值观念的萌生,迫使传统价值观的没落与现代化转化发展过程。
(一)“三纲五常”价值体系的确立——传统价值观的同构
秦汉时代,价值观变革经历从秦推崇法治、欲利为核心的法家权力价值观体系到汉“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体系的转变,实现了传统价值观的同构发展。自秦王朝的建立,奴隶社会宣告结束,封建社会正式开启。在儒、墨、道、法等派别的价值角逐中,秦统治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考虑选择法家的权力价值论。在理论上,法家主张君权至上,崇尚急功近利,强调严刑峻法,提倡实干风气,这与秦统治者及其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相符合;在实践中,战国之初,秦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国家十分贫瘠,然经商鞅变法后,秦国国力跃居七雄之首。历史和现实,强化了秦统治者对法家权力价值观的认同。但法家权力价值观体系中的尊君权轻民意、崇功利轻精神、尚法律贬道德等价值观在大一统年代无法得民心,这种统治也无法长久。秦朝灭亡,给汉统治者提出重新确立价值观体系的历史任务,在破旧立新之际,主要采用了承接道家价值观但又破除其消极的“出世”价值取向,而追求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的黄老之学的价值观体系,包括“刑德相养”、“清静无为”、“生财富民”、“养神重生”等一些列温和的价值观念。然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者拓展宏业的追求,黄老之学的天道自然无为、人道顺应天道这种价值取向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建立大一统秩序和强化君主中央集权,乃是儒家思想的特长,更是儒家思想的深层次价值取向的选择,于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是异于先秦儒家思想的,它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核心,又采纳道、法、明、阴阳等各家之所长而构筑的封建思想体系,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取向。“三纲”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乃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蕴涵的是君权至上、注重人伦道德、尊卑等级严明、重视家国群体利益、重义轻利等价值观念。“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体系是应君权至上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而建立,是汉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和灵魂,对维护、巩固封建社会,发生了巨大作用。“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体系的确立也体现了各传统价值观念体系的碰撞、渗透、融合发展之势,是人的价值意识自觉加强的结果,也是传统社会价值观逐渐同构的表现。
(二)价值观念的震荡到多元综合——传统价值观的反思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上,主要有两次变革,一次是自春秋战国时期价值争鸣到秦汉时期“纲常”为核心价值取向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体系的同构,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价值观震荡到隋唐的儒释道三教价值观鼎立再到宋明 “存理去欲”道德价值观的重建。实质上传统价值观经历了同构到反思再到重建即复归的螺旋上升演进。魏晋南北朝的价值观念震荡到隋唐儒释道三教价值观鼎立的多元综合发展就是传统价值观发展演进的反思阶段,是价值意识觉醒的时代,而并不是价值观发展的回流与倒退,它的碰撞与融合而生成的新的价值要素,为传统价值观更高层次的发展奠定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充满战乱的时代,而“三纲五常”的价值观念适应的是集中的君主权力和大一统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其一体化的调节功能自然失灵。而价值信仰危机的出现,造就了这是一个没有权威价值指向的时代。人们又无拘无束地凭借自己的利益需要、价值满足而构建出一些列的价值观念体系。如,“任自然”的价值观念体系在此时广为推崇,“这是由于道家思想对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愤激批判,以及对超越这种黑暗和痛苦的个体自由(尽管是单纯精神上的自由)的追求”。[4]6而相反,从政治局势发展出发的名法学派则将关注点从天道转向人道,突出个体的价值,深刻揭露社会的各种腐朽和弊端,主张依法治国、唯才是举的价值取向。佛教东渐之后,逐渐摆脱对中国文化的依附,建立起一套以因果报应为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系,广为人们认可。此外,道教价值观念在上层士大夫和民间也大为流传,还有胡文化的价值观念的介入等。儒家的纲常价值观念遭到叛离,但并未彻底被背弃,它依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这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代表各种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冲突与渗透、融合,形成了与动乱时世相适应的价值观念震荡态势。社会分久必合,历史结束了四百年的战乱,出现了统一稳定的太平盛世。新的局势的产生,必然会引起相应的价值观念变革。隋唐时代依据凡是有利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各种价值,都是他们所崇尚的对象原则,建立起以儒家价值观为正宗,儒、道、释“三教”鼎立的价值观念结构,形成了多维一体的价值观体系。归而言之,隋唐这种三教鼎立价值观取向的演变,也并不是要渐行与儒家纲常伦理价值观体系的决裂,而是在既有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增加新的因素,实现新的超越,推动了价值观念由旧到新的演变。
(三)“存理去欲”价值体系的营建——传统价值观的复归
从北宋至明代中叶是中国社会处于封建社会后期,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又一次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价值取向的价值观念体系得以营建,实现了汉代以来的“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取向的道德价值观体系的复归。但不是简单的对 “三纲五常”为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继承,而是一种上升的发展,即在儒释道价值观念的进一步融合发展过程中,实现了由外在的行为规范向内在的伦理道德的重大转折。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王守仁说:“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传习录上》)也就是说,“天理”是人的道德理性,“人欲”是人的生理欲望,“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高扬人的道德理性,抑制人的生理欲望。从而衍生出包括尚公非私、重群轻己、崇义贬利等一系列道德价值观念。可见,“存理去欲”价值观的建构方式,是将封建的三纲五常、人伦道德常态化、形式化,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理论思维最严谨、内容构思最充分、体系设计最完整、持续时间最长久、影响范围最深远的价值观念体系,它把封建集权主义价值观推向了发展的高峰。然而“存理去欲”的价值观体系,并非价值观发展的完美顶点。它一方面增强道德价值意思的理性与自觉,确实提高了道德人格的价值地位,深化了精神境界追求的层次,具有把人从狭隘的物欲世界解脱出来的积极作用,但它过度压抑了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欲望,弱化了人们的现实经济生产活动,具有阻碍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和物质文明创造的消极作用。因此,到封建社会末期,随着新兴生产关系,生产阶层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价值观念的崛起,又造成价值观念的冲突世态的出现。
(四)“天理”的背离,启蒙意识的开启——传统价值观的没落
随着生产实践的推进,生产力的提高,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的萌生,社会发展在逐渐冲破旧的束缚与羁绊。晚明至清中后期,价值观领域的主旨都是对“存理去欲”道德伦理价值体系的批判、抨击与反思,这是人们对秦汉以来以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进行的自觉反省与理性批判,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十字路口,也是传统价值观崩溃,新价值观絪缊的时代。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从它确立的一刻起,就内在地包含着批判自我、否定自我的因素,从而决定着它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存理去欲”价值取向的对立面就是现实欲利价值取向,在对“存理去欲”价值观念体系的批判、抨击过程中,追求现实欲求的价值观念日益得到认可、推崇和弘扬。该价值取向是伴随经世实学思潮的出现而出现,其主张经世致用、实事求是思想,高扬个性、人欲、功利、情感等价值理念。而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宣告中国进入近代史,意味着中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趋势无法阻挡,为适应社会的急剧转型,保家卫国,代表中国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进步势力又致力于适应近代社会生产发展要求的新价值观念的建构,他们以人权为核心价值取向,提出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等价值观念,开启了近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启蒙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新时代新生力量,高扬“个性”解放旗帜,对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束缚人民头脑的重君轻民、重群轻己、重义轻利、重德轻智等价值观念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抨击,对翻转价值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标志着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没落与向近现代化转变道路的彻底开启。
四、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生成演进规律厘析
经过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生成、发展、演进历史脉络梳理,归结起来,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生成演进遵循的规律主要有经济基础决定律、意识形态掌控律和文化生态建构律等。
(一)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生成演进的根本原因——经济基础决定律
“经济基础决定律”指,一定社会的价值观是由该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物质生产状况所决定,该社会的价值观是建立于该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物质生产关系的价值观念反映。该规律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生成、发展、演进的起着根源性、根本性作用。马克思曾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5]186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属于观念上层建筑,自然由该社会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必定是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生存离不开对自然的依赖,因此形成了对自然的依赖、崇拜价值意识,同时,由于生产工具粗糙,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必须依附集体力量,从而形成了集体高于个体,个体埋没于整体的集体主义价值意识。进入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引起的经济、政治、阶级等方面的变化和矛盾斗争必然在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上反映出来,于是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价值争鸣与多元化发展趋势。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社会自然采纳追求大一统和维护君主权力的儒家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为主流价值取向,于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价值观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始终,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价值观念的适当调整与变化也是出于社会的经济制度的调整和经济自身的发展。而明末至清王朝统治时期,出现的追求现实欲利、崇尚个性解放、推崇自由平等等新价值观念则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关系萌芽的价值观念表现。可知,一定社会的具体经济生产水平对该社会的价值观念取向具有决定性意义。
(二)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生成演进的主导因素——意识形态掌控律
“意识形态控制律”指,一定社会的价值观是受该社会的统治阶级掌控,是统治意志和统治思想的集中反映,服务于政治统治与意识形态建设。该规律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生成、发展、演进起着重大的主导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550该社会的具体价值观念便是其统治阶级统治思想的现实实践。由于在原始社会,国家还未出现,不存在统治阶级,该社会形态下形成的前价值观念便是自然形成。随着分工的出现,进入奴隶社会,便出现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分。不论是夏商的尊命、尊神还是周的“敬德”,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统治者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对儒、道、法、墨等的各自推崇,都体现了奴隶制王朝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力对社会价值观念选择起到的重大作用。进入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王朝的建立,秦对法家权力价值观的情有独钟,汉代以维护君权之上为要旨三纲五常价值观体系建立,隋唐时代的儒释道三教鼎立的价值体系选择,宋明时期的“存理去欲”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可以说都是封建统治者直接推行的。而那些相悖、相左的价值观念则遭受残酷打压和排斥,如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等都具有对统治者所认为的异端价值观进行严格限制、打压的意义。因此,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就相应存在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不论是奴隶社会维护奴隶主分封统治的各派传统价值观观还是进入封建社会后为维护封建君主中央集权制而选择的以儒家道德伦理价值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的价值观是受意识形态在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之下的可选择范围内的掌控行为所致。
(三)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生成演进的导航向标——文化生态建构律
“文化生态构建律”指,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受该社会的具体文化环境、文化生态影响,由该社会的文化世界所建构。该规律对传统社会价值观生成、发展、演进的起着导向作用。价值意识是伴随文化世界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文化世界的逐渐丰富,又逐渐同构价值思维方式,进而促成社会价值观的产生。原始社会属于前价值观念阶段。在原始社会状态下,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文化世界对人的影响作用和人对外部世界的价值反思作用都很弱,主要是被自然力所影响,因此形成了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及朦胧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奴隶社会,文化世界、文化生态逐渐丰富起来,人的自我意识逐渐提高,文化对人的影响及自身对外界的价值反思作用逐渐增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齐聚形成的百家争鸣之势,为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文化基础,而根据不同的文化体系建构起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如代表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代表墨家思想的功利价值观、代表法家思想的权利价值观、代表道家思想的自然价值观等。封建社会,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便就凭借其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的优势成为贯穿封建社会始终的主导文化,引导着整个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取向,纲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便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随着明末清初,一大批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思想文化的传入,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等新兴价值观念也便应运而生。此外,“文化生态建构律”在强调文化世界、文化生态对社会价值观的导向意义时,也强调社会文化的传承性与其深层结构——价值观的传承发展意义。因此,传统社会价值观是在具有传承意义的文化生态下建构起来的价值观,其灵魂、精髓自然具有一致性。最具有代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延续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然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以纲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为主流价值观,只是随着价值理性逐渐觉醒、价值反思逐渐增强的逻辑理路向前展开演进。
五、余 论
从原始社会的混沌意识与前价值观念萌生到奴隶社会的传统价值观生成与多元化发展再到封建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同构、反思、复归、没落,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生成演进遵循着经济基础决定律、意识形态掌控律、文化生态建构律等规律,是客观历史条件发展与历史主体合力作用的必然。而贯彻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历史生成演进的规律具有普遍性与根本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与确立便是其作用所致及其在当代的最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对传统社会价值观进行批判继承与自觉反省的结果。因此,科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实践必须立足于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演进脉络及其规律掌握的基础之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 2 卷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