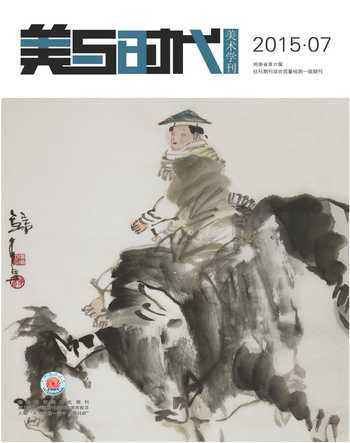论日本美术因素对任伯年绘画的影响
摘 要:在任伯年初出道时期的上海,已经出现了三种传播日本文化的载体可能会与其本人发生接触,并对其艺术创作产生影响。这三种载体分别为:(一)当时出现于上海的日本进口工艺品或商品;(二)伴随日本移民一同流入上海的日本本土文化(其中以日本歌舞妓、浮世绘为代表),任伯年当时在上海的朋友交际圈。加之任伯年“学古而变,取洋而化”,善于借鉴各种新鲜事物或舶来品之精华。为此,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认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及社会情况下,任伯年在通过各种途径接触或了解了存在于上海的日本文化或者是来自于日本的手工艺品后,很有可能将其中的一些元素或是技艺借鉴或应用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
关键词:任伯年;本艺术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于1853年,结束了近两百年的锁国政策。在贸易上由被动的“居贸易”成为主动的“出贸易”,促使中日官员,商人及文化人在文化方面等积极互访,交流。日本在上海的移民从1865年到1903年急速增加三千多人[1]。东洋茶馆、东洋戏法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上海成为风尚。至此日常层次的日本物质文化产品在中国已得到大量的流通。
说到美术、艺术品等文化交流,我们可以从商业交易情况中寻找痕迹。
名仓予何人在《支那见闻录》中记录到1862年日本锁国后第一艘到达中国的商务官船千岁丸号的交易情况:
“本朝产物中,支那人得之而喜之物,大概如下:刀枪、陶器、人参、赤铜、纸类、椎茸、葛粉、熊胆、晴雨伞、漆器、金、鸡、杂药;……。”[2]
而中国上流社会喜好赏玩日本折扇、莳绘漆器、屏风、日本刀等工艺品的意识,并不是19世纪特有的现象。而早在北宋就出现记载,南宋已经初具模型了。书成于1621,由文震亨(1858-1645)著的《长物志》,就已开始品评日本的各种工艺品。而千岁丸号所带来的工艺品总体上也是继承了晚明的传统。
在不久后的1868年,日本人在上海经营的第一家商店“田代屋”,是一间以售卖进口日本莳绘漆器、有田烧陶瓷为主的商店[3]。而这正是任伯年入沪的那一年,说明任伯年来到上海时,上海就有了正规的日本工艺品店了。后来,“崎阳号”“木棉屋”等商店也陆续开业,并在当时的《申报》上刊登售卖莳绘漆器的广告。
蒔绘,实为日本一种漆器技法。用漆描绘图案,撒上金银等金属粉及色粉,等干燥以后再在表面涂漆,完全干燥后用木炭打磨,以求达到精巧华丽,整体大方的装饰效果。题材多为花鸟、装饰纹样,也有部分是描绘人物、山水的。
在任伯年的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不少用金粉掺胶作于黑纸上的作品。如任伯年作于1872年的《鹦鹉》。其是在蓝盏扇面上,鹦鹉与果树均由金液积染、厾点、勾勒而成。鹦鹉的刻画相当细致。嘴部与额、颈部的衔接,耳羽的区分均十分到位。覆羽的刻画更是精致,除每片都有深浅虚实变化外,还刻画了羽茎,而羽茎的走向也完全符合鹦鹉生理结构,使整只鸟颇为生动、逼真。除落印外均无它色。而从大量的这种类似黑底金绘的蒔绘作品来看,我们不能否认任伯年有可能受到了当时在上海受欢迎的日本蒔绘工艺品的影响。
另一个可以作为图像输出考虑的,就是日本浮世绘与歌妓。
首先,当时浮世绘的传入是有记载的,尤其是日本的春画,更是被政府禁止的。当时的日本浮世绘,从葛饰北斋(1760-1849)开始,出现了大量以对比色作主要基调的作品。
在葛饰北斋所作的春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戏剧性的衣服褶皱与人物表情,画面在统一的暖色基调中安排了黑白、红绿、黄紫的色相对比。这些颜色的比例又是经过巧妙安排的,整体统一之中又以色彩的强烈对比加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我们可以在任伯年的一些人物画作品中寻找到相似之处。
葛饰北斋这一代的日本画家色彩运用的特点大多以对比强烈为主,并且影响深远。不仅现代的一些日本画家受这样的色彩运用特点的影响,如佐伯俊男(1945-)、村上隆(1963-)等,甚至当时印象派的梵高、莫奈等都有临摹、研习的记录。而这些画家的绘画题材丰富,从人物、风景到花鸟静物都是他们的绘画题材。有视觉冲击的图像被输出到上海,作为当时的海派画家的任伯年,也是有被影响可能的。
至于当时成为申江一景的歌妓,如在1884年吴友如(-1894)的《申江胜景图》中,“东洋茶楼”已成为申江一景。[4]我们也能从他们的服饰上找到丰富的色彩元素。需要注意的是,和服的华丽色彩和明快的对比的确影响了当时不少日本画家的创作设色,如铃木春信(1725-1770)、喜多川歌磨(1753-1806))。这种歌妓的服饰,是从奈良时期从盛唐引进的。虽然后来平安、桃山时期渐渐摆脱外来的影响,发展出独有的奢美与精致的特色,其衣服色彩也开始多样化,但整体还是保留唐代“唐衣”的样式的。而这种类似唐衣的和服在一千多年后又出现在上海,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回流。所以当时歌妓在上海的风靡,甚至有详细地叙述日本歌妓的发式、衣服的书籍,如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而这种在服饰上的色彩关系也影响到了海派画家人物画,甚至花鸟画的。
而17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任伯年在上海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除了众所周知的西洋文化外,其所面对的,正是重新发现日本商品及文化的上海,自然会接触到这些图像语言并可能受其影响。这些鲜艳明快的图像语言是有刺激到当时海派画家的可能的。
另一个很重要因素的就是任伯年的人际网络。首先,任伯年运用家传的写真术为胡公寿(1823-1886)、张熊(1803-1886)……等绘过画像。而需要留意的是,这些书画名家,大多与日本人有交往的[5]。作为任伯年出道时上海的重要赞助人胡公寿和张熊,是当时上海中日书画界的龙头。几乎所有来到上海的日本人都以能拜访其人为荣。如日本商人、收藏家岸田呤香(1833-1905)就希望以日本画家川上冬崖(1828-1881)的画作换取胡公寿等人的作品,后来也成功获得张子祥赠送的《淞江送别图》[6]。
在任伯年早期的人物作品中,常见有胡公寿补景、题字,任伯年也曾作《胡公寿夫人像》。张子祥更是“见伯年画大奇之,乃广为延誉,不久,伯年名大噪”[7] 。胡公寿和张子祥不但拥有丰富的人脉,帮助任伯年建立其在上海的关系网,同时也应该引荐了不少日本关系。《沪吴日记》就记载到当时与胡公寿深交并互相学习的日本南画家安田老山,“寓沪以有三五年,稍解唐话,常与胡公寿任伯年缔交”[8]。
然而,上海书画家与日本人交往,一方面是上面谈到的艺术交流,另一方面是有着相当大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王冶梅在日润笔费也有三、四千之多,王韬在1879年旅日时,“卖字一月,而获千金”。胡公寿、张子祥与日本画商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当时上海书画商圈已经比较成熟,旅沪的日本画家安田老山(1830-1883)可以在上海“以书画供旅资”也能说明,不但日本画商收藏中国书画,不少受过教育的上海人也是相当喜好收藏日本书画的。
任伯年所处的交际圈和当时上海的社会背景,会使任伯年有很大的机会促使其与日本画家、画商有密切的接触,并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日本文化。
任伯年作于1873年的《三狮图》,图中金盏纸上描绘一只母狮正转身注视着正在嬉戏的两只小狮,略带灰绿的母狮与淡染赭红及白色的小狮子们与金盏背景的搭配。这种有变化和非戏剧性冲突对比的和谐感,在国画中相当少见,却接近于16世纪日本狩野派的一些配色做法。而狩野永德(1543-1590)的代表作《唐狮子图》,画面中的一对狮子的用色就与《三狮图》近似。
《三狮图》中的母狮动势由左上而右下,斜跨画面,用俯视的角度描绘母狮的硕大的体型,还有那刻意的以右边画边裁去母狮左肩,非常成功制地造出一种有动势与空间深度的效果,可能更接近于后来对狩野派改造的“四条派”。之前提到的川上冬崖,主要是以学“四条派”入门的。因此,任伯年是否从胡公寿或者其他来源看到过“四条派”的作品并尝试借鉴,这种可能性也是值得考虑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发现在任伯年初出道时期的上海,已经出现了三种传播日本文化的载体可能会与其本人发生接触,并对其艺术创作产生影响。这三种载体分别为:(一)当时出现于上海的日本进口工艺品或商品;(二)伴随日本移民一同流入上海的日本本土文化(其中以日本歌舞妓、浮世绘为代表),任伯年当时在上海的朋友交际圈。加之任伯年“学古而变,取洋而化”[9],善于借鉴各种新鲜事物或舶来品之精华。为此,根据以上种种,我们可以认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及社会情况下,任伯年在通过各种途径接触或了解了存在于上海的日本文化或者是来自于日本的手工艺品后,很有可能将其中的一些元素或是技艺借鉴或应用到了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中。
注释:
[1]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名仓予何人.支那见闻录[A]小岛晋治.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C]ゆまに书房,册11,第209-210页。
[3]米泽秀夫.上海史话[M].东京:东京亩傍书房,1942:92-93页。
[4]吴友如.申江胜景图.申报馆申昌书画室,1884年,卷下,二十四
[5]参考赖毓芝.1870年上海的日本网络与任伯年作品中的日本养分[A].《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4期,民国92年,第182页。
[6]《东京日日新闻》明治十年(1877年)12月26日
[7]徐悲鸿.任伯年评传[A].龚产兴.任伯年研究[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页。
[8]冈田篁所.沪吴日记,明治五年二月。
[9]薛永年.海派巨擘任伯年的生平与艺术[M]卢辅圣主编.朵云第55集.任伯年研究[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
吉哲夫,美术学硕士,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美术学。
——从任伯年到徐悲鸿”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