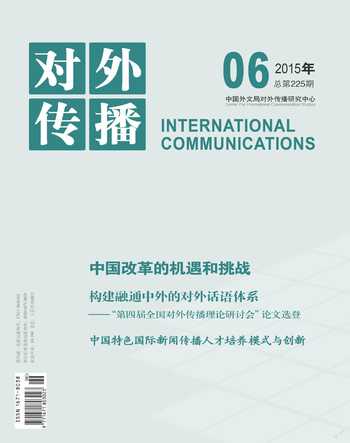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焦虑与因应之道
刘洪涛 谢江南
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性”
自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伊始,学术界就将其应用到中国文学全球发展的论述中。其时,中国正在经历从朝代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日益觉醒,中国的“中国文学”、“世界文学”观念因此得以创生。郑振铎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世界文学的学者,他于1922年发表的《文学的统一观》一文,认为人类文学虽有地域、民族、时代、派别的差异,但基于普遍的人性,文学具有了世界统一性,这就是世界文学。把普遍人性视为世界文学统一性的基础,虽非郑振铎独创,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这样的世界文学观反映了中国新文学渴望与域外文学建立广泛联结,从“人类性”的高度思考民族文学发展方向的思想。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的世界文学观经历了二次重大转向,其一是接纳了前苏联的“先进世界文学”观念,其二是增加了世界文学的东方维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文学开始复兴,而“走向世界文学”被看成是复兴的重要途径。曾小逸在其主编的文学研究著作《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1985)一书的导言中,系统而强烈地表达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趋势与愿望。而事实上,这部著作的实际内容,是研究中国现代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学的影响。这样的内容与曾小逸在导言中的表述构成了一種对应关系:所谓走向世界文学,就是接受外国文学的影响,用西方的先进文学革新落后的中国文学。1949年之后,中国文学先是经历了17年单方面向苏联文学学习,随后是10年“文革”时期的闭关锁国,已经饱受封闭之害。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急迫地需要打破自身的孤立隔绝状态,汇入世界文学大潮,而学习、借鉴、化用外国文学的先进经验,被描述成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学者们谈的虽然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功经验,关照的却是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发展的现实问题。
进入到21世纪,这种依靠单方面输入来建立与世界文学联结的模式在中国开始受到质疑。这一质疑,集中体现在陈思和等学者2000-2001年在《中国比较文学》杂志上发起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的讨论中。这场讨论的初衷,是试图解决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出现的方法失效问题。但以今天的眼光看,其意义远不限于此。它是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民族越来越自信的背景下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走向世界文学”的概念,是将中国文学当成自外于世界文学的“孤儿”,其地位和性质是从属性的,依附性的。而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是把中国文学看成世界文学的参与者,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其诸多世界性因素,具有本土生成性和原创性。由此,中国文学被放到与其他国家文学平等的地位上,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构建者。
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开始在国家汉办支持下,实施了“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其具体内容,是在美国创办Chinese Literature Today英文杂志,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召开“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三项活动响应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无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这样的命题在二十年前,甚至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标志着百年来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在经历了一个“我拿”到“我有”的发展后,开始向“我给”转变;这也说明中国文学已经自信强大到拥有了足以影响他国的实力,并且试图“输出”这种影响,使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
“成为世界文学”是始终不变的追求
纵观百年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史,可以发现,其中包含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论述,虽然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从世界主义到民族主义,从吸纳到输出的转变,但“成为世界文学”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如此强烈的“走向世界文学”的冲动,与国际学术界对世界文学的复杂论述形成有趣的对照。卡萨诺瓦在其《文学的世界共和国》一书中,把近代以来的世界文学看成是欧洲文学力量(尤其是法国文学力量)不断扩张,逐渐征服,同化亚洲、非洲、美洲文学,使之一体化的过程。按照这样的论述,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处于这个世界文学体系的边缘地带,是“西方化”的产物。汉学家宇文所安更早感应到世界文学发展的不平等性,在1990年发表《全球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借讨论北岛诗歌的可译性,反思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西方霸权及其危害。安德鲁·琼斯在1994年发表《“世界”文学经济中的中国文学》一文,呼应宇文所安的观点。他直言歌德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充满了东方主义修辞,是以帝国主义方式构造的一个概念。而要减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阻力,应该推倒世界文学话语高墙。
自歌德创制世界文学观念以来,“成为世界文学”一直被看成民族文学获得提升的通道,意味着至高的荣誉。在当今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代,国际上形形色色的奖励机制,如评奖、排行榜、文学节庆、会议、书展等活动,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把民族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变成了一种竞争活动。这种现象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肯认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因为评价体制永远受少数人控制,而获奖者少之又少,加之有高额的物质奖励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荣誉,这一荣誉反过来又会刺激图书的出版和销售,给作家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争取肯认的竞争往往异常激烈。这就会给很多作家一种导向,让他们去费心猜测:这些奖项授予了什么类型的作品?然后去投其所好。又因为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评价体系都在西方,而最想进入世界文学空间的往往是非西方作家,因此,投西方所好就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给指责者以口实,给作家以巨大压力。1987年张艺谋执导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之后就受到过这种批评。宇文所安、安德鲁·琼斯等汉学家感应到世界文学发展的不平等性,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著文,反思世界文学话语中的西方霸权及其危害。他们认为要减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阻力,应该首先推倒世界文学话语的高墙,抛弃这套游戏规则。但如何能真正打破这种魔咒?其实宇文所安和安德鲁·琼斯提供的并不是有效的办法。他们不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在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走向世界文学”的巨大惯性,也不能深刻体悟后发国家的文学在世界文学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强烈愿望。而在全球化时代,更不可能再关上国门,自产自销、自吹自擂。参与国际竞争是必然的,无从回避,也不能回避,国家如此,文学同样如此。
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翻译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首要选项。美国学者达莫若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以及“因翻译而增色加分的作品”。第一个定义之所以重要,在于提出了一个“世界文学”的公共空间。民族文学不是天然就能成为世界文学,而必须像光线发生折射那样,穿过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构成的介质,在椭圆形空间中反射出的第二个焦点,由此形成一种混杂、共生的作品。“椭圆形折射”理论预设了文本经过翻译被扭曲和变形的必然,但这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会使原文本获益。莫言2012年获得诺奖,证明了达莫若什的论断。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英译本存在大量改写和变异的现象,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如果我们取原作本质主义的态度,它们就是次级的衍生品,但如果从世界文学角度看,这些译本体现的就不止是文本的遗失和变形,更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以及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移植与重生,因而对中国文学是有益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受限的。翻译受译者、市场等因素的制约,而最终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国是外国文学翻译大国,每年有海量的外国作品翻译到中国。比较之下,又有多少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又有多少优秀的译作产生?我對此并不乐观。如果我们都挤在翻译这座独木桥上,认为成为世界文学只有这华山一条路,那是目光狭隘的表现。
成为世界文学不止翻译一条路,至少还有另外四条途径是以前中国学界所忽略的。
其一是区域世界文学。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唐丽园写于2010年的论文《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①是一篇研究东亚区域世界文学的佳作。按照西方的世界文学话语,世界文学的形成从欧洲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区域。因为占据了所谓“源头”的优势,西方文学于是被安稳地放置在世界文学的中心区域,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文学,则被置于边缘区域。唐丽园认为,这样的世界文学话语应该被打破,新的世界文学研究必须采纳对文学、文化和民族更多元的理解。唐丽园这篇文章考察了东亚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现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改写、化用、交流等现象,指出其创造出了一个相互平等、彼此混合、边缘模糊的文学接触“星云”(nebulae/ nebulas),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共同体。唐丽园期许如此分析非西方文学作品在区域内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整合与重塑“地方的”和“全球的”概念,为世界文学找到一条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并接近区域中立的途径。
其二是华语世界文学。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在非华语地区用华语写作的作家及其作品。它以中文及其文化为根,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其中北美、欧洲地区的汉语世界文学更为活跃,产生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传统上,国内学界将其称为“海外华文文学”或“世界华语文学”;在论述性质和地位时,多认为它是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的延伸和发展。而一批北美汉学家,如王德威、史书美等人,则用“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来界定这些“中国之外和处在中国或中国性边缘的文化生产场域的网状系统”中生产的文学,意在强调其独立于中国大陆文学的性质。“华语世界文学”的概念能够整合和超越上述两种认识的差异性,既不回避其驳杂性、异质性、在地性,同样重视其与大陆中国文学的血脉联系。这个概念犹如一根魔棒,有点石成金之妙,把原先被看作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围或边缘的部分,变成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锋,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世界文学的中国性。不可否认,华语世界文学还远没有达到像英语世界文学、法语世界文学那样的世界化程度,但这的确是可以期待的。
其三是华裔世界文学。这是以血统作为联系纽带的世界文学,有犹太裔世界文学、非裔世界文学,当然应该有华裔世界文学。所谓华裔世界文学的概念,是指来自中国或有中国血统的作家,用其所在国家语言进行创作的一个群体,如华裔英语文学、华裔法语文学等。目前北美华裔文学的影响尤其大,谭恩美、汤婷婷、赵建秀、裘小龙、哈金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些作家所在国来说,他们是本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从族裔角度看,他们又是世界化了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同双重国籍一样。历史上,林语堂、张爱玲的英语作品,也是被当成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在当今族裔多元、血统混杂越来越普遍、跨国迁移越来越频繁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这些作品拒之门外。
其四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世界文学。它是指在异文化空间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碎片式存在。前几种形态的世界文学都体现为具体的文本,是一部部完整的作品,而这里所指中国贡献的世界文学并不以独立、完整的文本形态出现,而是寄生在受中国文学与文化影响的域外作品之中,构成了这些文本的重要元素。这些作品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学文化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在东亚各国如此,欧洲、美洲也是如此。诗人庞德通过翻译创作的诗歌《神州集》《刘彻》,以及化用了许多中国文化文学元素的《诗章》,都属于这一类作品。现在美国有一批学者研究的“跨太平洋诗学”(TransPacific Poetics),着力点就是美国文学中的东亚文化元素。费诺罗萨、庞德、斯蒂文斯、摩尔、斯奈德、叶维廉、车学敬、凯鲁亚克、金斯堡、肯尼斯·雷克斯罗思、约翰·凯奇、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布莱、默尔文、罗伯特·哈斯等众多美国诗人和作家的创作中表现了这些元素,从而构成了“跨太平洋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跨太平洋诗学”不同于传统影响研究,它摆脱了仅重视文本影响和文化还原的狭隘思路,从民族志、翻译、互文旅行等多角度切入,对这类美国诗人和作家作品中蕴含的地域之间对话、想象、相交、混杂、统一特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目的是呈现西亚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如何注入以欧洲文化为根基的美国文学,帮助其形成自身特性。这一类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化融入异文化最深,影响最持久,也最重要,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追求的最终结果,理应受到重视。
总之,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有多样形态的世界文学,任何一种世界文学都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持续增强中国文学母体的强健,使之从多种途径不断扩大国际影响,让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
「注释」
①译文载《世界文学理论读本》,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