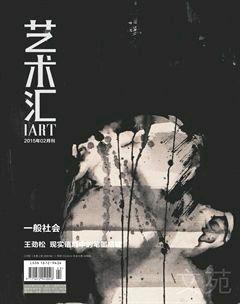投入还是抽身而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参与与否的问题(五)
在研究当代艺术与思想实践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遗产时,我们将董希文的经历和实践作为一个历史个案来进行考察。1976年文革结束以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唯一的、合法的和压倒一切的创作形式的历史也随着结束,并成为艺术创作中被抛弃、被反思和被批评的对象,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来渐渐地淡出我们的视野之中,不再成为一个与当今的创作和思考直接关联的显性影响。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种伴随着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架构被搭建和确立而被塑造出来的艺术思潮只是停留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末。恰恰相反,当代艺术领域还未充分地厘清和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其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冲击、摩擦、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结果极其蔓延至今的深刻的影响。当代艺术家们和当代艺术的论述中往往试图通过摆脱它的外在形式,通过站到它的对立面,来宣称在创作上具有独立的、反叛的、自由的和当代的姿态,这种独立的、反叛的和自由的姿态似乎给艺术的当代合法性建立了基础。这种主导性的思潮使我们在观看和论述当代艺术时人为地将它与1976年之前的艺术历史划清了一条本不存在的界线,也使我们未能充分地审视在此之前几十年中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潮和话语包裹之中但想法立场迥异的历史个案。与此同时,我们也仍然未能透彻地理解我们今天对于创作和历史的评价机制和价值判断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对于这个问题甚至存在着一种有意无意的回避。
自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逐渐转化成为超越创作技巧和风格之上的意识形态语言和逻辑之后,我们一直生活在文革期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加速内化后对于它的反思不断被延迟的状态之中。而这个延迟的过程既包括了自上而下的压力、整个社会的意识,也包括了个体的无意识和自我需求,它并不是某一方面单独的意志。在社会政治和思想史的视野和范围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进行理论探讨,是祈望借此获得我们看待历史与现实的视野,最终的出发点是提醒自己在观看当代创作和思考的时候必须始终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对于国家和艺术现代化的诉求一起带进来考察。直至今天,在中国艺术行业中所开展的工作——包括了创作和对于创作的批评——并没有脱离这样的一种思考逻辑,只不过我们将描述的基础错误地建立在一个将当代艺术家的工作与官方体制中对于艺术的期待和诉求割裂,甚至彼此对立的角度来观看。我们总是带着同一个视角和期待来选择创作和选择描述创作的角度,并且掉入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逻辑来创作和评判创作。
作为一种创作方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除了被共产党所推崇以外,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当现实主义最初被一部分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介绍到文学领域之时,它与现实形态的亲密感就立即吸引了从事文学、戏剧和艺术创作的知识分子。在艺术领域里,现实主义油画和刻画生活的版画被艺术家们所青睐。在对于现实问题的投入当中,一方面人们希望通过国家的强大,包括在文化上的强大来摆脱来自西方的入侵;另一方面人们也希望通过学习借鉴来自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方式来反映对于国家和生活组织方式现代化的诉求,并逐渐摆脱封建的社会形态。这些交织着对于欧美等国作为殖民者的仇恨与文化思想上的向往并希望能有所借鉴的复杂情绪笼罩着中国的知识界,而且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们始终以自己国家的兴旺作为这些诉求的根本基础。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现代化的理想结合起来观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它本身所具有的先进性的意义和对于艺术家们的吸引力。对于知识分子们而言,它具有一种投身于现实的在场感,这本身是充满魅力的,同时,它符合了艺术家们将自身的理想与对现实的改造和对于国家的进步的追求结合的深层欲望。这也与他们所依赖以为思想之本的中国历史文化资源的限制有关,他们的用意在于使危机之中的国家适应于现代条件的挑战,在艺术方面如何使国家的主体叙述能够形成,并在国内和国外能够具有说服力和影响。
进入20世纪,占据了舞台中心的是以“救亡”为主要诉求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想呼应的以“改天换地”为目标的历次革命。自20世纪初期,向西方学习的倾向与行动,已实践在私人兴办的油画美术教学和流传甚广的通俗美术之中。上半个世纪接受了西方早期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熏陶和训练的艺术家们,比如象董希文等同时代的艺术家,在中国进入革命时代之时很快找到了一种位置感。这种位置感是置身于革命之中的,也是与当时在国内倡导阶级平等、消除封建制度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思想相呼应的。在对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时期的印象之中,共产党总是以正确的、正义的、进步的新青年的形象被描述和呈现出来。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纷纷在40年代末开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将自己对于艺术的抱负和对于国家、民族以及文化的责任感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了一起。新中国建立后,从解放区进入到北京的大批文艺工作者也把革命的文艺思想带到北京。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形成了一种时代精神,对于当时的创作者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如此的时代精神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承载了在建国初期一批艺术家所提出的“油画民族化”的思考和所开展的创作实践,这使一种源自欧洲的艺术样式找到了与本土的政治方向、野心和关注点相结合的可能性,也使其进入中国的艺术领域有了最有说服力的中介:为政治而服务。在共产党所开辟的天地之中,在20世纪早期接受西方艺术熏陶的艺术家们找到了将他们所学习的变成中国的,用于中国的现实的用武之地和在政治上的动力。他们受到重用,获得施展手脚、发言的平台,一方面在被划定的意识形态边框中工作,一方面,作为艺术家的本能不停止地对于艺术实践本身进行锤炼和思索。
因油画作品《开国大典》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家喻户晓的董希文为例,自小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和受敦煌艺术的深刻影响,他的父亲董萼清是浙江绍兴颇负盛名的收藏家,“以酷爱艺术的情性为他的早期艺术教养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使他在正式开始绘画生涯之前便已经熟悉了像董其昌、任伯年、徐渭、石涛、八大山人这些对他产生了启蒙作用的大家,从而对中国传统艺术有了非同一般的了解和认识。” 1而身为油画家,他虽没有去欧洲留学的经历,却到过法国统治时期的越南,在巴黎美专分校跟随法国人学习。而对董希文影响更深的是他在1943年至1945年的两年半时间里,对敦煌艺术的深入研究与临摹。“从表现形式上,董希文高度称赞敦煌壁画上的人体描写,认为这些艺人能用极其单纯的色彩和线条,画出肉体细腻的色调和弹性,实在令人折服。”2在潜心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和踏踏实实的临摹壁画的实践中,董希文深深受到传统绘画的审美熏陶,并且学到了形成这种审美情趣的传统造型手法。“通过对敦煌壁画的研究,董希文更加深了对民族艺术传统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他对于民族文化艺术的崇高信仰。正是这种信仰,使他在学习外来的油画时,自觉地把民族艺术的形式与精神融入到油画中去,从而使油画体现出中国风格的艺术精神。” 3除了个人所受的艺术教育和熏陶,董希文对于民族形式的热切追求,同时代的精神也分不开。“董希文欣然接受了党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方针,以及文艺面向工农兵的服务思想。” 4他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专注点与共产党的文艺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甚至可以说,董希文的个人理想与新政权所倡导的文艺发展方向在现实中达到了统一。董希文由此在现实中进一步探索并不断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而新生的中国也需要董希文这样出色的艺术家来实践自己的国家意志。董希文的艺术创作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就大大增强了他进一步追求民族表现形式的自信心。”
尽管董希文追求“油画民族化”的诉求与共产党对于文艺创作为政治服务的要求有重合之处,但在艺术家个人的实践之中,国家的政治标准与个人的艺术标准并不总是彼此呼应。在当时,人们所推崇和讨论的现实主义主要还是指苏式的现实主义,这种压倒一切的艺术取向给董希文,与他同龄的一代人,甚至上几代那些在法国、日本等其他国家接受艺术教育的实践者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力。在一篇1958年刊登于《美术研究》的《我的检查》中,董希文反省了自己在创作问题上的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以及在美术观点上强调风格、个性与感情的问题。他写道,“我对于欧洲的近代绘画如印象派、后期印象派,虽然口头上也在批判,但当我见到那些原作时,我情感上就激起了一种不可自制的兴奋。‘双反运动开始时……就突然又看到自己在十多年以前曾走过的资产阶级的艺术道路,它至今仍在继续。在思想性与形象性的关系上,在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上,我以强调所谓造型上的感染力来冲淡前者在政治上的首要性。这种至今还相当浓厚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显然的是与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造道路背道而驰的。”
到了50年代中期,他的绘画手法比起50年代中期大批从苏联学成回国的艺术家的绘画手法和塑形效果已经不大符合时代的需求了。在这种氛围中,当教师的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并没有受到重用,董希文的社会主义美学诉求也面临了挑战,而他所提倡的“油画民族化”诉求虽然传播广泛,实则被当时民族主义的氛围裹携着。各种不同的压力和因素促使他不得不压抑他对于当时已经处于潜流的浪漫主义之后的现实主义的思考和看法。在这种情形下,他得到文化部资助,和一些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一起去重走长征路,去体验生活。他在西藏和西北农村沿途所见的绘画呈现了他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这组画中,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来,他多次去乡下写生,画了大量的风景和人物画,这些作品实际上只是写生,并不是创作。作为一位艺术家,董希文在经历了事业的高峰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寻自己的位置,将自己的能量和思考投入到这样的创作经历之中。以乡土风景和农民为题材的绘画在美院系统中自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至今是艺术家们往往会主动选择的题材。八十年代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艺术家们非常看重自我放逐和将自己投入到一个不同的环境中,几乎大多数在1985年前后参与过“新潮”运动的艺术家们都曾经到过农村写生,画过大量的风景画。
已故的历史学家高华写道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叙述是从莫斯科和日本传来的。阶级斗争的叙述强调关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侵略以及中国人对此的痛苦记忆,同时又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远景,在理论上,它叫“共产主义”,在现实,它就是“苏联”,在左翼十年(1927——1937),基本如此。在30年代初之后,左翼又增加了一个有号召力的旗帜:“抗日救亡”,把民族主义的元素融入左翼革命的叙述之中,从此,左翼占据了两个道德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民主义。1949年前,中国的左翼文化长期占据中国思想意识很大的空间,就是由于占据了这两个道德制高点。 5中国还有自己的背景——“文以载道”的传统,利用文学改造社会的传统。20世纪初就有这样一种利用文学艺术介入社会改革、参与社会改革的潮流。1927—1937年是中国“红色的三十年代”,是以文学、艺术介入社会、介入社会改革的10年,不少文学家和艺术家更是直接投入到社会革命。20世纪50年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新国家在建国初期通过不同层面、方式和路径的操作和行动,“依着某些重大理论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 6实现它对全社会的“统合”,形成在理论表述和认识上的高度一体化。在这个阶段,以“阶级论”为思想背景的政治运动推动了一个新的超强的政治结构的形成,并构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叙述、统一了社会的意识和共同的价值观。这种意识形态叙述在政治上结合了中国传统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使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在文艺方面,民族主义的精神如此强烈,以至于无论何种立场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仍然向往于国家。现当代中国艺术的实践与成果,是在接受现存的社会秩序和中央政权的这种“框架”中产生的,并未能就政治权力的本原异己与之相关的权力合法性根基的问题。这个超强的社会政治和意识结构成为了所有在中国开展的艺术实践的前提和基础。
把董希文的工作单独隔离为政治上的董希文来观看或者只是把董希文单独隔离为艺术上的董希文来进行评判;把当代艺术独立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外来赋予其合法性,以及就当代艺术而谈当代艺术,两者都是在遮蔽历史进程之中个体与创作所同时面临的内外力的冲击。在这个进程之中,我们每个人和每一种创作或者思考上所出现的可能性都同时承受着来自内部的欲望和外界语境的影响的勾兑。试图更充分和深入地去洞察研究和论述对象所处于的历史情境才有可能不以判定是非、得出某种确切的结论或划清界线作为关切的焦点,才有可能在我们的认识和理解中表现能让事件栩栩如生的情感与思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