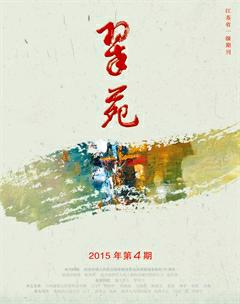铺深墨绿色丝绒布的会议桌
那天我到外单位开一个时间很长的会,因为是代人顶班,便有种与己无关的感觉。又实在是因为会议太冗长无聊,我注意起与会者们面前的这些会议桌来。
桌子摆成了正四方形,众人围桌而坐。但我们围着的,其实只是一大块深墨绿色的丝绒布而已。因为,桌子被丝绒桌布完全地覆盖住了,就像一个长裙曳地的古代妇人一样,连桌子腿也没有露出一点。
这是多么大的一块布啊!触目所及之处,都是深深的墨绿色。这种平日里很容易就被我忽略的颜色,在灯光下看来就像千年老潭深处的那种苔绿,仿佛有无数时光凝结其上,无比地滑、老、厚、灵。
它非常深,深到几乎暗黑。
但它又焕发出光芒!那光芒并不刺目,它幽微,但从不消失。
它衬托一切颜色,但它自身也并不泯灭个性,并不丧失自我。
这是一种决不压倒别人,又决不被别人压倒的颜色。
现在,这罕见的深墨绿配上丝绒这样一种高贵的质地,成为一块桌布,平铺在所有与会者们面前。
桌布上面,摆着笔记本、矿泉水以及高档白瓷杯——仿佛老池塘上安静浮游着的一群鸭子,那些白色的杯子与深深的墨绿成为绝配。
还有一张张写有名字的粉红色小卡片。每个人坐在自己的名字后面,似他自己,又不是完全的他自己。
最重要人物的面前,还摆着一个做成了造型的花篮。
这就是一张会议桌上的全部内容。
厅长、处长、科长都坐在桌子前。他们面上神情庄严、正经,有的手指轻叩桌面,仿佛在沉吟;有的胳膊肘撑在桌子上面,学生听课般认真安静。但他们的腿在丝绒布的遮覆下,正安装了一个小马达般,踌躇满志地轻微抖动。
也就是说,凭借一块桌布,他分为两截。但凭借同一块桌布,他的两截又浑然一体,打成一片。
在我看来,他们和这张高贵的桌子完全地相得益彰了,甚至其乐融融。如果没有这样的桌子,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会议如何进行得下去。
这时,一个女人提着水壶走了进来。我来这里开会的时候,见到她在扫地。现在她脱掉了袖套,放下了扫把,显得要整洁、利落一些了。显然,是会议组织者们临时给这个女人加派了倒水的活。
她给所有的人倒了一圈水,然后,她来到了最靠边的桌子一角。她打算歇一会再接着给人们续水。要知道,在这样的场合,人人都有话要说,人人都觉得自己要表达的是最重要的。以至于人人讲到口干舌燥是极为正常的事。这样,一个倒水的人,在这样的场合,又是多么地必备。
我看见那女人极慢地坐下来,慢得仿佛经过极艰难的选择才确定下来一样。我知道她这样干活泼辣的女人平日决不是这样坐法的,她肯定是俗语说的那样,一屁股坐下去,又一屁股站起来的人。
她的手明显不知道怎么放,最后只好搭在自己腿上。她的身体并不像我们一样正对着桌子,而是侧向的,与桌子形成一个四十五度角。仿佛她与这张桌子刚刚口角过,或是赌了一点小气。那姿势里有着别扭、不得劲以及随时要离开的冲动。
其实不光是与这桌子,她整个人,她的衣着、气质,与这整个会场,都有一种“隔”,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和谐。以至她一走进来,有种一群相同的动物里,来了另外一种动物的感觉。
显然,这一切都透露出一种端倪:她与这张桌子、这个会场,“质”是不同的,因而根本没有磨合成功的可能性。
有的人与桌子相得益彰,有的人却无所适从——看来,人们与桌子的关系,是多么重要啊!如果找不到一张合适的桌子,人就会像这个女人坐在深墨绿丝绒桌布后面一样,坐立不安。他甚至无法建立起正常的生活,仿佛世上只有一张桌子,才是他安身立命之基……
我想起我搬家时,因为懒得把旧家具带走,我连书桌也留在了老屋里,留给父母使用。
等到了新家,我们去家具市场里很随意地,就购买到了自己满意的新餐桌、新床,以及新书架。
但是搜寻无数,我找不到自己需要的那一种书桌。
你要找什么样的书桌呢?每回家具销售员无比热心地追问我时,已经看花了眼的我都语塞。
我不能够告诉他,我在老房子里使用的那张书桌是张怎样的老桌子。它两次易主,掉漆、大、方正、木质,连墨水汁也已经渗到桌子的纹路里,彻底去不掉了。而且那张凌乱之桌,上面什么都有,连小字条都有十几张之多……
——只有在那样的一张书桌上,我才可以正常且畅快地写字、思索。
家具市场里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桌子呢?
后来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姐听到我在四处寻找一张奇怪的书桌而不得。于是她把我领到她正出租给两个大学生的房屋里,那里有一张免费提供给房客使用的旧桌子。我姐告诉我,她心里早就打算好,只要随便哪任房客嫌桌子碍事,她随时会把桌子拖到楼下垃圾场去丢弃。
但是我一看到桌子,就扑了上去。它符合我所有关于书桌的条件。
我知道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桌子。我总是坐到这桌子后面,写字、思索。哪怕什么也不做,也感到心情舒畅,仿佛这桌子已成我身体的一部分,有它也不觉得多了什么。但是没有它,却是万万不行。
桌子就是这样一件家具。你可以称它为一件家具,但是它更可能是你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看过无数形形色色的桌子:凌乱不堪的书桌、灯光晕染下的温暖的饭桌、聊以打发活着的时光的麻将牌桌、气派无比却又空洞无比的老板桌,以及眼前这一张铺了深墨绿丝绒桌布的会议桌……
在这些桌子后面,不同地位身份、不同情趣爱好、不同年龄性别的人们各自如鱼得水,彻底成为他自己。他们在这些桌子前的表现,甚至比在床上、沙发上还要放松。仿佛这张与众不同的桌子,把他与别人区别了开来。
无疑,与自己相配相衬的桌子,这世上,每个人都有一张。
此刻,我设想着会场里的这女人该坐在哪一种桌子的后面才够自在优游。那肯定是一张平民之桌。上面会铺麻布吗?不,那太带着小资情调了;一块塑料布吗?廉价倒是真的,但是不一会就要叫剪刀、水果刀什么的戳破了。不,那一张平民之桌上,应该是什么也不铺的!她节俭的生活,必定配着一张什么桌布也不铺的节俭的桌。那桌子斑驳、油垢,上面有孩子或老人的口水、男人的烟灰或酒瓶盖,甚至可能还有母亲的泪水……
但是这女人坐在这样一张桌子后面,一定是和她坐在深墨绿丝绒桌布后面,完全不一样的状态的。你甚至会以为那是两个不相干的人。
在那样的桌子后面,她会像个女王一样决策家中事物,她也会是管家一样给家人添饭加菜,她还会悄悄地瞒着孩子们,在桌子底下把自己的腿搭在丈夫的腿上……一家人在她周围,也像开会一样地各就各位。但是她成为核心人物。
总之,在那样一张桌子后面,她显得很正确。用一句哲学的话来说,她找到了自我。
鱼 迹
1
我在桥上走着。三月天的大风,把这一整座桥的桥面刮得干干净净,灰白雅致得就像电影里适合谈恋爱的桥。正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桥上人迹稀少,这使我有闲心四处张望,欣赏桥与岸的风景。
然而,我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在脚下,桥面的地砖上,稀稀落落散布着一片片暗红的斑迹。那斑迹深深浅浅——浅的是旧痕,已开始变淡与发白,再过些日子,也许就与桥砖的本色融为一体,再也辨认不出来。而深的,是还很浓重的暗红,有点触目惊心地显现在那里。
人行道两旁布满了这样的斑迹,连日的雨水也没有冲刷走它们。显然那不是一日两日留下的。
起初我并不确定这是血。我只是疑惑,这像血一样的斑迹,是什么东西留下的呢?
2
我又于桥的旮旯和桥岸背阴的地方,也就是一些不起眼处,搜寻到了另一些触目惊心的斑迹。
那是一片片像人的手指甲盖一样薄的物质,它们凌乱无比,毫无秩序地,一片片粘在地上。那颜色是暗灰白的,大多已经风干了,因此微微地卷曲了起来。
满地都是。总有几百片吧。有的嵌进泥里,有的只剩了半片。也有的,竟叠在了一起。
——就像有一个谁,把许多人的许多手指甲盖粗暴地撬了下来,然后又粗暴地撒在这里!
虽然没有人注意到此,但是在习惯放大细节的我来看,这多么像一个犯罪现场。
——这斑迹我却是认得的。
那是一些鱼鳞!是我们从教科书或一条活鱼身上已看见无数次的、有着银色光泽的、美丽的鱼鳞。现在它们脱离了母体,与风中飘落的叶子一样,丧失了所有光彩,丧失了所有生命迹象,作为一种犯罪现场的证据,留了下来。
3
现在,把这些像血一样(其实就是血)的斑迹,把这些鱼鳞,综合在一起判断,我就知道了,这是一些鱼迹。是鱼留下的、它们身体的某些部分。
我们无聊时会剪自己的指甲,我们的头发偶尔会被物体勾挂下来,我们咽喉不适会自然而然地吐一口痰。
——也就是说,作为人,我们会随时遗弃下自己这些几乎多余的身体部分,制造这些最微不足道的人迹。
但是鱼鳞和鱼血不是鱼身体的微不足道的部分。鱼只有负伤或死去才会见血,鱼只有被撕扯才会掉落美丽的鳞片。
桥下的河,流了无数年。河下的鱼,游了无数年。鱼不会自杀,鱼也没有到自相残杀的地步。这些鱼迹,自然不是鱼们自己干的。
4
我开始认认真真观察这座桥。每天两个、四个甚至更多的来回,使我自以为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座桥。但是如此细腻的、侦探一般的观察,才刚刚开始。
除了一天来一趟的城市清洁工、除了像我一样来回于这座桥的行人、车辆,除了在桥边偶尔以河水洗脸、以石凳当床的流浪汉……还有谁呢?
眼前突然浮现出一群又一群人,这些我熟悉却一直没有特别注意的人。他们多半头戴鸭舌帽,总是挂着个篓子的自行车停靠在身边,嘴边多半有烟斜斜叼着,他们自己也像那烟一样,悠闲悬挂在桥边。
他们像鱼一样群聚在这里,有时是这几个,有时是那几个,往往也有交叉出现。总之他们是松散,但又按照某种规律组合在一起的一群。
他们身上散布着一些特别的味道,细细闻去,会发现那是一股原本属于鱼的味道,那样一股细细的腥气,藏在他们衣服的褶皱里。偶尔他们喷出的烟雾里,也夹带了一些。
他们来到桥边,第一件事总是从桥栏空隙伸出长长的竿子,顶端垂着无比长的线,线头直落进流淌的水面,那从天而降的线头上,正绑着诱惑他们的饵(在看不见的水下,鱼们正悠闲嬉戏。他们却不知道,危险已经逼近)。
然后他们才开始得闲,互相打招呼,他们总是这样对话的:
老王,今天钓几条了?
一条也无。白守一上午。你呢?
今天运气也不行。嘿,你不知道,昨天老子中了彩,钓到两条大的,一条起码二十斤,一起给那个“小南方”老板收去了……
啧啧,他馆子里昨天生意肯定好,现在喜欢吃鱼的多……
他们就这样偶尔谈着“鱼经”,更多的时候,他们只专注于水面。只有当顽劣的小男孩向水面投掷石子,才可以惊起他们的头颅。
他们的专注,和半蹲于起跑线上的短跑运动员无二。只不过一个等待的,是刺动心脏的发令枪响声;另一个等待的,则是激动人心的鱼竿的微微颤动。
钓鱼客!
长期固定于桥上或桥边,几乎成为这桥的一部分的,就只有这帮钓鱼人了。
那鱼迹,准是这帮人弄下的。
5
除了钓鱼客,另外常出现的,是那些对话里出现过的餐馆小老板。
他们陪在钓鱼客身边,议论着,指点着,仿佛是运动场上的看客。要是没有他们,这场景真不知要冷清多少。
一条大鱼上来了,钓鱼客兴奋地收竿,把鱼放在地上。鱼不停地、竭力地跳跃着,却于事无补。
“看客”判断着鱼的重量以及品种。开口了:
鲤鱼。这条给我。多少钱?
于是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拍板成交。
我以为小老板把鱼带走,带到他们肮脏的餐桌上,以为钓鱼客即将重新开始新一轮垂钓,这一轮就这样完事了。
但是远远没有结束。我甚至可以说,对于鱼们来说,对于我这样的观察者来说,一出大戏中最惨烈的一幕才刚刚开始——
原来鱼们早已经感应到了巨大的危机,自从被钓上岸,一直在奋力摆动。他们全身滑滑的,钓鱼者与小老板感觉怎么也抓不牢这活物。
于是他们气了:鱼,你都被我钓着了,你都快成我餐桌的供品了。你还不服?!
只见他们用双手紧紧揪住鱼,然后用尽全力举高,再重重地摔向地面。几个动作都在一瞬间完成,就像那开山工,摔一块石头;就像那下棋输了,棋风太差的人在摔一盘棋。
鱼,被如此无情的命运之手,狠狠地摔向地面——它前几分钟还在河里游走、与水相依相逐,此刻,它称得上幸福的生活就被无情虢夺。
一下是摔不死的。
于是两下、三下、十下……
钓鱼客和小老板,轮流摔着鱼,他们还比试谁摔得更狠,更具杀伤力一些;他们还边为自己的行为配着音:“耶荷,还不死啊!”
屠杀,就这样做成了一项游戏。
鱼血一滴滴出来了,鱼鳞纷纷跌落,鱼的腮,可怕地鼓动着,鱼的躯体,弯成了U形——和我们在杨柳青年画上看见的“鲤鱼跃龙门”的姿势是多么一样啊!二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向死的挣扎,后者则是兴奋地起跳。
最后,鱼的鳍无力地摆了两下,嘴无力地张了两下。它死了。
它所遭受的惩罚,会比二战时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遭受的刑罚更轻、更柔和一些吗?
我所目睹的人的残忍,会比任何一种动物的厮杀更为文明些么?
鱼们永远无法喊疼,但是,我听见了一万句它疼痛的呼救。
6
此后,每日从这桥上走过,短短几百米,我总要把脚步放得更轻。
在那越来越暗的血红色下,在那一片片已风干,随时会被风不知带向何方的鱼鳞下,有着一颗颗鱼魂。它们用这些身体的残留,自己悼念自己。
我惟恐惊动了这些屈死的鱼魂。纵然它们有着成为人类餐桌上的食物的命运,这些美丽的生灵,也不应遭受那样残忍的凌迟。
纵然人类可以创造种种游戏,运动娱乐自己,却不可以以此激发或释放自身更多的残忍心,为自己增添新的罪名。
痴立于这些鱼迹前,我大恸。
作者简介:
王晓莉,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江西省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创作评谭》杂志主编。出版有个人散文集《双鱼》《红尘笔记》,八人合集《怀揣植物的人》《当代先锋散文十家》。作品入选《21世纪散文典藏2000—2010》《21世纪2005年度散文选》《21世纪2006年度散文选》《2006中国散文年选》《新世纪散文选》《散文2007精选集》《散文2009精选集》等多种国家级选本。两次获江西省谷雨文学奖。作品《暗房》获《散文选刊》“2014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