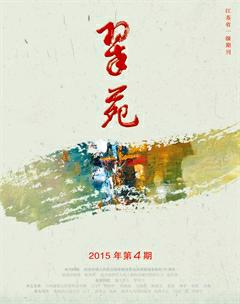旧话二题
1966年的晚报
打扫卫生的时候,翻出两份压箱底的《上海晚报》,是1966年9月份的报纸,距今已将近50年了。半个世纪,虽然于“历史长河”算不了什么,但手捧这两张多处开裂,既黄且脆,并已失去水分的报纸,再读一读报上的满纸文字,仍不免生出天悬地隔、遥不可及的陌生感。
与时下的晚报相比,这两份报纸的最大“特色”,是表决心一类的政治语言过多过滥,简直无孔不入了。试举两例:
在各书店里,人们不时欢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革命歌曲,来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
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都是红五类的子弟,都是红卫兵,……请您放心,我们一定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红色小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文学作品里,作为笑谈的“文革语言”,在这两份晚报上得到了充分淋漓的发挥。
《上海晚报》的前身是《新民晚报》,但这只能算是《上海晚报》的自说自话。该报创刊于1966年8月,创刊时曾在“本报启事”中留言:“本报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建议,自今日起将《新民晚报》改名为《上海晚报》。”然而《新民晚报》并不领这份情,或者说并不买这个账。我们知道,《新民晚报》很早就创刊了,它的前身叫《新民报》,创刊于1929年,报名是孙中山先生书法的集字。细说起来,它的创刊地还在我们南京。到1958年,《新民报》才改名为《新民晚报》。但到了1966年8月,该报被迫停刊,报社一干人等还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到1982年1月复刊的时候,为了与《上海晚报》划清界限,《新民晚报》延续了当初停刊时的第7256号,新出的一期报纸,直接沿为第7257号。
但凡报纸,都该有个主管或主办单位。然而搜遍《上海晚报》的边角旮旯,只在中缝的最下边留下这样几行字:“今日4版,零售每份2分,地址:上海市”,再就是一个电话号码,一个电报挂号的号码。这份没有出版机构的报纸,伟大领袖的照片却异常地醒目。据说这报纸是当年造反派办的,但从报中,却找不到造反派机构的一点儿痕迹,不知何故,甚为可疑。
讲起来,晚报和日报应该是有区别的。比之于日报,晚报集知识、娱乐于一体,应该更为活泼、更加生动。然而这四开四版的《上海晚报》,虽然也有诗文、有照片,还有插图,可以说是图文并茂了,但读来却完全是另一番滋味,只能给人留下一种苍白单调、千篇一律的印象。个中原因本来是无须解释的,倒是其中有一篇批判周扬的文章,自圆了读者的这种感觉。文章是这样写的:
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借反对我们工农兵写文章“千篇一律”为名,妄想不让我们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我们警告周扬:“千篇一律”是我们亿万人民的革命心愿,我们就是要“千篇一律”地歌颂党、歌颂毛主席;“千篇一律”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们要用“千篇一律”的语言来斗倒、斗垮、斗臭周扬这个文艺界黑线的“祖师爷”,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瞧瞧,是什么话呀?简直不跟你讲理了!
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运动,从这两张不像晚报的晚报上透出了一斑。50年前人们的狂热、盲目,以现在人的眼光看,或许是一种滑稽,一场悲剧。然而那时的人们却那样生活着,真真实实地生活在狂热、盲目里。
如何还历史于本来面目?电影也罢,回忆录也罢,最切合历史的,恐怕还是要属报纸为第一。
1969年的防空洞
1969年,至少有三件事情在长江下游地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南京长江大桥顺利通车,还有一件,就是全民深挖防空洞。前两个事件,直到今天人们都记忆犹新;后一个事件,现如今的年轻人,恐怕知之者甚少。
在当年,“深挖洞”可是家家户户都要参与的大事啊!当时没有电视,报纸也少,小道消息也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泛滥,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广播。收音机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通过广播,我们了解到上面的政策,其实说“号召”更为妥贴。那时候,我们大抵生活在政治号召的旗帜下,没有娱乐。懵懂中似乎也有奔头,台湾等着我们去解放,美帝国主义等着我们的红缨枪去打垮。
通过广播,我们闻听到一条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虽然另一条与之配套的口号“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是在三年后才提出来的,但在1969年,全国已经开始了大范围的“深挖洞”。那是感性的、生动的,看得见,摸得着,大家都能积极参与。那年我还小,五六岁。上面来了号召,说要备战,于是大家都备战。其实上层的空气已十分紧张,中苏边境军事冲突不断,毛主席明确指出,要准备打仗。但我们是普通居民,缺乏战争到来前的紧迫感,只觉得有意思。每家每户都要制造“战备砖”,于是家家铺开场面,生产砖头。
我家制砖的模具是我哥哥动手自做的,那时候他的岁数也不大,十三四岁,但木制模具做得有模有样。两个横档,两个直档,四个接头一卡,就把中间的填充物固定成一个长方形的“砖块”了。我哥还喜欢画画、写美术字,在模具内侧刻上两个反写的“备战”,是新魏体的。制成砖,两个字就正过来了。那两个字的姿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战”字最后那一勾,把新魏体的笔法全都活脱地表现出来。所以,我家制造的砖块与别人家的不同,因为有了凸显于外的两个字,立体感很强,颇具美感。
模具中的材料,是江沙和黄泥。浦口镇紧挨长江,江沙取之不尽。那江沙细细的,呈银灰色,在江边的断岸沙滩上,绵延数里,随处可取。至于和泥、制砖的过程,我已记忆不深。只记得有一次,在露天水泥地上垫了旧报纸,把模具放上去,将和好的江沙、黄泥填入,按压结实,我哥就拿一截长木条,沿着模具的上沿平扫过去,把上面多余的沙泥剔除干净,然后小心地拆下模具,一块砖头就出世了,并直接在太阳底下得到晾晒。
这些未经烧制的砖头是否被“上级”拿去建了防空洞,我无从知晓。但我想应该是拿去了。因为接下来,我们听到一些不妙的消息,说荷花塘旁边那条小路上,正在挖着的防空洞突然塌陷,有人被埋在里面,死了。害得我们多少天也不敢走那条路。若干年后,我将我们制造的砖块与防空洞倒塌事件联系起来,就觉得联系得有理。那些砖从未进过砖窑,从未经由烧制,到底能有多大作用?拿它们来加固防空洞,垮塌的可能性占百分之多少?
修建地下人防工事,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1969年,进度明显加快。一些省份要求城镇居民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防空位子,而在一些公社,村道口、大路旁,到处挖满了战壕、坑道和单人掩体,房屋的墙上也备有枪眼,不禁使我想到了电影《地道战》。抗战时期的地道,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以人防工事的名目,大范围地展现在我们的视觉里。
那时的防空洞,虽然在我们周围建造得热火朝天,我还真是难得进去一回。记忆中只有一次,是在之后的1973年,郊区汽车站与轮渡码头、浦口火车站紧挨着,汽车站中间一圈围墙,就是个防空洞。公交车从防空洞的一侧进站,从另一侧出站,所以那防空洞也成了汽车站的一部分。但那时的防空洞在我们眼里太神秘了,那是一个方方正正的砖墙院,里面堆起一座坟似的小山。对开的院门常年关闭,但小孩可以钻进去,里面还有一道门,是防空洞的门,斜倚着,差不多要败落了。两道门都落满了灰土,使人对其中的阴冷和恐怖浮想联翩。终于找到机会,和两个大孩子进去,果然一片阴湿,有怪异的冷风。其实什么也看不见,点着“洋火”,火光如豆,讲话的时候有回音,自己都把自己吓住了。也就往前走了七八米,再不敢深入,赶紧回逃。逃到外面,阳光却是一片灿烂。
前不久,有幸参观了某地的人防工程,并且看录像,听人防办主任作情况介绍。走进人防工程,才觉到,如今的人防工程体系与我当年所见到的防空洞大相径庭,不是狭巷窄道,而是现代化的地下停车场。宽阔的甬道,规模浩大的隐蔽所,一流的设施。这盛大的规模,真要是遇到空袭,地面上除却武装的防御者,还用得着留人吗?
回来以后便想写篇文章,很自然地想到了1969年。于是就想,当我们在那个全民“深挖洞”的年代挖下那么多防空洞的时候,我们是否想到了一个词,叫“政治神经质”?战备是必需的,但战备应该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稳固的、理性的发展过程。看看四十多年后的今天,看看今天的人防工程,我们就知道“平时可利用,战时能防空”的真实含义了。
作者简介:
李敬宇,供职于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作协重点扶持项目签约作者,南京市文联签约作家。在《钟山》发表长篇小说《沉沙》,在《中国作家》《花城》《清明》《长城》《北京文学》《十月》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100余部(篇),共170余万字。有中、短篇被《小说选刊》等转载,有作品入选《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