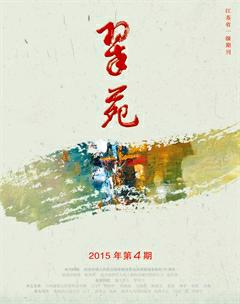我与《古文观止》
是谁背着行囊汲汲于道,推开一间又一间特色书店的门?是谁挟着风尘游目书林,追寻着形形色色的冷摊书肆?——徐雁
喜欢书,至少四十年了。那时候不是为了藏书,只是因为小小的一本书,里面有浩瀚的内容,太神奇了,所以要留住它。
1975年冬天,我插队住在永宁公社一户老乡家,发现铺着稻草的床头有一本很厚的竖版书,无封无底,我吃力地看下去,是《红楼梦》。那个冬天,我整天窝在屋里,也只有看这本书。临走时,老乡把这本书送给了我。这是我收藏的第一本书。
1978年以后,书店里逐渐有了“小说”,我一本一本地买,包括世界名著。1980年,有朋友送我一本1948年香港版的《围城》,朋友说这书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当时大陆还没有《围城》出版,我从严肃的世界名著里走出来,从未见过书还可以这么写。再后来,又读戴厚英的文革小说《人啊!人》,读美国的黑色幽默《第二十二条军规》,读台湾浪漫诗人郑愁予的《郑愁予诗选》……
读书的过程也是买书的过程,常常揣着微薄的工资徘徊在书店,盘算着用于买书的钱。我不喜欢到图书馆借书,不喜欢读书时间被人为地约束住。重要的是还得在书上写呀划呀,留下自己的痕迹。书对于我很重要,不仅书的内容,还有书的形式。凭借着书的信息,可以培养我对往昔的回忆,对生活的回想和回味。这于我,已经成为一个情结。
从文学类到艺术类,后来到收藏类,喜欢买书的过程,也成了收藏书的过程。
2002年2月,我在江浦一地摊上买了一本《周与嗣千家诗》,两块钱一本。拿回家细看,发现是“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出版”。我很惊讶,这可是民国版的书啊,我还没有一本民国老书呢!让我惊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丝毫没有怀疑这本书的真伪,全然没有收藏瓷呀、玉呀那种真假难辨的困惑。这本竖版《周与嗣千家诗》,无论封面、封底,还是版权页,一页页、一字字无不充溢着浓郁的民国味。我坚信书做不了假,一是技术难度大,二是成本高,三是书的气息蒙不了真正爱书识书人的悟性。
2003年2月,大年初六,我到南京朝天宫,大院内人头攒动,古玩大市令人兴奋。在东大门我发现一本民国二十三年的《笔生花》,接着又在一堆乱纸中发现雕版书《古文观止》,这书线断了,页散了,微风中一页页飘飞。我细看书牌是丙辰年(1916年)印制,一套四册,雕版封面、封底都在。我想,书散了自己可以线装成册,于是仅用30元就悉数买下。这是我收藏的第一套《古文观止》。
上海福州路,解放前称“四马路”,即古旧书一条街。2005年11月,我和设计院的同志去上海办事,回程时我们特地去了四马路。在古旧书店的四楼,我发现一套破旧的民国六年雕版线装的《古文观止》,卖家说是残本,愿以180元低价让我,我知道破旧的书不叫“残本”,这可是一套六册全本啊。
在后来的若干年,我以十年时间为一段,收藏了民国四个十年的各种《古文观止》版本。
《古文观止》是清康熙年间浙江绍兴吴乘权(字楚材)、吴大职(字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古文读本,共十二卷,收录自秦至明末散文二百余篇。吴乘权的伯父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官至两广总督。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春天,他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右翼汉军任副都统任上,收到吴楚村、吴调侯寄来的《古文观止》后“披阅数过”,认为其选简而赅,评注详而不繁,遂于当年五月端阳日“丞命付诸梨枣”。这就是《古文观止》的最初刻本,这套最初刻本已失传。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鸿文堂增订古文观止》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映雪堂刊古文观止》均署“大司马吴留村先生鉴定,山阴吴乘权、吴大职手录”,前有吴兴祚序,但没有吴乘权、吴大职二人的自序,也没有编选例言。显然这两个版本都是根据吴兴祚康熙三十四年初版翻刻的。鸿文堂本现由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收藏,映雪堂本现藏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馆。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吴兴祚去世。一年后的仲冬,吴乘权、吴大职在浙江家乡又将《古文观止》“付诸梓人,以请教于海内君子”。这就是文富堂(尺木堂)版本。这个本子也注有“吴留村先生鉴定”,所不同的是有二吴叔侄的自序,并有吴乘权所写的例言,却没有吴兴祚的原序,不知二吴是因有自序而故意略去,还是没能见到吴兴祚刻本上的序而未收录。此本刻工粗糙,讹错较多,但亦存在前两种版本有误,此本无误的地方。篇末评语,与前两种版本略有不同,推测二吴在付梓前做了少许改动,改动处较前两本为妥贴。此本现藏于中华书局图书馆,也是现存《古文观止》最早的版本。
我藏有这套康熙三十七年尺木堂版本的第一册和第五册,缺二、三、四、六册,好在有最珍贵的第一册,封面、书牌、自序、例言俱全。第一卷就等于是全卷。因为古籍善本只要求有第一卷,并不强求全本。
版本目录界研究对象是宋元本,然而留存至今的古书却以明清为主,宋元时期的还不到百分之五。清代刻书曾不为重视,是因为贵古贱今,只认宋椠元刻。明本虽多,比清刻又要珍贵许多。但于我,更喜爱清刻之美。
2009年9月,我从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报国寺古文化市场书报馆吴庚先生处,以2200元购得一套清嘉庆六年(1801年)《三槐堂详校古文观止》。该版本品相上乘,书牌呈淡红色,横刻有“嘉庆辛酉年新鐫”,竖刻“山阴吴楚材、吴调侯同辑”、“三槐堂详校”,原装绿锦函套,吴留村原序为软体字,字体灵动漂亮,半页七行十三字,主文是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单边、白口、开化纸、单鱼尾,一套六册全。是我目前拥有《古文观止》最早、最全的版本。
此后,我又从河北石家庄《藏书报》旧书部以1600元购得咸丰三年(1853年)《古文观止》雕版线装(残本),该书字大如钱,墨黑如漆,规整的宋体字赏心悦目。又从苏州市金闾区仁安公寓一户人家,以700元购得清同治丁卯年(1867年)一套六册全《古文观止》,该书书牌呈黄色,署“姑苏小酉山房梓”,吴留村原序。又从安徽天长石梁东路一户人家,以1300元购得光绪癸巳年(1893年)《古文观止》,文运书局藏板。此本为清地方政府书局刻官本“局本”,静雅的气息,疏朗的格局不失精美之处。
安妮宝贝有一篇叫《线装之美》的文章,其中云:“一沓一沓、一册一册小心收藏的古老书籍,如果轻轻从其中抽出一部,就能亲眼看到古代制作的书,墨与纸之天然,版面之细腻,书法之精妙,装帧工艺之清丽考究。”
从2002年至今十余年,我从地摊、书店、拍卖会、网上及全国各地搜求《古文观止》各种版本,最早的从1698年清康熙开始,有嘉庆版、同治版、光绪版、民国版、康德版若干;有雕版、活字版、石印版、铅印平装版若干;亦有英文版、韩文版、现代电脑版、彩绘版若干,前后相距300多年。有人说我的《古文观止》专题收藏最早、最全、最多,可称中华第一人。而这其中的负累,只我一人知道,我自知冷暖。这就是人生真味,不可复述。
拥有《古文观止》收藏,沉浸在故纸犹香里,可以感觉收藏的真正内涵,感觉历史的厚重感和丰富的文化信息,不以金银、玉帛等材质优越取得铜佃价值,而是以脆黄的老纸取得文字价值。捧在手上,看在眼里,这些古籍,历经数百年的水、火、兵、虫四厄,依然一页页飘飘洒洒,无不承载古代贤人的智慧。雕版的凿痕,油墨的清香,完好无忧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房里,享受着我的珍藏。我守护着它们,为它们登记造册,为它们裹以黄绸,装以木匣,藏于书柜。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逝水悠悠,这么些年来,《古文观止》的各种版本成为我的至爱。坐在书房里,慢慢静下来,再静下来,能闻到空气中一股股幽幽扑鼻的气息——清幽、鲜活、沉凝的“书香”。书香只能来自古籍,来自久远前的墨,来自古纸在岁月沉淀后与书柜壁板樟木芳香的融汇。藏书使我能够享受缓慢的时间,虽然有缺,也是光华。
我每晚坐在桌前,喝茶、抽烟、听音乐、展纸研墨,画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古文观止》在我的身旁。我为书房取名“观止楼”,意即有此精神享受人生足矣。神话中天帝藏书的地方叫“嫏嬛”,常被用做藏书楼的美称。古人说“有福读书”,我即视我的“观止楼”为嫏嬛福地。
作者简介:
甄浦鸣,祖籍江苏淮阴,1958年8月生于南京江浦,1975年9月插队农村,1987年9月毕业南京大学法律系,1988年从事职业律师,现在江苏三宝律师事务所工作。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在《老山》《藏书报》等报刊发表多篇散文。